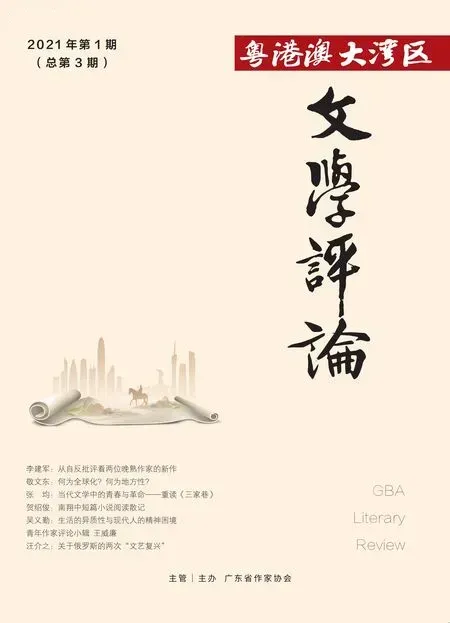何为全球化?何为地方性?
——以吉狄马加的《迟到的挽歌》为中心
敬文东
民族性
作为诺苏彝人(彝语意为“黑色的部族”)的后裔,吉狄马加早在他的大学时期,就有十分自觉的民族意识:“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吉狄马加:《自画像》);而从创作谱系上说,20 世纪80年代早期令吉狄马加名满天下的那批作品,至少受到过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影响。前者有《黑人谈河流》,后者有《彝人谈火》。即使不做比较文化学方面的研究,也很容易得知:所有有意义的影响都不可能是狼吞虎咽的,都无不源于被影响者的主动追求;被影响者从心灵营养学的层面将影响者拉向自身,再经过复杂的内心转换、心灵转折或曰内心的生化反应,影响者才能够以营养身份——而非影响者本身的模样——供养被影响者。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结成的关系,更像是食物和食物享用者之间构成的关系。享用者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食物的营养能力就越劲道;影响者的效用,反倒是取决于被影响者。一个人在下午三点对准某个目标猛击一拳,但这个人别指望自己能够弄清楚:这一拳需要的能量到底来自午饭时的鸡块和火腿呢,还是早餐时的牛奶与面包。因此,《彝人谈火》才显得迥乎不同于《黑人谈河流》。事实上,几十年来,吉狄马加一直在持续不断和力所能及地关注世界各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但他进行关注的出发点,却是超民族的,这是他对“世界”而不是对大凉山说“我——是——彝——人”的原因。打一开始,吉狄马加就非常清楚,如果仅仅局限于民族性,这种关注就显得毫无意义。果若如此,纯种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根本不需要黑人兰斯顿·休斯;后者的河流和前者的火原本就搭不上关系、攀不上亲戚。纯粹的民族性更有可能意味着文化的内循环;在本质上,文化内循环乃是一种反旋涡运动:最外圈的波纹在不断向最内圈逼近,最后,必将无限趋向于圆心而终止于死亡。或许,文化内循环正是被遗忘的诸多文明之所以被遗忘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乎于此,在一篇短文中,吉狄马加才颇为明确地写道:“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是哪个民族,有很多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必须共同遵从的。”[1]他的言下之意大概是:所谓民族性,更有可能是因地理环境等差异生产出的处理相同问题、主题、难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各自特殊的应对机制;但无论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有多大,各个部族都必然会为整个人类孕育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吉狄马加的上述言论意味着:这个世界自古以来都应该是、事实上都已经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世界;他大约会同意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一个小观点:普遍性必须与民族性相兼容[2]。在另一处,吉狄马加还说:“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3]梅丹里(Denis Mair)是吉狄马加的诗作的美国译者(很可能是主要的美国译者),在他眼里,吉狄马加“既是一个彝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位世界公民”,还三者兼容,“互不排斥”[4]。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时代,任何种类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5]如果只是一味地固守自身,就注定没有前途;如果不针对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发言,或者竟然无视最大公约数的世界,专注于文化的内循环,任何语种的诗篇都无异于自寻死路、自掘坟墓。有人说:“全球化的两个政治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世界和如何反思个人。”[6]与此类似,全球化的两个诗学基本问题是:诗在如何反思孤独的自我以及孤独的自我在如何面对最大公约数的世界。
孤独
孤独更有可能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能被毫不犹豫地认作陈子昂的孤独,或无可争议地据此认为陈子昂处于孤独状态[7]。现代性定义下的孤独以抑郁症等病灶为途径,吞没了太多可怜的现代人。哲学家赵汀阳对孤独有很深的理解,却也悲观透顶:“现代人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孤独不是因为双方有着根本差异而无法理解,而是因为各自的自我都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才形成了彻底的形而上的孤独。”[8]依靠彝族传统文化中至今有效的万物有灵论,吉狄马加在他的众多诗篇中找到了抵抗孤独的方法。对于万物有灵论,他有过质朴但又颇为抒情的申说:“我相信我们彝民族万物有灵的哲学思想是根植于我们的古老的历史的。我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森林和群山都充满着亲人般的敬意。在我们古老的观念意识中,人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9]《迟到的挽歌》是吉狄马加的最新作品,是献给谢世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的长诗;长诗围绕父亲的葬礼辐射开来,气象宏大、法度森严,却又灵巧和富有弹性,像旋涡运动。去世的父亲在通往祖灵的路上,除了为他送行的诸多亲人,还有太多他生前熟悉的事物与他相伴相随。那些被伟大的彝族经典所道及的物尽皆有灵,那些围绕有灵之物组建起来的事也尽皆有灵,但父亲生前自己为自己选定的火葬地点则最为有灵,那是因为——
从那里可以遥遥看到通往兹兹普乌的方向你告诉长子,酒杯总会递到缺席者的手中有多少先辈也没有活到你现在这样的年龄存在之物将收回一切,只有火焰会履行承诺加速的天体没有改变铁砧的位置,你的葬礼就在明天,那天边隐约的雷声已经告诉我们你的族人和兄弟姐妹将为你的亡魂哭喊送别。
(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
诗中被称作“兹兹普乌”的那个地方,据信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境内,是传说中彝族六个部落会盟迁徙出发的地方,是彝人子孙回望来路时应该凝目的所在,吉狄马加曾对它有过素朴的歌吟:“我看见他们从远方走来/穿过那沉沉的黑夜/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浮现在遥远的草原/他们披着月光编织的披毡/托着刚刚睡去的黑暗……”(吉狄马加:《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但被吉狄马加歌颂的那个地方,也是谢世的父亲仰望的所在、渴望奔向的目的地。在《迟到的挽歌》中,死者被有灵的事、有灵的物所包围,孤独由此被解除,死亡因此可以被视作对逝者的恩赐。虽然死亡留给亲人的是哀痛,但哀痛仅仅出于生者暂时见不到逝者,而非永不相见。死者生前最后的遗嘱是:“给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都能分到应有的食物。”(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食物当然是有灵之物,这份遗嘱因此显得大有深意,也大有分教:给帮助自己解脱孤独的人以食物作为回报,给帮助自己解脱孤独的万物以自身的躯体作为回报,这是死者摆脱孤独的彻底方式。但最彻底的方式无疑是:抵达最接近天堂的神山姆且勒赫。因为那里才“是祖灵永久供奉的地方”;唯有与祖灵在一起,才算“跨入不朽的广场”(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从而永享没有孤独的生涯,并且静等尘世间哀痛自己的亲人。
在尼采看来,“现代精神”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Nihilismus)[10]。赵汀阳则认为:“现代性的一个本质就是使一切廉价化。”[11]所谓孤独,无非是现代人彼此之间视对方为可抛弃物,或多余物[12]。但归根结底,孤独还是源于人对自身的虚无化,尤其是人对自身价值的廉价化;人对自身的廉价化和虚无化,更能鼓励人与人彼此抛弃,视无算的他者为多余物。因为这样的人原本就不值得彼此收藏和珍惜。人的自我矮化也是一桩典型的现代性事件,A.阿尔托(Antonin Artaud)坚持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不是把人变伟大了,而是把人变得更加渺小。”[13]作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著名产物,哈姆雷特则蔑视道:人“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14]?吉狄马加从其创作伊始到眼下这首《迟到的挽歌》,都一直在致力于维护人的尊严;在彝族人民的伟大经典《勒俄特依》看来,人原本就是天神之女和凡间英雄产下的后代,乃是一切有灵者中最为有灵者,绝不可以自轻自贱地将自身虚无化和廉价化。因为那样做,不仅是人对自身的矮化,更是对神灵的亵渎和冒犯;何况神灵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人自轻自贱,宛若在上帝语义中,自杀是对神的绝对冒犯。当然,自杀是对人的最彻底的矮化和虚无化。在《史诗和人》一诗中,吉狄马加似乎提前为他的英雄父亲看到了祖灵:“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我看见一扇门上有四个字:/《勒俄特依》。”
因此,作为天神的外孙的儿孙以至子子孙孙,彝人在和祖灵相偎依时,一定是温暖的、安详的和澄明的:
亡者在木架上被抬着,摇晃就像最初的摇篮
朝左侧睡弯曲的身体,仿佛还在母亲的子宫
这是最后的凯旋,你将进入那神谕者的殿堂……
(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
死亡(赶路)
古老的华夏文明只承认一个世界,不存在拯救、彼岸,唯有昙花一现、万不可逆的现世;即使是佛家的六道轮回,也不能被认作有另一个世界存在。成佛意味着超越时空,却不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试图修补现世之残缺的儒家人生目的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只限于贵族阶层)、道家的飘逸人生观、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说,还有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觉悟理论,只算得上功效有限的解毒剂。无论后来者如何将汉代对抗死亡的“神仙思想”美化为“入世”(this-worldliness)和“出世”(other-worldliness)[15],都跟来自彼岸的拯救无关。在汉族人的生命意识中,生命必然通往死亡,死亡是生命的绝对终结,灵魂是不存在的,“人死如灯灭”。《列子》说:“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列子·天瑞篇》)”。对于汉人来说,祖灵是存在的,但没有在灵界等待“行人”成为“归人”的祖先。吉狄马加很早就对祖灵和祖先做出了回应:“总会有这么一天/我的灵魂也会飞向/这片星光下的土地……/那时我彝人的头颅/将和祖先们的头颅靠在一起/用最古老的彝语/诉说对往昔的思念……/用那无形的嘴倾诉/人的善良和人的友爱……”(吉狄马加:《故乡的火葬地》)大约在三十多年前,吉狄马加在其著名的短诗《母亲们的手》的“题记”中,如是写道:“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在《迟到的挽歌》中,父亲的身体“朝左曲腿而睡”。《迟到的挽歌》很肯定地认为:“这或许是另一种生的入口/再一次回到大地的胎盘,死亡也需要赞颂。”在彝人看来,即使是死亡也必将是积极的、向上的、可以被饱飨的。在更早的一首短诗中,吉狄马加这样写道:“我了解葬礼,/我了解大山里彝人古老的葬礼。/(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吉狄马加:《黑色河流》)看起来,对彝文明持高度信任的态度,是诗人吉狄马加数十年不曾间断的日常功课。像死去的母亲还要去神灵世界纺线一样,父亲要去神灵世界与祖灵汇合,因此还需要赶路,还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走错了地方,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走。”有万物有灵论撑腰,提醒父亲不要走错路的就不仅仅是父亲自己,还有他生前熟悉的一切有灵之物,这些有灵的物、事在暗中夹道欢迎死者,耐心指引死者走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彝人的伟大典籍《指路经》保证了这一点。因此,《迟到的挽歌》才有如此饱满的诗句:“打开的偶像不会被星星照亮,/只有属于你的路,才能看见天空上时隐时现的/马鞍留下的印记。听不见的词语命令虚假的影子/在黄昏前吓唬宣示九个古彝文字母的睡眠。”
钱穆先生这样论说汉人的人生实况,并不乏令人感动的舔犊之情:“从中国人观念言,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产业亦可传百世。五口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骨肉蝉联,亦已三世。言其身生活,则血统贯注,我生即父母生,子女之生亦即我生。小生命分五口,大生命属一脉。故中国人言身,必兼及家。一家之生命,实无异我一人之生命。而祖孙三世相嬗,至少当在百年之上,或可超百五十年。”[16]但这只是唯有此岸者的生活。在汉人看来,延续父系的血缘是任何一个庶民、黔首必尽的责任和义务,但也只限于活着[17]。彝人活着为祖灵所祝福,死后则汇入祖灵而成为后人的祖灵。对祖先的崇拜让彝人相信,活着不会孤独,死后不会落寞;死不仅是生者对生命的完成,而且是迈向神灵的起点。万物在《指路经》的指引下,指引死者小心翼翼向祖灵赶去;悲伤仅仅属于暂时和死者无法相见的生者,死者则为自己终于可以去往祖灵显得平静、从容和高洁:
对还在分娩的人类
唯有对祖先的崇拜,才能让逝去的魂灵安息
虽然你穿着出行的盛装,但当你开始迅跑
那双赤脚仍然充满了野性强大的力量。
(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
米兰·昆德拉认为,一个绝对真理粉碎后,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数百个相对真理[18];叶芝则乐于这样暗示:具有向心力的中心粉碎而“四散”后,替代它的,必然是数不清的偶然和偶然性(叶芝:《基督重临》,袁可嘉译)。奥克塔维奥·帕斯说得更加绝对:人不过“时光和偶然性的玩物”而已[19]。种种迹象和悲观的言说不断表明,在现代性当家作主的日子里,在全球化吆三喝四的年月,现代人被数不清的偶然性所包围;他们深陷于偶然性,成为命运不确定、方向不确定的偶然人,死亡因此不再成为绝对自然的事件。很容易想见,在遍地偶然人的时代,非自然的死亡必然数目庞大,它往往与现代器物、现代社会的消费特性联系在一起,小小一个手机充电短路,能烧掉一栋大楼,何况肉身凡胎的偶然人;非自然死亡在数量上的暴增,在质量上的惨烈,更凸显了“死之荒谬”[20]。但被“荒谬”所定义的“死”,在更深的层面上源自遍地皆是的偶然性。吉狄马加固执地坚信:伟大的彝文明在偶然人出没的年代依然有具意义。彝文明对于生死的看法在充满因偶然性而死亡的年代,可以起到解毒剂的作用:
马鞍终于消失在词语的深处。此时我看见了他们,
那些我们没有理由遗忘的先辈和智者,其实,
他们已经成为了这片土地自由和尊严的代名词……
(吉狄马加:《火塘闪着微暗的火》)
英雄
许慎曰:“英,草荣而不实者;” “雄,鸟父也。” 有迹象表明:“英”“雄”二字连言合称为“英雄”,最早见于《黄石公三略》,在此后的汉语文献中被广泛使用。一般情况下,它指称的是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狠心之人,其中的“狠心”是关键词,与单独的“英”“雄”基本上毫无关系。顾随有言:“不动声色是‘雄’(英雄、奸雄),不著色相(才)是‘佛’。”[21]“佛”在此姑置毋论。“英雄”一词自其出现起,语义就相对稳定,它更倾向于褒义;被目为英雄者——哪怕是枭雄、奸雄——也至少令人羡慕,虽然不一定令人口服心服。在革命话语中,“英雄”一词被破天荒地赋予了新意:它特指那些为人民、为民族、为集体或国家勇于奉献,尤其是勇于和敢于牺牲的人。这些人被认为坚钢不可催其志,蛮力不可折其腰,这些人还必须“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22];春天和严冬的辩证法,则是英雄们必须熟练掌握的革命方法论。1980年代初,北岛有两句名诗迅速赢得了读者的共鸣:“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有迹象表明,自北岛以后,“英雄”一词似乎很少在新诗中出现。但在《迟到的挽歌》中,“英雄”却是关键词之一:
哦,英雄!我把你的名字隐匿于光中
你的一生将在垂直的晦暗里重现消失
那是遥远的迟缓,被打开的门的吉尔[23]
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英雄时代,这只是时间上的差别。
你的胆识和勇敢穿越了瞄准的地带
祖先的护佑一直钟情眷顾于你。
就是按照雄鹰和骏马的标准,你也是英雄
你用牙齿咬住了太阳,没有辜负灿烂的光明
你与酒神纠缠了一生……
哦,英雄!你已经被抬上了火葬地九层的松柴之上
最接近天堂的神山姆且勒赫[24]是祖灵永久供奉的地方
这是即将跨入不朽的广场……
哦,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所能命名的全部意义的英雄
你呼吸过,你存在过,你悲伤过,你战斗过,你热爱过
哦,英雄!不是别人,是你的儿子为你点燃了最后的火焰。
…………
有专家建议:可以将彝语的“英雄”一词以音译的方式在汉语中发声为“惹阔”;在用汉语写成的《迟到的挽歌》中,发声为“惹阔”者却另有语义:“惹阔”被光定义,被逝去的祖先定义,被彝人的神鹰和骏马定义,被所有正面并且光明的意义定义,也被彝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火定义,最后,被万物有灵论定义。《迟到的挽歌》为“英雄”一词赋予了古老的汉语思想和革命话语不曾拥有的语义,但又大规模地扩展了它的语义;黑格尔洋洋自得的“扬弃”(aufheben)一词用在它身上,看起来是非常合适的。这就是说,汉语中古老的“英雄”一词,被彝文明中的“惹阔”拓展了边界,让“英雄”超出了机心、谋略、国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结成的窠臼,强化了用于牺牲和敢于牺牲的价值与意义;却在更大的范围内,直接在现象学的层面上,和自然与生命连为一体,赢得了生态美学的意义。比如,吉狄马加在其诗中如是说:“我完全相信/鹰是我们的父亲。”(吉狄马加:《看不见的波动》)。
生态美学是时下被频繁提及和谈及的学术关键词。但也有学者很谨慎地提醒:生态美学似乎有生态、有美学,却没有人。这个提醒虽然善意,却很可能是一个误会。《迟到的挽歌》对汉语“英雄”一词的扩展,意味着不仅将人托付给大自然,托付给人与人之间结成的那种健康的关系,还意味着人必须成为大写的人,高贵的人,容不得人的矮化和价值的虚无化。赵汀阳无意间为此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超越个人但并不超越人的事才是高贵的。最高的存在比如自然规律或上帝高而不贵,它高于人但不属于人,因此与人的高贵无关。人尊敬与自己同等的人的行为才是高贵的。当人立意高贵地存在,就会创造生活奇迹。最大的生活奇迹就是给人幸福。幸福是来自他人心灵的高贵礼物。”[25]吉狄马加如此这般地用心于《迟到的挽歌》,也许当得起臧棣的诗句:“用了力,语言能留下的,无非是/一种高贵的疯狂。”(臧棣:《墓志铭协会》)也配得上西渡对诗歌的想象:“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但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西渡:《同舟》)
诗
可以想见,唯有颂歌和赞词,才更有理由成为世界各民族的诗歌的真正源起[26],彝族自不例外。彝族经典《六祖史》毫不含糊地说起过:“制酒盛壶中,敬献各方神。天神见酒乐,地神见酒喜,松柏见酒青,鸿雁见酒鸣,日月见酒明,天地见酒亮。”[27]吉狄马加也很说得很清楚、很恳切:“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捕捉到人类心灵中最值得感动的、一碰即碎的、最温柔的部分;”而赞颂,他说,“从来就是我的诗歌的主题。”[28]《雅》《颂》被认作汉语诗歌的源头[29],却因为人生歧路的无所不在,使得以哀悲为叹的怨刺很早就取代了赞词与颂歌,成为古代汉语诗歌的正宗,所谓“诗可以怨”。陈子龙说得最直白:“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陈忠裕全集·论诗》)”。一曲顿足拊胸的《黍离》(亦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开启了古代汉语诗歌以哀悲为叹的怨刺之旅[30]。新诗作为典型的舶来品(foreign goods),一向被认为是“有罪的成人”之诗[31]。唯其有罪(或有病),才称得上作为舶来品的新诗,因为新诗的发源地是病态的和有罪的[32]。因此之故,张枣倾向于将书写病态的鲁迅认作新诗的第一人;将满纸自虐气息的《野草》认作新诗的奠基之作[33]。事实上,鲁迅自己就曾将《野草》谓之为“地狱边沿上的惨白色小花”[34]。
和吉狄马加此前的几乎所有诗作相似,《迟到的挽歌》也是一首颂诗,它在万物有灵论的支持下,歌颂万物、神灵、英雄,视孤独为无物,视隔阂为通衢,以至于见孤独杀孤独、遇隔阂灭隔阂的境地:
那些穿着黑色服饰的女性
轮流说唱了你光辉的一生,词语的肋骨被
置入了诗歌,那是骨髓里才有的万般情愫
在这里你会相信部族的伟大,亡灵的忧伤
会变得幸福,你躺在亲情和爱编织的怀抱
每当哭诉的声音被划出伤口,看不见的血液
就会淌入空气的心脏,哦,琴弦又被折断!
(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
因为“词语的肋骨被置入了诗歌”,颂诗才拥有它自己的骨头,能笔直地挺立,也因笔直的挺立显得刚健、勇武。自有新诗以来的阴霾、忧郁和病态之气被一扫而空,但又绝不同于新诗曾经经历过的颂诗阶段所拥有的模样,后者因其容貌上的假、大、空而被抛弃,被新诗惩罚。事实上,在一个充满雾霾的时代,颂歌远比“有罪的成人”之诗更需要强大的心性;不用说,这样的心性在遍地偶然性的时代,的确缺乏信念上的支撑。因此,颂歌特别容易陷入矫情和滥情;作为偶然人的诗人们中鲜有问津者,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罪的成人”之诗极有可能是诚实之诗,但它揭示的真相太令人无助,太令人沮丧,甚至让人绝望。从心理上说,没有方向感的偶然人既需要揭示真相的诗(唯有建立在真相上的事实才更可信),更需要鼓舞士气的诗(唯有鼓舞士气的诗才更可靠),一种让人站起来却绝不矫情和滥情的诗(唯有不矫情和滥情才更可爱)。
或许,某些论者会认为《迟到的挽歌》在诗艺上有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它好像显得不那么现代,不那么洋气。这样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和古诗不同,新诗一直渴望拥有它的自我意志,这的确是新诗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拥有自我意志的新诗愿意与诗人深度合作,虚构新诗和诗人共同认可的抒情主人公,这个抒情主人公则负责对偶然人的生存境况发言。吉狄马加不可能不知道:新诗作为一种典型的汉语文体被发明出来究竟要担负何种任务;但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纯种的彝族人,吉狄马加固执地背靠本民族的伟大教义,愿意从新诗的现代性的反面进入新诗,将自己的意志变作新诗的意志,将自己更愿意礼赞世界的愿望当作新诗的愿望,由此写出了和纯粹的汉语书写者不一样的汉语新诗。要知道,对人而言,愿望从来就以幸福为核心,给予诗歌以发源地[35]。吉狄马加如此样态的写作乃是对汉语新诗做出的别样的贡献:他以自然流露出的真诚赞美,为“有罪的成人”之诗注入了新鲜的、异质的成分。
汉语需要异民族说汉语的人丰富汉语。
新诗需要异民族写作新诗的人丰富新诗。
[注释]
[1]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 页。
[2][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 页。
[3]吉狄马加:《一种声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442 页。
[4][美]梅丹理:《译者的话》,《吉狄马加的诗》,杨宗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 页。
[5]关于“地方性知识”,可参阅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大著《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的详细论述。
[6]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 页。
[7]钱穆对陈子昂的不孤独有妙解:“即如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己独酌,若觉有三人同饮,此亦太白一时之心情与意境,亦即其心德之流露。诵其诗,想见其人,斯亦即太白之不朽。又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与李太白心情意境又异。一人忽若成三人,斯即不孤寂,举世忽若只一人,其孤寂之感又如何。然在此大生命中,必有会心之人,或前在古人,或后在来者。斯则子昂之不孤寂,乃更在太白一人独酌之上矣。”见钱穆:《晚学盲言》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587 页。
[8]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3 页。
[9]吉狄马加:《寻找另一种声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371 页。
[10][德]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9 页。
[1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 页。
[12]参阅敬文东:《论垃圾》,《西部》,2015年第4 期。
[13]参阅[美]詹姆斯·米勒(James E.Miller):《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 页。
[14]参阅[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 页。
[15]此为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参阅具圣姬:《汉代人的死亡观》,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 页。
[16]钱穆:《晚学盲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5 页。
[17]《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注:“于礼不孝者三事: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中,无后为大。”何炳棣认为,这是对贵族的要求,因为贫民、庶人本来无祀,只有到贵族体制崩解后,此种观念才下替民间。参阅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4 页。
[18][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 页。
[19][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双重火焰——爱与欲》,蒋显璟,真漫亚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 页。
[20]钟鸣:《涂鸦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 页。
[21]顾随:《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前揭,第33 页。
[22]雷锋:《雷锋日记》(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15 页。
[23]《迟到的挽歌》自注:“吉尔:彝语中的护身符,在凉山彝族不同的家族中都有自己的吉尔。”
[24]《迟到的挽歌》自注:“姆且勒赫:凉山彝族聚居区布拖县境内的一座神山。”
[25]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 页。
[26][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4-213 页;[波斯]昂苏尔·玛阿里:《卡布斯教诲录》,张晖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4-147 页。
[27]《六祖史》,转引自朱琚元:《言近旨远的哲理诗篇——论彝文古籍〈训迪篇〉》,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彝文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 页。
[28]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389 页。
[2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9 页;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4 页。
[30]李敬泽:《〈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十月》,2020年第2 期。
[31][美]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语,参阅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 页。
[32][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 页。
[33]张枣:《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 页。
[34]鲁迅:《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 页。
[35]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