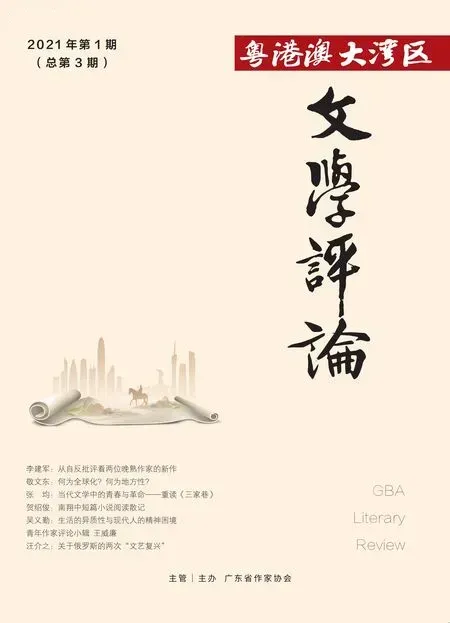“苏州想象”地域书写的现状与未来
房 伟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的这首《送人游吴》,经常被概括为苏州风貌的特点,小桥流水,水巷明月,渔歌唱晚,还有艳丽的绮罗和好吃的菱藕。还有一首诗,就是著名的《枫桥夜泊》,则进一步写出了苏州夜晚的静谧温柔。千百年来,富庶的江南之地,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梅雨季的湿润黏稠,暧昧多情,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貌,进而和文化风气遇合,出现了唐寅、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一系列优秀的古代文学家和评论家。叶圣陶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代文学领域,从陆文夫开始,范小青,苏童,到叶弥,朱文颖,戴来,荆歌,王啸峰,苏州优秀作家层出不穷,不仅在江苏,而且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么,要怎样认识“苏州想象”在中国当代小说地理版图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呢?
“世情”是理解苏州当代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水乡相对富足的生活,都市文化的发达,对经济生活和个人价值的肯定,使得很多苏州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俗世的欢乐,对世俗生活的热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个体的普通人的价值的弘扬。由此,苏州才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家,和金圣叹这样充满艺术叛逆气息的才子。大部分苏州作家,天然地对“宏大叙事”有着警惕性,愿意保持一定距离,并接续《红楼梦》一派写“世情”的小说路子。晚清以来,大量苏州籍才子,来到十里洋场,没有成为政客与革命党,没有书写革命文学,反而变身为职业通俗小说家,为鸳蝴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徐卓呆、程瞻庐、顾明道等。可惜的是,40年代之后,一体化叙事的形成,很多通俗作家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即便是书写知识分子启蒙的叶圣陶,我们也能看到《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小说中,流露出的对民俗风情的热情,对平凡琐细的人生的关注。而当代苏州小说发展中,“世情”成了潜在影响,写俗世的悲欢离合,写真实人生的爱恨情仇,写个体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写小巷生活的家长里短,这也都是“苏味小说”常见的主题。然而,当代苏州小说,并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民俗书写,更在于化“世情苏州”为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在“中国故事”与“中国诗学”的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全球化的景观之中,塑造独一无二的“地方性民族志诗学”。
谈到“文学苏州”的当代形态,不得不提到陆文夫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陆的小说,很早就在新中国文坛崭露头角。“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优雅精致的文风。他对于徐文霞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很多禁忌,表现了人性人情之美。《探求者》事件,让陆文夫受到了影响,创作上很难施展拳脚。直到八十年代《美食家》的发表,才让陆文夫重新回到了“小巷文学”。短篇小说集《小巷人物志》中,《圈套》《临街的窗》等作品,是问题小说式的写法,挖掘社会的荒诞与苦涩。而《美食家》则意义重大。陆文夫从温婉秀丽的文风入手,逐渐在内容层面,接近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朱自治这个人物形象,从闲人和边缘人,堕落资本家的角色,成了一个尊严被肯定的“美食家”。“美食家”的名字,更像是一段记忆的重新打捞,一种人物形象谱系上的接续。对吃的关注,就是对人的物质欲望的肯定,这其实也是接续了《棋王》的思路,但不同之处在于,阿成在“棋”的玄学和“吃”的朴素物质哲学之间,寻找着道家的精神支撑。《美食家》则更彻底,更接近人的本源性欲望,并将之上升为一种个体性生命的美学选择。陆文夫对小巷美学的关注和对个人物质尊严的注目,成了一个时期寻根文学、市民小说的标志性文本,而将这个热潮发扬光大的,则是范小青的“苏州系列”小说和苏童的先锋小说创作。其实,范小青的“神性写作”与苏童的“巫性写作”,犹如苏州文化的“一体两面”,对于苏州文学提升为一种独特的,象征域的地域想象,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范小青的苏州写作,以《裤裆巷风流记》为标志,走向了风俗学意味的成熟。而后,她的《鹰扬巷》《朱家园》《六福楼》《顾氏传人》等小说,不断热衷书写苏州小街小巷的故事,并将那种底蕴深厚的小市民生活,从相对固化的民俗传统走入真实现代苏州生活,上升到一种民俗学意味的美学高度。她的小说在题材和手法上是多变的,有尝试侦探小说笔法,如《真娘亭》《老岸》等,有书写当代官场女性的《女同志》,写现代城市转型的《百日阳光》《城乡简史》,她的小说还时常出现神秘氛围和鬼怪传说,如《在那片土地上》系列小说,以及《瑞云》。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灭籍记》,“苏州风味”,由实入虚,成为一种意境性和哲学性的存在,不但肯定了凡尘俗世生活的价值,而且在面对真实人生基础上,不断赋予其“神性”的伦理光芒。这些长篇小说,不仅涉及乡村权力秩序,城乡改造等现实问题,而且将笔触深入到“文革”、农村医疗制度、佛教与革命、户籍改革等诸多宏大历史题材,甚至是个体身份与集体命名、救赎与沉沦等哲学命题,而无论范小青的文学疆土如何扩大,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真善美的热爱,对平凡人生的悲悯,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价值态度。范小青的写作,一直在变与不变的徘徊中前进,然而她所言的坚守的东西就是“想丢了丢不掉的,只有事关生命的东西”,坚守的是她痴迷于刻画大时代下细微的个人,而没有追求史诗的雄心壮志[1]。她曾讲到过,苏州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后,就有了一种悠远绵长的“佛性”。这种“佛性”的神性光芒,具有很强的伦理意味,是人性的悲悯,是人性坚强的韧性,也是一种平淡却充满活力的烟火意识。
如果说,范小青是将苏州文学“世情传统”的写实一面发扬光大,形成了某种中国南方特有的,神性的伦理光芒,而苏童则是将苏州文学“世情传统”的写意的一面挥洒成雨,形成了更具象征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巫性写作”。苏州除了佛教文化影响,也有着很强的南方巫术传统的影响。苏州风味,在苏童笔下,更多的是一种写意性的氛围,存在于南方魔幻般的巫术体验的仪式之中。那些来自南方的,缠绕着死亡与欲望的故事,被苏童赋予了很强烈的仪式感和虚构意味。小说《仪式的完成》,苏童虚构的“拈人鬼”的伪民俗故事之中,民俗学家最终死于人鬼不分的诡异氛围。批评家王德威,就是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意义上理解苏童小说的南方地理坐标的独特意义。它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对巨大的卡里斯马能指的断裂。南方的堕落和诱惑,形成了地缘的,对北方宏大话语的质疑,也成为中国面对西方现代性主体的另一种边缘化,抒情化姿态,这种民族志诗学意义上的南方,其后现代化的断裂诱惑,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形成了一种时间的共识性:“苏童的南方写作如果成了他的正字标记,正是因为他的南方,早已被抽空了被指涉的实体,悬浮飘荡,反而摇曳生姿,这一意符和意指的断裂,是我们社会迷思的开始。[2]”
在苏童的笔下,像范小青那样的,具象化的苏州景观是不存在的,而是存在着“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两个虚构的地理坐标,也代表了乡土与城市的想象性对立。《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祖先》等系列小说之中,苏童以华丽颓废的意象和弥漫的欲望,书写了南方乡土的独特风韵,而在《城北地带》《刺青时代》《肉联厂的春天》等小说之中,苏童以青春叙事,缠绕着欲望与死亡,绘制了一幅充满诱惑与堕落的南方城市记忆。《红粉》与《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作品,则将这种南方秘史与民族志的先锋书写,进一步扩展到了历史和民俗领域,将欲望、死亡、颓废等诸多南方体验融会其中。而在《我的帝王生涯》,虚构的夑国与少年皇帝端白的传奇人生,形成了某种强烈的中国历史互文性。可以说,苏童的小说,苏州书写闪烁着上升为南方书写,又标识着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文化空间隐喻关系。
范小青和苏童,代表着“苏州书写”的地域性特征,由世情传统出发,在当代生发出的写实与写意,现实与先锋,神性与巫性的不同面向。在这期间,推崇个人化叙事,质疑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人价值的发现,对抒情性的推崇,语言的精致圆融,则是他们的某些共性的东西。也正是在范小青和苏童所开创的这两种新苏州小说的传统之中,新一代苏州作家,不断展现出了艺术上的探索和新的风貌。叶弥的小说,擅长探讨现代都市之中,人类情感的救赎与坚守。她的《天鹅绒》《猛虎》深入到了现代人的情感世界之中,笔调空灵细腻,又不乏犀利。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更是以“吴郭城”隐喻苏州,写出了一种个人化的,充满了抒情风致,又有着大胆批判反思的“共和国苏州史”,有效弥补了苏州书写中的历史理性不足的缺陷,是这些年来苏州小说之中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朱文颖的小说,则具有更强的现代都市写作气质,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高跟鞋》,写出了苏州、上海等地在向大都市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则更具苏州书写的精致气息,具有着江南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戴来的小说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对面有人》《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等,则不但有苏州的细腻抒情,且有着北方书写的豪放不羁,她能将粗俗幽默与微妙情感结合,将世俗写作烟火气与荒诞哲思结合,将男性视角的阔大与女性视角的敏锐结合,创造了别样文学世界。苏州男作家荆歌,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等作品,小说在灵活多变叙事中,还有着荒诞的黑色幽默和悲悯阴郁的气质。他的作品具有更强烈的哲学意味。苏州另一位男作家王啸峰,则从散文开笔,进而进入小说世界。他对苏州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掌故非常熟悉,将幽暗细腻的苏州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常常深入到世界和人性的极深远之处,《井底之蓝》《甜酒酿》《隐秘花园》《双鱼钥》等短篇小说,如同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追寻一种不能被坐实的记忆,是一种叙述意义上的间离效果,将“隐秘空间”描写扩展为一种弥漫于无处不在的世界悲剧感认知。
2003年,江苏作协曾举办“苏州小说创作”研讨会,众多学者和作家,都对苏州书写提出了很多看法。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作为地域书写的苏州小说,不仅是重要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着强烈的南方文化志的象征寄喻性。然而,正如格尔茨所说:“地方知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任何文化制度,任何语言系统,都不能够穷尽‘真理’,都不能够直面上帝。只有从各个地方知识内部去学习和理解,才能找到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我文化和他文化的个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重叠共识’,避免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起来,明了二者同时‘在场’的辩证统一。[3]”地方性书写的意义,也许正是在对比之中发现问题,也在于互相借鉴,既追求特殊性,也追求共性。在当下的苏州地域书写之中,也有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如何将苏州的传统文化意蕴,更好地与当下现实书写结合的问题。很多苏州的小说,沉溺于熟悉的意象和物象,固守于程式化的故事形态,过分重视隐喻性和诗学意义,忽视当下社会的千变万化,久而久之,不免陈词滥调,未能给读者有效地传达文化的美感,反而是某些通俗作品,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了苏州的文化形象,比如,根据阿耐的长篇小说《都挺好》改编的电视剧放映后,将苏州文化与当下人的情感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养老问题结合,“同德里”等苏州小巷,再一次成为旅游热点,甚至有人戏称,一部《都挺好》拉动了苏州的房价。再比如,当“纤细”“阴柔”“抒情”成为苏州小说的代表标签时,如何立足于此,又不断突破局限,创作内在维度更丰富的苏州小说,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风格一旦固化,就会成为桎梏。另外,就小说内部的类型发展而言,中短篇小说创作,是苏州小说的强项,长篇小说相对偏弱;写世俗世情世相的小说多,写情感类的小说多,而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偏弱,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偏弱,这反映了苏州作家在历史理性的把握上,轻巧灵动有余,而厚重阔大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普遍意义上的南方书写,共同要面对的问题。未来的苏州小说的发展之中,如何能打破现有的美学原则,将地方性与世界性结合,将地域的独特性与人性的普世性价值结合,出现更丰富、更阔大,更具有原创性的文学形态,如何能在中国文学版图之中,形成持续的,具有更高辨识度和更强的象征力度的书写,则是摆在苏州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务。由此,才能真正实现“最具民族特色的,才是最世界的”这样的文化目标。
[注释]
[1]何平编:《范小青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 页。
[2][美]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3 页。
[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导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