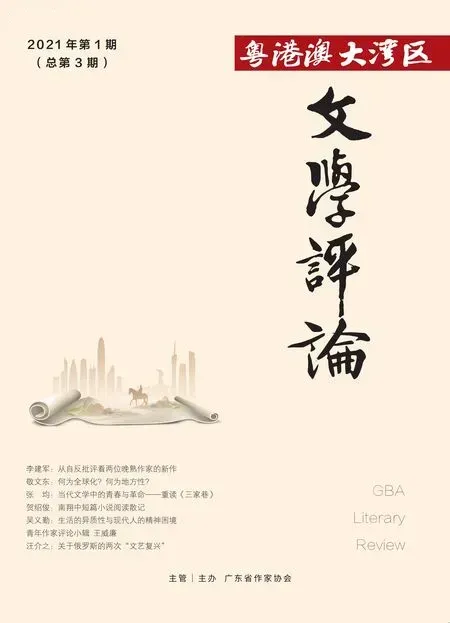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何吉贤
近年来,从多学科(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融合和跨学科方法角度对“共和国史”以及整个20 世纪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研究渐成人文学术界的热潮。长期受20 世纪历史争议问题困扰,从而无法形成“整体性”的历史叙述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也处于这一潮流的影响之中。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讨论热度正高的“历史化”问题即属该脉络。此一“历史化”与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和90年代的“再解读”不同,其动力远远不限于对历史叙述的“反写”“重写”或将文学虚构作为历史或政治的象征符号,以此打开文本、历史或政治的罅隙,而是要通过重回历史形成的“现场”,还原或重构历史形成过程中的诸因素的构造及其作用,如此,文学便成为历史构造过程中的构成性因素,或是其过程和后果的想象性表达,“文学实践本身即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就必须‘历史地’来研究文学”[2]。在“历史化”的脉络中,困扰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延续和断裂冲突的问题,通过还原历史细节,从而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历史的视野,有可能得到适当的缓解或解决。
“历史化”的取径带来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多种可能性,“20 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作为一个研究思路的提出,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思路或领域的成立,首先在于历史展开过程中“革命”和“文学”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艺”,“革命”和“文学”在理论、实践、生活、思想等各个层面上复杂纠缠,相互渗透。发生在20 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革命,既是一些连续不断的事件,同时也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理论争论,留下了很多用一般性的(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理论性问题。要探讨20 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这一课题,需要重新回到产生20 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同时进出文学和历史,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动力的追索,阐释历史,发明文学。从思想和人文的角度进入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经验,从中国革命经验历史化的角度阐释20 世纪文学及其经典的特质、逻辑和艺术魅力。
而要进入20 世纪中国革命的细部,把握20世纪中国革命和历史的重要动力和经验,并以之为基础,重新打开阐释20 世纪重要文学经典的阐释空间,这一诉求背后的难点在于:如何真正进入历史的细部,同时又不陷于历史琐碎的细节,去把握历史的整体和趋势;进一步,如何将对历史的把握贯穿于对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的解读,掌握历史叙述和文学研究及批评之间的张力和界限。也就是说,在处理历史叙述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时,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社会政治阐释方法,又不是如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海外中国研究者所言,要将20 世纪中国革命中的文学文本作为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印证材料”去处理,而是反过来,通过将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还原到具体的地域文化和与具体的人、事、地的实际关系中,通过考察其“结构过程”(structuring)及其与更为广大的历史过程的关系,凸显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文学的想象和叙述如何参与并内在化为历史变化过程的内在动力和因素,同时进一步形成和确立其自身的形式特征。因此,在关于20 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既在于要形成某种新的有效的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阐释方法,更在于要深入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内部肌理,探讨、形成某种更丰富、有效、开放和贴近现代中国认识的历史观。两者互相促进,互为条件。也就是在这一追求的驱动下,近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路径,通过对一些已经被某些认识所固定化的作家进行重新研究,以图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新的方法和视野。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从地方到中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革命的意义上,“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和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概念[3]。在武装斗争、地方军事割据、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展开过程中,地方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地方”既是在地的、又是流动的;“地方”既是地方性的、又是普遍性的。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在“地方”上普遍展开,但这个过程又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和文化的争论,理论争论的指向之一即是为在“地方”上展开的革命实践提供“普遍的”目标和意义。在这一脉络上,20 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发生过三次剧烈的转化:第一次发生在晚清和“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开始“开眼看世界”,而且从文学和文化上突破,去揭开“瞒和骗的历史”,正眼面对世界和现实;第二次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转入军事割据式的武装斗争,人文思想界发生“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不仅要认清“现实”,而且要“科学地”认清“现实的本质”,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更深更广地嵌入“现实”和“地方”;第三次转化发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严峻的民族危机使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离开中心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到内地、到乡村,发生了数量巨大的人口流动,“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漂泊、流亡、人口的流动带来的不仅是“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4]的情感结构,也是个人和集体视野的重构、知识的再造、知识—实践/地方—普遍关系的重新连结。20 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展开过程,都伴随着这一思想、知识的转化过程。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代知识不断“下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方性”知识反过来重构现代知识和“改造”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
在“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5]。讨论的触发点来自毛泽东提出的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的倡议,讨论最后指向了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如何建立“民族形式”为核心的诸多问题。关于“民族形式”,尤其是其“核心源泉”的问题,讨论各方观点相异,但“各派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都认为‘民族形式’是一种现代形式”。“‘民族形式’既不是‘地方形式’,也不是‘旧形式’,既不是某个多数或少数民族的形式,也不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形式。所有这些已有的或现存的形式仅仅是‘民族形式’的素材或源泉,却不是‘民族形式’本身。其理由显然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既不是某个地区,也不是某个种族,而是一个现代国家共同体。由此‘形式’不是某种地方性的形式,也不是某个种族的形式,而是一种现代的、超越地方性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创制。”[7]讨论中争议最多的是向林冰提出的“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问题,但不管对“民族形式”有多少歧义性的理解,都包含了民间形式与普遍形式的结合问题。“民间形式”是跨不过的基础,而民间形式必然与地方性密切相关。20 世纪革命中产生的大量文艺实践和作品,都与地方性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理解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不仅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将视野拓展到地方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志等,还需要在空间上拓展,拓展到地方、乡村和边疆。
将“地方性”因素看作“20 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中的构成性因素,我们又可按“地方性”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其与作品和作家个人的关系,及其产生的诸多综合性问题等方面,将其进一步分出多种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地方性”因素作为文学叙述的“装饰性”因素,附着在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叙述上。因为有这些“地方性”因素——诸如方言俗语、民谣或地方戏的片段和潜在影响、民俗、地方风景、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性格等等——的存在,叙述体现出了很强的“地方”特色和“在地性”,但叙述和故事本身是普遍性的,“地方性”因素只是使其“形象化”,将其激活和落地。在一些成功的作品中,它们也与故事本身融为一体,构成叙述的有机成分,成为作品成功的艺术特色。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两者都大量使用了东北和河北方言、展现了地方民俗和地方人物的性格,但很明显,“地方”本身并不构成这两部小说的内在因素,批评者看重的也不是包含在作品中的“地方”特色,而是其普遍的意义(如彭真对《桑干河》的批评,冯雪峰对其的褒扬等)。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层次上的“地方性”因素是流动的,可以从此地转移到彼地。
第二个层次中,“地方性”因素构成了作品的在内要素,构成了叙述的动力和特色,它们驱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发展,形成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家的个人“风格”。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赵树理。赵树理的创作有鲜明的山西“地方”特色,由此也发展出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山药蛋派”。这些“地方”因素既呈现在诸如语言(赵树理较少使用方言,但使用经过提炼的地方口语)、民俗、生活细节、地方风景、人物性格等外在性的叙述因素上,同时也内化为作品动力性的要素,与叙述和作品整体及作家个人“风格”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这方面能举的例子很多,这里举一个以前较少受人注意的例子。赵树理的作品中,“算账”的描写和叙述几乎比比皆是,无处不在:与不同的人算,有各种各样的算账方式。家里过日子要算,父子算、夫妻算、婆媳算、邻里算;种地算、做生意算;地主向农民租地和放高利贷算、农民与地主“清算”也要算;组织互助组要算、加入合作社也要算;个人与集体之间要算、集体与国家之间也要算……“算账”在赵树理作品中的频繁出现,既承担着重要的小说叙事的功能,又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伦理、政治和思想的意涵,可看作理解赵树理作品及其创作的重要“纽结”。怎么理解这一现象?近来的研究中有研究者用农民“说理”的世界、“翻身”的理性来进行解释[8],有一定的道理,但还远远不够。“算账”显然是作为写农民“铁笔圣手”的赵树理理解其家乡农民生活、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要打开这一视角,需要引入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赵树理作品中叙述的晋东南是历史上晋商的核心地区之一,而远距离贸易和记账法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复式记账法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之一一样)。所以,算账如何深入到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乃至形构了其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某种超验性的价值观等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自有其“地方性”的背景和存在基础。在这里,“算账”已经内化为作品的要素,也是作家观察和表现生活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第三个层次,“地方性”因素本身就构成了普遍性,也就是说,地方风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等的纯粹呈现,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就构成了普遍意义的表现。在这里,“地方”既是具象的、实体的,同时又是抽象的、象征的。“地方”处在历史的势能中,生生不息,充满生机,预示未来。这对写作者的经验和视野、写作者与其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作者浸润在“地方”和经验之中,又要超乎其外,有更广大和普遍的视野。“五四”之后形成的现代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重构了城乡关系,使得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也使得现代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但20 世纪频繁发生的战争和革命,又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发生了一定程度和形式的“反向”流动。中国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创作的大量作品,都与作者在地方上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这也是内在于中国革命和文学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和“深入生活”的工作方法和原则的,这些作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都有或深或浅的、密切的同构关系。这里可以以周立波在50年代“回乡”之后的创作,尤其是其短篇小说创作为例。周立波这时期创作的作品,皆以家乡湖南益阳的农村为背景,地方方言、民俗、风景密集呈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个人风格”。短篇小说如《山那面人家》《禾场上》《下放的一夜》等,通篇几乎全为民俗、风景和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和日常对话,但正如唐弢所言,作者在呈现这些民俗的时候, “又给所有民俗习惯涂上了一层十分匀称的时代的色泽,使人觉得这一切是旧的,然而又不完全是旧的,时时反射出一种新的光彩,这是什么呢?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折光……”[9]而在风景与故事中的地方人物“相认”的过程中,人物的主体及地方人物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0]。
在这一层次中,作为批评者和研究者,还应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不同作品中“地方性”因素的呈现是分散、琐碎的,但这些不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丰富“地方”内容的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时间里集中出现后,又会形成一些什么新的问题,构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普遍的、理论性的趋向呢?20 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过程中出现的多数作品都以农村为题材,而这些作品大多又以村庄为单位组织叙述,在相当的规模上(往往人物众多、关系层次复杂)深入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多重人物关系,个人、家庭、村庄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村庄本身也在不同层次上被打开。在20世纪文学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中,很多都是这样的作品,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柳青的《种谷记》《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评论家雷达在评价王蒙小说《这边风景》时敏锐地注意到:他以前认为浩然的《艳阳天》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现在看来,随着《这边风景》的出版,从时间上算,真正的幕终曲,应该还是王蒙的《这边风景》[11]。当然,认定这部作品为“幕终曲”并不仅仅在于时间因素。《这边风景》叙述了南疆一个以维族为主的多民族村庄的故事,构建了村庄内部多重的复杂关系,涉及人物80 余位,这种“雄心”和叙述方式,在“十七年”之后几乎已经绝迹,即使是以“民族秘史”为己任的《白鹿原》,处理的也只是几个家族之间的纠葛,对于村庄内部的其他结构层面并不涉及,从这一意义上,《这边风景》确乎可称“十七年”时期的作品。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基本构成单位。“所谓农村本来首先即指村庄。‘农村’一语所指涉的人口、土地、组织与文化,在中国首先是与村庄单元联系在一起的。即,农民大部分还被组织在村庄之中,农业主要发生在村庄所属的土地上,村庄文化对于农村人口最具有可分享性和纽带作用。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说,农村、农业、农民的变迁,首先会表现为村庄的变迁……’[12]关于村庄的研究,也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传统,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等学科,更是在方法论和经典作品上都有相当的积累[13]。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村庄叙述,也是20 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革命文学”所留下的、有待进一步清理的独特传统。“新文学”发端之时,即以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发轫,村庄也开始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中。但在启蒙和某种“怀旧”情绪的背景下,村庄只能作为承载某种观念或情绪的抽象“表象”,既不能具体而微地呈现其复杂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叙述单元呈现。在相当的程度上,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向文学的渗透,“社会史论战”等所展开的思想和知识视野,为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村庄叙述,为地方性的村庄作为一个叙事对象提供了条件,而伴随战争和社会革命而起的社会动员及其相应的文化创造要求,则为此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应该指出,以上三个层次并没有层级或高下之分,对于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而言,是否能成功运用“地方”资源,“地方”的活力能否被激活,端赖其生活与“地方”经验的关系、创作“个人风格”的取舍与个人的才能等。而“地方路径”的引入,确也能为“20 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研究带来很多的可能性。
[注释]
[1]按学科划分,“20 世纪中国文学”被分别置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下。但突破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对“20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整体性”叙述的努力,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论;1987年,陈思和提出“新文学的整体观”;90年代,洪子诚等人从“五四”文学传统角度出发对“当代文学”学科化建设的工作;以及近些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关于贯通1949年、1979年两个转折的论述,等等,都是在断裂中寻求“整体性”历史叙述的努力。
[2]倪伟:《社会史何以作为视野?——关于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思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5 期。
[3]由于论题所限,本文仅仅从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考察“地方”,实际上,“地方”的凸显也是现代民族主义工程的重要表现之一,也与现代性(包括现代技术)的扩张性后果有关。
[4]参见[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刘绍铭、李欧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赞同他的归纳,却对他的分析持有保留意见。
[5]“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1939—1942年,从延安开始,扩展到国统区的重庆、桂林,甚至香港等地。郭沫若、茅盾、胡风、陈伯达等许多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卷入其中。
[6]毛泽东:《论新阶段》,延安《解放》(周刊),第57 期,1938年11月。
[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论争》,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98 页。
[8]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
[9]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10]详参何吉贤:《“小说回乡”中的精神和美学转换——以周立波故乡题材短篇小说为中心》,《文艺争鸣》,2020年第5 期。
[11]雷达:《这边有色调浓郁的风景——评王蒙〈这边风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 期。
[12]毛丹:《村庄的大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0 期。
[13]相关综述性研究,可参看谷家荣:《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村庄表述》,《学术探索》,2012年第2 期;杜婧:《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2 期;邓大才:《如何超越村庄:研究单位的扩展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3 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