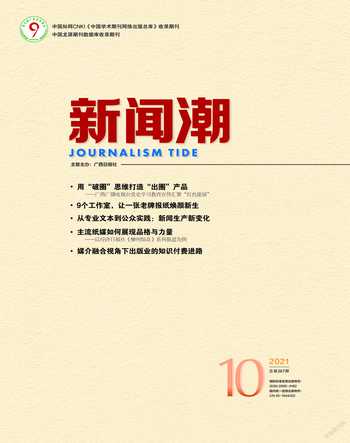融媒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传播研究
刘宇青
【摘 要】融媒时代的到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在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特征基础上,从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选择四个方面,结合融媒时代成功的非遗传播案例,探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创新方式。
【关键词】融媒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创新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既包括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也包括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在特定群体与所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密切互动中发展,非遗的传播有助于传承特色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融媒时代的到来,为非遗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融媒体依托技术发展,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功能优势,提升在传播中的竞争力,就非遗传播而言,通过传播理念创新、传播主体创新、传播内容创新和传播媒介选择创新,实现非遗文化魅力的全面展示,体现非遗传播的文化价值。
一、传播理念创新:从“重藏轻用”到回归日常生活
(一)传统非遗传播理念及其误区的认识
“重藏轻用”原是指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重视对文物、书籍或是档案的收集和保存,却出于主观原因或客观条件限制而不重视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在非遗传播中,一直以来只重视展示被保护、被抢救的非遗对象,关注传承过程、文化价值、历史意义,而对于非遗如何利用并应用到群众日常生活里,很少体现在非遗的传播理念中。在融媒时代,创新非遗传播理念能够更好地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
受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影响,传统生活方式、日常仪式及其场所受到挤压,一批曾经沁润在人们生活中的礼仪、民俗、技艺、艺术和体育活动逐渐消失,承载在非遗中的文化传统变得遥远而陌生。人们对非遗的认识局限在博物馆馆藏、民俗展览或数字化展示中,对非遗的体验常常只是在旅游景点的浅尝辄止。这种认知方式和传播框架会使大众不能完全理解非遗传承的意义,单纯停留在文化差异欣赏甚至文化猎奇层面。
文化的活力和繁荣源于整个族群对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源于人们在生活中对文化的运用和发展。如果非遗与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联系或交集,人们对非遗的文化意义缺乏亲身经历,就很难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这与非遗保护理念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保存和复制,而是使之服务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1]。因此,通过非遗传播使其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二)非遗走入日常生活的方式
让非遗真正走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自然而然的简单回归,还有可能使其立于时代的潮流前沿。例如相声,由于极富幽默感,作为“谐趣”娱乐类表演相对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走入日常生活。值得关注的是,相声受到广泛追捧,与近年来以德云社为代表的相声创作与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过去,多数人接触相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广播或电视收听观看相声节目;“现在,多位青年相声艺人参加各类电视综艺节目和互联网直播,开通个人微博,录制短视频,所吸引的粉丝量,已与当红潮流明星无异”[2]。相声与年轻人中流行的粉丝文化紧密结合,衍生出相声艺人带动粉丝联合推广非遗的各种传播活动,进而形成精英引领、大众参与的非遗发展模式。
融媒体为非遗走入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新选择。近年来,许多媒体平台也做了很好的尝试和探索。如“云游非遗·影像展”有八大网络平台深度参与,除了公益性展播非遗纪录片外,更重要的是发起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的非遗手艺”“我的非遗故事”“我身边的非遗”等,让非遗真正走进和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抖音推出“抖音非遗市集”,将风靡一时的直播带货与非遗紧密结合;B站举办中国华服日线上活动,通过汉服产生交集,蜀锦、缂丝、苏绣、湘绣、扬州玉雕、北京花丝镶嵌工艺、庆阳香包绣制、南京绒花制作等非遗共同组成衣冠系统,成为当代青年时尚、新潮的服饰穿搭选择。不同风格的非遗聚合形成规模化的传播矩阵,让群众乐享非遗大餐,引发出对非遗强烈的兴趣及關注度。
二、传播主体/受众创新:从对立走向融合
(一)传播主体/受众身份在融媒时代的变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都是相互对立的。经典模型如拉斯韦尔的“5W”模型、贝罗的“SMCR”模型都严格区分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在实践中,信息是由传播主体发出,经过媒介传递给受众,传播什么内容、内容该如何表达等皆由传播主体掌控,传播受众缺乏话语权,只能在极其有限的选择中被动接收信息。融媒体时代,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对立走向融合,取而代之的是集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受众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用户”。
(二)传播主体和受众“合一”与非遗保护的关系
融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具有非线性、社会化和产销合一的特点。[3]当“受传合一”应用于非遗传播时,却引发多重疑虑。原有线性传播模式中,非遗传播的主体通常是非遗传承人或保护单位,因其权威身份,其所发布信息的可靠性毋庸置疑。当下参与传播的一般用户没有经历非遗研习,不具备专业素养和能力,尤其是一些非遗鉴赏的门槛很高,远非娱乐式的学习就能掌握。人们担心,非专业人士参与传播会导致非遗被误读、曲解,甚至退化和消失。
这种担心混淆了非遗传承和非遗传播的概念。非遗传承是指文化在社会成员中纵向交接的过程,代际完成的是观念、技能、物质、模式、意义、场所等的传递,通常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完成面对面的传授。非遗传播通常是指大众传播,探讨的是信息的传递、知识、意见、情感、愿望等,大众传播的目的并不是继承,故而只要传承还在,就不会因大众传播导致非遗断代或消失。“受传合一”中由见解不同引发的争论、思潮对于本身就具有活态性和适应性的非遗而言,是走入现代性生活的必然历程,这种传播中的“热度”对非遗的传承有促进意义。对于可能存在的用户蓄意歪曲非遗、传播不实不良信息,实质上涉及的是传播伦理问题,互联网治理相关规范和平台监管应起到管控作用。
三、传播内容创新:从传播知识到传播美好
(一)非遗传播内容变化引发的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估非遗项目的价值时,应用到的标准包括独特性、濒危性、历史性、传承见证、特色技能、表现性和影响力。受非遗价值评估的影响,非遗传播特别关注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无论是有关特定文化群体非遗的历史知识、地方性知识,还是集体经验、智慧结晶,对非遗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传播中却很难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与之相反的是,以传播美好为内核时,能够获得热烈反响和情感认同。以爆红的李子柒系列短视频为例,可能很少有观众能从中学习和掌握全面的食材知识或烹饪技法,但却能从其有人、有物、有场景、有情节的美食故事中感受美好。作为非遗推广大使,李子柒在视频中唯美、浪漫化地呈现了传统乡村生活,激发了观赏者对田园牧歌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讨论。把历史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够领略的意象美嵌入当代生活,从而使非遗对当代社会而言具有活的精神价值[4],从此意义上讲,非遗传播从传播知识向传播美好延伸和转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内涵,为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二)非遗传播内容变化与非遗原真性问题
非遗传播的内容变化,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非遗的原真性问题。一部分研究认为非遗保护和传播的对象应该是未经改动的、具有原生态的文化,但这并不符合非遗不断演进和发展的特性;所以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盲目崇拜非遗的历史表现形式,而应该推动其再创造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5]对传播非遗知识而言,真实地反映非遗的实际情况、准确无误地传递出非遗的形态和传承脉络,就是实现了知识传递目的。但对于传播美好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对非遗所涉及的社区、群体、社会实践、观念表述、工艺技巧、工具实物等做出一定的筛选、修饰,甚至是提炼、升华,才能真正将传统文化打造成令人心生向往的美好。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极大限度上改变了非遗原本赖以存在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下,传播非遗美好一方面将非遗从编年、考据、遗存整理的固化和单向阐释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非遗增添了商业价值。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如果传承者完全不能据此获取经济收益,那么传承能力就会下降、萎缩、衰退乃至消亡。
四、传播媒介选择创新:从追随流行到媒介适配
非遗的门类十分广泛,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除了具有活态性等共性特征外,从表现形式上归类,非遗可以分为造型(技术)文化、表演(讲述)文化和活动(民俗)文化。[6]不同的表现形式意味着其所适配的传播媒介会存在差异,在媒介选择方面,完全追随当下流行的趋势可能收效甚微,选择适配的传播媒介才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造型(技术)文化类非遗以传统技艺为核心,能够生产出有形的产品,如美术作品、工艺品、醫药产品等,适合直播加带货的方式开展传播并获得收益,但也需要注意防止非遗因长期处于被全方位参观状态导致原有秩序被破坏。表演(讲述)文化类非遗应将直观与隐喻相结合,通过语言、形体、声音等完成文化展示,促进文化共鸣,所呈现的展示结果看得见也听得见,却是无形的,这类非遗适合以视频形式传播,但是需要注意短视频虽然具有覆盖面广、信息点突出、理解成本低等优势,其对非遗文化空间的剥离和去语境化重塑也会导致非遗呈现碎片化和标签化的形象。[7~8]活动(民俗)文化类非遗同时具有有形和无形属性,依托一定的文化场所开展特定仪式和活动来完成文化表达,具有参与性、体验和观感相结合的特点,这与慢传播强调内容和品质、突出“沉浸式”体验的理念相吻合,慢传播“跨媒体叙事”的模式更利于非遗全景式再现。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是保护、宣传非遗文化的重要手段,融媒体时代,各种媒介的竞争格局、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创新非遗传播方式能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全社会认知、尊重和弘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而言,应该与时俱进开展创新探索,优化创新实践,担负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杨程.生态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斗争与适应性变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 36(11): 34-42.
[2]游红霞,田兆元.粉丝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以德云社相声为例[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38(3): 146-152.
[3]杨光宗,刘钰婧.从“受众”到“用户”:历史、现实与未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7):31-35.
[4]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到美学[J].江苏社会科学, 2020(5): 151-158,239.
[5]刘鑫,苏俊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内涵辨析与实现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1): 55-62.
[6] 陈华文. 创造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DB/OL].[2021-02-08].http://www.ihchina.cn/luntan_details/22468.html
[7]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J].民族艺术研究,2020, 33(4): 137-143.
[8] 秦翠平,邓年生.探析移动短视频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以“抖音”短视频为例[J].新闻潮,2020(7): 20-23,38.
(责任编辑:杨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