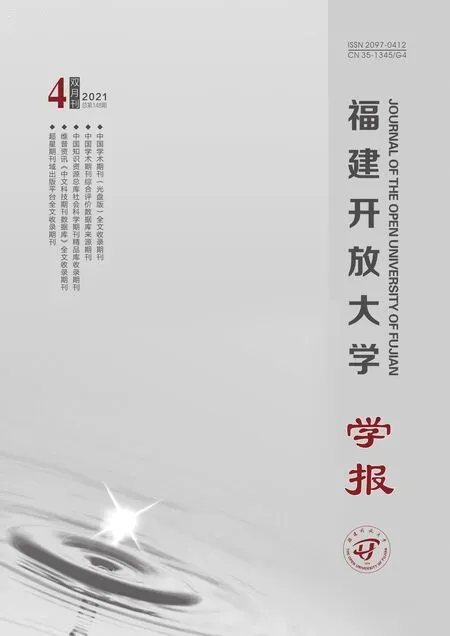论唐代保辜制度对当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戴 滢 邱 唐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50)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学术研究领域备受瞩目,刑事和解是一种运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特殊的案件处理方式,加害人通过与被害人及其亲属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与协议的方式可以免去司法的定罪量刑。[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古代的保辜制度有着一定的相通性。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成熟时期是唐代。将其定义为案件发生后,加害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受害者竭尽全力地给予补偿,在期限截止时,再对加害者进行定罪,具体的量刑要根据当前受害者的情况进行判定的制度。加害者在伤害造成后是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让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推断出加害人是否在主观上真心悔过。两种制度都强调了对受害人进行保护、对加害人赋予悔改机会以平稳修复社会关系的深层内涵。然而观察我国当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会发现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着诸如“花钱买刑”,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唐代保辜制度中蕴含的习惯法思维,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践应用方案,以更好地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二、“刑事和解”之必要性审查及重要地位
“刑事和解”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认可。在过去,它的参与主体是被害人和犯罪者,双方进行主动协商、私下解决,因其弱化了制定法的权威力量,曾遭到部分学者的非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志刚提出,“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如果国家刑法的价值、刑罚的目的根本没有实现,则国家只能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迳行作出其认为符合最大效益的判决”。[2]但是,这些批判也受到专门研究“恢复性司法”学者的回应。复旦大学杜宇教授便在《“刑事和解”:批评意见与初步回应》一文中提到,“在存在类似风险的辩诉交易中,我们不用首先考虑到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其置后……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和解中,公共利益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大大降低,此时恢复性司法更为重要”。[3]由此可见,刑事和解之必要性问题在过去曾引起学界一番博弈。
当然,无论学术界如何争议,古往今来我国民间基层组织在处理案件时往往采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古代,由于人们大都认为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进入衙门对他们而言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通常情况下是他们都将邻里之间的矛盾通过私下协商解决,而不是由官府做出判定,由此可见,很少有案件是通过政府进行处理的。在乡村社会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民间权威,如族长、首领等,通常在发生刑事案件时,由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族长、首领等的主持下协商解决。因此,在正式法规定以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有刑事和解制度的渊源。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将刑事和解作为特殊程序,正式将其纳入刑事诉讼规制中。随后2018年修订的刑诉法第288条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范围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细化规定。立法的这种修订也从侧面反映其重要地位。
三、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缺陷
刑事和解制度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加害人,这样有利于提升加害者的配合度,最终达到被害者补偿最大化,实现和谐社会。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反映了该制度亟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良。
(一)“花钱买刑”问题
“花钱买刑”的现象在目前的刑事审判活动中频频出现。虽然立法中明文规定了“真诚悔罪”“赔礼道歉”,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的指导,比起“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司法工作人员更倾向于采取可以简单量化的物质赔偿的方式来考察加害人的悔过程度。但是这种以物质为衡量标准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诟病,认为富人可以用金钱操纵刑事裁判。但是刑事和解过程可以双赢,和解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尽量使得形式对自己更有利。加害人用自己所长来赎罪,被害人如果不要求加害人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则希望获得大额赔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但是这种操作也会降低刑罚的教育作用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而且对于物质条件比较丰厚的人会认为犯罪的成本并不高,从而会更容易犯罪。此外,由于司法机关对于被害人和解的原因调查较为困难,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可能由于资金较为紧张、对于加害方有所畏惧,或者由于对方的赔偿数额较高,因此出现被迫和解的情况,从而导致很多犯罪行为被判无罪,并且此类现象的发生还可能增强一些有钱人的犯罪心理。
(二)适用范围较窄问题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的规定,刑事和解只能适用于量刑“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七年以下”过失犯罪的初犯人员。这类犯罪的主要特点是犯罪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多数是熟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纷争,犯罪人本身并没有危害社会等的想法,对其加以改造是比较容易的。也会出现某些案件不属于以上案件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刑事和解制度之外的情况。比如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件,情侣中的女生一方想要避开男友从高楼上摔下来变成了瘫痪,女方家里经济拮据,为了给女孩医治还差十几万元的治疗费。[4]这个案件里的男方没有伤害女孩的故意,而且也明确表示自己希望求得女方的原谅,并且解决女孩医疗费,但是法院对此予以拒绝并且判处了男方有期徒刑。最终女方因难以忍受治疗痛苦选择自杀。在该案件中,尽管加害者本身本不符合刑诉法规定下的两类适用范围,但是念在加害者并不是故意为之,女方也急需一笔赔偿金,在此情况下,刑事和解的结果既有利于加害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弥补过错,也有利于对被害人的损害加以救助。
(三)监督机制不完善问题
《刑事诉讼法》中提出,在进行刑事和解过程中,关于和解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和解流程是否合理、合法要进行全面的审查,审查人员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构成,并由他们主持并制作和解协议书。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为促进刑事案件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司法机关会督促双方早日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而且对这种情况也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也就致使刑事和解制度偏离了设立的初衷,并且损害双方当事人之利益。
四、唐代保辜制度中的习惯法思维
(一)明德慎罚:给予加害人机会赎罪
将加害人在施加了犯罪行为后是否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等行为作为定罪量刑的影响因素。加害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如果对被害人有救助行为,在量刑阶段可以适当进行减刑。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一些加害人在加害后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后悔等心理,加之看到被害人的状态心理有所变化,可能会回顾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自身还是被害者造成的伤害,从而在道德层面反省自己的过错,继而积极弥补其过错带来的损失。从这方面来看,保辜制度将惩罚与教化相结合,蕴含着西周时期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的思想。
(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更多的关注
唐代保辜制度惩处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被害者的受伤害程度;二是加害者的事后弥补程度。与此同时,对加害者在案件发生后一段期限内进行的救助,该期限要根据被害者的伤情进行判定。[6]加害者为了能够得到较轻的量刑,在规定的期限内会不遗余力地对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进行弥补,尤其是很多情况下受害人的家庭较为困难,无非是负担高额的医疗费,此时加害者的救助就能够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从而使得被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提高被害人的治愈可能性。由此看来,保辜不仅能够使得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还能够使加害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以及补救,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三)儒家“和文化”的思想
孔子称“和为贵”,要求人与人和睦相处,提倡用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纠纷。民间有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新建立正常的相处关系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未来的生活。受该影响,我国自古以来追求实现社会和谐。加害者在加害后的一些补救行为不仅是对自己行为的悔过,也能够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进而原谅加害人此前的行为带来的伤害,无论是被害者还是加害者都能够获得比原来更少的伤害,也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复,避免给社会秩序带来麻烦。
(四)“无讼”“息讼”的理念
中国古代向来有“无讼”“息讼”的理念,邻里之间的纠纷尽量不要诉诸公堂,这是避免司法浪费的有效措施,从而提升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保辜制度往往用于案情争议较小的案件,此类案件中,加害人需要提出保辜请求后,只要通过官府的审核,加害人即刻停止关押,使得其能够尽快对于自己的行为进行补救,该方式的优点在于整个流程较为简便,使得诉讼过程时间大大缩短,进而能够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一些难以解决的案件中,大大提高司法办案效率。
五、保辜制度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
二者的深层理念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由加害者自身进行弥补带来减轻惩处的过程,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其蕴含的习惯法思维对完善当代刑事和解制度有很大的价值。
(一)理论上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肯定
1.经济时代下诉讼成本的节约与效益的提高
保辜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将被害人的救助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使得官方很多时候不必浪费过多的资源在一些案件的证据收集以及定罪量刑等方面。而刑事和解也同样具有此功能,即提高有效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成本。与此同时,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重要价值之一,它要求用最小的刑罚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也展现了我国刑法的谦抑性。
2.充分尊重当事人双方意愿的实现
由于伤害性案件往往在熟人之间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的关系。而很多刑事案件在处理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主要包括加害人的实际家庭情况无法进行足够的经济补偿,加害人家属不执行法院的判决等,导致民事责任重的经济赔偿很难落实到位,进而使得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及时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可在执法机关的监督和管理下,观察受害人的真实需求,如通过加害人对受害人施以救治和照料,或者以特定物件作为弥补。唐代保辜制度的成功应用也印证了这种尊重双方意愿方式的成功性。刑事和解的达成使得受害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加害人能够得到弥补自己过错的机会,能够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使得案件的处理更加顺利。
(二)实践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与完善
1.扩大案件范围
综上所述,唐律中保辜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斗殴等引起的伤害罪还有一些非斗殴的伤害案件。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事和解仅适用于轻罪案件,对此,出现学者认为有关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完全不适用于我国的情况,因此提出“重罪的刑事和解”的存在是不必要的。[7]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具体应用于司法实践还是会有不少的弊端。首先,很多情况下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十分有限,会使得被害人家属无法获得足够的补偿进而给正常生活带来一些困难,此时运用刑事和解能够使受害人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避免了受害人家属打赢官司但是获得赔偿很少的情况出现。其次,刑事和解的基础是自愿原则,只有当受害方同意和解时才能够继续进行,因此适度括大刑事和解的范围并不会增加刑事和解的可能性。
2.延长观察期
唐律保辜期限由两个因素确定:一是加害者使用的器具,二是被害者的受伤程度,加害者可以通过竭尽全力地补偿受害者来减少量刑。如果被害者能够在该期限内得到好转,加害者自然被降低量刑;若死亡,则不会被减少量刑。借鉴唐朝制度,当今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增加观察期,根据案件的轻重程度设立不同的观察期限。首先提出者是加害者,其次需得到被害者和司法机关的同意,之后对被害者进行验伤,还需被害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并且设立一个时间段来对加害人进行考察,在此期间加害人负责医治和救助被害人,期满后对受害人的情况进行鉴定,最终的量刑会参考两次的伤情鉴定,而且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适用于刑事裁量过程,在民事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也会参考上述的做法。这种做法既有利于加害人也有利于被害人。观察期限让加害人救助被害人的做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花钱买刑”的产生。
3.司法机关加强监督
唐代保辜制度的提起人是加害人一方,不过最终决定是否使用这个制度的决定权掌握在官府的手中,由官府来控制这一制度的适用可以避免有钱人利用该制度强迫受害人一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里依然是由公权力掌握主导权,尽管无论是刑事和解的提出还是最终的结果均在于当事人双方,但司法机关也得参与其中。而且刑事和解过程中设计的许多专业性强的事情都要由司法机关来主导。不过制度设计固然美好,但是实际运用中却不得不面对一些阻碍,我国司法机关的任务非常重,导致很难拿出时间精力来监督这个过程。由此可见,为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可以在司法机关设立刑事和解部门,专门负责刑事和解的过程,能更好地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监督作用。
六、结语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基于传统中有利的部分加以创新,创建更利于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环境。虽然我们不能将唐代保辜制度里面的许多内容直接照搬到今天的法律规定中,但是包含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其本身就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与其被动地添附西方外来文化,不如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消化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新发展使其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