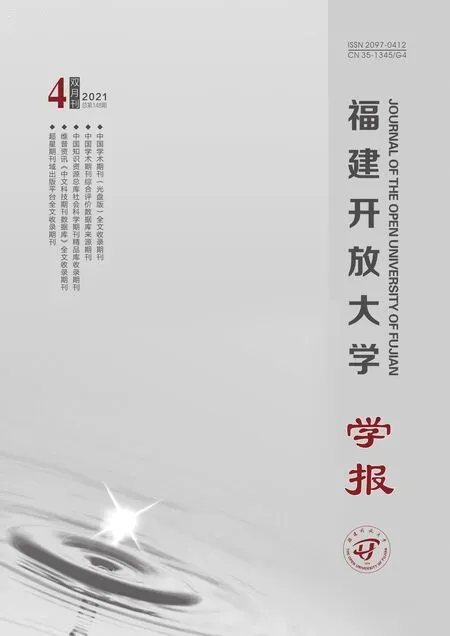“纯女性”的复杂历史生态: 《女子月刊》及其研究史初探
王 燕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1756)
一、引言
1898年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标志着女性报刊在中国的发轫。从此,以研究女性问题为主、反映和指导女性生活和斗争的女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预示着中国妇女的解放和觉醒已经同挽救国家危亡、促进民族解放一道成为了不可抗拒的时代发展潮流。妇女报刊成为一些精英男性和知识女性探讨妇女问题、传播新知的公共空间。从维新变法号召“废缠足、兴女学”,塑造“国民之母”形象,到辛亥革命争取男女同权,建构“女国民”身份,从五四运动家喻户晓的“新女性”“女学生”到都市文化中的“摩登女郎”的出现,女性报刊伴随着中国妇女走过风云际会的革命浪潮和社会变革。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其半殖民地属性及公共租界设置,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现代出版业空前发达,各类报刊异样繁荣。据上海市地方志统计,1930年前后创刊的女性期刊就有50余种。这些妇女刊物,虽然都以女性为诉求,但是因为刊物背后的阶级、政党、团体及出版公司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很多报纸的副刊都以《妇女与家庭》命名,体现了以女性与家庭、婚姻、儿童等为主题的综合性内容,还有一大批以明星、娱乐与时尚生活为主题的商业消闲读物,如《电影与妇女》《玲珑》《摩登周刊》《妇人画报》等,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下的党派报刊《妇女生活》。其 中,创刊于1933年的《女子月刊》是一本特立独行的“纯女性”刊物,它由知识分子创办,散发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无关于政治倾向和经济利益,在30年代“政治与消费话语的夹缝中”横空出世,恰逢其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销毁在日军的炮火中,被迫停刊,《妇女生活》还未创刊。《女子月刊》一面世就得到了女界的关注和支持,被誉为黑暗女界的一线光明。
二、特立独行的《女子月刊》
《女子月刊》的创办和发行是知识分子夫妇姚名达和黄心勉倾注女子解放事业的一个理想。《女子月刊》1933年3月8日创刊于上海,因战争停刊于1937年7月。刊物每月一期,每年12期为一卷,共出版5卷,53期。《女子月刊》的特立独行与创刊人姚名达、黄心勉的经历和发心不无关系。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曾在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研习历史,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后来在《女子月刊》存续期间,他还出任暨南大学教授,以教授薪水维持期刊的运营。他同情中国妇女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途径获得智识,于是他“大发宏愿,要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著作一部中国妇女史”,[1]黄心勉,婚前已经完成女子小学的教育,与姚名达成婚生育后,得到夫家支持,依然求学家乡赣县省立女子师范,因一子一女相继夭折,料理家事中断。后因北伐战争学校停顿,奔赴上海与姚一起生活。“一·二八”事变日本军队的炸弹炸毁了商务印刷馆和他们上海的小家,夫妻俩的藏书、手稿等资料付之一炬。姚黄夫妇亲历国破家亡的悲痛,东奔西逃之余目击了战事中劳苦人民的水深火热及租界里的歌舞升平,浩叹“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 识”。[2]他们于是想办一个女子刊物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
于是,1933年3月8日《女子月刊》在上海应运而生。首期《发刊词》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独立而纯粹的办刊立场:我们都是纯洁而诚恳的女子,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宗教背景,亦没有经济背景。所以当然没有政治作用,没有宗教作用,没有牟利的企图。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作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够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知识,文艺和图画贡献给读者。[3]
先后担任《女子月刊》主编的有黄心勉、陈爰、封禾子、高雪辉、姚名达,除姚之外,均为女性。除了主编,《女子月刊》为了获得稳定的高质量稿源,还聘请了一批特约编辑,[4]方晨[5]特别统计了特约编辑的性别,男女几乎持平(41 : 40);《女子月刊》第1卷7月号黄心勉又发表了特约撰稿人名单,[6]包括谢冰心、赵清阁等35位女士,萧百新、孙昌树等23位男士,这表明,《女子月刊》的编辑及作者,女性比例几乎占了一半。原《妇女杂志》编辑金仲华也曾肯定《女子月刊》,“《女子月刊》的编者似乎希望使这月刊成为一纯粹的妇女刊物,……还要有多数的妇女来执笔,我希望……这计划能够得到良好的成功。……究竟,谁能比妇女本身更知道她的一性的需要呢?”[7]
《女子月刊》的内容栏目,也借鉴承继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发行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妇女杂志》(1915—1931),内容主要涉及“妇女问题”“妇女生活”“妇女常识”“妇女文艺”四大板块,只是栏目设置名称变化频繁,但万变不离其宗。创刊初期,“妇女问题”和“妇女常识”辐射的内容都是以“讲座”的形式出现。如妇女问题讲座、恋爱问题讲座、女子体育讲座、女子卫生讲座、女子实业讲座、女子工艺讲座。赵蓓红认为,五四时期将“讲座”这种西方大学教育的方式引入报刊界,一方面呼应了当时男女高等教育平等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一教育的“新”式和“西”式,得以满足五四报刊精英们与西方接轨的愿望,保持线性时间的追求和革新的渴望,[8]《女子月刊》突出“讲座”也是此理。“妇女文艺”则根据文学作品的体裁,细化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艺理论”“小品”“诗歌”等,刊登了大量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陈爰任主编时期,期刊还增加“女性的呐喊”和“生活记述”,为女性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平台。《女子月刊》也多次征集主题征文,它涉及编者、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也是妇女期刊设置议题、唤醒女性解放的一种方式。如1933年第5期《理想的爱人》,1933年第7期《我的烦闷》,1933年第8期《假如我有了爱人》,1934年第2期《自我的表白》,1934年第3期《女性的自觉》,1936年第3期《过去三年的我》《未来三年我应该怎样生活》。此后,《女子月刊》还将“女子常识”扩容细化为“时代知识”“百科学问”“应用技术”三栏,以适应时代,帮助妇女们增长学识。
《女子月刊》初期为32开本,后改为16开本,黄心勉主编时期每期少则160多页,多达200多页,内容丰富,视野广阔,始终关注妇女运动发展动态与方向,女性如何实现真正自我解放,在兼顾思想深度和内容广度的基础上具有严肃的“启蒙”姿态,发行量高达万余册,行销境内外40多个城市,这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不多见的。郭汾阳先生所著《女界旧踪》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写道:“那时中国妇女刊物,是三面大旗:‘商务’的《妇女杂志》、‘生活书店’的《妇女生活》,再就是‘女子书店’的《女子月刊》。”由此可见,《女子月刊》在当时的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三、《女子月刊》研究现状与学术梳理
关于《女子月刊》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发现以《女子月刊》为研究中心的学术专著。诸多以女性期刊史为研究中心的论文大多提及了《女子月刊》,如李晓红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选取《女子月刊》作为30年代女性传媒的样本,通过分析其编辑群和撰稿人的组成和变动,揭示了女性报刊活动中隐蔽的“男性之手”,女性被代言和失语的现象常有发生。赵蓓红博士论文《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中,以“纯女性报刊”为题,对《女子月刊》创刊宗旨、主编立场、栏目内容及经营策略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女子月刊》在整个女性媒介发展中的坐标与地位。
数篇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女子月刊》,从某个角度切入,以《女子月刊》作为个案来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如方晨以《女子月刊》为中心分析了30年代都市女性问题,张淑贤则通过《女子月刊》聚焦民国时期女性婚姻观念的演变过程。孟雪欢关注《女子月刊》中的职业问题,王双双分析了《女子月刊》的救国思想,隋明照选取了《女子月刊》中女性爱国救国的社会动员作为研究对象,王虹婷则着重研究《女子月刊》与女性主义表达问题。
日本骏和台大学前山加奈子教授《围绕 〈女子月刊〉—1930年代的中国的女性主义》,详细梳理了《女子月刊》几位主创的生平经历,来探索期刊的立场倾向。黄江军《觉悟女性的自我书写:以1930年代的〈女子月刊〉为中心》,以期刊《过去三年的我》主题征文为分析中心,梳理十二位女性作者的基本情况,描绘了当时觉悟的女性是如何认同并表述自我的。汪炜伟以《女子月刊》为中心,分析20世纪30年代女性报刊对乡村妇女问题的诊断与求解。林英关注《女子月刊》中的女权论述,她认为这种女权是基于“爱国救国”前提下的“女权”,更关注女性的声音及女性本身的“自觉”,并对女性有了“家庭”及“社会”角色的双重期待。他们的研究,回归《女子月刊》的内容与血肉,通过一个个研究的向度,我们可以拼凑出《女子月刊》展现的30年代女性生活的丰富图景。
此外,还有黎德亮的《姚名达研究》谈及《女子月刊》,对其创刊背景、刊物定位和栏目特色均有简略提及,对《女子月刊》本身内容关注不多。徐柏容的《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黄心勉:三十年代女编辑出版家》同样是从《女子月刊》的创刊背景、刊物经营发行、创刊过程的曲折艰辛而言,肯定了《女子月刊》在当时传播价值和历史意义,对开启女智,推动妇女解放有所贡献。杨联芬在《解放的困厄与反思——以20世纪上半期知识女性的经验与表达为对象》中,把黄心勉作为一个兼挑“家庭”和“事业”的知识女性进行个案分析,频繁的生育,繁杂的家务,加上超负荷的工作造成了黄心勉的英年早逝,女性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又陷入了职业女性两难的人生困境。李强的《姚名达和〈女子月刊〉的命运》,赵雪芹《首家女子书店的出世和陨灭》此类论文都关注到了创办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女子月刊》的兴衰命运。
因为姚黄两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自发甘愿为女界服务的发心,使得《女子月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发售书店,而先创办女子书店,女子书店的些许盈余又投入到公益性质的女子图书馆、女子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一揽子工程中。他们几千元的积蓄和每月收入,除了维持最低的生活费,都奉献给了女子解放的事业,这使得本来拥有教授优渥薪酬的家庭一贫如洗,为了节省开支,在《女子月刊》的创办初期,他们不曾雇用一个人,“自审查文稿,发出排印,校对,发行,登报,收账,通信,会客,乃至包书,寄书,送书,任何琐事都是我们夫妻俩亲自做”,[1]姚黄夫妇对《女子月刊》的发心和倾其所有的付出,在《女子月刊》中随处可见,编者与读者水乳交融般的沟通和倾诉,构建了一个亲密和谐的编者读者关系。
四、《女子月刊》研究拓展及未来展望
综合前文《女子月刊》相关的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媒介史的梳理中,《女子月刊》确实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分析文本,然而,这里的《女子月刊》更多仅仅体现了一个坐标,或者一个符号。关于《女子月刊》的样本独特性和历史珍贵性则语焉不详。诸多的硕士论文,所谓的个案研究,也并非期刊的整体研究,更多是把《女子月刊》作为一个史料库,选取一个问题,进行论证与史料佐证。其他学者文章中提及的《女子月刊》多将其作为历史长河中女性期刊一种,太多的研究指向姚名达和黄心勉,他们的身份、观念、初衷与实践势必导致《女子月刊》与其他女性期刊迥然不同,然而,大多数的论文也只是重复前人不断叙述的史实,从未将二人的烙印与期刊的内容一一印证。大多文章集中分析其创刊宗旨、主编立场、期刊栏目变化、经营策略等期刊外围因素,并未观照到《女子月刊》作为一个女性期刊,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语境,期刊中众声喧哗的珍贵细节,尤其是大量女性自觉发声的文学表达及文字中关于女性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所蕴含的历史独特性和思想价值性。
经历了民国初年及20年代女性解放的社会探讨热潮和观念变革,女子教育的发展与积累,知识女性群体日渐壮大,为女性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作者群也提供了受众群。因此,30年代的女性期刊不再是男性主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再是一个提供诸般女性话题给男性评点的平台,而有更多的女性自觉阅读及写作,为女性发声,为女性代言。
从研究内容上看,《女子月刊》中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探讨的重要内容。因为主编的频繁更迭,《女子月刊》栏目变化较大,但是关乎女子文学的版块或者作品一以贯之,从未缺席。这与期刊主编的身份背景不无关系。《女子月刊》历任主编均是女子文学的专业人士或者爱好者。发起人黄心勉创刊之前就喜欢“一面读书自修一面练习写文章,期初投稿到各报刊副刊,有时登出,当然增加兴趣,后来《妇女杂志》社找她做文,她做了一篇长文,名叫《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9]1935年陈爰(笔名白冰)任主编,黄心勉曾在刊物上称其“最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天才作家白冰妹 妹”,[10]可见陈爰是文学专业出身,她任主编后,将“妇女文艺”置顶,更名为“文艺领域”,且细分栏目体裁为诗歌、小说、游记、小品、剧本、书信、日记、自述等,开辟了“女学生园地”,发起征文活动。1936年第4卷8月号起,期刊聘请封禾子担任主编,并介绍其“优等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长于文学,著作散见于报章杂志者甚多,嗜学之余,兼好戏剧,复旦剧社历来公演之名剧《委曲求全》《雷雨》,均属女士主演”,因此,封禾子在原来基础上,开辟“戏剧”专栏,并开辟赛金花专辑,从戏剧的角度讨论妓女出身的赛金花的价值。由期刊作者、编辑升任主编的高雪辉更是在“我爱什么”的征文中,奋笔高呼:“还是文艺我最爱”。[11]《女子月刊》对于女性作家的推崇和关注更是近乎偏爱。有读者给刊物写信反映“刊物所刊照片太少,尤其美女照片太少”,与同期摩登女性期刊的女性照片的“满天飞”相比,《女子月刊》确实对“野鸡式的舞女和电影明星、小姐们的玉照”不屑一顾,偶尔的几页黑白图像版面都贡献给了女作家。如1933年第1卷第6期,刊登了四位女作家的素雅的头像照片,分别配文:“搁笔有余的冰心,生死未明的丁玲,继续创作的庐隐,病入膏肓的白薇。”此外,《女子月刊》还集聚了如高晓兰、陈碧云、段英、冯沅君、冰心、陆晶清、赵清阁、金光楣等四十多位女性作者或编辑,这使得一直作为“历史的盲点”而存在的中国女性不仅“浮出了历史的地表”,还登上了“女性文化的大舞台”。余蔷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19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及其文学史命运》多次提到《女子月刊》中的女性诗人及诗作,作者认为,“在今天看来已经难以数计的‘无名’女诗人,是一群基于女人的眼界和心性在迎面而来的时代潮流的边缘顾影自怜的自我抒写者。她们默默无闻,仿佛安于且乐于在自我的诗园里耕耘,安于用另一只眼看自己的世界”。《女子月刊》中大量的女性文学创作标志着女性思想解放诉诸笔端的实践与表达,女性如何用文学来建构自身,如何以文学来关怀现实,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发现。
从研究视角上看,上文的学术研究主要从女性媒介的角度展开。一方面,放眼30年代的文化出版业,从文学制度的视角来研究《女子月刊》,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及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全部关联起来,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女性期刊传播方式下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姚名达围绕《女子月刊》、女子书店所设计的女子图书出版、社员招募、女子图书馆、女子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一系列女子实业系统化工程,“人办杂志”的美好愿景终究抵不过“杂志办人”的传播原则和市场运行机制。姚名达为女子解放谋划的系统化工程的理想落空,究其原因,除了时局动荡等外部因素,在一个需要深谙文学传播市场变化的场域里追求一种不计经济利益的初衷和坚守,或许这也是知识分子办报的局限和宿命。
从研究方法上看,诸多文章对女性期刊个案研究较为普遍,而期刊和期刊的比较研究较少。我们在研究《女子月刊》的同时,可以类比同时期的女性时尚摩登杂志和党派运动刊物等,从而可以窥见期刊的立场观念。比如,1933年到1937年,社会上对于“贤妻良母”“妇女回家”一直争论不休。1935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第2期发表文章《新贤妻良母主义论》,作者志敏指出“‘贤妻良母,实在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也就是女子教育唯一的目标”。虽然作者在文章中解释,“贤妻良母”并非复古主义,而是新时代的“贤妻良母”,但作者强化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和责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篇文章再次将1933年以来就争议不断的“妇女回家”问题又一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新贤妻良母”的说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妇女界、文化界、政界等人士都纷纷参与其中。《女子月刊》在1934年第2卷第10期、第11期连续发文《娜拉何处去》《贤母良妻》《贤母良妻主义》等文章,斥责“贤母良妻”是性别不平等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麻醉剂,《女子月刊》鼓励妇女们勇敢步入社会,寻求职业和经济独立。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的激进派妇女报刊,更是旗帜鲜明地痛斥一切形式的“新贤妻良母”论、“妇女回家”论,如《妇女生活》先后发表《娜拉三态》《妇女回到家庭中去吗?》《从厨房里走出来》《良妻贤母教育的嘲讽》等文章鼓励妇女做“贤妻”做“良母”之前先做一个“人”,勇敢走出家庭,争做“社会人”,投入到民族国家解放的洪流中。
正如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所言:“唯有精芜并存的报章所刊载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诗文,都成为在‘众声喧哗’中存在的开放文本,从而带给阅读者立体回声的感受。”[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拓展研究的内容、视角及方法,通过《女子月刊》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场域,聚焦女性的文学表达,窥见女性的自我建构与现实境遇,剖析女性文学对解放的召唤和现实情怀,凸显《女子月刊》的启蒙立场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