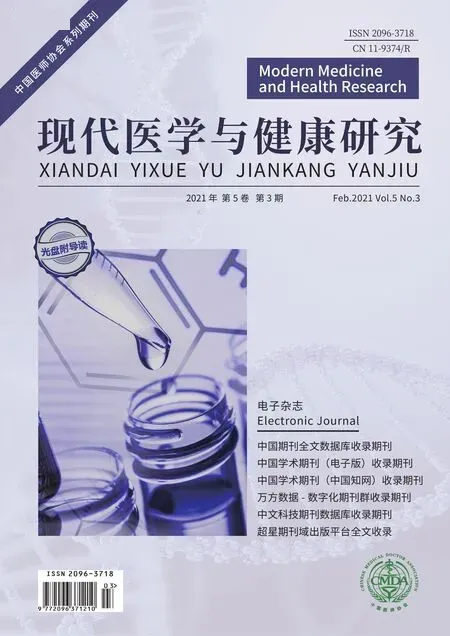纤维蛋白原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王义华,刘胜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外科,重庆 400016)
乳腺对于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影响不大,原味乳腺癌并不具有致命性,但因丧失细胞活性,乳腺癌细胞之间连接松散,容易脱落,癌细胞一旦脱落,在游离状态下可由血液或淋巴液转移至全身,构成生命威胁。目前,乳腺癌是女性患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占比约为1/4,致死率也较高[1]。新辅助化疗已成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降低肿瘤分期、增加保乳率,并监测肿瘤对化疗方案的敏感度,但目前新辅助化疗的缺陷也很多,部分患者在接受化疗后的疗效并不确切。因此研究新型生物标志物的队伍开始壮大,其以寻找预测新辅助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因子、探索潜在的肿瘤治疗靶标及发现肿瘤异质性机制为目标。有研究显示,肿瘤患者存在血液高凝风险,凝血系统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密切相关,而纤维蛋白原作为关键的凝血因子参与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及血管生成的过程[2]。本研究查证相关参考文献,从纤维蛋白原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关系入手进行综述,以期评估血浆纤维蛋白原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中的价值和潜在可能。
1 纤维蛋白原的结构和功能
1.1 纤维蛋白原结构 纤维蛋白原属于一种共价二聚体,其由两个完全相同的亚基组成,每个亚基由3条非等同的多肽链(α、β和γ链)通过二硫键连接而成,呈两侧对称性排列,其分子量为340 KDa,共包含了2 964个氨基酸,其主要在肝细胞内合成并分泌,正常血浆含量为2~4g/L,是人体血液中含量最多的凝血因子,其半衰期为96~144 h[3]。
1.2 纤维蛋白原功能 作为凝血酶和纤溶酶的底物,纤维蛋白原在凝血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可调控炎症与肿瘤发展的关系。凝血系统激活后,凝血酶原经由内源性或外源性凝血途径活化并作用于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原分解成两个单体,分别为纤维蛋白单体Ⅰ和单体Ⅱ,在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的相互作用下,纤维蛋白原可促进血管生成[4]。纤维蛋白在相互交联中形成可溶性网络结构,包裹血小板等血液成分,形成血栓。纤维蛋白原作为一种急性反应蛋白,在机体发生创伤、炎症、妊娠时,其水平显著升高,其在白介素-6和白介素-1β在两种炎性因子的刺激作用下,通过JAK/STAT途径介导,参与急性期炎症反应[5]。此外,纤维蛋白原还参与细胞的增殖、黏附和分化,其可促进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加强黏附。在凝血酶的作用下,纤维蛋白原包绕肿瘤细胞,而肿瘤细胞将血小板聚集起来并形成血栓,进而形成物理屏障对肿瘤细胞进行保护,可避免受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的攻击,发挥保护机体固有免疫的作用。由此可见,纤维蛋白原与血小板之间具有双向影响作用,进而可保护肿瘤细胞。
2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新辅助化疗是在实施局部手术之前进行的全身化疗,其已成为乳腺癌患者进行综合治疗的关键,广泛应用于局部晚期患者。新辅助化疗可使临床分期降低,并杀灭全身转移病灶,提高病灶切除率及乳房保留率,其还可用于评估肿瘤对化疗方案的敏感性。
2.1 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衡量指标 评估化疗反应不仅可预测患者存活率,还可指导后续治疗。乳腺癌从临床和病理反应两方面对新辅助化疗进行评估,其中临床反应主要评估腋窝淋巴结变化情况测量时间点在新辅助化疗前与术前具体可分为病理完全缓解(pCR)、部分病理反应(pPR)、临床完全缓解(CR)、临床部分缓解(PR)、临床进展(PD)和临床稳定(SD)。病理反应的评估常用的是MillerPayne(MP)分级系统,参考化疗前穿刺活检组织和乳房切除标本之间肿瘤细胞的减少量进行评估具体可分为:肿瘤细胞无明显减少为1级,肿瘤细胞减少30%以下为2级,肿瘤细胞减少30~90%为3级,肿瘤细胞减少90%以上为4级,无浸润性细胞残留为5级;其中1~4级归为pPR,5级归为pCR[6]。pCR是指术后乳腺组织中无恶性肿瘤的组织学存在,或仅存原位癌成分,而淋巴结转移性病变消失不见,其与改善生存结果联系密切,可评估个体患者长期预后效果,而实现pCR主要由癌症的分子类型决定。因此可以说,pCR的预测有效性是可变的,具体如何由肿瘤免疫组化类型决定。
2.2 新辅助化疗的药物选择 当前,新辅助化疗的方案并无确切的标准,较为常用的是蒽环联合紫杉类药物治疗。其中蒽环类药物多用多柔比星和表阿霉素等,紫杉类药物多用多西紫杉醇或紫杉醇。另外,上述药物通常需与环磷酰胺、氟尿嘧啶等细胞毒性药物联合使用。研究显示,该方案用于新辅助化疗可使pCR率显著提高,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也因此得到改善[7]。新辅助化疗与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息息相关,寻找预测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有助于开展乳腺癌个体化治疗和增强疗效。
3 纤维蛋白原与乳腺癌的关系
3.1 纤维蛋白原与恶性肿瘤 纤维蛋白原是一种由肝细胞合成并分泌,且具有凝血功能的蛋白质,其参与凝血和止血过程,是血浆中含量最高的凝血因子,因而高纤维蛋白原水平通常表示血液的高凝状态,其是各种血栓类疾病的危险因素,在临床中可被视作疾病状态的标志物。黄冬连[8]研究显示,纤维蛋白原不仅参与凝血过程,其水平高低与恶性肿瘤的侵袭、转移也具有相关性,与肿瘤侵袭、转移的潜能呈正相关。纤维蛋白原与降解产物纤维蛋白通过包绕肿瘤细胞可将多种类型的细胞和生长因子聚集起来,作为肿瘤和上皮细胞之间的桥梁,同时也作为肿瘤基质的骨架,纤维蛋白原可促进肿瘤的浸润转移。在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血管内皮钙黏蛋白与纤维蛋白原β链的交联作用下,有助于增强内皮细胞的增殖、血管生成及白细胞渗出,血管内皮通透性也相应增加,有助于促进乳腺癌细胞通过内皮间隙转移。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在术前升高意味着癌细胞发生转移,其中较高水平的纤维蛋白原与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均存在密切关联。肿瘤患者的高纤维蛋白原水平还可反映机体凝血系统的亢进,提示机体血液存在高凝状态,易发生血栓。此外,王玉婷等[9]研究显示,若恶性肿瘤患者同时伴有血栓类疾病,则其预后效果通常来说更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纤维蛋白原水平与恶性肿瘤的预后相关性。
3.2 纤维蛋白原与乳腺癌 在一项包含2 073例乳腺癌患者的大型回顾性研究中,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于术前升高与接受手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明显相关性,可单独作为总体生存率的预测指标[10]。另一项临床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研究人员对520例连续的乳腺癌病例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血浆纤维蛋白远水平于治疗前升高预示着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较短[11]。任晖等[12]研究显示,微核糖核酸(miRNAs)调控下游靶基因和靶蛋白表达是导致乳腺癌发病的主要原因,其中miR-1246通过定向调控下游靶基因细胞周期蛋白G2(CCNG2)表达可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与黏附,乳腺癌化疗抵抗的形成与其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下,纤维蛋白原可由肝细胞合成,其还可由乳腺癌细胞自源性生成,并参与到乳腺癌的增殖的转移过程中。肿瘤细胞具有良好的促凝血作用,大量纤维蛋白原在肿瘤细胞附近聚集,后转化为纤维蛋白,参与到肿瘤的血管生成与基质形成中。李颖等[13]研究表明,纤维蛋白从两方面参与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一是纤维蛋白可为肿瘤血管的形成提供支架支撑,二是周围的纤维蛋白可对癌细胞进行保护。当癌细胞出现转移现象时,在纤溶酶的作用下,纤维蛋白可发生溶解,进而引发癌细胞扩散。除乳腺癌以外,关于纤维蛋白原与其他恶性肿瘤侵袭转移相关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数,胥芸芸等[14]研究证实,肾细胞癌的淋巴转移及临床分期与高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有关,尤其是术前纤维蛋白原水平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此外,研究表明,机体在恶性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免疫应激反应,炎性因子大量产生,凝血功能出现障碍,形成血栓[15]。并且,转化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可将机体凝血系统激活,加快血栓的形成速度[16]。KVOLIK等[17]研究认为,恶性肿瘤进展的重要机制与凝血激活、血管外蛋白水解活化及纤维蛋白原等急性相蛋白的活化与释放等过程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纤维蛋白原及其分解物参与细胞增殖、血管形成、血管损伤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基本可证实纤维蛋白原可通过调节血小板活性、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恶性肿瘤进展[18]。在肿瘤环境下,对于促进肿瘤生长过程而言,纤维蛋白原与纤溶酶原具有重要意义,其可促使恶性肿瘤加快转移。另外,纤维蛋白原还可使血小板与肿瘤细胞加强黏附,形成血小板-纤维蛋白原-肿瘤细胞聚集物;反过来,血小板也可通过凝血酶系统将更多的纤维蛋白原转化成纤维蛋白,并将其凝集到肿瘤细胞表面;在纤维蛋白原与血小板的相互促进下,肿瘤细胞可避免自然杀伤细胞细胞的毒害。通过体外细胞模型可发现,高纤维蛋白原水平可促使波形蛋白上调、上皮钙依赖性蛋白下调,促进上皮细胞转化为间质细胞,使肿瘤细胞的侵袭性与粘附性得到增强。可以说,乳腺癌作为一种富含血管的恶性肿瘤,其与高表达的纤维蛋白原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4 纤维蛋白原和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在实施新辅助化疗前检查中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凝血系统,发现部分患者存在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的现象,而该现象在实施化疗后得到明显改善。一项研究对正常乳腺、乳腺良性肿瘤及乳腺癌组织中纤维蛋白原表达情况分别进行检测后发现,纤维蛋白原的表达仅发生在乳腺癌细胞外的连接组织中,而不参与局部凝血过程,该研究认为纤维蛋白原可维持乳腺癌结构的完整性,术前的纤维蛋白原可作为乳腺癌细胞迅速增殖的生物标记物[19]。李思佳[20]纳入了200例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其研究结果显示,若患者在实施化疗后纤维蛋白原水平降低则更易达到pCR,若患者在实施化疗后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则说明其无病生存期更短,但在总生存期上无明显差异。因此可以说,新辅助化疗前纤维蛋白原检测对乳腺癌预后评估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5 小结与展望
纤维蛋白原在血液凝固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其分子结构发生改变时,可影响凝血功能,当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高于正常范围时,将成为血栓性疾患的致病因素。而乳腺癌患者存在血液高凝风险,纤维蛋白原与乳腺癌的浸润、转移及预后等联系密切,治疗前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的癌症患者,其预后效果相对更差,死亡风险更高。接受新辅助化疗后纤维蛋白原水平下降的患者虽然可获得较为确切的治疗效果,但治疗前纤维蛋白原水平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关系尚无定论,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