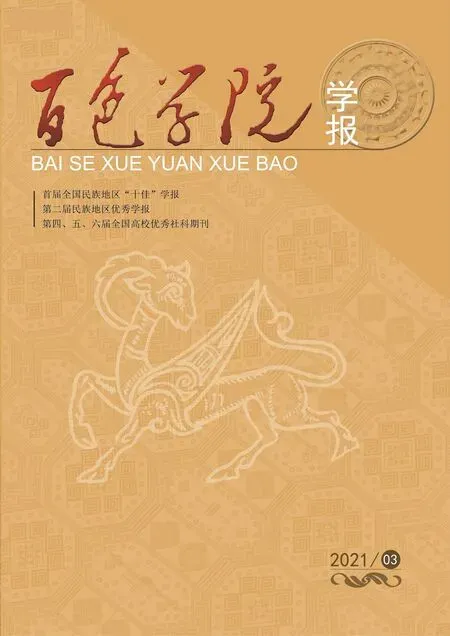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与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1949—1966)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引 言
晚清民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及本土变革的推动下,文学承担起唤起人心、改造国民乃至塑建国家之责。[1]“五四”时期,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强调,民间文学“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2]渐为知识人所重,尤其是1919 年兴起的“到民间去”,参与者意识到民间文艺在发动民众革命意识中的特殊作用。1927—1936 年的民间文学运动①指的是从1927 年中山大学出版《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成立民俗学会始,至抗日前夕,即1927 至1937 国统区的民间文学研究。当时在国统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文化战线上日趋分野,各阶级、各阶层因参与斗争的需要,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民间文学运动也以新的姿态、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文化界。参见蔡铁民:《对1927—1936 年民间文学运动的考察》,《民间文学论坛》1983 年第 1 期。除了理论探索外,注重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民间文艺在革命运动中的独特意义;另外就是这一时期对瑶、苗、黎等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进行了调查,还辑录出版了藏族民间故事、壮族谜语等。②如20 世纪30 年代对我国西南、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民间文艺在“文艺为人民”这一权威话语架构下呈现出新的革命样态③革命民间文艺成为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特性逐渐向“人民性”靠拢。参见毛巧晖:《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1942 年—1966年革命民间文艺对人民性的凝铸》,《华中学术》2020 年第2 期。;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包含的民族、语言、传统与时代的“文化同一性”正在被创制④如1946 年9 月22 日至24 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王贵与李香香——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原名《红旗插在死羊湾》),运用民歌“顺天游”(信天游)的形式写三边民间革命故事。。1949 年以后,文学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其文艺以口传为主,这样新中国初期的多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首先从民间文艺领域兴起。
二、“民族”与“民间”: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滥觞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 世纪30 年代。①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 年第1 期;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 年4 月号;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 年第6 期。日文中“民族”一词受汉学影响出现,在日译西方著作中对应了volk、ethnos、nation 等,这些著作中nation 等词的定义及其相关研究,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1899 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②梁启超以“饮冰室主人”为笔名发表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9 期,第129-140 页;《新民丛报》1902 年第11 期,第110-127 页。全文后又予1904 年发表于《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960-974 页。一文中,称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3]中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 年,他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所用笔名为“中国之新民”,暗合其办刊宗旨“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③《新民丛报》1902 年创刊号上发表告白,阐述其办报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持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德育之本原。”此文在“中国民族”概念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中华民族”④“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 页。一词。1905 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提出中国民族的“混成”[4](P2)。1907 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5](P212-396)中沿袭了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之概念,且较为清晰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同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中华民国解》[6]一文,在梁、杨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之空模”之论。1912 年1 月5 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并将其运用于政治领域。
20 世纪初期,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不断加强,围绕着“中华民族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 年)⑤《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问世,便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自1904 年第一版刊行至1906 年先后发行六版。1933 年商务印书馆将该书加以句读,易名为《中国古代史》,并列为《大学丛书》(教本)之一,重新出版。1955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根据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三版校订整理,重新刊行于世。参见徐松巍:《夏曾佑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1997 年第3 期。顾颉刚回忆自己十五六岁的时候,“读到这部书仿佛把我的脑筋清洗了一下”,他开始感到传统的中国古代史里有许多不可靠的地方,并萌生了搜集民间传说与神话的想法。参见顾颉刚:《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载贾芝主编:《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487 页。、《共和国教科书 新历史》(1912 年)[7],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8],傅绍曾的《中国民族性之研究》(1929)[9],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10],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11]以及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12]等。20 世纪30 年代,随着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滇缅界务,日久未决,片马江心坡,已非我有,界碑外移,人民外徙”,“西教会已深入普及”,“外洋商品,充塞边市,印洋法币,横行垄断”[13](P1)。为了救亡图存,“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到西南去”的呼声此起彼伏,民族思想亦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生重要转变。如顾颉刚在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之后⑥1937 年9 月至1938 年9 月,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辗转于洮、岷、河、湟等地。,主张废除使用“中国本部”“民族”等带有分裂性意味的词汇,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⑦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第9 期,1939 年2 月13 日;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连载于《前线日报》1939 年3月 14 日第 4 版、1939 年 3 月 15 日第 4 版、1939 年 3 月 16 日第 4 版、1939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1939 年 3 月 19 日第 4 版;1947 年,《西北通讯(南京)》创刊号,第3-7 页刊载《中华民族是一个》,第2 期第1-3 页刊载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也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⑧如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鲁格夫尔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何轩举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性》、黄举安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其中,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14]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质疑,亦为他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奠定了基础。⑨这一时期的论争一方面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持不同意见。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 年第3 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主张中国“多民族”发展的观点并存。⑩如1941 年张大东在《中华民族发展大纲》一书中提到“中华民族”之说,“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另一派主张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参见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重庆: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1941 年,第21-22页。转引自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4 期。1939 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即为“中华民族”,明确提出中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且都拥有“长久的历史”。[15](P1)1942 年,《讲话》①《讲话》最初是1942 年5 月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口头发言时的速记稿,1943 年10 月在《解放日报》的第一次公开发表,被称为“四三年版本”。1953 年毛泽东进行了修定,将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参见毛巧晖:《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发表之后,开启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的新阶段②如搜集过近千首中国西北部的信天游民歌的诗人李季曾经谈到,毛泽东《讲话》推动了他去做这个工作。李季:《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载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1 年版,第128 页。。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创立③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提到“培养抗战艺术工作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参见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第50 册,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 页。之后,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歌曲调、民间戏曲、民间木刻等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培养了一批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的优秀人才。④如胡奇(回族)、穆青(回族)、陆地(壮族)、华山(壮族)、李纳(彝族)、思基(土家族)、苗延秀(侗族)等。如:1939年3 月,鲁艺成立了“民歌研究会”,研究会的师生在陕西、甘肃和绥远一带展开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歌。延安是各民族进步青年的“集散之地”。“民歌研究会”的师生还展开了对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歌谣的搜集[16](P106)。据统计,至1942 年底,他们搜集整理陕甘宁边区各县民间歌曲700 余首,还收集了一批蒙古、绥远、山西、河北及江南的民歌,各地数十首至一二百首不等。[17](P437)这一时期其他投身抗日的进步人士,也积极致力于搜集民歌,包括内蒙古、绥远一带的少数民族民歌,希冀建立中华民族的新音乐,如《蒙古歌曲集》《绥远民歌集》等⑤陶今也译:《蒙古歌曲集》,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 年版;李凌编:《绥远民歌集》,桂林:立体出版社1943 年版。。延安时期的文艺可以说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新版图的初步描绘。⑥具体参见毛巧晖:《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1942 年—1966 年革命民间文艺对人民性的凝铸》,《华中学术》2020 年第2 期。1945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写的《文教工作的新方向》中刊载了《蒙古民族文化座谈会》,此文谈到蒙古族同学在学习之余,开始学习秧歌的形式和表演技巧,采用蒙古民歌编出了蒙古戏剧《赶会》,其后又陆续编出了《找八路军去》《到好地方去》和《反抗》等蒙古歌剧,在“三段地、盐池、定边等地的骏马会上表演”;另外,延安还设有成吉思汗纪念堂,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18](P20-21)
1949 年7 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19]的报告,该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间创作的政策,并强调艺术作品与民族传统、民间创作之间的联系。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⑦1987 年5 月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该组织首任主席郭沫若,周扬、钟敬文、冯元蔚、冯骥才为历任主席,现任主席潘鲁生。。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⑧“民研会”成立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该刊1950 年至1951 年不定期出了三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文艺物刊,所刊文章兼顾民间文学理论与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目录引自毛巧晖:《民研会:1949—1966 年民间文艺学重构的导引与规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发表了大量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作品及相关研究论文。如安波的《谈蒙古语民歌》、马可的《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通信)》与《马头琴及其他》、赵沨的《云南的山歌》、许直的《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乔谷的《西康藏民的音乐生活》、波浪的《苗家的跳舞与音乐》等;《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中专设“朝鲜民间文艺选辑”栏目,收录《人鬼的故事》《爱穷苦的女人》《国王的耳朵》《大同江水为什么是绿的》等作品。《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亦设“藏族民间文艺特辑”,收录《藏族歌谣选》(27 首)、《藏族故事选》《藏族谚语录》等藏族民间文艺作品。
从20 世纪初期“民族”概念的讨论到1942 年《讲话》发表,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初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被纳入到“一个现代方案的历史框架中重新予以定位和解说”[20],围绕搜集、整理及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成为“在国家学术行为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21]
三、“以文入史”: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特征
1949 年之后,在借鉴苏联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20 世纪40 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除了延安时期的文学经验支撑外,亦广泛吸纳苏联的文艺理论。①仅从1949 年10 月到1958 年12 月,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 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 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之多。参见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 年第5 期。这一时期,《苏联文艺问题》《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苏联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方向》《苏联文学史》《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苏联文学小史》《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等译著陆续出版。②新华书店编辑:《苏联文艺问题》,上海:新华书店1949 年版;[苏]日丹诺夫:《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葆荃、梁香译,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 年版;[俄]法捷耶夫,等:《苏联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王子野译,北京:新华书店1950 年版;金人辑译:《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方向》,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50 年版;[苏]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曹葆华、徐云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苏]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水夫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江树峰编著:《苏联文学小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苏]索柯洛娃,等:《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刘锡诚,马昌仪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
我国很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文学以口传为主,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迅速发展[22],逐渐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体化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23](P167)。1951年,建业书局出版《少数民族文艺论集》[24],收录了费孝通、严立、孜牙萨买提、钟华、力文、郭基成、辛弘、杨放等人的文章,并将《阿那尔汉》(故事诗)③费孝通:《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严立:《开展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孜牙萨买提:《新疆各民族的文艺》,钟华:《贵州苗族的民歌》,力文:《藏民歌唱毛主席》,郭基成,李耀先整理:《锡伯族的文艺活动》,辛弘:《黎族的文艺》,杨放:《圭山撒尼族底叙事诗〈阿诗玛〉》等。作为书后附录,在篇目编排上呈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25]张寿康在《论研究少数民族文艺的方向(代序)》中提出“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后,他以苏联多民族文学的论述为理论依据,通过1950 年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的“题词册”,以及1951 年5 月20 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读者来信栏刊出的两封“希望出版界、文艺刊物注意介绍少数民族的文艺”的来信,进一步阐述了“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没有看见群众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分的一部分”。[26](序言)如当时出版的研究新文学史的著作④如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新建设杂志社1951 年版;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年版;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依旧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文艺。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有学者关注到各民族文学史的编纂问题。
在《1956—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说明”中明确提出当前研究工作的总的任务是,“运用正确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整理我国的科学文化遗产”。[27](P1)其中,“文学”学科的重要问题第二条“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的研究”第七点“各少数民族现代创作的成就”、第八点“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第三条“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及民间文学的研究”第七点“各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研究”、第八点“民间文学的研究”的提出,使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上升为一种“国家文化行为”。[28](P28-29)1953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亦为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提供了契机。⑤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儿》等,之后编成《大凉山彝族长诗选》《大凉山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入30 个民族121 篇故事,第二集中收入31 个民族的125 篇故事。1956 年2 月,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发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强调“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者。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29]此报告中提出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兄弟民族文学”之计划实为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之先声。1956 年3 月在昆明召开了云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发展民族民间文艺问题”。[29]1956 年4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 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研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⑥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孙剑冰、青林,民研会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此外,另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8 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分赴各地调查。从1956 年8 月到1964 年6 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整理资料340 多种,2900 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 多种,1500 多万字。[30](P124)在调查中,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由于“保留了大量的有关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民族战争与迁徙、民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31](P113),它们作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补充,以“民间信史”的面貌出现。
1958 年,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抢救、搜集、发掘、整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高潮。同年7 月1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提出“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提到:准备先编写“中国文学简史”,后出版“详史”。书中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部分,主要由“各民族自治区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省份负责编写。其中特别注明:凡是不能写出文学发展史的民族,均写“文学概况”。[32](P1)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任务由中共中央直接提出,这就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赋予其“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新内涵。[33]各民族文学史的编纂既是一次对已整合、写定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进行新的“历史的、科学的、系统的、纵与横的评介”,又是对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的“理性的认定”。[31](P130)经过几年的努力,截至1961 年“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夕,共有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等15 个少数民族完成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纂。①见《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1984 年,第4-5 页。已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有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著:《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编著:《白族文学史(初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青海民族学院中文专科编:《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等等。
四、“多元交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范式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民族理论的借鉴到1953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再到1958 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逐步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并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工程的具体体现。[34]
1951 年,何愈在其著作《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一书中提到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所有各民族文化实际上的成果,不问它们是多么古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非常珍贵它们的。这些成果现在在其本民族及苏联一切民族之前,已经成了一种再生的东西,表现出实际的思想的光芒。”此书根据语言将西南少数民族分为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后者又分为“藏缅、洞台、苗瑶”3 个语族。书内介绍的13 个民族,便是根据3 个语族分别排列。[35](P6)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即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民间文艺研究”,其后改称为“人民口头创作”②教育部高校文科教学计划中所定的名称。。为满足教学需要,1951 年4 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36],收录《原始文学的意义》《口头文学底基本形式》《对于民间文艺一些基本的认识》《论中国民歌》《从音乐观点上来看民歌》等十数篇论文,并将闻一多的《西南采风叙录》、曹靖华的《魔戒指序》、周立波的《民间故事小引》作为附录。1952 年前后,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人民口头创作教研室,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1959 年谭达先在其著作《民间文学散论》“序言”[37](P5)中自述,书末所附的一些例子,有一部分即出自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口头创作教研室的油印参考资料。③据许钰《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文中回忆:从1953 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到1958 年期间,不断有兄弟院校教师前来进修,在这些进修教师中,汪玢玲和第一批研究生一起学习了两年,其他进修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时间有长有短,来的时间也不一律,这些先后到来的同志有:谭达先、申文凯、何奇雄、梁宗亨、崔玉蓉、晓星、马名超、邵海青、陈国珩等。参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6-348 页。1954 年东方书店出版的“人民口头创作丛书”《苏联口头文学概论》[38]《苏联人民创作引论》[39],成为他们及当时学术界民间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苏联口头文学概论》是当时唯一以口头文学命名的著作,同时也是学界重要的理论参考书籍。[40]钟敬文在1953 年11 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搜集、发扬人民固有的优秀艺术,已经成了政府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全国高等学校里中文系的学生大都在修习着人民口头创作的功课”。各类文艺刊物或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也经常刊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及其相关研究。①当时除《民间文学》外,《人民文学》《诗刊》等也时有刊发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相关研究则有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论彝族史诗〈梅葛〉》,《文学评论》1959 年第6 期;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蒙族史诗〈格斯尔传〉简论》,《文学评论》1960 年第6 期;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文学评论》1961 年第4 期;袁家骅:《少数民族人民口头创作中的语言问题(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民间文学》1961 年第5 期;等等。“有些著名的民族口头文学(好像牛郎织女、白蛇故事等)更被反复覆地讨论着。”[37](P3)“口头文学”的意义被界定为“人民创作”“人民智慧”,内容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传说、勇士歌、童话、歌曲、谚语、俚语、谜语、歌谣”等。[40](P13-14)
“人民口头创作”理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 年第2 期发表了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初稿)》。该大纲第十一章“兄弟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崭新面貌”中着重介绍了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辉煌成就。如阿细人(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讲述世界起源的民歌集《阿细人之歌》的搜集整理[41],1954 年云南省文化局工作人员共同整理的撒尼人叙事传说《阿诗玛》,西藏、内蒙古搜集整理的史诗《格萨尔》及在苗、壮、白、维吾尔等民族所搜集到的叙事长诗。此外,各少数民族调查组依照“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推动了少数民间文艺资料体系与理论研究的完善与发展。如傣族调查队记录了将近100 篇传说、叙事歌和情歌;哈尼族调查队研究了创世纪的各种传说,以及广泛流传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广泛流传的有关1917 年农民运动的传说和歌谣;白族调查队搜集到几十篇长篇传说和500 多首歌谣。尤其是1958 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开展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文化史的视野,正式参与了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工程的建设。在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价值发现和重构中,“新型民族国家平等政策的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建构、对全体国民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以国家认同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等”[23](P176)多重目的的交融,赋予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参与“新中国文学秩序”建构的“合法性身份”。如1952 年《兄弟民族的赞歌》“引论”部分谈到参加1950 年国庆典礼的各族代表见到毛泽东的激动之情:西康巴安县咱中村的一位老人,将自己珍藏了15 年的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西康时所颁发的“保护喇嘛寺”的布告,请当地人民政府转献给毛主席留作纪念。此书收录的200 首赞歌也是兄弟民族在翻身之后唱出的“切身感受”,是他们感谢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主席的“心声”。他们在歌曲中用了“太阳”“明星”“高山”“大河”等“崇高和美丽的词汇”,以及“祖父”“父亲”“菩萨”“救星”等“尊贵和亲切的称呼”,藉以表达出自己纯真的情感。[42](P9-10)
围绕着各地域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高校、研究机构及地方文艺工作者多采用合作的方式展开调查,并出版了大量作品集和理论译作②楚奇,艺军:《湘西民族兄弟的山歌》,汉口: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樊圃:《西北的少数民族》第一分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年版;如卓编著:《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年版;华恩编:《青海民间歌曲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诗刊社编:《云南兄弟民族民歌百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故事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译作: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民族问题译丛》,北京:民族出版社1956 年版;[苏]查米扬,等:《民族问题、部族、民族、少数民族》,严信民,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6 年版;[苏]克鲁宾斯卡娅,[苏]希捷里尼可夫:《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马昌仪译,陈大维校,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版。。如1960 年5 月到9 月期间,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学校、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和群众艺术馆的人员共同组成的青海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到全省藏族自治州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调查,调查范围包括39 个县、135 个公社,涉及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等7 个民族,共搜集到的新、旧民歌17.7 万多首,民间故事、传说1500 多个,戏曲500 多部以及长篇叙事诗、谚语、谜语和其他文学资料、史料6000 多件。[43]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相关报道亦体现了其作为构建多民族国家文化基础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如《人民日报》对1964 年11 月26 日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开幕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进行了多次报道③如新华社讯:《五十多个民族的业余演员在颐和园联欢歌颂各民族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日报》1964 年12 月4 日第2 版;姜德明:《在兴无灭资的阵地上——记坚持革命文艺活动的张明兴和禹先梅》,《人民日报》1964 年12 月6 日第6 版;郭汾祥:《唱起民族团结的“花儿”》,《人民日报》1964 年12 月8 日第6 版;彦克:《革命的文艺 革命的人——看广东、青海业余演员演出》,《人民日报》1964 年12 月11 日第6 版;张紫晨、吴超、陈建瑜:《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各族新民歌》,《人民月报》1965 年6 月28 日第6 版;高庆琪:《撒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种子——记土族姑娘刁斯让索和祁兴兰从北京回村后》,《人民日报》1965 年 7 月 8 日第 2 版。,特别提到了青海循化县城关公社撒拉族色乙卜演唱的《新循化》①依据民间说唱“巴西古流流”曲调填写而成。。在这场演出中,各少数民族共同描绘和赞颂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各地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歌曲在意涵上有着“同一性”,但它们在曲调及演唱形式上或多或少都与各自的“传统”之间有话语上的衔接。可以说它们是对“从前的文本和习俗在文本生产中的表达方式”[44](P89)的再造或改变,同时又赋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以全新的社会功能。
五、结 语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转型发展及其与世界体系的互动,“民族”“民间”在五四运动及延安文艺运动影响下被赋予全新的现代性意涵。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延续了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新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说1942 年《讲话》奠定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的基础,并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文艺的政治文化功能。1953 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1958 年开启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在人民文学话语中逐步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同时也为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与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