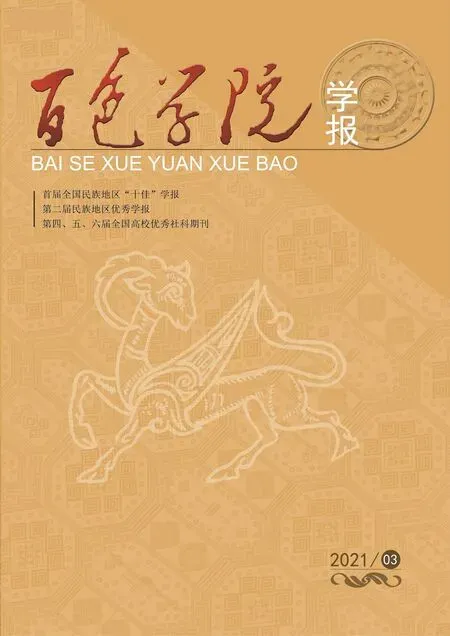理解农民与土地的多重价值
——以重庆D 村土地流转为例
刘建民,王 雨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一、引 言
自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来,耕地流转逐渐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1]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农村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机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反映了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盘活农村经济的关键则在于盘活农村土地。耕地流转,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包装、农机具等发展,加快了产品仓储服务、运输服务等农村服务业的发展;还可破解农产品供求不平衡,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
重庆D 村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西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典型的山地农耕经济类型。水稻、玉米、花生、豆类、优质蔬菜等为主要农作物,农业水稻种植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D 村共有12 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4195 人,共1295 户,耕地面积7688 亩。改革开放前的D 村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之中,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D 村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外出人口占到了村庄总人口的50%左右,主要到贵州、广州、厦门、南宁等地从事建筑业、手工制造业、服务业等。近年来,重庆市D 村作为国家乡村振兴土地流转的试点,率先开展新一轮土地流转工作。由政府出资平整土地,通过土地改造与集中承包,促进土地“宜机化”、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从国家视角出发,土地流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土地大面积抛荒的问题,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依据自家耕地面积,参与分红,提高经济收入。既可以盘活农村经济,实现经济内循环的目标,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达到国家和农民双赢的局面。
但是,从农民视角出发,土地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则不是单纯的经济收入所能替代的。土地之于农民,还具有承载乡土文化、实现自我价值、化解农民风险等作用。D 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同农民具有不用的意见和看法。基于对国家与农民两种立场的观察,笔者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尝试对D 村土地流转及农民观点做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通过理解农民,保障农民利益,更好地促进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
二、理解农民:土地的多重价值彰显
农村土地制度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在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紧张的人地关系。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去考量,提出通过“三权分置”等措施来解决土地效率低、农民利益受损、土地流转困难等问题。这样的提法虽然从经济角度考量具有一定作用,但还应考虑到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收益,其价值彰显具有多元性。对于西部地区农民而言,土地带来的收益较少,土地本身具有一种弱质性,但并非可有可无。相反,由于西部农村缺乏除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支撑,土地对于农民的作用还体现在承载乡土文化、实现自我价值、化解农民风险等方面。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农民作为耕地流转中的决策主体,对耕地流转的顺利进行起着决定性作用。[3]
(一)经济:两种视角下的收益比较
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通过土地流转参与分红是否一定会提高农民收入呢?D 村共有12 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4195 人,共1295 户,耕地面积7688 亩。①数据材料由 D 村会计 ZXR 提供,时间:2021 年 2 月 26 日,地点:D 村村委会。改革开放以来,D 村的年轻劳动力大多选择进城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从而形成了贺雪峰教授所提出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D 村85%以上的年轻人在外务工,老人则在家务农,一个家庭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带来的两份收入。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虽然D 村出现大面积抛荒,但仍旧有50%以上的农民从事着农业劳动。按照农民的算法,其收入远高于参与分红的收入。
个案一:D 村杨牌坊村民小组村民DGQ,男,64 岁。
我年轻时在外打工,2012 年才回来种地。虽然种地的收入没有打工多,但是总比闲着好。我去年挖了(指收成)5000 多斤红薯,自己用机器打磨制作成“红薯粉”,卖了4000 多元。这还只是种红薯的收入,还有谷子(指水稻)的收入将近5000 元,这两个是大头,其他的就是喂点鸡鸭卖钱,一年下来共有1万多元。我种植面积较少,我们村的那几个种粮大户收入更高。这些田土有一些是别人丢荒之后我捡来的,自己家里的没有这么大面积。不过话说回来,村里的种粮大户哪个不是捡的别人的田土,反正都不种,给别人种比丢荒强。②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4 日,访谈对象:DGQ,访谈地点:D 村笔者家中。
个案二: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村民GGL,男,55 岁,种粮大户。
我自己肯定是不愿意丢掉土地的,我这几年每年都种了70 多亩水稻,每年的利润都是好几万,你不要看我在家里种地,不比外面的少挣,还能在家里照顾父母。每年政府的补贴都是好几万③重庆政府将种地面积达50 亩以上的化为“种粮大户”,每年按照所种面积给予补贴。,如果收成好,一年挣个十来万是没有问题的。这几年添置了很多机器,还合资和别人一起买了一台水稻烘干机,以后要是不让种地了,那我肯定亏惨了。分红④村委会在村民大会上承诺村民,每年土地分红的价格为旱地每亩300 元,水田每亩500 元。那点钱是不够用的,哪有我自己种地挣得多。但是国家的政策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是不让我种地了,怕是只有出去打工了,总不能指着这点分红过日子吧。⑤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4 日,访谈对象:GGL,访谈地点:D 村笔者家中。
由此可见,农村始终还有大量的农民依靠土地获得一份收入,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土地在农民手里,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生态的可循环性,农民能实现对土地的最大化利用。一块土地在不同时间可以种植不同农作物,得到不同的收获。这样的“实物性收益”即便没有直接转变成货币,也会对农民的生活形成强有力的补充,可循环的土地利用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综合收入。
个案三: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村民HYX,女,63 岁。
我家里的种植面积虽然不多,但是自己吃足够了,自己的玉米和红薯拿来养点鸡鸭,这些东西就不用去买了。要是没有土地种了,想自己喂点鸡鸭、喂个猪都不行了,还得花这么多钱去买粮食来喂,肯定是不划算的。我们农民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这要是啥子都不让种了,光靠那点补贴,肯定是不够的哟。你去看看,家里有人的,哪家哪户不自己喂点鸡鸭鹅,自己吃也放心,不用花钱买,孩子们回来还能带点回城里。①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2 日,访谈对象:HYX,访谈地点:石灰山村民小组其家中。
基于此,笔者认为土地对于农民的收入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去衡量。一方面,农民依靠土地获得直接性的货币收入;另一方面,农民通过自己种粮种菜、养鸡养鸭,使自己的土地始终处于一种持续利用的状态,基于这样的可循环经济,获得一种稳定的非货币收入,即“实物性收益”。
国家视角下的土地流转是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益,为何与农民的计算相差如此之大呢?笔者认为,首先农民在考虑土地收益的时候,只考虑到参与分红的收入,却没有考虑到土地流转之后自己再就业的收入。土地流转后,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年轻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或者从事其他职业;年老且具有耕作能力的农民可以继续在原有的土地上打工,同样会拿到一份收入。其次,政府的政策宣讲不到位、农民与承包商的合作模式具有不确定性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想法,使农民对土地流转缺乏信心。
(二)土地:化解农民风险的屏障
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业收入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占比越来越小,农民似乎不再依靠土地。尤其是西部农村,由于缺乏农业之外其他产业的进入,土地更具一种弱质性,越来越不值钱。笔者认为,正是西部农村土地功能的单一性,才使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出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家庭更需要获得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只有这样,当一个家庭中的年轻劳动力在城市无法维系的时候,他才可以退回到农村,依靠家中的土地获得“温饱有余”的生活。农村土地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返乡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凸显了出来。
个案:D 村杨牌坊村民小组村民GQS,男,44 岁。
我是2016 年回来的。之前在贵阳工地上打工,跟你刘叔②笔者叔叔LXW,一直在贵阳做工地。一起,后来摔了一跤,很严重,腿里接了钢板,就没办法在外面打工了,只能回老家来。前年我承包了这十几亩地,种植柑橘,去年是头一年,收成不好,柑橘也不甜,加上人工费、秧苗费,不但没挣钱,还搭了几万块。今年收成不错,卖的也好,是能回点本的。但是土地收回去不让种了,那就亏得多了。眼看着刚起步,前期投入了这么多钱和精力,现在亏钱不说,以后能怎么办呢?出去干工地是不可能了,只能在家待着了。③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2 日,访谈对象:GQS,访谈地点:杨牌坊村民小组其果园。
笔者认为,土地对于进城农民工是一种极大的保障,一旦城市生活不如意,他可以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农村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极大的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恰恰是土地让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有了最后的保障,使得进城农民工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与缓冲的空间。土地既是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使农村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正是有了稳定的农业和广阔的农村,使得任何危机都有了回旋的余地。
(三)农业: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场域
赵旭东教授提出,中国农民将社会价值的实现场域限定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之中,通过修建新房,顺利完成人生婚姻礼仪等来彰显自己的社会价值。[4](P182)农民将自己生活的农村社会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场域,是基于生存环境与农业特殊性。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联系密切,知根知底。农民通过修建新房、举办宴席、帮助子女完成婚姻礼仪等实现自我价值,向其他社会成员展现自己的能力,以期获得一种成就感。其次,在西部农村社会,农业生产是多数农民主要的生计方式,农业自然成为农民相互竞争的一个领域。在D 村,农业耕种面积越多的农民,越受到大家的赞许,村民都会认为这样的人是值得称赞的;而对于那些具有劳动能力又好吃懒做的人,多数村民是嗤之以鼻的。
个案:D 村村支书 CY,男,50 岁。
我们村大多数村民还是很勤劳的,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家里以老人为主。我们村的种粮大户在整个镇是比较多的,有12 个。大多数在家的老人就算种植面积达不到这些大户这么多,也还是多多少少要种一点,不然大家会在背后议论,这样传出去不好听。你看你们小组的CLY①CLY,笔者老家所在的村民小组村民。,才40 多岁,年纪轻轻的不出去挣钱,家里的田地也荒着,在家里吃政府低保,这样的人大家都在背后议论,是不受人尊重的。像CLY 这样的人,我们村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了,家里一直是瓦房,去年政府才给他免费修了砖房,为此,村民的意见也很大,都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应该享受政府的福利。②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3 日,访谈对象:村支书CY,访谈地点:D 村村委会。
既然农民生活在农村,那么种地就是自己的职业,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一个年轻劳动力在家里好吃懒做,不勤于耕作,是会被村庄其他社会成员所不齿的。因此,农业就成为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场域,这样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面子”观念和农村传统的舆论压力。再者,农民在农业上的勤劳,也会使自身更有机会获得村中的各种资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变相实现自我价值。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组长GGL 就是一个种粮大户,村民都认为他是一个勤劳踏实的人,愿意选他为村民小组长。在村民中的声望高,更容易在村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
(四)文化:根植于土地中的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对乡土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新要求。保护乡土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多样性。乡土文化根植于土地中,是农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承的乡村而言,在我们当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振兴的话语构建中,应有意识地将文化这一为人所日益觉知到的存在放置在其应有的合适位置上去。[5]
D 村属于典型的西部传统村落,虽然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房屋建筑、饮食及村民生活观念等发生较大变化,但仍保留着诸多文化传统。在D 村的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依旧可以看到诸多传统文化内容,如“打连萧”“车车灯”“吹唢呐”等。这些地方性文化深受村民喜爱,成为各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民在农闲时,通过参与集体性的文化活动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保留下来的诸多传统文化事项,对农民的精神世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农民在农事活动中所创造的一整套农耕文化,也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以来,逐渐发展的农业文明便开始在神州大地上传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便是与农耕文化相伴而生。[6]农业耕种技术、农具的制作和使用、农作物的管理等,都是农民所掌握的独特技能。一旦农民失去土地,这样的农业知识便不再存在,土地对于乡土文化的保留与传承,便在这之中体现了出来。即便是与农业生产不直接相关的农村文化,依旧带有土地的味道,如果失去土地,现有的乡土文化便会失去本真,丢掉其文化内核。
(五)情感:农民对土地的天然依赖
中国的基层社会具有一种乡土性,中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乡下人离不了泥土,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7](P6-7)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农业是获得合法性财富的唯一源泉,以农业为底色的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被赋予正向的价值判断。[4](P21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不再是农民的唯一生计方式,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却依然深厚。在西部农村地区,传统农业生产一直得以维系,没有因为年轻劳动力进城而完全荒废,并产生了许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D 村85%以上的年轻人在外务工,在家务农的以老年人居多,笔者通过访谈发现,不论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还是在家务农的老年人,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土地。
个案一: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村民ZSQ,男,50 岁,工地包工头。
前几年村里修路,我是捐款最多的,一是为村里做点贡献,二是考虑到自己以后退休了还要回来。我家里的田都没有抛荒,这些年一直给我大伯他们家种,收成算他们的,只要不抛荒,等我过些年回来种就方便多了。前年我还自己出钱,修了一条支马路①指农村的泥巴路。,直接修到我那几块田旁边,以后收割就方便多了,你爷爷②笔者爷爷WHS,D 村村民代表。还帮了我很多忙,去协调土地。虽说这些年在外面挣了钱,但是老家还是不能丢的,落叶归根,总得回来的。③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0 日,访谈对象:ZSQ,访谈地点: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其家中。
个案二: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村民WHG,男,74 岁。
我早几年就不种地了,岁数大了身体不允许了,我只有两个女儿,现在政府给我办了低保,基本生活保障是没问题的。反正我也不种地了,土地怎么流转我不太关心,也没什么意见,但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留点旱地。水田有没有倒也无所谓,如果旱地都没了,以后死了都没地方埋④D 村所在的重庆市永川区,农村地区目前普遍实行土葬。,自己有点土地在手里,干点什么都踏实,不用求别人⑤访谈时间:2021 年2 月22 日,访谈对象:WHG,访谈地点:D 村石灰山村民小组其家中。。
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表现得最为直接,也最为基础的,既不能脱离,更不能将之抛弃,特别是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国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5]从D 村不同村民的态度可以看出,农民对于土地仍有深厚的感情,依然将土地看作自己非常重要的资产,且寄予土地深厚的情感依赖。正是这样一种依赖,使中国农民即使通过进城务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也不愿轻易放弃土地,农村的土地依然是他们心里最重要的财富。
三、总结与思考
在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耕地为主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要推动土地流转顺利实施,需要了解农民需求,充分考虑农民诉求,考虑这样的流转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增加农民收入。土地对于农民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作用,还具有化解农民风险、承载乡土文化、实现自我价值、维系农民情感等功能。进城农民工一旦在城市中工作不顺,农村的土地可以为其提供退路,返乡种地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可以成功化解农民工的失业风险。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土地可以很好地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为农民工提供面对危机的回旋空间。乡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土地承载着乡土文化,为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只要农民还在土地上耕种劳作,乡土文化就不会失去本真,其文化因子就会得以延续。村庄是农民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领域。在农民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土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勤劳与否是农村社会评判一个人的基本标准。中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无论是生活在农村或在外务工的人,都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有一种情感依赖,而土地就是这份依赖最好的载体。
土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乡村振兴尝试,存在系统性风险,面对这个系统性风险需要有系统性保障,这其中最先要保障的就是最大的利益受角色——农民。土地流转应该以农民的需求和风险为导向,需要充分考虑农民需求。首先,需要平衡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占比,尽可能为农民争取更多分红;完成土地流转后,政府应积极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推动农民再就业,通过制度性安排,使农民以雇工的形式继续在土地上劳作,发挥农民本领,促进职业农民的产生,实现农民自我价值。其次,政府应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逐步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收入,使进城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再次,在土地流转中,因充分考虑到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通过自留地等形式为农民留下菜地,满足农民的情感需求。最后,政府应积极引导乡村文化发展,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乡村振兴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与繁荣,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流转是一项政策导向型的乡村振兴尝试,具有系统性风险。农民是土地流转的参与主体之一,是土地流转最重要的利益受角色。基于土地对农民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土地流转的实施就必须要首先考虑和保证农民的利益。在具体过程中,需要有系统性的保障,针对性的布置,解决农民的实际需求,才能顺利推进土地流转的实施。
综上所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绝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多重利益诉求及土地在农村的多重价值彰显。从农民视角理解农民,了解农民需求,制定科学政策,合理规划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真正符合农民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