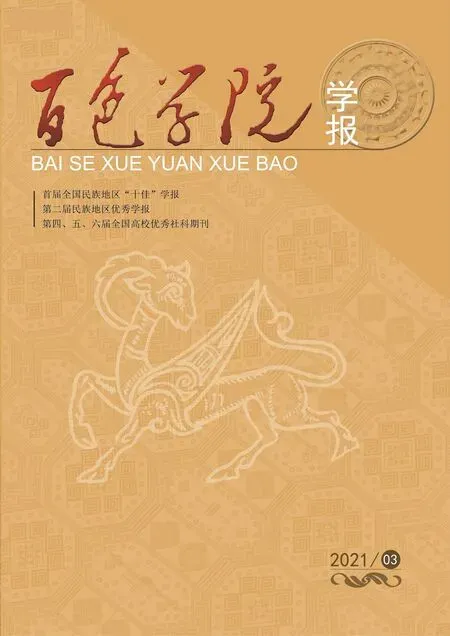中式哲理:土地生长粮食的道理
彭兆荣
(1.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2.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自拉丁语“philosophia”,本义为生命中“爱的智慧”,后被用于解释事物和知识的原因。[1](P235)只是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有些“面目全非”,甚至走到了戴着“理性”作为表述的“假面”。人们似乎已经很难再从“爱情的感性”与“思辨的理性”之间找到什么共相。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和误解,在西方的哲理(哲学-理性)的各种定义中,生命意义、生命价值一直都在,而且一直是主脉络;表现为对“人”的关注,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以人为本”,都在强调“人”的价值;只是,历史的变迁有时将人的生命意义抽象化、“悬空化”。
中西的哲理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都表达了对宇宙生命的认知和智慧。《说文》:“哲,知也。”《尔雅》:“哲,智也。”知者,智也。不同之处在于,中式的“哲理”是从土地生长粮食所获知的关于宇宙生命的道理,并没有将哲理异化成为“理性”束之高阁,恰恰相反,是将哲理“落地”——与土地相结合,“还俗”于民众的生活。笔者以为,认知中式道理,体悟农耕圭臬,便为知者、智者。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中式哲理与西方哲学一样都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式哲理对“人”的关注具体而务实。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没有土地,生命便失去“土壤”。“土地上的生命”是中式哲理的至高原则。然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忘记了这一点。我国现在的人口与土地关系已经逼近“生命底线”。近些年,中央多次重申中国的耕地不得低于18 亿亩——既是中国耕地面积的底线,也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14 亿人/18 亿亩地,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的说法:“一亩三分地”。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中央政府始终把解决好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因为,这是中国的终极哲理、根本事务。
一、田理与王道
如果“哲学”是生命的照相,那么,哲学第一要义是维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人若不能活,哲学也只是遑论。因此,“活着”最重要,而要“活着”,就要吃,果腹于是成为生命的至上表达,即生命的生物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一看周遭的动物,毕生以“吃-找吃”为目标便能省悟“生物生存”的道理。而土地提供粮食,农业为“管吃”的事业。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事业、行业、职业、生业可以替代农业,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基本的果腹需求。如果其他的行业都围绕着“管好”,那么,农业则属于“管饱”。人类自然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只有先“饱”,才能谈“好”。饥肠辘辘的哲学家注定谈不起“理想”“主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早已从管仲的箴言变成了百姓的口语。看一看身边的日常事务,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食物都来自于“农业”;而农业之重于又依赖土地,有土地才能生长粮食,因此,说中式哲理是“土地生长粮食的道理”大抵属于哲学中最朴素的原理。
字面上看,中式的哲理之“理”从“里”,从“田土”,为“王道”。这不仅是中国文字的表象,也是本真的表述。“里”是个会意字,是“田”与“土”的组合;“土”就是“田”。《尔雅》:“土,田也。”也就是说,欲说“理”,先要说“田”,说“土”。“理”为形声,声符为“里”,《说文解字》释:“理,治玉出。”《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故有治理、研磨、纠正等意思。[2](P442)很明显,个中关系是:中式的道理从田土中来;反过来,“土”(田地)也就成了实践这一中式哲学原理的“根据地”和“基地”,而治理田地、耕作粮食也就成了“王治”的道理。
田土除了表示农耕文明的基本构造之外,还上升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下田理”的高度——即以农 为 本 ,以 田 地 为 脉 ,并 与“ 里 ”“ 甲 ”“ 佃 ”“ 男 ”“ 亩 ”“ 畋 ”“ 甸 ”“ 畿 ”“ 稷 ”“ 苗 ”“ 畕 ”“ 畴 ”“ 壘 ”等 相 关 联 ,历史性地生成出了与男耕、井田、里甲、国家、城邑、街坊、邻里等各种关系,甚至连古代国家的“边疆”“边界”都是“田”来划定——“疆”“界”都从“田”,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边疆管理”的原初形态、形貌和形制。由此可知,“田”为基本和基础的历史元素建构出了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和重大的事务,演化成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中特有的土地哲理。
“田”作方形,大多数人或只是认为在农地耕作时方形较为便利,其实远不止于此。“田方”实为“地方”的直观形态。中国的哲学是务实的、直觉的。当“天圆地方”构成中式宇宙观的认知形态和表象时,田地之“方”就被确定了。这并非偶然,更非孤证,田为方,国为方(国的原型为“城”,“城”的原型为“囗”),街为方(街坊),根本原因皆与“地方”有关。可以这么说,要了解中国,需明鉴“田理”,因为,“理”从“田”来,“理”在“田”中,这也是“地方”的道理。这样的哲学唯中国独有,且标榜于世。①笔者此前已有所论述,参见彭兆荣:《天下田理——关于“田”的知识考古》,《思想战线》2020 年第1 期。
中式哲学的第一性为务实性。“务实”并非单一地对某一种功能的强调,而是表现为对生命、生态、生产、生计、生业之五生关系的协作与协同。原因是:它们皆与土地有涉,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果实。中国(人)的终极追求莫过于“富裕-幸福”,国如此,家如此,人如此。可是,我们是否曾想过“富裕-幸福”原本都是土地上的追求。《礼记·郊特牲》:“富也者,福也。”“富”“福”都从“田”,也就是说,没有田地,“富裕-幸福”便没无法落实。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人们对“富裕”“福气”的期待与追求皆在农作中,这是中国百姓基本和根本“道理”。②笔者此前已有所论述,参见彭兆荣:《脱贫攻坚:中国的致富之路与造福之理》,《学术界》2020 年第9 期。
由是可知,中国的“理”与西方哲学的“理”完全不同。众所周知,“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概念,是现代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热衷使用于阐述和分析的工具。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中常使用。虽然这一概念在西方并无公认的定义,甚至连使用的词汇也不相同,但似乎使用都公认“理性”为哲学最常用的“工具”,只是众人对这一“工具”的描述完全不一样,一幅盲人摸象的景观。在众多对“理性”的描述中,康德认为理性的前提是道德法则。近代以降,我国学者也纷纷使用这一“工具性理”,重视理性的价值。而当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却很少人去关注中西方赋予“理”的差异。事实上,我国古代说的“理”(道理),不是“理性”,“理性”是舶来概念,二者在总体上并无共识。
再则,“理性”作为工具在使用上具有广泛价值,但工具是被操纵、操作的,并以特定语境为背景。换言之,即便在西方,选择“理性”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在少数,概念亦不相同。①参见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 页注2。波普金(Samuel Popkin)曾经对“理性”做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对基于其偏好和价值观的选择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据对结果概率的主观估计来预估每一次的结果。最后,他们做出自认为能够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选择。”[3](P31)然而,当西方的理性来到“中华之道”上,必然和必须“受限”和“质检”。[4]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哲学、哲理不了解,搬运西方的“工具理性”有什么用,能怎么用都不了解,那么,效益必定很有限。
概而言之,中国哲学在土地上建立起了独特的农业伦理,其特点是以“五生”为依据,将“富裕-幸福”作为追求目标,形成了独特的土地哲学。而“理性”为西式的舶来者,似与中式同“理”,但并不同“道”,需择而用之。
二、理者,礼也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务实。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理”与“礼”有着剪不断的关系,二者都包含着务实精神。中国古代有“礼仪之邦”之称,凡是重大的帝王祭祀、祭典,无不祈求、诉求,希望、企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就是说,任何道理、仪礼首先建立在满足人类生物性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理”与“礼”通缀,与“饮食”通融。人们所熟知的古代伊尹为商朝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华厨祖。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对此,钱钟书有过专论:
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味具。”——笔者引注)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5](P30-31)
何以一位厨师会被视为“哲学家”?根本原因于在厨师“主导饮食”。而“食”来自于“农”;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自古以来农政与国政并置。历史上的政治家虽然有过不同的主张,但是,在“农本-农正(政)”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只是,传统的“农政-国政”也充满悖论:一方面,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霸气;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又编织出另外一幅图景,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引老子描述:“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即所谓的“小国寡民”。许多政治家把老子的“小国寡民”视为一种政治理想。其实,它毋宁是农业国家自然的政治形态。以管理“小国寡民”之经验却要彰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气度。
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传统的国家,土地是命根,粮食是依靠。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政治家,几乎都把粮食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国家之第一政务。《说文解字》释:“政,正也。”这样的关系可以简化为:国家最大的政治是农业(社),最紧要的事务是粮食(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也称为“社稷”的道理。而社稷之道的核心价值是天地人和,《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求中庸”,凡事不走极端,区分-包容尽皆囊括。[6](P13)“中和”包含了对自然节律的体能与理解。
土地虽然是一个通用概念,却生产出丰富的多样性,也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中国的历史诉求是“安天乐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下;不能乐天下,不能成其身。”[7](P267)土地养育万物,这是人们最为直观的认知,也是最直白的表述:“地生养万物”(《管子·形势解》)的逻辑关系是:土地生长粮食,养育生命,我故尊之、贵之,祀之。早在先秦时期,就以稷(粟)为谷物的代表,谷物之神和土地之神(社)合为社稷共同接受人们的祭祀的礼拜。[8](P43)所以“社稷”其实讲就是在土地上生长粮食。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的哲理。
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其他事务的延伸和延续。有学者考述:“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为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9](P27)而“粮食”又与宇宙观的认知有涉。古代通称粮食为“五谷”,“五谷”究竟指哪几种粮食作物,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较有代表性意见认为,五谷指黍、稷、豆、麦、稻。[10](P81)也就是说,传统农耕文明将宇宙观植入了土地与粮食之中。如果要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寻找最高层次上的共性——中国的哲学原理,即“道”的话,那么,五行必在其列。因为,“五谷”“五行”与中国哲学中的“五方”相配合。
中式的“土地哲学”必然演化出一个关系链接:“天地人和”的农本思想。《汉书·文帝纪》:“农,天下之大本也。”中国历史上商鞅首次将农业称作“本”:“凡将立国,“事本不可抟(专)”(《商君书·壹言》)。[11](P16)中国的农本思想中又贯穿着“和”;“和”从“禾”、从“口”;特指“稻子”,泛指粮食,也称“耕作”。“口”指吃、食,二者合并有祥和之意。[12](P177、179)“中和”——借粮食和饮食的道理以追求万物和谐。中式的土地哲学包含着明确的政治性。农业生产粮食,粮食生产于田地。这也便是古代政治之以“田”为“政”,即“田政”。古代“农政”之要务,是通过田地的大小、土壤等级的高低,农户的农作情形实行税收。“税”者,从“禾”也。就是用禾谷兑换田赋。
概而言之,中式哲学至高原则是天地人和;而最核心的哲理价值是以“时-利-和”的贯彻,时在天,利于地,人中和。“和”与“利”皆从“禾”(粮食)。当我们今天在讲“和谐社会”时,最直观的认知就是“社”与“和”,也就是土地生长粮食。
三、本味与中和
从文字的辨析,“理”之“礼”,古之为“禮”,原本与餐饮有着内在关联。[13](P209)《礼记·礼运》言之凿凿:“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然而,中式的“理-礼”却沿着着不同的路径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中式饮食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两翼现象:一翼高雅,往高处走——和平、中和、和谐;一翼通俗,往低处走——谷、俗、欲即为写照。在人们的认知中,日常生活的相关活动、关系、事务、器物等皆为“民俗”。所谓“俗”,其象形为“人”靠着“谷”。《说文解字》:“俗,习也。从人,谷声。”文字学阐释,“俗”与“欲”相关,本义为有七情六欲之俗人。白川静释俗中的“谷”为“容”,表示在祭祀祖先之录的祖庙和祭器。在祭器上隐约朦胧出现神的身影。是一般性的信仰和仪礼内容。而“俗-欲”之通,有世俗、习俗和凡俗之义,亦有卑贱、低俗之义。[2](P285-286)
这也说明在中华传统的文明中,“圣-俗”并没有被二元对峙化。这与西方的认知大为不同。在西方,人们通常将知识和认知分类置于不同的范畴,即以“低俗”活动、关系、事务、器物等为一端;而“高雅”活动被置于另一端。然而,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表述中,这样的分类没有依据。中国的道理是“圣俗”同畴、通融。我们只要到中国的博物馆中的“礼器专区”走一遭,便能够明白个中道理。所有重要的礼品,包括尊、鼎、爵等,与权力、尊贵、高雅有关的器物,大多与生活中最通俗的饮食有关。其实,饮食文化何以不高雅?饮食的正义是以“谷”为本,既包容“欲”,又形成“俗”。也就是说,饮食之道无论往何处去,皆通“吃”。这是中国哲理中之至理。
除了“理-礼”之外,还包含着“美”。这成就了中华饮食的“本味”特色。中华饮食素以“本味”至上,其根本的特点是自然,——以自然为本。“本味”始见于《吕氏春秋·本味》,曰:“以味为本,至味为上”,旨在保持食物原料的自然风味(本),经过精致的烹饪技术使食物达到至美的境界(味),我们平日里常以“美味”俗称之;其实,“美”之原义为“大羊”,亦有“美味”来自于“本味”的原理和意思。[14](P246)
任何美味皆离不开亲身体验——“尝”。也就是说,“味”是一个前提,必须由“尝(嘗)”来实现。嘗,金文即(尚,高级的)加上(旨,品味)。造字本义:品味高级美味佳肴。《说文解字》:“嘗,口味之也。从旨,尚聲。”张光直说,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说的就是品尝食物。“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取的“实践精神”。
如果说,哲学的至高关注是人的生命的话,那么,除了在中式的道理中讲究农本、农政之外,也在饮食的“理-礼”之中包含了生命的意象。对接今日的语汇表述,“有机”可算是代表。所谓“有机”,指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所有的生命体都含有机化合物,如脂肪、氨基酸、蛋白质、糖、血红素、叶绿素、酶、激素等。事实上,“有机”不仅指生命的构成基础,也指供养生命实体的事物和因素。那么“饮食”为先。人们习惯于将饮食置于“民俗”范畴看待,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日常生活,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厨房锁务,置于“俗事”领域实属正常。
同时,中国的粮食耕作就契合着“有机性”。粮食食品便提升到了“命根”的地位,“民以食为天”,意思是“食品最大”的意思。粮食之大部来自农业,今天人们讲究“有机农业”,其实这是一个链条——事物的各部分互相关联协调而不可分,就像一个生物体那样有机联系。可推导的逻辑是:社会的“有机发展”建立在“有机农业”的基础上;“有机农业”来自于“有机土地”;“有机土地”生长、生产“有机粮食”;“有机粮食”制造、制作“有机食品”;“有机食品”养育生命的“有机体”。这也是中国农耕文明一路贯彻的道理。
在现代农业中,“有机”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有机食品-有机农业”存构成了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的结构产业的机理。这里涉及“有机肥料”的问题。在我国农业生产的漫长历史中,一直靠有机肥料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生产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化肥工业的发展,化肥在农业中的使用逐年增加。1987 年平均亩施化肥高达27.8 公斤。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绿色产业”的兴起,我国有目标的倾斜有机肥料的使用。恢复“有机传统”已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今天,“食品安全”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转基因生物的风险,主要有二: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①参见《人与生物圈》2018 年第6 期之“转基因专刊”。所以,全球都在行动,一方面在发展和利用,另一方面在防范和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机农业”的观念也因此越来越成为世界性共识。许多国家都因此加大了力度。以日本为例,为了确保安全的食物供给,日本在1971 年成立了有机农业研究会,2006 年,国会一致通过“有机农业推进法”,强化了对农药的限制,以及对产地和食品添加物标记的规定。[15](P154)
概而言之,中国的农耕文明之“理”与“礼”有着密切的关联,“礼”与“圣-俗”又相互交织;都包含着对生命的认知、理解与关怀。今天,“有机”这一洋名也进入到了中国,与传统的“生命养育”结合在了一起,值得特别关注。
四、饮食遗产机理
当下,饮食在很短的时间内骤然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近年来,世界著名、知名饮食仿佛着了魔,对着世界遗产的大门纷至沓来,迅速登陆世遗名录:2010 年,以“法国大餐”(法国美食,the gastronomic meal of the French)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的还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摩洛哥联合申报的“地中海饮食”(the Mediterranean diet)、“传统墨西哥餐饮”(traditional Mexican cuisine-ancestral, ongoing community culture, the Michoacan paradigm);2011 年,土耳其饮食“麦粥传统”(ceremonial keşkek tradition)紧随其后。接着,日本和食(WASHOKU: traditional dietary cultures of the Japanese)和韩国的“韩国越冬泡菜”(republic of Korea——Kimjang, making and sharing kimchi)等东亚饮食也不甘人后,成功登陆。饮食入世遗包含着食品安全等全球化语境。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提示的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验收的“国家主体性”饮食,已经从包含的民间、民众、民俗层面上升到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层面。饮食成了人们通过品尝的原始方式提醒和提示“我是谁?”当“法国美食”成为世界遗产,重新唤起法国人历史自豪感的时候,这一事件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的相关部门做了一个日本食文化申遗提案的社会普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民众对饮食申遗具有高度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饮食从业人员共同参与多次检讨会,反复讨论日本食文化的具体内容。2012 年1 月24 日,《日本食文化申报无形文化遗产提案书(概要)》完成,正式进入申遗程序,2013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而今,日本的和食进入到了所谓的“后遗产时代”。
日本和食申遗的语境和历史事件是:2010 年“法国美食”等项目成功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国民呼吁日本食文化申报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呼声”的基调包含着现代民族主义的成分。日本相关部门专此做了一个调查,结果绝大多数日本民众支持将日本和食申遗。①参见日本食文化申报世界无形文化遗产提案书(概要),日本食文化申报世界无形遗产检讨会制成,2012 年1 月24 日。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官方网站http://www.maff.go.jp/j/keikaku/syokubunka/ich/index.html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和饮食从业人员着手和食的“申遗”工作,他们共同参与多次检讨会,反复讨论日本食文化的具体内容。为了满足申报的“主体性”,“提案书”在介绍“和食”时强调其存在于缔约国全境,即“和食”一方面具有基本性的共通要素,确认和食的担当者和实践者是全体日本人。
另一方面也强调和食所包容的各种差异性,如由于各地地理条件与历史背景的差异,鱼油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各种类型的“和食”都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地域。例如,佛寺的宗教料理和茶汤宴席主要集中在古都京都,以新鲜的鱼为材料的寿司文化集中在以东京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以及与鱼、农产品、山菜等多样性的食材相对应的各种乡土料理形态。日本最后一次申报提案审议会(2012 年2 月)上强调从日本食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出发,说明全国有1.5 万种以上的乡土料理同时存在。2012 年3 月,日本以“和食:日本人的传统食文化”(WASHOKU: traditional dietary cultures of the Japanese)为主题,申请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名录并获得成功。②参见日本食文化申遗检讨会/审议会会议资料、议事概要、议事录(日本食文化の世界無形遺産登録に向けた検討会と文化審議会:配付资料、議事概要、議事録)http://www.maff.go.jp/j/keikaku/syokubunka/ich/index.html。
当饮食遗产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体代言时,中国人以及全球华人也都会将其视作文化认同的一个载体;或在中华饮食中寻求“国族”的认同感。客观而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外国人,都会在现象学意义上确信、确认和确定,中华食物(中餐)是“中国制造”系列中最尽风光、最劲风头的产品和品牌。而中华饮食作为东亚饮食文化的体系重要源头——日本的和食中就包含着来自中国的元素,深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16](P18)可是,遗憾的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讲求农业、土地和粮食,中国的饮食彪炳于世,迄今为止,却没有一种中国的饮食进入到世界的遗产名录之中。
这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1)中式的农耕文明非常独特,中式哲理太简单深奥,甚至到了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高度;(2)由于中国的地方多元、地缘多样、饮食多系,一时难以找出一个足以代表“中国”的饮食作品;(3)中国饮食与中国的文化人格或有关系。中国人讲究“致中和”,可以包容“他者”,烹饪技艺中很难找到一个“共认”品尝标准,这与法国大餐、日本和食、韩国泡菜那样的“一致性”不同。不过,笔者相信,中华饮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只是时间问题。毕竟,世界饮食舞台上缺了中国饮食必然失色。重要的是,中华饮食中有着“中国哲理”“中式道理”。
概而言之,中式哲理中土地生长粮食的道理,在饮食遗产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既然中国的伊尹厨师可以成为“第一位哲学家”,那么,中国的饮食智慧也就必然嵌入在了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之中。中式的饮食智慧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五、余 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国家。“文明”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同时也彰显着普世性与多样性。有意思的是,中西方不约而同地在“土地-农业-粮食”中确立文明的基调和文化的底色。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一种解释是,由集约粮食生产维持,围绕提供管理、商业、艺术等有组织的复杂社会。[17](P36)英语“agri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语“agricultio”,“agri”的词根是“ager(土地)”,“cultio”词根是“colo(耕作)”,即“耕作土地”,强调“文化”(culture)——文化地缘说(agriculture)。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为农耕文明,“文明”与田地关系更为密切;“文明”一词初见于《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农业的根本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并由此生成和演化出复杂的土地伦理。[18](P45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9](P23)今天,我国正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这不是一般的“运动”,而是文明之根,保命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