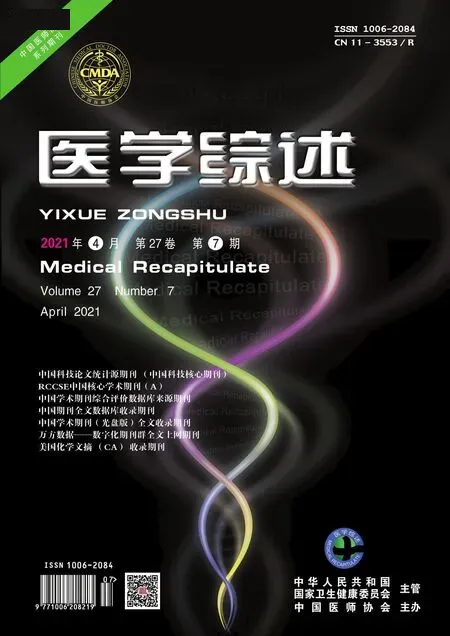血清分泌型Klotho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王喆,胡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哈尔滨 150001)
抑郁症是一种由遗传、神经生物因素、心理社会因素等共同作用引起的多因素精神疾病。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抑郁症的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研究显示,我国20%的人群表现出抑郁症状,其中7%为重度抑郁障碍,且抑郁症居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1-2]。除情感障碍外,认知功能障碍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随着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抑郁症被确诊,且抑郁症认知功能改变可能与相关脑区结构网络及功能连接异常有关[3]。Travis等[4]通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抑郁症患者海马脚和齿状回等部位的细胞容积减少、萎缩甚至坏死。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生物化学、遗传、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此外,还可能与免疫系统的改变(包括细胞因子假说与单胺假说)、人体菌落比例失调以及神经系统相关功能脑区的改变等相关。目前,抑郁症的治疗以抗抑郁药物为主,物理治疗为辅,因此明确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对于其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人类Klotho基因位于常染色体13q12,该基因编码的具有抗老化性质的蛋白质家族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5],能保护神经元免于退化,其中分泌型Klotho蛋白(secretory Klotho protein,sKlotho)是Klotho基因编码的具有抗老化性质蛋白质家族的成员之一。现就sKlotho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sKlotho概述
Klotho基因最初于1997年由Kuro-o等[6]在抗衰老研究中发现,Klotho基因缺失动物模型表现出寿命缩短、血管钙化、生长缓慢、骨质疏松以及其他器官萎缩,并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等衰老征象;而Klotho基因过表达动物膜型的寿命延长,且衰老表现得到改善[7]。Klotho基因可编码α-Klotho、β-Klotho和γ-Klotho三种蛋白亚型,其中α-Klotho是最主要的蛋白亚型和功能类型,通常可分为膜结合型Klotho蛋白及sKlotho。sKlotho是一种游离蛋白,以游离形式在生物体内发挥不同的生物学作用,如调节多种离子通道、抑制氧化应激、调节转运蛋白等,在肾脏及大脑脉络丛表达量最多,在脑垂体、胎盘和骨骼肌等部位也有少量表达。Klotho基因编码的蛋白有α-Klotho、β-Klotho和γ-Klotho三种亚型,该家族蛋白的各个分型在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中均起到一定的作用,如α-Klotho与肾脏疾病、心脏疾病以及酒精性肝硬化[8]相关。与无饮酒史、无肝硬化病史的健康人群相比,有酗酒史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α-Klotho水平较高,可能与α-Klotho可作为抗氧化剂并具有抗炎和抗纤维化作用有关。β-Klotho主要存在于肝脏和脂肪组织中,具有调节代谢、加速葡萄糖摄取、促进胆汁酸合成和脂肪酸代谢等作用,与酒精成瘾的相关精神疾病有关,该蛋白可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结合,其含量减少可增加患者对酒精的渴求,并增加饮酒量[9]等;γ-Klotho蛋白表达相对较少,与膀胱癌的侵袭相关,但尚未发现其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目前,sKlotho水平的变化与多种疾病相关,如急慢性肾损伤[10]、血管动脉硬化、内分泌系统疾病以及肿瘤[11]等,但其与抑郁症的相关研究较少。
2 sKlotho与抑郁症的研究现状
sKlotho是Klotho基因编码表达水平最高的家族蛋白质之一,也是与精神相关疾病关联密切的家族蛋白质之一。Crasto 等[12]的研究表明,sKlotho水平较高的老年抑郁症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较好,且死亡率较低。另有研究发现,慢性心理压力与女性血清sKlotho水平降低有关,且sKlotho水平降低与女性更多的抑郁症状有关[13]。Hoyer等[14]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显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脑脊液中Klotho蛋白水平升高,电休克治疗对中枢神经系统Klotho蛋白有特异性影响,表明Klotho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并影响患者的治疗反应。国外研究表明,sKlotho蛋白可显著影响少突胶质细胞功能,如诱导大鼠原代少突胶质细胞祖细胞的体外成熟和髓鞘形成,而少突胶质细胞增加可逆转慢性应激动物模型的抑郁样行为,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显示,Klotho基因敲除后,sKlotho蛋白分泌减少,导致基因敲除小鼠的成熟少突胶质细胞数量明显降低,进而产生抑郁样行为[15]。由此可见,sKlotho可能是治疗情感及认知障碍的潜在靶点。
3 sKlotho参与抑郁症发病的可能机制
sKlotho与抑郁症的发病有紧密联系。有报道指出,sKlotho可通过内质网应激、炎症及氧化应激、海马胆碱能神经系统等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感及认知功能障碍[16]。
3.1内质网应激机制 内质网应激指内质网腔内错误折叠与未折叠蛋白聚集以及钙离子平衡紊乱激活未折叠蛋白反应、内质网超负荷反应和胱天蛋白酶(caspase)-12介导的凋亡通路等信号途径,既能诱导葡萄糖调节蛋白78、葡萄糖调节蛋白94等内质网分子伴侣表达而产生保护效应,亦能独立地诱导细胞凋亡。多种生理或病理条件均可影响蛋白质折叠和内质网折叠能力,导致细胞的内质网需求与内质网折叠能力之间的不平衡[17]。内质网应激会导致细胞凋亡或细胞复原力受损,与疾病状态有关[18]。sKlotho可提高内质网应激的反应率,减少凋亡信号,并增加化学内质网诱导治疗后的细胞存活率,提高重度抑郁发作患者的神经元复原能力。
3.2炎症及氧化应激机制 在其他可能的机制中,Klotho基因分泌的sKlotho与抗抑郁药物治疗反应有关。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通过影响钙通道降低某些区域的突触功能,sKlotho可通过血脑屏障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钙代谢[19]。sKlotho是通过人解整合素样金属蛋白酶10和人解整合素样金属蛋白酶17切割细胞膜中Ⅰ型跨膜蛋白而得到的游离型蛋白[20]。sKlotho可调节细胞内的信号转导,参与体内多种生理功能的调节,并可拮抗多种应激诱导的细胞衰老过程,其机制与抑制氧化应激有关。Klotho基因的缺失导致自身抗凋亡作用减弱,进而易导致海马区细胞的凋亡。动物模型sKlotho的减少降低了海马突触密度,反映了氧化应激的增加。sKlotho缺乏小鼠表现为明显的一氧化氮缺乏,导致广泛的内皮细胞坏死,中枢神经系统氧化应激的总体负担普遍增加。因此,sKlotho可能具有脑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可能干扰抑郁症正常应激反应的所有阶段,包括适应性海马神经发生和产生神经干细胞的能力[21]。
此外,sKlotho可能作为重度抑郁发作应激过程的潜在调节因子。反复的社会和其他压力以及遗传倾向可能导致神经元恢复力下降以及抑郁症状产生,sKlotho有助于对抗应激,限制与重度抑郁发作相关的炎症和代谢变化的有害影响。Zhu等[22]的研究发现,脉络丛分泌的Klotho蛋白在免疫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幼鼠和成年小鼠、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脉络丛中高水平Klotho蛋白的表达可能限制外周免疫细胞对脉络丛的渗透,并抑制可能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介质的产生。脉络丛中Klotho蛋白的表达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脉络丛中Klotho蛋白水平的降低,促进了外周巨噬细胞的进入,并显著增加了多种促炎介质的产生;在自然衰老过程中,也会发生类似上述促炎变化,因此Klotho蛋白表达的年龄相关性下降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衰老相关炎症的原因之一。脉络丛产生的Klotho蛋白存在于脑脊液中[23],炎症介质很可能通过脑脊液循环[24]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位置(包括脑和脊髓),并通过自身或与其他因素共同促进神经功能的老化。外周注射相对低剂量的脂多糖后,脉络丛中Klotho蛋白减少,海马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加剧,表明脉络丛引起的Klotho蛋白耗竭可能“启动”小胶质细胞的年龄依赖性,引起外周感染的激活。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白细胞介素-1β升高与海马突触可塑性缺失有关。体内外数据均显示,脉络丛上皮细胞产生的Klotho蛋白通过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Klotho信号通路抑制巨噬细胞和其他细胞(包括脉络丛上皮细胞)中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的激活,对抗1,25-二羟维生素D3,并抑制依赖于1,25-二羟维生素D3的硫氧还蛋白结合蛋白表达。Klotho蛋白减少后脉络丛中硫氧还蛋白结合蛋白含量增加,可直接增加促进白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促炎基因产物的表达,其中包括细胞间黏附分子-1;硫氧还蛋白结合蛋白还可促进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的激活,可能导致多种与衰老相关的缺陷和疾病,包括认知功能下降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3.3海马胆碱能神经系统损伤机制 除情感障碍外,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伤也备受关注。Klotho蛋白作为脑脊液中分泌的体液因子是其在大脑的关键功能之一,更详细的功能分析表明,Klotho蛋白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不同区域具有特异性效应,如海马神经元的表达可能影响空间记忆,而杏仁核的表达可能与恐惧学习有关,相关基础实验通过Sholl分析与染色分别评估神经元形态与突触密度,结果显示,Klotho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结合后能够进一步改变海马神经元的形态与突触的数量,进而影响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25]。有研究表明,sKlotho水平与神经内科疾病患者的认知损害程度呈正相关,如老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脊液sKlotho水平较健康年轻人降低,且老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脊液sKlotho水平低于非阿尔茨海默病健康老年人[26]。sKlotho的减少与脑白质损害密切相关[27],并与认知功能直接相关,提示脑源性sKlotho具有多种作用,如预防脑动脉硬化、抑制脑内淀粉样物质产生、脑神经保护和预防认知功能下降,因此,对于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病史的低水平sKlotho中老年人群,有必要在头部核磁共振检查和认知功能测试后进行积极的早期干预[28]。
Klotho基因缺陷损害了海马胆碱能神经系统,导致M1毒蕈碱胆碱能受体(M1 muscarinic cholinergic receptor,M1mAChR)基因表达、M1mAChR结合密度、乙酰胆碱水平、胆碱乙酰转移酶(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ChAT)活性和ChAT基因表达显著降低,以及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和乙酰胆碱酯酶基因表达显著增加。胆碱能神经元系统的变化可能由突触前胆碱能神经终末和海马内表达M1mAChR的突触后神经元缺乏导致。Klotho基因缺陷持续降低蛋白激酶CβⅡ、磷酸化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以及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依赖性长时程增强作用[29]。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激活导致Janus激酶2(Janus kinase 2,JAK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和酪氨酸激酶B(tyrosine kinase receptor B,TrkB)信号,ChAT活性和乙酰胆碱水平升高,进一步刺激M1mAChR增加[30]。动物实验显示,Klotho基因突变小鼠ChAT损失明显,与人类大脑类似。因此,Klotho基因突变体小鼠中突触前ChAT和JAK2/STAT3水平的改变可能与基础海马神经元凋亡同时发生,并可能导致认知和行为症状。此外,Klotho基因缺陷显著降低了磷酸化JAK2/磷酸化STAT3在海马神经元中的表达,表明JAK2/STAT3信号轴与胆碱能神经递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由此可见,Klotho基因突变体小鼠JAK2/STAT3失活通过双重机制导致胆碱能功能障碍,即胆碱能基因的突触前下调,如ChAT和M1mAChR突触后脱敏。
Klotho基因突变小鼠NMDAR依赖性长时程增强作用降低可能由M1mAChR表达降低或机制下调所致,如蛋白激酶C偶联M1mAChR。Klotho基因突变小鼠JAK2活性降低可能导致NMDAR功能受损。动物实验显示,6周龄Klotho基因突变小鼠记忆功能正常,视觉识别记忆和联想恐惧记忆受损,在轻暗穿梭箱和高楼迷宫箱任务中的表现正常;在条件性恐惧任务中,突变小鼠与非突变小鼠的电击伤害性阈值无明显差异,表明与非基因突变小鼠相比,Klotho基因突变小鼠的探索活动、情绪性或休克敏感性无重大变化,故推测Klotho基因突变小鼠可能主要为记忆能力受损[31]。Klotho基因的扩增避免了海马中NMDAR亚基的减少,改善了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功能;此外,小鼠Klotho基因扩增使得突触后NMDAR谷氨酸受体亚基的密度以及NMDAR数量均增加,这对学习和记忆具有决定性作用,表明Klotho基因表达水平升高或活动增强可促进突触和认知功能,并可能对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其他认知障碍具有治疗作用[5]。
4 小 结
目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尚无明确的生物学诊断指标,影响了抑郁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准确率。在众多抑郁症机制的假说中,sKlotho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相关性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sKlotho可通过内质网应激、炎症及氧化应激等机制诱导抑郁症的发生,并可通过提高血清sKloth水平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及认知功能障碍,故可将sKlotho作为抑郁症治疗的潜在靶点,未来仍需继续探究sKlotho在抑郁症中的具体机制,进一步明确sKlotho的作用机制可能为改善抑郁症情绪和认知障碍提供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