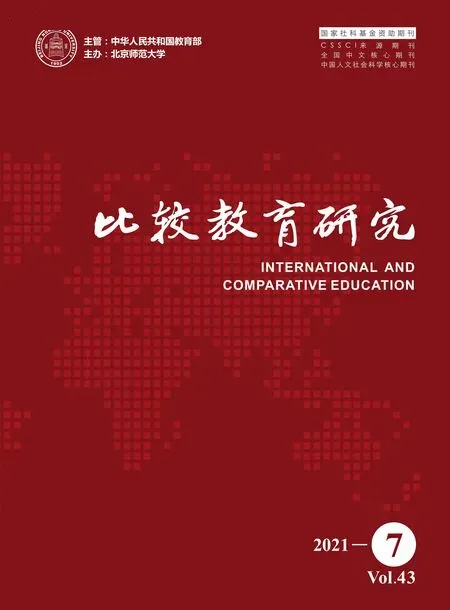论我国比较教育的科学化:必要性与可能性
吴宗劲,饶从满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4)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谋求学科的转型和发展便成为比较教育学科共同体成员的核心关切。[1]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一再对比较教育寄予厚望[2],比较教育也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基本结构[3][4],但不得不说比较教育这项工作的定位是十分不安全的,研究者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提供辩护。[5]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 主要取决于两个前提因素或条件,一个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另一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6]。就比较教育学科而言,其发展深受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研究科学化两大历史传统的滋养。目前,学界更侧重于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探索我国比较教育的转型和发展,以凸显比较教育在国家教育改革、对外开放、全球教育治理中的现实功用和价值。[7][8][9][10][11]这些研究往往强调我国比较教育要遵循文化研究范式[12][13],要从单一的借鉴转向理解或诠释。[14][15]虽然少数学者注意到教育决策的科学向度,并指出比较教育需要提高其知识生产水平[16][17][18],但学界就此并未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相比之下,鲜有学者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传统来探讨比较教育的发展。尽管学界日益重视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19][20][21][22],但不能不说比较方法①在这里的“比较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小样本的少数国家比较”(comparing few countries)和“国别研究”(single country studies)。的功能及其对比较教育学科化的意义乃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议题。正如项贤明所言:“很少有人注意到,比较教育及其方法论的发展历史,其实一直与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发展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23]此番遗憾的产生与此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属性)尚存争议[24],以及比较方法的科学性曾为我国社会科学界所忽略不无关联。[25]
作为一种尝试,本研究旨在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历史传统来探讨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图激活学界对比较教育科学化的探讨,深化对比较教育学科转型的思考。
二、我国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内涵与必要性
对因果规律的探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26]唯有发掘出现象背后恒定的因果机制,社会科学才能实现有效的知识积累,继而发展出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理论。[27]这就意味着社会研究科学化的关键在于提升因果分析的有效性。比较教育是教育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来命名的学科,比较方法构成了比较教育的“硬核”①此处借用了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观点,他指出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是一些不容放弃和不可改变的哲学信念和基本假定。(参见:伊姆雷·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7.)借用此概念是为了强调比较方法乃是比较教育等比较学科的基础和特质,它是界定比较教育学科边界的核心要素,因而它也是推动比较教育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因而,其科学化的实质在于提升比较方法(包括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在因果分析方面的有效性,以实现教育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理论的建构。
当前,比较教育存在的最大缺陷莫过于知识积累的不足。就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比较教育虽然大量地描述和介绍了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但缺少系统的比较和分析。[28][29][30]与基数庞大的国别研究相比,真正运用比较方法从事因果分析和教育理论建构的研究可谓十分稀少,大部分研究成果未能超越表层的、形式比较的水平。[31]与此同时,国别研究也存在弱化的趋势,具体体现在对国别教育的跟踪研究或历史透视不足、系统的跨学科的深描或诠释不够、研究覆盖的国家和区域有限。梁忠义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研究,我们距离全面、系统、深入、跟踪的研究还有一段距离。”[32]无论是出于服务国家教育决策的需要,还是为了夯实学科的知识基础,我国比较教育都需要启动科学化进程,以提升其知识生产能力。
一方面,比较教育唯有通过科学化才能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对内,我国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为了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我国政府正着力打造一个公平且高效的教育体系,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这意味着比较教育借鉴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描述和概括外国教育经验,而是要以此为基础探寻教育的规律、发展教育理论。对外,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我国正积极承担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加强同各国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比较教育将自己打造成“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33],通过推动国家间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来促成国际理解与和平。这就意味着比较教育需要通过科学化来强化其知识生产能力,才能在国际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为世界教育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另一方面,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地位的巩固同样需要比较教育通过科学化来完善学科知识体系。所谓的“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尽管学科的建立带有人为推动的痕迹,但从本质上讲学科的发展和分化是以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分化为基础的。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教育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基本结构,当务之急是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过去比较教育所从事的那种“信息搜集”式的外国教育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教育改革对教育借鉴的需要,但它却无助于比较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自我建构。也正是因为比较教育未能实现有效的知识积累,为教育学贡献独特的理论,外界才会质疑比较教育的研究水平和存在价值,并引发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对“身份认同”问题的争论。由此观之,比较教育若想成为一门既有特殊方面又涵盖实质内容的学科,它亟须从教育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育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化对于比较教育成为知识生产者而言,不可或缺。
三、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历史溯源
比较教育自创生以来就怀有科学化的理想,其学科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为追求科学化的历史。如果将马克-安东尼·朱利安(Marc-Antonie Jullien)奉为比较教育科学化之先驱,那么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乔治·贝雷迪(George Z.F. Breday)、哈罗德·诺亚(Harold J. Noah)和马克斯·埃克斯坦(Max A.Eckstein)、布莱恩·霍姆斯(Brain Holmes)等人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实证主义传统则是这项事业的继任者。他们的观点一再强调比较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异域教育现象来探究背后的因果关系,揭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何这一理想至今未能实现?下文将通过历史溯源来回答上述问题。
比较教育创生的19世纪正值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时代。就如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所倡导的那般,人类思想已经进入科学的或实证的时代;凭借科学方法,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将得以解释,并能够形成一门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社会物理学”。[34]比较方法(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①关于密尔比较的详细解释,参见:MILL J S.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M].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 2002: 255-256.SKOCPOL T, SOMERS M.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0,22(2): 174-179.)就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各类社会研究,由此还催生了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一批以比较方法来命名的学科。须知,比较方法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与描述工具,而是一种通过控制无关变量来建立变量间因果关系或普遍法则的方法。[35][36][37]在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看来,比较法是一种最接近比较方法并可用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因而他将比较法视为一种“间接实验”。[38]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关于比较教育的构想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诉求是一致的。他认为:“就解剖而作比较解剖的研究,终于促进解剖而使之成为一门科学。同样,做比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为教育的完善而成为科学,提供一些新的手段。”[39]在朱利安看来,教育学应该是一门“近乎实证的科学”,教育的原理或一般原则应当从各国教育的比较中推导出来。为此,他主张通过建构系统的事实与观察,列于分析表中,以便对照和比较,从而推导出若干原理、一定规则。[40]质言之,在朱利安的构想中,比较教育就是教育科学的同义语或代名词,它代表了当时教育学科学化的一种努力。
遗憾的是,朱利安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构想并未在19世纪付诸实践。比较教育的科学化毕竟只是少数研究者的理想。相比之下,当时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建构对教育借鉴的需求强大而迫切,这就促使比较教育将研究重心置于对外国教育的描述和诠释而非比较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上。这也使得历史人文主义传统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传统旨在诠释构成一国教育系统之基础的“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和文化力量”[41],并希望从中获取对本国教育发展有益的经验。
比较教育的科学化真正被提上议程已经是“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了。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讲,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比较教育能够更好地发挥解释和预测功能,以期为教育决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42]此外,伴随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也日益趋向实证主义传统。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者都希望在比较分析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技术来提升比较教育进行假设检验或因果分析的能力。诺亚和埃克斯坦作为比较教育实证主义传统的代表就坚信,采用“经验(实征)和定量的探究方法”,比较教育便能够成为一门社会科学。[43]他们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即案例的比较、理论分析)引入比较教育,完善比较教育进行假设检验的程序(确定问题、提出假说、明确概念、选择例证、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说明结果)。[44]他们的方法曾被广泛应用于“二战”后各类国际调查和教育援助项目中,以揭示教育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并推动比较教育走向一时的繁荣。如今看来,他们对定量分析策略和数据的过度推崇完全是一种忽略教育和社会现象之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衰落,上述研究取向也遭到了比较教育学界其他阵营的清算,比较教育的科学化也由此陷入停滞。
纵观比较教育科学化的曲折历程,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科学化是比较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比较教育不仅需要从事应用研究,为教育改革和人类福祉服务,它作为一门学科还需要从事基础研究,探索教育的规律和建构教育理论。光知道“是什么”(描述教育现象)是不够的,唯有知道“为什么”(进行假设检验或因果分析),人们才能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并对其趋势做出预测,从而得出相应的干预政策。比较教育的科学化是一个美好愿景,只不过因为方法论的局限和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而落空。
第二,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不足以支撑比较教育科学化。(逻辑)实证主义持有的是一种普遍论科学(nomothetic science)观念,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做出因果解释,科学知识就是对普遍规律的揭示。[45]这种观念的引入,虽然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程序的科学化,但也导致了比较教育对定量方法和数据的过度推崇,忽视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此前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就对普遍论科学和特殊论科学(idiographic sciences)做出了严格区分,以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现象发生的历史文化脉络。在比较教育领域,安德斯·卡扎米亚斯(Andreas M.Kazamias)等比较教育学家也强调比较教育研究是对历史和科学的综合。[46]这就表明,教育的法则有别于自然规律,比较教育的科学化需要另辟蹊径。
第三,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比较方法本身的不成熟制约了比较教育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因为信息的有限性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对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可望而不可及。正如约瑟夫·拉帕龙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极度缺乏关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的信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47]事实上,在信息化社会到来之前,如何有效获取有关各国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有效信息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者面临的难题。其次,尽管社会科学家寄希望于借助比较方法来获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但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比较方法还不够成熟。导致社会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①当代社会科学更倾向于认为导致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复杂,是联合起因(conjunctive plurality of causes)与选择起因(disjunctive plurality of causes)的复合。换言之,起因是具有结构性的。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单个因素既不是结果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参见: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6,(4): 132-156.密尔比较却只能解释单个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无法对更为复杂的因果机制做出解释。[48]当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无不以密尔逻辑为基础,其科学化进程受阻也在情理之中。
四、我国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可能性:基础要件与必要举措
(一)我国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基础要件
第一,后实证主义为比较教育科学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后实证主义为“科学”概念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解,它将“科学”理解以求真的态度永无休止地参与理论的证伪或反驳交替进行的学术活动。[49]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是在此意义上强调教育是一种蕴含科学的活动,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50]这种对待“科学”的开放态度将带来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就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存在两重功用,一是为社会行动提供诠释性的理解,二是寻求对社会行动过程、结果的因果解释。[51]前者是历史人文主义范式的诉求,后者是实证主义范式的诉求。比较教育的知识生产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中,一端是“诠释”(阐明外国教育的特质),另一端是“解释”(探索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其对教育规律的探究要兼顾对个案(国别教育)的深描或诠释。比较教育研究是基于案例的比较,所追求的因果规律或“法则”都是嵌入情境中的(context-embedded),其求得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概率性或趋势性(tendency law)。这暗示着比较教育是在得失之间进行权衡的选择者,其科学化进程需要在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和策略中进行平衡与决策。①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指出:“我们并不是封闭的、不可测量性的囚徒,而是在得失之间进行权衡的选择者。案例研究牺牲普遍性: 研究者需要对‘少’的东西理解更多。相反,比较研究牺牲理解的情境: 研究者需要对‘多’的东西理解得相对少。”参见:SARTORI G.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 3(3): 243-257.
第二,大数据时代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海量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所谓的“大数据”是指“规模超出了典型的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捕获、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52]。它因数据体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数据生产速度快(velocity)、数据价值大(value)的特征[53],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海量的有关世界各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状况的数据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而言无疑是一座金矿。在教育领域,随着“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等国际测评项目日渐兴盛,比较教育研究者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关于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情况的信息越来越丰富。这些海量的信息能够深化比较教育研究者对各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解,并帮助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探寻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律。[54]
第三,比较方法的突破性进展为比较教育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和技术的支撑。如果说此前密尔比较寻求的是“单因解释”,那么最近几十年学界有关比较方法的探讨则致力于让“多因分析”成为可能。[55]就如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的 “多重并发原因”(multiple conjectural causation)概念所指出的那样,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案例中,同一类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由不同原因按照不同条件组合而导致的。[56]比较研究的目的不仅要建立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应该阐明使因果关系得以建立的各类“中介性机制”(intervening mechanism)。近二三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均以多因分析见长。如若将这些新方法引入比较教育,对比较教育科学化,即提升比较教育在多因分析方面的效用大有助益。
(二)推动我国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必要举措
第一,加强比较教育研究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方法意识是研究者必备的素养。然而,此前比较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学的人才培养并不重视研究方法的学术训练。[57]就如比较政治学家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曾批评比较政治学的学生在方法论问题上属于“无意识的思考者”(unconscious thinkers)[58]一样,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共同体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了解实证科学和逻辑的方法,也不接受其指导”的情况。从已经发表的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研究方法部分是相对薄弱的。研究方法缺失、堆砌、误用和虚设的现象,屡见不鲜。以文献法(document analysis)这一比较教育研究所惯用的研究方法[59]为例,对它的误用可谓比比皆是:有的研究仅是交代使用了文献法,但并未详细阐述选用了哪些文献,运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有的研究宣称是文献研究,但却并未使用原始文献(primary documents)而是采用研究型文献(二手文献)进行分析,这是典型的“炒冷饭”行为;有的研究甚至将“文献研究”和“文献综述”混为一谈,作者的观点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综上,比较教育研究者的方法意识有待提升,有关方面应该加强比较教育研究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课程应该加强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探讨和实践训练,力求让研究者掌握有关方法的理论知识,并能够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选择适切的方法来从事研究。
第二,注重对比较方法的跟踪研究和创新发展。比较方法在因果分析方面的有效性,决定了比较教育科学化的成败。然而,在我国,就如比较方法曾长期为社会科学界所忽略一样[60],比较教育研究者对比较方法的讨论并不成熟。他们更倾向于将比较视为一种归纳和诠释外国教育特质的手段[61][62],而非进行变量控制和探求教育发展规律的方法。这与“二战”后比较方法在国际社会科学中的发展相比,可谓相形见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比较方法操作的讨论便是比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是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提出的“最具差异性系统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和“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63]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则致力于让“多因分析”成为可能,代表性成果便是“比较历史分析”①“比较历史分析”在研究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有其悠久的历史。《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在2003年的出版是该研究传统形成方法自觉的一个转折点。其方法论特征有如下三点:注重因果结构(casual configuration)的分析、关注时间进程(historical/temporal processes)、重视个案研究或系统的背景制约式比较(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参见:MAHONEY J, RUESCHEMEYER D.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M]// MAHONEY J,(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15.)在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下,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或过程追踪(proces stracing)技术注重挖掘那些使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得以成立的“中介性过程”(intervening causal process)或“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参见:MAHONEY J.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8,40(02): 122-144.)时序分析(temporal analysis)是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因果概念中时空毗连这一条件的重申,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事件发生的时机对特定历史结果的影响。和“定性比较分析”②“定性比较分析”由拉金(RAGIN C.)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研究》(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中首次提出。定性比较分析注重对“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分析,通过引入布尔代数或模糊集合来进行中小样本的跨案例比较,以揭示导致某一社会现象发生的不同原因组合。在集合思维的规范下,案例可以被抽象为一系列条件的组合(configuration),再通过比较,研究者便能甄别出影响结果变量的各类条件组合,从而发现蕴含在这些案例背后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参见:RAGIN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3-25.)这使得定性比较分析不仅能够实现对案例进行综合描述、类型学上的建构和检验诠释性模型的异常,而且还能实现对理论的评估、检验和完善,甚至建构新的理论。(MARX A,RIHOUX B, RAGIN C.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irst 25 years[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6(01): 115-142.)的创生。鉴于此,我国比较教育若想实现科学化,亟须做好对比较方法的长期跟踪研究。
此外,不得不承认比较法对变量的控制力度,还远不及统计控制和实验控制。[64]利普哈特也曾指出,比较方法(包括案例法)“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才使得如何以最小化弱势、最大化优势的方式去运用这些方法,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挑战性任务”。[65]这意味着比较教育等比较学科肩负着比较方法的创新发展。因为比较方法乃是比较社会科学的“内核”,比较方法在因果分析中的有效性,关乎比较教育学科的前途和命运。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山田等人强调,比较学科的独特性不仅在于比较方法的使用,而且更在于比较方法的开发。[66]质言之,开发和完善比较方法即是我国比较教育学人需要积极面对的课题,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发挥国别研究在比较教育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应有作用。直至目前,国别研究依然是比较教育研究者涉足最深、发表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67][68]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他们专注于国别研究更有可能有研究成果产出。因为从事跨国教育的比较研究是很难的,它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资金和时间都有很高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别研究的优势体现在,即便在可支配的研究资源相当有限的条件下,研究者聚焦于单个案例也可以使案例得到深入的考察。[69]鉴于此,研究者要发挥好国别研究在比较教育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应有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延续过去那种信息搜集式的外国教育研究,而是要通过加强和改革国别研究使之得以振兴。[70]
首先,国别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71]世界教育是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各国教育的独特性是由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塑造的。[72]国别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深描”功能,它帮助我们深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从这个国家特有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透视该国教育的发展,诠释该国教育发展的特质。贝雷迪正是洞悉到这一点才一再强调“系统的比较教育研究”由“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预备。[73]质言之,比较研究如果不建立在全面深入的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的表层化就不可避免。[74]比较教育若想实现科学化,需要加强作为基础和预备的国别研究,即发挥好国别研究的“深描”功能,把一国教育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说清楚,搞明白。
其次,国别研究①此处将国别研究类比于个案研究。还是比较教育不可或缺的知识生产路径。[75]甚至可以说,以理论生产或因果解释为目的的个案研究本身就是比较研究。[76]二者分析问题的逻辑是一致的,皆是通过控制无关变量来揭示教育现象中所蕴藏的因果规律,以建构具有普遍法则意义的教育理论。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个案研究,可以认为是比较方法的隐含部分:要研究的个案就好比“实验组”,理论以及能够被理论所解释的案例则代表了“控制组”。[77]如果说跨国比较研究是案例同案例之间的比较,那么国别研究的比较是特定案例同理论之间的比较。国别研究的因果分析或理论创新是由理论所驱动的。就如罗伯特·殷(Robert Yin)所言,个案研究的概括是理论驱动下的“分析性概括”(analytic generalization)。[78]理论被当作“模板”(template)是用来同个案的经验发现展开进行比较的,它同时也构成了发展新理论的前提。这种基于个案经验的概括或者说是外推的有效性,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79]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把基于单一研究对象国教育情境得出的发现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的桥梁,通过理论与个案经验的比较,使得“走出国别”,即凭借个案研究来进行概念建构和教育理论的创新成为可能。据此,比较教育研究者不能只关心和了解自己所研究的国别,要把国别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考察,开展基于理论的国别研究,最大化发挥好国别研究在因果分析和教育理论建构方面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