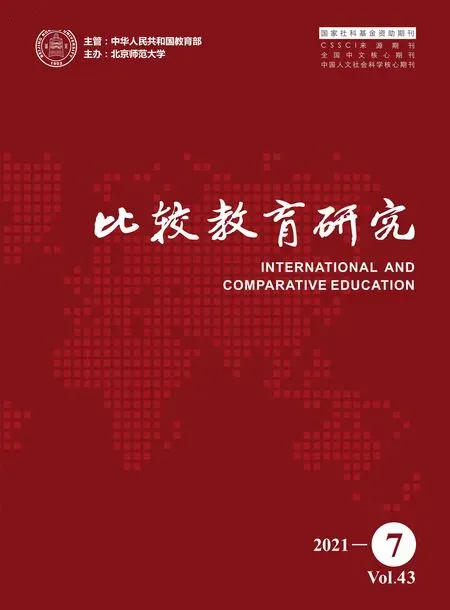哲学视角下教师发展的历史流变比较与反思
王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透过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有效应的历史”(eあective history)[1]眼光来看,“教师”是一种演进的社会反映、建构的文化荟萃,不是静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动态的功能性存在,处于不断再造的历史洪流中。纵观教师发展的流变,可以看出理论张力与内在需求既较量又融合,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趋势。
一、教师职业的本质不断重构
教师职业自独立之日起,便为了自身定位开始了漫长的奋斗之路。对教师职业本质的辨析,成为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理性-人性之辨
理性在古希腊思想渊源中对应逻各斯(Lagos)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前者泛指外在、客观、规范性的理性,后者指更为纯粹的理性,是通过理智手段导向真理的“理性的迷狂”。[2]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人类行为的天性,是人运用智慧以实现目的的过程,包含知性、情感和社会性等。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理性具有更高的价值,可以为了它牺牲个人需求、快乐和自由;洛克(John Locke)刻画了一副理性塑造下的个人行为模板;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维护社会契约而要求个人无条件顺从。从理性设计出发,教师一度被框限在冰冷的应然形象中,成为千篇一面孤独矗立的“理想型”。但斯腾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在人文课程研究中批判了教育设计中的“防教师”(teacher-proof)原则;[3]奥凯(Ted T. Aoki)在课程概念重建运动中同情教师“被限定为严格结构的课程的一部分,不再会创造性表达”[4];马丁(J. R. Martin)剑指理性价值观下扭曲的“象牙塔人”(ivory tower person)[5];尼尔(A. S. Neill)直接以《问题教师》(The Problem Teacher)为题叩问教师本质[6]。理性“抽象掉了作为活着的人的生活主体”[7],对人性的隐匿不彰,忽视了教师职业的心灵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危机,加剧了教师职业背后深层次的匮乏,教师宛若“洞穴囚徒”,在处处设限的虚假语境中踽踽前行,导致精神家园的荒芜、苦闷和彷徨。教育终归是人性化的事业,既需要理性的启蒙,也需要防范理性的张扬对人性的侵犯。教育砌成的城墙,永远不应厚到将理性与人性完全隔离。隆升人的地位、获得主体解放、追求生命感悟是每个教育者的理想,没有任何事业在追求人性化方面堪与教育相媲美。在教育彰显人性的呼声中,撕破教师形象的僵化面具,对教师作为“人”的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成为学者们的共识,[8]翻开了教师研究的新篇章。
(二)手段-目的之争
在技术理性主义主导下,“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深入人心。人们习惯把教师看作传递知识的手段,仅考虑手段的效用性、合目的性,至于教师本身是否作为目的则未予重视。学校被比拟为工厂或产业,教学是一种工具化行为,课程实施是一门管理技术,教师沦为生产消费模式下的“课程装置者”(curriculum installer),[9]如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形容的“末人”(last man),失去了创造力和自主性。然而,有识之士通过对生活的内向观察有所反省:康德(Immanuel Kant)强调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目的,永远不能成为手段和工具;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指出生命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珍贵,倡导“敬畏生命”;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强调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批判将存在者当作存在本身的做法;福柯(Michel Foucault)关注“自身”;胡塞尔(Edmund Husserl)关注“生活世界”……这些思想映射到教育领域,体现了生命呵护、职业关怀的逻辑反控。人们意识到教育结构具有交互二重性,从而关注教师本身作为目的的生存方式、成长过程,敦促教师在“育人”的过程中也实现“育己”,开辟了教师发展的新方向。
(三)单向度-完整性之思
随着教育流派的发展,教师职业的内涵历经了从狭隘单一到百花齐放的过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现代化开创时期,三大教育学流派(实验教育学派、自由主义教育流派和实用主义教育)呈鼎立之姿。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教育现代化进入反思时期,改造主义、新行为主义、要素主义、结构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激进主义和制度教育学等对传统派教育进行了反思和开拓。随着20世纪70年代教育现代化正式确立,终身教育、人本主义、解释教育理论、批判教育学、建构主义教育和后现代主义教育等理论层出不穷。在各种思潮的摇旗登场中,否定和反思成为常态,知识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向,传统教育模式的地位逐渐坍塌,建构教师定义的淤窄圩坝随之决堤,不断有学者以新视角诠释教师内涵。如里普斯基(Michael Lipsky)形容教师为“自主和权威的街头官员”[10],凯米斯(Carr W. Kemmis)认为教师是“解放性行动研究者”[11]。随后新的比喻不断涌现:布劳(Pete M. Blau)的“法理型专业权威”、麦克尼尔(John D. McNeil)的“课程编制中的重要层级”、艾略特(John Elliot)的“行动研究者”、舍恩(Donald A. Schon)的“反映的实践者”、罗蒂(Richard Mckay Rotty)的 “激发学生想象力的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有机知识分子”、吉鲁(Henry A. Giroux)的“转化智慧者”、鲍尔斯(C. A. Bowers)的“看守教室生态圈的管理员”……新的理解突破了认识论的限度,打破了原有的僵化镜像,促进教师职业身份的“祛魅”——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复杂人”,从“单向度人”向“全人”发展。
(四)职业-志业之盼
教师曾长期处于被裹挟的状态,教师被塑造、宣传为自我牺牲的蜡烛,是不知疲惫的春蚕,是默默无闻的春泥。在机械物化的隐喻下,教师的发展需求无人关注,劳动的快乐无人提及,价值的升华无人重视。然而,教育旨在解放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是解放教师,不快乐的教师如何带出快乐的儿童?于是有志之士呼吁,教师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项“志业”(Beruf),[12]教学是对教师人生意义的召唤。人类对意义有一种近乎执着的追求,它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志业状态下的教师是心灵守护者,带人进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13],促人升华和自我升华;志业状态下的教师是快乐从业者,“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黄榦《行状》);志业状态下的教师是理念铸造者,“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正是他们维护了理念世界,实现了圣化怀想。因此,从职业到志业的转变,意味着教师提升了教育境界,从牺牲自己转向点亮自己,享受工作过程带来的生命欢乐,让工作成为延续生命意义的载体,超越职业自限,迈向志业之盼。
二、教师发展的样态日趋开放
随着对职业本质的反省,学界悄然迎来了职业发展样态的境遇开放,这为教师发展开辟了新的疆场。
(一) 发展方式上,从技术训练到人文开发
曾几何时,教师培训就是技术性训练。当教师的发展“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14],当技术成为新的控制手段被用来规训、审掣、监控教师时,教师就沦为科层技术统治下服从技术逻辑的奴隶。但是,教师毕竟“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的力量,并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15]。20世纪下半叶以来,教师发展观在整体上“由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模式,向以认知科学、建构主义和反思性研究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模式转型;由以训练技术型为主的培训模式,向培养专家型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型”[16]。学徒制“默识”隐喻下的“传统—技艺取向”、实证主义“生产”隐喻下的“行为主义取向”,朝向现象学“生长”隐喻下的“人格论取向”,“解放”隐喻下的“探究取向”前进。[17]具体到学者,吉鲁指出,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有着转变“潜能语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ies)来改变社会的作用;[18]弗莱雷(Paulo Freire)指出,教师应具有对话精神,批判了对教师的压迫意识;[19]范梅南(Max Van Manen)提出,教师需要培养比技能复杂的教学机智;[20]古特曼(Amy Gutmann)认为,教师必须以“民主职业精神”自律,培养民主思考的能力;[21]朱小蔓等将教师职业发展与价值超越相联系,[22]等等。总的旨归都是使教师免于技术奴役,从“役于物”走向“役物”,从“他治”走向“自治”,从“执照型”走向“情感型”,从专业技术化走向专业人文化。
(二)发展动力上,从被动形塑到自觉建构
如果希望儿童是自己的创造者,那么教师也不可能是别人的灌输品。没有育己何谈育人?没有自己的主动发展何谈儿童的主动发展?外在嫁接的理论和模式只有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方式才能持久。于是,在教育理念上,结构-功能观转换成了文化-个人观,前者将教师看作被动的受管理者,后者将教师看作主动的自我引导者。[23]在教育理论上,杰克逊(P. W.Jackson)指责被动专业化为“缺陷观”,称主动专业化为“成长观”;多勒(W. Doyle)指出,教师发展应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过程;[24]伊劳特(M. Eraut)提出教师发展的补短取向(defect approach)、成长取向(growth approach)、变革取向(change approach)和问题解决取向(problem-solving approach);[25]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技术兴趣、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均促进人的发展;[26]金美福提出,以“发展极”为特征的教师自主发展论;[27]白益民指出,自我更新取向将是教师发展的新趋向;[28]程凤农设想,组织边界弱化、远离僵化态势的自组织生态系统让教师自由交换能量[29]……教师发展逐渐从外铄走向内发,从被规则走向自我解放。
(三)发展时间上,从断续培训到终身学习
断续培训是对应发展静止观的传统做法,这种做法具有片段性、断裂性,缺乏对发展水平衔接的考虑和职业生涯的规划,不利于教师的持续发展。20世纪初期,美国兴起职业指导运动,在生命发展全程观①代表有埃尔德(G. H. Elder)生命历程理论、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生命周期理论、布勒(Buehler)生命阶段理论、伯克(Laura E. Burke)毕生发展心理学理论。—职业生涯全程观②代表有列文森(Daniel J. Levinson)成人生涯发展理论、泰德曼(A. Tiedeman)自我发展生涯体系、舒伯(Donald E.Super)生涯彩虹图等理论模型、霍兰德(John Holland)职业类型理论、金斯伯格(Eli Ginzberg)职业选择理论、戈特弗雷德森(L. S. Gottfredson)职业抱负理论、阿斯汀和法默(A. W.Astin & Helen S. Farmer)女性生涯发展理论、威斯布鲁克和桑福德(B. W. Westbrook & E. F. Sanford)少数群体生涯发展理论。—终身发展观③代表有诺尔斯(Malcolm S. Knowles)成人教育理论、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自我实现理论。的影响下,[30]教师发展被统合进生涯发展研究。学者们达成共识:教师发展是持续不断地适应、应对和反思,教师需要增强终身学习能力,增加专业发展支持,积累长远职业资本,建立起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教师终身发展观照体系。
(四)发展范围上,从单一狭隘到多元生态
“教师发展”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有限境域,被限定在基本需要与实际利益的范围内,而“找不到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它开放的”[31]。因此,在承认境域之有限性的同时,也需要从广义范围来看待教师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发展除了理智取向、实践—反思取向之外,出现了第三种取向——生态取向,[32]关注与教师发展有关的广泛内容。如哈格里夫斯和古德森(Andy Hargreaves& Ivor Goodson)提出,将教师发展拓展到文化、社会中,从限制的专业主义(restricted professionalism)向扩展的专业主义(extended professionalism)转变,由个人能力本位的孤立发展转为合作共享的社群化发展;[33]利特尔(J.W. Little)指出应为教师提供学识的、社会的和情感的多方面投入;[34]埃文斯(S. L. Evans)认为教师的发展包括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在内的职业态度发展;[35]哈蒙德(Darling Hammond)认为教师发展需要校内外资源支持;[36]戴(Christopher Day)强调将教师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37]21世纪,随着信息化工作方式和“无边界职业生涯”(boundaryless career)[38]时代的到来,网络虚拟组织、跨界社群组织等为教师发展提供了更多样的途径。
三、教师发展的研究不断创新
“有效地做”是在“做的意义”和“怎么做”的归属下进行的,“怎么做”成为教师发展研究的创新点。
(一)从教师缺席到教师卷入
“教师自我缺席”“教师声音不合法”曾经是研究者的默认规则,教师也习惯于这种不在场的存在模式,把自己仅仅当作研究对象。然而,教师研究的终极指向是教师本身。一方面,教师有自我理解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携同“局内人”、排斥“局外人”是人类社会的天然本性,纵隔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群沟”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开展。20世纪30年代进步教育协会开展的“八年研究”和“南部研究”,促使研究者与教师之间形成主体间性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凸显教师自我剖析和自我建构的价值。近年来教师研究领域的新运动——自我研究[39]、自传研究[40]、合作性叙事研究[41],彻底打破教师与研究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教师成为研究者。
(二)从居高临视到在地倾听
研究者在教师研究中习惯从居高临视的角度,让教师陷于古德森形容的“被沉默”(silenced)状态,导致教师生活世界与公共教育话语的分离和对立。在后现代思想影响下,教育研究从自然科学范式转向人文理解范式,[42]“倾听”与“对话”的潮流席卷了教师研究领域。通过倾听与体验、对话与理解,关注弱者权利和底层心声,放大了教师微生活,揭示了教师群体的复杂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倾听是把握教师研究精髓之所在:当研究者是倾听者而不是打扰者时,更能获得被研究者的接纳和亲近;当研究者主动追问与倾听,而不是被动等待与观察,更能获得完整、深入的结果。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倾听是教师发展本真之需要:因为个体习惯于自己原有的经验模式,所以难以从自身经验之外的角度发现矛盾和问题。如果研究者与教师共在,研究过程即是一种交往、移情和体验,就能帮助教师从封装(encapsulation)状态解脱出来,促进教师自我理解。
(三)从重视结构与结果到重视现场与过程
重视结构与结果的代价往往会导致“学究式谬误”,即用研究者逻辑代替实践者逻辑,造成研究结果与研究实际二者之间的断裂,也让研究者解释无力、指导无效。这种研究惯习已逐渐被重视现场与过程的思维打破。教师的发展要在教师工作现场获得。[43]教师研究就是一种在场(presence)和际遇(encounter)。有效的教师发展是“嵌入”日常工作的,与教师的具体需求和关心的事情相联系。[44]关于教师的知识、场景、身份、个人叙事和经验反思的研究很重要,每个教师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都是生动的故事叙事者,持有现象学中的“第一体验”,只有到现场观察才能理解其言行。因此,教师研究要回到教育现场,弥补教师研究远离教师生活的遗憾。教师发展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只要与过程的关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45]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视界融合”的过程,[46]通往视界融合的途径是对话,理解和对话消解了主客体对立,研究的意义应该建立在坦诚的对话过程中。因此,注重现场与过程的研究,特别是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显得更具有价值。学校生活是教师基本生活形态,需要进场研究、场域分辨、在场分析,进行过程探访、过程积累、过程分析,通过现场和过程来建构教师生活的意义结构。
(四)从批判矫正到关怀唤醒
研究者相对于教师总是具有知识权威性,而教师也在权威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中工作。根据福柯后结构主义模式,知识是权威人士认定的,权威是权力场的话语主导者。权威控制的弊端使得优势阶层利益合法化,对教师批判、矫正的思维倾向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得以持续。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促使人们意识到被日常理解所掩盖或扭曲的矛盾冲突。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秉持关怀伦理立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鼓舞自己迎向光明的力量。[47]研究者应成为教师的重要他人,关注教师的实存状态、心理健康和职业幸福。教师发展即是赋权教师的过程,教师研究也是提升教师的过程。这种转向体现了一种“关系关怀”,即用相互接纳的温情方式,站在增进了解、角色共生的高度上,为教师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景敞视的大门。
四、结语
从教师发展的历史深处走来,静观社会和文化对教师的冲击和濡化,一路寻绎教师职业的变迁脉络,展望教师发展的样态趋势,期待高质量的教师研究模式。当前的教师发展已呈现出多样化的走向,教师自身迁就现实的心理消耗与追寻理想的精神向往,会在现实情境中长期相较相持。“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是教师职业的神圣使命,是每个有理想的教师的终极目标。回顾以往、反思当下,正是“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精神动力”[48]。我们相信并向往:当理想与现实相互辉映之时,当职业与生活齐头并进之时,当身体与心灵融为一体之时,教师的发展就能收获持久的动力、真正的意义和内在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