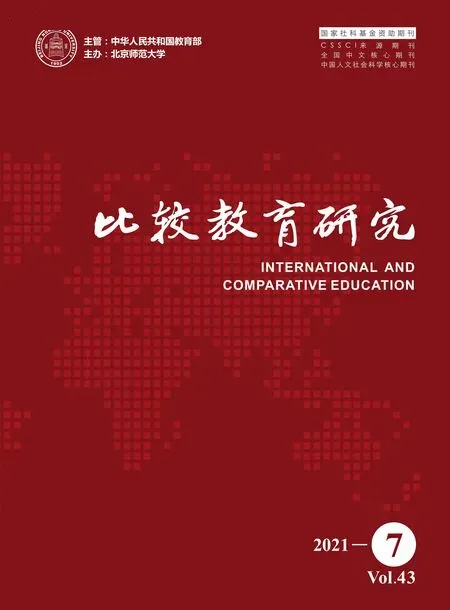美国联邦政府干预公共教育起点问题的再讨论
陈露茜,夏青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联邦政府无权干预教育问题,源于美国宪法及其第十一修正案的推论,而非事实情况。针对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干预教育事务的现象,国内外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关于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起点问题,已有研究认为,联邦政府干预公共教育源自18世纪中后期的《西北土地法》,即18世纪中期的西进运动对西部新州土地测量与管辖的讨论所形成的1784年法(The Ordinance of 1784)、1785年法(The Land Ordinance of 1785)和1787年法(The 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这三部《西北土地法》共同塑造了联邦以赠地的形式干预教育的起点。①国外核心研究成果包括:LEEG C. The struggle for federal aid, first phase: A history of the attempts to obtain federal aid for the common schools, 1879-1890[R].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No. 957, 1949; ZEITLIN H. Efforts to achieve federal aid to education: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new deal[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59 (69); BERKE J S. Full federal funding: educational nightmare[J]. Current History, 1972 (63);KAESTLE C, SMITH M S. The federal role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1940-1980[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82(4); BEADIE N. Educ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capital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国内核心研究包括: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朱旭东,李立群.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1999(4).但在系统梳理这三部《西北土地法》制定、讨论、生成的国会记录和档案后,本研究发现,《西北土地法》中教育条款的出现并不是联邦有意为之,而是意在提高西北新州的地价、稳定移民的妥协方案。《西北土地法》颁布后,并没有增强联邦的角色,反而给各州向联邦索要赠地或者等值的土地期票以有力的法律依据。它在事实上增强了各州的权利,而非联邦的干预。如果18世纪中期的三部《西北土地法》不足以作为联邦干预公共教育的起点事件,那么美国公共教育中的联邦角色又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开始出现的?本研究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回答。
一、重新认识《西北土地法》:政治经济学设计中的1784年法与1785年法
本研究发现,18世纪中后期,联邦出台三部《西北土地法》的初衷意在土地售卖和移民安置,其中教育条款的提出仅是建立有序西部社会刺激下的附属品,并非联邦有意干预公共教育的产物。
早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各州就开始针对西部土地问题争论不休。1783年4月,当时的大陆军军官将领就曾经为解决遣散士兵的生计问题草拟了一份西北新州建立和政府运行的详细计划,被称之为《军队计划》(Army Plan)。该计划要求国会向大陆军军官和士兵拨赠土地在俄亥俄以西建立一个新州,新州加入联邦并享有和其他各州一样的联盟权利;拨赠后的剩余土地作为州的共同财产应根据人民的共同利益来处理,例如修建道路、桥梁,建立学校、学院,支付政府及其他公共开支。[1]这份计划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在西部土地的设计使用中提及教育问题的草案,并曾在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支持下提交到国会讨论,但国会并没有通过这项计划。[2]
1784年2月,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あerson) 再次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西部领地临时政府计划书》。这份计划书于1784年4月23日在国会讨论通过,即后来的1784年《土地法令》。但不论从1784年《土地法令》文本,还是法令讨论的过程来看,有关教育的问题从未被提上国会议程。这部法令的主要目标是尝试解决西部新州土地的售卖和管辖问题,“这一时期的所有金融家都把西部土地视作一种可以马上变现的资产,用以支付当前政府开支、偿还国家债务”[3]。同时,一旦涉及土地售卖问题,又将牵涉各方的利益,对于人口本就有限的大西洋各州政府来说,失去人口就是失去财富的重要源泉。[4]也就是说,如果西部待售地的价格足以吸引东部各州居民购买、移民,这将加速西部土地的出售、开发以及新州的建立,那么,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增值空间的广袤西部将对东部的经济政治地位造成潜在的威胁。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地售卖土地以解联邦的燃眉之急且兼顾未来东西部之间的政治经济平衡,这是摆在国会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针对土地的安置和售卖问题上,杰斐逊在1784年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西部领地安置模式与土地处置草案》(An Ordinance for Ascertaining the Mode of Disposing of Lands in the Western Territory)。[5]这份草案与1784年《土地法令》一样,并未提及未来新州的教育问题,在1784年5月28日的国会讨论中也被否决。但与此同时,国会开始与印第安人就俄亥俄河以北的土地事宜进行谈判,目的是希望尽快迁走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彻底开放西部土地。为此,国会所指派的事务专员分别于1784年、1785年在纽约州斯坦威克斯堡和匹兹堡附近的麦金托什堡同印第安人签署了土地割让协议。协议签署后,再次使得西部公共土地的安置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杰斐逊在1784年所提交的土地处置草案被再次讨论。在讨论中,原《军队计划》的执笔人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曾致信议员卢弗斯·金(Rufus King)指出,目前的方案中“没有福音事业的条款,甚至也没有学校(schools)或学院的条款……至少后者应被纳入考量”[6],这一意见最终被国会采纳。在1785年4月15日格雷森致华盛顿的信中,格雷森提出,“因为提出了支持宗教和教育的诱因,镇区的理念有利于吸引土地购买者并促使定居者们居住在一起”[7]。
格雷森口中的镇区理念,即后来的1785年《土地法令》中所采取的土地安置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新英格兰(这一模式在之前的军官提案中也曾被提及)。不同于南部分散定居、大块授地的管理方式,镇区理念强调定居者的集中性和互助性。在镇区模式之下,土地勘测先于定居。也就是说,先由政府当局对土地进行测量、划分,再将确定的地块数量及其布局边界登记在册,最后以镇区拍卖的方式进行售卖,其中“用于教育和宗教目的的土地拨赠是该土地系统中的一部分,这种拨赠常常是为了土地改良”[8]。教育授地不仅可以成为吸引移民群体的诱因,还能成为提升周边地价的手段,而学校本身的文化力量也使得地区居民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利益、情感的一致性,进而实现社会同质化,这将让有序的社会生态得到良性循环。
教育拨地这种一举多得的利好手段在1785年《土地法令》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国会的青睐。对于债台高筑的联邦来说,国会无疑期望增加现有土地价值,吸引更多的购买者,通过土地变现以缓解财政压力。这种观点在之后的国会讨论中再次得到确认,“捐赠第16地块来支持镇区,这对买家来说是一个诱因,并且增加了周边土地的价值,周边土地的出售则补偿了政府的教育赠地”[9]。
1785年5月20日,国会最终通过了西部土地勘测安置计划,即1785年《土地法令》。法令规定在土地勘测方面,由联邦指认地理学家领导、组织公地勘测,测量员应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直线将公地划分成为6英里见方的镇区(township),再将每个镇区划分成1平方英里(或640英亩)的地块(lots),并标以1-36的数字。在土地分配上,除军功授地外,剩余土地以不低于1美元的价格公开拍卖,每个镇区要为合众国保留第8、第11、第26和第29四个地块,以备将来出售,第16地块留作每个镇区中的公共学校用地。[10]
由此可见,在1785年《土地法令》的制定考量中,国会关于教育条款制定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促进教育本身,教育问题的出现仅仅是联邦在债务危机下最大限度进行土地出售和建立有序西部社会刺激下的附属品。其中对教育赠地的规定并非源自联邦对教育的有意干预,但这里对教育的讨论成为日后1787年《西北土地法》关于建立西部永久性政府详细计划的基础。
二、联邦意图的初显:公立学校运动中对“同质化”的寻求
直到19世纪早期,联邦都没有直接干预教育的意图,它对教育的考量更多的是从学校与教育的外部功能——抬高地价、稳定移民——出发,而不是从教育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出发,这使得早期的联邦角色显得暧昧与不确定。而这一时期,公立学校运动的出现迫切要求打破教育的地方主义传统、塑造“同质化”的学校形态,这成了联邦干预教育最早的突破口。
(一)1787年法中教育条款的出现仍意在联邦所有地的保值
1786年3月,俄亥俄公司(The Ohio Company)建立,决定以股份认购的方式公开募股,开始了俄亥俄地区购地拓殖计划,但认购率一直非常低。1787年3月8日,俄亥俄公司派出公司董事与国会商讨西部购地问题,并于5月9日向国会提交了购地备忘录,建议将每个镇区中的第16地块永久地用作公共学校;第29地块用作宗教;第8、第11和第26地块留给未来国会处理。另外,将4个完整的镇区用作大学。[11]在此基础上,1787年《西北土地法》成型,并于1787年7月13日被讨论通过。
1787年《西北土地法》颁布后,俄亥俄公司与国会签订了西北土地购买协议。但在购地案生效后,联邦政府并没有马上进行教育拨地,这是因为西北准州的建立需要一定数量的移民。而早期迁入西北的移民数量少、分布分散,且移民成分多样,其中不仅包括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还有来自中部、南部的移民。移民团体的分散性和异质性引起了俄亥俄公司的注意,公司董事们再次呼吁应尽早关注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在1788年3月的公司会议中,决议要求“要在首批移民中推广公共教育,如果可行的话,应聘请一位拥有丰富知识与良好道德的导师监督学术机构、指导教学方式,保证(公司)董事会的决议精神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并希望业主们和开明人士能捐款成立一项基金支持这一事业”[12]。可以看出,在俄亥俄州建立早期,由于没有形成相当数量的移民群体,联邦政府并没有立即对该地区予以任何形式的教育资助,教育事业仅在地方层面受到关注。
直到1802年,俄亥俄达到准州建立资格时,联邦政府才通过授权法案向俄亥俄进行教育用地的拨赠①尽管一些公共土地早已向移民开放,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任何教育赠地行为。相较于俄亥俄州,一些南部的公共土地州更早建立。当1796年田纳西成为新州时,国会没有做出任何条款规定,即便国会在1796年、1800年通过了一些土地法令,也没有任何关于教育赠地的条款。密西西比领地立法机关曾在1799年向国会请求拨赠学校用地,国会在1800年讨论该请愿时以密西西比领地内一些土地问题尚未解决为由驳回了密西西比的授地请愿。Ellwood P. Cubberley, Edward C. Elliott.State and county school administration: source book.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15, pp. 21-22. Howard Cromwell Taylor.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early federal land ordin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22, p. 103.,规定向每个镇区拨赠第16地块用于教育。但国会对所赠土地进行了以下限制:一是俄亥俄在5年内不得向联邦所持有的公共土地进行征税;二是联邦只在七排镇区、俄亥俄公司和西敏司公司的购地范围内向各镇区拨赠第16地块。这些限制性条款引发了俄亥俄州土地业主们的不满,业主们希望国会能修正赠地条款。1803年3月3日,国会对赠地条款进行了修正,最终由财政部挑选269,771英亩的土地拨赠给俄亥俄地区内的各镇区,用于领地内的教育事业。[13]
从俄亥俄州的教育赠地实践中不难看出,联邦政府没有对新州的公共教育管理进行过多干预,仅仅是对教育用地拨授的范围作出限制,这是联邦政府需要保证它手中所持的公共土地价值不致贬值。在之后的实践中,联邦对俄亥俄州的教育赠地经验被移植到其他西北新州的教育授地中。例如,印第安纳州在1816年加入联邦时,联邦将第16地块拨赠给了各镇区,将用于建立大学的赠地拨赠给了州。[14]
(二)公立学校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对抗成了联邦干预教育的突破口
值得关注的是,与西进同时展开的,还有美国的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学校运动。事实上,在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所谓“公共学校”的称谓与内涵是非常混乱的。即便如此,在林林总总的早期的“公共学校”之中,还是可以观察到两种最基本的模式。其一是志愿主义模式,它由无薪的、志愿式“不求回报”的家长团体或者拥有特许状的法人团体负责组织管理,代表着市民阶层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例如,纽约公共学校协会就是此类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类学校由于其管理开销小、财政整合极为细致所带来的高效运转,使得该协会得以在数十年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学校网络,每年能教育数千名学生。其二是地方主义模式,它由地方学区来运营学校并保持各个城市中独立学区的独立性,进而使得教育的“全权”保留在“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人民手中”,早期的学区制就是此类学校的典型代表。[15]
当时无论是志愿主义模式,还是地方主义模式,其宗旨都仅是为极贫困者提供免费的学校教育,为贫困儿童提供基本的读写能力与道德行为的培训,以此“对抗由儿童家长的状况而导致的弱势处境”。这说明,一方面,在共和国的早期,“公共”意味着行使广泛的社会职能,面向庞大的、多样化的社会底层,带有社会阶层标定的意味;它不属于社区或州,也不归社区或州管理;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普及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为目的的、以税收来维持的、由教育专业团体来管理的免费的公共学校。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散乱的学校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杰斐逊式的民主政治治理模式——由低税收所保证的小政府、由小政府所带来的权力分散——的延续。因此,19世纪上半期,美国所延续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本能地对全国性的运动持有怀疑态度,这使得19世纪上半期的公共学校运动的推进步履维艰。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在《美国公共教育》一书中所描述的公共学校体系建立过程中所遭遇的激烈对抗中得到印证。可以说,贺拉斯·曼(Horace Mann)和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erd)等公共教育运动的领导人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棘手。第一,如何将公共学校与施舍式的慈善事业或者阶级标定切割开来;第二,如何将公共学校与家长的付费能力切割开来;第三,如何将公共学校与外行管理分割开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公共教育运动的领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来消解不同的意见与抗争。换言之,就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充满异质性的社会环境中更加有效地去领导一场全国性的以学校制度的高度同质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运动。
三、联邦角色的确立:联邦政府、工业化与公共教育“同质化”的达成
(一)联邦政策的强势引导成就了工业化
19世纪中期,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崭露头角,制造业迅猛发展,工厂制和生产的集中化在全国范围内快速铺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联邦政策的强势引导。它所依靠的三大核心政策包括: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结构;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和对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16]
首先,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是政府控制的政治结果。在前工业化经济中,美国所遭遇的核心困境在于美国国内市场的分割状态,国内的市场事实上被切割成许多小的市场单元,这极大地拖延着强势工业化的整合:市场供应中心与需求中心之间相隔甚远;由农业生产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铁路运输的特殊需求。前两个因素产生了对大规模、长距离的货运的巨大需求——如何有效地将南部和西部的农产品运到北部市场,又如何将北部的工业制品倾销到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一切都要求美国铁路网络的迅速扩张。1836年,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出售公共用地,将2000万英亩的西部公共土地抛向国内市场;1837年,因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拒绝接受私有银行的支票购买公共用地,土地热潮暂时低落;1855年和1856年,第二次土地热潮出现,3500万英亩土地由公共用地转为私有财产;1883-1887年,第三次土地热潮出现,在这一过程中,每年都有超过16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转化为私有经济。[17]当时联邦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通过销售公用土地来推动宅基地定居和以后铁路建设的授权。也就是说,只要飞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建设能够给这些土地开出一个价格,就尽可能地将这些土地转为私有土地。联邦政府释放给市场的信号是:只要修建通向美国平原与山区的新铁路线,就可以从联邦政府手中划拨走大片土地。就这样,美国庞大的铁路运输网络飞速完成——联邦太平洋铁路、圣达菲铁路、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铁路,等等。
在铁路修建完成后,铁路的管制问题得到了政党的关注。例如,1880年的《里根法案》(Reagan Bill),后来成为《洲际商业法案》的原型被纳入国会的议事日程。[18]在绝大部分的政党纲领中,他们都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对铁路网络施行政府所有的制度;“政府管制”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府的政治纲领之中。[19]而对于要求施行联邦一级的管制或者拥有铁路的运营商,公众与政党并没有给政府有效施压,或者说,其中潜在的隐患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可见,在寻求统一的国内市场过程中,留给自由市场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多,虽然市场依然需要价格信号来反映需求,但是原料的供应、生产、协调、销售等一系列市场交易行为都转变为企业的统一决策;而决定企业的统一决策的核心要素在于,美国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建立并主动行使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促成了国内统一经济体的成型。
其次,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宣布放弃金本位,这导致了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美元的实际购买力的大大下跌。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重新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并于1879年重回金本位制,从而保证了美元与主要国际货币(特别是英镑)之间汇率的稳定性。这一担保消除了外国在美投资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由此决定了欧洲资本市场与美国资本市场相对紧密的一体化。这种紧密的一体化一方面“使得纽约与伦敦的资本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便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市政府发行公债……这两个市场在金本位制下的融合鼓励资金的保留,避免资本聚集到不能盈利的工业企业”[20];另一方面,保障了工业公司产生的巨额利润滞留在美国——要不是金本位制及其配套的中央财政政策的运作降低了投资于美国的风险,这笔巨额的财富完全可能被转移到国外去。尽管金本位制在当时多次遭到国会的攻击[21],但是两党总统所率领的行政部门先后成功地在政坛捍卫了金本位制,并强有力地在金融市场上操作了这一政策。
再次,关税保护政策。从经济上看,关税政策保护了美国工业免遭外国工业的竞争,促进了北部地区制造业快速地扩张。西部农业出口地区,以及(特别是)南部农业出口地区被迫从受到关税保护的国内制造商手上购买工业制成品,同时,成为竞争性世界市场的农产品——诸如小麦、棉花等的价格接受者。换句话说,美国通过将财富从消费型农业(尤其是棉花与小麦)重新分配到重工业当中,加速了重工业产业的资本积累。从政治上看,19世纪的关税保护政策还与民族主义的情绪捆绑在一起。通过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工业关税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英国的利益之上,并且通过这一方式向那些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北方士兵支付战争抚恤金”,“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国内对国家忠诚的呼声”[22]。
由此可见,这三大政策一方面刺激了美国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过程;另一方面充分地调动起国家政治对工业化的高度关注,联邦政府构成了政治与经济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可以说,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个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的成就,政治与经济发展并非两个泾渭分明的过程。恰恰相反的是,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正是根植于联邦政府这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23],它们密切联系、不可分离,最终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创造了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奇迹[24]。南北战争的爆发和战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强有力地扭转了19世纪初期所保留下来的分权化倾向;在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统一以及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机器,也进一步明确了联邦政府的权威。
(二)工业化的胜利整合了公共教育系统
由联邦政府所强势领导的工业化过程驱逐并消解了自18世纪以来由小政府所带来的地方主义情绪,进而领导了公共教育系统的整合。“如果民主政治要求它的公民具有诸如稳健、理智、诚信这样的品质,他们需要用其他的方法去获得这些品质……匆匆填补这个缺口的教育改革家——贺拉斯·曼、亨利·巴纳德及其助手们——许诺在孩子们性格可塑、容易形成习惯的公立学校读书时期,塑造这些民主分子的公共品质。财产不再能做到的事情,学校里老师们将能够做到。曼宣布,民主的公民拥有‘接受教育的绝对权利’,他们的社会同样有一种使他们接受教育的强制性责任。”[25]
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贫困、犯罪和不道德现象蔓延,使得城市之中的阶级鸿沟日益扩大,学校开始被视为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性机构;而学校如何防止城市的堕落,其中愈合城市中阶级的分化就迫在眉睫。“没有人了解家庭环境的缺陷,没有人了解家庭生活、贫困家庭以及文盲家庭的混乱无序,更不要说一些不节制的行为。例如,粗鲁的态度、肮脏猥亵的语言以及散懒成性带来的种种恶劣的习性,这些问题在某些人满为患的地区比比皆是。因此,毫无疑问,要尽可能地让儿童远离这些环境与反面教材,而且要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作为家长的城市贫民的无能,意味着需要改变天然形成的家庭背景,取而代之以人为形成的家庭环境。”[26]这要求学校用一种长时间的、制度化的、结构缜密的正规教育来确保所有儿童合格的出勤率,让儿童摆脱家长的影响、转而接受学校的影响。因此,学校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智育,而是要规范情感和品格、纠正恶习、让心灵美的种子播散在儿童年幼的心灵狂野之中,通过清洁、缜密、文雅、好性情、温顺、善良、公正和真理等习惯的养成来塑造天真可爱、德才兼备的品格”。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长时间的、制度化的、结构缜密的正规教育暗含了城市生活和制造业对“合格的工人”的要求。1841年和1859年,当贺拉斯·曼和乔治·鲍特韦尔(George Boutwell)分别就教育的意义问题征求企业家意见时,他们收到了如下的答案。有人认为,相对于品行而言,知识是次要的,一个受过教育的工人,其行为应该“更有纪律、更有礼貌”,更愿意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同样有经验的资本家认为,“我往往支持那些最有智慧的、最有教养的、最有德行的人”。这无异于说,“最吵最麻烦的,往往是那些无知和没教养的人,他们往往容易情绪激动、嫉妒猜忌”。德行兼备是极为重要的:教育、品德、顺从都是同等重要的;这成了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三大品格,这“既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又是一种美德”。[27]
由此可见,联邦政府、工业化和公共学校运动开始进入一种“互惠互利”的循环之中。其一,19世纪由联邦政策的强势引导促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自由市场”在全国范围的崛起。与此同时,由联邦所赞助、鼓励、支持的快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集权的需要。其二,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带来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结构与要求,现代企业由诸多专业化部门构成,由领薪水的管理人员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为公共学校的快速推进提供了迫切需要的全国性的、同质化的助力——科学、效率、一致性与科层制。其三,公共学校运动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化提供高水平、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日益提升的专业化、系统化知识结构。[28]
综上所述,在推演美国联邦政府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开始干预公共教育时,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条逻辑:19世纪早期的美国公共学校运动迫切需要一条有效的“同质化”策略来消解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教育地方主义;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的工业化与工厂制——科学、效率、一致性、科层制,有效地为美国公共学校运动提供了一条逻辑缜密的“同质化”策略。但美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一条有效的“同质化”策略,根源在于南北战争后强势联邦政府态势的出现以及它在19世纪后期的引导、干预、成就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因此,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的联邦政府的强势角色与干预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无论是经济手段也好,组织模式也罢,都仅仅成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联邦政府借由具象技术手段和强有力的显性措施抽身而出,并将其意识形态隐性地、更加牢固地“嵌含”在教育教化之中,进而在实践中达成了美国公共教育的“一种最佳体制”(One Best System)。[29]
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邦政府在美国公共教育中主导角色的成型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伴随着由联邦政府所主导的美国工业化进程而逐渐完成的过程,而不是某一部法案或者法令一蹴而就的结果。1867年,美国教育署(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成立;1875年,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在对国会呼吁要求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联邦给予各州永久维持免费的公立学校所需的必要支持[30];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的颁布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标志着联邦政府在美国公共教育中隐形的、牢固的干预角色的成型,并由此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公共教育中的不断强化的集权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