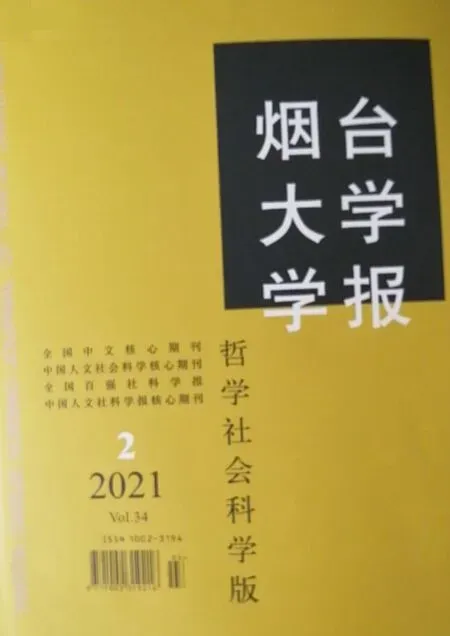“子道治子身”: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刘国宣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近二十年来,一部本是民国中学教科书的《中国史纲》成为众多出版机构竞相出版的历史作品,该书作者张荫麟(1905—1942)随之进入大众文化视阈,且日渐“升温”。身为在学术上臻于早熟的天才型学者,其短暂而传奇的生涯,及其偏向于普及的史学实践,致有今日这一现象的出现,殊不足异。然而当一位专业学人成为世俗追捧的对象之时,对他的认知往往会偏离严肃的学术史叙述,滋生出对其思想的臆测误判、对其学术的偏见曲解等一系列问题。1963年,谢幼伟撰文称,“这一位天才学者”,“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1)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67页。俗世的善忘本属常态,但按诸张氏身后史事,谢氏此言或不免失实。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张荫麟的著译作品在海峡两岸多次重版刊行,有关他的回忆文字、研究论著也不时涌现,可见所谓“遗忘”一说难以成立。尤其近年来陈润成、李欣荣诸先生在汇编张氏遗著、蒐辑生平资料方面做出的努力,更值得研究者深致感谢。(2)参见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欣荣、曹家齐:《张荫麟评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通常来说,张荫麟以通史和宋史研究著称,但许冠三教授根据徐规先生《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3)此文收入徐规:《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而察知,“在史学上,他的兴趣不只广泛,且显得有些杂乱。遗文不只品类繁多,且良莠不齐”,“直到受托写作《中国史纲》以后,他才以秦汉前古史为撰述主体;直到抗日圣战爆发之年,他才以赵宋往迹为研究对象”,(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5页。研究者对许先生的这一论断多所忽视。再如张荫麟承梁启超的影响而措意于“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探讨”,一度潜心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并成为其早年治学期间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此节即少为学界关注与探讨。(5)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1年)与朱潇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之辨:1920-1940年代史学转型中的张荫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一章第一节《大师的引入:梁启超与张荫麟的学术渊源》对此点先有所涉及,但俱非两家着力考论之处,研究取径亦与小文殊科,然而对增进笔者的理解均助益甚多,殊未敢以拔赵立汉自视耳。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张荫麟的学术研究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一、“第二梁任公”:追踪梁启超
一位卓异的史学家,固当“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6)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2页,但要使沉潜考索的研究得到理想的呈现,由考据进乎义理的同时,更需在表述上构思涵泳,用张荫麟的话说,即“忠实之艺术的表现”(7)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他素以兼擅词章、考据和义理的治史风格见称(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55页。,生平持论,也向以“科学”与“艺术”相兼来界定史学(9)见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张氏这一持论或有意针对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主张,参见王家范:《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3页。但先此两年,胡适即曾指出:“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事实的叙述与解释。”这对张荫麟或不免有所影响。语见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0页。。“科学”侧重于史料解读,“艺术”侧重于史学表述。在崇尚考据且多有将考据等同于史学全体的当时,很少有人如他这般着意强调史学表述的重要性。事实上,张荫麟“是以考据起家的”,“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考据的”。(10)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67页。但即使是考据文章,在文字的斟酌锻炼上也多费思量。为其博得盛誉的《中国史纲》,淋漓尽致地将作者的史学、史识与史才表见无遗。爬梳前贤时彦的议论,此书最令人惊羡的,乃在以现代语体文,贯以沛然的文思、华美的辞采。虽然间有学者指出其译述古事,在“文字的优美与意境的神远”上,尚“不能企及于原文”,“轻灵有余、翔实不足”的写作风格,“在充分反映近代史学的成就方面,则显得单薄无力”。(11)杜维运:《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序言》,《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7页;王晴佳:《张荫麟的史学》,《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508页。然而试与同时及后出的通史著作相比,《中国史纲》在表述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不容置疑的。追溯张荫麟这一取向的源头,无疑当推之于他负笈清华时的老师梁启超。
当张荫麟读书清华时,专业化的现代学制尚未建立,导师个人的学术与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往往很大,如梁启超、王国维和吴宓等,都是对张氏产生持续而深刻影响者。尤其梁启超在张荫麟早期的学术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2)参见朱潇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之辨:1920—1940年代史学转型中的张荫麟》第一章第一节《大师的引入:梁启超与张荫麟的学术渊源》,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影响远在他人之上。但这段师承授受之谊,却很少为张氏本人述及,或许与他平生刻意强调“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有关。就其早年发表的论学著作观之,多与梁启超密切相关。此时已值任公晚年“专力治史”之日,“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其治学重心则在史学方法的归纳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13)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1929年1月。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典范的确立,即完成于此时。梁漱溟曾指出,“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14)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转引自李渊廷:《梁漱溟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78页。张荫麟在史学上,无论所呈现出的敏锐史感与丰茂辞采,抑或对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汲取与蕴藉,无不折射出梁启超的治史身影。
师友谈及他对梁启超追蹑效仿,多从史学造诣尤其行文表述方面着眼。如吴宓称张荫麟“博雅能文”,为“第二梁任公”(15)吴宓:《吴宓日记》(第8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04页。;贺麟称之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16)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谢幼伟说“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17)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79页。;李埏称其“最向往追踪梁任公”(18)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169页。;等等。这是有实据可验的,并非印象之说,揆诸张荫麟对梁启超的评骘,足相印证。在他看来,“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如《春秋战国载记》《欧洲战役史论》等名篇,“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19)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这便是他心仪梁氏史才的直接袒露,而尤偏重于其表述方面。他总结梁启超“自戊戌至辛亥间”异彩纷呈的学术贡献有三,“一则介绍西方学问”,“二则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三则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20)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1929年1月。浦江清称张荫麟此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清华园日记》1929年2月6日),但未必没有暗含张荫麟的“夫子自道”。综观张荫麟的治学实践与风貌,从关注并翻译西方哲学、社会学论著,到长期研治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凝聚毕生心力从事史学的探讨与撰述,与任公何其酷似乃尔!可以说,他早年治学,全面接受了梁启超的影响。
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初成为新的学术领域。当清廷政治权势尚存绪余之日,章炳麟、刘师培、王国维、邓实等已然率先展开对清代学术的回顾与总结,预示了一个时代学术即告终结。然而真正将清代学术的研究引入现代进以形成风尚的,决属梁启超,至如胡适、钱穆、顾颉刚等,均是承梁氏启发而参与到这一学域中的后起者。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趋进与形成,建立在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民初以来,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和重估被持续提倡,自有其现实意义。章、刘、梁等人本身即是脱胎于清代学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与关怀,借其门人弟子在民初学界的权威而产生深远影响,亦不足怪。但究其根源,这一风气的形成,终究系于清代学术的特质:清儒嗜古的治学宗尚和考古的学术工作,使清代学术的范围涵纳了自先秦以来历代的学术思潮,隐然化身为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缩影。而梁启超顺应晚清以来国内社会政治激荡、欧美思想资源涌入的时势,有意赋予清代学术以“文艺复兴”的况味,更使之具有了不止步于维系古代与现代的意义,同时也关联了晚明以来的东方与西方。遗老新进,无论基于感情抑或治学之需,咸有寄寓焉。
梁启超身殁不久,张荫麟撰文纪念,称誉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21)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1929年1月,另见《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熟悉其行文者不难发现,凡张荫麟对前辈学人激赏推崇的方面,往往也是他深予认同并追随投入的方面。(22)一个可以参证的事例是,张荫麟称王国维“治学方法与并世诸家有一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锐敏是也”,又称之“当此举世沉溺于实用观念与功利主义之中,独有人焉,匡矫时俗,脱屣名位,求自我之展伸,为学问而学问”。类似议论,盖实录之外,多见张氏的夫子自道。语见《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设定(范畴、意义与学理基础)为张氏接受,心同理同,更继而有所深入。就其后来发表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著而言,许多篇章撰写的初衷,人物研究的缘起,正是基于“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均无只字及之”而去补苴阙遗、匡正疏失的。(23)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年1月25日。应予注意的是,梁启超对自己开辟的这一学术领域的认识并非前后一致。他早年师从康有为,崇尚今文经学与宋明理学,对清代学术本存轻视,在承认清儒治学“饶有科学精神”的同时,也强调清代考据学“支离破碎,汨殁性灵”的面相,甚至目以“牛鬼蛇神”。(24)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第87页;《新民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6页。其观念认识与论述系统臻于定型,尚在新文化运动之后。(25)据胡适说,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其最终研究趋于定型,实因受到自己“整理国故”的影响而亦步亦趋。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433-434页。这未必是胡适的自我标榜,吴稚晖即有同样的观点。他观察到梁氏“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语见《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载《吴敬恒选集(哲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133页。值得注意的是,张荫麟与胡适的学术立场始终相左,并曾不著名姓地对他“整理国故”的事业予以挖苦,对此,胡适晚年尚不无遗憾(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但果若胡、吴二家所述,那么张荫麟不啻为胡适的间接受益者。张荫麟对梁启超开拓学域的赞许,其实特指梁氏晚年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结撰以后的学术努力。换言之,张氏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实际影响,集中于梁启超“为学问而学问”的晚年“专力治史”之后。
二、“感应”与“发皇”: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索
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张荫麟早年倾注心力最多的领域,他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才名震一时”(吴晗语),多半得力于这方面的积累。1923年,仅为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学生的张荫麟发表了《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载《清华周刊》第300期)一文,是他研索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篇作品,至1940年《王鎏——道光间建议管理货币及白银国有政策者》(载《益世报·史学副刊》)的发表,前后十七年间,他一共撰写了相关论文四十余篇,约占全部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这些论文大都属于作者的创制,或有依傍,绝无蹈袭,诚能为此方面的研究开出光焕的新景。
他曾就撰写通史时的史事取舍提出“新异性”(Novelty)、“实效”(Practical Effect)、“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训诲功用”(Didactic Utility)、“现状渊源”(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等五项标准,这五项标准恰恰可以移作他择取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主题的依据。作为学术史处女作的《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是对乃师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补苴修正之作,由此发轫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科技史研究的先河,为中外科技史家提供了研究范式与取材之资。(26)关于张荫麟对科技史的兴趣与成就,参见徐规、王锦光:《张荫麟先生的科技史述略》,《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稍可补述的是,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很可能受到了阮元《畴人传》的启发。此外,《钱大昕和他的著述》(1924)是近代首篇研究有清最具“科学精神”的一代通儒钱大昕学术著述的论文;《洪亮吉及其人口论》(1926)以比较史学的眼光展现洪亮吉的社会学思想;《纳兰成德传》(1929)系以翔实的史材、严谨的考证结撰的行文粹美的纳兰氏传记;《戴东原乩语选录》诸篇仿照《浮士德》,以颇具文学意味的体裁和奔放的历史想象力剖析戴震的哲学旨趣,间论时政;《清代生物学家李元及其著作》(1924)、《王德卿传》(1929)、《王鎏——道光间建议管理货币及白银国有政策者》(1940)等则着力表现清代学术史上的“小人物”在生物学、女性文学及社会经济学诸方面取得的成就。即使在清代学术研究甚为成熟的今天,这些论文依旧没有过时,仍具参考价值。若以研究范围之广、视域之博、方法之精、创作之巧衡量今昔之间,竟使人每生有退无进之慨。
张荫麟学术自期极高,治学历程颇为曲折,正如谢幼伟所说,他“以考据起家”。清代学术最以考证谨肃见称,在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几无学人不受此影响。相比于梁启超那一代人,张荫麟已属新派人物,但他自幼接受的仍是正统的经史考据之学,后来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便是标准的考据文章。从这一层面上讲,纵说张氏的学问由清代考证学而入,亦不为过。他早期论文中表现出的对钱大昕、戴震、洪亮吉等精擅考证的乾嘉学者的熟知,也就不难理解。他年甫弱冠,即撰文评介《清史稿》,展现出对有清一代历史文献的掌握已臻于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令人心折。(27)燕雏(张荫麟):《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素以周闻博学见称于世的陈寅恪,在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入职北大时,也以其“记诵博洽”倍加称赏。(28)陈寅恪:《致傅斯年(1933)》,《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47页。同时,清代学术包罗甚广,领域极多,凡属中国旧学范畴的内容,几乎都能囊括。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辟四章篇幅论述清儒“整理旧学”的成绩,凡列科目十二种。本来,中国学术传统崇尚博综,而不重专精,与西方学术分科范式本存隔阂。梁氏治学虽通达,但西方学科分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推广,则多赖其力。张荫麟虽属新派,并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与学科分类观念,但在博综的追求上,始终坚执旧学传统,与自幼浸淫于清代学术关系匪浅,颇具吊诡意味。
我们今天日益相信古典文明的更生系于个体研究的推进,而所谓学术史者,更应该展现学人治学的历史。(29)近年来,罗志田教授曾倡议“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试图构建以人为主体的学术史,盖“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惜乎响应者寡。见氏著《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页。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以人为本的传统,张荫麟本人亦奉行不疑。他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多取以人为纲的路径。首先采辑传记诗文,构建人物的行为、言论,在自觉层面上重建历史,更能借助驰骋奔放的史学思维与想象,从外在表现潜入古人的内心世界。依主题内容来看,这些研究所涉既包括纳兰性德、钱大昕、戴震、袁枚、洪亮吉、龚自珍、曾国藩等烜赫一时的硕学鸿儒、文苑才彦,也包括如李元、王德卿、王鎏等声名晦黯但别具意义价值的边缘人物。这一偏重于清代学术史中的个体研究而绝少玄虚疏阔的概念叙述的取向,似乎表明张荫麟并无营造一个完整的学术系统的兴趣。他的实践,是凭借敏锐的史感和鸿博的才识,捕捉无人问津、乏人体味的历史信息,以若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上有待拈出董理或重新审视的人物为主题,在梁启超开拓出的学术领域中创获不断,故不限于擘绩补苴而已。
当年,王国维曾力倡在京师大学堂中教授外国哲学、文学,以为“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30)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之十》,《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页。张荫麟是这一倡导的直接受益者,并且予以积极的应和。后来在给张其昀的信中,他坦承:“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31)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载《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这里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接近于陈寅恪提倡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他所掌握的旨在支持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思想资源远较同时史家丰富,哲学上服膺叔本华与摩尔(G.E. Moore),社会学上接受孔德与斯宾格勒,以现代学术对“国史”重作逆向的审视,更能不着痕迹地将这些西学观念化入论著之中。对于“客观征实”的清代学术符合近代科学精神这一前提,张荫麟从无怀疑,但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别人不经意的学术史角落,探求不止于边缘学人,也包括名儒大师身上少为人知的治学面相,追寻“旧踪迹”在“新时代”的意义。故其讨论主题多为前人忽略,具体论述又能言人所未言,有类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跨学科”多元研究。当然,刻意强调“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及其时代意义,难免会产生过度解读的障蔽,对此,张荫麟始终保持自觉的分寸感,不致偏离学术规范。
民国新史学发展的一大特征即是追求史料上的积极扩充,甚至还因此引发了极端的倾向。(33)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读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126页。陈寅恪在诠释学术“预流”时,强调以新材料研求新问题,(3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而“材料”与“问题”的更新,常常与社会思潮的兴替、学术关怀的转移相始终且互为因果。所谓“新材料”,不仅指新出的稀见文献,也当包含传世典籍中素为人忽视的细节的重拾,史料的更新与扩充,固不宜狭隘地注目于地下考古的发掘。晚近史学研究与上古、中古一段的重要差异,即在于史料的天然限制。纸上遗文汗牛充栋,即使再狭窄的研究也难以在史料占有上做到穷尽,而古史研究的推进,则往往严重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
在史料的蒐辑方面,张荫麟的殷勤与颖悟引人注目,甚至将视阈延至域外。寓居京华,琉璃厂、隆福寺是其足迹常履之所,聚书至夥,且有志于《民国开国史编年》的纂著。留学北美,访书西洋,更有编辑《清史外征》的计划。以上种种,不惟昭示出他强烈的史料观念,更彰显出广博的史学视野与气象。可以说,他在扩充史料方面付出的努力,绝不弱于任何史料学派,一个生动的事例即是《水窗春呓》一书的发现与考实。(35)见吴晗:《记张荫麟》,《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58页。张荫麟为此书撰作《跋〈水窗春呓〉——记曾国藩之真相》一文,载《国闻周报》第12卷第10期。至于应用传世典籍扩大清学史的研究范围,解决新问题,揭示新意义,亦略如上述,毕见其目光四射。
张荫麟自陈其思想在北伐后发生重大的转变,“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而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36)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41页。前举事例,十九完成于这一思想转变之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发之下进行的。当时持此关怀以治史者殊不乏人,与张氏广东同籍的前辈史家陈垣便是显例,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以及宗教史著作,都抱持一种“动国际而垂久远”的期待。(37)陈垣著,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5页。张荫麟最初对明清之际西学东传的持续关注,即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他排纂史料,爬梳故实,考论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西文明的冲撞与融合对此后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影响,主旨却落实于中国在近代世界文明的地位问题上。他考察洪亮吉对乾嘉时期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虑,要证实在同时期对西方来说属异域的中国,也有一位与马尔萨斯同样目光如炬的“社会学家”。那些如李元一般的边缘学人,置于其所处时代,何啻微茫,而张荫麟却汲汲突显他们学术史意义的目的,无非是在西方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近代学科兴起之后,从中国历史陈迹之中择取相应的学人学说,以示不弱于人。这固然得益于张荫麟的西学背景,但更重要的应是基于现实关怀的寄托,与社会息息感应,他的清学史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强烈的以学经世的特色。
应该承认,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映射出同时代许多前辈学人的影子。梁启超自不必论,他者如对纳兰性德的研究之于王国维,对清代基督教传播的考察之于陈垣,(38)张荫麟尝撰《五代时期波斯人之华化》一文(载《益世报·史学副刊》第5期,1940年5月30日),以后蜀李珣为例说,实为补苴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之作。案:王国维曾致书陈垣,已先以李珣做过提示,张荫麟当未知悉。详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对戴震的研究之于冯友兰,对龚自珍的考证之于陈寅恪,等等。这足证明他确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启示与激发,并非空无依傍。
1934年,张荫麟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最先教授的课程即中国学术史,可见此时他的治学重心尚未完全转移。次年,他被委以清华历史系清史课程的讲授,并指导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偏重学术史),(39)受张荫麟指导者有李鼎芳、王栻,分别以《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严几道》为学位论文。不啻在客观上肯定了他在清史领域内的专业水准与成就。他在1935年开始潜心创构《中国史纲》,学术兴趣与重心渐向先秦两汉倾斜。两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张荫麟转徙南国,至其弃世的1942年,他的治学主要又围绕宋史展开。(40)参见曹家齐:《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期间虽也偶尔涉及清代学术,但已不复作为他治学的重心了。
三、余 论
章学诚被近代学界“重新发现”,他的学说成为可以与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比较借鉴的圭臬,张荫麟对章氏也一再表示推许,对其学说间有阐发。据学生回忆,他曾以赵翼的《廿二史考证》《陔馀丛考》为例,“归纳为比论、对照、校正、补缀、实证、显示”等史学法则。(41)管佩韦:《张荫麟先生的历史教学》,《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220页。合观那篇反映他对史料的反省体认且备受推崇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明显具有一致的理路。这提示我们,清代学术给予了张氏史学法则上的启迪,促使他在方法论上更进一层。
在钱穆的眼中,张荫麟是一位“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的史学奇才,(42)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3年1月。最有撰述通史的资格,这代表了时人的普遍意见。早在留学北美之时,张荫麟即表露出有经营“通史艰巨之业”的计划,“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长编不必有一贯之统系,各册自成段落,为一事、一人、一制度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可,为丛杂之论集亦可”。(43)张荫麟:《与张其昀书》,《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这与《中国史纲·自序》中所云“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一以贯之,(44)张荫麟:《中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自序一”,第1页。均呈现出一种退让的思路,后来所计划的《宋史新编》即是沿着这一思路设计的。至于此前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以及《民国开国史长编》的著述计划对这一思路的形成是否有所推动,尚在未知之域。张荫麟在清学史的研究上似乎无意营造“一贯之统系”,前文已及,然而个体研究建立在对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散钱可串,其著述形态已然呈现出与“国史长编”一致的风貌了。
张荫麟对学术的追求有种近乎宗教的热情,又兼天资明敏、感情丰沛,兴趣所涉遍及史学、文学与哲学,确能迷人眼目。学术面相的繁复,体现出治学风格的多样,然而愈炫惑于他的博学多才,愈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境地,忽视他早年治学重心所在。他在诠释、应用史料的方法上承清代考证学的轨辙,恪守学术规范,在构思与意趣上却能不受束缚,突破考据的樊篱,尽显驰骋奔放的想象力,兼寓其致用之志。日后治史途辄稍变,渐倾向于专精一壁,史学境界亦臻圆熟,饮水思源,实肇基于早年潜心学植、措意研索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历程。放眼一时,后顾前瞻,张荫麟虽非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学域的开创者,却是最早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与胡适、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同时代的参与者相比,他年纪最轻,行辈最低,其风格取向之异同,俟于专文详悉讨论,但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探讨”已足使之立于不朽之境,于他治学生涯中的意义尤其不可轻忽。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拙文仅就张荫麟的清学史遗著,综理线索,循其理路,追踪其早年学术思考与实践的轨迹,不过一“代下注脚”之作。值张荫麟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年之际,拈取学界忽视的学术面相为题,撰文为念,亦师张先生治清学史之法度,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或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张先生的治学风格及其转向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