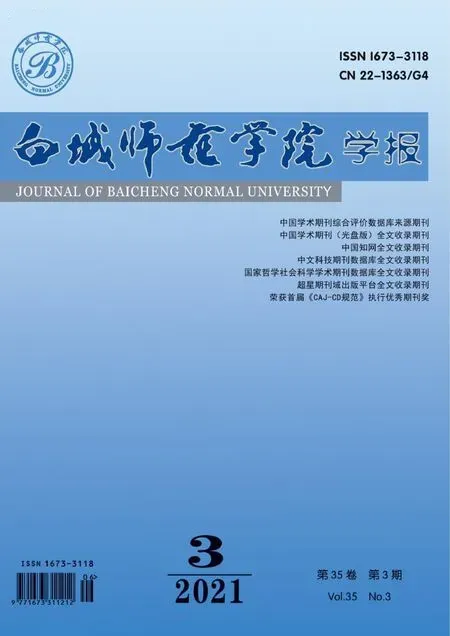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失范与重构
宋 扬,张 婧
(1.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2.吉林体育学院 基础课教学研究部,长春 130022)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非典、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埃博拉以及时下扩散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世界民众带来极高健康风险的同时,也在考验着媒体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的能力。对比2003年的非典报道与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可以发现媒体报道在时效性、公开性、广泛性等方面有明显提升,但仍折射出不少新闻伦理失范现象,不仅损伤了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也不利于战疫工作的有效进行。因此,梳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失范表现,提出新闻伦理重构的可行路径,既可为后续的此类报道提供参照,也对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原则、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失范表现
(一)信息失真
信息失真是指信息偏离了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与一定的衡量标准。在信息的反映、传输和理解过程中,都有可能造成信息的失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出现的信息失真主要有两种类型。
1.源头失真
2020 年2 月1 日,一张伪造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截图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称国务院决定暂停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发放工作。伪造的图片在某卫视当晚的“抗疫情特别报道”中正式播出,导致假截图升级为假新闻。
2.编译失真
2020 年2 月15 日,某网官方微博发布“湖北武汉迎来降雪”组图,误将山东寿光的雪地画面当作武汉雪景发出;2 月16 日,某报头条号刊发“汉中抗疫大事记”时误将前一天刊发文章中的人物故事混淆,文章前一段刚写“出生不到20 天的双胞胎儿子”,后一段便出现了“刚起床不久的两个孩子稚气地问”的文字。
源头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源信息不完全、不准确,编译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在编译和传递过程中受到干扰,这说明作为记者和编辑,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一定要客观严谨、调查核实、严加审核。
(二)侵犯隐私
侵犯个体隐私是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常见病”之一。“根据关于名誉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健康状况属于个人有权不公开的私人信息。尤其是传染病,法律规定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公开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1]2003年非典时期,有媒体擅自公布了国内传染人数最多的患者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等信息,并在报道中冠以“毒王”称号;某电视台未经允许,公开了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患者的姓名。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时期,多名患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工作信息等被媒体曝光。个人隐私的泄露干扰了患者和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使患者遭受到社会歧视、孤立和不公正待遇,给患者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侵犯隐私的现象再次出现。因有在湖北工作、生活、学习或旅游的经历,不少人在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后,其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个人详细信息在微信群、QQ 群、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中传播,给当事人造成严重困扰。
恩格斯曾说:个人隐私一般应受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私,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当中也明确规定了个人有义务提供个人行踪、人群关系等相关情况。特殊时期,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体有必要让渡部分隐私。但是,个人隐私的让渡并不是无原则、无范围的,毫无原则地采集、传播反而是权利滥用的一种表现。
(三)强化性别差异
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女性医护人员是一个重要的报道群体。据统计,在驰援武汉的医护大军中,女性占总人数的2/3。然而,媒体对女性医护人员的报道角度更多地集中在其身体形象和弱者形象上,忽视了女性医护人员的职业身份和专业性。无论是“医务工作者怀孕九个月,依然奋战在一线”“流产十天后,武汉90 后女护士重回一线”还是“女护士集体剃光头”“小镇90后护士:坚守隔离区30多天的‘女汉子’”,可以发现,这些新闻报道强调女性身份,在宣扬女性医护人员奉献与付出的同时,也无形中放大了她们的弱者形象。美国学者盖尔·塔奇曼提出的“反映假设”理论认为,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大众传媒必须选择反映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将社会状况加以象征性的表现。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种“真实”的同时,也必然会掩盖某些“真实”,从而导致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歼灭”。在这一“象征性歼灭”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所表现的性别成规再次确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2]女性医护人员不仅在新闻标题中被贴上了性别标签,相较之下,她们的家庭生活也更大程度地被呈现,女性医护人员被塑造成肩负家庭与事业重担的奉献者、牺牲者。而忽略男女的性别差异,将“女护士”称为“女汉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性别群体的否定。
(四)道德观念滞后
疫情期间,不少媒体报道了老人捐款的新闻。“退休环卫工人捐出10 万元积蓄,卡里只剩13.78 元”“87 岁老人为抗疫捐空毕生积蓄20 万元”“八旬残疾夫妇捐出3 年积蓄抗击疫情”……尽管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是以传播感人事迹、歌颂奉献精神为主,但受众在接收此类信息时却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式解读。[3]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老无所依的人们本身就是需要社会照顾关怀的群体,当他们倾囊而捐时,抵抗日后生活风险的能力势必降低。一直以来,此类强调“牺牲感”的宣传式报道并不鲜见,放下植物人丈夫奔赴抗疫一线的护士、父患肝癌仍坚守岗位的民警、儿子去世仍坚持工作的交警、患病坚持上课累倒在讲台的教师,新闻中涉及的人物固然高尚伟大,值得钦佩敬仰,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公民意识的提升,这种“牺牲”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逐渐成为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实质上,这也反映了传媒工作者在道德观念上并未与时俱进。同时,基于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这种宣传“牺牲感”的报道逻辑也可能会引发某种道德绑架。譬如,当网友发现高收入的明星与环卫工人捐款数目成反比时,网络暴力也可能随之而来。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重构
(一)及时公开准确报道,均衡信息,强化舆论引导
2020 年2 月2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新冠病毒的疫情报告中指出:伴随着新冠病毒的爆发和防控出现了一场大型的“信息疫情”,即信息泛滥。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很可能加剧公众恐慌情绪的蔓延。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媒体有责任及时公开准确地向公众提供疫情相关情况。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时期,媒体报道也应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在事件初期,媒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及时发布新闻。在中期与后期,则要着眼于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事态的发展、探讨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案并实时报道方案执行进展。”[4]此次疫情初期,媒体及时对疫情进展、患者动态、政府决策、防护知识等信息进行报道,有针对性地破除谣言传言,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疫情中后期,媒体在保证信息畅通流动的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多个领域,如抗疫过程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庸政懒政、企业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中国为他国疫情防控提供的援助等,保证了信息的均衡呈现,营造了良好的抗疫舆论氛围。
(二)注重人文关怀,恪守道德原则
“现代新闻传播所谓人文关怀,既是指对报道主体的尊重与关注,包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权益,也意味着‘受众本位’的回归,及时了解受众需求变化,让受众从报道中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价值与尊严。”[5]高龄老人捐出全部积蓄、护士放下植物人丈夫奔赴一线、护士们集体剃光头……这些事迹固然令人感动,但与其歌颂英雄们的苦难,受众更愿意看到的是每个个体都被给予社会关怀。当社会文明环境与公民权利意识发生明显变化,媒体需要敏锐地捕捉时代脉动,更新道德观念,增强人文关怀意识。根据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和信息需求设置议题,提高报道的品质与温度,避免正面宣传产生负面效果。
当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博弈时,媒体在信奉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同时,还需要遵循狭义比例原则与安全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指媒体要考虑“是否欲达成目的与采取该手段所造成对人民的负担明确不合比例”,当保障知情权与限制隐私权比例失衡时,媒体应谨慎选择报道范围和方式,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安全性原则指“媒体要确保信息的采集、存储和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避免发生泄露问题。
(三)提升记者科学素养,加强医疗卫生报道专业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在《风险社会》中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并指出“(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6]因此,媒体在报道社会问题尤其是各类风险议题时需要秉持科学谨慎的态度。
为使报道更加深入和专业,国外一些主流媒体倾向于要求记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如CNN的首席医疗新闻记者桑杰·古普塔是神经外科医生、医疗卫生专家,《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医疗卫生版的记者也多具有医学教育背景。与国外相比,记者缺乏专业学科背景训练、媒体机构专业知识培训机制缺位以及医疗跑口记者换岗过快,无法形成长时间有效的积累导致我国缺乏专业的公共卫生记者。[7]因此,我国可改革当前新闻教育模式,适当借鉴西方国家高校新闻专业与医学院联合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医学和新闻双重专业背景的人才;或是由媒体定期举办卫生记者培训班,聘请专业医疗工作者担任特约记者等,提升记者报道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四)创新报道理念,强化建设性新闻报道
丹麦学者哈格鲁普2008 年提出“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它“包括积极的和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元素,以增强受众的能力和呈现更全面的真相,同时维护新闻的核心职能和道德”。[8]“建设性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对新闻报道流程与产品的质量负责,还应对新闻对个人与社会产生的影响负责”。[9]特殊时期,媒体人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传播疫情信息、报道事实真相的同时,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公共利益。
面对疫情,媒体有必要运用建设性新闻理念进行多维度的探索报道,如强调公民赋权、调动积极情绪、解决特定问题等。疫情期间,多家媒体刊发“武汉日记”,邀请不同职业身份的个体记录他们的亲身经历,弥补了大众媒体受限的视野,更容易让受众共情;记录感人故事,让受众在报道中看到温暖与希望,增强共同抗疫的信心和决心;针对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生产困难的问题,《光明日报》连续刊登“疫情之下,如何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多措并举提升中小企业抗风险力”等多篇文章,提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多种可行性措施;在“老人捐款是否接受”的相关报道中,“上观新闻”与“吴晓波频道”刊发的两篇文章《疫情围城,老人捐赠带来的伦理难题:温婉谢绝,还是附条件式接受》和《老人捐款20万,要不要接受穷困老人的捐款?》,针对政府接受捐款后对老人的救助安排提出了建议,体现了媒体为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所做的努力与实践。
三、结语
1971年,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无知之幕”这一概念,即要求各方从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退回到一个消除了所有角色和社会差异的隔离物后面的“原始位置”。为避免幕布升起后自己成为“最少受惠者”,最弱小一方的利益势必得到考虑并将得到最大化的保障。罗尔斯认为,人们应当首先判断什么是道德正确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地以多数人受益为原则。[10]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工作者不妨卸下自身身份与目的,预设情景,进行道德推理,在“个人诉求与伦理道德”的博弈中寻求最佳报道方案。同时,作为新兴媒体赋权下的受众,有必要提高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提升信息的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与思辨能力,发挥对媒体的监督作用,避免成为不实信息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