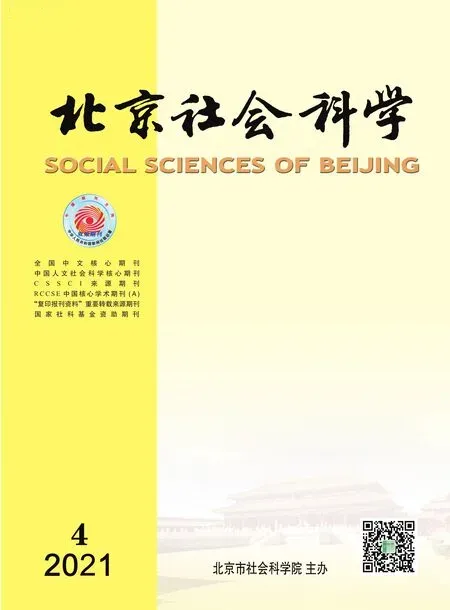“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
——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刘 璇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由毛纶、毛宗岗父子所改定评点的《三国志演义》卷首有《凡例》十则,其中最后一条说道:“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1](P8)可知在当时有以“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为内容的戏曲演出。其中,“关公斩貂蝉”的故事在元杂剧、明清传奇中均有流传,[2]这一故事在戏曲、说唱中的传播和流变,已经引起学术界关注。[3]不过,《凡例》中与“关羽斩貂蝉”对举的“张飞捉周瑜”却少有人注意。实际上,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刊《草庐记》中即有关于“张飞捉周瑜”的相关情节。[4]不仅如此,“张飞捉周瑜”故事在各种戏曲、说唱类别中都有流传,题为《芦花荡》《花荡》或《三气周瑜》,直至今日在舞台上仍有演出。可见这是一个流传时间较长、且在民间颇受欢迎的故事题材。
值得注意的是,“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形式如昆曲、京剧、苏州评话中广泛流传,在故事脉络、具体情节上既彼此关联,又呈现出了相当丰富的面貌。这一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小说之中,却能够流传至今,与其不断主动向小说情节同化有着密切关系。以“张飞捉周瑜”故事为线索,还可以观察到在通俗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中,“小说故事群”和“非小说故事群”之间互相影响、相互纽结的复杂关系,可以为研究小说、戏曲、说唱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全新视角,颇具典型意义。
一、通俗文学中“张飞捉周瑜”故事的承继关系
目前可见最早叙述“张飞捉周瑜”故事的是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刊《草庐记》,此剧作者不详,正文书名题为“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全剧共54折,从刘备求贤若渴、决心寻访诸葛亮开始,到刘备称帝,众将受封结束。“张飞捉周瑜”之事发生在全剧的第46折。
此外,清代宫廷连台本戏《鼎峙春秋》中也有“张飞捉周瑜”故事。《鼎峙春秋》共10本,240出,全剧故事始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造反,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终于刘备称帝建立蜀汉,诸葛亮率军平定南疆。清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大戏节戏》中言乾隆帝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5](P267)可知此剧为乾隆初年庄恪亲王允禄奉敕编撰。不过一般认为此剧的实际撰写者为参与允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编撰的周祥钰及邹金生。“张飞捉周瑜”之事发生在《鼎峙春秋》第六本卷下第22出。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昆曲剧本选集《缀白裘》,卷三收录的《西川图·芦花荡》也讲述“张飞捉周瑜”之事。已经有学者指出,《缀白裘》中所收《西川图·芦花荡》一折当摘自《鼎峙春秋》:
考诸家曲目,清代无名氏之《西川图》已知者有三种:一是写张松献地图,刘备进兵西川事;二是写刘备入吴招亲事;三是《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七著录,写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刘永诚的战功业绩。但近代昆班所演的《西川图》,与这三本戏毫无关系,其中的折子戏基本上是从《鼎峙春秋》中摘出的。[6]
不仅如此,京剧剧目“龙凤呈祥”(《甘露寺》《回荆州》《芦花荡》3剧的合称)中也有关于“张飞戏周瑜”的情节。如果将《草庐记》《鼎峙春秋》《西川图·芦花荡》与京剧《芦花荡》的曲牌、唱词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相当明晰的承续关系(见表1)。
通过比较可知,《鼎峙春秋》在《草庐记》的基础上,对曲牌、唱词、宾白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而《西川图·芦花荡》及京剧《芦花荡》则更多地照搬了《鼎峙春秋》的情节、曲牌、唱词等内容。
不仅如此,如果将《草庐记》和《鼎峙春秋》中涉及“张飞捉周瑜”的情节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它们在剧情安排上有几处明显不同(见表2)。
首先,二剧“张飞捉周瑜”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不同。《草庐记》将此情节安排在刘备参加周瑜在黄鹤楼所设宴会之后,随后衔接刘备与孙夫人完婚、返回荆州等情节。而《鼎峙春秋》中并无黄鹤楼相关情节,“张飞捉周瑜”的情节是在刘备完婚、返回荆州之后。其次,随着此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有不同。《草庐记》中此情节只是作为插曲存在,周瑜只是被张飞气昏,并未对整个故事走向产生实质影响。而在《鼎峙春秋》中,周瑜最终被张飞气死,构成了“三气周瑜”故事的最后一环,在剧情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昆曲《西川图·芦花荡》中,“张飞捉周瑜”发生于刘备携夫人返回荆州之后,最后周瑜被张飞气死,剧情发展与《鼎峙春秋》的相关段落完全一致。而在京剧“龙凤呈祥”中,涉及“张飞捉周瑜”的部分题为《芦花荡》,又名《三气周瑜》,可知其与《鼎峙春秋》也有着直接关系。此外,在秦腔、川剧、赣剧、粤剧等地方戏中,也有题为《芦花荡》的剧目,都讲述“张飞捉周瑜”之事,情节也均与《鼎峙春秋》一致。除戏曲外,不少曲艺类别中也有演出“张飞捉周瑜”故事。如靳派乐亭大鼓,保存下来的传统小段中即有《芦花荡》一出,从周瑜孙权合谋定下美人计讲起,结尾讲刘备携夫人过江返回荆州,周瑜率兵追赶,在芦花荡遭遇张飞埋伏,最后也以周瑜不敌张飞又被羞辱、羞愤交加结束,情节也与《鼎峙春秋》一致。此外,在苏州评话、南阳大调曲子、西河大鼓等曲艺门类中也有题为《芦花荡》的剧目,在情节设置上均发生于刘备赴东吴完婚、返回荆州之后,结果也均为周瑜被张飞羞辱,慨叹“既生瑜,何生亮”而结束。
综上所述,地方戏曲及说唱曲艺中的“张飞捉周瑜”故事,源头都可追溯至《鼎峙春秋》中的相关情节。据此可知,目前可见最早的“张飞捉周瑜”故事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行的《草庐记》,经过清乾隆年间成书的《鼎峙春秋》改编后,影响渐广。此后在戏曲、曲艺中出现的“张飞捉周瑜”故事,基本都与《鼎峙春秋》相关。
二、“张飞捉周瑜”故事的定型过程
通过前文叙述可知,《草庐记》和《鼎峙春秋》在涉及“张飞捉周瑜”故事时,故事情节产生了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两剧在成书时取材来源不同而导致的。
从故事细节来看,《草庐记》和《鼎峙春秋》都有相当明显的拼贴痕迹。《草庐记》第44折写鲁肃来到荆州给刘备做媒,到了第45折,周瑜上场时却说:“昨日着甘宁去请玄德赴壁联会,就筵间杀之。”[8](P173)另外,第44折写诸葛亮嘱咐简雍前往黄鹤楼营救刘备,到了第45折前半段却写孙乾扮作渔翁前来营救刘备,后半段则又改为简雍。之所以会产生前后矛盾,大概是因为作者在拼贴组合剧情时没有仔细检查前后文,才留下了疏漏。
《草庐记》在创作时参考了不少前代作品,明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提及《草庐记》曾说道:“此记以卧龙三顾始,以西川称帝终。与《桃园》一记,首尾可续,似出一人手。内《黄鹤楼》二折,本之《碧莲会》剧。”[9](P84)即指出《草庐记》中涉及黄鹤楼的相关情节与《碧莲会》一剧相关。有学者考证认为,《碧莲会》很可能是朱凯《黄鹤楼》杂剧的别称。[10]此外,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阳虞氏刊行的《全相平话三国志》中也有周瑜黄鹤楼设宴的情节,以及“张飞捉周瑜”的故事雏形。在平话中,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后,刘备行军与周瑜相遇,周瑜邀请刘备过江往黄鹤楼赴宴。刘备趁周瑜酒醉逃走,周瑜大怒,派凌统、甘宁追赶。这时,“先主上岸,贼军近后,张飞拦住,唬吴军不敢上岸,回去告,周瑜心闷”。[11](P439)接下来周瑜得知刘备夺取荆州,鲁肃献计假意与刘备结亲,趁机囚禁刘备,取回荆州。平话的情节脉络与《草庐记》大致相似,只是叙述较为简略。由此可以推测,《草庐记》诸折所叙故事,应当大部分都袭自前代戏曲或平话故事,其中“张飞捉周瑜”故事的题材来源可能与《全相平话三国志》相关。
《鼎峙春秋》中也有相当明显的剧情拼贴痕迹。如在第22出有一支【越调支曲·调笑令】,曲词中有“黄鹤楼上,痛饮醉喧哗。道是,沉醉染黄沙”几句,[12](P488)提到周瑜在黄鹤楼设宴,意图加害刘备之事。实际上在《鼎峙春秋》中并无涉及黄鹤楼的相关情节,可见《鼎峙春秋》的作者在创作此剧时,也参考了不少前代剧作,但其并非完全照搬前剧,而是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然而在改写时也没能仔细核查前后文,遗留下了一些漏洞。
《鼎峙春秋》创作完成于清代乾隆年间,故事来源则更加复杂。有学者对《鼎峙春秋》的文本来源进行考辨,归纳出其与《连环计》《续琵琶》《古城记》《草庐记》《赤壁记》《西川图》《四郡记》《狂鼓史渔阳三弄》等多个剧目之间的关系。[13]而对剧中涉及到“张飞捉周瑜”的相关情节进行回溯,不难发现,此剧在成书时,除《草庐记》外,在剧情设置上可能还参考了《两军师隔江斗智》一剧的相关情节。[14]在《隔江斗智》第三折结尾,写张飞奉诸葛亮之命护送刘备夫妇登船过江到荆州后,躲进刘备夫妇车中。周瑜赶来跪在车前,向孙夫人陈述自己夺取荆州之计。张飞从车中出来羞辱周瑜,周瑜羞愤交加,旧伤复发,被甘宁、凌统扶下。张飞说道:“周瑜,眼见的你这一气,无那活的人也。”[15](P1318)不难发现,这段故事也发生在刘备完婚之后,张飞对周瑜的戏弄也构成了“三气周瑜”的最后一环,直接导致了周瑜的死亡,与《鼎峙春秋》的故事发展十分相似。由于目前可见最早收录《隔江斗智》的《元曲选》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远早于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鼎峙春秋》,且《鼎峙春秋》在成书时广泛参考了前代戏曲,因此有理由认为《鼎峙春秋》在涉及“张飞捉周瑜”的部分,除《草庐记》外,很可能也参考了《隔江斗智》的相关内容。《鼎峙春秋》将这些剧中的相关情节杂糅重组,才形成现在所能看到的“张飞捉周瑜”故事面貌。
三、“张飞捉周瑜”故事与小说情节的离合关系
根据目前所见文献,“张飞捉周瑜”故事源头最早可追溯至《草庐记》,在《草庐记》基础上创作完成的《鼎峙春秋》,则使这一故事定型,并对此后的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鼎峙春秋》中的“张飞捉周瑜”故事之所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
《鼎峙春秋》作为奉敕所撰的宫廷大戏,在此前各类“三国戏”的基础上纂集完成,可称之为明清“三国戏”的集大成之作。此剧创作完成之后,曾在嘉庆、道光年间多次演出,据王芷章《昇平署志略》所载,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三年(1843)均演出过《鼎峙春秋》。[16](P77-79)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中也记载,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1849)也上演过《鼎峙春秋》中的折子戏。[17](P140)可见,《鼎峙春秋》是宫廷演剧中颇受欢迎的剧目。
不仅如此,清代中后期以来的宫廷演剧对民间戏曲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宫廷演剧的形式和剧目会对民间庆典演戏产生影响,同时宫廷演剧也会吸收外班剧目及使用民间艺人进行表演。在这一过程中,宫廷与民间戏曲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18]齐如山在《京剧之变迁》中就指出,清末三庆班连台本京剧《三国志》即源自《鼎峙春秋》:
全本《三国演义》乃乾隆年间庄恪亲王奉旨所编,名《鼎峙春秋》。原系昆曲,场子剪裁,都非常之好。小生陈金爵等,曾演于圆明园,后经卢胜奎手,改为皮黄,由三庆班排演出来,脚色之齐整,无以复加。[19](P51)
相较之下,《草庐记》虽成书较早,但其流传程度远远不及《鼎峙春秋》,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有限。
其次,通俗小说对民间社会的知识体系建构、道德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通俗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文体。[20]因此,其他通俗文学形式与通俗小说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流传的广度。一般来说,戏曲、说唱常从通俗小说中汲取灵感,将通俗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改编。这样产生的通俗文学作品容易被观众所接受,也更容易得到好评,从而广泛流传。
《草庐记》刊刻于明万历年间,此时《三国志演义》已经有嘉靖壬午(1522)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本等多个版本,各版本在文字、情节上虽有不同,但主体故事已经定型。以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书中仅用了12则的篇幅,便讲述了诸葛亮计取四郡、孙曹合肥之战、孙刘联姻、曹操大宴铜雀台、马超兴兵造反、诸葛亮三气周瑜等内容,情节十分紧凑。并且小说涉及到三气周瑜的情节分别以“诸葛亮一气周瑜”“诸葛亮二气周瑜”“诸葛亮三气周瑜”为题。说明在小说作者的设置中,“气周瑜”的主体始终是诸葛亮而非他人。而在“张飞捉周瑜”故事中,虽然张飞是在诸葛亮授意下埋伏在芦花荡,但诸葛亮在其中起到的只是间接作用,自然不符合小说作者的情节设置。因此,“张飞捉周瑜”及类似故事,既背离史实,又对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无益,在成书时自然被小说作者舍弃掉了。不过,这些未被小说采纳的故事大多曲折新奇,多有情爱、打斗描写,符合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才在民间戏曲中具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相较之下,《鼎峙春秋》与小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复杂。在《鼎峙春秋》创作完成的清乾隆年间,最早的毛评本——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已于康熙十八年(1679)刊行并成为通行本,小说文本已经完全定型。不仅如此,经过百余年的流传,《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所叙故事,在雅俗社会的影响都已经相当深远。连《三国志演义》的评订者毛宗岗都批评“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等戏曲故事为“后人捏造之事”“此其诬也”,可见在清初的文人读者中,已经有了“小说故事”和“非小说故事”的区分。在文人读者眼中,“小说故事”的可信程度和文学地位,远远超过“非小说故事”。不过,诸如“张飞捉周瑜”这样的“非小说故事”,能够从明代流传至清初,自然说明其有能够吸引观众之处。对于《鼎峙春秋》的创作者而言,如何在已经定型的小说故事与戏曲观众的观赏趣味之间寻求平衡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鼎峙春秋》的剧情是在小说基础上敷演而成。以涉及“三气周瑜”的相关情节为例,《鼎峙春秋》用了15出来叙述这一事件,其中第6本第8至12出对应小说第54回,第15出到第17出对应第55回,第19出到第22出对应第56回。由于《鼎峙春秋》用了15出篇幅来展示小说3回的内容,因此在进行创作时,便有大量空间可以增加细节描写和支线情节。如小说在提到孙夫人之时,仅介绍孙权“有一妹”,未言其姓名,而《鼎峙春秋》中则称其为新月公主,并补充曰其“二八年华,文兼武备,尚未适人”。[12](P449)又如小说在描写孙刘成婚时,仅言“数日之内,大排筵会,孙夫人与玄德结亲”,[1](P611)而在《鼎峙春秋》中用了整整一出描写婚宴之景(第12出)。此外,在剧中还增加了一些左慈在曹操酒宴上展现异能(第13出)、曹操派人接蔡琰返回中原(第14出)、蔡琰创作《胡笳十八拍》(第15出)、张飞捉周瑜(第22出)等情节。这些情节或在小说其他地方简要提及,或未被小说采纳,《鼎峙春秋》将它们巧妙地移植、穿插进已经定型的小说体系中,在不违背主线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小幅度改写。
《鼎峙春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改动,当与宫廷演剧的实际需要和观众喜好有关。清代宫廷的连台本戏,多与宫仪庆典相关,因此《鼎峙春秋》在涉及庆功、宴饮等情节时,都会极力铺排。此外,清宫连台本戏擅长演出宏大场面,并善于利用道具来展示演员的高超技艺。《鼎峙春秋》中也常出现此类描写,如在第6本第13出中,既有宴饮场面,又安排杂扮左慈登场,上演将枯草变为牡丹、将玉杯变为白鹤的绝技,能够给观众极大的视觉刺激。此外,宫廷演剧的观众很大一部分为后宫女眷,出于对观众群体的考虑,在以征战谋略为主线的三国戏中增加一些诸如孙夫人、蔡琰等女性角色的描写也在情理之中。而《鼎峙春秋》将“三气周瑜”的最后一环改为“张飞捉周瑜”,相较于小说所叙的周瑜退兵后被诸葛亮来信气死而言,显然更具戏剧冲突,也相当于在前后文戏之间穿插了武戏,使得剧情节奏张弛有度。也就是说,《鼎峙春秋》在叙及“张飞捉周瑜”及相关故事时,选择以小说情节为纲,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小幅增删、改写,这样在不违背小说主线故事的前提下,既能够符合表演的实际需要,又能使剧情富于变化。
这种向小说情节靠拢的趋势,在地方说唱、曲艺类别中也有所体现。这些通俗文学形式因使用方言进行表演,往往仅在某一地域内传播,相较于昆曲、京剧而言,传播空间更为狭窄,因此它们在进行改编时,会更加主动地向通俗小说靠拢。如南阳大调曲子中的《芦花荡》,其故事虽脱胎于《鼎峙春秋》,但结尾却与《鼎峙春秋》不同。大调曲子《芦花荡》结尾唱曰:“周郎不死得活命,匹马单枪回柴桑,张翼德得胜回营去,诸葛亮又订计一桩。一封信气死英雄汉,只因为讨取荆州一命亡。这本是三气周瑜一段事,这位卧龙公柴桑口吊孝又假哭一场。”[21](P287)可知周瑜在芦花荡和张飞交手后,并未被其气死,而是在战败回营后读到诸葛亮的书信才一命呜呼,与小说中的描写一致,可见这是曲词作者根据小说情节而进行的改动。
又如张国良整理的苏州评话剧本《三气周瑜》,有关“张飞捉周瑜”的情节发展也与《鼎峙春秋》一致,但在写到“张飞捉周瑜”的具体细节时,便开始向小说靠近。小说第57回写周瑜旧伤复发坠马,被救回营中,听手下回报“玄德、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1](P634)此段不见于《鼎峙春秋》,但在《三气周瑜》中却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此事,作为“张飞捉周瑜”的铺垫。不仅如此,《三气周瑜》在讲述“张飞捉周瑜”时,也反复强调诸葛亮在其中起到的主导作用。作者先安排诸葛亮在芦花荡内操琴,周瑜听到后心想:“不如去访访他,乘机将他们君臣擒下了。”[22](P239)作者安排诸葛亮设计将周瑜引入芦花荡,说明《三气周瑜》中主导故事发展的人物从张飞变成了诸葛亮。而在“张飞捉周瑜”之后,作者又安排张飞俘虏周瑜并将其带回荆州,诸葛亮释放周瑜,在其回营后安排张飞前去送信,信中内容则与小说完全一致,周瑜读信之后才慨叹“既生瑜,何生亮”而死。这几处改动显然也是以小说情节为蓝本的。南阳大调曲子与苏州评话中的这些改动,恰是民间通俗文学主动与小说情节同化的表现,也能愈发显示出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各文体传播中的权威地位。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张飞捉周瑜”故事本来是流传于民间的三国故事,在《三国志演义》成书时,一部分民间故事被纳入小说之中,而包括“张飞捉周瑜”在内的另一部分未被小说采纳的故事则继续在民间流传,并逐渐形成与小说并行发展的故事群。在通俗文学这一范畴中,“小说故事群”与“非小说故事群”时有交集。有时小说刊刻者会将流传于民间的三国故事增插入小说之中,以吸引读者。如明代建阳所刊各版《三国志演义》中出现的关索故事,便与《花关索》等说唱文学形式密切相关。[23]而随着小说的影响力渐大,以戏曲、说唱为代表的民间三国故事有时也开始主动向小说靠拢,以寻求生存空间,前文所述的“张飞捉周瑜”在昆曲、京剧、苏州评话及南阳大调曲子中的改编便是典型例证。随着时间发展,两个故事群之间的关系便愈发复杂,呈现出扭结的状态。
不过,在通俗文学系统中,正是因为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说唱有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才使得这些故事的影响愈发深远。《小说林》主编徐念慈在《觚庵漫笔》中曾说道:[24]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得力于梨园子弟,如《凤仪亭》《空城计》《定军山》《火烧连营》《七擒孟获》等著名之剧何止数十,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足使当场数百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二也。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三也。有是三者,宜乎妇孺皆耳熟能详矣。[25]
通俗小说可奠定故事的基本走向,戏曲表演能够突出人物性格,而说唱则以细腻铺排见长,这些不同的通俗文学形式共同促进了三国故事的经典化。
不过,通过徐念慈此段叙述也不难发现,在通俗文学传播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通俗小说,戏曲和说唱都是在其基础上通过强化人物性格、丰富心理描写等方式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学术界也多以通俗小说为中心,关注小说情节如何下沉至戏曲、说唱的过程。不过,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戏曲、说唱中的传播为线索,可以了解到在戏曲、说唱中,“非小说故事群”通过努力向通俗小说靠拢,被更多观众认同,获得更大的传播空间,文学地位得到上移的过程。这两种传播路径在通俗文学范畴中,一直都是并行存在的,通俗小说情节下移至戏曲、说唱是显而易见、即刻完成的,而戏曲、说唱中的“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则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累积才可能完成。因此,这一特殊的经典化过程,更需要得到关注。
注释:
[1](清)毛宗岗.凡例[C]//.三国志演义.北京:中华书局,1995.
[2]按元杂剧中即有名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的剧目,然现已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关羽斩貂蝉”故事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刻的戏曲选集《风月锦囊》,其中《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即有“关羽斩貂蝉”的情节。此后,《缀白裘》十一集卷三收录《斩貂》,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卷六中也有类似情节。
[3]有关此问题,可参见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生成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日]伊藤晋太郎《关羽与貂蝉》(《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日]大塚秀高《关羽为什么斩貂蝉》(收入《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相关论述。
[4]按《草庐记》目前仅见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刊本,作者不详,正文书名题为“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有1954年商务印书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本,1987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全明传奇》影印本以及2003年北京学苑出版社《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影印本。
[5](清)昭梿.啸亭杂录·续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吴新雷.昆曲剧目发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7]按表中引《草庐记》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鼎峙春秋》为《清代宫廷大戏初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西川图·芦花荡》为汪协如点校本《缀白裘》(北京:中华书局,1955),京剧《芦花荡》为《京剧丛刊》本(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引文中有个别涣漫不清之处,暂用“□”代替。
[8](明)无名氏.草庐记[C]//.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2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9](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0]胡莲玉.《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故事考辨[J].明清小说研究,2007(1).
[11]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0.
[12](清)周祥钰,邹金生.鼎峙春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3]可参见李小红《〈鼎峙春秋〉研究》第三章“《鼎峙春秋》文本来源考辨”的相关论述(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75-146页)。
[14]按《隔江斗智》有《元曲选》本及《酹江集》本,讲述周瑜设美人计夺取荆州,但被诸葛亮识破之事。
[15](明)臧懋循.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6]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C]//.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
[17]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C]//.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18]有关此问题,可参见曾凡安《晚清演剧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45页)的相关论述。
[19]齐如山.京剧之变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
[20]有关此问题,可参见赵益《论“宗教生活”与“通俗文学”之互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纪德君《明代通俗小说对民间知识体系的建构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的相关论述。
[21]雷恩洲,阎天民.大调曲词(中)[C]//.南阳曲艺作品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2]张国良.三气周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3]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李伟实《花关索故事非〈三国志演义〉原本所有》(《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韩]金文京《三国志外传——〈花关索传〉》(《〈三国演义〉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刘海燕《(花)关索故事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文章与专著的相关论述。
[24]按《觚庵漫笔》署名为“觚庵”所作,据栾伟平《〈觚庵漫笔〉作者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一文考证,认为“觚庵”乃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
[25](清)觚庵.觚庵漫笔[J].小说林,19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