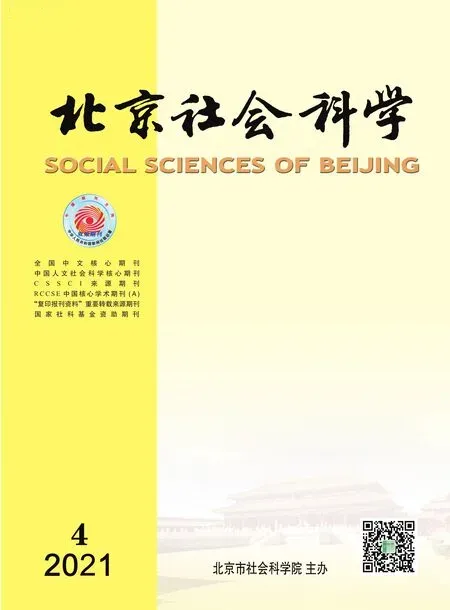陶渊明《荣木》的作年和篇旨
——以末章为重点的重读
归 青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荣木》是陶渊明为数不多的四言诗之一,这首诗在清淡典雅的风格中流露出作者内心的焦虑。对于这首诗的作年,多数研究者认为作于陶渊明40岁时。对于其篇旨,研究者多认为表达了作者争取早日建功立业的急迫愿望。笔者最近重读《荣木》,对这两个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整理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一、《荣木》作于作者40岁时吗?
《荣木》作于陶渊明40岁时,这在陶学界几乎已经算是一个定论了。判断的根据就在末章开首的四句: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1](P13)
后二句明明白白说了“四十无闻”,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本篇的作年吗?
但我觉得问题仍有讨论的空间。这里的关键就在如何理解这两句话。我认为,这两句不是作者的自述,而是对《论语·子罕》中孔子原话的引述,也就是本章开头讲的“先师遗训”。孔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P114)
意思是,在求道的道路上,年轻人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着很强的潜力,可是一个人假如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取得名声的话,那他也就不具有什么竞争力,就不会让人畏服了。
有些先生在解释陶渊明诗中“四十无闻”这两句话时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这两句话是反用《论语》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即使到了40岁还没有成名,难道就不足畏服了吗?[3](P17)把一个陈述句变成了反诘句,意思就变成这样的了:一个人即使四十无闻,也没有关系,照样可以有所作为,让人畏服。这样的解释会是陶公的意思吗?试想陶公对孔子充满崇敬,在本章开头还口口声声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怎么可能在紧接的两句中就公然挑战夫子,说出直接否定孔子原话的意思呢?这岂止是“坠”之,简直就是质疑和颠覆了。自相矛盾如此,这是很难说通的。我觉得,这里的问题不在作者,而在今人的理解。只要把“四十无闻”二句当作陶公的自述,就一定会出现这种解释上的困难。反过来,如果把这两句看作是对孔子原话的引述,也就是对“先师遗训”的补充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作者服膺孔子的这句话,并且把夫子的教导当作衡量自己境界的标尺,确实表现出他对“先师遗训”不敢“云坠”的态度。这样的解释不是很自然顺畅、也比较合乎情理吗?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从中引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不能以“四十无闻”二句为依据断定本篇作于作者40岁时。
不过,“四十无闻”两句虽然不能直接用来证明作者的年龄,但对于考求本篇的作年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从作者对“四十无闻”的强调和诗中流露出的焦虑感中,是不是能找到解决本篇作年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的这段话虽然讲的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话一经孔子之口说出,而且载在《论语》里,势必会对士人产生莫大的影响。40、50,尤其是40岁,必然会被所有的士人视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陶渊明在诗中特意拈出“四十无闻”这句话,流露出的心态应该是要千方百计避免“四十无闻”这样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安然接受“四十无闻”的现实,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宽裕的时间段里在50岁之前求得有闻的结果。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诗中为什么会流露出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了。
我们不妨把全篇各章统贯起来看一下吧。作者在前几章中流露出强烈的焦虑感。他从荣木的朝盛暮衰,联想到人生短暂。不知不觉间,年光已流去了大半,可是回顾以往,感到“业不增旧”,[1](P13)进步不大,内心很着急。这时孔子的话就浮现在脑子里,一个人如果到了40、50岁还一无所成的话,也就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一想,他就紧张得自我动员起来,便要赶紧驱车策马,直奔那理想的目的地。诗中流露出来的是时不我待、时间不多,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的紧迫感。如果要推测本诗的作年,我以为应该是作者处于40岁将至而未至的时期,具体在哪一个时间点,材料不足,未可遽定,但相对于40岁说,40将至说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
二、名车名骥,奔向何方?
在本章的下半段,作者继续写道: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P13)
意思是要赶紧登上快车,鞭策快马,急速地赶往目的地。
这里对“名车”“名骥”之“名”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名”是优良的意思。“名车”“名骥”就是良车、良马;[4]还有一种解释是,“名”指的是功名,“名车”“名骥”就是功名之车,功名之马。[5]两种解释的共同点,都是把“名”作为有声誉的意思理解的。区别在于,第一种解释中的“名”是车马的属性。在一般情况下,质优的东西才会享有盛誉,所以,“名”也可以成为质优的代称,“名车”“名骥”也就是良车、良马的意思。第二种解释中的“名”,虽然形式上修饰的也是车和马,但从实际意义看,这个“名”并不是车马的属性,而是车马奔趋的目标和结果,是属于驱车策马之人的。两种解释中,第一种解释的用法更流行、更易解,在本篇中解释起来也很通顺。第二种解释的用法比较少,也比较特殊,但放在本篇的语境中来考察,却也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本章通篇都是在讨论名声的问题。作者引述孔子的话,说的就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有闻才是“可畏”的,无闻则是“不足畏”的,君子应努力争取成为一个有闻的人。“闻,知声也”“引申之为令闻广誉”,[6](P592)就是有名声的意思。对于孔子的“遗训”,陶渊明当然是认可并且准备身体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驱车策马,要去追求的难道不是孔子所讲的,成为一个有闻的君子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本章中的“名车”“名骥”就很可能是作者相对于孔子原话中的“有闻”而有意构造出来的词语。比较起来,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更接近陶公的本意呢?问题只是,直接把“名”解释成功名,把“名车”“名骥”翻译成功名之车,功名之马,我觉得尚欠确切。如果要求释义更精准的话,那么“名车”“名骥”似乎可以翻译成,快速奔向成名目标的车马。
现在,我们就顺着第二种说法来探讨本章乃至本篇的旨意。前面说过,陶渊明在诗中表达了一种对成名的迫切心情,很容易让人感觉到,陶渊明似乎是一个追逐名声的人,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些辨析。
从孔子的原话讲起。在《论语·子罕》中,孔子确实表现出重视名声的倾向,他主张有所作为的君子在40、50岁时就应获取名声,这是确实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是名实一致论者,在他看来,名声只是内容的反映和标志。他在《论语》中讲“有闻”“无闻”表面上似乎谈的只是名声,实际侧重的还是由名声所标示的实际,也就是学道的进步和悟道的境界,而不是一个空头的名号。和孔子比较起来,陶渊明对名声的态度要淡泊得多,“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1](P98-99)“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1](P119)这才是他对名声的基本态度。他在本篇中所以说要驾驭着“名车”“名马”去追逐理想,主要还是对应着孔子“有闻”的话语,表达他想要达到和声誉相匹配的思想境界。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孔子还是陶渊明,他们对名声的表述,都是一种借代手法,是借对象的某一部分来指代对象本身。说得具体一点,他们所谓的名声(“有闻”)所指的并不限于名声,还兼指(实际更侧重)名声所代表的思想境界。这一点是我们在解读这首诗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否则很容易把陶渊明对道的自觉追求说成是单纯对名声的追求,是一种受名声驱动的行为。如果这样理解陶渊明,就会把他的思想行为肤浅化、庸俗化,就会误解陶渊明。
还需要一辨的是,本章中讲的“名车”“名骥”之“名”到底是什么名呢?是功名之名呢?还是求道、悟道之名呢?很多学者都把这个“名”解释成功名之名,也就是建功立业之名,从而也就把本诗的主旨理解成作者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政治抱负的心愿。这样的说法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陶渊明在诗中引述的孔子原话,本来就是指学道、求道而言,并不是讲事功的。孔子还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2](P71)表示要用一生的努力去追求道。孔子还自述思想境界提升的历程,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2](P54)终于达到人生的化境,可以见出他对求道、体道的重视。按照孔子的标准,人生的价值并不一定取决于事功方面(尽管他也是非常看重事功的),是否真正理解、领悟了道,并且实践了道,才是根本之所在。
再回到文本。这首诗中的确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紧迫感,但这个紧迫感的内涵是什么?是因为对道的把握还有距离呢?还是因为事功未建而忧心忡忡呢?我觉得应该是前者。小序中说“念将老也”“总角闻道,白首无成”。[1](P13)这里“总角”和“白首”两个年龄段所面对的理应是同一对象,就是“道”,而不应“总角”时讲的是一件事,“白首”时讲的是另一件事。“念将老”和“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三句共同揭示了本篇的主旨,那就是对自己学道“无成”所产生的焦虑心情。
再看全诗各章的内容。第一章说,看到荣木早晨盛开,晚上凋谢,不由得联想到人生的短暂,内心惆怅万分。第二章说,既然生命短暂,那就要尽可能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因此就要依从道,勤勉于道。第三章说,时间飞快地流逝,但反思自己在修身的道路上却进步不大,还要时时被惰性支配,不禁自责不已。经过了以上三章的抒述,自然就引出了末章的打算和决心。通观全篇可以见出,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对学道未成、因而要急起直追心情的表达,建功立业的思想在诗中是看不到的。如果把末章中“名车”“名骥”之“名”解释成功名之名,那就会使读者产生这样的疑惑:前面三章明明讲的是学道未成的忧虑,为什么到了末章就忽然变成对事功的追求了呢?
也许有研究者会说,对道的追求中也可以包括对事功的追求。我的看法是,道固然是根本性的原理,一个人学道、悟道、体道必然会体现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狭义地说,内心修养和功名事业还是侧重点不同的两个方面,判断成功(有闻)与否的标准也不相同。传统的三不朽说,也是把立德、立功、立言分开来说,并且有着层次高低的区别。立德有成的人,并不必然立功、立言也有成。德、功、言三方面都可以有名或无名。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的“闻”和陶渊明在本篇中讲的“名”都是指立德之名,而不是事功之名。把“名车”“名骥”之“名”理解成事功之名,说陶公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恐怕是误解了陶渊明。
对这首诗的旨意比较合理的概括可能是这样的:陶渊明在四十将至而未至之际,想到自己少年学道,迄无成就,距离孔子讲的“四十无闻”的时间节点却越来越近了,内心充满了焦虑,他决心从现在开始,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强修养,朝着悟道的目标全速前进。
三、40岁前后的陶渊明有没有功名事业的追求?
上面分析了《荣木》的篇旨,指出诗中表达的是对学道未成的忧虑,而不是对功名事业的急切追求。这还是基于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看法是否站得住脚,还需要结合陶渊明40岁前后的创作和出处行为来考察,看看这一时期的陶渊明是否存在着对事功的追求,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占着怎样的位置。需要说明的是,对陶渊明作品的系年,各家分歧很大,而且相当数量的作品又是无法确切系年的。为谨慎起见,以下用来举证的材料都是有着明确作年标记的作品。对陶渊明的年寿,取影响最大的63岁说。
隆安五年辛丑(401),陶渊明37岁。这年他出任桓玄的僚属。七月前他曾回家度假,假期结束返回江陵时,他写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1](P170-171)
诗中流露出他对林园生活的无比依恋和对官场生活的不适和勉强。他叩问自己,为什么要舍弃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来过这种昼夜奔波、不得安宁的辛苦生活呢?结尾六句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功名(“商歌”)事业并不是我的追求,我想要的只是回到田园,去过那种躬耕自足、无拘无束的安逸生活。这年冬天,其母去世,他便辞官回到了柴桑。
元兴元年壬寅(402)至元兴二年(403),陶渊明38-39岁。他隐于柴桑,为母服丧。这一时期有明确作年标记的诗共有三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只举前二首诗: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1](P177)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1](P181)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诗中对仕途生活的感受相反,这两首诗中对田园景色和生活的描写十分优美和宁静,已经透露出他对仕隐两种生活的取舍;其次,诗题中提到的“怀古”,怀的是《论语》中提到的隐士:荷蓧丈人、长沮、桀溺,这是一些不愿大济苍生、只愿独善其身而被子路讥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2](P185)的人物,但陶渊明在诗里对这些人却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理解和认同,明确表示他要取法先辈,“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首中的末尾二句,他明确地说,他没法像那些具有“通识”(例如“朝隐”之类)的人那样,做一个尸位素餐、却又假装清高的名士。如果一定要在保天下和保一己中作一个选择,那就只能选择保一己了。“所保”二句用的是《后汉书·逸民传》的典故。
(刘表礼请庞公出山,)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7](P2776)
文中的“保全天下”,指的就是建功立业,大济苍生;保一己,指的是只求个人安逸闲适,独善其身。陶渊明的回答已经很明白地表明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
元兴三年甲辰(404),陶渊明40岁。这一年他第三次出仕,任刘裕的镇军将军参军,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1](P158)
他说他这次的出仕只是“宛辔”,也就是在纵马驰骋的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停顿,和林园生活的疏离只是暂时的。他又说,对于这次出仕,他感觉到愧对高鸟和游鱼。这样的意思在《饮酒》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说第一次出仕时的感觉是“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其十九)》)。[1](P246)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接下来的四句就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心怀“真想”,不愿去过那种受人拘牵的生活。这里的“真想”和陶诗中的“素志”“素抱”“素襟”“志意”“平生之志”一样,都不是建功立业、垂名不朽的事功之志,而是过一种悠闲安逸、躬耕自足、既普通又有诗意生活的“闲居”之志。
义熙元年乙巳(405),陶渊明41岁。上半年他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将军参军。三月出使建康,作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描写了钱溪的美好景色和淳朴风气,并对此表示无限向往。他问自己到底所为何求,要来服这种苦不堪言的劳役。诗中写道:“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1](P189)和上举诸诗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对仕隐选择的态度也非常鲜明。到了八月,他抱着“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宋书·隐逸传》)[8](P2287)的动机,谋得了彭泽县令一职。在官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惠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事业心。十一月,因为妹妹去世,他要去奔丧,便自免去职,从此再没有返回官场。他在《归去来兮序》中解释归隐动机时说: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1](P391)
挂冠而去不是因为宏图大志受到了打击,建功立业的理想遭到了阻遏,而是因为自己的天性遭到了强制,违拗了爱好自由的本性,由此可知他是把个人的自由看得最重要的。遵从自己的天性,不勉强自己,才是他出处选择的第一标准。这样的人生观,是很难与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兼容的。从他40岁前后的思想和出处行为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并不存在强烈的事功观念,退一步说,即使有的话,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也不占主要位置。回归田园,独善其身,过闲适而有诗意的生活才是他的生活理想。[9]
以上我们把陶渊明40岁前后思想行为的脉络作了初步的梳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来审视《荣木》的主旨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把《荣木》理解成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就很难解释他同时期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二者间就会显现出明显的矛盾。反之,如果说《荣木》所表达的不是事功观念,只是追求道的急迫心情,对二者间的关系就能得出合理的解释。陶渊明遵从个性,以个人自由为第一标准,和他独善其身的自我砥砺,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相辅相成,成为陶渊明式的儒道兼综、自然和名教合一的样本。
注释:
[1](东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东晋)陶潜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参见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49页;魏正申.陶渊明集译注[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第148页。
[5]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7页;郭维森、包景诚译注.陶渊明集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1页。
[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南朝宋)沈约撰.宋书·卷九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参见归青.陶渊明“有志不获骋”句新解[J].云梦学刊,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