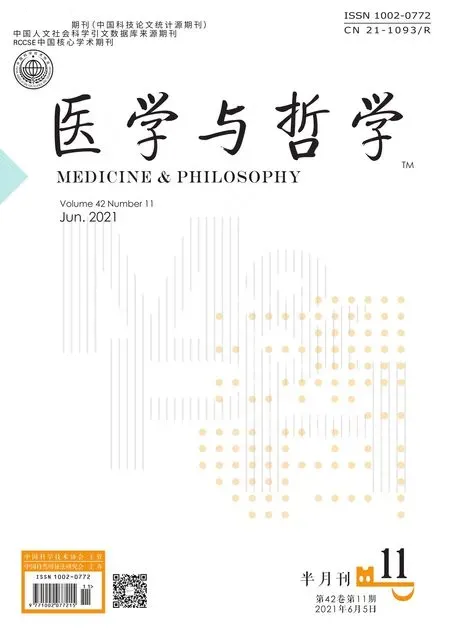照护对叙事医学教育与实践的启示*
李 飞
美国学者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中文名凯博文)在新书《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以下简称《照护》)里,以人性互动的基础进行概念界定,提出照护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他在“写给中国读者的话”里开门见山:《照护》提出一种思考关爱与照护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也可以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各种疾痛(从突发性的健康灾难到慢性病)中。照护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家庭和朋友关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既是一件为人的善事,同时又是一件为己的大事。照护是将我们的社会黏合在一起的“胶水”。
作为被我国医学人类学、医学教育相关领域所熟知的著名学者——凯博文,他的名著《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等影响极其深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赴中国多地进行田野工作,与华人学术界有着长达30余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其研究和学术成果汲取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以中国人的视角去理解中国人,以跨文化视角来反思人类健康问题。凯博文成功地改造了医学人类学这个学科,令其绽放出勃勃生机。他将社会理论、文化、心理与哲学等因素系统地编织进临床医学实践的框架里,《照护》的出版则标志着探讨“通过联结医院与社区、家庭与社会的方式,来弥合医疗照护与人类问题之间的缝隙”。
作者从临床医生、人类学家、医学教育家、家庭照护者等多元身份出发,融合了理论与个体经验的照护,对叙事医学教育与实践富有启示。
1 《照护》的写作特征与关键概念
全书以作者经历为叙事主线,从年少时光写起,包括成为医生、与妻子琼相遇相知、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学术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以及琼的发病开始转换为照护者角色的经验等,将关于照护的理论以夹叙夹议的形式镶嵌其中。作者集中讨论的关键概念包括照护、人性、“在场”、关系、苦难与救赎等。在感受作者与妻子之间旷世的爱情与生命的守候中,关于照护的理论框架逐渐浮现,而作者本人的照护体验让这一领域充满了温情与力量。
1.1 照护
照护远远大于医学这一学科范畴,并在一种最普遍的人性活动基础上进行讨论。“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1]前言3照护的本质是基础的人性互动。它是一种行动,一种实践,一种表现,往往还是一种反馈,一种对于不同境遇中人们的需求以及自我需求的固定反应。作者高度概括了照护带给他的感受:忍耐。他说,照护教会人谦卑,而“忍耐”二字更接近他的真实体验。
延续着对生物医学实践一贯的反思和批判,作者再次强调了道德,认为照护其实是一种捍卫道德承诺的存在性行动。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技术革命实质上并未带来更好的健康结局,代价是对照护的削弱。其现行的医疗实践方向,并没有增进人性互动,而这样的后果必然降低照护的质量和结局。
作者在人类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的意义上讨论照护。在阅读《照护》的过程中,叙事医学与照护两个领域的问题自然地发生了关联。叙事学家认为,借助于间接认知和中介化力量,叙事对 “归属性疑难”提供了其独特的诗学回答,即:一个既非实体亦非幻象的“被叙述的自身”[2]。疾病如认知障碍,会带来主体性的改变、中断甚至消亡。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叙事是医学处境真理的栖身之所。生病后,病人被强行牵引回自己的身体,并深陷其中的存在困境(即病痛)转换为一个要解释的主题并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即通过叙事理解和讲述所经历的一切”[3]。在这个意义上,照护与叙事都是基础的人性互动,切近人类的本质需要。
1.2 人性
“人性”在作者多部学术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在《照护》中则达到了阐释的顶峰。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人性在医疗领域引发的是广博而又聚焦的讨论。广博是因为它既能在时间的长度上引发人们深刻持久的讨论与思考,又能够在跨文化的不同区域和文化的维度上进行比较;聚焦是因为它能够从一个学科的核心概念(如人类学)来引领一个学科及其相关的学科,从而发生交互深远的影响[4]。
知微知彰。人性可以是学术讨论的焦点,也由日常生活折射。随着病程进展,“她渐渐失去了那些构成她人格特质的核心部分,那些价值观、那些情感、那些使她成为琼的部分,都渐渐随风而去了”[1]146。令人心碎!成为琼的照护者以后,作者变得更加“柔软”,以至于他90高龄的母亲一针见血地说“他变得像个人了”!对认知障碍患者进行照护的独特与艰难在于,照护过程中病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解;与此同时,更加凸显出照护者的角色与价值,以及经由照护产生的共情、丰富人性的过程。
1.3 在场
“在场”(presence)既是丰沛的哲学呈现,又是温暖的人文关怀。凯博文以“在场”概念强调了临床实践或家庭照护工作中,亲力亲为、关注与见证的核心意义,从而与卡伦的叙事医学理念中倾听、关注、解释等叙事能力相得益彰。
凯博文在告别临床医生职业生涯时,曾撰文回顾作为临床医生、教师、导师、研究者和家庭护理者的经历,最突出的是对“在场”的阐释。“在场”是一种前行的召唤,或是一种走向对方的脚步。它是富有活力的[5]。在对“在场”阐释的基础上,人们通过倾听、回应、解释以及医疗情境中的检查、治疗等各项互动,共同界定了照护。在场,注重情感和道德结果,对当下医疗体系运作的价值体系构成批判。我们也再次找寻到了照护的界定与叙事医学实践的一致性基础。
2 在照护的路径上重新审视医学本质
首先,叙事医学实践需要对苦难进行深度理解。作为人类生存机遇与发展深层次意义的命题,苦难与医学相伴而生。以回应苦难、弥合医患分歧、注重关系等为特征的叙事医学实践模式,对何为苦难,怎样回应苦难是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
从西方哲学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稍作追溯。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第三个成分是苦难。悲剧引发怜悯和恐惧,其目的不是为了赞美和崇扬这些情感,而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6]。在古希腊哲学里,情感被归为人性的一部分,并对其发生机制和作用展开了在今天看来是医学价值的思考。在《照护》里,凯博文继续强调了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的,并认为社会苦难构成了医学的基础。他同时以其个人的、独特的境遇给出一种解释:医学院期间的出国经历,意识到人类社会的骇人的危险与撕裂的贫穷,真正感受到所肩负的尊重历史与见证人类苦难的责任[1]25-26。作者坚守着这份从医的“初心”,对疾病的多元认知和理解,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构成了社会苦难是医学基础的观点,并将其视为毕生的研究主题。
其次,中国并没有西方情境下苦难的概念框架。在中国,从社会文化的、历史的、观念的,以及个人层面医学认知的视角出发,都与上述西方情境下苦难的概念框架相异。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医师崇高、美好的愿景与期望。例如,“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悬壶济世”“德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家国情怀”等,并形成强烈的感召与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有着以中国社会文化为基础的学医动机和阐释。根据研究发现,“通过学医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策略选择,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诠释途径,尤其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家族理念)之韧性。而对医学专业/职业的认知基础,在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中,形成了实用性、稳定性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并内化到学生及其家庭中,以文化资本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进一步的医学教育过程再生产出来”[7]。即以个人的“稳中有升”的社会流动,来换取家庭或家族的荣誉与反哺。
最后,在照护的路径上增进了对医学本质的认识。在《照护》的序言里,记录了一个墨西哥裔学生在《社会苦难》这门课上对作者的发问:“您为什么这么关注痛苦?您会不会开一门课程叫‘社会幸福’(social happiness)?”这个提问充满意义。换句话说,医学为什么不是回应社会幸福的学问?如果认同医学的本质在于助人幸福,仍然启示我们的是:医学的诞生,是在面临自身的生存困境时,以人类互助的本质行为趋向幸福的努力。对医学本质的长久思考,如今从照护的路径上带着对叙事医学的思考有了新的延展:照护,以理论和体验的全面呈现,诠释了互惠与长期照护的实现。
3 对叙事医学教育与实践的启示
第一,在医学教育和训练中尊重人性。凯博文曾大声疾呼:“(美国)住院医生所受的夹道鞭打式的严格训练,甚至可能使医生的人性退化,当然不可能促使他们致力于社会心理上的治疗训练。要改变(住院医师培训)这种环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医院的训练课程。年轻的实习医生往往在无意中剥夺患者的人性,如果我们要阻止这种现象,就必须停止剥夺年轻医生的人性。”[8]305-308在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负担以及复杂的健康风险背景下,照护在拓宽生物医学实践的范畴,并强调道德和对人的关注。基于照护的医疗实践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要从专业化的技术知识,走向更为普遍化的人类知识,要从抽象的概念,走向真实的人,走向他们的道德体验,走向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1]62那么,医学教育或者具体到叙事医学领域能做什么?经过几年探索,国内叙事医学教育以培养倾听、共情、反思等叙事能力为主要目标[9-10],关注并回应了尊重人性、还原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的需求。具体教学形式整合了理论与实践[11]。例如,在完成叙事医学与共情的理论学习之后,学生在早期临床接触课程里,与医生如影随形进行观察体验、进行患者访谈和反思性写作;教师指导学生关注病人,帮助形成“以病人为中心”的视角;通过病人访谈,学生尝试着经由病人本人或家属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并探究与疾病体验相关的心理、社会因素[12]。或是安排学生进入医院病房,以一个纯粹的“人”的视角观察参与志愿活动[13]。即通过将医疗情境中的人际互动还原为自然的社会的人际互动,以善意出发,进而平衡由于医学训练导致衰减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痛苦的尊重及伦理识别能力。
第二,培育感性能力与照护精神。不仅在遴选医学生的过程中,对这些人格特质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要在医学教育阶段去守护这些特质。这些能力将构成未来临床医生的基础素养,围绕这些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在叙事、照护的临床框架里成为核心工作。学习如何诠释病人及其家人对疾痛的观点,有临床上的用途。凯博文认为,诠释疾痛经验的故事,是医生的核心工作。虽然这种技巧在生物医学训练中已经退化萎缩[8]前言4。笔者曾将卡伦与凯博文两位学者在叙事医学领域的主要观点进行对照[14],发现他们在学科定位、理论前提、对关系的强调、临床实践方法与工具等方面,异曲同工。例如,卡伦界定的叙事能力指“倾听、阅读,识别、吸收、解释并被听到或读到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15]。与此对应,凯博文认为:“医生尽可能地了解(甚至发挥想象力去感知、感觉)疾痛经验,就像病人那样去理解、领会和感觉它”[8]281-282。即经验丰富的医生会像民族志者一样拥有共同的感性能力。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死亡作为独特的不可逾越的医学生必修课,在叙事医学境遇下获得了强调。研究表明,当直面病人死亡这样的场景时,改变了学生对医生角色、医学实践和身份认同:从英雄式的治疗转变为照护与关心[16]。在情感触动的基础上,发挥并调动学生的直观感受力,同时增强对隐喻、“不可言说”内涵的理解力与解释力,从而预期转化为关爱他人的意识和实践。
第三,强调叙事医学教育与实践的中国本土化发展。前文关于苦难概念框架的分析抛砖引玉,提示我们中西方叙事医学存在相异的哲学根基、文学发展路径(中国文学特点包括抒情、尚善、乐观、含蓄[17])、价值观基础。尽管文化交融、时代变迁、技术革新,使得人际互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思考的根基与起点,致力于发展符合中国文化土壤特质的叙事医学成果。在中国当下的叙事医学实践中,中国本土文化尤以中医为代表,正在展开与西方叙事医学积极的对话。例如,“深入共情是反思的基础,仁孝文化是共情的土壤。仁孝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别注重人的情感能力及事物的意义。仁孝文化与中医相结合,或可将这种共情和反思能力从原始血亲家族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18]。与此同时,在对西方叙事医学理念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部分优秀医生自觉地践行叙事医学,积累着区域性的个体化的经验,不失为学科本土化努力的另一个方向。
第四,建立起跨文化理解的视角。从事叙事医学的学者和践行者经常忽视叙事的文化和历史维度[19]。从叙事医学角度出发,如果称其为“医文交融”,与以对人的尊重、关注,以及交流、互动、文本分析等为特征的叙事表达相得益彰。同时,立足于医学本质之上的思考,医学实践者应关注人类的价值、回应社会苦难,并建立起跨文化理解的多元视角。
作者在《照护》里将人性与中国文化中的“做人”等概念进行了关联。从医学人类学、叙事医学等学科领域视角出发,亦或是照护与关怀的理念与实践,其中涉及到的关键概念如共情、反思、人性、“在场”、照护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孝”“恻隐之心”等有契合之处,能够搭建起彼此理解互通的路径。与此同时,作者以照护者的个人经历,及其反思照护中的人文主义伦理在实践中遇到的挑战,提示我们不能在自己的文化框架里去解读作者的照护与关怀伦理,而是要超越狭隘的伦理照护观。
4 结语
在《照护》一书的推荐语中,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写道:“凯博文教授是我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他在近八十岁之际撰写此书的动力,是要探讨‘照料之魂’。通观全书,魂之意涵,在于两点,一是形形色色的护理者对患者发自心底的精心照护,二是患者从各式各样的护理者得到的无比之爱。两者之并联是现代医学一直难以面对的重症病人的精神慰藉问题。”
作者小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能从事照护工作,少年时曾经是“黑手党杀手”物色的目标,到后来成为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主要照护者,潜力被激发出来,他的生活方式变得柔软起来,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而对妻子的照护过程,也确定了作者对医学实践的思考转向道德与情感。
如《照护》所言:归根到底,照护的灵魂也就成了对灵魂的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