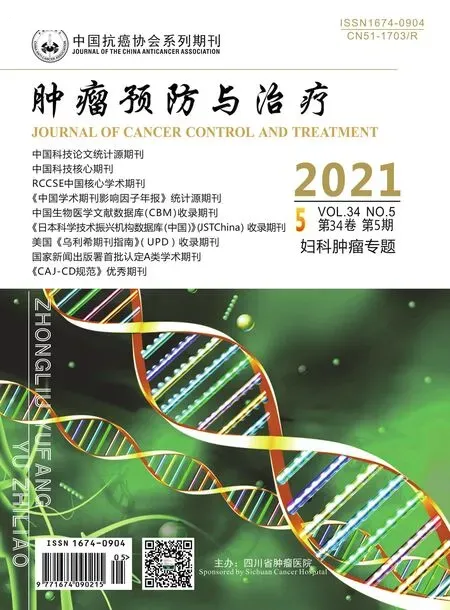妇科肿瘤免疫治疗的新靶点*
程红燕,向阳
100730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
免疫治疗已成为继外科手术、放射治疗、抗肿瘤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支柱[1]。经典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CTLA-4)是研究最成熟的免疫检查点通路,作用于PD-1/PD-L1和CTLA-4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等实体肿瘤的治疗方式,有显著的疗效和持久的治疗反应,目前有从二线转成一线治疗的趋势[2-3]。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了PD-1/PD-L1和CTLA-4抑制剂在晚期妇科肿瘤中的应用,但其临床获益率有限,由于免疫信号通路和免疫微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使用单一的免疫靶向药物不太可能获得抗肿瘤作用[1]。因此,深入了解肿瘤免疫的通路,寻找新的免疫靶点在妇科肿瘤的免疫治疗中至关重要。本文总结了以下妇科肿瘤免疫治疗的新靶点。
1 共抑制分子
1.1 TIM-3
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 cell immunoglobulin-3,TIM-3)是一类I型跨膜蛋白,首次被发现表达于分泌干扰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的细胞,包括CD4+的T辅助(Th1)细胞和CD8+的细胞毒性T(Tc1)细胞,还有Th17细胞,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s)、NK细胞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4-5]。TIM-3通过与其配体半乳糖凝集素-9和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1(carcinoembryonic antigen-related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CEACAM-1)结合从而促进钙离子内流、细胞聚集和凋亡,进而抑制T细胞的激活和增殖[6]。CEACAM-1和TIM-3在T细胞上共表达,共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7]。
TIM-3的表达被认为是T细胞耗竭的标志之一[6]。在卵巢癌和宫颈癌的TILs中均可检测到TIM-3的高表达。Yan等[8]的研究发现卵巢癌和宫颈癌组织中TIM-3CD4T细胞的比例明显高于患者外周血和非TILs组织中TIM-3CD4T细胞,且肿瘤来源的TIM-3CD4T细胞产生IFN-γ和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的能力受损,但和TIM-3-CD4T细胞相比表达更高水平的CD25、Foxp3、CTLA-4和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glucocorticoid-induced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GITR)。同时晚期卵巢癌患者T细胞上TIM-3的表达显著高于早期卵巢癌患者,且复发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TIM-3CD4T细胞的水平也显著高于初治卵巢癌患者,该研究认为卵巢癌组织中TIM-3的表达与预后不良相关[9-10]。此外抗TIM-3抗体和抗CD137抗体联合治疗可以抑制卵巢癌荷瘤小鼠的肿瘤生长,约60%的荷瘤小鼠能够获得长期生存[11]。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宫颈癌中,肿瘤转移淋巴结中TIM-3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淋巴结[12]。在子宫内膜癌中的研究表明,肿瘤内的NK细胞细胞表现出更多的共抑制分子,例如TIM-3和含免疫球蛋白及ITIM结构域的T细胞免疫受体(T cell immunoreceptor with Ig and ITIM domains,TIGIT),并且这些分子的表达随着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增加[13]。目前已有多项针对TIM-3抗体单独或联合PD-1抑制剂的I期临床实验正在进行(NCT03652077、NCT03099109、NCT02608268、NCT02817633等)。
1.2 TIGIT
TIGIT是2009年首次被鉴定为T细胞和NK细胞的免疫检查点分子,可以在记忆T细胞、Treg细胞和自然杀伤T(natural killer T,NKT)细胞上检测到[14]。TIGIT与免疫激活分子CD226(又称DNAM-1分子)竞争同一组配体:CD155(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和CD112(Nectin-2或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2)[15]。TIGIT与CD155的亲和力高于CD112[16]。TIGIT与CD结合后参与抑制T细胞,使T细胞从分泌IL-2改为分泌IL-10,而TIGIT与CD112的相互作用较弱,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还不清楚[17]。
TIGIT的配体在多种妇科肿瘤组织中均被发现有表达。Oshima等[18]利用基因表达谱分析和免疫组化在卵巢癌细胞系OV-90表面和48.4%的卵巢癌组织样本中发现了TIGIT的配体之一Nectin-2的高表达,此外抗Nectin-2的抗体可抑制OV-90细胞的体外增殖,在小鼠肿瘤模型中,Nectin-2单抗可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在宫颈癌中,有研究发现TIGIT的另一配体CD155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高于宫颈上皮内瘤变和正常宫颈组织,CD155的表达可增强肿瘤细胞的活力,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进行性生长[19]。在子宫内膜癌中,共抑制分子例如TIGIT和TIM-3的高表达与淋巴结侵袭和疾病晚期有关[13]。TIGIT的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研究阶段,目前至少有3种药物(AB154、BGB-A1217和MK7684)正在进行晚期实体瘤的临床实验。
1.3 LAG-3
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LAG-3)最早是由Triebel等[20]在1990年报道,其在结构上类似于CD4共受体,LAG-3与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I(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II,MHC II)具有高亲和力,因此,MHC II被认为是LAG-3典型的配体。纤维蛋白原样蛋白1作为LAG-3的配体比MHC II的作用更为重要[21]。LAG-3可表达于T细胞和NK细胞,阻断LAG-3可改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的增殖和效应功能[22-23]。
LAG-3在卵巢癌和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Tu等[24]通过分析Oncomine和PrognoScan数据库发现LAG-3、PD-1、CTLA-4和TIM-3可能是卵巢癌的预后因素和治疗靶点。在宫颈癌转移瘤引流区的淋巴结中LAG-3水平明显高于正常淋巴结[12]。在上皮性卵巢癌中,肿瘤来源的CD8T细胞的效应功能受损,并有LAG-3和PD-1的共表达富集。而IL-10、IL-6和肿瘤来源的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共同上调了LAG-3和PD-1的表达。联合阻断LAG-3和PD-1可有效增强CD8T细胞的增殖和增强细胞因子的产生[25]。目前有多项正在进行的单独使用LAG-3单抗或联合使用PD-1单抗治疗妇科肿瘤的早期临床实验(NCT03250832、NCT03538028、NCT01968109、NCT03365791)正在进行。
1.4 VISTA
T细胞激活抑制物免疫球蛋白可变区结构域(V-type immunoglobulin domain-containing suppressor of T cell activation,VISTA)也称为C10orf54、B7-H5或血小板受体Gi24的前体。VISTA的胞外结构域与B7家族配体PD-L1和PD-L2同源[26]。VISTA主要表达于髓系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在T淋巴细胞中,VISTA主要在naïve CD4和FoxP3Tregs上表达[26-27]。值得注意的是,VISTA即可作为配体又可作为受体发挥作用,但这些作用并不相互排斥[28]。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VSIG-3是VISTA的配体,二者结合可显著减少人T细胞产生细胞因子和驱化因子[29]。而VISTA的配体功能最早是由Wang等[26]报道的,该研究发现VISTA抗体可抑制激活后的T细胞产生IL-2和IFN-γ,VISTA可能通过抑制早期T细胞受体的激活和阻止细胞分裂来负性调控T细胞的功能,但对T细胞的凋亡影响很小,目前VISTA的受体尚未被确定。
VISTA在人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中高表达,但在正常卵巢上皮和正常子宫内膜标本中不表达或低表达。在Mulati等[30]的研究中,体外肿瘤细胞中表达VISTA可抑制T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而在人子宫内膜癌细胞和卵巢癌细胞中沉默VISTA的表达可恢复T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的分泌,体内研究发现,抗VISTA抗体治疗可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时间。在卵巢癌和宫颈癌中,肿瘤细胞或肿瘤来源的免疫细胞上VISTA高表达可能与肿瘤晚期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31-32]。在最近本课题组的一项研究发现VISTA在98.2%的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组织中广泛过表达,但在正常成人和胎儿组织中不表达[33]。迄今为止,有两项关于VISTA单抗的I期药物临床临床实验:一项是正在研究的CA-170,一类选择性靶向PD-1和VISTA的口服小分子双拮抗剂(NCT02812875),该研究结果暂未公布;另一种是Jassen公司开发的VISTA单抗JNJ-61610588(NCT02671955),在此项研究中,有12名患者被招募,其中有1例发生了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相关的剂量限值不良反应,因此提前终止了这项临床实验。
1.5 B7-H3和B7-H4
B7-H3(CD276)和B7-H4(B7x或B7S1)均属于B7家族免疫调节配体的成员,二者受体尚未被确定,有研究表明B7-H3和B7-H4的潜在受体可能分别为髓系细胞触发受体2和B、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他们共同参与了免疫的共刺激和共抑制途径[34-35]。这两种配体的mRNA在大多数外周组织中均可以找到,但在蛋白质水平并没有组成性表达。研究表明B7-H3和B7-H4蛋白在多种肿瘤,包括肺癌、乳腺癌、胰腺癌和卵巢癌中均高表达[36-37]。
在妇科肿瘤中,B7-H3在高级别型和II型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高于低级别肿瘤和子宫内膜样腺癌,且与患者总生存呈负相关[38]。我们前期研究发现B7-H3在几乎所有的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病理亚型中高表达,与临床结局不相关[33]。在卵巢癌中,所有类型的原发及转移的浆液性和子宫内膜样癌中均可检测到B7-H4细胞质和细胞膜的表达,而在正常卵巢组织中B7-H4始终阴性[39]。
除了单独表达以外,B-H3和B7-H4也在多种妇科肿瘤组织中共表达。Zang等[40]的研究中,103例卵巢交界肿瘤和卵巢癌样本中,B7-H3和B7-H4在93%和100%的卵巢肿瘤中表达。Han等[41]的研究发现B7-H3和B7-H4在宫颈癌中均高表达,它们通过抑制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TGF-β)的产生,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从而导致宫颈癌的而发展,且与患者不良预后有关。目前关于B7-H3和B7-H4的临床实验均处于早期阶段,未有相关结果报道。
2 共刺激分子
2.1 TNF受体超家族
2.1.1 CD27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受体超家族包含死亡受体和结合TNF受体相关因子的受体(Traf)的受体[42]。CD27属于Traf样受体,仅在淋巴细胞上表达,naïve CD4和CD8T细胞也表达低水平的CD27[43]。CD27与其配体CD70之间相互作用可能促进CD8T细胞分化为效应T细胞,并通过T-B细胞和/或B-B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促进T细胞增殖和B细胞分化[44]。
在妇科肿瘤中仅有卵巢癌有CD27/CD70相关研究报道,其发现CD70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在正常卵巢组织中不表达,CD70在耐药卵巢癌细胞系A2780的mRNA水平和蛋白质水平高表达。与CD70抗体共培养后,发现顺铂耐药细胞的增殖明显下降,在小鼠模型中,CD70过表达的小鼠的CD8T细胞表现出比野生型小鼠更强的抗肿瘤反应[45-47]。近期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报道了一项关于CD27激动剂Varlilumab联合PD-1抑制剂治疗晚期卵巢癌的1/2期临床实验(NCT02335918)的结果,共66例患者被纳入实验,有49例患者可评估疗效,其中部分缓解5例(10%),疾病稳定19例(39%)。结果表明Varlilumab联合PD-1抑制剂对晚期卵巢癌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2.1.2 OX40 OX40(CD134)是TNF超家族成员之一,为分子量50kDa的糖蛋白,结构上具有胞浆尾部、跨膜结构与和胞外区域[48]。OX40主要在活化的效应CD4T细胞,尤其是Treg细胞和NKT细胞上表达[49]。OX40的配体CD252主要在活化的APC上表达,包括树突状细胞、B细胞和吞噬细胞[49]。Treg是众所周知的免疫抑制细胞,可以抑制效应T细胞分泌IL-10和TGF-β等因子的分泌,而OX40与其配体结合后可抵消Treg的负性调控作用,削弱其抑制能力[50]。
Ramser等[51]评估了47例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样本发现卵巢癌中OX40的高表达可能与良好的化疗敏感性和预后有关。在动物模型中,单独使用PD-1抑制剂或OX40激动剂对肿瘤生长无明显影响,当联合使用PD-1抑制剂和OX40激动剂可产生显著的抗肿瘤作用,60%的小鼠在接种肿瘤90天后达到无瘤状态[52]。除了蛋白质水平的表达,OX40在RNA水平上也有表达,Zhao等[53]分析了30例宫颈癌和20例正常宫颈组织标本,发现宫颈癌组织的免疫微环境中OX40mRNA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宫颈组织,高级别鳞状细胞癌中的水平略低于低级别鳞状细胞癌。目前有一项OX40激动剂针对卵巢癌的II期临床实验正在进行(NCT03267589)。
2.1.3 4-1BB 4-1BB又称为CD137或TNFRSF9,属于TNF受体超家族成员,主要在活化的T细胞和APC上表达[54]。4-1BB的配体与OX40的配体类似,在未激活的T细胞上并不是组成性表达,在被激活的24小时内诱导表达,在几天内达到高峰。因此,在一定条件下,OX40和4-1BB与OX40和4-1BB的配体在活化的T细胞和APC上的表达可以互相平行,这表明它们可能存在相似的作用[55]。
在卵巢癌中4-1BB的相关动物研究证明4-1BB共刺激和PD-1共抑制联合分子治疗可诱导协同抗肿瘤免疫反应,增强顺铂治疗的敏感性[56]。另一项研究报道联合抗TIM-3和4-1BB单抗治疗可显著抑制小鼠卵巢癌肿瘤的生长,60%的小鼠在接种肿瘤90天后达到无瘤状态[11]。目前没有专门研究4-1BB相关的药物在妇科肿瘤中的临床实验。
2.1.4 CD40 CD40是一种I型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B细胞,也表达于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和巨噬细胞,还表达于造血细胞、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57-58]。CD40的配体CD40L为CD154,二者结合后可在体液免疫应答的启动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在体外触发B细胞间的粘附、增殖、扩张、分化和抗体转换,是生发中心形成和发展以及亲和力成熟所必须的,是记忆B细胞和体内浆细胞生成必不可少的过程[59]。
多项研究表明,肿瘤细胞可以利用CD40/CD40L通路维持增殖能力和生存,建立免疫抑制微环境。Wang等[60]的研究中发现卵巢癌组织中CD40的低表达与晚期疾病和预后不良相关。Melichar等[61]的研究检测了8个卵巢癌细胞系,其中5个细胞系中CD40高表达,且IFN-γ可增强CD40的表达。体外细胞实验证明,腺病毒介导的CD40配体治疗可诱导来自新鲜手术标本的卵巢癌细胞的凋亡,同时还可增加卵巢癌细胞对顺铂治疗的敏感性[62-63]。在宫颈癌中,CD40在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的宫颈上皮内瘤变和晚期鳞癌中过表达,但在正常宫颈上皮中低表达。此外,CD40对宫颈癌细胞的刺激可激活NF-κB和MAPK信号通路,增强特异性CTL细胞的杀伤作用[64]。CD40激活巨噬细胞在子宫内膜癌细胞的生存和侵袭中发挥双重作用,CD40活化的I型巨噬细胞可显著增强细胞毒性并抑制肿瘤生长,而CD40活化的II型巨噬细胞可增强细胞侵袭和生存能力,因此,CD40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中的作用可能会限制CD40激动剂在子宫内膜癌中的治疗发展[65]。目前有正在进行的CD40激动剂ADC-1013用于人类实体肿瘤的临床实验,早期结果显示肿瘤内注射临床剂量的ADC-1013在患者中反应的耐受性好(NCT02379741)[66]。
2.1.5 GITR GITR又名TNFRSF18,是一种II型跨膜受体,主要表达于活化的B细胞、NK细胞和T细胞,特别是Treg细胞[67]。作为共刺激因子,GITR可参与T细胞的增殖、活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在Treg细胞免疫耐受的维持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GITR的相关研究已经在卵巢癌和宫颈癌中有报道。Lu等[68]的研究中发现单独使用PD-1抑制剂或GITR激动剂均表现出较弱的抗肿瘤作用,而联合使用PD-1抑制剂和GITR激动剂治疗可显著抑制小鼠卵巢癌的肿瘤生长,80%的荷瘤小鼠获得长期生存,还可增强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类似地,另一项研究表明,腺病毒载体治疗T细胞疫苗AD-P14和GITR激动剂单独治疗仅能治愈10%和30%的宫颈癌小鼠肿瘤,而二者联用可使完全缓解率达到100%,使荷瘤小鼠达到长期生存[69]。然而有研究显示,在HPV感染的宫颈组织标本中GITR阳性率为75.9%,而随着宫颈癌前病变的进展,宫颈组织中的GITR阳性率逐渐增高,GITR可能参与了HPV诱导的宫颈癌的进展[70]。
2018年ASCO会议公布了一种GITR激动剂(MK-1248)在37例晚期实体瘤患者中单独或联合使用PD-1抑制剂(NCT02553499)一期临床实验的结果,其中1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2例达到部分缓解,结果显示MK-1248对治疗剂量有良好的耐受性,未出现治疗相关死亡。
2.1.6 ICOS 诱导共刺激因子(inducible co-stimulator,ICOS)又名CD278,属于CD28受体超家族成员,与共刺激分子CD28和免疫抑制分子CTLA-4具有显著的同源性,主要表达于活化的CD4和CD8T细胞[71]。在体外结合ICOS与其配体B7-H2可诱导抗炎因子IL-10的释放,而阻断ICOS信号可导致T细胞分化不良,从而减少IL-4的产生[72-73]。
研究表明ICOS的配体B7-H2在铂耐药卵巢癌细胞系的mRNA和蛋白质水平均高表达[46]。在Conrad等[74]的研究中,卵巢癌组织微环境中,ICOSTreg细胞水平显著升高,肿瘤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表达高水平的ICOS配体可共同刺激ICOSTreg细胞的表达,并可被ICOS配体的抗体所阻断,生存分析显示ICOSTreg细胞可能是预后不良的预测因子。与TIM-3类似,ICOS也不太可能被用作单一的治疗方法,因为它们不能独立诱导细胞毒性免疫反应。虽然有关ICOS在妇科肿瘤中相关研究较少,但目前已有几种相关抗体在筛选中,并在动物模型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目前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研究ICOS激动剂JTX-2011和GSK3359609与PD-1抑制剂或CTLA-4抑制剂联合治疗晚期实体肿瘤的临床实验目前正在进行中(NCT02904226、NCT03693612、NCT02723955)。
2.2 B7-H6
B7-H6是近年来新发现的B7家族成员,分子量51kDa,为I型跨膜蛋白。B7-H6可结合其位于NK细胞上的受体-天然细胞毒性受体3(natural cytotoxicity receptor 3,NCR3),然后触发NK细胞的抗肿瘤细胞毒性作用,导致细胞因子分泌[75]。B7-H6可表达于黑色素瘤、神经母细胞瘤和血液系统或骨髓肿瘤细胞的表面[76]。
在妇科肿瘤中,B7-H6主要在卵巢癌细胞的胞膜和胞质中表达,与外周血中的NK细胞相比,肿瘤相关的NK细胞中激活受体NCR3的表达显著降低,这种受体表达减少与其可溶性配体B7-H6的表达有关,且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晚期和远处转移相关[77-78]。在宫颈癌中,B7-H6的表达与宫颈癌疾病进展和分期呈正相关,且在宫颈腺癌中的表达水平高于鳞状细胞癌[79]。B7-H6在妇科肿瘤中的研究处于基础阶段,目前尚无相关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
3 讨 论
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研究日新月异,如何将新靶点的基础研究应用到临床实践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虽然作用于PD-1/PD-L1和CTLA-4的抗体已经广泛应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但在妇科肿瘤中已报道的总体缓解率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免疫相关的靶点繁多,针对不同的肿瘤需要全面了解各靶点以及其受体在肿瘤或TILs中的表达后选择合适的靶点,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尝试。一般情况下,针对单独靶点的药物并不能成功诱导细胞毒性免疫反应,而联合用药可提高疗效,但也可能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在最近发表的一项II期随机临床试验中,PD-1抑制剂Nivolumab治疗复发性卵巢癌的客观缓解率为12%,而联合CTLA-4抑制剂Ipilimumab可提高客观缓解率至31.4%,且毒副反应可耐受[80]。此外,联合靶向治疗药物也可有助于治疗免疫治疗的副作用,同时提高药物疗效。我们的临床经验例如抗血管生成药物阿帕替尼联合使用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可降低卡瑞利珠单抗导致的特异性毛细血管瘤的发生,同时亦可增强抗肿瘤作用。同样也有研究表明预防性阻断TNF可提高CTLA-4和PD-1双重抑制剂免疫治疗的抗肿瘤疗效,减轻免疫相关性的结肠炎和肝炎[81-82]。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联合用药的顺序,特别是当共抑制分子和共刺激因子药物联合使用。已有研究表明,同时阻断PD-1和OX40并没有增加OX40激动剂的抗肿瘤作用,而是上调了T细胞共抑制受体的表达水平,反而加速了肿瘤中T细胞的消耗,显著削弱了OX40激动剂的治疗效果,而先使用OX40激动剂,再延迟使用PD-1抑制剂可减少T细胞消耗,维持T细胞增殖,从而增强OX40激动剂的抗肿瘤作用[83]。
由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和调节的复杂性,免疫靶向分子的药效指标的预测比较困难。根据PD-1抑制剂使用的临床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检测肿瘤组织或TILs中的相关免疫靶点配体或受体的表达、微卫星不稳定性、肿瘤突变负荷和错配修复缺陷等来预测药物的作用[84]。此外,循环生物标志物和肠道微生物群在动态监测肿瘤免疫状态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5]。
4 总结与展望
尽管针对免疫靶点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数量众多,但在妇科肿瘤中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卵巢癌的靶向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旨在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逐渐普及,子宫内膜癌的内分泌治疗也日趋规范。免疫治疗以其固有的特异性、适应性和持久记忆反应,仍可为难治性和复发性疾病患者提供补救治疗。这些新出现的免疫靶点的表达模式与治疗反应密切相关,相关研究多处于早期实验阶段,其潜在的机制和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