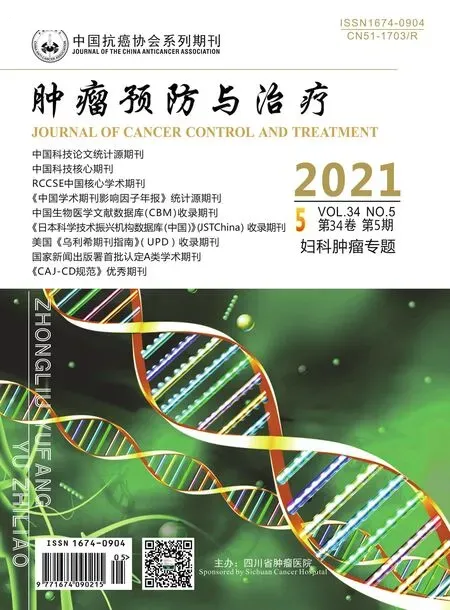PDS或NACT
——晚期卵巢癌患者的初始治疗该如何抉择?*
张国楠
610041 成都,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妇科肿瘤中心
肿瘤细胞减灭术(primary debulking surgery,PDS)及术后辅助化疗是晚期卵巢上皮性癌全程管理治疗中的硬核基础[1]。长期以来,PDS一直是卵巢癌的首选治疗方法。但晚期卵巢癌患者肿瘤病变广泛和/或具有严重内科合并症时,手术困难常导致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morbidity and mortality,M/M)增加[2-4]。因此,治疗前需要确定PDS达到满意减瘤水平的可能性以及患者自身因素(合并症、虚弱和营养不良等)相关的承受手术的可行性。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后再行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IDS)是降低这类患者术后并发症M/M的另一种替代选择[1-7]。两种治疗模式的目标都是术毕达到无肉眼残留病变(R0),因为它是卵巢癌患者最重要的独立预后因素。自从4个主要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实了两种治疗模式患者的生存期相当,奠定了NACT在晚期卵巢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NACT的理由,并呈上升趋势[8-11]。遗憾的是,目前针对是否能达到理想减灭术或选择NACT的术前评估方法通常是基于各医疗中心和医师的临床经验偏好,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其实用性和同质性欠佳而难以被推广。毕竟NACT不是所有晚期卵巢癌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法,那么,哪些患者进行NACT是恰当的呢?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的初始治疗,是选择PDS,还是NACT?一直是妇科肿瘤学界颇受争议的话题。在既往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中,PDS达到理想减灭术的晚期患者中不乏长期生存获益者。这可能源自患者自己的选择,也受益于妇科肿瘤医生手术技能的不断提高和/或术者对努力达到R0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并支持在适当的情况下应该首选PDS[2-4,12]。因此,目前临床实践中最困难与困惑的是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如何抉择PDS或者NACT?
1 明确NACT的适宜患者
PDS一直是晚期卵巢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对于PDS,手术达到R0或残留病变<1 cm是提高生存率的理想选择,但如果病变广泛严重,需要进行更复杂的手术,尤其是上腹部病变严重者,可能需要行膈肌腹膜切除术、脾脏切除术、胰腺部分切除术和肝脏病变切除术。手术的“根治性”程度增高,势必会增加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M/M[2,5,13-14]。同时,晚期患者通常有内科合并症,也可能不适合进行大范围手术。无论PDS还是IDS,毕竟R0和低M/M是卵巢癌手术的最佳结果。为此,在为新诊断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制定最佳初始治疗方案时,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1)预测哪些患者的病变是可以切除的,也即适合行PDS;2)确定哪些患者是围手术期低风险者,能够承受预期的PDS。换言之,如果PDS不能达到理想的减灭状态,或者患者具有围手术期发生严重并发症/死亡的高风险,就是NACT的适应证,就应该选择NACT。这也是美国妇科肿瘤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等于2016年提出用于判断选择治疗方式的标准,并特别强调NACT的应用应该由妇科肿瘤医生进行全面评估[14]。在临床实践中,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针对肿瘤病变的(应该努力切除),另一个是针对患者的机体状态的(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不能随心所欲手术),二者是互相制约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孤立地或者想当然进行评估与手术。尽管必要的手术切除病变的范围越广,减灭术就越彻底,达到了R0,那么“合适”的患者就越有可能成功地从手术中获益。但是,不能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否则,事与愿违,不是手术的初衷。
1.1 术前对可切除病变的预测
预测肿瘤病变的可切除性,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去探索、又难以捉摸和不断发展的挑战性问题,包括了临床查体、影像学评估和腹腔镜探查术中病变相关变量都具有标准,如目前临床实践中普遍采用的Suidan评分[15]和Fagotti评分[16]系统,可操作性较强,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由于成像工具和软件的改进和新发展,术前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晚期卵巢癌患者重要且精准的影像学特征,显示肿瘤粘连或侵犯的关键器官,以及手术难以切除的肿瘤部位(高风险的病变残留部位)[17-18]。因此,多学科综合治疗(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团队仔细评估影像学特征是决定是否NACT或需要其他外科专业医生参与手术以达到最佳切除的关键。
1.2 围术期高风险患者的确认
确定患者机体状态是否适合接受手术治疗是另一个难题,这涉及患者各种内科疾病合并症、围术期并发症甚至死亡风险、后续肿瘤治疗的开始时间及住院时间等,这些因素都应该作为确定患者是否适合PDS的参考条件。
对于国际妇产科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Ⅲc期和Ⅳ期卵巢癌患者,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的Narasimhulu等[3]应用PDS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与死亡的高风险来确定不适合行PDS的患者,符合以下任何一条标准,则定义为高风险患者(简称梅奥标准):血清白蛋白<3.5 g/dL、年龄≥80岁或年龄在75~79岁之间,但需同时满足其他一项危险因素[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能状态评分>1分或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分3~4分,IV期,或可能需行复合手术者]。血清白蛋白含量是临床上常用的反映患者营养状况的可靠指标,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作用,低白蛋白血症是卵巢癌、结直肠癌等患者围手术期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2,19]。因此,血清白蛋白是反映卵巢癌患者全身状况而作为筛选适合NACT的可靠指标。梅奥医学中心的Straubhar等[2]对1 777例接受了手术治疗的晚期卵巢癌进行分析,其中28.2%的患者为高风险患者不适合PDS而选择了NACT。高风险患者术后30天内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高2倍(6.2%vs3.5%),30天内死亡率高3倍(1.4%vs0.5%)。就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而言,NACT-IDS是一种并不劣于PDS的替代方案。NACT可使达到R0率翻倍,也不影响生存期;然而,它确实降低了严重的手术并发症M/M[20]。
2 平衡手术风险与获益
平衡手术的风险和获益永远是外科手术的基本原则,这在晚期卵巢癌手术中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只有直到手术开始并探查完毕,才能充分明确手术需要涉及切除的病变范围。无论选择PDS,还是IDS,手术减瘤至最小残留病变,同时低的手术M/M发生率,才是最佳的卵巢癌手术结果。因此,应该权衡PDS相关的围手术期并发症M/M的风险与其生存获益,孰重孰轻?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法应该基于可衡量的危险因素来预测围手术期M/M。
梅奥标准有助于识别PDS后显著增加的严重并发症的M/M风险的患者,从而选择NACT。反之,这也是选择手术适应证的条件。这在目前算是一个明智的、基于证据的方法来选择PDS或NACT的策略[2,4]。这关乎PDS和NACT患者的分类问题,确切的说是晚期卵巢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决定何时手术时机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确定患者的手术危险因素以及预期的手术复杂性(难度)。大多数患者能够承受低难度的手术,但如果预期进行高难度的手术,围手术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而术前NACT是可以降低相关患者手术的难度与并发症M/M。
然而,美国凯特琳癌症中心Chi等[21]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即使面对较高的手术风险,只要在PDS时达到了R0,就与改善生存期相关。他们对141例肿瘤负荷较大晚期患者在PDS时实施了广泛的上腹部肿瘤切除手术,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22%,患者中位OS达到了57个月,明显长于现有的评估PDS与NACT的随机对照试验的中位OS(22~49个月)[8-11]。
由此,我们面临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在实施晚期卵巢癌PDS时,多大的风险才算大?前面提及高危组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为6.2%,30天死亡的风险为1.4%。面对危及生命的高度恶性且晚期的卵巢癌,PDS是不是太危险了?而放弃PDS是否又过于保守呢?Havrilesky等[22]谨慎地从患者的角度调查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患者愿意接受增加15%的并发症发生风险和增加4%的死亡风险,以此将OS从3年增加到3.5年。说明患者有接受较高的围术期并发症风险和手术死亡率,以换取延长生存期的愿望。该研究为妇科肿瘤医生提供了应该适度考虑患者意愿的思路,今后应该将其纳入临床试验设计中。PDS和NACT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初治医生偏好的影响,因此,医生对治疗获益和风险重要性的判断可能与患者的意愿不一致。理想情况下,应考虑到患者的意愿并知情告知达成一致。基于此,这引发了大家重新评估验证高危患者的围手术期严重M/M对选择PDS或NACT的标准的关注与争论。对于高危患者,如果降低PDS或者理想减灭术的标准,必然会降低围手术期的M/M,但也可能会缩短患者的生存期,并可能增加潜在疾病的痛苦。选择恰当的患者,或者医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或者不做手术,永远是医生诊治疾病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好的外科医生知道怎么做手术,更好的知道什么时候做手术,最好的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做手术”[4]。既要彻底切除卵巢癌腹盆腔内病灶,又要减少手术并发症,这常常需要多学科合作。把握好“彻底切除病灶的合理证据”,既要考虑患者接受手术的高风险因素和肿瘤固有的生物学特征,还要依赖于所在医院的基础设施以及手术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包括MDT团队的医生)。高质量的专业培训和管理,才能保障手术的效果。所有晚期卵巢癌患者均应得到最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最佳的手术治疗,而缺乏专业知识不应成为影响患者获得理想治疗的阻碍。同时,主观判断为不满意减灭手术也不应该是滥用NACT的理由[1]。
3 NACT的优势与局限性
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接受了NACT,尤其是老年和广泛转移性病变的患者[6,23]。NACT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生存效果因患者因素和肿瘤因素而异。肿瘤病变的程度与范围是对晚期卵巢癌患者选择NACT的最可靠因素。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mittee on Computer Network,NCCN)指定机构以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1~2012年,NACT在FIGO Ⅳ期卵巢癌的应用超过了60%[24]。如此多的在Ⅳ期患者中应用可能源于PDS对这类患者本身的生存获益不大,而当PDS手术困难时,常常减灭术难以达到理想标准,而且手术并发症M/M很高。最近对两项随机试验的综合分析表明,与PDS相比,长达7.6年的随访显示Ⅳ期患者NACT的总生存期得到了改善[25],这可能进一步支持在Ⅳ期患者使用NACT。另外,老年患者因为内科合并症发病率较高和身体虚弱而不适合PDS,也应该接受NACT[23]。
目前的研究资料多表明,NACT-IDS的生存期虽不差于PDS,但也有研究认为NACT与OS相对较差相关[23]。NACT对生存期的影响是异质性(多元化)的,取决于患者和肿瘤两大因素。在老年、FIGO Ⅳ期和广泛转移病变的情况下(T3N1M1),NACT-IDS与PDS组的OS相当。相比之下,对于年轻和FIGO III期患者,NACT-IDS组的OS差于PDS。PDS与NACT相比,在Ⅲ期卵巢癌患者中具有相对较好的生存获益[24,26-31]。
值得注意的是,NACT降低了围手术期死亡率,而且接受NACT的患者比接受PDS的患者死于非卵巢癌原因的可能性更低。老年和Ⅳ期患者的非卵巢癌总死亡率显著降低了40%~50%[23]。这提示对于病变广泛且合并症多的老年患者,NACT的使用又增加了一个合理和适当的策略。有必要进一步探索NACT降低非卵巢癌死亡风险的原因。
当前研究NACT的优势包括对大样本的同质研究人群进行了NACT的研究,显示出NACT降低了手术的难度和并发症M/M、提高了手术的切净率,预后也不差于PDS。
但也有其局限性,缺乏一个实用性强的程序来明确选择NACT或PDS的适应患者,另外,NACT的方案和疗程数、患者的身体状态、内科合并症、术前白蛋白水平、妇科肿瘤医生的经验、手术类型、医院的重症管理水平、使用诊断性腹腔镜诊断与评估、上腹部肿瘤的具体位置和肿瘤负荷等和NACT的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23,32-33]。NACT提高了手术的R0率的优势,但这并没有转化为生存的优势,也是美中不足和值得探索原因之处。
4 结 语
目前的真实世界的研究数据[23-24,26-31]和试验[8-9,34-35]表明,在为晚期卵巢癌患者制定治疗策略时,应充分考虑患者和肿瘤因素的重要性。基于PDS的治疗方法更适合于可完全切除的肿瘤,和年轻身体状态较好的患者;而基于NACT的治疗方法最好用于具有高肿瘤负荷的FIGO Ⅲc、Ⅳ期患者;有内科合并症的老年患者,不适合实施PDS,也是接受NACT的适宜人选。总的来说,虽然NACT-IDS在特定的晚期患者中是一种合理的治疗方法,但就具体个体而言,可以考虑对体能状态很好和能达到R0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PDS,以改善患者的生存。对晚期患者不建议常规使用NACT,提倡个体化和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平衡治疗获益与风险,合理决策PDS与NACT。正所谓,将军决胜何止在战场?妇科肿瘤医生决胜卵巢癌又何止在手术台?根据患者围手术期的危险因素和肿瘤病变的程度,选择对患者最有利的治疗方式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