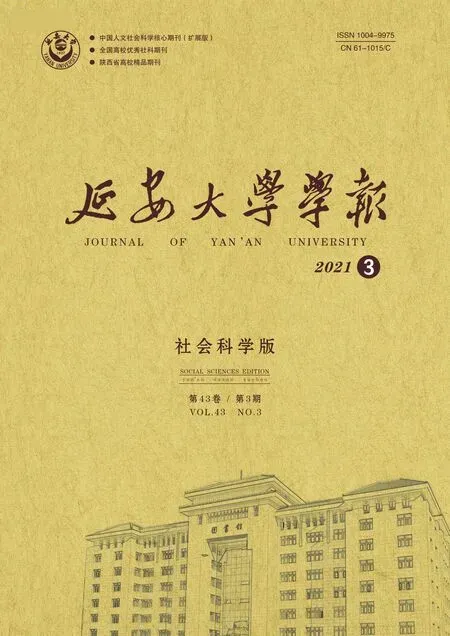论怀安诗社诗人对旧体诗之改革
徐钰茹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国家不幸诗家幸。当“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少爱国志士纷纷发起组织诗社,如绮社、国风诗社、枕戈诗社、青萍月刊社、中兴诗社、怀安诗社、湖海诗社、燕赵诗社等,他们以诗歌激昂士气,鼓吹中兴,抗战救国。在众多抗战诗社中,怀安诗社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团体,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古典诗词诗社”。[1]该诗社1941年9月5日由林伯渠倡议成立,取“老者能安,少者能怀”之意,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自然解散。
在激情的抗战时代,在一切文艺皆为抗战服务的思想下,怀安诗社诗人“陈诗以展义,长歌以骋情”“独向吟坛张旗鼓,好把诗魂壮国魂”。他们的诗歌创作“利用旧瓶装新酒,把旧体诗作为时代的号角,作为革命的投枪,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发挥它的战斗作用。”[2]276但是,在“共道旧诗不时式,缚人心意费人力”[2]87的社会认知和一部分怀安诗社诗人只会旧诗的客观情势下,怎样减少大众接受障碍、加强宣传效果,便成为怀安诗社诗人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旧体诗改革也就提上了日程。霍建波《论怀安诗的古典根柢与现代情志》、孙国林《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李鸽《论怀安诗社》、吕晴《小议怀安诗》等,都曾对怀安诗社的旧体诗特色作出分析研究,但没有集中探讨怀安诗社诗人对旧体诗的革新路径。基于此,本文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手论述怀安诗社诗人对旧体诗的革新探索。具体而言,怀安诗社诗人是以“旧瓶装新酒”为指导思想,对诗歌内容进行革新;以“通俗化与大众化”为原则,对旧体诗形式进行改良。下面就此两方面展开。
一、内容革新:“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一语源自西洋古谚“旧瓶不能装新酒”(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此语引入中国,经常用在政治改革和文学批评中。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云:“‘世界革命’诸先生似乎就有开埠头之意。他们虽失败了,但与他们同时的黄遵宪乃至现代的吴芳吉、顾随、徐声越诸先生,向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们都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功,他们在旧瓶里装进新酒去。所谓新酒也正是外国玩意儿。”[3]指出诗界革命派、学衡派诸人的诗歌创作皆是“旧瓶装新酒”。鲁迅当年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体诗,后来不仅自己做起旧体诗来,还说:“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4]承认“旧瓶装新酒”的合理性。胡怀琛在1936年元旦吟道:“新酒旧瓶君莫笑,敢云欲借此篇传。”此年,他又在南社最后一次聚会中咏歌:“新酒旧瓶谁管得,只贻朋好不须传。”以“新酒旧瓶”相标榜。含沙《“旧瓶”和“新酒”》:“‘瓶’和‘酒’的新旧是绝无关系的……只要改得好,换得妙,外国的东西可以变为中国的,古时东西也可以变成现在的。而且,在这‘改’和‘换’的过程中,也可以顺便就产生新的来。”[5]肯定“旧瓶装新酒”能产生合时的、新生的内容。他们对“旧瓶”的诗歌形式和“新酒”的思想内容,都持包容、肯定态度,即为旧体诗的创作张本。倡导和实践“旧瓶装新酒”最为有力的是怀安诗社诗人。
怀安诗社诗人李木庵在《秧歌舞吟》中云“制谱选词真个忙,旧瓶新酒由来妙”、[2]44谢觉哉《与钱老论新旧诗体》道:“可以旧瓶装新酒,亦可旧酒入新瓶”、[2]85刘道衡《读钱太微先生<孤愤草>诗集后》评云:“莫嫌瓶已旧,且喜酒常新”[2]222等,皆提到“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不过,还是诗社的发起人林伯渠说得最为详尽,“诗社宗旨在于利用旧形式,装置新内容,即旧瓶装新酿;用诗歌激励抗战,收复国土,反对专制,争求民主,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团结同情者,赞助革命”。[6]2对于怀安诗社的旧体诗改革,李木庵曾有诗句论道:“诗界革命倡有年,今尚无人新建绩。”[2]87可以说,怀安诗社诗人在创作上,接续诗界革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的精神。但是与“诗界革命”往往只着眼于形式,“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不同,怀安诗社诗人在“旧瓶装新酒”的指导思想下,努力以旧体诗反映时代内容。
纵观怀安诗社诗人的作品,或歌咏将士战场作战风采、或讴歌边区军民生活热情、或互励互勉赠人酬答、或批判时局讥讽恶势力、或宣扬马克思主义……总之,他们的诗歌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内心情感的真诚抒写。
赞助革命是“怀安诗社”成立的本旨,激励英勇奋战、歌颂将士风采是其最重要的主题。1941年1月,新四军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我军在英勇突围过程中,损失严重,伤亡惨烈。事变后,敷扬作《皖南零忆》十一首,回忆新四军进军沛岭、固守石井坑、黄昏突围、随温涛东征等场景,每首诗都苍凉悲慨,郁勃磊落,摄人心魄。试看其四:
退守穷坑粮久绝,旌旗傲日对重围。弹空刀折犹呼杀,阵失形畸未足危。
木石翻飞人作垒,青红狼藉草含悲。孤军义愤吞山岳,不许奸徒染血回。[2]98
此诗写新四军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顽强地固守石井坑。尽管子弹打完了,刺刀坎折了,但是将士们依然拼尽全力喊出厮杀之声;虽然木石被打得翻飞,也要用人体作堡垒,坚守阵地。诗歌生动地展现了战场上热血男儿将生死置之度外,同顽军浴血奋战、殊死搏斗的爱国情怀,场面惨烈,气势悲壮。与敷扬《皖南零忆》的壮烈底色不同,佚名的《东北行军途中》七首,充溢着胜利的欢悦,节奏轻快活泼,如其四:
轰轰大炮猛攻城,嗒嗒机枪袭贼营。高地围攻防守敌,迂回堵截增援兵。[2]115
此诗表现了我军在行军过程中,情势有利则一鼓作气,强攻猛打;处被动态势时,则坚防顽守,与敌人迂回截堵,拖延时间,保存自己。生动展现了将士们在战场上因势制宜、随机应变的作战方略与英勇风采。除此之外,郭子化《军行山中》、李木庵《抗战八年述》等,都描绘了我军在沙场作战过程中的光辉事迹。
陕甘宁边区,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后方。在这里,军民团结互助,为救亡图存、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奋斗。试观李木庵《开荒曲》(其二):
万千劳动手,改变南山岗。镢头翻上下,土块乱飞扬。
野草连根拔,新壤得阳光……敌去手把锄,敌来手持枪。
爱护我农产,保卫我家乡。生产同战斗,热潮满太行。[2]42-43
这首诗约作于1943年,此时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日军不断对延安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这一年太行山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蝗灾,抗战军民和边区群众都处于极度困苦之中。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首《开荒曲》就反映了军民自己动手,开荒南山岗,尽管劳累艰辛,但人人精神振奋,对新生活充满热情与期盼。全诗展现了军民万众一心、和乐融融的劳动场景,讴歌了艰苦岁月里军区民众克胜一切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又如李老的《纺纱词》:
咿呀不断纺车声,轮转纱长半欠身。姐妹班中群比赛,看谁细致看谁匀。[2]37
这是李木庵、张曙时等老同志与女同志们在窑台上学习纺纱,相互竞争,看谁的产量高质量好,争先恐后为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沸腾场面。这种欢乐的氛围、劳动的热情,着实令人感动。他如《陕甘宁边区普选》《边区乡居杂咏》《秧歌舞吟》《闹中秋》等,都描写了边区军民自由民主、融洽相处的生活图景。
酬答送别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为常见的主题之一,在《怀安诗社诗选》中,此类主题同样占较大的比例,而尤以任锐的《送儿上前线》最为动人: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悽伤。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衣,往事安能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2]234
任锐是烈士孙炳文的妻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炳文牺牲,任锐带着遗孤三子一女历尽艰辛,矢志不渝坚持革命。1945年9月,任锐的小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回延安看望失散多年的母亲。为了照顾任锐同志,组织决定留下孙名世在延安工作。但这遭到任锐的坚决拒绝,她认为儿子应该继承父志,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送儿子上前线那天,任锐写下此诗。诗中“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写出为人母的不舍与担忧;“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饱含了喜悦与热泪、无言与辛酸。但为了革命事业,她毅然将儿子送上东北战场。后来孙名世英勇战斗,最终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而任锐也因积劳成疾,不治身亡。其舍小家为大家,忘我的革命精神,时至今日,读之依然令人敬仰与敬畏。与女性笔下的送别充满着温情脉脉有别,林伯渠的《赠北赴热察诸同志》豪情壮阔,义薄云天:
不教大地闲吾侪,运启乾元一划开。为障狂澜作砥柱,还擎旗帜荡尘埃。
秋高爽澈玉关柳,云起遥倾燕北杯。别后佳章可寄我,好收诗话入窑台。[2]230-231
林伯渠的这首诗作于1945年10月,此时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干部赴东北扫荡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尘埃。此诗激昂雄勃,展现了诗人乐观开朗的胸襟,表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为将士赴热察的革命胜利而干杯。诸如此类,还有佚名《送夫出征东北》、李木庵《儿女离延北征,诗以壮之》、朱德《赠同袍战友》等,表达了诗人对将士的激励,希望他们为革命的光荣使命而奋斗到底。
怀安诗社诗人对自由、民主、勤劳、勇敢等大力歌颂赞扬,对于黑暗、阴谋、奴态、丑恶同样不遗余力揭露批判。1947年,蒋介石不顾中共警告,不顾民主党和人民的反对,伪造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为此,钱来苏作了一首《蒋记伪宪》:
盗国扰权二十秋,连番还政仅辞修。四家多喜万家哭,亲者如伤快者仇。
民治自由渔网尽,国权独立货金收。翻开伪宪条条检,唯我独尊莫外求。[2]245
此诗痛斥蒋介石盗取国家政权,扰乱民权二十余年。此番立宪,蒋记伪宪以“政协宪草”“各党派宪草”的名义,企图以之蒙蔽国人,又在条文上装饰若干民主词句,以期瞒天过海,但这也掩盖不了其专权的本质。因此有人讽刺,此部宪法可以用八字概括“人民无权,独夫专权”。这首诗对蒋记伪宪的无情揭露,可谓切中时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搜刮聚敛、崇洋媚外等种种丑陋行为,被刘道衡写入《哀江南》中,试观其三:
朝朝暮暮议纷纷,天下如何定一尊。扫境倾囊供内战,指挥台上有冈村。[2]125
《哀江南》本是南北朝时庾信所作的一篇赋的题名,抒发梁朝灭亡之悲痛、个人身世之不济,这里借古题寓蒋氏政权的没落。此诗痛斥蒋氏搜刮民财,致力于内战,揭露他利用日寇降将冈村宁次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这是典型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卖国求荣行为。诗人坚信,蒋氏政权违背民心,迟早会走向垮台灭亡的。此外,刘道衡《时事》、韩进《时事杂咏》、李木庵《发国难财》等,无不对时弊痛下针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郑大华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说:“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甚多,但能影响文化发展并具有重要地位的主要有三大思潮,即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7]在《怀安诗社诗选》中,突出表现怀安诗社诗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钱来苏《陕北杂咏》其五:
民主政权初展开,穷根拔去富根来。自由平等从何得?保卫田财反独裁。[2]59
“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权”的表现,而它必须从“土地改革”中来,诗人大声疾呼“保卫田财反独裁”,正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集中体现。他如李木庵《闹中秋》“赖有中国共产党,阶级翻身平分田……社会平等废特权,劳力获食无弃置”,也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思想的阐发。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李木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周年》指出:“取材日常生活地,理论实践交相融。文化须与劳力合,学习人民在虚衷。”[2]84理论来源于实践、真知来源于人民,这是对马克思唯物论和认识论的发挥。李木庵还有《依韵奉和太微叟甘泉归后》“理论还须实践之,万千民众是吾师”“真理须从辩证知,一编马列足忘疲。吾翁高举如椽笔,好振吟坛唯物诗”、谢觉哉《消暑续咏》“事实才能证理真,何劳挥汗论原因”等,都是宣扬马克思“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哲学思想,改变了新旧体诗的精神面貌。
因篇幅所限,每类题材仅例举两首以管窥之。从怀安诗社诗人的旧体诗题材来看,不管是传统的沙场战争、送别赠答、时弊民病主题,还是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抒写,无不洋溢着革命激情、无不切关民众生活、无不跳动着时代脉博。因此,韩晓芹对怀安诗社诗人的诗歌内容给予高度的评价:“综观怀安诗人的作品,在内容上都具有战争史料与革命掌故的价值……展谈一过,则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史实都可了然于胸,实是一部史诗”,[8]是不错的论断。
二、形式革新:通俗化与大众化
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皆以文艺为前锋。在艰难惨烈的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服务政治更为明显。为了有效地、广泛地宣传抗日,诗歌通俗化与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改革目标。关于旧体诗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李木庵曾自我批评道:“某些旧体诗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仍然务奥求僻,滥用古人辞藻,以攒簇雕镂为典雅,疑白话为打油,为鄙俚,以为它没有艺术性”,[2]277好在他们幡然醒悟,“朝着通俗性这条大道走去,以期与工农群众的歌谣合流,而使有着形式、节调和音韵的新诗出现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前”。[2]281
(一)诗韵改良
李木庵《论诗韵,给怀安诗社同志建议》“人问革从何者先?我意改良在格律。平仄对仗未可拘,五七定言亦不必”,[2]87钱来苏《谢老勉予改作新诗,破觚为圜》“歌能上口调平仄,律欲从心破偶奇”,[2]86力图放宽旧体诗的格律尺度,打破律诗的对仗要求,以期达到通俗化的目的。鉴于传统《佩文诗韵》分韵太多、范围太窄、古音与今音异读之处甚多,李木庵提出废除清代的《佩文诗韵》,初步拟定《怀安新韵》。《怀安新韵》是在《佩文诗韵》的基础上,把同一韵母(包括复合韵母)的各韵和历史韵书中可以合并的各韵参观互证地合并起来,归纳为若干韵,(1)参见李石涵《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如东冬合并,江阳合并等。诗社规定:“凡写作新旧各体韵文的作家,除随自己的方便,仍然可以用《佩文诗韵》押韵,或用方音押韵不加限制外,采用《怀安新韵》的同样认为合格。”[2]284-285从怀安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来看,他们的旧体诗大部分还是遵守《佩文诗韵》的规定,少部分采用新韵,如姜国仁《北上赴延》打破了传统律诗严整的平仄规范,音韵上也体现了《怀安新韵》江阳韵合的新韵特点;董必武《晨起书感》在平仄格律上虽比较规范,但在诗韵上采用的是《怀安新韵》“支齐”合并的规定。
除致力于改良诗韵外,怀安诗社诗人进一步冲破传统律诗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的规定。在怀安诗社诗人提出废除律诗对仗的主张后,一些同志就不再拘泥于五、七言律体的对仗。如佚名《战地口占》:
午夜军书急,轻装趁夜程。衔枚穿间道,万籁寂沉沉。
拂晓包围合,笼中鳖待擒。青山齐唤话,不战敌投诚。[2]93
诗中描绘了一幅出征图:在漆黑熟睡的晚上,万物寂静的山间,战地将士收到出征消息后,紧急出发。他们行走在丛林里,缓缓将敌人包围。尔后向敌人大声宣战,喊出“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口号,这时四周的青山也似乎加入了作战行列,随战士的宣喊而“齐唤话”。这样一来,敌人闻风丧胆,纷纷缴械投降。其场面之壮观,战士之激动,可想而知。此诗急中有缓,动中有静,诗中有画,颇为新颖。又如佚名的《打游击》:
鸟道丛林密,迂回斗虎狼。宿营依树幕,掘窖贮军粮。
挺进轻装急,潜师敌后扬。神威人莫测,一战扫搀枪。[2]94
此诗反映了八路军与敌军迂回周旋的抗战智慧,生动地展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地口占》《打游击》全用单行句法而无对仗,句贯意连,文从字顺,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二)语言改造
旧体诗语言古典高雅,要它与广大民众打成一片,发挥其在人民群众中的教化与感染力量,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对语言进行改革。谢觉哉云:“不改温柔敦厚旨,无妨土语俗词陈。里巷皆歌儿女唱,本来风雅在宜人”,[2]85-86李木庵去:“言与文分专制利,文比言深普及难。若从民主论文化,大众事应大众观”,[6]33提倡“土语俗词”、不避“里巷歌谣”,尽显“大众本色”。
一是口语、俚语入诗。在怀安诗社诗人的诗作中,可见王铁生《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服用三年”中的“装烟”、李木庵《延安新竹枝词》“一般装束一般好,说甚洋包与土包”里的“说甚”、李木庵《一九四五年元日诗》“年年岁首惊时乍,老来自笑还干啥”中的“干啥”,既是百姓口头语,又具地方方言色彩。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门面而今开放了”“陪都真个好”“荐任官儿”等口语入旧体诗,极富生活气息。为了达到通俗的效果,有些诗人将百姓现场说话的语句,直接放入旧体诗中凑句,使诗歌的真实性与画面感极强。如刘道衡《斗恶霸》:
血债终须用血赔,那能逃得到天涯!广场群众呼声急:“一切东西拿出来”!
攘臂婆姨争诉苦,低头恶霸假悲哀。万千仇恨齐清算,“决不容他这一回”。[2]62
写斗恶霸的现场,民众“呼声急”“攘臂”等动作描写,突出展现了他们积久怨深的情绪、愤愤不平的气势,为后面的情感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切东西拿出来”“决不容他这一回”两句,如神来之笔,民众正义又激愤的形象也因此而呼之欲出了。李木庵《陕甘宁边区普选》:
候选名单次第开,烧圈投豆各安排。一声报道大家听,“要把好人选出来”。[2]39
这是1945年延安边区组织的一次民主选举,为了组织老百姓选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他们为不识字的老百姓想出“烧圈投豆”(2)烧圈投豆,是为不识字者安排的选举方法,将候选名单张贴,依序唱名,投票人对某候选者赞成,就在他名字下用香火烧一小圈,代表一票。或在候选人名字前置一碗,赞成谁,就在他碗里投放一粒豆子,代表一票。的法子,并鼓励百姓“要把好人选出来”,语句温和平实,因此一句,主持者平易近人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凸显出来了。还有的诗质直如平常说话,完全不顾五七言旧体诗常规的句式节奏。拿七言诗为例,董必武《答木庵见赠元韵、兼呈林谢二老》“自从/九一八/而后,寇凶/事急/忧/锋镝”,谢觉哉《秋初即事》其二“再/百个旅/来/送死,更/三年仗/以/求生”,谢老又有《别甘泉》其六“公/余日/作何/消遣,一局棋/加/一首诗。”传统七言诗通常有四顿,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句式,然而用百姓平常的口话入诗,难免有不合节拍之处。怀安诗社诗人并未因此而刻意润色或回避,而是保持原貌写入诗中,打破旧体诗的常规节奏,读来亦妙趣横生。
二是新语词入诗。邓仕樑在《现代性与古典精神——试论古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割裂问题》中云:“从文学的角度看,诗人用的语言,从来都是最‘现代’的。”[9]的确,在怀安诗社诗人的诗作中,运用新名词、时新语是十分突出的现象。新名词入诗在《怀安诗社诗选》中可谓是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如李木庵《延安新竹枝词》(其二):“跻跻跄跄干部才,高呼同志笑颜开。半张活几书盈卷,大礼堂听报告来。”[2]33诗中“干部”“同志”“大礼堂”等新名词跻身古体诗中,并无刺眼硌脚之感。刘道衡《时事》(其二):“洋人说我顶呱呱,中美原来是一家。门面而今开放了,飞机大炮好援华。”[2]127“顶呱呱”一词晚清方产生,表“优秀”“卓越”等意,“飞机”“大炮”是近代以来新产生的交通工具、战斗武器,它们入旧体诗中,为诗歌别开一境。刘道衡《时事》(其七):“美械美机美国船,花旗布匹花旗棉。花旗奶粉花旗面,美国蜜柑美国烟。”[2]128全诗纯是新名词组合,而且首尾连贯,中间两句出以变化,给人回环往复之感,读来琅琅上口,并无不妥之处。还有鲜活的时语,如1941年3月,李木庵出巡视察子长、安塞、保安等县,作《春游杂咏》六首,其六云:“明天因事回延安,议会重开审预算。团结三三制有力,信心定可息狼烟。”[2]23诗中的“三三制”(3)三三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即在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各级参议会的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属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如果不经作者自注,或不查阅工具书,就不能很好理解其意。又如李木庵有感蒋介石大打内战,招致民变蜂起,于是作诗讽刺:
独夫好杀眼不开,杀得江山骨成堆。第一战场杀未了,第二战场又杀来。
纵然美械源源济,争奈民心去不回。杀来杀去等自杀,洋爸还骂不成材。
裤里英雄真可哀![6]115
诗中的“第二战场”是指蒋介石以正规军与地方团队压制因官逼民反的叛乱,却有不少降而加入民变队伍中,时人戏称之。同时,诗中的“裤里英雄”形容蒋介石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压迫人民的丑行,比喻可谓形象贴切,辛辣刺骨。
(三)诗体改革
对于诗体形式,谢觉哉《与钱老论新旧诗体》云:“新诗应比旧诗好,新代旧又代不了。旧诗古奥识者稀,新诗散漫难上口。”[2]85谢觉哉认为,旧诗确实没有新诗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但是新诗又不能完全代替旧诗。旧诗古奥,难与民众打交道;新诗散漫,难以上口传播。这两种诗体都与“有韵能歌兼有意”的理想有很远的距离。那么怀安诗社诗人对什么样的诗体表示青睐呢?李木庵在《漫谈旧诗的通俗化及韵律问题》中,就流露出对鲁迅用旧体诗七言古风歌行体和民谣的形式写的讽刺诗如《好东西歌》之类的作品表示欣赏。
无疑,民歌民谣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诗体。在《怀安诗社诗选》中,李木庵有多首民歌体诗,如《延安竹枝词》《纺纱词》《纺毛词》等。这里例举他的《延安思》:
塞上赋于役,星霜易岁时,他年瓜代去,何物最相思。
延水南北至,合流向东驰,形如丁字爽,此景丽人思。[2]50
此诗是民众熟悉的问答体,共有十三句,此后十一句皆以“此景……思”结尾,具有鲜明的层次感,易为大众接受。1948年春,我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奋战,聚歼胡匪,收复延安。同时在东北、华北进行的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捷报频传,极大鼓舞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在边区后方工作的陶承,闻报欢欣,作了三首《红云曲》,每首都以“朵朵红云直向东”起句,引起怀安诗社诗人如张曙时、钱来苏等人的唱和互勉,谢觉哉也写了五首《红云曲》,还风趣地吟了两句“陶娘妙句安天下,个个红云曲唱来”,可想见当时诗社的热闹与雅趣。试举谢觉哉和钱来苏各一首:
朵朵红云直向东,翻身土地尽归农。支援前线需粮草,瑞雪连朝兆岁丰。[2]252
朵朵红云直向东,耆婴欢笑路行中。歼顽驱帝新华现,亿万人心亿万同。[2]254
开头用“朵朵红云直向东”抒发诗人当时的欣喜欢悦之情,其后的内容则反映了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活的期待。这些诗歌感情自由奔放,形式不变中求变,富于音乐性,易记又上口,最为民众喜闻乐见。
除了整齐的民歌民谣形式外,李木庵对旧体诗诗体的改革提出“参以长短句何妨,所贵意明而气适”,[2]87创作一种雅俗共赏的新诗体,名曰“怀安诗体”。李木庵在《发国难财》诗后自注,“起句用短音,中用长音,原定为怀安诗体”。且看《发国难财》:
蜀山高,蜀水腴,昔为天府今陪都。陪都真个好,四境纵横汽车道……可怜抗战成观战,那堪重庆为重灾。因何致此谁敢说,放胆且发国难财。国难财,心死哀。[2]111-112
参见《发国难财》的诗体形式,再联系李木庵对“怀安诗体”的定义,那么他的《开荒曲》《秧歌舞吟》也都是怀安诗体的代表之作。这种诗体在形式上先用短音,后用长音,根据需要多次转韵;在内容上融记事、抒情、议论于一体,与传统的歌行体颇为相近。
不过,他们的诗体改革也未止于怀安诗体,而是走得更远。1946年8月,在延安诸老的一次闲谈中,林伯渠说:“怀安诗社作者不宜长时停滞在旧诗形式内,应求作品通俗化,以起到现实的战斗作用。”[6]110谢觉哉也发表意见:“旧体诗市场不大了,诗人应翻然改图。我意旧诗难合时宜,是因格调过于严整,含义每有晦涩。严整失自然,晦涩欠通俗,似应求整齐中不失自然,自然中不失整齐。嵌用韵脚以作整齐之矩,参用长短句藉传自然之神。不用乖典,不用僻字。希个人放宽尺度,不拘格式。”[6]110他们的这次谈话未就此作罢,后来还专门商之钱来苏。钱来苏对此亦表赞成,并谓革新的标准就是通俗易懂。此番倡议之后,怀安诗社擅长五七言文体的老人们也竞作新诗。如刘道衡的《打狗曲》:
天下不太平,来了老妖精。驱使中国狗,专咬中国人。
人民早觉醒,打狗棒一根。打折了两腿,妖精喊调停。
调停只是缓兵计,人民眼睛看得清。握紧棒,挺起身,打狗同时撵妖精,不绝祸根不要停。[6]113
刘道衡诗成后,自己附上一函与李木庵云:“林谢诸老,号召我们放脚,自己觉得上了几岁年纪,骨头有些硬化,真要放大,颇不容易,然而是可以放粗一点的,因而作了一首《打狗曲》,什么形式都说不上。”[6]113此是当时的放脚诗,诗中三言、五言、七言错杂,语言通俗明了,读来意趣盎然。李木庵读后,也作一首放脚诗取谑,谓刘道衡之新诗是半大的“黄瓜”脚,但依然称赏其作“别风姿”。另外,高敏夫的《将军愁》也颇有意味:
跑着来,爬着走,缺了腿,断了手;笑者来,哭着走,披长衣,挂短袖;
愁着来,恼着走,咒黄土,怪石头;饿着来,渴着走,怨梢林,恨山沟;
车上来,担架走,短命鬼,不长寿;要不死,当俘虏。[6]114
此诗描绘出打败仗后的残局:将军丧气窘迫,士兵丢盔弃甲、夹着尾巴逃跑……他们犹如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滑稽可笑,起到很好的讽刺效果。这首三言句式的新诗,神似里巷儿童口里的歌谣,简净活泼,趣味盎然,读来令人捧腹。
怀安诗社诗人用旧体诗的形式,传达出新时代的内容,在旧体诗的音韵、语言以及诗体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李石涵所云:“他们的诗也体现了人们对旧体诗的内容题材、形式、音韵和格律以及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改革和实践上的贡献,证明旧体诗,总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和继往开来的。”[2]3陈安湖也说:“其后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旧体诗词,这种古老的传统民族形式,在怀安诗社诗人们的手中,经过了改革创新,焕发了新的生机。”[10]他们的评价,可谓中允中肯。
自晚清以来,旧体诗改革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新世界”诗首取佳绩,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到南社的“歌体诗”、到学衡派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到胡怀琛的“新派诗”、到易君左等人的“新民族诗”、再到怀安诗社的“旧瓶装新酒”等,他们一直致力于旧体诗的现代探索,期望以旧体诗的形式,传达出新时代的内容。事实表明,这些旧体诗并不是僵死无用的艺术形式,而是艺术、思想俱佳,能够反映现实、作用现实的“通今适变”的艺术样式。因此,对于旧体诗我们依然有研究的意义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