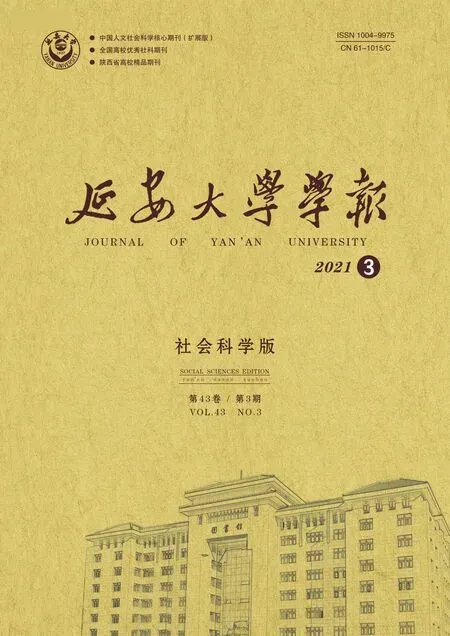“快闪”文艺实践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建构
——以“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题材系列活动为例
王 刚,肖 蕾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以央视2019年春节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爱国主义系列“快闪”活动共鸣于大江南北,在充分表达个性化主体审美意愿与价值诉求的同时,也负载了特定时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情感认同和文化建构的教化功能。大众文化的原生态、自发式探寻、怀旧意识,始终渗透在这一日常化的文艺实践转型进程中。而主流意识形态的融通、对话式建构姿态,更显示出国家审美治理趋向合流、导引、超越、提升的体系化探索。在“空间转向”愈来愈趋于“空间融合”、多元化审美趣味更加弥散的当下审美文化境域,新的大众文艺实践形式由无意识向有意识、浅表化向深层化的转型,深刻地标示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审美意识相融合、相激发的公共艺术生产机制的全新追求。
目前,针对“快闪”等广场艺术、城市空间行为艺术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传播学、亚文化层面的研究,热点在于形式感的关注,少见关于新型大众文艺实践的文化价值形态分析和审美文化阐释。特别是在“空间融合”的审美文化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意识开展大众日常实践分析,成果尚嫌不足,针对公共空间的群体性乐感文化形式的总体性研究还较为缺乏。
本文以爱国主义系列“快闪”为例,进行反思性研究。我们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日常生活化”更加明显,借助“快闪”大众形式的乐感化、仪式化、符号化、网络化制作与传播,既达到了大众文化的个性宣泄、群体启蒙和公共空间狂欢化的效果,又意象化、审美化、“复魅”地增强了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共鸣,因而成为一次意味深长的“泄导人情”的范例。
一、“空间融合”:系列“快闪”活动呈现的大众文艺实践新形态
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建设政策的放大效应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审美启蒙”的逐步兴起,“快闪”活动的频率与热度、参与度与认可度加大,专业性、团体性融合等显著增强,更趋于公共空间文化表征的“事件性”,在大众群体的艺术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新形式。2019年,以央视策划的“快闪: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为先导,经由各地政府与民间、各主导传媒与大众文艺团体的时尚化演进,“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快闪”风靡全国,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展,呈现出区别于以往“快闪”活动的新特点。
(一)具有鲜明的主题性和明确的宣传目的
“快闪”行为艺术,一般保留着大众情绪娱乐表达的嘻哈、搞笑、陌生化属性,以“发起者”的“邀约而趋同”的公共空间瞬时感的即兴歌舞,对组织化、纪律化、体制化的艺术修辞话语形成了悖反与冲击。不同于一般“快闪”艺术的追求无组织、游戏化、无目的、解构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气质,爱国题材大众“快闪”表演弘扬主旋律、抒发爱国情感,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系列“快闪”活动不仅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也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据笔者统计,从2019年春节之后各地开展的“快闪”活动,出现频率最高的歌曲是《我和我的祖国》《五星红旗》《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不管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地方的官方媒体,还是各地学校、党群组织等机构,在组织策划活动、呈现表演过程、传播引导舆论上都有鲜明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明确的宣传目标——即通过“快闪”活动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建构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使个体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参与意识审美凝结在“家国同怀”的艺术符号中,让“我和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意向性经由歌曲的情感表达而移情,外化为共同的“情感结构”形式,并形成巨大的心理感召和情感铺陈。一场“快闪”活动,在2—4首经典歌曲的联排、各种器乐和歌手的引领、现场群众的“代入感”中,形成十余分钟的集体性“瞬时共情状态”。同时,后期精心编辑、制作,经由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广泛传播的信息投放效应,则更加完整地用“短视频”等新型传播话语形成了持续性的话语修辞,扩大宣传,达到了“乐可以群”的效果。
(二)注重集体性感性经验的有序分配和建构
在常态表演中,“快闪”艺术形式更强调个性表现,以此激发现场观众的互动与融合,给人造成震惊情绪和狂欢化的审美效果。其背后隐含的,是一种个体对艺术文化公共空间场域自主性的吁求,也隐约地体现了多种审美趣味、多元文化空间相互交汇、相互融合、相互弥合的象征性。由于其参与者的非组织化,追求瞬间的“共时性”、表演时与日常生活状态的“跳脱(中断)-复归(还原)”感觉,因而更具有突如其来的感召效应,以及表演群体自身审美趣味的满足感。不同于国外闪客组成的松散性、无序性、随机性和匿名性,“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的参与者更加注重群体性、秩序感,活动人群身份上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与社会分工特征。歌手、运动员、科技工作者、清洁工、主持人、大学老师、学生等“身份角色”都是当下的主流人群。表演的地点选择、背景描述方面,更加强化时代感、象征性和公共趣味,在具有文旅融合双重特性、辨识度强的公共空间“符号”中,歌唱大家耳熟能详、相识度高的歌曲,让表演者“从日常生活状态中来”(特别注重“快闪”之前的群众幸福生活的“类状态”情绪铺陈)。以怀旧意味浓厚的旋律为导引,不同身份角色的共同“出场”,呈现“生命共同体(大我)”的息息相通与“小我”的瞬时匿名,本身就对应着“中国”这个能指符号所蕴含的不同群体的身份指认。系列“快闪”注重再分配、再生产的感性体验,打破个体的审美经验,强调集体化感性经验的有序和共通(而非芜杂和差异),“使它们重新集体地被分享,由此而使各种实践汇合形成全新的总体一致性。审美革命使共同体的集体感性配方整体地转变”。[1]12在共同体的集体感性域中,“将他们的个人经验表达为共同体的共同经验”。[1]13在此,中国化了的“快闪”契合了当下语境中审美-政治的全新价值指向,消除了艺术形式创造、接受、传播语境中的“审美区隔”,营造了全民同赏的新的感性文化氛围,体现了朗西埃所谓的艺术的“感性经验的有序分配”,“审美平等”激发了爱国主义经验的“集体共通”。
(三)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表达从形式到内涵上转型
系列“快闪”活动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突出地呈现为形式上的“顺应”(正向启蒙、喜闻乐见、大众感官娱乐)和情感内涵上的“泄导与引领(而非以往的教化与灌输)”上。一方面,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与大众文化和民众审美表达的多年共生、共随中,彼此间已经在相融、和合而非隔膜、拒斥,逐渐生成了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相通性、一致性。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生产部门和行业的路径选择与话语策略更加灵活有效,更加注重对大众审美文化的传播规律与生产、调控机制掌握运用,因而借用、化用大众文化群体的审美经验模式和话语形态来有意识、针对性地采取“喜闻乐见”策略,多用视听融合、智能互联、网络链接、多种艺术门类交汇等方式加速空间传播,辐射具有审美象征性和情感共通性的文艺符号,促进群体间的深度沟通与广泛认同。无论是爱国题材电影《战狼》《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还是主题晚会、大型广场艺术和情境表演等,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大众、复合审美、趣味融合等方式转型。这既是对当下文艺语境的适应,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自觉,体现着不同话语空间相互对话、“场域融合”的新趋势,其中蕴含着日渐深化的艺术人民性所主导的“审美启蒙与审美平等”。
二、“感性共通”:系列“快闪”新大众文艺实践建构着国家认同意识
爱国题材系列“快闪”艺术,作为一种“境域化的生成”“事件化”的文艺实践形式,其中,审美共通性是其表征“人民性”、[2]实现价值趋同和区隔消弭的根本。丹纳认为:“人在艺术上表现基本原因与基本规律的时候,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定义,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通人的感官与情感。”[3]“快闪”作为大众娱乐形式,决定了它所负载的理应更适合日常生活审美口味和精神取向,通过在“新时代里重新搅拌出共同体的新感性……制造出异感”,[1]9表达出全新的集体感性。
(一)表征层面:具体可感的内容在“陌生化”的形式中呈现
就情感表达而言,没有艺术审美体验的“人民性”厚重情感表达做基础,一“闪”而过的是喧闹;没有“代入感和共情化”大众审美符号的修饰,机械复制的是苍白。艺术的情感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感性共通”的最大化效应。系列“快闪”正是从日常生活的感性层面建构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感。作为一种艺术化、公共化、符号化的美学话语,《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融合了具体可感的内容和陌生化的形式,将人们日常意识中相对含混、多意的“国与家”的原型具象化、感性化,以此感发志气、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这其中,最具符号作用的经典爱国主义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曲目无疑具备了作为公共文化“最大公约数”的情感象征作用。歌曲将“我”和“祖国”相依相伴、水乳交融的关系作为表现的主题,把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具象化为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和感恩。“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将“国”的形象具体化为每个人心中的故乡山川风物。温情而优美的家园想象能调动人们的情感认同。一旦人们熟悉的爱国情感对接上“快闪”这种“陌生化”的表演形式,就会在瞬间激发强烈的共鸣效应。当《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以一种“出乎意料、猝不及防”的方式,在喧闹拥挤的机场和火车站、在轻松惬意的大型超市被资深的演奏家和顶级的乐队倾情演奏出来的时候,便直指个人情感,唤起人们感官对质朴音乐的分享和喜爱。震惊四顾,参与合唱和围观的民众都是一些和“我”类似的人,铁路工作人员、清洁工、老师、学生、普通的居民和旅客……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中,跨越性别、身份、民族、地域、贫富的平等发声、即兴合唱,在理性与激情的巨量凝聚与释放中升华为普天同庆、其乐融融的普遍情感认同。“人同此境,乐以和同”,这种普遍认同包含着国家富强文明和谐、民族伟大复兴给国人带来的荣耀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个体身心经验中的归乡意识、富足感和受到群体文化尊重的自信力,以及沉浸、融合在公共空间“偶合与相遇境界”的审美想象。境生于象外,乐在其中、流连忘返,通过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在相逢”的艺术感遇方式,含蓄蕴藉、余味曲包地为我们浮现了一个宏大壮美的国家形象。通过现场热烈的气氛、集体感性的快意抒发、美美与共,系列“快闪”活动生动而响亮地向人们传达了——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当年众望所归的历史选择,是最能代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共同家园。今天的中国正在人民当家、生活富美、明天更美好的前进征途中散发着无尽的诗意。于是,“我活故我美(叶秀山语)”、我歌故我在,“我和祖国一刻也不分离”的公共空间审美体验感,恰恰在陌生化的艺术话语表达中,成为每一位行人、观者意兴阑珊的当下认同。
正所谓“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语),在“快闪”相逢、空间共在的那一刻,每一个行者的脚步都停歇下来,在匆匆耽溺的现代性时空节奏中体会到了身体感官“慢下来”的舒缓、精神家园“被召唤”的丰盈。大众的“音乐性”情感得到了激发与组织,因为“音乐早已存在于人们身体当中,只是需要特殊的条件将其引发出来。由于音乐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增强人的意识来提高音响组织起来的人性,因此,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可以表达出文化和社会中的动力”。[4]同时,系列“快闪”艺术实践经由新型传媒技术和环境,强化了“二次传播”的话语修辞技术,把具有现场感的“闪演”震惊感与电视传播的剪辑技术“延时”效应、“意境化”处理等巧妙融合,形成了“慢速现代性”的视听体验的新奇感、复合性,从而为进一步激发大众点击、回放的重复身心体验提供了“视听景观”。经由新传播语境形塑、复现的爱国“快闪”活动,更加注重“情感意象”和“共情氛围”,加深了我们对“陌生化”形式的共鸣感。毕竟,“审美经验离不开我们在凝神专注和自我意识对立之间的摇摆。今天的慢速美学促使我们探索不同的感知模式……慢下来意图探索多样化的时空感知模式,而不以一种平滑、统一的实践形式将其遮蔽;它通达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不确定性领域,其中不仅充满惊奇,还包含着极乐、兴奋和狂喜”。[5]
(二)话语层面:宏大的“国家”话语化入大众日常生活经验
系列“快闪”既是公共空间的十余分钟精彩亮相的“爱国歌曲大家唱”,也是经过新型传播语境、高科技传媒手段和自媒体联合加工演绎的复合型艺术表演实践,其中的认同感包含着形式(随时可感的当下交流与传播方式)与内容(紧跟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体验),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空间美感的“意兴直寻”,每个人在“快闪”活动的现场或“视听景观”中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时间、空间、景观与人文的体验元素,很容易地“刷到存在感”。这也是“快闪”活动能够迅速打动非组织、流动化的社会公共群体的重要因素。
海南三沙的“快闪”活动,人们看到的是海鸥、渡轮、渔船、居民、水兵以及美不胜收的南海。永兴岛本是重要的海军基地,泊有大吨位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但“快闪”影像中都没有出现这些气势恢宏的国之重器,取而代之的是三沙市民真实的生活空间——绿水青山碧海蓝天。而四川成都的“快闪”活动甚至取消了乐团,歌曲部分全是围观居民们自发的热情合唱。成都的“快闪”活动影片里呈现的是成都人的富足放松的日常饮食娱乐(火锅、川剧、街头演艺等),连五星红旗都没有出现,实感地化国家认同于“成都人对安逸生活的热爱与确信”的地域文化体验中。活动后的采访环节,谈到对祖国的感受,人们则直接将这种情感对应上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深圳的一位受访者讲到他非常高兴今年买房了,接了家乡的父母来深圳过年。厦门的一个受访者则很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身上的衣服很好,是儿子给自己买的……这种对宏大的“国家”话语和政治符号的刻意回避,将“我”与“国”的关系具体化、感性化,让我们看到了“祖国”话语“能指”并非我们从小被灌输、早已“餍足”的红色理想,而是具体可感的、形象生动的你我他,是着墨于普通人(小人物)喜怒哀乐的当下“此在”姿态,是基于地域、民族、行业、身份、角色等的本位化、地方化了的日常生活审美经验,而这恰恰是共通可感的“文化自信”。种种聚合的文化符号在音画时尚的公共空间呈现中将普通人的个人生活与国家“叙事”连接起来,将普通人的生活梦想和国家的复兴理想连接起来。这种将宏大的“国家”话语化入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比兴、象喻”式表达,十分巧妙地“境生于象外”,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个人”话语在心里先验的优势地位和定向表达,瞬间造成了巨大的审美空场(空白点),在瞬间的移情效应中接受了“海是那浪的依托”(没有祖国哪有我)这一信念符号。
(三)意义层面:大众文化主体在审美“共同体”中得到了“价值重建”
当下,在“国家(民族共同体)想象”话语与形象建构的具体实践中,利用喜闻乐见的公共文艺形式建构新的国家形象认同,成为文艺实践需要面对的全新课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视域下“艺术-政治”或“审美革命”问题的重大现实指向。
系列爱国主义“快闪”无疑是一种大众文艺的实践形态,但是从新时代审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作为范例的特殊性在于复苏和重建了基于“共同体”情感经验的“审美新感性”。对于大众文化主体而言,一场“快闪”表演活动具有人性建设的美学意义。在“事件化”的公共空间境遇中,建构了具有生命超越性和价值皈依感的“情感本体”。被瞬间召唤、热情激燃的个体,从日常生活的“单向度”中实现了自我与群体的“价值重建”(如李泽厚所论,“价值重建”就是人性重建,而人性重建就是……使情感真正取得“自由的形式”的本体地位[6])。诚如赫勒在《日常生活》理论中揭示的,“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自己在直接共同体中的生存……日常生活人道化的任务正是培养自由自觉和总体性的个体”,“培养新的人道的日常生活主体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个体同‘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自觉关系”。[7]赫勒所谓的“日常生活的人道化”,与李泽厚对当代美学的人性建设的吁请,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建设性路径而言。社会学家曼海姆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新的意义上重新发现情感的重要性,更多地强调对那些最终整合诸群体的基本问题的鉴别,那些作为共同体历史生活之产物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旨在合理地进行社会重建的新理想。”[8]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下,这种基于中华民族“情感本体”的日常生活“价值重建”(人性建设),无疑具有着重要而切实的现实意义。作为建设性(而非一味地批判认知)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应该充分肯定并大力倡导、孕育和建设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又能提升人民群众审美新感性的文艺形态。
三、“泄导人情”:新大众文艺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合流”
文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它所包含的结构和内容是一组丰富的文本,而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呈现哪些符号(内容)、如何呈现(形式),则是这种话语和文本能否实现其诉求的关键性知识选择。通过对系列“快闪”活动的形式内容和话语层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国家”话语在审美感性层面对受众的感情认同的建构模式,以及激发公众由自发到自觉的情感认同的内在审美机制。“选择本身就意味着立场、归属或倾向性,它都与时代的政治导向和行为相辅相成。”[9]系列“快闪”活动中,作为一种新的大众公共文艺实践形式的“合流”效应更加明显,原生自发型渐渐让位于自觉引领型,其对活动空间的选择、音乐的编排、乐器的安排、参与者的身份甚至服饰、视觉影像的制作和传播,每个环节都是服务于主流话语建构、体现组织性特点。
我们看到,北京和深圳的“快闪”活动,选择了人流密集的交通集散地——北京机场和深圳北站。这二者恰恰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两个空间象征。政治中心北京象征了新中国现代性追求在政治上建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作为改革开放门户的深圳则象征了现代性追求中国民享有充分的个人生存发展权利和发展机遇的成就。北京和深圳,作为国际大都会,都选择了交通中枢——机场和高铁站,这种选择极具象征意味。机场和车站都是人们“出发”和“归来”的起点和终点。北京机场、深圳北站象征了中国对世界大门的打开。北京机场的建筑材料是现代化的混凝土、钢筋和透明玻璃,从室内可以直接看到建筑的轮廓和框架。透过玻璃,阳光可以直接进入宽敞的建筑内部。而坚实的混凝土和钢筋材料支撑起整个玻璃的外墙和天花板。玻璃的使用让自然光最大限度地进入,使得室内空间无遮蔽地、透明地呈现于阳光中,消除了室内幽闭、晦暗的空间。室内装潢上也没有刻意为之的“中国民族形式”,而是简洁的现代国际风格。这样一个开阔、敞亮、透明的建筑“身体”,不像传统的中国建筑内部注重空间的分割、掩蔽,给人以神秘化和威严感甚至压抑感。北京机场的建筑空间给人的空间感觉——透明、敞亮、开阔,“以小见大”地隐喻了主导意识形态意欲建构开放、包容、中正、平和的大国形象。此外,在北京的“快闪”地点选择上,避开了天安门、故宫、长城等深入人心的北京地标。这样做一方面回避了人们对其政治“能指”的惯性冷漠,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西方人心中的古老、陈腐、神秘的“他者化”的中国形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我们不再被“他律”的眼光所宰制(以往宏大话语叙事中认同感和自豪感主要建基在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而是自律地、自主地认同我们今天的国家形象时,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
从西安、厦门、成都、乳源、长沙、三沙的“快闪”中,可以更多地看到各地的民俗特色和地方日常生活元素。这是国家内部不同的文化主体参与建构国家形象的表现——多元化的主体带来了国家形象的多元化色彩,激发着一种囿于民族内部的审美共通感、一种中国人才有的“中国经验”。透过它,受众得以对自己所处的“日用而不知”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经验产生强烈认同,进而对孕育多彩文化的祖国“母亲”产生深深地内在皈依情感。但是,这种缺少“他者”的认同形式,如果失去一种更高维度的、更具包容性的“崇高”形象来支撑,在现代性多元价值和技术理性的集约化冲击下,很容易陷入“不可持续性生成”的话语修辞危机。北京和深圳恰恰为此打了“补丁”,兴发于此的“快闪”活动中表现的正是一种“全球”维度的国家形象。如果说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更多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后两者,则为这种“自我认同”指明了必要的“他者”——世界(其他国家)。黑格尔认为“他者”的显现对构成“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他者之存在使得主体意识得以确立。当下,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西文化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完成文化自觉。那么这种“交往理性”必得建立在“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重建主体性中国的形象”[10]的过程中去。也正是在这种“自我—他者”的对抗型的认同形式中,“国家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地位、效应才能再次得到凸显。“地方化”的独特审美经验各美其美,但是我们都需要“美美与共”,认同“想象共同体”的母体——更加强大从容的中国。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多元的主体认同融入强大的国家认同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占据话语强势的西方平等对话。这样的审美化、象征性认知,其价值意义、文化分量和实践理性,更具有内在的情感支撑性,值得倡导与弘扬。
由此看来,具有鲜明“中国韵味”的系列“快闪”活动无疑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以载道、泄导人情的“共谋与合流”。让我们在国家认同、民族自信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构话语方式转变的融通与接纳。然而,主流审美与大众审美的遇合与共通,究竟是回眸瞬间一次美丽的邂逅、还是心灵记忆中期待已久的相逢?怎样让公共艺术传播与载道的“耦合”效应不成为“偶合”?在感奋、激动之余,我们也要从系列“快闪”活动的“合流”中看到:艺术自发生产的内在动力、原生智慧、个体感性、特异风格,存在着被重新编码、规训、集成为模式化的“独白艺术话语”的可能误区与现实苗头,对于感性化的公共审美经验,如何“以道制欲、以理融情”,使其在不失去审美意趣和个性风格的前提下实现理性凝聚和价值升华?这是保持“快闪”等群体性公共艺术实践的生命力,并进而以此增进审美认同和趣味共通的现实问题。
同样,我们认为,观照和阐释以爱国“快闪”为表征的大众文艺实践新形式,既是因为它作为公共文化和艺术实践的“事件化”呈现方式,越来越由“自动化”趋向“陌生化”,顺应了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共有经验,并采取了“语境杂糅”的策略,经历了从个体无意识娱乐到群体精心策划组织、从多元化审美愉悦到主题化的政治表达、从浅层的情绪感染到深层的精神情感认同的结构转型,成了真正值得我们审美观照和文化阐释的大众文化的“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由于,它也深刻地意味着中国大众文化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结构转型与价值共通”。在这个快速转型过程中渗透和彰显的,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乐感文化的大众审美意识生产机制对建构新时代国家形象价值认同的体系化探索。其中所蕴含的当代中国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全新诉求和科技工具理性垄断所共同激发的“审美新感性”的公共经验,需要各方面充分珍视和持续开掘,特别是基于爱国主义情感的群体性、时代性、地方性的“审美新感性”,对于我们建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十分可贵。同时,在大众文化审美生产机制方面,“快闪”等公共艺术实践中“原生趋向合流”的审美认同模式化、类型化,也会加速新型公共空间艺术实践形式感的“重新自动化”。一旦缺少了特定历史节点和国家仪式感的背景与支撑作用,带有新的宏大叙事和审美规训力量的形象和话语共通模式,是否还能持久地激活蕴含在个体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与情感能量”?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近两年来唱响大江南北、激荡全国各地的系列“快闪”活动,不仅在客观上“境域化”地生成了一种“空间融合”进程的群众性文艺欣赏趣味,也从主体精神层面倡导着基于公共文艺符号和共契审美情感的价值判断。爱国“快闪”因“节庆、团拜”而兴发,但是蔚然于“怀旧、感奋之共情”。溯其源,作为一种“兴辞”话语,爱国“快闪”呈现了新时代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人民性。这一镌刻在政党叙事、国家复兴、民族富强辉煌记忆的公共文化景观中,主流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要将民众的日常经验、大众体验浓缩、凝结成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记忆,基于怀旧、崇高、反思等复杂情感结构的“共时”效应,以此来升华群体体验,导引建立公共空间的国家认同感,助力更明晰的政治话语建构和更宏大的文化精神形塑。用阿斯曼的话说:“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11]系列“快闪”通过感性、集成的方式建构了开放、包容、大气、奋进的国家形象的话语能指,并通过大众艺术实践的时尚化潮流,将这种共情氛围、认同建构“仪式化”,使其逐渐成为行之有效的文艺实践的“地方知识”。这样的审美文化知识建构路径,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形态的积极顺应,也是多元文化意识自我确证、自为合流的现实路径,更是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在“空间融合”进程中日趋审美化、区隔消弭与价值重构的重要表征与知识路径。
“合流是路径,关键在疏通”。在全球“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自我认同意识加剧的当下,文化认同的“地方知识”建构更显示出紧迫性,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对内提高人们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对外彰显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的阶层弥合、文化融通和审美共享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新时代的公共文化精神中,更需要不断地借助于艺术想象来实现公众的和谐交往和社会的感性建构。群众基于共同生活经验的自发性和实践感,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生产的源泉,而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对话、主动顺应、引导形塑大众审美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路径依然深远而漫长,需要不断地观照、反思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