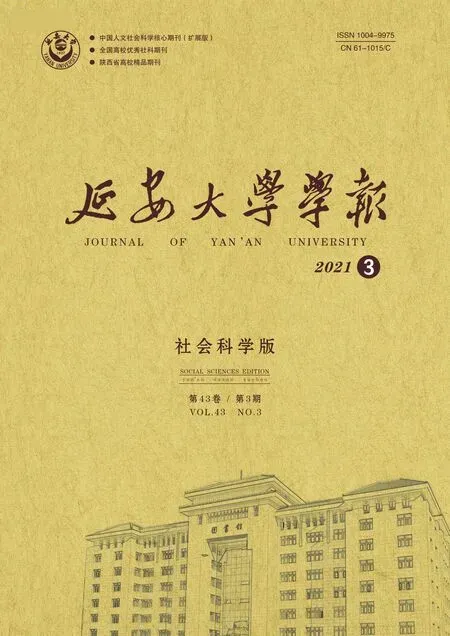《人生》中“红头巾”“红盖头”象征符号解析
孔 岩,朱文丽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路遥站在城市与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断裂带上苦苦追寻年轻一代的出路与归宿,他的许多作品都重复着“出走——追寻——回归”的模式,呈现出年轻人由乡土文化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与追寻无果的心路历程。在《人生》中高加林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戴红头巾的“女神”像,这也正是路遥心目中那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路遥的创作深受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路遥在回答《延河》编辑部提问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尤其喜欢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1]“红头巾”“小白杨”等象征符号的使用能看出路遥对艾特玛托夫《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有意借鉴。但在《人生》中,路遥不仅赋予“红头巾”更为复杂的内涵,还借用“红盖头”这个代表传统文化的符号显示高加林精神逃离的迫切与现实突围的艰难。
目前对“红头巾”“红盖头”象征意义的挖掘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只有李解在论文《此岸的彷徨与彼岸的梦碎——路遥<人生>中“桥”的意象解析》中简单提到“红头巾”是“高加林对于理想恋人的深层心理渴望和窥探”。[2]刘素贞在《“时间交叉点”与两种“结局”的可能——再论路遥对〈人生〉中“高加林难题”的回应》一文提到巧珍蒙上“红盖头”是对“乡村共同体的一种拥护”。[3]本文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结合艾特玛托夫对路遥创作的影响,揭示“红头巾”与“红盖头”两个象征符号所代表的深层含义,更深入地解读高加林的心理困惑与文化选择。
一、“红头巾”“红盖头”的符号意义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Symbol兼具“象征”与“符号”两种含义。虽常有关于“符号”与“象征”两者区别的辩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两者的含义在很多时候是等同的,符号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象征是需要符号指称的象征。象征符号与其他符号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是它有着自身的规约性。在发展过程中,许多象征符号被人为构建以体现人的主体意识、承载社会文化观念,象征符号的意义也不断衍生。
“红盖头”是我国传统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物件,其基于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未婚女子通常不见外人,红盖头的作用就是在出娘家入婆家的路上保护女子不被外人看到,后来衍生出趋吉避凶、新旧身份转换的意义,往往是新娘出嫁时的必要物件,也是女子进入婚姻关系的标志性符号。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及改革开放的潮流,出现了结婚穿西装、穿婚纱的新风尚,“红盖头”这一符号则用来指代传统婚俗,进而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有戴头巾的习俗,头巾也有保护头部的实用功能和装扮的审美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20世纪20年代,一批下南洋的广东三水籍的华人妇女被称为三水“红头巾”,“红头巾”的称呼虽源于她们习惯头裹红头巾,但后来“红头巾”一词逐渐成为“努力追求新生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女性的一种象征符号”。[4]后被引申为一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现代精神。“红头巾”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红盖头”的定义,具有开放、现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
“红头巾”和“红盖头”在社会文化的规约下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一种心理符号,以这种特殊的象征符号来表现人类特有的文化积淀与心理经验。其指称的意义也会随着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转变而不断扩大。“红头巾”多用来指称现代文明的相关理念,“红盖头”多用来指代传统的乡土民俗。
二、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符号的“红头巾”
符号与意义紧紧相扣,任何符号都是“意义”的凝聚,也是“意义”的呈现。“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5]《人生》中的“红盖头”和“红头巾”正是透过符号的表层意义赋予其更加复杂深广的象征意义,用来传递与“红盖头”“红头巾”相似的观念或者寄托更为隐秘的心理,承载小说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思。
路遥在《人生》中曾两次写到“红头巾”,第一次是“见巧珍情牵心中画”。高加林和刘巧珍刚开始接触时,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高加林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是他看过一张类似的油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6]48第二次是“至精诚稿费换头巾”。巧珍来城里探望高加林,此时的高加林明显感觉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巧珍亲热了。但善良的巧珍依旧对他嘘寒问暖,高加林忍不住鼻子一酸,纯粹的爱情暂时化解了高加林内心的躁动。在送巧珍离开的时候:“他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6]125“高加林一直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头上。”[6]125
在《人生》的电影中,路遥作为编剧也刻意保留了“红头巾”这个细节:高加林十分温情地为巧珍戴上红头巾,两人深情凝视,心情略显沉重。这成了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并在后来的诸多当代小说恋爱叙事中得到延续。路遥对“红头巾”的钟情刻画并不止于《人生》,他在《平凡的世界》中也特意安排了“红头巾”。在《平凡的世界》结尾处,孙少平面部被毁,他拒绝了金秀的深情告白,也放弃了去大城市里工作的机会,再次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在黑油油的煤堆中路遥安排迎接孙少平的是“头上包着红头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7]显然,包着红头巾的女性对男主人公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路遥作为一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力求客观描写现实,然而却让“红头巾”“小白杨”这样的象征符号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全然不避重复之嫌。显然“红头巾”“小白杨”“红盖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人物描写手段,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表达人物的隐秘心理与作者的内心倾向。那么为何路遥会如此钟情于这类象征符号?
回溯路遥的阅读史和创作史,可发现其审美心理深受苏联文学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写于1962年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描写了司机伊利亚斯和美丽善良的阿谢丽之间的爱情故事。“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是伊利亚斯对阿谢丽的爱称,也是阿谢丽在伊利亚斯眼中呈现出的永恒形象。在小说一开始伊利亚斯对阿谢丽一见钟情:“我赶快从车底下爬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窈窕的姑娘,严厉地皱着眉头,头上包着红头巾。”[8]81一见钟情后,两人大胆冲破现实的束缚,伊利亚斯在伊塞克湖边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爱的誓言:“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我永远不让你受到任何人的欺侮。”[8]103然而好景不长,伊利亚斯因自己工作失误,在失意时又受到卡基佳的引诱,最后背叛了阿谢丽。在故事的结尾处,伊利亚斯痛苦地喊道:“别了,阿谢丽!别了,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8]209“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贯穿整部小说。
艾特玛托夫通过“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来表达自己对女性的审美态度,在他的爱情叙事里,完美的女性是一定要具有“小白杨”一般苗条修长的身材和坚韧不拔的品格。而“红头巾”则是对其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和完善,来凸显女性的柔美热情、勇敢独立的现代文明气质。这部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大放异彩,“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这一经典形象也深入人心。“红头巾”不仅象征着阿谢丽的纯洁美好,还成功地建构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女性以及对爱情的一种浪漫的审美想象。也正是如此,其深深地影响了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气质的路遥,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方式上,还影响了路遥的审美心理和精神特质。
路遥在《人生》中塑造了有着白杨树般的身材、红头巾般的热情,还有着金子般的心的巧珍形象。他用“红头巾”赋予了巧珍一个不真实的艺术形象,多次将理想配偶的幻想附加到她的身上。巧珍既是高加林回归乡土的心灵安慰,又是他不安于乡土的遗憾,所以具有“小白杨”特质的巧珍与高加林心目中的“女神”始终有着一条象征现代文明气息的“红头巾”的差距,于是高加林为刘巧珍买红头巾、戴红头巾,试图改造刘巧珍,赋予了“红头巾”丰富的象征意义。
首先,“红头巾”是现代文明与理想的象征。没戴“红头巾”的刘巧珍缺少现代文明浪漫气息,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改造更凸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追求。而且由于路遥当时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使用“红头巾”也一定程度表明他想打破“蓝、灰、黑”的压抑局面,向往开放文明的社会环境。卡西尔明确指出:“象征符号是指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揭示出意义的一种过程。”[9]“红头巾”这一象征符号的意义正是通过高加林心中想象戴红头巾的“画中女神”与给巧珍戴上红头巾成为“心中女神”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高加林既对巧珍美丽外貌、美好心灵、质朴品质表现出接受与肯定,但对她身上所带有的乡土气息又隐隐地不满,透露出他对巧珍未完全达到自己心目中女神形象的遗憾。通过“红头巾”对理想伴侣再创造,可看出高加林对乡土文化眷念,又对现代文明渴慕的深层矛盾心理,也可以看出路遥对艾特玛托夫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创造性转换,对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思考与别样呈现。
“红色”象征着热情浪漫、开放文明,“鲜红”也象征着牺牲。刘巧珍在高加林人生失意时用“小白杨”般的美丽和善良感动了高加林,但巧珍并不是高加林心目中的理想恋人,对“红头巾”的执念才是高加林内心最真实的追求。但在现实打击面前,乡村里的“人梢子”巧珍的爱慕犹如挂在这个失意青年胸前的“勋章”弥足珍贵,使高加林暂时获得了价值肯定与精神支撑。“红头巾”正是高加林对刘巧珍理想化的艺术想象,也是一种带有明显“移情”的审美欣赏。
其次,“红头巾”还象征着女性的牺牲。在《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建立在纯粹的感情之上,后来情感的破灭是男主人公的背叛所致。但女主人公阿谢丽时刻给予了恋人大地母亲般的关怀与宽容,在得知恋人背叛后她选择静静离开。再看《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从第一次在回家路上萌发爱意到最后在大马河桥上痛苦离去,其间的爱情曲折十分相似,富有牺牲精神的巧珍用“红盖头”出嫁自己而成就高加林。路遥对转折性的事件作了创造性的置换,将个人感情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伊利亚斯因工作失意背叛谢阿丽,而高加林是为了逃离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落后农村,去追寻城市现代文明而舍弃巧珍。路遥将高加林置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了“红头巾”以及整个故事时代性、民族性以及地域性的内涵。虽然众多研究者包括路遥都无法评判高加林的选择正确与否,他到底该何去何从,但毋庸置疑的是艾特玛托夫和路遥都高度赞赏拥有大地母亲般包容和牺牲精神的女性。
最后,“红头巾”也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审美心理。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小白杨是包着红头巾的,红头巾是小白杨的一种外在特征,两者完美地显示了“优美”与“壮美”两种审美风格的结合。从艾特玛托夫笔下长满白杨树的广袤群山和大草原下出现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阿谢丽到路遥笔下厚重的黄土地上有着小白杨的身姿和坚韧不拔品质的刘巧珍,可以看出路遥的审美机制受到了艾特玛托夫的影响,使其在严肃的现实主义叙述中增加了一笔浪漫色彩。但由于现实的局限,黄土地上的“小白杨”暂时还无法真正戴上富有现代文明气息的“红头巾”,最终不得不转向有着乡土文化气息的“红盖头”。由此也能够看出路遥的创作立足于陕北大地,有着关于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的独特理解,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进行了更为真实地呈现。
象征符号既是人类精神的需要,也是人类主体状态的投射和创造。在《人生》中的“红头巾”这个象征符号,既是高加林对乡村姑娘刘巧珍的一种艺术想象,也可以看作是高加林对理想恋人的深层心理的显露,同时也是他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理想追求。可以说对“红头巾”的渴望是现代文明与高加林精神追求之间的一个媒介,映射出高加林在追求现代文明时的精神状态和深层次的心理活动。
三、作为乡土文化象征符号的“红盖头”
传统的乡土空间是在现代文明笼罩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当面对精神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移到乡土民俗上。从“红头巾”到“红盖头”是理想的破灭,是出走的回归,是乡土的疗愈。但路遥并不是一味地推崇乡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一种情感的守望,一种暂时的选择。
巧珍一开始被动地接受了高加林对自己的改变,但后来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时的巧珍选择了马拴,要求用最传统的习俗举行婚礼。父亲刘立本都觉得有些惊讶和为难,主动找高明楼商量。从两人的反应来看,旧式的乡俗在当时已经很少见了。为什么路遥要这样安排?目前这一问题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的看法都认为这是巧珍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无奈与妥协,暗含了女性的困境。
黄平认为,“被严重伤害的巧珍,退回到乡村共同体的深处以求得庇护与安慰,要求婚礼完全采用旧式风俗”,[10]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厚夫在2015年撰写的《路遥传》里提及了这一细节:“在细节处理上路遥特别认真,他写到巧珍要出嫁的那一章时,专门找了几位甘泉县里的老人采访,这章前前后后反复了好几回。”[11]这个描写别有深意,巧珍在路遥的笔下可以说是德貌双馨,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所以巧珍嫁给马拴并非是赌气。路遥在高加林追寻现代文明失败,回归乡土时安排了这场极具乡土气息的婚礼,并非是为了凸显刘巧珍身上某种女性的妥协性,以此来指涉女性的困境,而是从“红头巾”到“红盖头”的呼应,呈现理想与现实的撕裂,暗含了巧珍的“红盖头”的选择也是高加林对乡土的选择,这也正是路遥的一种心理精神倾向:城乡二元对立状态下对乡土文明的眷恋。
巧珍出嫁时,她的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红丝绸,这是传统婚礼中必不可少的“红盖头”。巧珍放弃了高加林给她的象征现代文明气息的“红头巾”,主动戴上了象征传统文化的“红盖头”。作为乡土伦理的象征符号,它不仅有字面的意指作用,还有情感、记忆和想象等意义,甚至在卡西尔哲学中,象征和文化是一体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会渗透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乡土民俗来渗透在个体的心理情感上。这里巧珍戴上的“红盖头”正是以巧珍所代表的乡土文明向高加林所追寻的现代文明进行的一种告别,也是这种群体规定性成为个体深层次心理需求的一种体现。巧珍由一开始被动接受“红头巾”到主动戴上“红盖头”的过程,也是巧珍开始审视自我处境与出路的一个过程,她在认清现实状况后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以身体的出嫁,让自己精神找到了最后的皈依:传统的乡土文明。
高加林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一开始对现代文明有着很多美好的想象。他也始终以一个现代青年的眼光来审视乡土文明、传统习俗,甚至自己的理想伴侣。他用饱含现代艺术想象的“红头巾”来改造农村姑娘刘巧珍,也用“三接头皮鞋”来包装自己。马占胜的“帮助”、景若虹的认可、张克南的仁义都无法让高加林顺利融入现代文明,个人的理想与抱负也无法挑战体制的严整。张克南母亲的一封举报信就匆匆结束了高加林的现代文明追寻之路,高加林不得不再次回到高家村,但这时自己昔日改造失败的伴侣已蒙上了“红盖头”。
从“红头巾”到“红盖头”,从“三接头皮鞋”到“布鞋”,正是体现了路遥对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非此即彼”选择的冲突。此时的路遥由现代文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利用乡土文明所存有的温情对出走失败者进行一种心灵救赎,这并非路遥想利用传统文化或者道德情感来解决城乡之间的冲突,而是此时的路遥还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的哲学判断和找到真正的解决之策。高加林重归故土后又该如何?路遥曾明确表示:“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12]
“红头巾”和“红盖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农村;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现代文明,一个是传统民俗;一个是追求,一个是回归;一个承载了接受文明洗礼的年轻人对现代文明的艺术想象,一个寄寓了从黄土地走出却无法割舍乡土文化的青年对乡土文明的眷恋。两种符号的不相融,也是路遥对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两难取舍的一种表征。
通过“红头巾”和“红盖头”这两个象征符号,可以看到现代文明与乡土经验之间、远方之子与农民之子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这是几代人共通的经验与感受,这种感受与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也屡见不鲜。但是在路遥这里,矛盾但不分裂,痛苦但不绝望,黄土地依旧是让人灵魂得以栖息的净土。所以此时的路遥选择肯定传统道德中的合理成分,在对乡土文明的深情守望中思考出路。
由艾特玛托夫《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红头巾”到《人生》中的“红头巾”,不仅可以看到路遥对其有意借鉴,更看到了路遥的创造性发展。由戴上“红头巾”到戴上“红盖头”,是高加林改造刘巧珍的失败,也是他追寻城市文明的失败,“红头巾”与“红盖头”无法在刘巧珍身上融合,高加林也面临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难以融合。高加林最终只能由“红头巾”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理想空间又退回到“红盖头”所指称的最原初的乡土现实空间。“红盖头”的凝望是暂时的,“红头巾”的理想才是更执着的。
这样的两难困境一直伴随着写作前期的路遥和《人生》中的高加林,直到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才走出了《人生》中非此即彼的困境,《人生》中两种文明冲突在《平凡的世界》里开始走向缓和。孙少平和孙少安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加林的一种分化:孙少平是走向城市拥抱现代文明的高加林,孙少安是回归黄土地守护乡土文明的高加林。但是两者身上都实现了乡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融合:孙少安在守护乡土文明的同时,敢闯敢干,为双水村迎来了象征现代文明的造砖机器;孙少平在乡土文明美好精神品质的支撑下,勇敢地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闯荡。并且在《平凡的世界》中再次安排戴着“红头巾”的惠英嫂的出现,也进一步表明路遥对“红头巾”的理想化想象一直在延续,也充分体现了路遥始终具有基于现实的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