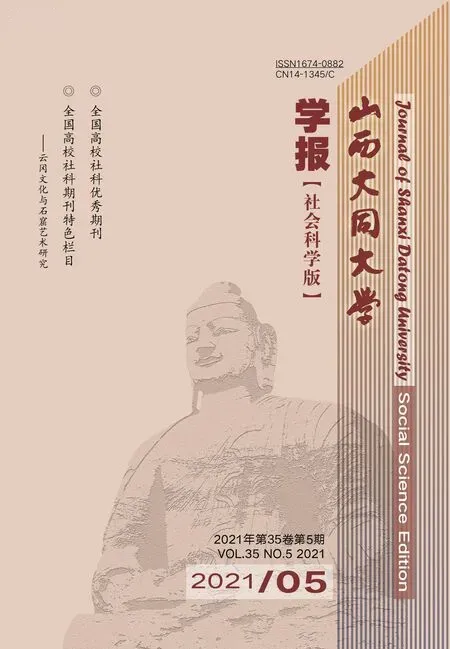北魏比丘尼墓志中女性形象的书写策略
王婧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兴盛为六朝女性提供了全新的社会活动空间,也令比丘尼这一新的女性群体走入历史视线。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兴盛之状从僧寺数目可见一斑。这一王朝虽经历了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之难,但此事并未真正影响佛教的迅速发展,至孝静帝时,已达“僧尼二百万人,寺三万所”[1](第49册,P465)的繁盛之况。在北魏一朝,诸多皇后、太后及公主出家,佛门与宫廷之间产生了分外紧密的关联。而正史及其他史料对这些后宫出家女性及当时其他比丘尼的记载相对较少,流传下来的由她们书写的文字作品也相对贫乏,因此出土的若干篇北魏比丘尼墓志便显得尤为珍贵。它们或由墓主人的比丘尼弟子书写,或由文人执笔,由此可以对北魏时期的比丘尼形象及女性的文学书写有更多认识。
《文章辨体序说·墓志》云:“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2](P52)墓志本是墓地的标识物,以防陵谷改迁。广义上的墓志包含了埋在地下的墓志铭和立于地面的墓表文,属碑文的一种,多记叙死者的家世及生平等,行文有简易与复杂之分。从北朝墓志的具体名目来看,称墓铭、墓志、墓记、墓表的情况皆有,北魏时期的比丘尼墓志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创作主体独特的书写策略。
一、比丘尼墓志中的形象虚构
综观北魏时期的比丘尼墓志,其行文和结构已较为定型,散韵结合,多记叙墓主人家世、生平并赞其功德,具有一定的文采。诚然,要想做到对个体客观而准确的描述是十分不易的,就墓志对个体的描摹来看,比丘尼墓志的书写中存在着形象虚构的现象。这一现象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文学层面的虚构。
《文心雕龙·诔碑》云:“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忒。”[3](P115)首先,刘勰将立碑叙述死者的文章和诔文归为一类,他认为碑文和诔文的作用在于叙述具体的行事和追写抽象的道德。如此,人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书写对象的影像及风采。这就说明了对墓主人的描摹势必包含虚、实两个方面。书写者往往不吝笔墨来颂扬墓主人的才华与品德。如,《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云:“禀三才之正气,含七政之淑灵,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4](P20)僧芝尼的墓志由弟子僧和、道和两位比丘尼撰写,她们用比拟及夸张的手法表达对师父的钦佩与敬仰。故而在涉及僧芝尼才能及品德的描绘方面,“追虚”是其显著的特色。又如:“法师雅韵一敷,慕义者如云;妙音蹔唱,归道者如林。故能声动河渭,德被岐梁者矣。”[4](P20)寥寥数语,便将僧芝法师的才德表达得淋漓尽致,宛在目前。再如:“皇上登极,皇太后临朝,尊亲之属既隆,名义之敬踰重,而法师谦虚在己,千仞不测其高,容养为心,万顷无拟其广。”[4](P20)据史书记载,“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5](P338)僧芝尼即是宣武灵皇后胡氏的姑姑,灵皇后胡氏后来被肃宗尊为太后。僧芝可谓皇亲国戚,与皇家有密切的联系,地位殊荣,但能做到谦虚而有涵养,可见其令人敬佩的修为与德行。其弟子又称其“道冠宇宙,德兼造物”,[4](P20)无一不是在用夸张的文学手法来树立其光辉的形象。另外,在表达其对逝者的哀痛之心时,又云“山水为之改色,阳春触草而不荣”[4](P20),达到了刘勰所说的“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效果。
此外,由北魏名家常景书写的《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亦用比拟的手法描摹墓主人的外在风姿与内在品行:“于昭淑敏,寔粹光仪,如云出岫,若月临池。”[6](P23)另一文人所书写的《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并序》同样用比拟与夸张的笔触来描摹女性的风姿与神韵:“蟠根玉岫,擢质琼林,姿色端华,风神柔婉,岐嶷发自龆年,窈窕传于丱日。”[6](P298)在文末的韵文,即铭文部分更是用多种手法生动展现了书写对象的德行与风采,并用拟人手法来叙写哀情:
以上所列举的“追虚”特色是从文学层面而言的,也是人物描绘的必然现象。《文心雕龙·夸饰》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3](P332)毕竟,人物的声貌及道德都是难以用语言精确描绘的,而文学性的虚构反而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读者不仅能从这种“夸饰”中感受到描写对象的人格魅力,亦能体会到书写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及素养。
除了文学层面的虚构,北魏比丘尼的墓志中还存在着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虚构。在社会环境影响下,书写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许多重要事实,所建构的人物形象与史料中的记载相比有较大出入,使人由此而怀疑其形象建构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在《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的书写中表现较为突出。
墓志中记载:“尼讳英,姓高氏,勃海条人也。文照皇帝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7](P44)慈义尼在出家前曾是世宗宣武帝的皇后,据正史记载,这个皇后有妒忌的特点:“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5](P336)因高皇后嫉妒的特点,后宫很少有人能亲近皇帝。正史中又记载:“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5](P337)因高后悍忌,所以直到皇帝去世,后宫还有从未被皇帝宠幸的妃嫔,因而世宗宣武帝也仅有肃宗一位皇子得以保全,高皇后的专宠跋扈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前皇后之死似乎也与其有关。史书中记载:
宣武顺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世宗始亲政事,烈时为领军,总心膂之任,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谒于太庙。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岁夭殁。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5](P336)
于氏是世宗宣武帝的第一任皇后,具备“静默宽容,性不妒忌”的贤良淑德形象,且生下皇子。但其皇子三岁时便夭折,于皇后本人也在不久去世,世人认为他们都被高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高皇后所害,虽然后世无法知晓此事的详细经过,但历史上对高皇后的记叙和评价却着实是负面的。肃宗即位后不久,尊高皇后为皇太后,尊其生母胡氏为皇太妃,后又尊为皇太后。然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第二个月就去了瑶光寺出家。史书记载:“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为尼。”[5](P221)高太后出家之后,人身自由遭到限制,没有重大节日不能随意入宫,其女儿建德公主也被灵太后夺来抚养。神龟元年,最终被灵太后迫害致死,以尼礼下葬,足见宫廷斗争之惨烈。
肃宗孝明帝于公元516年即位,高太后在其即位后不久出家,于神龟元年即公元518年去世。由此推算,其出家修行的时间应不满三年,且显然是被迫出家。佛门生活的时间如此之短,很难令人相信其有多么高深的佛学素养或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高太后毕生都见证了宫廷斗争的复杂与残酷,深陷宫廷斗争的泥潭,甚至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弟子法王为其书写的墓志,依然以“贤”、“哲”、“善”为其形象的关键词,且希望其“芳猷”(美德)永远流传,为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与正史记载反差极大的超尘拔俗之形象。《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云:
2014年宇舶推出最贵重和密度最高的锇金属晶体表盘的腕表。锇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俄罗斯和南非。约10,000吨铂矿石中含约28克锇,据估计,全球约有200吨锇储量。相较于贵金属的铂(全球约有13,000吨铂储量)更为稀有。作为地球上最稀有的金属,锇质地坚硬,22.6克每立方厘米的密度使其成为自然界密度最大同时也是最重的金属(重于铂,铱,铼等)。
其辞曰:三空杳眇,四果攸绵,得门其几,惟哲惟贤。猗与上善,独悟斯缘,出尘解累,业道西禅。方穷福养,永保遐年,如何弗寿,祸降上天。……式铭慈(兹)石,芳猷有传。[7](P44)
这种虚构属于认识评价层面,是个人一种社会心理的反映。其弟子未必不知道慈义尼出家前的经历和遭遇,但这样的书写或许是因对皇权的尊崇和依附而有意美化,也或许是出于师徒之间的真实情分。
另外,《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也存在这一现象,上文已经分析过书写者用文学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位“道冠宇宙,德兼造物”的高尼形象,才德堪称完美,但对比正史中的记载,僧芝法师未必有墓志中所书写的那般超脱和完美,或有虚构的成分。史书记载:“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5](P337)僧芝即是灵太后的姑姑,在灵太后当年还未入宫前,其姑僧芝尼已经在为世宗皇帝及后宫宣讲佛法。僧芝暗示左右称赞其侄女胡氏的容貌与品德,遂引起了世宗的注意并将胡氏纳入后宫,最终生育肃宗而成为后来的灵太后。可见,灵太后的荣宠与其姑姑的助力密不可分,而僧芝正是有意令其侄女吸引皇帝的目光,终获富贵荣华。这样的形象到底难与其墓志中的书写完全匹配,而这两篇墓志均由其弟子书写,此种虚构也许是出于师徒间的真挚情感,或许她们书写的形象更多是基于个人情感塑造的结果,但也不排除有意美化的因素。
总的看来,对北魏比丘尼墓志中女性形象的书写,既有文学性质的虚构,又有社会心理化的虚构。而在文学层面的虚构中,读者能够体会到的是情感的真实。如此,其行文才有“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忒”的书写效果。
二、身份差异下的多元想象
目前所能见到的北魏比丘尼墓志,或由其弟子书写,或由文人书写。而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其对墓主形象描绘的侧重点便有较大差异,书写的风格及行文特点也各有不同。诚然,书写者无法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精确的评价,对比丘尼的评判和眼光,更多是基于自身视角的认识与想象。
文人视角的观察与想象,以《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及《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为典例。前者明确署“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领中书舍人常景文”[6](P23),常景是北魏的名家,尤其擅长碑铭。世宗时,崔光曾评价:“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5](P1801)常景尤为重视礼法。高肇曾娶平阳公主,在平阳公主去世后,高肇想让公主的家令居庐制服,相关官员征求常景的意见,常景严守纲纪,认为此举于礼法不合:
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朝廷从之。[5](P1801-1802)
常景引经据典,以古礼纲纪为训,循君臣、男女伦常之节,最终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另外,史书记载:“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5](P1803)朝廷在典章方面但凡有疑难问题的,也往往征询常景的意见,可见其对礼法的推崇与熟稔程度远超他人。因此,从他为慈庆尼书写的墓志来看,其笔下的比丘尼更接近于一位遵守礼法的妇人形象。“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6](P22)在介绍慈庆尼的出身与家世后,开篇即以文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来整体塑造慈庆的人格特点。又详细记叙了她出家之前的经历,称赞其嫁人之后,“谐襟外族,执礼中馈,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6](P22)
至于《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其崇尚礼法的特色便更加鲜明。这篇墓志虽没有明确署名是哪位文人所书写,但从通篇称呼墓主人为夫人来看,书写者并非是佛门弟子。这篇墓志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记叙及评价其出家前的生活经历,而遁入佛门后的经历只有一两句话一笔带过,详略之安排一目了然。且令人从中领略到的,依然是一位贤良淑德的女子形象:“初笄之年,言归穆氏,勤事女功,备宣妇德。”[6](P298)其行为举止遵从礼法的要求,婚姻生活亦满足文人的想象与理想:“婉然作配,来嫔君子,好如琴瑟,和若埙篪,不言容宿,自同宾敬。奉姑尽礼,克匪懈于一人;处姒唯雍,能燮谐于众列。”[6](P298)其形象在文人眼中完美至“女宗一时,母仪千载”:“稀言慎语,白圭无玷,敬信然诺,黄金非重。巾帨公宫,不登袨异之服;箕帚贵室,必御浣濯之衣。信可以女宗一时,母仪千载,岂直闻言识行,观色知情。”[6](P298)文中只简单交代了慈庆出家的因缘,并不能令人深刻感受到其在佛门的形象及人格特点。从文人的视角出发,其笔下的比丘尼形象蕴含着鲜明的世俗礼法之内涵,恰是文人理解与想象的结果。
然而,由墓主人的比丘尼弟子所书写的墓志,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风貌,她们笔下的比丘尼是一副不累于物,超尘拔俗的高尼形象。如,由其弟子书写的《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开篇则以“禀三才之正气,含七政之淑灵,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4](P20)来赞其总体的人格魅力。在铭文部分,更是用幽玄的笔触总结并赞美其智识与德业:
般若无源,神理不测。熟诠至道,爰在妙识。猗欤上仁,允臻寞极。凝心入净,荡智融色。转轮三有,周流六道。独善非德,兼济为功。幽镜寂灭,玄悟若空。怀彼昭旷,落此尘封。洞鉴方等,深苞律藏。微言斯究,奥旨咸鬯。宝座既升,法音既唱,耶(邪)观反正,异旨辍鄣。德重教尊,行深敬久。[4](P20)
铭文既体现了书写者的佛学素养与文学功底,也展现了她们对其师生平的认识与想象。又如,《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云:“三空杳眇,四果攸绵,得门其几,惟哲惟贤。猗与上善,独悟斯缘,出尘解累,业道西禅。”[7](P44)《魏比丘尼慧静墓志》云:“离欲出家,舍身救人,摄心不乱,乃能成仁。悉除嗔恚,慈悲众生,猛勇精进,始名净行。”[7](P47)这两篇墓志亦均由墓主人的比丘尼弟子书写,她们则以佛门弟子的眼光及想象勾勒并赞颂其生平,令人感受到是智慧与慈悲并存的女性形象。
墓志浓缩的是人的一生,如没有史料记载,后人便只能通过墓志的书写去了解墓主人的生平及形象,而其形象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写者决定的,他们的认识与想象对逝者生前的形象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文体特质与形象建构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虚构和想象都是其中重要的书写策略。而对墓志文体特点的充分把握也是书写主体需要考虑的。《洛阳伽蓝记》云:“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佞言伤正,华辞损实。”[1](第51册,P1006)应该认识到,墓志的基本特点在于为逝者歌功颂德,故碑文多有溢美之词。因此,墓志语言虚饰、浮华的现象在所难免,墓志中的形象存在虚构成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所有的墓志都以夸饰为显著特征。《文体明辨序说·墓志铭》曰:“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徇人以情也。”[8](P148)正直之人书写的墓志,仍会尊重客观事实,即使虚构也是在文学的手法范围之内,而这类墓志往往情辞恳切,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另外,墓志本来是防止陵谷改迁的标识物,所以比丘尼书写的墓志文中亦反映了这一观念,如,《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云:“弟子法王等一百人,痛容光之日远,惧陵谷之有移,敬铭泉石,以志不朽。”[7](P44)但对比同一时期的高僧墓志,却显示出不同的见解,《大魏比丘净智师圆寂塔铭》云:“陵谷有迁,佛国久在。”[6](P357)书写者认识到对僧人而言,陵谷也只是诸法相而已,超脱生死轮回之后的佛国永远存在,又何惧陵谷迁移。显然,慈义尼的弟子法王仍然沿用世俗的观念,对佛法的理解有其局限性。
从墓志文的结构安排来看,开头往往要叙述逝者的家世,一般都要写明家族历史上的显达之人,尤其要凸出本姓历史上最声名显赫之人。由比丘尼弟子书写的墓志依然沿袭这一习惯,可见官位及祖宗崇拜心理影响深远,其时的出家之人也未能免俗。
法师讳僧芝,俗姓胡,安定临泾人也。虞宾以统历承乾,胡公以绍妫命国,备载于方册,故弗详焉。姚班督护军、临渭令、勃海公咨议参军略之孙,大夏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圣世宁西将军、河州刺史、武始侯渊之女,侍中、中书监、仪同三司、安定郡开国公珍之妹,崇训皇太后之姑。(《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4](P20)
尼讳英,姓高氏,勃海条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7](P44)
慈义尼的墓志体现得尤为显著,家族中地位最显赫的要属其姑文昭皇太后了,所以墓志只提及其与太后的亲缘关系。这种表述固然遵从墓志文的习惯,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人们自古以来的文化心理,《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9](P1355)因此,从这些墓志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北魏时比丘尼对传统思想的接受及对皇权的依附形象。有学者指出:“北魏僧官大多主动依附王权,这与南朝的僧官及许多上层僧侣为坚持佛教的特殊礼仪及政权的相对独立性而进行长期的斗争是大异其趣的。”[10](P69)北魏僧官对皇权的依附性格应是整体氛围下的一种局部现象,北魏时期的僧尼当在此方面具有一致性。
另外,渐区定型与成熟的墓志文中往往有表达生者哀痛之情的部分,有学者称其为“述哀”[11](P171)。这些比丘尼在书写中依旧沿袭了这一特点:
弟子法王等一百人,痛容光之日远,惧陵谷之有移,敬铭泉石,以志不朽。……徒众号慕,涕泗沦连,哀哀戚属,载擗载援。(《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7](P44)
第(弟)子等痛徽容之永绝,嗟大德之莫继,为铭泉石,以志不朽。……徒侣追慕,涕泗长沦。(《魏比丘尼慧静墓志》)[7](P47)
在述哀部分,她们无不将痛苦流涕的哀痛景象描绘地淋漓尽致,显示其内心的悲痛与酸楚,以“涕泗长沦”、“涕泗沦连”来描摹众人痛哭的场面。这一特点仍旧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礼法特色。《礼记·丧大记》曰:“敛者既敛必哭。”[12](P650)《礼记·奔丧》曰:“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12](P838)因此,用“哭”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悼是丧礼的必备环节。于是,在墓志中表达对亡者的思念,以对哭的描绘显示生者的悲痛心理便成为一种必然和固定的书写模式。
北魏时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后,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其少数民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孝道的重视和推崇成为其时的显著特色。后来北魏王朝甚至废除了“立子杀母”这一残忍的宫廷制度。其所重视的《孝经》即云: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13](P57-61)
因此,“死事哀戚”的传统思想必是举国上下所尊崇与深入人心的理念。但比丘尼作为佛门弟子,其对这一思想的接受与佛教所宣扬的理念相乖违。佛教追求能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所以必不会执著于死亡的苦痛。故而历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都对死亡表现出超脱的态度。六祖慧能甚至告诫自己的弟子不要像世俗之人那样为其死亡而身着孝服,痛苦流涕,应能领会佛法的真谛:“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14](P187)据《大般涅槃经》的记载来看,佛祖释迦牟尼在临终前也告诫弟子不要愁苦,当知诸行无常,自己将入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之境,所以不应啼哭,其说偈曰:“我今入涅槃,受于第一乐。诸佛法如是,不应复啼哭。”[1](第12册,P373)
由此看来,北魏时期比丘尼的墓志书写仍遵从墓志文体自身的特色,反映了她们依然遵循现实礼法及传统的伦理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与原始佛教观念相冲突的世俗化特点。
透过北魏时期的比丘尼墓志,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基于虚构、想象等书写策略下的佛教女性形象,其对皇权的依附性虽是她们形象的重要之维,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必然需要适应其本来的文化传统。此外,从当时女性的普遍文化水平来考量,其中由比丘尼弟子所书写的墓志已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这也得益于佛教文化的兴盛改变了这些女性原有的生活与活动空间,并为她们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平台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