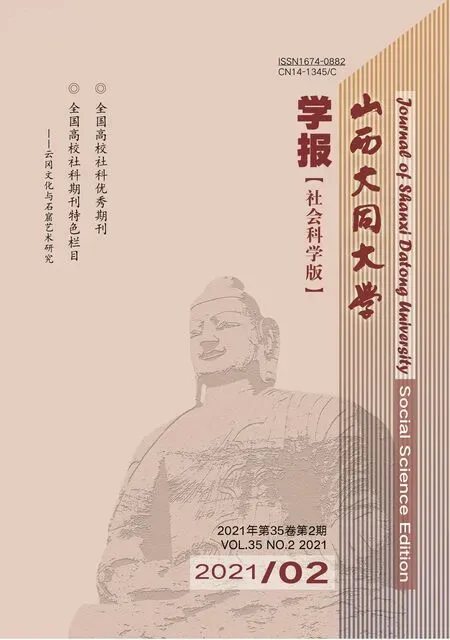儒玄同构:魏晋前期文学审美过渡态势研究
——以何晏与阮籍的赋体创作为例
苏 婳,马晓虹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魏晋时期所谓“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学独立。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与“诸子”的并列,到《后汉书》中“文苑”与“儒林”的并列,都可以看出文学的独立意识,似乎后者更有文学独立的意味。古人对“文”与“文学”的定义,与儒家政教观念息息相关。《论语》中提到的“文”与“文学”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含义:典籍义、礼仪制度义、个人道德修养义、社会文化义、文采义或是专称“文王”等。①可见已经被规定在“血缘—国家—天地—宇宙”的社会文化建构下的“文学”,即使到了魏晋这一“越名教”的时代,也无法达到完整的解构。这一时期在儒学与玄学撕扯下,文学审美方式出现了过渡性变化的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下面以何晏与阮籍两位魏晋前期名士的赋体创作为例,进行论述。
一、“鸿鹄之篇,风规见矣”:赋颂与玄学的碰撞
在众多魏晋名士中,何晏(?—249)名声尤为显赫。他被认为是“空谈”与“吃药”的祖师,是正始年间清谈的主导人物,其著作概涉儒玄。据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一书统计,何晏著有《周易解》、《孝经注》一卷、《论语集解》十卷、《魏明帝谥议》二卷、《官族传》十卷等,另外还有文集十卷,今存赋、奏、议、论、铭等十四篇,五言诗二首。[1](P383-384)后经学者研究,目前收录于严可均《全三国文》中的属于何晏创作的奏论疏议赋颂只有十一篇[2],其中赋体一篇名为《景福殿赋》,颂体一篇名曰《瑞颂》。
(一)“劝百讽一”:赋颂中的儒家审美特征 作为何晏唯一留存于世的赋篇,《景福殿赋》的形式与气格全然是汉大赋的翻版。赋篇开头将魏明帝前往许昌避暑美化为圣王东巡,对于景福殿的描写套路显然大部分继承自班固的《两都赋》,其中对《东都赋》借鉴尤多。他的整套话语体系全然是在儒家诗学的框架内积极建构的经学中心主义。他援引《尚书》《礼记》《周易》等经典用来支撑儒家的审美感应论,如“皆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上则崇稽古之弘道,下则阐长世之善经。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载祀二三,而国富刑清”,[3](P1271)实是“天人合一”“阴阳共生”的经学话语体系的重塑。在完成时空架构与解释宫殿“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饬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的天子重威之后,文章就开始对宫殿极尽奢华的铺排描写。从“远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云”的远近观看,到“芸若充庭,槐枫被宸。缀以万年,綷以紫榛”的文德芳馨;从“于是列髹彤之绣桷,垂琬琰之文珰。蝹若神龙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的圣人灵气,到“故将广智,必先多闻。多闻多杂,多杂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择人。故将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礼之不愆,是以尽乎行道之先民”的仁儒归指,[3](P1272)在这个支离破碎、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作者仍想谱写“大一统”的辉煌乐章。由于这个时代已无汉代那样的现实背景的宏大观照,对“丰层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的全力夸饰,后世读者只能从中感受到过分虚拟与伪造。
当然,同汉代的散体大赋一样,在介绍完豪华的宫殿之后,结尾部分还应有一段固定模式下不温不火的“讽谏”,来达成儒家诗学审美中最重要的文学“可以怨”的社会功用。这篇赋也说到了“睹农人之耘耔,亮稼穑之艰难。惟飨年之丰寡,思《无逸》之所叹。……观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诚伪。瞻贵贱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风助教,岂惟盘乐而崇侈靡?”又说“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於太素”,[3](P1273)何氏从广开言路、任人唯贤、去除冗官、减免杂役等各个方面对政务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契合了“劝百讽一”的经典模式。这种对儒家美学的全盘接受与儒家政教观的积极消化,与其玄学祖师的名号产生严重的悖反。他的《瑞颂》篇对儒家经学符号——“祥瑞”大力鼓吹,写下“应龙游于华泽,凤鸟鸣于高冈。麒麟依于圃籍,甝虎类于坰疆。鹿之麌麌,载素其色”的颂美话语,[3](P1275)这种生命体验的感性的、模糊的向外求索,似乎远远未达到个人理性的自觉。而且其《言志诗》中也出现将“鸿鹄”与“逍遥”并立的现象。[4](P468)这种儒家入世的建构意象与道家出世的解构意象相结合的写作模式,使得其玄学体系构建更加矛盾更加复杂,对这一问题的阐释研究应进一步深入。
(二)“有所有”:圣贤道德与人格本体混融的玄学体系 所谓“圣贤道德”即是儒家经学体系中圣贤树立的道德标准。在汉代将儒学神学化的过程中这一道德标准逐渐成为能够代表“天道”的道德范式。“人格本体”即是对个体内在道德理性的挖掘与回归。原始道家提出“无所有”的命题,即所有“有”均生于“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圣贤道德”与“人格本体”的双重降格。何晏借用道家“无所有”的命题,进一步提出“有所有”的观念,再次权衡“无”与“有”、“圣贤”与“个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与价值比重。
1.“无所有”与“有所有”的比较分析
作为玄学大师,何晏除了在对经典的注解中片段式反映出自己的思想之外,大段论述其玄学思想的散文所存不多,今存最完整的篇章是《无名论》,以下是节选:
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然与夫可誉可名者,岂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3](P1274)
这段话是在名理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名理学中,“名”与“实”是一一对应的,而且是先有具体的“实”才有抽象的“名”。“誉”为民众所能指称之“实”,“有所誉”就等于“有名”。若是一直这样理解“名”与“实”,也就不会有玄学的思辨,即何氏提出民众与圣人的不同,圣人能够“名无名,誉无誉”。老子《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5](P1)“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5](P59)为何指示宇宙本体的“无”能够用“道”字给以其具体之“名”?是否即使“无实”也可“有名”?由此“名”与“实”的对应关系被打破而进入到玄学的思考。这里何晏突破了原始道家话语中“有”与“无”的思辨,提出了新的关于“无所有”与“有所有”的思考。
如何理解“无所有”与“有所有”的关系?文中提到“于有所有之中,当于无所有相从,而与夫有所有者不同”。首先“无所有”是要靠“有所有”来体现其实质内涵的,其次“无所有”与“有所有”截然不同。要清楚地理解其含义,就要弄清楚何氏在残存的《道论》中对于“道”的认识。“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6](P3)何氏认为:一、“道”的宇宙本体论对应着“全”,它绝对是在“无语”“无名”“无形”“无声”的“大”的状态下包含着宇宙万物。二、“道”又具有超越性。在何氏的构思中,“道”并不是完全形而上的不可把握的存在,而是时刻被“有”所反映着的切实具象。“有”生于“无”,“无”要依赖“有”来表现。放在玄学化的名理学中来研究,即“无实”也可“有名”,而“无名”也必然要“有实”。此时回过头来再去分析“无所有”与“有所有”便可知,“无所有”即是“全”的无规定性状态,“有所有”是“道”反映在“有”中的具体规定性。借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即“道”是客观的“进行时”的存在,“无所有”是“道”的存在方式;“有所有”是具体的存在者,是已经成为“道”的体现者的“完成时”。
2.“有所有”的话语背景阐释
从《无名论》中可以看到,何晏积极建构着“圣人”可以“名无名”的体系,将老子“虚空”之“道”拉入现实的“名实”下进行探讨。这种“天人之际”的探讨脱离了汉学感应论的研究,进入到理性思辨层面。试将他与同时期王弼的玄学思想作一比较,王弼清晰的提出“崇本举末”(“无”为本,“有”为末)、“守母存子”、“体用如一”(“无”为体,“有”为用)的观念。[7](P240)这种将道家的话语带入现实人生中进行再度阐释的行为,实则是将“纯粹理性”向“实践理性”进行转化,他们的立脚点都是对“人”给予关注。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先生认为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判断是十分有见地的。以“人道”为核心的先秦儒家在经历汉代神学化的阐释之后已经失去了其本质的“人道精神”,而魏晋玄学对“人道”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则是用“天道”与“人道”的思辨来建构人格本体的高尚。其重点是要建构一个“圣人”的政治理想,来协调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在这段兵荒马乱正朔紊乱的时代中,如何同时保持伦理的皈依与本性的清醒,是那个时代的玄学家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综上所述,何晏的赋颂创作中对儒家政教的大肆弘扬虽看似与玄学悖立,实则是有内在联系的。我们也可从何晏的散文创作中清楚地看到,处于魏晋初期的名士们心中内守性与渴望超越的矛盾状态,他们没有了汉代外向型审美观产生的现实环境,仍在苟延残喘的儒家审美感应论中做着努力,而为了填补信仰的“失语”,一个儒玄同构的理论体系正在悄然出现,这就是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为之后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做了铺垫,同时也是文学审美气质从外向内转变的重要过渡期。
二、“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儒趣与玄思的磨合
前文分析了作为玄学祖师的何晏在赋体创作中对儒学审美的吸纳与在玄学架构中对儒家人道的重释之后,从中可以了解到所谓的“魏晋自觉”绝非是瞬时的,在与儒教剥离的过程中,魏晋名士所作出的努力值得深入探索。而作为“正始之音”的首位代表人物——阮籍(210—263),在何晏、王弼等人创立的玄学体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其赋篇创作更是十分清晰地显示出儒玄的磨合。
阮籍文集保留较多,且版本众多,严可均《全三国文》中共十九篇,其中赋存六篇,分别是《东平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清思赋》和《元父赋》。[3](P1303-P1306)
(一)“耳目之内”:儒家批评符号的沿用与重释公元249年发生的高平陵之变,成为司马氏王朝失败的起点。政变失败者曹爽等人遭到了夷三族的血腥屠杀,其中就有何晏。这一次事变是政治的博弈,也是文人的浩劫。信仰体系的全面崩盘、价值取向的重新选择、生死攸关的再度判断成为当时文人深刻体认的时代危机。
曹氏一行惨遭屠杀,掀起了舆论同情。阮籍时迁司马师从事中郎,于252 年写下《鸠赋》,赋序中言:“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8](P47)借对两只鸠鸟从获救被豢养到最终落入犬口的描写,表达了人生易逝的感怀。以鸠作为对象以及“旷逾旬而育类,嘉七子之修容”的描写,[8](P47)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诗经·曹风·鸤鸠》篇。鸤鸠即布谷,“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历来被褒扬为“仁”。如曹植在《责躬有表》中曰:“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9](P269)正是此意。在阮赋中,对“仁”的撕毁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与政治内涵。“背草莱以求仁,托君子之静室”的高尚生灵最终沦落到“捐弃而沦失”的地步,而儒士眼中的慷慨赴死是否成为政治家眼中的荒诞玩笑呢?阮氏在赋中饱含感性的热忱,对鸠的仁义以褒奖,对美貌以赞言,对死亡以同情,这种悲伤也恰好控制在儒家诗学所规定的“哀而不伤”的框架中。在这种对外在事物的感性抒发中,读者也能深刻体认其理性的自我反思意识:“求仁”生灵的自我比附以及“洁文襟以交颈,坑华丽之艳溢”的埋葬举动实则是一种道德反思与自我告别。
更加理性的自觉体现在之后的赋体创作中。公元254 年,阮氏作《首阳山赋》。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10](P2123)“首阳山”在传统文人心中一直与忠贞大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阮氏似乎想抛却该符号原本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阮氏在首段末尾就给出了自我定位:“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怀分索之精一兮,秽群伪之射真。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这里已经有了想将自己抽离出现实涡旋中的冷静思考。消解掉历来对伯夷、叔齐行为的推崇,而言“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亡国后投周的举动实已不忠,何来仁义的美誉?之后又连用两个反问,“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8](P27)不仅对历史记载的美饰成分发出质问,也颇有想抛弃无妄之“言”而直达人生第一义之“意”的哲理思辨。对于该赋的现实背景与创作主旨,前人已有结论:“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辞隐。”[8](P28)同时,该赋对于儒学批评的剥离与人格本体的反思也是应该把握的。阮籍次年任东平相时所作的《东平赋》,看似继承汉都邑赋,对都城进行四面八方的极致渲染;实则是在浩大的铺展中编织孤独的灵魂,在宏阔的纵深中书写游仙的神思。可见,此时阮籍的玄心与传统儒教已经有了深层次的磨合,即将迎来“任自然”的超越。
(二)“八荒之表”:“无名”与自然的冥合 迫近晚年,因朝政日趋暴戾,生母悲惨离去,阮籍的避世之心尤胜,甚至到了日夜饮酒、不置一言的颓丧境地。将对朝政纲常的不信任转移到哲理玄思领域,即是对任何语言指称的不信任。这种对“自然”的本体论的认知,一方面来源于庄子的“言不尽意”,另一方面来源于何晏、王弼所重构的“贵无”“无名”的认识论。从将语言作为“工具”到最后将“工具”都抛弃,实则是对周遭现实深感失望继而转向对精神超越之希冀。
在《清思赋》中,开头便对“美”与“善”予以否定:“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用黄帝之乐于夔牙之际而不知所云和精卫志之宏大也无法感染瑶台神女这两个例子,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消解经过世人定义的变质的概念。“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伊衷虑之遒好兮,又焉处而靡逞?”无声反而听得更仔细,无虑反而思考得更深入。外物终是繁杂,他认为以“性”和“情”为旨归才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接着,在“乃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惊”的顿悟体验后,与屈原一样,作者也开始在天地八荒的神游。此刻没有女嬃的诘问,也没有形神分离的“枯槁”,而是“心漾漾而无所终薄兮,思悠悠而未半”的真正的逍遥状态。“敷斯来之在室兮,乃飘忽之所晞。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清言窃其如兰兮,辞婉婉而靡违。托精灵之运会兮,浮日月之余晖。假淳气之精微兮,幸备宴以自私。愿申爱于今夕兮,尚有访乎是非。被芬芳之夕畅兮,将暂往而永归。”[8](P29-P39)阮氏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自由徜徉。赋末作者直言“既不以万物累心兮,岂一女子之足思”,没有求女之欲望,亦不会有失落之涕零。阮籍真正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至境。
阮籍晚年创作的《大人先生传》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其晚年的政治哲学观。其曰:
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滞而不振。[8](P170)
阮籍认为“君臣”“礼乐”的规则设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导致从“假高尚”到“真贪恶”,从“金玉其外”到“败絮其中”。这种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对庄子的继承,也映证了《清思赋》开头对“美”“善”的解构。这种对儒家文艺思想与儒家政治制度的突破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觉醒。
综上所述,阮籍的赋体创作从对儒家审美意象的沿用到重释,再到超越,最终达成“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的自在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越名教”也并非真正的“越”,从积极角度看来是一种审美突破与自我觉醒,但从消极看来仍只是一种精神安慰。在儒玄同构的本体论的影响下,文人的避世并不能永久,这种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固定的依附关系,使得名士们常处于“名教”与“自然”的痛苦挣扎中。这样看来,阮籍的神游是否也像屈子一样最终“从彭咸之所居”呢?历史已予以回答。
三、总结:从“润色鸿业”到“宅心高远”
艾略特在分析“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时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11](P109)从上文对何晏与阮籍赋作的分析中可知,他们的创作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的。在经历汉代将儒家诗学提升至经学本位之后,中国文学的“传统”就已经与政教脱不开关系。这也直接影响到后世学者对于“文学自觉”分期的争议。
老子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5](P4)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玄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必然要在同儒学的比较中来定义其特征。何晏的赋体创作和玄学体系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汉代“大美”的重释,将其规定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即是一种“有名”“有形”的实体状态,虽然在文学文本创作中向内的倾向并不明显,但读者也能明显感受到那种专属汉代的文气渐趋薄弱。而在经历过政变的阮籍那里,审美向内挖掘的进程开始变快,其赋体创造就呈现出更多智慧的理性思辨与高远的自在境界。
注释:
①在《论语》中除去“君子博学于文”的重复,“文”字出现在单句中一共二十三次。同时除去人名中的“文”字,指典籍文献义六处如“文献不足征”;指礼仪制度义两处如“郁郁乎文哉”;指个人道德修养义两处如“君子以文会友”;指社会道德一处为“修文德以来之”;指文采义两处如“质胜文则野”等。(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