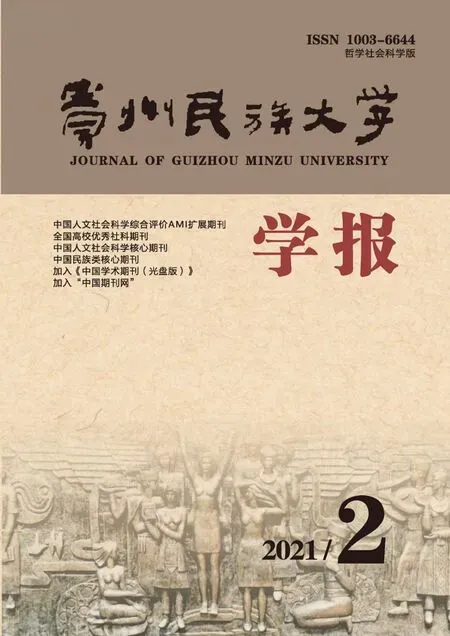口述史研究及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
肖 唐 金,肖 志 鹏
一、前言
美国著名口述史和口述传播学者Donald A.Ritchie在其所著的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1)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一书中,对口述史研究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层次探讨,如:口述史的界定、口述史研究的意义、口述史研究的来龙去脉、访谈的方方面面、社区史和口述史的关联、口述史学家的资质、口述史的作用,等等。另外,对于口述史所涉及的情感研究,Fussel(2)Susan R.Fussell,The Verbal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Mahwah, New Jersey/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2.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首先摘录这两位外国学者的观点,探讨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接着,我们拟结合Vansina(3)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Abrams(4)Lynn Abrams,Oral History Theory,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0.、Nicolas Tapp(王富文)(5)王富文:《海外苗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兰东兴(6)兰东兴:《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中外学者的观点,探讨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具体以贵州雷山的苗族口述史为例,展示口述史研究的实践意义,结合相关事例,说明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意义。
二、口述史的界定和研究的意义
记忆是口述史的核心,从记忆中可提取和保存意义。简言之,访谈记录中包含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和个人评述。口述史访谈包括三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的访谈者、对被访谈者提问、以声音或图像的形式记录两者之间的交流。访谈记录可转化为文字,做成总结,建立索引,存放在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访谈资料可用于研究,摘录在出版物中;作为电台或图像文件,在博物馆展出;通过戏剧加以表现,或出现在其他公共表现形式中。所记录和拍摄的访谈内容、目录、照片、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可发布在网上。为了防止常见的错误,口述史学家创造了访谈的标准,确立了与被访谈者打交道的伦理原则。然而,口述的动态性特征,使得我们难以用一个单一的定义去把握。有规则就有例外,想象力丰富的访谈者总是在不断发展、分享口述史研究的新方法和用途。要规范口述史采录过程,或对访谈提出操作建议,就必须考虑具体工作目标、现有资源以及其他实际情况。
口述史研究不会简化历史叙事,反而使其更复杂、更丰富。访谈者要做的事就是做好访谈前的准备、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克制交谈的欲望、专心听被访谈者的声音。当然要做到这些很难,大多数口述史研究者虽然在访谈中保持安静,但在专业会议上却侃侃而谈。另外,虽然口述史研究者擅长提问,却对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以及新技术的应用经常质疑。尽管如此,世界各地口述史研究者大有人在。访谈者的足迹涉及政治家、移民、艺术家、工匠、士兵、平民等。访谈重要历史事件,如纳粹大屠杀、日裔美国人的拘留,也捕捉了城内、城外乃至边远村寨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经历。历史学家意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在某些历史文本中存在展示不足的现象,口述史学家记录了其声音,从而构建了更为多样、精确的历史描写。口述史研究对未来意义重大。随着历史事件参与者的逝去,未来的研究者只能依靠早期搜集、加工储存的口述档案。他们会如何评价我们现有的口述史研究?是重要补充,还只是肤浅、表面的研究?现有的口述史研究有多少可以保存到未来?口述史研究者应有远见,从规模、效度等角度充分考虑口述史研究语料库的建构。
三、口述史研究的来龙去脉
口述传统是通过口头形式传承的。(据此,口述史访谈晚于口述传统)3000年前,中国周朝的文人就记录了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为宫廷历史学家所使用。几个世纪后,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访谈了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s)的参与者。同时,人们对历史见证的质疑之声,同样悠久。修昔底德曾抱怨“不同的证人对同样事件说法不同,由于记忆不完整对事件只说到一部分”。16世纪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的时候,西班牙的编年史学家就依赖口述资料建构阿兹特克、印加等美洲印第安土著人的历史。他们搜集这些历史上曾辉煌的文明的幸存者的口述,着重关注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成为欧洲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历史建构的重要资料来源。1733年,英国著名辞典编撰家萨缪尔·约翰逊就反对历史不能根据体验过相关事件的人物生平来撰写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人们参与了相关事件,历史学家与其交谈,就能记录下所听到的东西,最终成为叙事的好素材。约翰逊告诫我们,所有历史首先就是“口述的”,并提及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正是这样对法国君主的历史进行构建。伏尔泰写道,他向旧臣、仆人、大贵族以及其他人提问过,只记录了那些他们同意的事实。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法国革命发生半个世纪之后研究了其历史,对比了官方文献和“农民、市民、老人、妇女甚至儿童”的回忆,这些回忆在村寨小酒馆中俯拾皆是。在19世纪末之前,学者们在构建历史时既使用书面文献,也搜集口述材料,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德国科学历史学派倡导文献研究,排斥了其他“不大客观”的资料。莱奥波德·冯·兰克强调,历史事件发生时创建的文献是最可靠的历史证据,兰克的追寻者将书面文献历史转变为一个学科,并强调严格使用证据。他们将文献逐一筛查,把口述资料斥之为民俗、神话,只有意图良好但略显幼稚的业余研究者和古文物收藏者看重。他们认为口述资料过于主观。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家不看重口述资料,但其他专业和学科却对访谈持拥抱态度。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期间记者们把访谈当作看家本领(mainstay of their craft)。19世纪90年代美国民族志局派遣研究者在蜡缸上记录美国土著民族的歌曲和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派遣了一些无业的作者,编撰普通民众的生活,对早期的美国部份黑人的访谈尤其具有价值。40年代后,历史学家最终接受了这些包括长达1万多页的访谈的记录,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对美国黑奴制的解释。
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命令政府所有军事分支和文官机构记录战时经历。美国军队推出了战后史以及一系列提升士气的“美国现役部队”小册子,派遣携带沉重有线录音机的史学家到战地。马绍尔中校是个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和记者,后转为部队史学家,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开拓了战后访谈,即在战斗发生之后立刻访谈士兵以构建当日事件。佛瑞斯特·波哥中士(Sgt. Forrest Pogue)在计划行动日(D-Day)访谈了撤退到停泊在诺曼底海滩附近的船上医院的受伤士兵。波哥中士回忆,起初有些担心,身负笨重的有线录音机,可能会成为狙击手的活靶子,但部队有任务,需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史学家。虽然“口述史”这一术语早就使用了,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与访谈联系起来。约瑟夫·古尔德(Joseph Gould)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是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人、廉价旅馆的居住者,也称“海鸥教授”(Professor Sea Gull),曾在曼哈顿区四处走动,搜集他所称的“我们时代的口述史”。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1942年在《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约瑟夫·古尔德生平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后者历经各种困难记录了普通百姓的故事。古尔德认为,“人们说的就是历史”,“我们以前认为的所谓历史—国王和王后、协约、发明、大型战斗、凯撒、拿破仑、哥伦布、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美国政治家、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演说家)只是正规历史,且大部分是错误的,我要记录穿着有袖口的衬衣(shirt-sleeved)的民众的非正规历史——他们对工作、爱情、食物、玩乐、困境、悲痛要说的话,不成功则成仁(or I’ll die in their attempt)”。古尔德的抱负为他挣来了不少免费餐,但他的口述史其实只是自己的虚构之物。古尔德去世时,除了名声没有留下什么精神遗产。另一位由记者转变为史学家的人物,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第一所现代口述史档案馆。而在创立这一机构的10年前,他曾在《通往历史的大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一书中提议重振美国的历史研究,具体做法是从生活经历丰富的现有美国人那里获取口头和书面资料,这样可更为完整地记录其过去60年里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参与。内文斯认识到,现代通讯和交通较为便利,写信、记笔记显得较为落伍,继而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办公室。他的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内文斯所谓的“口述史”要么缺乏精确度,要么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Freudian)。到了20世纪60年代,内文斯的继承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指出,“口述史”这一术语已经以小写的方式在报纸语言中被提及(说明已开始显示重要性)。斯塔尔宣称,“口述史,不管你喜欢与否,已立足,成为通用类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54年发起了相似的口述史研究方案,接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于1958年也效仿了此举。哈里·特鲁门图书馆(Harry S. Truman Library)于1960年发起了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口述史研究方案。约翰·肯尼迪图书馆(John F. Kennedy Library)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就在约翰·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后不久开始访谈相关人物。口述史随之就成为搜集总统生平事迹的标准做法。1967年美国口述史研究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吸收了境内外会员。此后,口述史研究项目在各大洲兴起,全国性口述史组织相继在墨西哥、新西兰等国家成立。1972年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 in London)成立了“声音记录部”(Department of Sound Records),搜集、保存男女军人的口头证词,如果不是这样,这些人就会因为缺乏意愿、机会或文学技能而不会有其他历史记录。1987年在英国牛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口述史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该协会每两年在世界某地举行一次研讨会。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政局、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史学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档案文献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多为政府工作效率较低,而不是对文献档案的抵触情绪。亚洲、非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发现,书面文献反映的是先前殖民者的观点,因此使用口述史可以重塑被埋没的民族身份。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口述史研究项目记录了军人专制时期的受迫害者的经历。南非黑人也利用口述史研究种族隔离期的真相,借助口述史在后隔离期愈合受害者的心灵。许多国家的访谈者发现,在遭遇压制需要调和的时候,访谈是关键有用的工具。
四、访谈的方方面面
(一)访谈者
首先寻找那些有访谈经验的人、那些已经做过访谈的人或那些学习过口述史研究课程或参加过工作坊的人。从理想的角度看,访谈者应该对项目主题有一定能力或经验。偶尔能力和经验兼备的访谈者可以找到,但一般来讲项目组织者只需取其中一个资质就行。进入某新领域的有经验的访谈者需要对主题做广泛的研究。那些熟悉主题但没有访谈经验的人需要在访谈技巧方面受训。没有经验的访谈者应该参加有经验的口述史学家主持的培训会。所有访谈者在开始访谈前,都有必要充分了解项目的目标以及相关伦理、法律责任。志愿者一般来自受访的社区或群体。由于志愿者是社区的成员,因此在对主题进行研究、与受访者建立融洽关系方面有优势。使用“熟人”(intimate)也有不利的方面,如他们不愿意探讨不愉快的话题、受访者对坦率透露信息给社区的另一成员心存迟疑。相比较而言,来自社区外的“门诊式”(clinical)访谈者可能会被视为更中立、慎重。外来的访谈者会鼓励受访者谈论本社区知晓但组织不佳、社区之外了解甚少的主题。但也应注意,有类似经历的访谈者通常有自己要讲述的故事,可能忍不住打断受访者进行插话(如,“哦,是吗?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经历”)。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应提前对访谈者进行访谈,先把他们讲述的故事录下来。
受访也可让志愿者、访谈者熟悉访谈过程。不论是有报酬还是志愿服务,所有访谈者都应该在访谈前准备好记录其准备的东西和方法以及访谈情形。访谈者除了录音和文字转换外,还应附上一份书面个人简况。这对未来的研究者在理解访谈的动态性方面会有一定价值,如考虑访谈者的背景对访谈可能产生了什么影响。传记作者会考虑口述史本身怎样成为受访者生平中的一个事件,访谈时受访者是否有机会反思过去的成功与失败。未来的研究者会想知道访谈发生的时间和情形。访谈者和受访者在录音和文字转换方面以及各种后续的引用或使用中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认可。
(二)受访者
在美国,第一个口述史档案馆力图避免约瑟夫·古尔德所提及的“穿着有袖口衬衣的民众”。阿兰·内文斯是一个政治史学家,访谈了政府、企业、社会的主要代表。在内文斯退休之后很久,哥伦比亚大学还在访谈各种社会名流(people of the stature),如法官、内阁成员、参议员、出版商、企业高管(business executive)、市政领导。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口述史研究项目一开始就为社会史学家所主宰,他们试图记录普通劳动者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经历。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有新一代的美国史学家开始从社会底层书写历史(writing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由于缺乏关于社会精英的丰富手稿、正规的文献资料,美国史学家只有求助于口述资料。这样的做法得力于芝加哥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前公共事业振兴署访谈人斯塔德斯·特尔克尔(Studs Terkel),他出版了《艰难时刻》(Hard Times)(1970年)、《工作中》(Working)(1974年)、《美好的战争》(The Good War)(1984年)等著作,着重刻画了日常百姓的声音。阿莱克斯·哈雷(Alex Haley)的《根》(Roots)(1976年)同样给人们(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以较大的鼓励,让他们通过访谈搜集家庭史。卡式录音带、录像带方便且价格较低,进一步促进了口述史的研究。多年来,口述史学家就“精英”和“非精英”访谈的优点进行了争论。随着争辩趋于结束,口述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访谈者对自己的具体操作研究越多,就越会发现,没有哪个群体可对历史具有独有的认知力,最好的研究项目应该广撒网,尽可能多地记录事件参与者或社区成员。过去,军事口述史学家被问及是否可使用口述史重构军营生活的文化适应情况,他的回答很冷淡,“我只访谈将军”。但现在口述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便在部队里,史学家也会访谈各级应征人员和军官,这些人或为驻扎军人,或为战斗人员。这样,他们就可搜集重要的口述史研究资料。
(三)访谈者的立场
口述史学家对访谈者介入访谈的程度进行了辩论。起初,有人认为独立研究者(为个人研究做访谈的人)在进行口述史研究时过于偏见,而档案馆口述史学家在任何解释中都没有既得利益,可能是更好的访谈者人选。对于阿兰·内文斯所开拓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类型,访谈者被设计为其他人回忆的中立、客观搜集者。这一理念偏激到将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访谈文字记录中的问题全部抹掉。受访者的回答设计为不受打扰的叙事。虽然哥伦比亚大学不久就文字记录采用了“问-答”格式,但许多以口述史证词为重点的著作仍然抹去了访谈者。例如,斯塔德斯·特尔克尔只展现了几个十分需要受访者回答的问题。
有些口述史学家拒绝接受中立提问者的形象,认为自己在访谈过程中是主动施事者。美国杜克大学口述史研究项目(the Duk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负责人之一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认为,如果访谈者过于被动,其职业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古德温也承认,如果访谈者过于积极,会出现因为介入自己的文化主张、政治观点而扭曲访谈真实性的风险。倡导学者型访谈者的人认为,访谈中的主观性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访谈者的提问实际上是对受访者叙事的“第一解释”。受到人类学、文学批评论、社会史发展趋势的影响,他们考察的不仅是访谈者所说的内容,而且也包括访谈者没有说出来的,并对历史记忆中的疏忽(lapses)进行推测。注重方法论的口述史学家批评了对证词不加批评地接受的做法,呼吁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对访谈设计了更高的标准,感叹访谈者和访谈使用者缺乏学术分析,将口述史变为“没有目标的运动”(movement without aim)。20世纪70年代以来,口述史的方法论研究日益深化,口述史研究不仅增加了“目标”,而且还增加了研究深度和复杂度。但是,研究上仍然区分为口述证据搜集之后进行分析、建议访谈前进行相关理论构建两个方面。访谈者总是要准备放弃仔细准备好的问题,沿着意料外的路线跟踪受访者,随时通过提问、引导、引诱、挑战的方式帮助受访者。迈克尔·佛里希(Michael Frisch)在他的著作《共享作者》(Shared Authority)(1990年)中提出了折中的方案,正如书面所示,访谈参与的双方对访谈共享责任,共享作者地位。访谈者可能会认为,在这样的共享作者关系中他们不只是平等的合伙人,他们的问题与回答息息相关,他们在提取原始记忆材料(raw material of memory)用于学术研究。
实际上,访谈者的地位还达不到平等合伙人的状态,口述史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受访者所讲故事的实质内容。另外,对访谈的解释不只是在手拿麦克风的访谈者这边,受访者在回忆、描写相关经历过程中总是不断重新解释、分析自己的动机和行动。口述史实践的相关讨论受益于相关理论的新应用,如传播学、女权主义的访谈、记忆的心理研究。刚入门的口述史研究人员不应被一系列复杂的理论吓倒,如解释学(hermeneutic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语言运用)、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叙事中隐藏的或未说出来的信息)。他们不应一开始就试图将某种理论用于实践,而是应该采取较为实用的“将实践放于理论中”的路线。先从访谈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再深度介入理论议题。访谈实际上可提升对方法讨论的好奇心,不久人们便清楚,访谈者所做的“不只是搜集事实”。这些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早在1966年的第一次口述史学术研讨会(colloquium)中就出现了。在对那次会议论文的述评中,赫曼·卡恩(Herman Kahn)就注意到与会者花费了不少时间盘算口述史的本质和效度。所有的自我质问都让他感觉就像一个青少年在镜子前端详自己,问道,“我是谁?”“我为什么知名度不够更大、受欢迎程度不够更高?”这样的自省将会也应该继续,但卡恩督促口述史学家继续自己的访谈。“他们需要培养耐心,获得自信,满意将自己‘布丁’的求证留给成为‘布丁’最终消费者的学者去考虑。”
(四)访谈者考虑的内容
人们能记住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访谈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有位口述史学家研究了德克萨斯的教师,他们经历了从种族隔离的学校过渡到现代化民族混合学校的过程。研究发现,白人老师对种族隔离或民族融合过程的细节几乎只字不提,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在其记忆中大都保持“隐形”状态。相比较而言,非洲裔美国人能生动回忆起民族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不论研究项目的目标多么有价值,要做好口述史,就必须留点空间让受访者袒露心扉,不要试图用鞋拔(shoehorn)的方式让他们的回答与访谈者设计的问卷或心态吻合。人们能记住的多为最激动、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最生动的记忆往往与事业早期有关,那个时候他们的地位也许不高。到了他们身居要职时,日常事件实际上变得很琐碎,因而在访谈中难以区分、辨别。有位受访者曾在参议院工作过30年,刚开始工作时她很年轻,参议员年纪较大,等到她退休时,她年纪变大而参议员很年轻。如常规模式一样,她对青年时期的经历描述较为详尽,而对近期发生的事情的回忆甚为简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会调查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事件,海军行动总指挥哈罗德·斯塔克舰队司令(Adm. Harold Stark)却回忆不起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进攻前的那个晚上他在哪里。相比较而言,斯塔克的副将基尔克(H. D. Kirk)却能精确地回忆起他们和妻子去看了《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演出,然后回到舰队司令的家,斯塔克在家里接到了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Roosevelt)打来的电话。考虑到斯塔克对这事记不起什么,参与调查的一位参议员问基尔克他怎么对这件事记得这么清楚。基尔克回答说,“我是一只‘小鱼’(职位一般的人物),大事情沸沸扬扬,不会忘记那种事情的。”人们会定期重新评价、重新解释以往的决定和行动。
就像史学家重写历史以融入新证据嵌入新理论一样,人们会从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获得新见解,重塑决定和行动并重新评估以往的经历。这种反思没有什么不好,访谈者和研究者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并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记忆从感觉初期就已开始。受访者从自身的观点讲述,两个人讲不了一模一样的故事。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发生的事情,明白其意义,或有接受责任的足够自信心。经典电影《罗生门》(Rashomon)(1951年)讲述的自相矛盾的故事代表了讲述者的不同印象、自我形象、自欺欺人的心理,但这并不是记忆差的表现。在战斗中,后方的将军对战斗有总体观察,而参加战斗的部队对作战有具体“显微镜般”的观察。二战期间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曾在所罗门群岛(the Solomon Islands)上写道,“坦率地说,我真不知道整体情况,我订阅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Herald)因为物流困难晚到两个月,除非坐在纽约或华盛顿甚至卡萨布兰卡(摩洛哥城市)否则很难了解全球战局。我明白我们要获胜,这让人备受鼓舞,只是很难看到相关迹象,也许身处战场之外看得更清楚点,我知道要是我不在战场而在战场外就能做到。”位于事件中心的人们能够较好地讲述其成就,而身处边缘的人们则能对主要参与者进行较好地比较。一开始就有瑕疵的感知会产生扭曲的记忆。遥远的、二手的信息更容易扭曲。相比较而言,直接、戏剧化、情感性场景往往会产生更为固定、长久的记忆。正因为如此,口述史研究项目试图搜集广泛的访谈,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解答疑惑。
不是每个感知的事件都能在记忆中保留。电台和电视播音员大卫·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撰写了《华盛顿参战》(Washington Goes to War)(1988年),讲述二战期间他第一次来到美国首都成为年轻的新闻播音员的经历,他很吃惊能读到旧报纸里那么多在他的记忆中已褪色模糊了的东西。布林克利评论道,“我一直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好,现在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曾经了解的、确实存在的、观察到的、访谈人们得到的东西,我竟然全忘记了。这着实让人惊讶——我居然这么记性差。”通过比较后来发生的事件,曾经有意义的信息会显得无关紧要或微不足道。由于布林克利是个记者,他要不断接收时事新闻,因此过去发生的事情离现在的报纸内容时间间隔越长,要将其留在记忆中的可能性越小。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能够评估早年发生的事情。行动能否产生新意义,与后续效应有关。有些参与者在故事中的份量会增加,而另外一些参与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份量减少。根据访谈时的情绪和时间状况,人们的记忆中会出现更为成熟、更有魅力的人物,也可能出现更为失落的人物。有过共同经历(如洪灾、飓风)的社区成员会交谈多年的经历,强化记忆。因为有必要获取相关第一手材料,口述史学家访谈“幸存者”,他们因为亲身经历而记忆深刻,甚至不是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事业有成。这些因素对记忆的形成及内容影响较大。访谈者要考虑受访者作为证人的可信度。受访者是否为第一手经历者抑或只是简单传递二手信息?是否因为过去的事情不再重要或者这些事件很琐碎不值得回忆而让受访者忘却了过去的很多事情?受访者在回忆过去的事情不同的感受点是什么?什么样的后续事件可能会让他们对过去重新思考、重新解释?他们的证词与那个时期的文献证据吻合度如何?他们如何解释其差异?这些考虑不能剥夺受访者提供证词的资格,但是尽可能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评估所记录信息的价值。直接参与者的记忆很丰富,历史研究者切不可忽略。访谈者必须意识到记忆的特性,善于利用各种方法处理记忆,意识到记忆的局限性,对记忆的价值持开放的态度。
(五)公共记忆
个体记忆与个体经历相关,而公共记忆代表了社会对过去的集体观念。社会记忆涉及符号和故事,根据对过去的回忆方式(或愿意回忆的方式)帮助社区界定和解释现有状况。回忆呈现的形式为游行(parade)、团聚(reunion)、复演(reenactment)、庆祝,或为纪念碑、地标,有助于用平和的心态看待战争或悲剧性事件,或愈合心灵创伤。史学家约翰·波德纳尔(John Bodnar)提及,这样的纪念形式具有政治含义,目的是“为了强调维持社会秩序和现有制度的希望”。由于人们经历事件的方式不同,持有不同的社会目标,因此会对公共记忆议题产生激烈争论。可预测到的是,人们会就纪念碑的设计、选址以及碑刻进行热烈的争论。以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为例。对于如何设计越战纪念碑人们争论不休:战争是否该打本来就争议挺多,现在如何塑造越战也争议很大。每个公共纪念碑都具有政治含义,有些纪念碑或纪念馆缺失了社会刻意忘记的人物和事件,同样具有政治含义。公共记忆也可能影响个人记忆,身处社区的人们参加了公共辩论,内化(接受)了某些特定的立场。访谈者应该意识到社区的集体信念,透过公共记忆触及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学者们认识到,人们记忆的内容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会去分析社区构建、使用集体记忆的方式以及传递给后代的信息。民俗学家阿力山德罗·波尔特利在意大利城镇特尔尼(Terni)进行了访谈,搜集了对钢铁工人鲁依基·特拉斯图里(Luigi Trastulli)之死的几个版本。特拉斯图里是一位21岁的钢铁工人,死于与警方的冲突。当时的报纸报道其死亡的时间是1949年,当年钢铁工人走出工厂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集会,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merican Treaty Organization)。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镇里的居民集体将故事改编,以史诗的形式呈现。一个接一个的受访者把特拉斯图里的死亡日期、语境从抗议加入北约的集会改变为四年后钢铁工人遭大规模解雇继而引发街头冲突。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把故事“弄错”了?波尔特利认为,社区居民不能接受特拉斯图里死于因短暂政治事件中的小冲突而引起的偶然枪击这个事实。因此,居民们将事件重置在一个涉及重大冲突事件中。故事经过改编,特拉斯图里之死有助于愈合社区的心灵创伤、教育下一代。
(六)个人记忆
老年学家将“生平史”称为年长者“生平评估”过程,口述史学家也谈及做“生平史”,其意思是全方位(full-scale)的自传式报道,允许受访者谈论从儿童时期到现在的整个生平。社会科学家可能专注于一系列更短的访谈,访谈对象是某社区或环境的成员,如商店工作人员。口述史学家将它们称为“情景式”(episodic)访谈。对刚刚分享共同经历的群体成员进行的短暂访谈可称为“情况报告”(debriefings)。进行生平访谈,通常意味着选择较少的受访者,对每位受访者花费更多时间,做多场访谈。生平史可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时间,讲述访谈者想得到的信息、受访者本人想告知的信息。口述史学家即便是从事主题导向性项目(subject-oriented project)研究,也应认真考虑扩大问题范围,尽可能详尽地记录每个受访者的生平。提问范围更广,则可建立记录关联性,而访谈范围更窄、更集中,则访谈者、受访者皆有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关联性。美国俄勒冈历史学会(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发起了联邦法院口述史研究,关注点是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院机构本身。言谈过程中,采取全传记的方法路线在研究法官任命方面确实特别有用。采取机构方法路线也可对法官任命提问,但是访谈者觉得在法官完整的生平语境中对提问进行回答,意义和重要性更强。第一批总统图书馆口述史研究项目几乎专注受访者与总统的关系或受访者在执政当局中的角色。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简短访谈。后来,部分图书馆从更深层次再次访谈了关键人物。在第二轮访谈中,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the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的口述史学家分别对劳伦斯·奥布莱恩(国会联络官和邮政局长)(congressional liaison and postmaster general)、约瑟夫·卡利法诺(总统国内事务特别助理)进行了36小时、64小时的访谈。虽然这个层次的深度访谈超出了大部分口述史学家的财政预算,但其他类似性质的访谈至少应在选择上有所偏重,以便让生平史访谈做得更完善。即便是个体研究者在访谈时也应有长远眼光,不能局限于即时利益。美国历史研究协会建议,“从实用范围看,访谈者应将询问扩展到眼前利益之外,这样访谈尽可能完整,对他人有利。”
(七)受访者的数量
试图提前计算受访者的精确数量会对口述史研究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抢着达到数字上的目标只会牺牲访谈深度以及处理信息的合理节奏。一旦访谈开始,人们会发现有的受访者说的要比其他受访者更多,更有见解,更具合作精神,记忆也更清晰。这些受访者值得多花费时间。因为年龄、身体状况或性情总体特征的原因,有些受访者说不了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一般要等到访谈开始的时候,访谈者才能决定受访者能否说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年纪偏大的受访者记忆力惊人,甚至精力也比别人更好。因此,初步的接触可以让访谈者更好地理解受访者的能力,进而测量出一场或一系列访谈需要准备多长时间。有位口述史学家花了不少人力和物力,组织了一队人马拍摄一场访谈的影音,结果很晚才发现受访者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口述史研究项目工作人员经常收到推荐,说当地某人善于讲故事(raconteur),什么主题都能说上一些,应该访谈他。这些人虽然非常愿意接受访谈,但讲来讲去都是那套固定不变的故事。同样,人们认为某人是某个事件最有名气的人物,但接受访谈时讲的尽是些断章取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最有潜力的受访者可能是不大知名的“二线人物”(secondary figure),他们对发生的事件有敏锐的观察且记忆清晰。如果不加以区别,所有人的访谈时间都一样长则失去了意义。同时要讲究灵活的工作方法,受访者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可不必花费大量时间,而那些信息贡献量大的受访者则可多花点时间。在设计项目、寻求资助的时候,安排好访谈的时间或场次,受访者的数量可不做要求。如果一个口述史研究项目预算经费可用于访谈100个小时,那么可在某位受访者身上花费一个小时,在下一位受访者身上可能花费更多时间,让每个受访者有足够的受访时间,充分发挥其能力。
(八)访谈时间长度
一场访谈通常最好控制在1.5-2个小时之内,这样访谈者和受访者都不会疲倦,但实际上访谈没有理想的时间长度。访谈时间的安排取决于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对项目的价值以及项目研究的是某人生平史还是其生平经历的小部分。如果访谈者需要长途跋涉去进行采访,就需提前估计访谈时长,但他们无法知道时间是否充裕。因此,如果经费预算允许的话,再跑一趟也是有必要的。要注意不要把访谈旅程安排过满,这样做只会让访谈者疲于奔命,也会造成受访者被频繁打断的现象。如果受访者仍然活跃在职业岗位上,那么他们可能对访谈时间有严格的限制,相比较而言,退休人员可能在时间上、形式上更加包容,甚至午饭或其他休息时间也可用来接受访谈。访谈者必须判断受访者何时会疲倦,思维不再清晰。如果访谈者工作开展得好的话,他们通常会发现在访谈情形中自己比受访者的压力更大,也就是说,访谈时间越长,他们的注意力、互动能力会越差。
(九)访谈的地点
访谈地点通常取决于受访者。有些人比较忙,访谈只能在办公室开展。这个地点存在受干扰和打扰的问题,如电话铃响、秘书请示、当天日程的其他事项等,这些都会分散受访者的注意力。同样,在受访者的家里,电话、配偶、孩子、宠物甚至电器的噪声都可能干扰访谈的进展。噪音太大,会使文字转换变得困难,也限制了录音最终为媒体或展览所使用。所以尽量在远离日常干扰的安静的地方开展访谈。如果不在项目办公室或受访者的办公室,则选择受访者不大常用的房间甚至只是房间一角。让受访者走出办公桌,坐在办公室另外一端的椅子上,或者坐在大厅附近的会议间里,甚至也可在餐桌边进行。访谈前可请求周边的人保持安静,如果房间有门则可关上。让受访者来和访谈者见面,可更好地控制设备,更好地放置录音机、摄像机或麦克风。与受访者打交道时,要留足时间架设好设备、携带电池或延长电线。通常需要多带些磁带,以备访谈持续的时间超出计划。在访谈前应对设备进行测试。因为访谈者要去访谈的地方越远,越要保证设备不出故障。墨菲规则在口述史研究中也适用,如果设备可能出故障,它就真地有可能出,而且刚好在需要的时候出故障。
(十)访谈的方式
一般来讲,口述史访谈最好一对一进行。这样,访谈者可以专注于一个受访者,其讲述的故事不至于受到打扰。然而,有时很难做到房间里只有受访者一个人,其配偶或年龄大的孩子可能会插话,对证词进行反驳、纠正或补充。虽然这样的打扰会让访谈受阻,但也有一定的好处,如提供遗忘的信息,支持信心不足的受访者。群体访谈会增加麻烦。面对群体,访谈者成了主持人,试图给每个人回答的机会,确保没有人垄断讨论。文字转换者也会有困难,可能难以辨别群体中谁在发言,所有的声音听起来很相像。但这个问题也可得到缓和,如在访谈过程中,别人(不是访谈者,访谈者很忙)可以安排发言顺序,让受访者按发言顺序发言。对群体发言进行录像也有助于辨别发言人。虽然操作起来困难不少,但群体访谈也可收集有用的信息。置身于群体中,受访者能记起独处时可能记不起的常见事件。同时,自我夸大也可得到压制。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曾做过几个成功的群体访谈,受访者是报道总统的记者以及肯尼迪总统任命的独立管理委员会的头目。群体访谈应主要视为个人访谈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口述史研究的访谈最好是一对一的关系,如果访谈者超过一个,就破坏了这种关系。人类学家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告诫,虽然让一群访谈者共同做某个访谈有时行得通,但是存在破坏性风险:“虽然这种研究技巧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它也可能转变为最糟糕的记者招待会,受访者要么完全受到恐吓要么感到被冒犯,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访谈者超过一个也有一定的好处。年轻学生缺乏经验显得紧张,常结伴或在家长、老师的陪同下进行访谈;新手访谈者同样可能搭档一个合伙人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有些研究项目完全由团队完成。团队成员中最好有人对具体主题较为精通,能够领头发问。但是在团队中,通常以某位访谈者为主要访谈者,负责提问大部分问题,吸引受访者的主要注意力。陪同访谈者尽量不要插话,除非首席访谈者遗漏了某问题,他们才可插话补充。
五、社区史和口述史的关联
广义上讲,社区是一群有共同身份的人在某一地域里所形成的一个集体,该身份基于地点、种族或民族群体、组织隶属(affiliation)或职业。某个群体可能因他的集体身份而感到自豪。口述史学家通过考察政治制度结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和职业构成帮助拓展传统意义的社区史。有些口述史研究项目通过访谈,了解被拆除的建筑物以及除了人们记忆之外各方面皆已消失的制度,试图保存已失去的社区。弗吉利亚州的伊万荷(Ivanhoe, Virginia)农村社区的居民发起了口述史研究项目,帮助挽救快速消失的历史,重现社区活力。他们的“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项目结合了外来研究者、教育者、基层社区群体和社区成员,共同设计项目,分析结果。他们的志愿者“研究小组”访谈了邮局工作人员、民团办公室(the Civil League Office)工作人员、街道行人、商店顾客和售货员,完成了53个访谈,收集了800多张照片。项目主任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提及,通过搜集社区历史的过程,“伊万荷社区尊重长者,重点记录了往事,从传统中寻求可创造性地运用到现实社会中的经验教训。”在内陆城市费城(Philadelphia),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启动了“发现社区史研究项目” (the Discovering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鼓励各小区的居民通过口述史、书稿和照片的方式记录他们的过去。项目工作人员想帮助并鼓励各小区完成此任务,而不是自己去做。一开始他们放映了幻灯片,把项目介绍给社区,但发现只是说明社区遗产的重要性不具备说服力。起初邻里们对分享回忆和照片表示迟疑,他们认为外人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平凡。随着项目工作人员不断造访,居民们最终认识到社区对于外界的重要性,社区成员可为记录社区历史出力。天普大学的经历说明,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是每个社区都反应相同。小区居民对项目反应的主要差异不是基于种族或阶级,而是近来历史和人口统计情况(demographics),也就是小区是否稳定、衰落还是在经历富人化移居(gentrification)。如果小区的组织(如市民协会、俱乐部,尤其是关照老人的机构)强大,愿意负责接触访谈者和受访者人选,“分配任务,检查进度,跟踪相关工作”,那么项目就能取得最大的成功。反之,如果社区缺乏这样影响力的组织或社区协会受到更紧迫问题的干扰,就很难说服其居民参与口述史研究项目。
六、口述史学家的资质
口述史一直以来是多学科所涉及的领域。虽然很多专业史学家做访谈,但历史学学位从来就非进入该领域的先决条件。有时专业素养较高的学者在访谈方面表现较差,而一般的社区工作人员如果在做口述史研究方面能得到适当训练,在建立融洽关系、拥有先前知识方面却具有优势。如法学专业的学生访谈过法官,女性煤矿工人成功访谈过其他女性煤矿工人,社区成员对其邻居进行过口述史访谈。在阿拉斯加州,一位肖像画艺术家对她的画画对象进行访谈,以进一步了解其性格,落实在画板上。在日本,一位内科医生在访谈正在快速消失渔村的年长病人。他的办公室俯视建在渔村河床上的一条公路,他把访谈发现写在书本上。“那条已经消失的河流,那个水边,曾经人声鼎沸,渔民们在收网,而船屋上的夫妻们在芦苇中等待太阳西下,这些情景不久前还有,可是那个时代、那个情景、那些人的生活气息却像幻影一样消失殆尽。”那位医生如此写道。他所搜集的口述史是对时光飞逝的见证。我们说,历史学博士学位对于口述史研究不是必需条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记录的任何事情都是口述史。美国口述史研究协会制定了原则、标准和指导路线,以提高所有口述史学家的意识和职业标准。人们要学习访谈技巧,严格区分可用的口述史和无用的口述史。口述史对于学术研究者和业余人士都有发展空间。只要经过合理的培训,参加了相关口述史课程、工作坊或对手册进行学习,任何人都能做出有用的口述史。很多学习参与者都参加过口述史研讨会,其中就有电台和影像纪录片制作人、博物馆馆长、档案馆人员、记者、老年学专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尽管他们的目标不一,但其访谈方法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果访谈进展顺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加拿大调查记者约翰·萨窝特斯基(John Sawatsky)如此评论,“但如果不是那么神奇,肯定事出有因。这是理性的活动,是一门技术,人人都能学习这些技术。”
访谈者和受访者都参与了口述史搜集,双方的作用都不应该弱化。从实用目的来讲,口述史学家应该是策划、准备、运作、加工和解释访谈的人。访谈者通过提问、跟踪受访者的回答以及提供名字、日期和其他常忘记的信息,参与访谈的给予和获得(give-and-take)过程。但是访谈者(尤其是从事生平史的访谈者)绝对不应忘记故事讲述的对象是谁。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一名称,认为其有被动之意,而喜欢使用显得更为积极的名称,如“线人”(informant)、“调查对象”(respondent)、“口述作者”(oral author)、“叙述者”(narrator),其中“叙述者”常为民俗学家(folklorist)和社会科学家所使用。“受访者”和“叙述者”两个术语使用权重较大,可从口述史研究论文的索引中加以反映。多个作者两个术语都使用。“受访者”的索引单可分为“……的放弃”“明显与……矛盾”“……的欺骗”“……的操控”“……提供的误导信息”。“叙述者”的索引术语包括“自由表达”“……的权利”“与研究者协商”。两个术语的角色相同,只是名称(nomenclature)不同。不过,这样的用词差异反映了口述史学家意识到访谈者——受访者关系不平等,可能会影响访谈。在起草评价指导路线时,美国口述史研究协会有意保留了“访谈者—受访者—访谈”的三角关系。不论使用什么术语,我们一定要记住,口述史是合力之作(joint product),由访谈、受访双方塑造而成。
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都使用访谈搜集信息,但不一定是相同类型的信息。这两种类型的研究者可放在一个刻度的两端:口述史学家专注记录受访者的个人经历,而民俗学家搜集社区的传统故事、歌曲和其他表现形式。口述史学家访谈一对夫妻时将丈夫和妻子分开,以便辨别夫妻各自的视角。民俗学家对故事讲述的方式和内容都感兴趣,更倾向于对夫妻进行集体访谈,夫妻一人开始讲故事,另外一人结束故事,这样可观察其相互影响(interplay)。民俗学家芭芭拉·阿伦(Barbara Allen)提及,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口述史资料来源看作原始数据矿,从中提取历史证据”,而民俗学家把更多关注放在辨认人们塑造叙事的模式上。尽管口述史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都对访谈感兴趣,但他们的不同目标,影响其研究方法。“关注田野调查”(field-oriented)的学科依靠参与者的观察,研究对象出现时甚至连笔记都不做,事后凭记忆做笔记。历史学家寻求实际发生事件的具体证据,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加以记录,而民俗学家、民族志学家、人类学家不大关注对事实的验证,他们将传说、民俗和其他故事同等看待,同样合情合理。语言学家更多关注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不是故事内容。尽管上述学科在分析、使用访谈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技巧也有交叉点,因此可以就一系列的社区、种族、移民事宜开展跨学科的口述史项目。
要做好口述史研究,首先确定自己的目标。不是所有的目标需要曾经尝试过,但是它们可以逐渐实现。比如,在确定了受访者人选后,口述史学家通常会首先访谈年长的、最重要的人物,同时根据经济状况、访谈者队伍规模、访谈后的处理能力,计划后来的访谈人物。在组织项目之后,可开始几个程序完善的深度访谈,然后对访谈信息进行处理。访谈的结果可以作为寻求进一步资助的佐证。通过集中几个访谈,项目组织者可以建立管理和文件处理模式,这一模式涉及准备、访谈以及处理等程序,可依据项目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一定要平衡好目标和可用的资源。鉴别处理好录音带,在访谈中处理好扩展方面的问题。
七、口述史的作用
历史学专家借助仍然健在的受访者回忆重构过去的物质文化(如家具装饰、工具、房屋结构、车辆和许多其他物体),确定这些物品如何使用、由谁使用、如何与社区更广的社会经济模式相适应。口述史研究项目帮助搜集历史建筑物中的日常生活细节,具体做法是访谈相关时代造访某房子的人员,造访者造访此屋时里面居住着某个家庭或某个著名人物。受访者的回忆可为过去的黑白照片增色,提供语境,这样文献证据不至于粗略不完备。在大规模再开发时期为了试图挽救圣地亚哥的古老建筑,圣地亚哥市区项目(the Downtown San Diego Project)发现官方的记录有空缺,而此时只有口述史研究才能填补。于是项目成员访谈了建筑工、拆迁公司雇员以便了解推土机(bulldozer)、反铲挖土机(backhoe)在某些地区的施工情况。加利福利亚历史保存办公室(California Offic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呼吁对该州的建筑师、工程师进行访谈,鼓励访谈建筑行业人员、市政工程网(utility networks)开发人员、交通运输规划者、桥梁建筑工、地方政府开发机构的官员。在国家层面,1966年的国家历史保存法(the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of 1966)要求联邦机构考虑像公路建设、水坝、水库、机场和公园类的得到联邦资助的项目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影响程度如何。为了贯彻这一法令,文化资源管理(culture resource management)队伍从考古学、建筑设计史、民俗学、口述史等视角,探讨城市规划、资源保护(resource conservation)、公共工程项目以及商业开发。考古学家在得克萨斯州的伊里昂县(Irion County, Texas)参与文化资源管理队伍工作时,在石灰脱落处发掘了成百上千看起来像史前的岩画(petroglyph)。但是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刻在岩画上的名字——布尔特·斯马利(Burt Smalley),标注的时间为1921年,那个时候,斯马利已去世。通过对健在的家庭成员和社区中经历过过去事件的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谜底终于解开。这些访谈塑造了一幅终生在他的农场附近的岩石边凿刻岩画的隐士(recluse)肖像。口述史访谈帮助文化资源管理项目确定未标注的坟墓地址、废弃的农舍以及未标注名字的佃农(sharecropper)。访谈有助于重构农民的生活模式,如院落和房子、花园、农田、水井、粮仓、户外厕所(privies)的布局(layout)。“通过口述史研究,草原的一块地基证实曾经是汉斯佛德县(Hansford County)的一个单间校舍——帕罗杜罗校舍(Palo Duro Schoolhouse)”,在文化资源管理队伍工作的口述史学家丹·尤特利(Dan Utley)认为,“口述史研究可将似乎不关联的文物(如T型信号传播器、散落的砖块、焊接的金属桶)转变为灌溉系统,抽取康卓河(Concho River)的水到河堤上,通过沟渠灌溉了20世纪50年代龟裂的棉田。”
在暮年之时,记者亨利·费尔赖(Henry Fairlie)评论,“人们年事已高时,爱搞个阁楼,上面堆了些货物,闲暇时刻可搜寻观察往日情形和盛景,经历了那么多起起落落心里感到欣慰。”对年长者的访谈目标是搜集回忆加以记录,但是年长者也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收获。亚里士多德提到,老年人“经常谈论过去,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回忆”。有些家庭成员可能嘲讽他们的年长亲戚“仍然生活在过去”,但是正如老年学家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所说,老年人在回忆过程中自然经历了生平评估期。在整体评估(take stock of)人生时,他们可揭示压抑已久的信息,这些信息甚至家人之前都不知道。口述史学家经常评论许多老年人带着渴望之心同意接受访谈。在谈论过去的时候,这些老年人似乎回到年轻时代。他们行动充满活力,将知识丰富的访谈者当作自己的同龄人。久而久之,这些老人的子孙再次听到这些故事,不再对老人讲述的内容表示疑问,这时受访者的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已去世。民俗学家帕特里克·缪兰(Patrick Mullen)认为,“好像老年人在等待某人过来问及这些故事,因此民俗学家最好认真倾听。”亨利·格拉西(Henry Classie)也提到,“老年故事讲述着在怀旧的荒原上并没有迷失道路,他们在社区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保存了智慧,解决了争端,创造了娱乐,谈论了文化。如果不是他们,当地人可能无法发现自己。”从事回忆理疗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参与这一项目的养老院老人自尊心增加了,身体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位回忆理疗师提到,在初期几场访谈中,她的受访者勾着背坐在轮椅上,低着头,说话时几乎没有眼神接触。随着访谈增多,受访者对他自己的回忆能力感觉更为自信,更相信访谈者会倾听他的故事。“他的背挺直了,眼睛打量着他的听众眼睛,脸上更有活力了。”她发现这样的身体语言变化在参与访谈理疗的男女受访者身上都很典型,访谈过程将老年人带出了生活的“壳”,使其充满活力。养老院鼓励、有时还雇佣口述史学家记录他们的回忆。堪萨斯州威奇塔(Wichita, Kansas)的拉克斯菲尔德园区退休社区(Larksfield Place retirement community)与堪萨斯州立大学威奇塔、恩波利亚分校(Wichita State University and Emporia State University)合作创立了口述史研究项目,搜集生平故事,鼓励社区居民使用那些访谈作为其他自传项目的起点。纽约新海德公园(New Hyde Park, New York)的帕克犹太人老年医学研究院(Parker Jewish Geriatric Institute)将社区居民的访谈进行录像。这些访谈给家庭提供了“珍藏故事的永恒记录”,而且对于故事讲述者也有理疗价值,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经历过程中对自己和人生有了更为积极的看法。“这让他们更确信生活有价值有贡献”,研究院理疗康乐(therapeutic recreation)主任艾迪丝·沙皮洛(Edith Shapiro)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其他人看来,口述史访谈的经历可让他们将长期压抑的感情发泄出来。罗纳尔多·马塞洛(Ronald Marcello)访谈了二战期间当过战俘的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马塞洛说,“访谈的一个附加产品(意外收获)是对他们的理疗价值”,许多战俘受到了妻子和子女的鼓励,参与了录音。“有些受访者对我说,要是1946年我可不愿意和你说这些,毕竟战争伤疤才结不久。”然而,口述史学家应该注意,回忆痛苦的经历除了理疗效应也可能产生创伤效应。例如,访谈过二战受害者的人们提及受访者表示有义务给未来子孙们留下记录,但访谈让受害者噩梦重现。
任何经历了共同困难的群体都能通过口述史访谈去记录记忆从而受益。女矿工口述史研究项目记录了煤矿女工的生平。20世纪80年代项目组开始搜集访谈,那时女矿工们正是人生危机时刻,失业率高,矿工工会在为矿工的生存而斗争。许多女工处于无限期失业状态,面临惨淡的经济前景。在这一困难时期,女矿工们能够用口述史研究项目“作为情感支持的手段”是十分难得的。这个项目利用与女矿工有关的个人回忆、书写、艺术品和其他历史材料,进行录像访谈。根据项目主任玛拉特·摩尔(Marat Moore)所说,访谈有助于为女矿工建立“自信的语境”,比如“我们的问题涉及日常生活如何,是否在磨难后继续鼓足勇气生活,还有采矿和其他高技术、高报酬产业任何有助于自信行动的事件。”
八、口述史的情感研究方法
在研究口述史中的情感问题上,Fussel(7)Susan R .Fussel,The Verbal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提出了“语义法”(semantic approach)、“语言和非语言综合研究法”“比喻语言研究法”。下文将做简单阐述。
(一)语义法
假设:(1)情感词汇(emotion words)的意义对于心理学非常重要,心理学家需要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情感概念。(2)语言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个人心灵(individual psyche)的构成具有形成性(formative)影响。正如杰罗姆·布鲁内(Jerome Bruner)(1990)所言,“我们最初学习了民俗心理学,边学边用,然后将其用于共同生活中的人际交往”。(3)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告诫,“哲学家(人们认为心理学家也如此)只需要避开自己的语言习惯去理解其他语言。”欧洲心理学理论用欧洲语言的属性建立一些基本的假设,这实际上不明智。为了避开这种问题,众多语言学家倾力构造跨文化语义学,威尔茨比卡(Wierzbicka)主张使用“自然语义元语言”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对情感意义进行跨文化分析。
具体操作方法:(1)确立“语义基本单位”(semantic primes),存在于所有或大部分语言中,如:某人、人们、好、坏、认为、知道、想、感觉、做、发生。应该指出,所有的语言都有表达“好”的词汇,但是人们对于“好”的看法却可能因文化而有差异。确立各种语言的语义基本单位的“表现指数”(exponent),会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是二级意义或一词多义)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如,英语的“想”(want)可表示“缺乏、亟需”的意思,如“地板需要清理干净”(The floor wants cleaning),与“我想和您说话”的“想”意义有所出入。威尔茨比卡确立了大约60-65个“语义基本单位”。(2)设定一套普遍的基本意义(primitive meaning)组合模式,适合各语言同一语义概念的解析,此套模式与典型的认知情景(prototypical cognitive scenario)相关。比如,“伤心”(sadness)与“想要的目标失去了” 的情形相关,即与“损失”(loss)相关。相比较而言,“不高兴、郁闷”(unhappiness)需要体验者的某种真实思想,意味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更为负面的评价,比“伤心”更具有个人色彩,持续时间较长。据此,“自然语义元语言”也可称为“情感语义学”(emotion semantics)。(3)公式化说明基本意义组合模式,然后对比不同的语言进行解析。(4)通过情感语义模式的分析且对比其在各种语言中的应用,提出“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加以说明,即“文化语用学”(cultural pragmatics)视野,如有些文化认为别人说话时自己却沉默是尴尬的行为,而另外一些文化则刚好意见相反。例如,“愤慨”(outrage)的意义组合模式如下:
(a)某人因为想某事所以感受某事
(b)有时有人想
(c)我现在知道: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人们身上
(d)因为其他某些人做了很糟糕的事情
(e)我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做这种事
(f)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g)因为这事我想做点什么
(h)当此人如此想的时候,此人感受到某种糟糕的事情
(i)某人如此感受某事
(j)因为某人如此思考某事
对比“惊骇、胆寒的”(appalled)和“愤慨的”(outraged),两者反映的态度差异明显,试看下例:
When allegations of physical violence emanate from a classroom, parents are outraged, the community appalled.
(当传来教室里发生的身体暴力的指控时,家长们很“愤慨”,社会感到“惊骇”)
从某种意义上讲,“愤慨的”有点类似“义愤填膺的”(indignant),情感感受者认为某人做了“糟糕、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采取一种既不接受也是抗议的态度(即沿着“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的路线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主动、目标导向的(“因为这事我想做点什么”)。此外,“愤慨”隐含了“某人做了很糟糕的事情”的意思,同时隐含了“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的意思,这也说明了此词所包含的道德份量较大。此外,“愤慨”一词具有区分社会品质的作用:坏人代表某个群体,受害者是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员。比如,如果我的孩子受到虐待,我会“生气”(angry),甚至“暴怒”(furious),但不是“愤慨”;如果我发现某些老师虐待我孩子所在学校的孩子,我确实会感到“愤慨”。上述例子说明:家长感觉对自己的孩子要负责,他们想对此情形做点什么,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得这样做;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们的反应更像“旁观者”(onlooker),感到“震惊”(horrified)、“惊骇”,但不是“愤慨”。这说明我们不应假定“惊骇的”适合于“因为这事我想做点什么”。当然,上述解释是否在各语言中都通用,没有任何差异,还需要通过“文化脚本”加以验证。但“自然语义元语言”是解析口述传播中情感意义的一种有趣、程序严谨、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方法。
(二)语言和非语言综合研究法
语言与非语言综合研究法分为三种具体的方法:表达性(expressive)研究法(将语言看作思想和情感的媒介)、传统性(conventional)研究法(将交际看作根据社会传统规则和程序合作进行的游戏)、修辞(rhetorical)研究法(将交际看作社会自我与情形的创造和协商)。
1.表达性研究法
定义:情感是中心,表达是情感的副产品或表现。这一定义隐含一个隐喻:情感是从容器(身体)中压出来或泄漏出来的。据此,情感可以表达(expressed)、克制(repressed)、抑制(suppressed),或泄漏、迸发、倾倒出来(就像液体从容器中流淌出来一样)。这一隐喻说明情感有三种形式:好、中性(neutral)、坏。因为情感应该“释放”或“发泄”而不是“煨炖”(stewed)或“锁住”,所以这种表达可以视为好的甚至必要的。假如情感不能完全遏制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泄漏,相关的表达则可能是中性的。如果情感要“迸发”或“爆炸”,则可能是坏的。表达的目的是释放情感,所以唯一需要掌握的技术就是遏制或释放适量的情感(“情感水龙头”需要性能良好)。
操作模式与方法:(1)情感分为不同类型(category),就像容器中的物质一样,如“热”(愤怒)、“温暖”(爱)、“冷”(害怕)。情感有可能为混合型(blends),但一般纯“物质”状态的较多。最好研究纯“物质”状态,混合型(如“胆怯性愤怒”)多为其衍生产品(derivative)。总的来说,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暗示”(cue),如“愤怒的暗示”“快乐的暗示”,但同一暗示也可能在共同的“维度”(dimension)上有差异,如“温暖的一瞥”“冷漠的一瞥”。(2)情感通过眼神、声音、词语和身体运动表现出来。一种模态的情感表达可促使另外一种模态的情感表达,手势可促进非情感信息的语言编码。实际上,非语言的暗示更直接表达了情感,因而更为可靠。(3)典型的“表达性”研究范式是鉴别情感类型(自变量),然后确定相关表达(可变量)。形象来说,将不同的“物质”放于“容器”中,发现“释放”的东西。这样研究法的操作困难有四点:一是难以鉴别单一的情感;二是难以测量表达(特别是几种同时出现的身体或/和语言表达);三是情感和表达存在重叠现象;四是很难确定自然的语境(有些情感和表达不一定出现在自然语境中,语境中出现的情感和表达未必自然)。
2.传统性研究法
定义:交际是中心,情感是信息的内容。这一定义隐含一个隐喻:交际就是“接招”(playing catch)或“打靶”(hitting the target)。某人发送情感,另外一个人要么“接住”要么“未接住”。也许发话者将信息表达清楚了,但受众“跑垒跑偏了”(off base)。交际的目标是精准交际,需要发话者、受话者具有一定的沟通技能。
操作模式与方法:(1)情感可分为不同类型(如“害怕”“羞耻”“爱”)或维度(如“积极/消极”)。(2)暗示种类可分为面部的、声音的、身体的、语言的,交际渠道(channel)分为语言的、语言+声音的、综合渠道。(3)传统性研究法基本上属于实验型研究法,自变量为暗示和渠道(需控制),可变量为精确度(需测量)。本操作模式要求观察者能鉴别出情感暗示,研究者能假定情感和暗示的某种关联(需要预先测试或提问)。(4)大部分传统性研究法为多模态或多渠道研究,比较各种暗示和渠道以发现集合性所“携带”的意义。分为三种具体模式:增加性模式(additive model)(如:基于面部表情的精准度<基于面部表情+声音的精准度<基于面部表情+声音+语言的精准度)、平均性模式(averaging model)(如:积极面部表情+消极声音=中性信息)、主要暗示模式(dominant cue model)(如:视觉暗示比声音暗示携带的意义更多)。存在的问题是很难量化各种表达或暗示所占的比例,因为如此相关的结论差异很大,研究结果极其复杂。
3.修辞研究法
定义:社会情形(包括交际双方的关系)是中心,情感交际是协商情形的方式,情感、交际协同作用以实现社会目标。社会目标具有多样性、无限性的特点,常见的有三种: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 的管理(如:显得坚强、和蔼、真挚)、自我和他人关系的管理(如:传递温暖)、他人情感的管理(如:安慰、恶化、激怒)。在这一模式中,可牺牲表达和精准度目标以实现其他社会目标,如:为了不伤害别人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使用模糊表达以避免站位。表达性研究法强调发送情感信息,传统性研究法强调精准接收情感信息,而修辞性研究法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都很重要。
操作模式与方法:(1)最为综合的模式是过程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情感过程由下列成分组成:促使(诱发)事件、评价过程、生理变化、行动准备(或趋势)、调节(regulation)过程。(2)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有可能需要传递,但不一定是典型或必要的。操作问题是传递的未必是语言表达的情感,而是情感过程的两个关键成分,即行动准备状态、诱发事件。其实,交际的成功在于发话者与受话者的目标是否一致。
有的学者主张症状(symptoms)(有点接近“表达”)、符号(symbols)(有点接近“暗示”)和呼吁(appeals)(有点接近“修辞”)的一体化方法,用于研究口述传播中的情感。
(三)比喻语言研究法
基本理据:使用比喻性(figurative)语言的目的是出于礼貌,避免对所传递信息的责任,表达字面语言无法传递的思想,更为简练、生动地表达思维。在叙事过程中,比喻可使读者了解叙述者复杂的情感状态,唤起读者对主人公的情感,甚至与其建立互动关系。
操作模式与方法:(1)认知科学相关实验说明,发话者通过语言表述交际意图,受话者能清晰地明白该意图,但在交际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不确定的非言语意义和感情。(2)隐喻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相比字面语言更能创造交际双方的亲密感(sense of intimacy)。这种亲密感是一种可通过美感语言共享的情感,其意义难以从内容形式上加以描述。(3)我们不能要求所表达的情感信息必须在发话者头脑中清晰地罗列出来,也不能让它有意识地存在。这意味着受话者可从多种程度上推测发话者的情感状态,即发话者的“认知内容”(cognitive content)无需清晰表述。(4)在许多种类的话语情形(如政治辩论)中,比喻性语言可用来表达、唤起情感。在1991年1月的美国参议院辩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力图阐述自己的立场,其中有位共和党参议员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比作“地缘政治的贪食者”(geopolitical glutton)以博取眼球,唤起情感上的回应。该比喻可唤起具体的形象、联想或情感。(5)除了隐喻,人们还可使用反讽(irony)等修辞性、比喻性语言表达幽默、批评,唤起受众的情感。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情感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概念化的,通过基于体验(grounded in embodied experience)的隐喻加以表达,如“愤怒是容器中加热的液体”(anger is heated fluid in a container)。实验说明,情感一般可从事件序列的模式加以理解,包括“先前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s)、“行为反应”(behavioral responses)、“自控程序”(self-control procedures)。
可见,对比喻性语言表达情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会有较大的收获,对于口述传播的情感研究大有裨益。操作实践的成功在于研究者对于情感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有充分的认识,需要结合比喻性语言使用者的个人、集体背景以及相关文化、历史状况加以考虑其传递的情感信息。
九、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其口述史研究意义重大。李生福(8)李生福:《云南彝族神话创世史诗同源异流浅析》,《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探讨了云南彝族创世史诗同源异流,认为彝族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是集体创作、口头流传造成同一内容同一作品出现多种变异文体的情况。这说明,口述传播的方式、路径、主体与客体对于口述产品的现状影响较大,研究口述过程就是研究口述史,是历史文化的重要建构方式,也是其重要体现。下文我们先以贵州雷山籍苗族学者的口述史研究为例,探讨口述史研究理论的具体应用情况。贵州雷山籍苗学专家人才辈出,张晓、李锦平、李天翼、李国章等学者尤为突出。现就几位专家的研究做简单地回顾。
张晓教授对贵州雷山西江苗寨妇女的口述传播史研究采取了田野调查、访谈的方法,加之她本身是西江苗寨苗族的后代,对于西江妇女的口述传播史研究可谓深入细致,饱含民族情感。在《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9)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的第五章,张晓提及“(龙玉琼)丈夫本来是孩子的父亲,作母亲的她竟然难于向他启齿生孩子的事情。而这种害羞情感的力量竟然达到置生死于不顾的地步”“后来我的访谈印证了龙玉琼所说的是事实,也证实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西江妇女对夫妻生活话题有着强烈的羞耻感,包括一切与其有关的事情,诸如生孩子之类,因为孩子是该行为的直接结果”。作者探讨了西江男人、女人羞于谈论男女问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江人来说,绝大多数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祖祖辈辈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他们固定的社会关系网。这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社会;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只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妇女的角色转换便是在这个‘家庭’的转换过程中完成的。问题就在这里,妇女从原来大家庭的角色突然变成小家庭女性的角色,这才使她对她的丈夫,采取回避的态度并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同样,作为男性也是,由于妻子的突然到来,使原来的他突然有了男女意识,被推向了小家庭男性的角色,他仿佛觉得大家都在异样地看着他,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突然照射在他的身上,使他难堪,不自然起来。”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的观点可佐证西江男女对夫妻生活话题的羞耻感。张晓指出,“既然人的两囗行为对社会具有两重性,那么社会的绵续和稳定就取决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强弱和措施的取舍又取决于具体社会组织结构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西江的实际情况,作者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夫妻生活话题禁忌的历史成因,“西江社会为了维护其内部的父系血统和社会稳定,从观念上和法规上都给‘囗’树立起一个丑恶的形象。它要求西江人,尤其是妇女应清纯、端庄、稳重。这些行为规范必然导致西江妇女一方面外表上要做得对囗很害羞、很害怕,疏远、冷淡男人;另一方面自己也真的相信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就必然导致了一个结果:对男人必须疏远。这就是西江女人对男人的看法和态度。”
张晓教授对西江妇女的访谈反映了苗族女性的“娘家”社会隐喻背后的深刻社会、家庭与情感含义。第五章(第100页)的访谈节选如下:
我问:“为什么我们苗家新娘结婚了还回娘家住?”
我母亲:“就是因为要成别人家的人了,没有机会回娘家住了。要趁早多住些日子,一旦生了孩子,就一辈子住别人家了。”
龙玉琼:“回家来休息一些日子,以后到别人家就很辛苦了。在自己家才可以自由自在。出嫁回娘家,娘家也不叫干活了(龙的丈夫插话:‘回来时,就抓紧做针线,绣背带’)有的做了几床背带才去。”
作者指出,“如果新娘不赖在娘家,不经过夫家三番五次来请,爽爽快快地、三天两头地往夫家跑,人家必定会认为她没有身价。因此,在娘家赖得越久,越显得她纯洁、稳重。”可见,“娘家”在这里是个社会隐喻,是苗族妇女家庭抚养、社会氛围影响的结果。从语义的角度看,“娘家”的结构如下:
(1)“娘家”是女性的出生地,可以在此回避害怕,可以在此为下一步的家庭、社会挑战而做准备;
(2)“娘家”是女性的情感原归属地,结婚意味着进入下一个情感归属地,苗族女性难以割舍原归属地,是重情重义的表现,是家庭、社会因素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表现;
(3)“娘家”一词在苗族女性口中饱含了情感,是家庭传承的结果,影响其人生和社会交往,代代相传,是中华美德的体现;
(4)透过“娘家”这一社会隐喻,我们可以解读苗族家庭、社会关系及其伦理道德。
应该说,张晓教授的苗族女性口述史研究遵循了国际学术界的口述传播史研究规范。可贵的是,她的研究是本土化的突出表现,通过调研、访谈,清晰地勾勒了苗族妇女的口述传播史的社会发生背景、家庭与社会生成机制、话语表现方式、女性性格刻画等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余未人女士如此评论《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回头看,张晓的这本《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当是我国第一本用人类学、民族学视点来写作出版的口述历史及研究著作。这可以看出张晓在二十多年前,学术的起步就挺高,眼界开阔;她身在大山中,却初具了写作这本书的最佳条件,当是水到渠成,不须疑虑。”(10)余未人:《一位苗族女性的学术视野》,https://www.sohu.com/a/328635914-488491。张晓教授的苗族口述史研究范围广泛,据《张晓知青回忆》(11)与张晓教授微信采访,2020-03-30。,“2018年1月已经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苗族移民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更名为《美国苗族移民口述史》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见,海内外苗族的口述传播史都是她的研究内容。据此,其研究成果可视为苗族族谱、苗族口述传播史、苗族社会概况的“视窗”。Abrams(12)Lynn Abrams,Oral History Theory,P.19-25,154.提及口述史的几大特点:口头文体性(orality)、叙事性(narrative)、表演性(performance)、主体性(subjectivity)、记忆性(memory)、可变性(mutability)、合作性(collaboration),认为口述访谈最大的特点是对受访者的“赋权”(empowerment)。这些理论阐述在张晓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苗族村寨走出来的她能以口头交流方式和苗族乡亲交流,从口述传播中彰显叙事者的主体性、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对话性、苗族同胞的文化自豪感与家国情怀。一个个苗族妇女的形象既是文化、历史的缩影与体现,也是张晓个人的写照,在“赋权”给受访的苗族妇女的同时,也给访谈者本人“赋权”。
李锦平教授在苗族语言与文化、民间文学经典作品、苗族家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口传家谱调查研究”)等方面颇有研究,他还主持贵州省民宗委重大项目“苗汉英大辞典”东部、中部、西部、滇东北次方言四种苗语方言的辞典编撰工作,其中涉及苗族口述与口述传播史的研究。苗语原先没有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助字母得以创建,李锦平在苗语书面和口头文字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如,中部苗语的yeuf voud可指“姑爷”“姑父”“姐夫/妹夫”,yeuf zid可指“岳父”“大姨夫”,yeuf hluak可指“姨父”“妹夫”,称谓的多义性、多指性,反映了苗族称谓的独特性,对于苗族相关故事的传承研究无疑具有帮助。在《苗族语言与文化》(13)李锦平:《苗族语言与文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44-245页。一书中,他指出,苗名并不是随意乱取的,往往要按出生的年份、日子、时辰、季节、排行,按出生时家里或左邻右舍抑或寨上发生的事件,按苗族的传统习俗,按父母及家人的某种良好愿望来取名的。他还指出,苗族和汉族一样,认为龙是吉祥之物,龙年、龙日吉利,龙时就更吉利,可谓吉日良辰,苗族更喜欢用Xenx(辰)、Vongx(龙)作苗名。李锦平的研究从语义、文化语言学角度解读了苗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说明了苗族词汇表达在民族文化代际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Vansina(14)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P.94.指出,口述传播的信息是社会产品,具有“社会表象”(social surface)的特征。李锦平在研究中将称谓与社会亲属关系挂钩,从家庭层面扩展到家族乃至整个苗族社区,给予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词汇语义解读,在语义解读中又赋予了社会隐喻与家庭、社会情感性,读者可通过他的研究将“社会表象”与“语言表象”有机结合起来。
李锦平(15)李锦平:《苗族口传家谱调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研究报告)(未出版)(项目批准号12BMZ033),2018年。的苗族口传家谱研究涉及中部、西部、东部苗族,分为“人囗共祖”的苗族祖先谱系、“蝴蝶妈妈”与苗族祖先谱系、“亚鲁王”与苗族祖先谱系三大类型,认为口传家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祭祀、婚姻制度的建构、继嗣制度的确认、家庭伦理和社会规范四个方面。李锦平指出:由于苗族没有成体系的文字,所以苗族人民在追溯祖先时,除采用说唱形式记述以外,还采用独特的“父子连名制”来追溯祖先;苗族的子父连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子名在前,父名在后。”连名规律为:BA→CB→DC→ED→FE……。苗族口传家谱反映的就是苗族文化口述传播史,包含了丰富深厚的家国情怀、祖先尊崇思想,在语言上通过形式与语义加以体现。
另一位雷山籍苗学专家李国章先生对雷公山苗族传统文化做了深刻的研究。在其著作《雷公山苗族传统文化》(16)李国章:《雷公山苗族传统文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页。一书中,通过词汇含义与词汇隐喻进行表达,他表示:
苗语称燕子为bad lind(“摆利”)、bad lius(“摆柳”),liux是lind的转音,故liux自称是燕子氏族。但对于凤凰,苗族与汉族不同,并非是指云鸟,而是指锦鸡。苗族锦鸡即凤凰,凤凰亦锦鸡。鸟氏族中有以锦鸡为氏族尊崇的。现苗族中自称为Dail Nes(“德闹”)、Ghab Nes(“敢闹”)的,就是锦鸡氏族的后裔之一。
李国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亲身经历、观察、思考、比较的方法呈现中部苗族文化的多姿多彩,体现了词汇含义与隐喻在苗族口述中的作用,进而展现苗族文化传承的独特性与魅力。
李天翼是雷山籍苗学研究的后起之秀,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所倡导的“西江模式”研究引起了学界、业界的极大关注,其学术核心观点在于“西江模式”是民族文化合理利用和成功开发的有效组织方式。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西江模式”研究》,出版了《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2018)(17)李天翼主编:《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和其父亲李锦平先生一样,生在雷山西江苗寨,从小沐浴着地道的苗族文化,对雷公山的苗族文化了如指掌,深谙口述传播在苗族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李天翼参与了李锦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口传家谱调查研究”,对苗族口述传播史有较好的田野调查与理论反思。
贵州雷山籍苗学专家是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其出版和发表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主持并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和影响力来看,无疑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张晓教授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与重大招标项目以苗学为研究主题,涉及海内外苗族,拼构了本土苗族与离散苗族的文化共通性,在建构文化共通性与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口述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苗族古歌、史诗、理词、神话皆以口头叙事为载体,传承了中华文化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口述传播史。
李锦平、李天翼教授和张晓教授的研究虽然内容侧重点不同,但是都讴歌了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传统民族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继承了具有中华美德的苗族先民在昔日的蛮荒之地创造的灿烂织锦文化,既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贡献,又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正如王富文教授(18)王富文:《海外苗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所说:“我觉得苗族的历史不应光属于苗族, 同时也是与其他民族共享的, 其他民族也可以对苗族历史进行解析。”王富文教授对苗族历史解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认为写苗族的历史, 就应该由苗族自己去把握, 我们说身份认同跟我们的历史相关, 需要在挽救历史方面发出声音, 当然我们应该听取不同人对历史的看法,特别是听取过去被忽视的声音, 这些声音可能跟精英分子在书本上写完全不同。”这似乎有点矛盾,但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很有道理。贵州雷山籍苗学专家在对苗族口述传播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是中部苗语地区苗族口述传播史研究的主力军,但如果能和其他地区的苗学专家甚至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学者合作,成绩可能更大、更突出。兰东兴(19)兰东兴:《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对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五论”思想(即“空间论”“进程论”“符号论”“客体论”“主体论”),对于解析口述传播的演变、文化环境、主观和客观因素、角色类型和功能具有指导作用。如,口述传播可反映生活的内部结构—血缘家庭传播、地缘村社传播、业缘师徒传播、特定习俗传播。兰教授的观点可以为张晓、李锦平教授的研究提供较为充分的理论解析,是具体可操作的。
贵州雷山籍苗学专家还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多元化。Ritchie(20)Donald 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认为,博物馆和多媒体展示以及艺术展示、互联网站、电台节目、儿童、教师教育材料是互联网时代口述史的重要应用路径。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做得不够,甚至还没有起步。如能做到这点,世居民族口述传播史就可置身于更大的中华文化语境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一员。
上文提及兰东兴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口述史的研究。兰东兴(21)兰东兴:《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第122,127-129页。认为:
历史上许多官员或学者的著作只是作为他者在对少数民族的口述传播进行阐释,他们立足于自己的语言特征,从自己的心理结构出发只是对少数民族的口述传播语言符号做纯粹的语法分析,没有把语言放在叙述结构之中和当时的传播环境之中,没有从整体与其他部分的内在关系之中来综合分析。他们对世居少数民族的口述传播理解得过于简单,只看到了一首情歌的语言特征和意境,没有考虑到文本特征,没有对歌唱的环境、歌唱的对象、歌唱的旋律以及运用等其他非语言符号进行深度考察。今天的有些学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些口述传播理解得过于复杂,对一部神话、一首古歌,按照繁琐的学术路径探幽发微,努力寻找当地世居少数民族闻所未闻的“学术见解”或“社会现象”。其实,神话就是西南世居少数民族心中的历史,歌唱古歌就是对祖先的赞美和对历史的回顾。
如此看来,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史的时候,应该考虑“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关系。按照民族志学家的做法,“主位”为研究对象,而“客位”为研究者。对口述中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解读,重点应放在“客位”身上。深入访谈,让世居少数民族同胞说出自己的历史、传说、神话,讲述自己的民族情感,才是真正意义地对其口述史进行研究。“灾难”一词,在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语言中分为“光明的灾难”和“黑暗的灾难”;居都仡佬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用“放牛郎山歌”间接告知人们躲避匪患;苗族祭辞中大量运用隐喻,其含义只有祭师明白,俗称“囗囗囗”。苗族古歌在很多苗学学者看来是一种叙事诗,所以“苗族古歌”的英译可以是Hmong (Miao) Epics。叙事诗是一种口述活动,是对历史的叙述。龙仙艳(22)龙仙艳:《苗族古歌唱者与听者探析》,《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认为,苗族古歌的歌唱者较为多样,如巴兑、东郎、褒牧、理老、歌师,接受者呈现多元化特点,既有苗族民众,还有世间生物。
罗正副、肖唐金(23)Luo Zhengfu and Xiao Tangjin,“Song Ning drum ritual : practice memory of the Buyi people”In Khun Eng Kuah and Zhaohui Liu (e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7,P.74-91.研究了贵州镇宁布依族的“送宁”实践记忆。该仪式在元宵节举行。在“送宁”过程中,铜鼓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铜鼓的储存家庭是德高望重的,非常重视仪式。参加“送宁”的村民也是受大家公认、推荐的,在敲锣打鼓、唢呐吹奏的音乐中,在走家串户的路途中,人们互送祝福,通过“实践”传承民族记忆。这是一种语言与非语言结合的口述传播,集体参与、个人感受结合得非常完美。在交谈过程中,传承了民族历史、家族来龙去脉,也厚植了家族、民族、社区情怀。“送宁”作为一种仪式表演,能唤起集体记忆并使之不断出现,按照杜尔凯姆(24)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Trans.) Lin, Z. and Peng, S. Y,Beijing: The Central University Press,1999,P.230.的观点来讲,这是社区而不是个人“言语”,具有具体、个人体验(personalized)的特点。
综上所述,口述史的研究具体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研究点多样性和研究方法丰富性的特点。另外,访谈者、受访者特点不一,也说明将西方的口述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史研究时,应注意我国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即家国情怀浓烈,对祖先感恩报德,对后人寄予厚望,生于斯死于斯,故土感情强烈,愿意和汉族分享自己的心理感受和历史文化,把汉族同胞看成大家庭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少数民族的口述传播、口述史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结语
本文梳理的口述史研究框架涵盖理论与操作层面。借助中外学者的观点,我们陈述了口述史涉及的研究者、参与者、口述内容、口述意义、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通过对口述史在中国不同地域世居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口述史理论的本地化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的口述史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本质,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