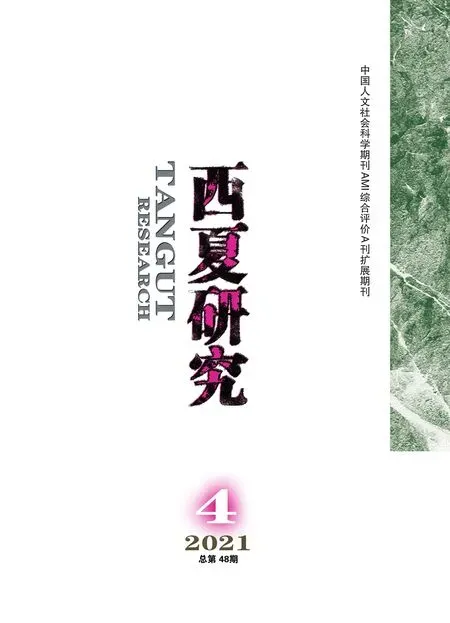再论西夏榷酤制度
——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分析
□王思贤
榷酤制度是西夏榷禁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西夏榷酤制度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关于西夏榷酤制度,史料主要集中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卷十七《库局分转派门》、《物离库门》和卷十八《杂曲门》中,其他散见于黑水城文献社会经济文书部分,由于材料缺乏,相关的论述并不多,现有研究主要涉及西夏酒业管理机构和管理方法、榷酤形式、刑法适用和赏格法。杜建录在《西夏经济史研究》[1]171-172和《西夏经济史》[2]168-177中,为西夏酿酒业设立专门章节进行阐述,其中提到了西夏榷酤制度的三种形式:官榷、买扑和民酤。史金波先生在《西夏社会》中梳理了西夏酿酒业的发展情况,并对酒业管理机构与管理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涉及酒曲种类、酒曲法、损耗和对饮酒、醉酒行为的相关规定,较为全面[3]136-141。而戴羽《比较法视野下的〈天盛律令〉研究》[4]则就《天盛律令》中酒务管理机构、具体刑法适用及赏格法进行了讨论,得出西夏多曲务法、少酒务法,以曲价为量刑标准和量刑较重的特点。学界的已有成果为我们搭建了西夏榷酤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量刑方面尚未见到与《天盛律令》中其他法律的对比研究,关于酒价及其原因的分析和告赏法也鲜少涉及,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将《天盛律令》的相关规定和宋代榷酤制度进行比较,论述西夏榷酤制度的特点。
一、酒业管理机构
西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多取法唐宋,如“设官之制,多与宋同”,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榷酤制度也不例外。在机构统属上,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杜建录先生的《西夏经济史研究》和《西夏经济史》均指出,西夏酒业管理机构与宋朝相仿,隶属三司,在机构设置上,亦将酒务、曲务分置,但在衡量西夏自身国情和社会经济生产能力基础上,侧重发展曲务机构,对酒务机构的管理则较为宽松。
西夏字书《杂字》(乙种本)司分部第十八中有“蟖筞”(曲务)这样的称谓[5],足以说明此时西夏的曲务管理机构已经具备专门性、普遍性,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其下辖专门曲务管理机构主要有踏曲库和卖曲库,涉及酒务的税务机构有租院。踏曲库一般设置在京师、大都督府、中兴府、官黑山、黑水、鸣沙军等中心城镇,分布较为集中,而卖曲库除京师、大都督府、官黑山以外,还设在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会州、保静县、南山九泽、五原郡、宥州、夏州、黑水、富清县、文静等18地,较为分散[6]532-535。而根据西夏《天盛律令》卷十七《库局分转派门》中所载,西夏的曲务,与宋朝三司掌榷酤相似。租院的行政等级或高于“卖曲库”和“踏曲库”,其职能范围较为广泛,当专为收取包括“卖曲税钱”在内的各类赋税而设。《天盛律令》中就有涉及中兴府租院、五州地租院对账目审核及上报的规定,前者每日审核一次,后者一月审核一次,“当告三司,依另列之磨堪法施行”。据《天盛律令》,西夏主要租院设于灵武郡、中兴府、大都督府、五州地、富清县及诸渡口。
关于主要卖曲库、踏曲库、租院官吏的设置情况,杜建录、史金波等学者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仅仅对不同地域或不同酒务机构中的官吏建制差异略作探讨。

表1《天盛律令》所载三地租院官员设置情况①

表2《天盛律令》所见踏曲库、卖曲库官员设置情况②

表3主要府郡踏曲库、卖曲库官员设置
由以上三表可知,租院、卖曲库多设有“拦头”一职,是负责收酒曲税的基层官吏,与北宋时期拦头职务类似,且可以领到固定俸禄,《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就规定了各租院、踏曲库和卖曲库官员的“禄食次第”,这在戴羽文中也有所涉及。而中兴府与大都督府踏曲库设有提举,灵武郡、中兴府租院设有指挥,体现了这些府郡租院与踏曲库规模较大,且地位较为重要[6]531-535。其中中兴府租院设有40拦头,数量最多,应是地处首府、人口聚集、手工业经济发展、酒务繁忙所致。
有关西夏酒务机构的史料记载较少,在黑水城出土西夏字书《杂字》(乙种本)司分部第十八中有“阂筞”(酒务)这样的词汇[5],说明西夏已有专门管理酒务的机构。有关酒务的律令,在《天盛律令》中仅有2条,分别为关于私造小曲酒、酽酒和普康酒的处罚;而关于曲务的律令则多达7条,如果将散见于其他卷目中关于曲务机构的记载也计算在内,则有20余条。由此可见,西夏榷酤制度是有重点的,即主要控制酒曲的生产和销售,而对酒务设限较少。[4]
二、酒曲法的特点
由于《天盛律令》中涉及酒曲法的条目总数有限,故下文将酒曲和酒放在一起分析。
(一)量刑
1.适应官阶和官民的差别量刑
不论是与《天盛律令》中其他方面的律法还是与宋朝律法相比,西夏酒曲法的量刑都有着显著的特点。此前在戴羽文中和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社会》中对酒曲法的量刑方面已有细致的探讨,但将其与《天盛律令》中其他律法对比可发现,西夏酒曲法尚有一些前人没有注意到的特点。
在量刑上,“有官”较“庶人”更重,且“有官”中官阶愈高者,量刑愈重。《天盛律令》中对私酿私饮普康酒、酽酒、小曲酒的处罚上,“诸都案、案头、司吏、卖糟局分人”,与其平级之司中“大人、承旨、偏问者遣诸检校”或其他“有位臣僚、种种执事等”,“因是执法者,一律酿五斗以内者无论大小,徒六年,五斗以上一律八年长期徒刑”,而“溜首领、种种待命、军民”则“酿五斗以内者获徒四年,五斗以上一律当获五年劳役”。[6]564以上所列种种官职,除“军民”应都可归入“有官”一类,据此可见西夏酒曲法对“有官”量刑较“庶人”更重。而在“有官”中,“都案”、“司吏”、“承旨”等此类官阶较高的行政官员和“溜首领”、“待命”这种军事编制中品阶较低的官员相比,前者所受刑罚更重。
差别量刑普遍存在于西夏各类法律条文中,但通常情况下“有官”较“庶人”量刑较轻,而“有官”中官阶愈高,量刑愈轻,如《天盛律令》规定州主、城守、通判当涂泥时,不好好涂泥者,三十人以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6]219。在“有官”的阶层中,亦会按照官阶高低进行不同程度的量刑,官阶愈高,量刑愈轻。如当有人蓄意放火毁坏财物时,“庶人造意斩,从犯无期徒刑”,“未及御印”以下官“造意官、职、军皆革去,徒十二年,从犯徒十年”,“及御印”以上官则“造意官、职、军皆革去,徒十年,从犯八年”,其中,“造意”与“主犯”同义。[6]292-293翟丽萍在《西夏职官制度研究》中对“及御印”、“未及御印”官作出了如下解释:“御印”即官印,西夏官阶由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及授、及御印、未及御印。“有官位人犯罪时,有‘及授’以上官者,应获何罪,一律当奏告实行。”[7][8]这说明,及授官等级较高,需要上奏方能定罪,而及御印官与未及御印官的区别在于是否可奏请官印。涉及“庶人”和“有官”以及“有官”中不同官阶的差别量刑在《天盛律令》中不胜枚举,可见西夏酒曲法相对于官员犯法的惩处更为严重,亦体现出西夏对于酿酒的重视。
在宋朝,并无以官、民为标准进行差别量刑,也无根据官阶区别对待,但其榷酤制度也独具特点,即存在显著的地域区别,分不同区域施行不同程度的酒禁。而由《天盛律令》可知,西夏酒禁并无区分城市、乡村及类似的地域划分,只对诸踏曲库、卖曲库在酒曲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分曲之粗细和“京畿、地边”进行规定,量刑时以重量作为统一标准,若卖曲过百斤,不论庶人、有官“一律徒六个月”,若转卖过五十斤,则“一律有官罚马二,庶人徒三个月”[6]552。现以《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中宋初相关规定为例,制表如下。

表4宋初酒曲法地域情况

续表4
宋不仅禁止私自造曲卖曲,而且对官酒的销售区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在特定销售区外一律以私酒论处,只此一地合法售酒,以价格垄断排除官私酒之争,同时能够防止官酒与官酒之争,这种划定有利于稳定酒课收入。此外,划分地域这一方法,除量刑外,还适用于下文所论之告赏。
2.以市值折算产值的量刑标准
关于私贩酒曲的量刑,历代都十分严厉,宋朝的量刑就经历了一个由重转轻的过程。宋太祖于建隆二年时“班……货造酒曲律”,规定:“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减造者之半。”[9]9此后,从建隆三年(962)至乾德四年(966)亦是如此,而在死刑以下,仍根据数量多少分别断罪,有一至三年的徒刑和一至三年的配役[10]1957。宋太宗端拱(988—989)时“令民买曲酿酤者,县镇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11]4516。就上述宋太祖、太宗时期立法量刑变化而言,显然有递减的趋势。
而到宋真宗时期,量刑逐渐放宽,直至天禧三年(1019)将死刑改为刺配之刑,“自今犯酒曲、铜钅俞等有死刑者去之,中书参详请今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牢城,诏可”[9]14。免除死刑,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但宋廷并没有放宽对榷酤专利的维护,而是随着榷酒制度的日趋发展,加强其缉私组织,对私酒私曲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范措施。量刑虽减,专利依旧,其程度甚至比此前有过之而无不及[12]120-122,就算免除死刑,贩酒之人也仍需受杖刑、黥面之后再发配。
西夏、宋初造私曲量刑进行比对(表4),可以明显看出西夏犯曲之人的最高处罚只是无期徒刑,并不会处以死刑。虽然西夏量刑标准为“缗”,其计量单位与宋不同,但从《天盛律令》卷十八《盐池开闭门》中可知当时官定酒曲价格为1斗15斤,共计300钱,那么一缗可换算为50斤[6]566-567。因西夏与宋长期保持或官或私的贸易往来,故二者度量衡差异应该不大。就算有些微差异,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夏较宋朝较为宽松,宋处死刑所对应的私造曲数甚至远低于西夏私造曲量刑的起始重量。
在量刑标准方面,西夏在对酒曲的售卖中以“斤”、“两”为单位,如“无御旨抽换卖曲”时,重达百斤时“有官罚马二,庶人徒三个月”,百斤以上“一律徒六个月”;又如卖曲和转卖量刑时,以五十斤为界,以下“庶人十杖,有官罚钱五缗”,以上则“一律有官罚马二,庶人徒三个月”。在对酿饮私酒的处罚中以“斗”为单位,尤以小曲酒为详,酿者中“执法者”五斗以下徒六年、以上徒八年,其他人五斗以下徒四年、以上五年劳役;饮者中执法者两年劳役,军民一年,酽酒和普康酒与此相同。[6]564-565这与宋代的榷酤量刑基本常用单位相同,《庆元条法事类》中记“诸禁地内……私造酒一升,笞四十,五升加一等,五斗徒一年,五斗加一等,五石不刺面配本城”[13]395。但西夏对私造曲的量刑标准却与宋代有着显著差异,为便于比较,现将《天盛律令》卷十八《杂曲门》和《宋会要辑稿》所记建隆三年州、府、镇、城郭内私造曲的相关规定列表如下。

表5西夏、宋初造私曲量刑对比情况[6]564-565[13]395
在西夏对私造曲的量刑中,先对所造酒曲称重,“量先后造曲若干斤”,再折以当时市值,并以此为标准进行量刑。但在宋代量刑中,则根据所造酒曲重量量刑。二者相较而言,以市值量刑更符合西夏对酒曲的严格专卖,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体现出不同酒曲的分别,比简单以质量或数量为量刑标准更加成熟。
(二)告赏法
在西夏法律体系中,不乏犯罪举告方面的相关规定,榷酤制度也不例外。举告私造酒曲、私酿小曲酒者时,按照犯曲量刑轻重行赏,而宋则将酒曲和酒并论,划分禁地(此处禁地指范围在东京城25里、州20里、县镇寨10里内,下文与此同)。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6宋夏告赏情况对比表[6]564-565[13]395
宋夏都根据犯曲价值量刑行赏。宋朝划分禁地区域,禁地内犯酒较禁地外量刑更重,且刑罚种类更为多样,包括笞刑、杖刑、徒刑等,从每种刑罚的最低等开始规定,每等增加固定的赏钱。而西夏告赏所对应的刑罚种类较为单一,就酒曲法来看,目前只有杖刑和徒刑两种刑罚,且以徒刑为主,偶尔严重者处死。就徒刑而言,5年及以下每等增加1年,从6年往上则每等增加两年,即徒6年、徒8年、徒10年,以此类推。
而在赏金来源方面,西夏规定由犯罪者或干系人出,“当由各犯罪者依罪情次第承当予之”,私酿小曲酒则更为详细,“钱由酿者承担,酿者不能则由饮者承担”,如若无能力,则由官府给予。[6]565-566而宋则“诸备赏应以犯人财产充”,“无或不足者,禁地内犯私有酒曲及外来官酒,责知情干系人及邻保、买酒户、酒曲贩,责知情酒户均备”[13]396-565。相较而言,宋法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广,具有连坐性质,而西夏的赏金来源仅限于犯罪者,且由官府作为最终保障。
(三)专卖性质:完全专卖
除生产领域外,西夏在流通领域对私卖及转卖酒曲也有所规定。前者以“百斤”为界,以下“有官罚马二,庶人徒三个月”,以上则“一律徒六个月”;后者以“五十斤”为界,以下“庶人十杖,有官罚钱五缗”,以上“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徒三个月”。西夏官方对买曲者也比对卖曲者更加宽容,“当比从犯减一等”,且不知者无罪,“若买者不知,勿治罪”。此外,还有一条规定专门限制西夏国人在境外购买酒曲,当有人“买敌之曲自用时,当比造私曲罪减一等。曲当罚没纳入官”[6]564-565。可见,西夏官榷的主要形式为完全专卖,且专卖的重点集中在酒曲而非酒上,对私造曲的处罚比之私卖酒也严苛许多,若是转卖则再减一等。
而在宋朝,则实行相当程度的不完全专卖,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买扑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宋会要辑稿》记太平兴国二年(977),“诸州榷酤募民,能分其利,即给要契,许于州城二十里外酤”[10]1957。罗浚《(宝庆)四明志》中亦载“国初有都酒务,官既自榷,亦许民般酤,即官给要契,许酤于二十里而外,岁输其直,今坊场课利钱是也”[14]。由此可知,这种官府募民酤酿,官给要契的形式将酿酒权下放了一部分到特定的人群手中,虽然能够胜任的往往是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乃至高官重吏[12]212-219,但官府毕竟从直接生产者退居二线,成为了“坊场钱”和“课利钱”的征收者,这在性质上属于不完全专卖。杜建录先生《西夏经济史》中根据宋代西北边境的榷酤地情况与西夏字书《杂字》中有“投状”一词推测西夏或也推行过买扑制度,即个人向官府承包某一特定区域的酒税,并在此地酿酒酤卖的酒税承包制度。这种承包的实质当为专卖税,即国家授权给某特定个人,由其垄断某一区域的酒曲生产与销售,是国家专卖更为高级的形式。但我们尚不能确定西夏是否真的实行过买扑制,或类似于买扑的榷酤制度。这样来看,西夏在曲务方面实行的是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模式,这样的完全专卖无法因地制宜制定酒法,易使有些粮食产量落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无法承担酒税,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从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固性。
三、酒价与曲价
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社会经济文书中的酒钱账,可以了解到所买酒的数量及价格。例如:俄Инв.No.4696-8所记甘州米酒的酒价钱账中,每笔账先计“挨綀”,意为一人,再记买酒人,最后是所买数量和价钱。数量以斗为单位,价钱以造酒原料大麦为单位,因大麦属于杂粮类,有时直接记为“杂”。结合文书中以杂粮换酒的情况和当时的物价,可推算黑水城地区每斗酒约合150—250钱。[15]161-167
在宋地,酒的数量单位以“升”最为常见,其次是斤。有宋一代,酒价总体呈上涨趋势,宋初酒价较低,仁宗时期一升酒只有23钱,约合一斗酒不到3钱,但随着西北战事加紧,酒价飞涨至斗酒千钱。神宗时虽稍有回落,但斗酒仍需百钱,与宋初相比仍较高。至徽宗在位时,酒价又一度飞涨,南宋初期亦是如此。[12]309-310
虽在黑水城文献中无从得知西夏境内的一斗酒究竟等于多少斤,但从整体的度量衡来看,与宋朝差异应该不大。由此可知,西夏的酒价相对于宋朝趋于平稳,变动幅度较小。纵观宋朝的物价变动,似与西线战事息息相关。但西夏在同时也陷入战事之中,故宋朝酒价波动应有更深层的原因。李华瑞在《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一书中提到宋代酒价的变动根源于土地兼并活动的日趋频繁[12]311,而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据此,西夏酒价相对于宋朝趋于平稳,正是因为其尚保有部落制和畜牧经济,封建经济的发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土地兼并活动并不猖獗,故地价、地租、政府赋税和物价都在有限范围内,酒价自然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的官方法律文书中并无对酒价的规定,反而对曲价进行了规定,“诸处踏去曲者,大麦、麦二斗当以十五斤计,一斤当计三百钱卖之”[6]566。可知当时酒曲价格为1斗15斤,共300钱,比酒价更贵,较宋初酒价亦十分昂贵。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合目的性的主体自觉选择过程的统一。我国现阶段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也是在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历史地形成的。
西夏法律中对曲价的规定和酒价在经济文书中的集中记载,体现出西夏榷酤以酒曲专卖为主的特点,这与宋朝对酒价的详尽规定和对酒曲的只用不卖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分析宋朝曲法,可以看出其更侧重人事管理,对监官轮值、强卖、违律不宿等行为都有所规定。[4]究其原因,宋朝商品经济更为发达,酒曲的消耗量巨大,对于其生产来说,则更加重视人事管理,而西夏经济相对落后,酒曲消费量小,加之地广人稀,粮食产量不如宋朝,对酒曲运输损耗的规定自然十分详细。
四、余 论
根据《天盛律令》中现存对西夏榷酤制度的相关记载,可以勾勒出其大致轮廓。西夏榷酤制度取法北宋及前代,设有专门的酒务、曲务管理机构,主要侧重对曲务的管理,其中结合自己本民族的特点在量刑及其标准、地域条件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但是根据现有史料来看,相比于宋朝,西夏的榷酤制度仍主要停留在完全专卖这一初级形式上,量刑也相对较轻,只有徒刑而无极刑。在量刑过程中也以折算当时市值为标准,不同于宋朝以重量为单位,在对酒曲进行专卖的条件下,能够根据私造的不同酒曲适用不同的刑罚。除此之外,西夏并无因地域不同行不同程度的榷酤之法,这点不同于北宋。各地同行一种酒法,可能致使粮食生产、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承担过重酒税负担,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细推之,造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主要与西夏农牧并重的独特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西夏榷酤制度本身有关。
第一,在生产方式方面,西夏虽受宋影响,农业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毕竟耕地、牧地并存,人口有限,粮食产量不如宋朝,对于酒的损耗也规定得极为详细。西夏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半农半牧构成的,农业虽作为封建文明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相当一部分的地位,但其畜牧业作为民族特色,在社会经济中亦是举足轻重。党项及其他少数民族人的主要食品中即有肉、乳、酥,手工业产品也主要依赖皮、毛、绒等原材料,对外贸易与大宗商品出口也以畜产品及其副产品为主。故首先,其社会生产资料——耕地面积较宋朝更少,《西夏经济史》中推断西夏耕地面积为200万亩,即2万顷,而其亩产最高在1.5石左右[2]123-130。《宋会要》中高宗建炎三年(1129),明州(今浙江宁波)的耕地面积为575顷,刚过西夏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但其税收就已经达到了1.3万余石,[10]1960由此可推知这些耕地的亩产应与西夏整体亩产相差不大,这还只是宋朝一个州级行政区域,可想而知西夏粮食产量与宋朝相差巨大。而粮食对于酿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西夏对于酒的损耗极为详细,对犯酒之人的量刑也较《天盛律令》中其他方面法律更为严苛。
第二,《天盛律令》中酒曲法只有徒刑却无极刑,或因社会生产不发达,人口有限,劳动力也较宋朝更少。杜建录先生在《西夏经济史》中经西夏丁壮人数、宋人关于西夏人口估计与部分州的户口数三方面论证,推测西夏人应在30余万户(帐)、150万口左右,上限不超过180万或200万,下限不低于100万或120万口[2]83-90。而据《宋会要》载:太祖开宝九年,天下主、客户390 540。而到了仁宗天圣七年,经历了靖康之变的战火,主、客户加起来仍破千万,为10 162 689,人口数达到26 054 238,这些数据还只是宋代的官方统计数据,历朝历代都存有因逃税、漏税而造成的瞒报户口现象。[10]1960虽然宋地较夏地较为广阔,且西夏户口数因史料较少无法窥见其变化,但若以《西夏经济史》中推论为准,可见其与宋代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样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其中的劳动力数量与宋代相比要少得多,因社会生产需要,每一分劳动力都很有价值,故在量刑中考虑及此,虽十分重视酒课收入,但只判徒刑,并无使犯酒之人身体致残之重刑。
第三,西夏榷酤制度本身取法中原榷酤制度体系,又据其地域、劳动力等因素进行调整,由于西夏政权存续时间较短,其榷酤制度尚未成熟。纵览中国古代榷酤制度可知,如西夏榷酤的不完全专卖多出现在榷酤制度最初盛行时,虽在各个环节都加以监管,事无巨细,但管理成本大,更无法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相比较而言,北宋后期出现的专卖税,只在流通环节上加以控制并收取税款,则更加适应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关键环节上加以管控,也更能体现出一朝政府把控经济形势的主动性。显然,就现有史料中总结出的西夏榷酤整体面貌而言,尚未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夏榷酤制度虽在整个中国古代榷酤制度发展史中只此一瞬,且因存在时间太短而无法发展成熟,但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在发展榷酤制度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因《天盛律令》有缺,大都督府租院、富清县租院、五州地租院作为酒税主要税收机构,应不可能只有两司吏,其他官职应实际存在,但未见记载。
②“院”与“库”在《天盛律令》中皆有所表述,今从杜建录《西夏经济史》。据《天盛律令》载,三地踏曲库适用表中官员设置,分别为鸣沙军、官黑山、黑水,其余未见记载,今仅据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