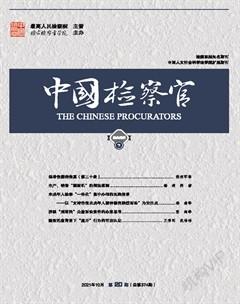“全控”型串通投标犯罪既未遂辨析
刘伟 肖恩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2018年上半年,游某某和中发公司股东刘某某为取得即将招标的艾都大酒店建设工程,决定借用其他建筑公司资质对该建设项目进行围标。同年8月,艾都大酒店建设项目招标入围公司名单确定后,游某某、刘某某安排中发公司员工陶某某等人分别花钱购买并控制8家入围公司资质。后来,其中6家公司按照陶某某提供的商务标底价格制作标书,并以本公司的名义完成投标流程。2019年1月4日,艾都大酒店建设项目评标结果公布,中发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投标报价178,920,000余元。[1]
案例二:2018年3月,崔某某为取得高平市神农镇XX村拆迁安置项目工程,通过裴某某、李某某直接或间接购买3家建筑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同时,崔某某向准备控制2家建筑公司资质参与投标的赵某某支付3万元,让其放弃参与投标。2018年4月28日,XX村拆迁安置项目开标,崔某某购买资质投标的晋城市XX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7,392,650.02元。[2]
二、分歧意见
本文两个案例的案情基本相同,因在中标公示期间有人举报,招标方都未发出中标通知书,但两个案例的审判法院对犯罪形态的认定结论完全相反。
第一种意见(案例一审判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第76条关于串通投标罪的立案标准第(三)项规定,中标项目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追诉。游某某、刘某某串通投标案的项目金额超过200万元,但是中标通知书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发出即案发,不能认定为“中标”,因而系犯罪未遂。
第二种意见(案例二审判法院)认为,崔某某等人串通投标的犯罪行为已经实施终了,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三、评析意见
对两种不同意见,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认定为犯罪既遂。具体理由如下:
(一)串通投标罪系行为犯而非结果犯
行为犯和结果犯,是以只要有一定的举动就够了还是以该种举动必须造成一定“结果”为必要的犯罪意义上的分类。[3]行为犯和结果犯都存在对法益的侵害以不同的形式呈现。通常情况下,结果犯的结果直观、具体,并且与刑法保护的法益直接对应(如故意杀人罪死亡结果与生命权的对应)。相反,行为犯的结果往往模糊、抽象。行为犯之结果,是指非物质性危害结果,预备行为犯、举动行为犯、过程行为犯、持有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五类行为犯均存在非物质性危害结果(具体包括精神性危害结果与制度性危害结果),但均不要求出现物质性危害结果。[4]此外,结果犯的结果一般具有终局性,而行为犯对法益的侵害通常是渐进地经历一定的过程,立法者设定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准作为结果。
串通投标罪保护的宏观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的更具体的法益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都是较为抽象、模糊的法益。另外,串通投标犯罪对法益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危害,不可能出现物质性危害结果。虽然《立案追诉标准(二)》中规定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万元”“違法所得数额10元”“中标项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或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物质性危害结果,其与盗窃、诈骗等犯罪的数额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类型划分来看,串通投标罪更符合行为犯的认定标准。
(二)行为人中标具有确定性,其对应的法益侵害的必然性符合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犯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具有互斥性,因而通过考察某一具体的、已经着手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符合未遂形态的特征,可以反向辨别其犯罪形态。根据比较古典的理论,未遂因结果不法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而应受到处罚。[5]易言之,如果结果不法已经发生或具有必然性,那么就不再属于犯罪未遂形态的范畴。
另一种观点认为,既遂犯是因为行为侵害了法益而受处罚,未遂犯则是因为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而受处罚,故未遂犯都是危险犯。[6]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此观点与前述犯罪未遂的可罚性根据理论具有相似性。
实践中,串通投标的围标人对中标结果的控制程度不完全相同。围标人掌控的陪标公司越多,中标概率越大,相应地串通投标行为侵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危险性越高。案例一和案例二涉及的公司,被行为人完全掌控,他们向招标人提交投标文件后,就已经完全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游某某、刘某某和崔某某的行为已经导致结果不法,侵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非仅仅停留在概然性、危险性的程度,因此理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三)穿透形式从实质层面准确把握“中标”与既遂的对应关系
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可能难以归纳行为犯的侵害结果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丝毫不顾及行为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而是意味着必须通过行为的进程认定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7]即行为犯以一定程度的法益侵害为侵害结果,也就是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立案追诉标准(二)》将“中标”规定为串通投标罪的追诉标准之一,表明其认为对金额2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串通投标达到“中标”的程度时,属于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达到应认定为侵害结果的标准,犯罪应认定为既遂。
案例一与案例二犯罪既遂未遂认定的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中标通知书是否对确定中标人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招投标法》的规定,招投标有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五个主要环节,第45条专门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没有串通行为的正常招投标活动和围标人只掌控部分投标人的招投标活动中,中标通知书确实是确定中标人的决定性文书。但是,中标通知书确定中标结果是立法的应然状态。当围标人完全掌控整个招投标活动时,中标通知书在招投标流程中的形式外观与实质作用不同步,不再具有实质性、决定性意义。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的时间,实际上就已经确定围标人必定是实际中标人。从此时开始,法益侵害的程度就不再受中标通知书及其余的招投标程序影响。因此,“全控”型串通投标犯罪认定既遂实际上并不依赖中标通知书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