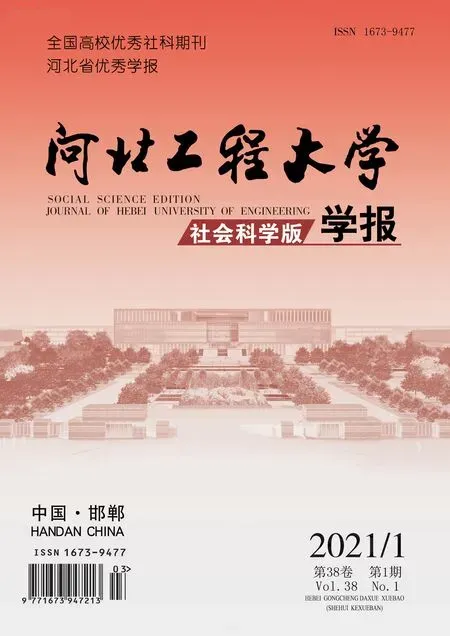马克思视域下的自由
刘文杰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世人多以为意愿无阻碍地实现即是自由、受到限制便不自由,这其实仍未真正认识自由的内涵。实际上,受限与自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错、辩证统一。要理解这一点需从根基谈起,需以马克思的视角进行解析。
一、自由何以存在?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证明人由古猿进化而来。古猿起初与其它动物一样,完全受自然的控制,其所有需要都是大自然规定的,满足需要的能力亦是大自然赋予的。但是,当通过物质生产获取生活资料时,古猿就与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过渡生物,进而最终转变为人类,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P196)所以,动物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是自我生成的,就像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即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人自身。如此一来,人便是双重存在物,既有生存、繁衍等自然规定性需要,又有审美、爱等自我生成的需要,即自我规定性需要。当然,自然规定性需要是通过古猿遗留给人类的,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兽性,由此可以说,承袭而来的是动物性,自我生成的才是人性。与此同时,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也超出了自然规定,从古猿那里继承来的能力(如感知)得到改造,其它能力(如理性)则是人类自我新生成的。而且,人类在生成之后继续进化,这一点永无止境。
对人而言,能力是中介,需要是动力,因为“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P286)。所以,需要才是本源,讨论自由就得从它发端。“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3](P926)这意味着,人即便不是因强迫而行动,可自主进行选择,但只要是为了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就仍然不自由,因为自然规定性乃是外来规定性,而非自我规定性。可人类恰恰有自我规定性需要,满足自我生成的需要的活动便是自由的活动,如“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4](P174)。
需要指出,人所有的活动都依赖和遵从物理规律,永远无法跳到其外,如力气再大人也不能将自己提起来、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行动就无法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或者说,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自由”,依附于外在条件的“自由”本身就是非自由的体现。因此我们讲,自由是在物理层次之上呈现,却又离不开后者,它们相反相成。有学者认为,除必然性之外,物质世界还必须有偶然性,这样自由才能存在。我们说,若整个世界只有一条因果链,那自由当然无法存在。但实际上有无数条因果链,事物就是无数因果链的相交节点,其发展方向并不唯一,在此情形下,即使无偶然性自由也可以存在。当然,现实中偶然性客观存在,自由的存在就更有保证了。
二、自由作为规范
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共存于一身,同时对人发生作用,人其实是自然规定性需要和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角力场。二者交会,自我规定性需要则成为规范。一方面,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有机统一,这两方面协同发展,才能够真正让人得到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辩证对立,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有效“冲突”,才能够真正确保人在约束中成长和发展。
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及其实现方式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和谐不悖,甚至是自我规定性需要得以实现的条件,如物质生产,因为人们必须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科学、艺术等等。对这类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活动要大力推动,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繁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大层次的需要之间是互相协同、层层递进的关系。只有首先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这个过程也正说明了自我规定性需要与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冲突,如支配欲;有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虽不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冲突,但实现方式却与自我规定性需要冲突,在人类能力超出自然限制的情形下,这点尤为明显,如性侵。对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这些实现方式,自我规定性需要会予以禁止,此便是“应当”,上述需要、实现方式其实就是“恶”。理由己出,这样,“休谟难题”便迎刃而解。即使委实没有其它方法压制恶,人至少还可以通过自杀来消解自然规定性对自己的控制,就如黑格尔所言:“唯有人才能抛弃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在内,因为人能自杀。动物则不然,动物始终只是消极的,置身于异己的规定中,并且只使自己习惯于这种规定。”[5](P17)牺牲生命以实现自我规定性需要是人类自由的终极证明,当然也是最消极的证明。所以,凡是正常之人都要对自己的恶行负责,因为本可以管制住恶,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奉命作恶的纳粹士兵也受到审判就是这个道理。
综合以上情形,可以说,人类就是要把自然规定性需要及其实现方式纳入到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之内,此乃本性使然,“惟有人作为全无规定的东西,才是凌驾于冲动之上的,而且还能把它规定和设定为他自己的东西”[5](P26)。或者说,就是为了管制自然规定性需要及实现方式才产生了自我规定性需要,也只有这样了才能说人类生成了。那么,所谓“意志自由”中的这个意志只能是自我规定性需要引起的意志,自然规定性需要引发的意志不但本来就无自由可言,而且要受前者的管制。
三、自由与限制
马克思认为自由离不开限制。从上述的阐释中可知,所谓“自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则及价值标准来进行界定,从而获得基于“物理规律”为参照的自由。以规范允许的方式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从根本上说还是不自由的,因为满足的是外来规定,但它又不同于恶,可称之为形式上的自由,以便区分。这样,人类活动就分为三类:做自由的事,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不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做自由的事是完全的自由,从内容到形式都自由,因为它所满足的自我规定性需要本身既是目的又是规范。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是相对的自由,即按照相应的规则和标准来做“不自由的事”,内容本身不自由,所以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我规定性与自然规定性的统一。而不自由地做自然规定之事,是彻底的不自由,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自由,分为作恶和在恶的压迫下行动,二者互为对立面。可见,自由具有对应的尺度和坐标,按照自由的实现程度,可以将之分成如上三类。这种界定其实也是对人类活动层次的再现,可以说,人类活动层次越高级,那么所获得的自由程度就越大,这个过程是现实向理想转化和趋向的过程。
恶乃是自然规定性需要的实现突破了自我规定性需要的管制,所以作恶之人与被压迫之人同样不自由,哪怕是他占据优势强迫别人,哪怕是他主观上愿意这样做。有的作恶之人会认识到这一点而改过自新,从而恢复自由,至少恢复到形式自由。有的作恶之人死不悔改,那就需要外人用强力迫使他的自然规定性需要的实现纳入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之内,甚至直接消灭不合规范的自然规定性需要,这是帮助他恢复自由,此时自由就与限制同一。自由和受限相对立是对受压迫之人而言的,他正当的需要不受自己的管控而是受制于外来目的,或自己奋起反抗或外人施以援手,打破限制才能恢复自由。但被压迫之人有时并不想反抗亦不愿别人救助,自己情愿受压迫,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那样,外人可限制其不自由的行为,迫使其自由,自由与限制此时又是同一的。
只要目的是恢复被压迫之人的自由,外人援助他也好强制他也好,都不会侵犯他的自由,因为这与目的相背离。对作恶之人进行限制也是为了恢复他的自由,外人对他的强迫当以此为限,因为作恶之人的自由恢复后,外人继续或进一步实施限制的话,就是在作恶,自己陷入不自由。同理,受压迫之人反抗作恶之人,恢复自身的自由即可,否则自己就转为恶人,变得不自由了,防卫过当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可见,他者的自由就是自己自由的边界。为此,康德提出一个判断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施加于他人的活动同样愿意施加于自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是哪样的活动不能做,而康德说的是哪样的活动能做,二者互为逆否命题。对于此问题,马克思这样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1](P4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必须要依赖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及价值界定,才能够产生现实意义。对于个体而言,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便要明确并遵循相应的法律规范和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其实也适用于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因为人的爱如张载所言乃是“民胞物与”,既施于人亦施于其他生物,这种需要会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使人与其他生物和谐相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总之,“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185)。
霍布斯认为,人类乃是自然的产物,和动物一样完全受自然控制。这样的话,无论人作何选择,都是大自然规定的,那就无所谓善恶,人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大自然就这样设定。现实中人类有道德伦理、法律制度,反过来证明人是自由的,而自由的根本在于自我生成,所以霍布斯的观点难以成立。在费希特那里,人不仅自我生成,而且创生世界,即所谓“自我设定非我”。以他看来,人只有自我规定性,而无外来规定性,所以绝对自由,善恶皆出自人性而不像我们说的恶出自兽性。但人创生世界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因此,费希特的自由观也不成立。
四、自由活动的异化
自然规定性需要受自我规定性需要的规范,但它不仅能突破管制,而且还反过来对自我规定性需要产生影响,如“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1](P192)。它甚至能异化自我规定性需要,使得原本自由的活动成为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手段,不再自由。
在人类诞生之初,尚未出现社会分工,对于个体来说,其在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在从事其他精神、文化层面的活动。可以说,每个人都富含艺术家的气质,相比其它自由活动(如道德实践),艺术更明显地体现了人类的超越性,即不为肉体需要也进行生产,“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163)。出现分工之后,物质生产劳动与其它活动分离开,人类群体中的底层沦为劳动工具,他们从事更多的是物质内容生产。而处于较高社会层次上的人,则将更多的关注点投射到社会变革、制度建设、艺术发展、科学进步等方面[6](P593)。只从事物质生产的阶层注定是不自由的,但即使这样,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存在艺术本身就是目的的情形,甚至从事手工业的工匠、画师为自己的手艺而痴迷,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算得上艺术家,“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从事本行专业和做好这项专业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原始艺术爱好的水平”[2](P59)。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职业都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轨道,“许多职能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光环,它们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现在一方面,直接变成了雇佣工人,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样不同”[4](P523-524)。艺术生产同样也成为资本入侵的牺牲品,对于戏院及相关娱乐场所的老板而言,艺术是他们得以谋生和获得利润的工具,在这里,演员作为工人而非艺术家而存在,他们创造出的艺术作品也不具备艺术属性,而是资本家用以获取利润的工具[4](P417)。可以说,获利是所有资本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便是艺术生产也无法逃脱此类命运,成为资本家逐利的重要方式[7](P346)。
但由于人类的自我规定性,也由于艺术本身的特点,“工业文化”无法占领艺术生产的全部纵深,异化只是局部的,“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P223)。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有人不为钱财、名声等等而舍己救人,这也是自由存在的体现。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自由的活动、形式上自由的活动、完全不自由的活动并存的格局。
五、自由的实现
人确如卢梭说的那样,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之所以有枷锁,是因为人类有自然规定性需要且能力超出了自然限制。而自我规定性需要推动人逐步解除枷锁实现自由,“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P120)。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的曙光已经显现。
对于完全不自由的活动,关键在于消灭恶,无恶就无压迫。一些恶是由自然规定性需要不合规范引起的,这类需要完全可以摈弃,而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既然代代相传,那必定有遗传基因,或许可以通过基因改造直接消除。另一些恶所实现的自然规定性需要合乎规范,只是实现方式不合规范,可实现能力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和实现能力都不应消除,那人作恶的可能性就永远存在。其中有纯粹的作恶,也就是说即使能以合乎规范的方式满足合规范的自然规定性需要仍然作恶,这只能通过法令来遏制,所以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一定会有律令存在,如“禁止性侵”必然贯穿人类历史始终;还有因为合乎规范的方式无法满足合规范的自然规定性需要而引起的作恶,如在极端贫困条件下生存必需品的争夺不可避免(虽然有人宁肯饿死也不作恶),这种情形的恶,除法令压制外,通过发展形式上自由的活动来消除更为有效,因为能以合乎规范的方式满足这些自然规定性需要,自我规定性需要进行规范所面对的阻力就小了,更易于克制恶。
形式上自由的活动能消解某些恶,是自由的前提,需不断推进。其实,人的自然规定性需要本身也这样要求,因为人的自然规定性需要与动物的还是不同,具有广泛性、无限性的特点。时至今日,物质生产已达到如此程度,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私有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P874)。私有制发展到极致必然转向自身的对立面,公有制才能发挥生产资料最大的规模效应。而且只要实行了公有制,被异化的自由活动就没有了束缚,重新成为自由活动,因为人已无需靠它来获得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东西。总之,单是自然规定性需要,都要求最终实行公有制,何况自我规定性需要也这样要求,所以,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很多人没有把握马克思的这个论证思路,只看到他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从而进行批判。这就陷入庸俗,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10](P239)
自由实现于消灭劳动。即使法度压制住恶、公有制使人不再为他人劳作、艺术成为目的本身,人类依然不自由,因为还得进行劳动,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P56)。作为满足自然规定性需要的手段,劳动不是自由的活动,实现自由的最后一步就是消灭劳动,即用自由活动同化劳动,马克思从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互转化的视角给出了解释:“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一一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4](P204)当生产力达到足够高的程度,在自由活动的范围内,在人还没有疲倦或兴趣消退之前,这段时间内获得的使用价值已足够人类的需要了。或者说将物质生产内化于艺术活动之中,在创造美、知识的同时完成物质生产,陶艺便是明显的例子,本身是一种艺术活动,但制作出的陶器可以满足生活之用。艺术活动的普遍化就是劳动的消灭,而劳动消灭之日便是自由实现之时。
六、结语
自由是人生的意义,也是人类这个物种存在的价值。由于人的双重规定性,所以并非但凡出于自愿的行为就是自由,很多世人未认识到这一点,错将任性当作自由,造成了恶。但人自我生成的本性一定能压制住恶,一定会使满足自我规定性需要的活动充实人类所有领域,只要人类不灭亡,自由必定实现,虽然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和经历曲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