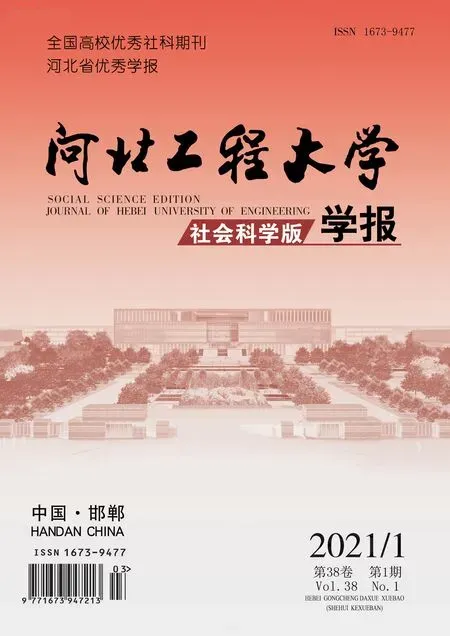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
赵猛, 尹舒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2488)
《第一哲学沉思》中并未直接出现“我思故我在”这一表述。事实上,笛卡尔是在“第一沉思”中普遍怀疑的基础上,通过证明“我存在”的绝对确定性寻找到纯粹思维这一主体本质,并将“我的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最终达到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论断。由于这一过程并不是以三段论等较为清晰的演绎推理方式建构的,且笛卡尔曾将“我思故我在”视为一种心灵直观的结果,“一贯地模糊了推论和命题之间的区别”[1],引发了大量学术讨论。主要分歧之一在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得出过程以及这一论断本身究竟是一种直觉(即不言而喻的东西),还是一种推理。Jaakko Hintikka曾指出,“我思故我在”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非推理的表现性话语,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从“我思考”到“我存在”的转变是非逻辑的[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理,只是其构成方式无法用三段论概括。如Margaret Wilson就明确提出“主张‘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论……并不等同于它是一种三段论”[3];Peter Markie也强调“我思故我在”是将“我思”作为前提,而“我在”是从这一前提得出的结论[4]。还有调和这两种观点的尝试,如以Anthony Kenny就认为“我思故我在”从认识方面来看是直观的,而从逻辑方面来看是推理的[5] 54-55。
本文提出,这一争论可以围绕“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理解,即考虑“我思”、“我在”与“我”这一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确定的内部逻辑,以及“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在确立主体存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首先通过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作为普遍怀疑中的例外的“我在”、作为“我”的本质的“我思”、“我思”与“我在”的关系问题。其次,在对这一论断中蕴含的自我关系问题作出解答后,即按照“我思”、“我在”与“我”三者的内部逻辑,“我思故我在”应当被视为一种非三段论形式的推理。而为确保这一推理在“第二沉思”的语境下的有效性,需要根据“我思”、“我在”与“我”的关系进一步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重构为“我思考我在,故我在”,且将“我”这一主体的指代范围明确为心灵中的纯粹思维。
一、“我在”作为普遍怀疑的例外
在分析“我思故我在”前,应当还原“第二沉思中”提出与阐释“我思”与“我在”两个核心概念的过程。笛卡尔首先证明的是“我在”的绝对确定性。“第一沉思”中,他从感官的欺骗性、梦境与现实的不可分辨性入手分析,最后引入一只具有强大能力的恶魔,从自然怀疑推进到哲学怀疑,摧毁了与感官对象有关的、组合事物的知识以及与原则有关的、最简单和一般事物的知识;而“第二沉思”则承接了这一普遍怀疑的方法:“我会在这条路上一只走下去直到遇到一些确定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不能做其他事情,至少直到我直到这世界上没有可靠的东西”[6] 24。可见,“第二沉思”是以在排除怀疑所摧毁的有条件者的过程中,寻找无法摧毁的无条件者为起点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论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首先,“我说服自己一些东西是存在的(或者仅仅是我认为它们是存在的),这就可以确保我的确是存在的。”(1)括号内的半句为法语版本中的原文,英语版本中将这半句放在注释中。[6] 25需要指出,普遍怀疑并非笛卡尔的目的,而是他用来达到不可怀疑之物的手段。而这一在“第二沉思”中处于较前位置的论断,不仅承接了“第一沉思”中的普遍怀疑的方法,更一转笛卡尔哲学沉思的方向,开始向寻找确定性这一最终目的过渡。同时,为了不让前半段的努力化为泡影,括号中的文字显得格外重要——笛卡尔在这里同时为那个可以欺骗一切的恶魔和自身存在的确定性这二者留出了空间。应当指出,不管这一论证的前提是“我确实相信一些东西是存在的”,还是“我仅仅认为一些东西是存在的”都可以被理解为“我思”的变种,在此处也都是可以确保“我的确是存在的”这一结论。
其次,上述推理显然是未证明其大前提的:是否所有被认为或被说服存在的东西都能存在呢?笛卡尔对此的补充涉及第二个关键论断:“如果有恶魔欺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存在,并且让他尽他的意愿去骗。只要我认为我是某物,他就永远不会说我什么都不是。”[6]25这就回答了大前提:“我”这一被认为存在的主体必然是存在的。如此,“我”的主体性特征已经逐渐被凸显了。即使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恶魔创造的谎言,那么被谎言欺骗的主体“我”也必须实际存在、不可怀疑,否则“欺骗”这一行为便没有了受动者,一切谎言也就失去了对象。换言之,从“我认为存在一个能力强大的欺骗我的恶魔”这一假设中,至少可以推出“我”这一存在作为一切表征物和表征活动的前提,普遍怀疑便达到了最终的确定性。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恶魔欺骗我,那么我存在”这一推论过程中仍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即所谓的恶魔本就是笛卡尔假设的产物。而这样一来,以恶魔这一不一定为真的假设作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为真了。不过此处也可结合下文对“我思”的论证进行理解。即使不一定真的有恶魔在欺骗我,单从“我认为有恶魔欺骗我”这一事实似乎也能够推理出“我存在”的结论,且“我认为有恶魔欺骗我”就可被视为的“我在思考”的变种。关于这一点,本文第二部分会进行着重讨论。
目前为止,笛卡尔已经提供了两个可以用来证明“我在”的论据——第一个主要关于“我说服自己存在某物”,第二个主要关于“我认为恶魔欺骗我”。二者都鲜明地彰显了“我”这一主体在存在层面的特殊地位。同时,笛卡尔已经意识到、或者已经有意在向读者强调,“我”这一主体与“思考”这一活动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我在”证明的必要性,这就为接下来证明“我思”与“我在”的关系提供了思维进路。而在经过上述两个论断的铺垫后,他终于得到了确定的结论:“我是(有我),我在,当我宣称它或心中想到它时,它必然是真正的。”[6]25这样,通过“第一沉思”与“第二沉思”前半段的哲学抽象的过程,笛卡尔已经取消掉了所有可被怀疑的东西,使得“我”这一主体最为清晰、最为明显地被凸显出来,并确定了“我存在”这一普遍怀疑的例外。与此同时,这一结论的后半段中对“宣称它”和“心中想到它”的强调,也为下文进一步认识“我”的本质,即纯粹思维做出了预告。可以说,在“我在”论证中已经初步彰显出了“我在”与“我思”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我思”作为“我”的本质
在上述论证中,笛卡尔将重点放在了对于“存在”的证明上,而没有对“我”的具体定义及本质进行说明。也就是说,“虽然沉思者现在知道他是,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是什么:他怀疑关于自己本质的旧观念,却似乎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来取代它。”[7]笛卡尔自己也意识到:“但是我还不够清楚,我是谁,确定我存在的那个我是什么。”[6] 25于是接下来的“第二沉思”中进行了两重区分,最终发现正是纯粹思维构成了“我”的本质,并确定了绝对确定性的自我存在。
首先,笛卡尔在从“我在”证明转向证明“我”的本质的过渡段中这样强调:“我要在这里思考一些以前就出现在我心里的想法,那些想法不是由我本质之外的东西激发,是在我思考我的存在时产生。”[6] 26也就是说,只有不能通过普遍怀疑而排除掉的东西,才是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我存在”不能通过普遍怀疑排除掉;因而思考“我存在”时产生的想法就是由我的本质激发的。以上也可被视为构成了一段三段论推理,使得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自然地从对“我存在”的证明过渡到对“我的本质”的探究。
其次,笛卡尔做出了两重的区分。在第一重区分即实在的区分中,他区分了作为纯粹心灵的“我”与作为经验性物质的“我”。从实在区分入手也是顺承“第二沉思”前半部分证明“我在”作为普遍怀疑的例外的自然思路。由于关于自我的存在可以在普遍怀疑之外确立下来,那么,普遍怀疑所取消掉的关于身体、外在事物和数学的知识即使分离出去也不会对我的存在产生影响。这样,在否定掉所有对象知识后,关于自我知识便能够呈现出来,此处的“自我”显然已经不是物质层面的“自我”,而是心灵层面的“自我”。可以说,笛卡尔视角下的思想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并且这种绝对确定性对于“我”这一思维主体而言包含着一种直观层面的自明性(2)许多学者曾分析过笛卡尔“我思”证明中“我思”与“我”这一主体间的直观性、自明性关系,即“我”作为思维主体不可能有一个思想而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具体论述可参见Anthony Kenny, Descartes. A Study of his Philosophy, Thoemmes Press, 1993, p. 51; Bernard Williams,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8, p. 66.。这也就构成了其后来将“我思故我在”视为一种心灵直观的部分理论基础。总之,笛卡尔在此处是将自我知识与对象知识区分开来,将“我”作为纯粹心灵与“我”作为经验性的物质存在区分开来,即分隔我的心灵(心灵领域)与外在的物体(对象领域)。因此,笛卡尔得出结论:“我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思维的东西……我在最严格意义上是心灵。”[6] 27
再次,笛卡尔考察心灵内部,并在此领域内进行了第二重区分——模态区分,即区分心灵实体与心灵模态(属性)。虽然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但若所谓的“思维”中仍蕴含不同属性,似乎就与西方哲学将本质规定为不可分之物的传统产生了矛盾。因此,笛卡尔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将宽泛意义上的思维活动分类:“但是我是什么呢?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样的思维的东西?它是一个怀疑的、理解的、思考的、肯定的、否定的、愿意的、拒绝的,拥有感官和感知的东西。”[6] 28他将心灵的模态粗略划分成四种:纯粹理智、意志、感知和想象;其中纯粹的理智思维是首要的模态。我们可以在笛卡尔分析中,发现三个主要的理由。首先,纯粹的理智思维呈现在其他三种模态中,后者可以变换,而前者始终保持。“如果不是以作为一个思想或依赖一个思想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无法将任何东西理解为是在心灵中的。”[6] 74当纯粹理智渗透于其他三种模态之中,我们才能理解自身作为人所具有的意志、想象与感知是有理智的心灵模态。其次,纯粹理智可以独立于其他模态。如果在心灵中屏蔽意志、想象与感知模态,那么仍然可以发现一个主体处于纯粹理智的思维中,即处于纯粹怀疑、理解、肯定或否定的思考之中。再次,纯粹的理智思维构成了自我的本质。上文论述到,通过普遍怀疑所达到的实在的区分,排除掉一切非自我的表象关系,笛卡尔确立了作为一个思维主体存在的自我;而通过模态的区分,笛卡尔屏蔽掉了非纯粹理智的心灵模态。那么,在抽象的排除之后,唯一剩下的作为思维主体的本质的就是纯粹的理智思维。如果排除掉纯粹的理智思维,就不存在一个思维的主体能够被认识;而一个思维的主体的存在之所以被认识,恰恰就在于自我处于纯粹的理智思维之中。如Martial Gueroult所说,“因为我不能通过除理智之外的方式认识自己,我立刻认识到我的本质是绝对理智。并且因为我只能是理智,而不是想象和感觉,才能让我知道我是什么。”[8] 37因此,纯粹的理智思维就是作为我思而存在的自我的本质。
由此可见,笛卡尔寻找自我的本质的过程中仍然是围绕能够确证“我存在”这一事实的因素展开的。可以说,这里的纯粹思维是一种对于“我”这一实体的存在的直接把握,正是“我存在”在“我思”与“我的本质”之间架起了桥梁。
三、“我思”与“我在”的同一化
目前为止,笛卡尔已经证明了“我在”是普遍怀疑中的例外,以及“我”的本质是纯粹思维。要想达到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结论,还需通过某种途径联系“我在”与“我思”。笛卡尔采用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我”这一主体将“我思”与“我在”的本质等同起来。他在“第二沉思”中写道:“思考?在这里我找到了它(本质):它就是思考。只有它才是不能从我身上分离出去的。……我是一个真实的和真正的存在物。怎样一个存在物呢?我可以说:思考着的。”[6] 27既然已经证明了“我思”这一本质不能从我的身上分离,那么就可以得出,如果没有纯粹思维,也就不会有一个正在思维的主体(我)被思维了。换而言之,“我”与“我在”的关系是纯粹思维的关系,我是在思维的关系中确定自我的存在的。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思考着的”存在物,“我思”与“我在”被“我”这一主体初步联系起来了。
此处论证的重点在于将主体有效性与对象有效性等同起来。关于主体有效性,即“我认识到的如此这般的自己”,笛卡尔是这样论证的:“因为事实上,我看见了光,听见了声音,感到了热……至少这是确定的,似乎我看见了光,听见了声音,感到了热。这是不会错的……而在精确的意愿上,这就是思维。”[6] 29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思维的主体之所以存在,乃在于我思考到我在进行思考,即使思考的内容可错,但思考这一心灵活动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我”只有是一个思维主体才能通过思维确定我的存在,这也就关涉到了笛卡尔对于对象有效性的论证:“很明显关于我存在这个认识的精确意义既不依靠我不知道存在的东西,也不依靠那些凭想象捏造的东西”[6] 28。“我在”的确定性是通过对“我思”这一活动、这一本质的发现而被认识到的;既然在纯粹思维中我认识到我是纯粹思维者,那么我就确实是纯粹思维者——笛卡尔就这样在纯粹思维的关系中确定自我的本质与自我的存在。
到此为止,“我思”与“我在”已经在本质上等同起来,如《哲学原理》中强调的,“思考而不存在是不可能的”[9] 196。同时,虽然这个结论一般被称为“我思故我在”,但笔者认为,不能将 “我思”与“我在”理解为因果关系,即由“我思”这一前提推出“我在”这一结果——二者其实是相互支撑、互为前提的。如果不先从普遍怀疑中凸显出“我在”这一确定性事实,就无法证明有“我”这样一个思维主体,所谓的“我思”自然无从谈起;而如果无法正确认识到我的本质即纯粹思维,亦不能证明我的思考中存在任何确定的因素,“我在”的根基就会被动摇。正如笛卡尔在对“第二反驳”的答辩中的解释:“当某个人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并没有通过一个三段论推理从思考中推出了存在,而是通过精神的直观认识到了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6] 140。
四、“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
虽然“第二沉思”的最终结论一般被表述为“我思故我在”,但事实上,笛卡尔在论证过程中是先证明“我在”而后证明“我思”的。为何要以这样的顺序构建“我思”论证呢?(3)如前文所述,笛卡尔虽然亦将“我思故我在”视为一种心灵直观,但本文此处的讨论将不仅限于直观层面,即尝试以逻辑的方式构筑“我思故我在”的论证思路,以此尝试反映笛卡尔这一命题中的自我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我思故我在”中自我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有助于我们理清其中暗含的逻辑过程。笔者认为,笛卡尔需要首先构建起“我”的绝对地位,这样才能为后面的纯粹思维提供确定的主体。在“第二沉思”中证明出“我在”这一结论时,他这样表述:“我是(有我),我在,当我宣布它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想到它的时候,它必然是真正的。”[6] 25这一结论不仅说明了“我在”,更彰显了所谓的“宣布它”和“在心里想到它”,即“我思”,与“我在”的紧密关系,同时树立起了“我”的主体性地位。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结论,似乎又可以引发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对笛卡尔的这一结论进行论证重构,即将其中的所有代词“它”进行替换,并且尝试按照符合逻辑推理的格式书写。这样,可以获得下面这个推理:
前提:
当我在思考“我在”时,
结论:
我在必然为真。
由于笛卡尔在第二沉思的答辩中反对将其以三段论格式进行理解,因此在此暂且不去尝试补充那个显然很难得到证明的大前提,仅仅着眼于“第二沉思”的“我在”论证中已经明确给出的前提和结论。这句论证是在“第二沉思”的中间部分提出的,虽然还没有对“我思”进行详细考察,但笛卡尔此时已经初步具有了较为清晰的将“我思”与“我在”联系起来的思路。显然,这一思路在后文中也得到了持续贯彻,因此采用此句逻辑性较强的表述进行分析。在这一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前提中出现了两个“我”:第一个“我”是整个句子的主词,而第二个“我”是充当谓词的“我在”这句话中的主词。
首先考察前提中的第二个“我”以及 “我在”这一谓词。显然分析到此处,已经不能用“我思故我在”简单地概括这一结论了:如果回顾前提,会发现“我在思考”这一活动的对象被明确定为了“我在”。正如A. 凯莫林指出的:“‘我思考’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的表达……思想这种行为本质上需要一个被思想的对象”[10] 80。而在笛卡尔的这一证明中,“我在”显然就是那个“需要被思考的对象”。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关于第二个“我”以及“我在”,需要考察的问题有二:第一,如果我思考的不是这一结论中的“我是”、“我在”,而是“猫在”、“天空是蓝色的”或别的以“我”以外的事物为主词的句子,能否从前提推出结论?第二,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两个“我”的指代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是否一定要确保第二个“我”与第一个“我”是同一个“我”,才能够确证“我在”必然为真?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在笛卡尔的哲学思考进行到“第二沉思”的这一阶段,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笛卡尔已假设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而在“我在”论证中,也仅仅达到了“我”这一个唯一的确定性。他明确提到,只有“我”在思考我存在时的想法才是由“我”的本质激发而产生的[6] 26。可以这样理解:思考不一定为真的东西应当可以确保“我思”的存在,因为“至少这是确定的,似乎我看见了光,听见了声音,感到了热。这是不会错的,恰当地说它是在我心里叫做感觉的东西;而在精确的意愿上的,这就是思维”[6] 29;也就是说,即使“我”仅仅是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心灵活动,“我”也的确是在思考。但是,思考不一定为真的东西却不能确保“我”存在,因为“很明显关于我存在这个认识的精确意义既不依靠我不知道存在的东西,也不依靠那些凭想象捏造的东西”[6] 28;也就是说,只有当我思考“我存在”这一确证的事实时,才能在最确切的意义上证明我的存在。正如Martial Gueroult指出的,“首先被确证的事物(即我思,译者注)不能依赖于尚不可知的事物,并且这些未知的事物被假定为无。”[8] 36前文已分析过,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首先证明的是“我在”的确定性。因此,唯一能够有可能作为“我思”的对象的也只能是“我在”。也有学者对思维活动的实体进行区分,以论证“第二沉思”中的“我思”应当有一个确切的对象:“‘我思’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它的成立按照笛卡尔的看法依赖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差异:只有我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不可怀疑的,而(除了上帝)其他所有实体的存在都是可怀疑的。只有当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时……‘我思’才得以成立”[11]。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只有在思考“我在”的时候,前提中的“我”与结论中的“我”才能是同一个“我”。这一思路有一定依据,且与这一部分中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总之,前提中的“我思”并不是任意的一种思考,而需要是一种关涉到自我存在的认知行为。通过这种认知行为将“我在”或“我存在”这一真理呈现于“我”的思维中,“我”才能构筑起主体不可动摇的确定性。(4)例如Cottingham就持类似观点, 参见John Cottingham,Descartes,Oxford&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6.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一论证在“第二沉思”的阶段应当被更准确地构建为“我思考我在,故我在。”
在这种视角下,“我思故我在”确实可被视为一种非三段论形式的推理。而这一推理的核心则在于以上讨论的“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如果将“我思考”这一前提补充为“我思考我存在”,那么根据“第二沉思”的思路,以“我在”作为被思想的对象的“我思”就能够在仅仅有“我在”作为唯一的真理被确证的情况下,确定主体“我”的存在。这样,从“我思”到“我在”的过程也就不是如反对者所言的非逻辑的了。Jaakko Hintikka曾对“我思故我在”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推理提出另一种质疑,其关键点在于,思考同时作为一种陈述和认知能力,在存在意义上是不连贯的:我不能一边思考这个陈述,一边又相信它是真的。[2]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实际上“我思考我存在,故我在”的内部逻辑并非是在将“我在”或“我思”作为一种陈述进行思考的同时判定其为真,而是在已经证明了“我在”为真的前提下,通过“我在”这一确定的事实与“我思”这一主体的本质推出“我”这一主体的确定性。总而言之,通过对“我思”、“我在”与“我”这一主体之间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构建起笛卡尔这一推理的内部逻辑。
关于第二个问题,“第二沉思”中比较模糊的是,笛卡尔并未强调第一个“我”与第二个“我”是否一定要是同一主体。当然,按照所论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已经不能被除主体以外的东西替代了。那么,此处便可着眼于笛卡尔对“我”这一人称的适用范围的限定。首先要澄清的是第二个“我”作为存在的主体,其指代范围是什么。在经过本文第二部分对“我在”中“我”的本质的探讨已经能够明确,作为主体的“我”不是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具体个人,而是一种心灵实体。在这一前提下,第二个“我”的指代范围应当被限定为心灵中的纯粹思维。如果能够确证自我存在的那个自我不是纯粹思维,那么就存在产生错误的可能性;这样,“我在”这一确定的事实就有被颠覆的危险。同理,如果思考到“我在”的那个“我”,即“我思”的“我”不是纯粹思维,就不能保证其绝对正确,“我在”这一作为确定知识的结论也就存疑了。用Martial Gueroult的表述来说,“既然关于‘我’存在的知识只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思维,‘我’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思维,因此也只能被理解为纯粹的心灵。”[8] 36总之,应当将“我思考‘我在’”这一前提中的两个“我”视为同一个纯粹思维。其次,虽然笛卡尔在“第二沉思”的证明过程中是先确证被思考到存在的那个“纯粹思维”,后确证思考着的那个“纯粹思维”,但这两个行为的主体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应当没有先后之分。因为,在“我”思考“我在”的同时,“我”的存在就能在现实与思维中得到确证,而“我在”也必定是在“我”的思考中才能够成立的。“如果我知道我存在,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在思考;……所有的知识,作为思维,包含一种必然性:我只知道自己是纯粹的思维,因为我明白有必要从我的存在中排除一切非纯粹理智的东西,等等。”[8] 46-47作为纯粹思维的“我”思考到了自身的存在,因而“我”以纯粹思维的形式确实存在,这也许能够构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较为精确的表述。这样,关于上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自然明确了:第一个“我”与第二个“我”应当是同一个思维主体,且这一主体的指代的纯粹思维。
五、结语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通过寻找“我在”这一普遍怀疑的例外、发现“我”的本质在于纯粹思维、将“我”的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三个步骤,初步建构起了被称作“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单就这一论证过程,笔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传统的“我思故我在”模式在“第二沉思”中应当被理解为“我思考我存在,故我在”,以此建构起“我思”与“我在”在自我这一主体内部的逻辑关系。在这种建构中,可以以一种推理的视角对“我思故我在”进行讨论,而非仅仅局限于其作为心灵直观的认识层面。第二,在将“我思故我在”重构为“我思考我存在,故我在”后,前提“我思考我存在”中指代主体的两个“我”之间的关系可进行商榷,如二者需要被视为同一主体,且其指代范围需要被限定为纯粹思维等。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一般认为笛卡尔是在1637年出版的《方法谈》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而在《第一哲学沉思》之后的《哲学原理》等书籍中,他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复对解释和修改。因此,本文所谈仅仅为“第二沉思”中与“我思故我在”相关的部分,而提出的问题也是针对“第二沉思”中的论证过程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