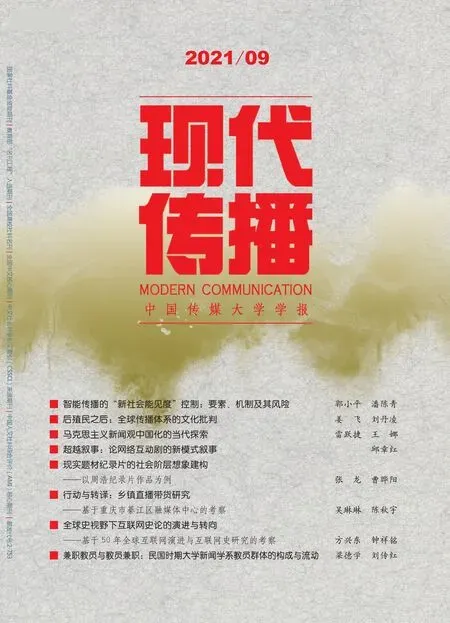逻辑转变与维度构建:智能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 王 虎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已经进入罗萨(Rosa)所说的“加速社会”①,科技加速、经济加速、社会加速,信息和人财物一样高速流动,带来信息泛滥、技术沉溺、数字鸿沟、疫情高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等社会性难题。在防控措施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将面临个人隐私泄漏与公共安全之间、技术高度发达与人的主体性丧失之间的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些挑战、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不仅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也需要相关学科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层面给予积极回应,构建新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体系②。
新冠疫情体现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在社会治理层面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疫苗研发、疫情防控、诊断救治,还是民生保障、复工复产,人工智能在新冠疫情下的场景应用加速落地,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智能应用的多方面、深层次需求。赫拉利(Harari)认为,基于大数据和复杂算法的人工智能使当今世界正经历“从智人到神人”的巨大飞跃,其革命性“比从猿到人的转变还要深刻彻底”③。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信息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和社会服务力,这都离不开智能媒体作用的发挥④。新闻传播学当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关注智能技术对媒介自身资源的整合、功能的提升乃至对传播伦理的影响,关于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在关系、机制、路径等方面还是囿于以往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关于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和方法构建研究还有所缺失。如何在社会媒介化持续演进的大背景下,挖掘社会治理体系背后的传播逻辑和技术逻辑,探究智能媒体在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创新作用,推动新型传播体系、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和文明生态的构建,需要新视角、新逻辑和新维度。
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媒体运行逻辑
传媒是最早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之一,传媒业务中的事实核查、信息采集、生产和算法分发等环节大量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媒体向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方向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传播生态成为未来媒体运行的核心引擎。同时,智能媒体与信息社会下的各行各业产生互动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相互关联、融合互动,逐渐形成强大的媒介社会生态,智能媒体以一定的社会角色介入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构成更紧密的社会关系⑤。基于以上特征,未来媒体运行的逻辑将向生活化、关系化、生态化演进。
一是媒体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早在1960年,互联网概念提出者利克莱德(Licklider)就指出,人机共生是人类和计算机合作互动发展的目标,二者将实现非常密切的耦合,合作做出决策和控制复杂的情况,而不依赖于预先确定的程序⑥。这是人类对人机关系设想的最早注脚。4年之后,麦克卢汉(Mcluhan)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从技术上模拟意识阶段”⑦。利克莱德和麦克卢汉的设想在智能媒体时代成为现实,在人体延伸的最高阶段,媒体作为内嵌在社会逻辑中的技术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愈发显著,即人类借助媒体延伸自身的感觉器官和情感体验,媒体则通过不断学习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功能实现自我进化,人与媒体从未像今天这样相互嵌入,突破“迷思”⑧,形成人与技术物的功能复合⑨。智能媒体可以满足人类社会对异质性新生产特征的追求,用户需求成为各种传播通道的核心,连接起传播价值链的两端,推动实现人与媒介的一体化。
二是内容与关系的紧密融合。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社交网络时代,内容与关系的交织就成为各类新媒体建立和维护自身社会资本的基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在多维度需求、场景精准匹配、用户自主生产和服务驱动下,媒体的社会资本呈现出网络效应,媒体和用户的连接和沟通成本显著降低,使“我们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更容易找到彼此”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深度开发关系的新基础,关系黏性成为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智能媒体的呈现形态和商业模式也更为丰富,在与多元主体、关系网络、社会行业的互动融合中,实现更为强大的开放性和无所不在的渗透性。
三是传媒业与其他行业边界的消融。人工智能打破了行业间的固有边界,尤其在信息的流动、匹配、确权、社会信任等层面,为媒体与不同行业间的连接和相互渗透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信息传播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两个方面推进媒体融合进程,一是交叉式融合,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媒体间的融合;二是嵌入式融合,智能媒体作为广义上的“媒介”将不同领域的事物连接起来,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媒介形态,而是成为一种普遍连接的、社会生活赖以发展的“基因”,将原本分散的社会主体、经济和生活场景相互联通,从而让任何主体都可以低成本在媒体平台上获得便利,让媒体与社会生活在融合互动中相互促进,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
三、现代社会治理视域下媒体社会功能的演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子系统,媒体以其传递信息、监测环境、协调关系等功能,成为社会结构、规则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赋能媒体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的变革,从而构建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和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最终将实现以人为本、发达便捷的新型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面对当时经济危机影响下的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等难题,胡德(Hood)首次提出“新公共管理”的概念,认为公共部门要实现专业化管理、转向组织单元的分解、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随后“公共治理理论”开始在西方兴起,将治理主体分化为社会组织、机构、媒体乃至公民,依据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决定参与程度并融入社会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奥斯特罗姆(Ostrom)进一步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用分级别、分层次、分阶段的多样性制度设置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系统共治。多中心治理强调以治理体系的开放性、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共同构成现代社会治理复杂而富于变化的内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善治”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它是指“利用民间和政府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管理和伙伴关系,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状态”,有学者认为善治理论是多中心治理的最高要求和理想状态。多中心治理向善治转化,代表着社会治理生态观的形成,它强调社会治理的主客体由共同参与转向有机统一。智能媒体以其与社会生活的高度嵌入、信息与关系的深度融合、促进行业之间的渗透融合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将为智能社会生态的构建起到关键性的中介和融合作用,推动社会实现斐迪南·滕尼斯所说的“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二)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不断增强
喻国明指出,当今社会的主流趋势就是媒介化,传播的逻辑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逻辑和核心法则,媒体将进入社会生活重构的非内容领域。在媒介社会学看来,媒体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它影响社会、作用人心、服务民生的能力使其成为多元治理的核心协调力量,它在履行治理职能时往往兼具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的多重角色,为了避免角色间的认知冲突和社会责任的混乱,需要破除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认知框架,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在媒体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中重塑媒体新的主体性。
从治理主体角度来看,媒体既是社会治理的协助者,又是公民参与的动员者。它可以通过自身技术优势帮助政府收集、分析、分发有效信息,还能够向公众提供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空间和功能性平台。从政府角度来看,媒体可以推动政府与公民之间商议治理社会问题的进程,诸如电子政务、电视问政以及在新媒体公共空间中各种回应机制、问责机制的完善。从公民角度来看,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赋予公民一定的议程设置权利,一些与公民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关注,公民的话语权、与其他治理主体的互动强度都得以加强。从治理工具的角度来说,媒体是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途径,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能力,创新了民主治理模式,还能在政务服务、电子商务、在线医疗等方面提供优化社会公共服务的新窗口。
(三)智能媒体发展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我国的媒体融合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的第三阶段即媒体深度融合阶段,强调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化媒体与人的连接,推进媒体与其他行业的深度嵌入,媒体的社会服务功能被突出,这既是万物互联时代对媒体运营模式的探索,也与现代社会治理息息相关。廖祥忠认为,新闻传播理论范式正在向信息传播理论范式转型,后者的聚焦领域经历了媒介融合、智能媒体再到媒介与社会一体化同构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范式中,智能媒体的本质特征就是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科技支撑”,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还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它不再是中性的,而作为‘座架’(gestell)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以智能媒体技术为核心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将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更好地打通信息和数据壁垒,构建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智能媒体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以科学的系统框架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广泛应用的社会治理场景、完整的社会治理生态等构成。
四、智能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构建维度
媒体智能化的目的也并不仅是传媒业自身的繁荣,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触点,激活与带动经济社会的全盘发展,打造高度复杂、全面和现代化的智能社会结构系统。
(一)安全维度:智能媒体+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保障网络文化安全
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内外的界限日益模糊,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无界性、难控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网络意识形态战场的争夺,必须创新治理的技术和方法。
新冠疫情已经充分说明,国家和社会安全也是媒体的传播逻辑、运行机制和融合路径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网络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件,占领舆论场和提升治理能力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两翼,二者的有机融合是面对后疫情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础。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连接和能量交换平台,媒体在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沟通、情绪疏导、舆论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在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最前沿的当下,既有的舆论引导方式和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力逐渐失灵。智能媒体在感知智能、计算智能、认知智能等方面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引领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形成治理机制的价值,在有效化解舆情危机、提升治理能力方面体现出核心要件的价值。可以基于国内外社交媒体的内容汇聚和信息智能分析,实现境外跨平台、跨语言的大数据内容汇聚,深度挖掘、分析和预测用户需求,生产和传播更多“流量爆款”产品,以互动增强黏性,进而引导用户;还可以通过跨类型大数据的知识化处理和语义化融合,有效发现和挖掘舆论动向、分析政策及公共决策反馈、及时预警危险舆论信号等。
以智能媒体为核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是保障网络文化安全的基础建构。全媒体传播与智能化科技的发展是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智能媒体是媒体融合发展和媒体进化的必然方向,它将人机对话和器物仿真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躯体在数字科技和文化融合的氛围中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媒介,人、媒介、物三者一体化发展的“万物皆媒”时代悄然而至。以智能媒体为核心、以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框架构建网络文化安全体系,可以将政府、传统社会组织、网络社会组织、网民等多元主体有效连接,构建全媒体传播时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多元治理结构,依靠传播手段推动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模式。
(二)信息维度:智能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商务数据、环境状态数据、行为数据和物理实体数据是智能社会运行的基础,O2O应用、场景应用以及各种共享平台都离不开对这些数据的采集与深层应用。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数据功能和信息服务方面具有全息、全员、全程的优势,可以推动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
在专业化方面,数据的获取、分析和分发已经成为智能媒体运行的标配,随着媒介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对这些数据信息的高效获取和应用已经超越传统媒体的运行领域,其手中的数据资源可以为整个社会的内容生产、信息流动和价值流通提供更为专业的匹配、驱动和管理服务,通过有效的数据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在信息化方面,智能媒体不仅是社会信息流动的驱动力,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大脑和躯干,形成“平台汇聚+智慧中枢+协同治理”的新型模式。当前,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开始着手以智能媒体为核心,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广泛纳入媒体矩阵、政务服务、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功能,提高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成为“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智能化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往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发展,“智慧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城市由“治理”到“智理”转变,体现出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和人性化。在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上海成为首座摘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WSCA)桂冠的中国城市。面对疫情,上海城市运行的“一网统管”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它将与入境人员有关的公安、政府、社会、企业、感知等数据源源不断地汇聚,打造了一条由“入境转运”到“落地管控”的闭环之路,提高了城市的“免疫力”,高效的智慧应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向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全响应型”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它以全面精准的个体化信息集成为治理基础,强调“全面感知”的制度设计,即通过大数据随时采集民意,并为民意表达提供便捷的网络通道;建立“全响应型”社会服务管理指挥系统,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与执法机关等共享、交换相关数据,达到社会的联动与精准化管理。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城市联动管理具有全员参与、数据支持、精准对接的特点,成为“全响应型”精细化模式的主要优势,大大提高了社会精准化治理的效力。
(三)经济维度:智能媒体+数字经济,助推智慧经济发展
智慧经济是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为先导的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之一。智能媒体以其广泛的用户和关系资源、强大的计算和分发能力,与不同产业、经济形态乃至经济场景之间互动融合,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它主要体现在需求引领、场景驱动、技术赋能和跨界合作等方面。
智能媒体拥有广泛的信息和用户资源,可以更好地感知和引领用户需求,挖掘潜在的用户价值,不断催生新的数字经济形态。丰富的场景资源是智能媒体的优势,当越来越多的信息与服务依赖场景这一变量时,场景本身可以成为信息组织、关系组织与服务组织的核心逻辑,成为“信息—关系—服务”连接的纽带。当前智能媒体在智慧旅游、智慧教育、电子商务、电子竞技等领域不断丰富的场景应用,都是以场景为核心重新构建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入口,场景成为智慧经济发展的决胜场。事实上,这些场景本身就具有较强信息传播属性,是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延伸。
智能媒体的技术赋能可以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治理问题。层出不穷的数字产业形态、错综复杂的价值联结通道,带来价值量化、交易确权、信用背书等一系列难题。实际上,媒体用户的信息消费场景中蕴含着大量的互动价值和情感价值,这些价值的有效流通和变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块链技术和通证经济模式,可以有效保障这些价值转化为可供使用的数据,再将数据转化为资产,并进一步将资产转化为有价证券,从而为媒体中广泛的互动和连接进行价值量化和灵活变现,赋能智慧经济的良性发展。
智能媒体也在与其他行业不断融合,新的商业平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人民网发布的《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规划》明确,将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生产体系、传播体系、商业体系,重构互联网内容生态,强化开发数字经济产业能力。主流媒体的跨界融合,为探索媒体参与数字经济创新模式提供了有益经验。
(四)生态维度:智能媒体+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治理生态建构
由各种媒体平台、形态和功能组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引导舆论、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生活的有力保障。因此,从生态观的角度看全媒体传播体系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二者有着较大程度的重叠与交叉。
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式创新正在全方位重建既有的媒体生态。从生态视角来看,未来的媒体是人与媒介在特定场景中进行互动的网络节点,为了确保信息、数据、价值等在生态中的有序流动、顺畅沟通和精确治理,确保社会治理由场景化向生态化发展,智能媒体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媒体的生态融合为社会治理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多元治理主体都可以从生态融合的高度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社会责任。
智能媒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生态建构,需要将全媒体传播体系化,其核心路径是在大量占有用户和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实施“软硬兼施、合纵连横”策略。“硬”是通过与硬件厂商合作,打造用户内容消费的入口;“软”是通过内容的生产和聚合,打造品牌力和公信力,增加用户黏性;“合纵”就是接入广泛的电子政务和公共服务资源,以本地用户的聚合和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发展O2O业务;“连横”就是形成媒体传播矩阵,构建一体化的舆论引导和公共服务平台。基于此,以“智能媒体+社会治理”为基础架构的全媒体传播生态,应当包括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协同发展的全媒体矩阵平台、云媒体内容集成服务平台、智慧城市综合应用数据平台,此时的智能媒体不再作为一种具体的媒体形态或工具,而是作为基因嵌入到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交叉叠加的复杂网络,成为整个社会生态的有机组成。
(五)人性维度:智能媒体+人性赋能,促进人机协同发展和智能文明建设
在社会媒介化的进程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也正在消融,虚实融合成为未来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则。但是,过度强调流量逻辑和机器智能的算法,会导致人机关系的错位和人主体性的异化,以及信息茧房、隐私侵犯、数据滥用、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等系列问题,使得人在这场信息技术变革中的地位越发渺小,甚至会演化出一种新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在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化为“神智”的时代,多数人将沦为赫拉利(Harari)所说的“无用阶层”,因为“技术公司或平台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向我们出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从产品到政治观点”。智能技术发展对人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延伸人类智力、增强人类,同时也有可能取代人类。
在未来的虚实社会的治理中,智能媒体要实现治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必须要解决人沦为技术附庸和人的主体异化问题,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共生和协同演进。生态观强调的是技术、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产物,而是鲍尔格曼(Borgmann)提出的“人—技术—世界”系统交互作用的生态产物。近几年,为了实现未来社会治理精准化与人性化的结合,混合智能的理念被提出,它兼具机器智能和生物智能的优势,以二者的协同运作为目标,将后者的环境感知、自我学习、道德判断与机器智能的生产分发能力结合起来,将价值和道德标准纳入智能设备和算法的标准,库兹韦尔(Kurzweil)称赞“它们结合起来的力量将十分强大”。
注释:
① [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③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④ 高晓虹、崔林、付海钲:《以媒体融合发展助力社会治理》,《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5日,第9版。
⑥ J.C.R.Licklider.Man-ComputerSymbiosis.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IEEE,1960.p.4.
⑦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⑧ Vincent Mosco.TheDigitalSublime:Myth,Power,andCyberspace.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p.1.
⑨ 曹劲松:《现代传播中的人与媒介融合》,《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19页。
⑩ [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沈满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