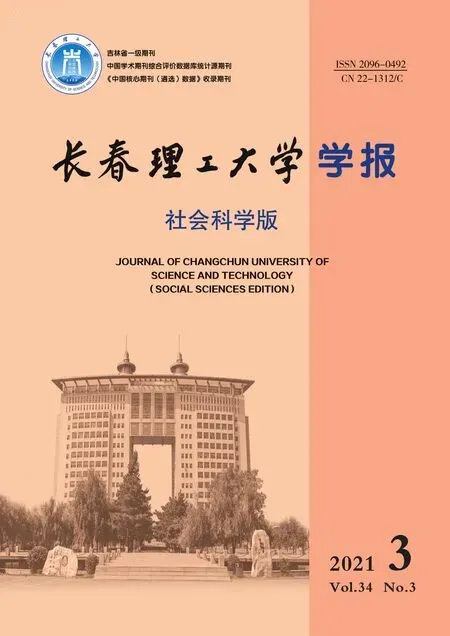论《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异国形象
曲 涛,矫 杰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44)
一、引言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在西方评论界,乔治·艾略特的名声现如今已经超过狄更斯和萨克雷,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尤以其对现实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力和对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腻笔触而闻名。艾略特不断突破当时传统且规范化的叙述方式,是一位产量不高但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2]在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弗吉尼亚·伍尔夫称赞她为“女性的骄傲和典范”。[3]经过时光的沉淀和岁月的磨砺,艾略特于1876年出版了其最后一部作品《丹尼尔·德龙达》(DanielDeronda),该小说生动地描绘出1865-1866年间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隅,凝结着她关于宗教、历史、文化等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思考与沉淀。
这部小说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现主要集中于女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互文性及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如殷企平(2015)着重分析了艾略特对女主公关德琳·哈利斯的心智成长之路的刻画,点明了心智培育对于女性自我成长的突出作用。[4]Priyanka Anne Jacob(2016)以小说犹太故事主线中屡次出现的物品——银扣为承接点,梳理了这一犹太物件在天主教书籍的中世纪起源部分以及英国宗教史上的相关重大事件,甚至延伸叙述了其作为珠宝的未来性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发展。[5]此外,徐颖(2017)通过对《丹尼尔·德龙达》与《旧约》两卷的互文研究,揭示出《丹尼尔·德龙达》“流亡”与“复归福地”的主题。[6]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丹尼尔·德龙达》的研究再现新的热度及视角。
现如今,比较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较新兴的学科,它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7]12但其研究意义并不是鉴定文学作品中某一形象的叙述或呈现是否吻合该形象在现实中的真实性,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这不仅对“他者”具有认知意义,对主体自身的端正也具批判性。但目前鲜有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理论视角对《丹尼尔·德龙达》进行阐释的文献,因此本文试从比较形象学角度入手,对小说中的“异国”形象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剖析犹太人物的言行特征及犹太部分的故事情节等,探究《丹尼尔·德龙达》这部作品对先前被刻板化的犹太人的“恶”形象的颠覆、重塑原因以及该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此彰显艾略特犹太性书写的创新与独到之处。
二、犹太“恶”之形象的颠覆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开始推崇伦理道德并追求宗教信仰,但随着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后,进化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唯心主义宗教观,使宗教和科学产生了冲突与碰撞。这导致维多利亚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8]这种两难困顿的处境在文学界的表现尤为显著,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这样充满了各种思潮和变革的背景下创作出了《丹尼尔·德龙达》。当时,英国人民对犹太民族排斥和歧视的情感早已根深蒂固,反犹主义盛行于世。徐新教授曾指出,反犹主义是指“一切厌恶、恐惧、憎恨、排斥、仇视、迫害犹太人的思想或行为……即认为犹太人从本质上、历史上、宗教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不应与之交往、理应受到谴责或一系列迫害的劣等族群。”[9]犹太人在英国社会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他们甚至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也体无完肤。英国作家的笔化身为尖锐的利器,将犹太人在作品世界里钉铸为“恶”角色。正如布吕奈尔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10]这也从文学领域印证了反犹主义渗透之广、之深。不难发现,在诸多英国作家笔下,犹太人道德败坏、贪婪吝啬、冷漠无情、狡诈诡辩、视财如命,代表人物有《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的主人公巴拉巴斯;《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艾凡赫》中的艾萨克;《雾都孤儿》中的老费金;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描写了一群依仗权势谋取暴利,令耶稣和信徒们所痛恨的犹太人。这便是将犹太民族“人格化”,是反犹者丑化、贬低犹太人的重要内容,在反犹动员的不断塑造与宣传下,犹太人丧失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格,被妖魔化。[11]由此可见,大部分英国作家笔下犹太人的形象是负面的、丑恶的、鄙俗的。这种以偏概全、有意加之的刻板形象是十分片面的,过度简化了犹太民族的特性。甚至在《丹尼尔·德龙达》这部小说中,也能找出许多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对犹太人抵触的例子。例如,当米拉(Mi⁃rah Lapidoth)被男主人公丹尼尔·德龙达从水中救回船上后,两人在交谈时米拉便担心自己会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歧视。
“我出生于英国,但我是一名犹太人……你因此看不起我吗?”米拉低声问道,声音里透露着莫名的悲伤,像是一只小动物在恐惧下发出的呜咽声。
“为什么?”德隆达说。“我没那么傻。”
“我知道很多犹太人都是坏人。”[12]160
当然,刻板印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少部分作家将犹太人的邪恶形象逐渐善化,如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对犹太人物丹尼尔、末底改(Mordecai)和米拉的描写便颠覆了这一定型化形象。由于艾略特打破常规、创新性地对犹太人物进行了褒奖式塑造,使得当时许多评论家们对《丹尼尔·德龙达》一书中的犹太故事线争议颇多,产生了两极化的英国式解读和犹太式解读,以至于艾略特的收官之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完全积极的反响。
《丹尼尔·德龙达》采用了双故事线并行交错的叙事结构,小说共有八章,前四章的故事主线是家境没落的英国中产阶级小姐关德琳·哈利斯(Gewen⁃dolen Harleth)的悲剧婚姻。从第五章开始为犹太故事线,主要叙述了从小生长在英国上层社会的男主人公丹尼尔·德龙达,在得知自己的犹太身份后,便果断放弃高贵的英国公民身份,在末底改的召唤下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故事。小说中关德琳所代表的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和以丹尼尔为代表的犹太精神世界,表达的不仅是两个不同的主题,还运用了两个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文体。两个故事同时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西方的、基督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是现代化的欧洲。[13]也正是由于丹尼尔对关德琳孜孜不倦地开导和帮助,将两个看似冲突分割的故事线串联起来。丹尼尔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绅士教育,为人正直善良、从容淡泊、敏而好学、有自己的主见,作者几乎将丹尼尔这一角色刻画为近乎完美的圣人。通过丹尼尔的视角,读者们可以客观地看到英国上层社会贵族生活的奢靡场面,以及当时绝大多数英国贵族的通病:目中无人、心胸狭隘、固步自封等特性,影射出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背后所垢着的拜金主义、宗教信仰危机和贫富差距悬殊等一系列社会冲突的加剧。
在小说的犹太部分中,除男主人公丹尼尔之外,另有两位犹太人物不容忽视,即末底改和米拉。丹尼尔先是在水中救起对生活绝望的犹太女孩米拉(实则为末底改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并主动帮助她寻找失散多年的犹太家人,以此拉开犹太故事的帷幕。由于米拉十分擅长歌唱,丹尼尔在听过她的歌声后十分赞赏,不忍见她被埋没,便决心帮她找舞台。
“我想我认识一些女士,她们会在圣诞节后为你找到许多学生。”德龙达说。“你不介意在想听你唱歌的人面前一展歌喉吧?”
“当然不介意,我想赚点钱……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找我学习,那就很难了。”米拉笑了,带着一丝他从未见过的喜悦。“我敢说我的母亲应该过的很拮据,我应该为她挣些钱。我不能总是靠施舍过日子。”[12]308
由此可见,米拉不是传统印象中的柔弱女子,她不仅没有坐享丹尼尔对她的资助,相反她积极主动地找工作以图养活自己,十分独立乐观。而丹尼尔为了尽早帮米拉找到失散已久的母亲和哥哥,他常常游逛于犹太人的生活区域,试图找到突破口。一日,他冥冥之中来到一家二手书摊,从众多冗杂的书籍中挑选了一部波兰犹太人所罗门·迈蒙的自传。他在付钱之际,见到了末底改,这是二人的首次相遇。“他的年龄很难推测,枯黄的皮肤像是一尊古老的象牙雕刻品……那是一张十分典型的犹太面孔……容貌特征十分鲜明,眉毛不高但很宽,留着一头清爽的黑发。可能他的脸称不上特别俊朗,但却能让人感觉到其中饱含着力量。”[12]319叙述者十分客观且准确地刻画出丹尼尔对末底改的初识印象,末底改虽具有犹太面孔,但丹尼尔并未对他产生任何抵触心理,相反却感受到了力量。在丹尼尔询问书价时,末底改十分感兴趣地与他交谈:“‘你是位有学问的人,你对犹太历史感兴趣吗?’他的语气深沉但却十分急切……‘你或许也是犹太人?’”[12]320字里行间透露出末底改对丹尼尔也莫名怀有某种巧妙的熟悉感,为后文揭示出丹尼尔的犹太身份埋下伏笔。
随后,丹尼尔被科恩母亲邀请去参加犹太人安息日的聚会,他原本想借此契机打探米拉亲人的消息,结果竟再次遇到了末底改。这次会面,叙述者对末底改的服饰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末底改并没有身着漂亮的安息日服装,也没有穿早上那件破旧的、满是腐渍的黑外套,而是穿了一件浅褐色的外搭。看得出来这件衣服之前是白色的、宽松的,现在像是洗缩水了。这身衣服使他乌黑的头发和热切的面孔更加惹人注目,像是先知以西结的脸庞。[12]329
原文中对于末底改的诸多样貌描述都是一身正气,字字句句都穿插着末底改是犹太先知化身的寓意。按照巴柔的界定,“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14]作者艾略特对于末底改这一“异国”形象的描写刻画,实际上是借助朴实无华的犹太人物特质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民夜郎自大、奢靡度日等风气的批判。末底改的博学广识拨开了丹尼尔心头对未来的茫然,引导着丹尼尔一步步走上寻根之路。文中对末底改心理活动的描写,也揭示出丹尼尔和末底改之间神秘的身份牵引关系。
他想找到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必须是犹太人,有智慧、有修养、道德感情强、热情等……他的脸和身材必须俊丽且强壮,他必须已经习惯了精致的社会生活,声线须流动自如,所处的环境必须远离肮脏的需求,他必须具备着荣耀犹太人的可能性。[12]391
丹尼尔便是这样的天选之人,而末底改的所思所想投射到现实中便正是丹尼尔的伟岸形象。虽然在小说第七章才揭开丹尼尔的身世之谜,然而读者并不会觉得出乎意料。相反读者在丹尼尔的个人经历中,已经潜移默化地做好了心理预期。故事的最后,末底改因病英年早逝,丹尼尔与米拉结合,他继承了精神先知末底改的遗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复兴犹太民族文化的道路。三者的故事情节相互依存,层层推进,都共同依托着“寻找”这一脉络,米拉“寻找血亲”,末底改“寻找犹太精神的继承人”,而丹尼尔则是“寻根”。从犹太故事文本的叙事进程中,体现出叙述者对于末底改犹太先知“异国”形象的成功塑造,对于犹太遗志最佳继承人丹尼尔身份的精彩扭转,以及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种族伦理意识形态的密切关注和阐释。
三、形象背后的文化反思——世界主义
对“异国”形象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将形象是什么梳理清晰,更不可忽视形象创造者的作用和意图。换言之,“异国”形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更具解读价值。若将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写就可看作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感受,而注重研究形象创造者一方,也就等于注重研究阅读和接受者一方。[7]6因此,他者形象与塑造者是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必然联系之中,二者相互作用。在《丹尼尔·德龙达》中,乔治·艾略特对犹太人物丹尼尔、末底改和米拉的形象塑造,开陈出新地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一经发表便引发强烈争议。尽管出版社极力相劝,让她删减掉犹太故事情节,但她一直坚持己见保留了全文。艾略特对这一形象的坚持和塑造,影射着她从“反犹”到“亲犹”的态度转变,这与她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艾略特自小一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也曾歧视犹太人为劣等群体。直到1841年她随父亲迁居到考文垂市郊后,结识了一批思想自由的学者和政治激进分子,并阅读和翻译了大量哲学和科学进步思潮的文本,使她对基督教产生质疑,与福音派教会彻底决裂,开始向“亲犹”转变,被称为“英格兰第一位不信上帝的伟大小说家”。[15]她曾在书信中提到:“对犹太教,我们这些受基督教教育成长的西方人尤其有愧。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之间绝对存在着一种宗教与道德情感的特殊联系……因此,我觉得应该给予犹太人同情和理解。”[16]最为特别的是,她与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犹太青年学者伊曼纽尔·多伊奇的结识,使她对犹太文化有了新的审视。伊曼纽尔·多伊奇(文中末底改的现实原型人物)曾辅导她学习希伯来语,指导她阅读犹太经典,并向她介绍了犹太民族的宗教和习俗。故艾略特多次游历于欧洲各国,不断地购置犹太书籍、参加犹太的教堂活动等,丰富了自己的宗教人文视野。夸尔斯曾说:“乔治·艾略特的宗教活动史是整个维多利亚英国信奉上帝和《圣经》的历史。”[17]正是这些经历日益扭转了她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偏见,使其将新鲜的价值观念熔铸于她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出末底改这一“异国”形象。
同时,在《丹尼尔·德龙达》的情节安排和人物中也体现出作者对犹太文化从反抗走向亲近以及她胸襟中的世界主义。主人公丹尼尔的亲生母亲——伯爵夫人利奥诺拉(Princess Leonora Halm-Eb⁃erstein),因自小厌倦自己的犹太身份,便擅自做主将丹尼尔寄养在朋友雨果爵士(Sir Hugo Mallinger)家中,替丹尼尔规划了一条英国绅士的成长道路,希望儿子能远离、乃至摆脱犹太身份。“我有权从我所痛恨的束缚中寻求自由……我希望你能逃离出这种生而为犹太人的禁锢,我已经竭尽全力做好母亲的本分了。”[12]519但丹尼尔在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之后,并没有抵触自己的身世,相反这更坚定了他要完成末底改未完成的犹太事业的想法。
在寻找祖先的过程中,他仿佛发现了另一个灵魂:他的决策力不再徘徊于由公正的同情心所建构的迷宫中,而是秉持着高贵的偏袒之心——这也正是男人的真正力量所在——去选择更为亲密的伙伴,让同情心变得更切合实际,抛弃鸟瞰般审视的理性,这种理性原本是要避免偏袒、避免失去对品质的所有感觉,而是去选择一种慷慨的理性,让有共同传统的人士肩并肩地走到一起。[12]620
丹尼尔在发现自己另一个犹太灵魂时,并没有拘泥于犹太人的宏图,相反他将自身放置于整个世界的背景下,怀有世界主义的情怀。此外,基督教作家行文历来都会遵循着基督教拯救异教徒的故事脉络谋篇布局,而在这部小说中艾略特却一反常态。叙述者不仅安排主人公丹尼尔放弃英国国教,改为信仰犹太教,甚至将末底改塑造为犹太先知的神圣形象。正是末底改的先知召唤,引领丹尼尔走上了犹太复国道路。诺普弗莱尔马彻认为,这部小说中的犹太故事,为信仰沦丧的英国基督教社会提供了避难所。[18]艾略特通过自强不息的犹太精神来鞭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拜金主义等现象,隐喻着生生不息的犹太精神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救赎和引导作用。换言之,这种故事走向实则是隐含作者的支配。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指出,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19]即对于许多小说家来说,他们的写作过程正是一个发现和创造自己的过程。因此,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或多或少地都会在各个方面相互关联。隐含作者的选择本身就已经隐喻着作者对于她所讲内容的伦理立场和态度。换言之,丹尼尔的妈妈象征着过去,即作者艾略特过去对犹太的误解和抵触态度,而丹尼尔最后选择回归犹太身份,不仅象征着犹太民族的复兴伊始,更彰显了艾略特对犹太民族文化的尊重以及自身对于犹太文化态度的改变。
另外,叙述者也几度借丹尼尔和末底改之口表露出世界主义的博大主题,即: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之间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这种单一的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被推广为全人类所认可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20]
在小说开篇,丹尼尔曾在解释为何自己要出国游学时,使用了明确的世界主义词语,“我希望成为一个英国人,但是,我也希望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并且,我希望在学习过程里,摒弃仅仅用纯粹英国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的做法”。[12]152此时的丹尼尔已建立了完备的世界主义情怀。而末底改也主张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应该享有独立和平等的权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事业,都是世界的一份子,都对世界有贡献。”[12]439言外之意就是呼吁克服种族偏见,求同存异,建立一种国际社会。这俨然具备世界主义宏图的雏形。在文中末底改曾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四分之三个犹太教徒。”[12]532即基督教和犹太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当了解其他区域的人们,关注他们的文明、他们的论证、他们的谬误、他们的成就。这样做不是让我们达成某种共识,而是有助于增进彼此的理解”。[21]末底改甚至提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在成长,它将欢乐与悲伤、思想与实践交织在一起,但又在不断扩展。它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以形成自己的形式,并把这种思想作为新的财富回馈给世界;它是一种力量,是国家这一伟大构造中的一个器官。”[12]435他前瞻性地预言了一个建立在世界意识之上的不同种族的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虽都出自丹尼尔和末底改之口,但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隐含作者或者说是艾略特所怀有的世界主义胸襟和广识的文学知识。“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这个世界的成员,融合于一个共同的人生命运:不论远近、肤色和信仰,经受不同磨难的人们因磨难而成为同一个世界的公民。”[22]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的创作上已然实验性地达到了世界主义的高度。
四、结语
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这部小说中对犹太人物的形象塑造,不囿于传统、开陈出新地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犹太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呈现出了犹太人物身上坚毅勇敢的爱国光辉。艾略特对于犹太性的书写,不仅显性地体现在男主人公丹尼尔身上,也隐性地体现在犹太精神领袖末底改和坚强独立的犹太女孩米拉的身上。这部作品真实地影射出乔治·艾略特对犹太民族的态度从排斥到友好的转变,她借助小说中犹太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呼吁各民族应独立平等共存、高歌世界主义的思想,为当时发生信仰危机和处于观念转折期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视角,这是极具道德拯救作用和跨时代意义的。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