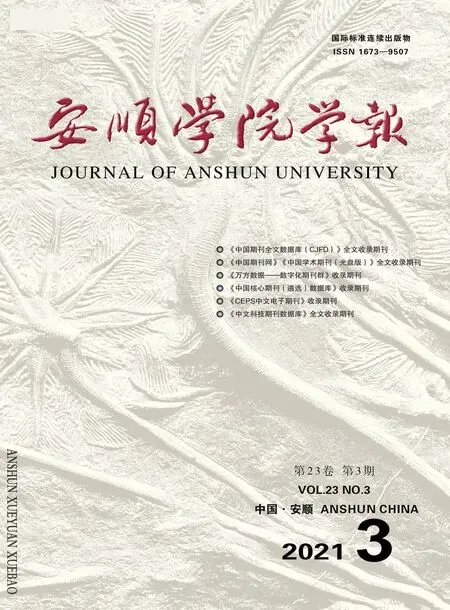从先秦到魏晋:“琴”诗意象美学内涵的基本定型
张菁洲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与推进以对“天人”关系的认知为外在表现形式,对性、气、理、情的关注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开辟了表里澄明、自在无束的审美境界,意象的混融、审美的中和、主体的显隐实际是哲学思辨的体现,文学创作生存在哲学理论构建的宇宙论、人生观之下,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在意象的选取与运用以及意象个体涵义之演变,无不表露出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对“天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一、先秦:鬼神信仰与“琴”的礼制作用
原始时代的先民在敬畏自然与向自然索取的矛盾中寻求“鬼神”的慰藉,先民的敬畏是出于求生欲的本能,故愉悦神灵的祭祀活动在彼时只注意到形式本身,并不涉及精神的探索,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此时人有迷信而无知识,有宗教而无哲学。”[1]。
(一)从娱神到娱人:人情与礼乐的调和
夏商周时期,人们通过祭祀的形式达到神人沟通的效果,在先民眼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神秘力量,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礼节制度,“礼”本作用于巫史文化的祭祀仪式,用之神、推及人,沟通天地人三者,由于古代中国的宗教意识并不发达,在不断专门化的祭祀活动之下,“礼”的使用范围转化为祖先,体现了祭祀者的追思、怀念、仰慕、尊敬等多种高级情感。《尚书·益稷第五》载:“戞击鸣球,抟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2]127孔颖达疏曰:“此舜庙堂之乐,民悦其化,神歆其祀,礼备乐和,故以祖考来至明之。”[2]127这种祭祀活动常伴随着某种人为要求,古人认为音乐、歌舞能起到娱乐作用,故“礼”常伴随“乐”的参与,《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3]1327-1328“琴”作为祭祀礼器见证了原始信仰的展开方式。
古史时期的“颛臾改制”利用先民对自然崇拜的迷信意识,实现以神职兼王权的宗教性转化,于是神与人、个体与社会等多重关联开始被建立起来,祭祀活动参与到贵族教育,而“琴”的实体及其相关参与到贵族教育成为技艺课程的“六艺”之一。《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4]352“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种乐曲,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技艺,“六艺”作为身份和修养的象征被运用于生活和社交中,贵族对繁育和血缘的重视又决定了技艺施用于婚姻生活的普适性,对生殖的崇拜是原始欲望在血缘势力的裹挟,于是“琴”从取悦神灵求得庇佑延伸为取悦对象期盼家族兴盛。《诗经》中对“琴”的描绘更加证实了其期盼子孙绵长的功利性质,《关雎》诗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3]26以“琴”取悦心仪的对象,既深情又克制。《女曰鸡鸣》诗曰:“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3]295通过琴瑟的和鸣表现出婚姻关系的和谐畅达和双方的相敬如宾。《莆田》诗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3]838此诗以琴瑟取悦“田祖”之神,以期风调雨顺,实现“穀我士女”的最终理想,形成了求神为人的内在逻辑,刻画出由娱神到娱人的内在历程。与《诗经》中其他表达婚恋的诗歌相比,带有“琴”意象的诗歌流露出中正平和、顺天应时的情感态度,而《汝坟》《野有死麕》《柏舟》《狡童》等诗则更加直白地表露出“以琴会偶”的思维方式。《诗经》中两种不同的情感倾向是礼制与人欲的交织,体现着贵族集团与平民团体的交互影响,更是先秦宗法制度建立的标志,在《诗经》体系中,对神灵的敬畏谱写出庄重肃穆的《商颂》,而那些活泼热烈、缠绵动听的“琴”诗却主要出现在西周及其后的《国风》之中,因为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兼有政治统治和血亲道德的双重功能,它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关系的基本精神渗透于民族意识之中。
当“琴”的施用对象从通神沉降为娱人,音乐就具有了调和人心、规制社会的重要作用。礼仪制度反映出等级压制和资源权力的不均,而音乐等审美性娱乐就成为调节民心、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以促发良善的意志使人们安居乐业,强化认同,于是以音乐观风俗、观社会的观点以“季札观乐”事件为标志走向成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有吴国公子季札聘问鲁国时的观乐与评乐活动,季札通过辨听各国地方音乐给出盛衰兴亡的判断,揭示出音乐风格与风俗制度的关系,说明了“乐政”的合理性,此种“乐政”之理想成为先秦乃至汉代政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曰:“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5]30将声音之道从一国之政联系到家庭人伦之关系,《荀子·乐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5]53其关键之处在于以“气”的生发变幻解释音乐的雅正与淫邪,与宋明理学家之“理气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一直到汉代,班固仍以“乐政”之观点看待音乐生发之机理:“哀乐之心感,而歌詠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詠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5]5乐府诗承担起了《诗经》以来的政治功能。
(二)“琴”归何处:制度转变下的文学生态
礼乐制度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因素,它开启了后世制度、思想、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而礼乐制度必须以王权的绝对保障作为施行前提,当政权不再集中,统治趋向弱化,礼乐失去支撑则必然走向崩坏而从贵族流向民间,礼乐散失的过程也是民间文化的塑造过程,制度的改变也使“琴”的文化内涵发生改变:其一,随着古代贵族政治逐渐弱化,原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制度走向解体,旧有制度的破坏为思想的解放提供必要条件。儒家维护传统礼乐文明的做法,实际上是维护旧有制度的理论依据,而另一部分人以此为契机开拓新的领域,当人的力量不再被神性压制,人的主体作用得到重视,一种类似于“人本主义”的东西开始生根发芽,《国语》中记载了展禽的一段话:
“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德令哲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6]
人本主义的发端使人们从对神的关注沉降为对人的关怀,施用者与受用者走向重合,通过对“琴”等乐器的操练,神性与人格得到过渡、融合。其二,孔孟学说奠定了“琴”在品性修养中的理论基础。既然神性被突破,那么礼乐制度必然要寻找到另外一种精神作为支撑,孔子“克己复礼”的观念正好填补了理论的空白。孔子从礼仪节度的文化形式中体悟出“仁”之所在,“仁”在孔子这里是人伦关系的总和,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1]46对鬼神之敬畏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人伦道德之重视,人论塑造作用之发挥使“琴”成为君子美好品格的代名词。其三,老庄学说拓展了“琴”的文化内涵。如果说孔孟学说强调修养志性的必然与重要性,那么老庄学说则赋予了“琴”俊逸潇洒的文化内涵。老庄之学本于杨朱之学,从本质上看都是当是当时传统制度是反对者,他们跳出礼乐文化的氛围去观察并思索人生,向往着出脱物外的高度自由。在老庄的思想体系中,玉帛礼器不再具有独立品格,而是除道体之外事物的符号,通过弃圣绝智的方式反对在礼乐制度严格要求下的理想君子人格之塑造,实现解放天性的最终目的。随着《庄子》“等万物”“齐生死”观点的成熟,物我界限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以道之观点观物成为精神流向,于是“琴”因为“道”的灌注从礼器功用中抽离出来,另辟施受一体、物我无间的境界。至《列子·天瑞第一》所载荣启期“鼓琴而歌”之故事,则成为忘尘超脱、物我两忘的代名词,远昭“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琴”获得了崭新的文化内涵。
《毛诗序》时代“六义”说已经成熟定型,确定了“名物+普遍认同义+深层情感义”的表达结构,即如闻一多在《说鱼》一文中所说“鱼”强盛的繁殖力是先秦时期的男女都渴望具备的能力,严格的宗族制度赋予鱼令人追索的美好品质,于是《诗经》中的“鱼”不再是单纯的游物,而是“鱼作为实体+生殖力+宗族制度”的综合。同理,如前所述,《诗经》中的“琴”诗具备了社会人伦的必要条件,凝结出“琴的实体+祭祀敬畏义+典雅宗正的情感取向”的内在结构。“琴”在历史的衍变过程中逐渐由单纯的个体名物升格为礼乐制度的隐喻标签,在历代文人雅士的创作语境中,又进一步演变为蕴含人格品质、寓意深邃的意象符号。
二、汉代诗歌琴意象的类型与品质
汉儒的基本思想是以“天人”对举,又以“天”为价值取向,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加入下,人的行为举止与内在品质均与外物相关联,既可以通过外物表现出来,也可以从外物的浸润中得到调节和整化,强调物与我的双向交流与互动,以“琴”为代表的五音声乐被认为的人情欲的表现和抒发方式。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开了盐铁会议,此次会议决定了汉代学术和思想的发展风向,贵德贱利、重义轻财的儒家原则占据主流。因此,在汉代,“琴”的文化内涵融汇于正道归德的风雅趣味。
(一)汉代经学家视域下的天“道”与“风雅琴”
1.“缘木为琴”的五行机制
随着汉代帝国中央集权的统一,礼乐制度在政权的支撑下得到复归,成为阴阳五行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体,在这一时期,“礼”与“乐”的分工更为明显,且拥有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哲学依据,“礼别异”,将人按照血缘、地位分成不同的等级,“乐发和”,用来修饰这套体系,提供审美愉悦,这不仅是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是天道理论施用流行的必然。西汉经学家以阴阳家之言说经,借鉴阴阳家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等方式构建的宇宙空间联系起万物生化感通的思维模式。《周礼·大司乐》载:“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4]578已经体现出音乐施用由神到人的逻辑递进。《汉书·律历志》以音律配天时,以黄钟、林钟、太簇三律入天地人三统。《吕氏春秋·月令》与《淮南·时则训》以五音十二律配四时,提出了春木音角,夏火音徵,中央土音宫,秋金音商,东水音羽的五音五行生发理论。
冯友兰先生指出,天地皆为物质、皆属自然。古代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使人们产生了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中判断吉凶祸福的要求。从劳动中获取的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适应体现为祭祀活动严格的规定,其时令、乐曲的运用要求符合“天道”变化的终极规律。随着音乐与五行的紧密结合,五行的主体性质逐渐转移到五音,《尚书·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2]301抓住了五者的自然特征,孔颖达疏曰:“万物之本,有生于无,者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2]302又曰:“木金阴阳相杂,故可曲直改更也。”[2]302“木”处中,最受阴阳交感,其形质随阴阳之气而曲直,“琴”属木,故其能体现人情感之正邪,阳胜阴则正心克礼,雅音流化,阴胜阳则淫邪妄生,艳曲俗弹,两种不同的情感倾向与气运方式为诗歌中“琴”意象的分化与凝固提供了阴阳五行与乐理的支撑。
2.汉代诗学经学化与“风雅琴”的固化
皮锡瑞谓两汉为“经学昌明时代”,汉代的文化、政治活动以经学为主要依据,《诗经》成为汉代诗歌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参照。汉代经学家在展开诗学理论的建构时以经为预设前提,刘勰以“征圣”“宗经”为作文之圭臬,或与汉代诗学之经学性质密不可分。经学家所提出的以政治教化为本的价值观、“发乎情,止乎礼义”为本的原则判定了汉代文学作品的生死,左右着汉代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汉代诗学以《毛诗序》为发展高峰,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观念灌注出“风雅琴”意象的产生。《汉书·礼乐志》谓礼乐可以调和天地人三才的自然秩序并完成治乱的思想成为主流,作为礼乐一环的琴成为个体修养的必备工具,班固《风俗通义》也将琴视为乐中之“君子”,显然,汉人将琴视作修身养性之必要工具,一直到宋代郭茂倩编著《乐府诗集》,仍然以社会治乱、礼乐要求为诗教的价值标准:“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7]821延续了先秦以来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传达出追求“风雅”的社会趋向。
(二)老庄思想的裂变与“情意琴”
劳思光先生认为汉代哲学思想有两个变化:儒学从“心性论中心”转变为“宇宙论中心”,道家学说追求“情意我”之自由变为追求形躯之永生。“宇宙论中心”体现为五行与五音之匹配,“超越我”之形躯化“琴”意象的分裂。老庄学说中隐藏于天道之下的自我原本是独立而崇高的,在原始道家思想中,外在的声色物欲是隔绝人本然之性的存在,唯有“去智”“绝欲”,方能无限接近道体。在阴阳五行学说的侵蚀下,天逐渐取得凌驾于人之上的主体地位,天地阴阳成为决定事物数理变化的重要力量与最高价值原则,在阴阳激荡的宇宙体中,人的“情意我”就被无限缩小,最终被天意和伦理肢解,分散在事物的内外,最终表现为阴阳五行与事物的通感,也即董仲舒所谓“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老庄之学说以人道适应天道,抛却外物的拘束,董仲舒的理论以天道束缚人道,寻求外物的束缚,“心性之善恶问题本身亦由自觉根源问题变为材质问题”[8]。外物之形气材质直接体现其秉受天道的具体过程。在老子原始的思想体系中自我精神超越形躯之上,汉代思想语境下“超越我”具象化为“永生不死”的形躯追求,肯定形躯的情感要求与抒发,“琴”作为名物被赋予了哲学的内涵而与人事物取得普遍关联,成为“形躯”情绪之载体,如《西北有高楼》一诗通篇未出现一个“琴”字,却处处渲染出“琴”音中透出的哀伤,借“琴”的意向抒发出离别的感伤,以心通琴,以琴传情。蔡邕《胡笳十八拍》诗曰“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溃死兮无人知。”[7]861又曰“对萱草兮徒想忧忘,弹鸣琴兮情何伤。”[7]864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情欲物气之要求。为什么“情意自我”的散失能进入到诗歌领域呢?从乐府诗的技法来看,作者对偶然事件的选取、对话形式的运用、在叙事中融入主观情感以及一唱三叹的回环复沓等创作手法有助于作者将主体情感杂糅到诗歌文本中。无论是像蔡邕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好,还是普通的社会民众也罢,他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诗作文本必然是时代的选择,是历经磨合之后的言志代表,哀婉诉肠、悲切迷离,是时代选择了文本,亦是文本选择了时代。
三、魏晋“琴”的乐理化
如果说先秦名家强化对个体直觉的需求,那么此时已经具备了理性自觉的条件,随着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天人之分”逐渐明晰,个体自觉逐渐从群体意识中抽离出来,在清谈玄风的推动下,逻辑层面的“名”“实”之风推演为语用层面的“言”“意”之辨,考察“言论”作为外在表意符号与内在思维的互动关系,探讨“言”作为能指与“意”作为所指的内在逻辑。“言”可以借助言语结构本身或修辞手法等手段,使能指与所指无限接近,其结果就是分裂了各语素的表意功能,破碎漂浮的语素为语义场的扩充提供了可能。
(一)“声无哀乐”
从某种角度来说,言意之辨实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情志的分裂、发展,故其又分化为名理辨析和情志辨析两个层面,这一发展贯穿了魏晋玄学的发展,人们对音乐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将“琴”的名与实、言与意之关系提升到新的境界,其文曰:“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9]198又曰:“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9]225情感为“实”为“意”,声音为“名”为“言”,心将哀乐寄托于音声,而非音声本身有哀乐。声音之“名”触发情感之“实”,则“琴”之名可存“情”之实。人的主观情绪是“琴”的性体,而五声八音是“琴”的气用,音乐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是表达的工具,必须要与情志相结合才具有完整的沟通功能,那么,“琴”的能指必须要包含深层所指,情感的本质并非声乐,只是借助其得以显现,声音本身并不表达情感倾向,这就与宋明理学家的“性”“情”观念有相似之处,“性”本身寂然不动不带任何情感,情感通过“七情”的方式得以宣泄,只是“情”的发用,“性”才是本体。“言”“意”之辨的解决以“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辞”为标准,于是到魏晋时期“琴”作为意象树立起清新高雅的语用表征,“琴”在指称上建立了“名”与“实”的联系,进一步固化了“借琴传情”的语用方式。
(二)审美意识与文论的发展:山水“隐逸琴”
魏晋时期养生避患的黄老之说转变为善言玄理的老庄清谈,其内在追求也从自然寿命的延长转变为精神世界的自满自足,内心充实的生活成为普遍向往,对自然美的欣赏,同时,“越名教而任自然”与郭象“独化论”深化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自然”开始具有独立的人格,“‘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即‘独化之理’也。”[10]75物自生自化,其全部动力及行为都包含于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事物自成一体互不相联,相反,郭象认为事物间存在普遍而紧密的关联:“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10]75物自化并与外物联通的思维模式刺激并推动了魏晋自然美学的发展,并催生了山水文学的兴起。另一方面,随着汉末士族集团的形成,士人地位上升,自我意识的增强,士大夫内心的自觉迎来了思想上的独立与解放,心灵的满足与安顿成为重要的课题,余英时先生指出了士人内心高度精神化与文化审美的深层关联:“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熟,而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悠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11]人与文艺的感通激发深层次的审美情感,“借琴传情”获得了成熟的理论支撑。
(三)公共场到私人域:“琴”境的变迁
随着士大夫主体精神的突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获得独立的发展契机,当作者主体精神灌注于文学作品中,作品中的各个因素都沾染作者的主观意识,诗歌情境从公共领域逐渐转移为私人空间。《诗经》是先民农业、田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故诗歌的发生场景主要是田野、祭祀、桑间、水洲等公共场所,如《七月》《采薇》等。到了汉代,乐府以及《古诗十九首》里已经有作者独处楼阁的情境渲染,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12]410作为代言体的诗歌,这种孤坐高楼的情境是诗人的想象。在“崇有”与“独化”“名教”与“自然”的碰撞冲击下,魏晋时期的文艺与人性、个人与群体、自然与制度等关系得到深入思索,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最终答案下,文士们用自由的笔触表达恣意的人生态度,指向自然和永恒,魏晋诗歌已经出现了作者的家园、田庄等私人环境的描绘,如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12]332就是作者此刻此地的当前情态之表露,诗歌中的情境已经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视域,从某个角度来说,“琴”的意象在私人视域中更能体现出其品格的涵养。“琴”被赋予了洒脱纵化的哲学意味,如陆机《拟行行重行行》诗曰:“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12]435表现出任情忘物的思辨倾向。至六朝,佛教文化已经渗入中土,“不立文字”的观念消解了文字的权威性,突显个体的感悟力,文学走向私密化、私人化。
至此,“琴”的意象已经有以下涵义:其一,表达礼仪节度中庄严肃穆的情绪,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君子品格,如谢惠连《琴赞》曰:“峄阳孤桐,裁为鸣琴。体兼九丝,声备五音。重华载挥,以养民心。孙登是玩,取乐山林。”[13]1202-1203其二,表示忧愁感伤的心情,如王粲《七哀诗》:“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12]329其三,表达思念之情,如陆机《拟东城一何高》诗曰:“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12]436其四,表达潇洒闲适的情感,如丘迟《题琴朴奉柳吴兴诗》曰:“边山此嘉树,摇影出云垂。清心有素体,直干无曲枝。”[13]1200魏晋时期是思想的转变与混融时期,“儒家理想多表现为世间的和谐与安定,道教理想多表现为自然的愉悦与适意,而佛教理想多表现为心灵的空寂与淡泊。”[14]160三种思想在文人士大夫胸中交汇出可进可退、恬淡自守的人生情趣。
结 语
文学可以显现制度,制度背后蕴含的是深层的文化现象,先秦诗歌的“抚琴”意象是神人交织的原始信仰之产物,也是民俗文化的载体。“琴”作为礼乐制度的产物体现出士人的生活情状,当“琴”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蕴并印上了时代的情感后,它就在长期的反复运用中固定并延续了该时代的内涵,补充了“琴”意象的语意。约定俗成语义内涵常常造成一种先入之见,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一个语词所获得的语义内涵总有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稳定性。”[14]100当“琴”出现在诗歌里,就包含了诗人对它语义功能的整体认知,呈现出它所有可能的意蕴。“常被诗人们写在诗里的词的象征涵义,其本身虽然只不过是语义扩展和隐喻比况,但从它的演变轨迹上来看,却与不同时代诗人的人生情趣与审美方式息息相关,透露了不同时代人们心境与视境的变化。”[14]109“琴”在各个时期的象征意蕴并不会轻易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