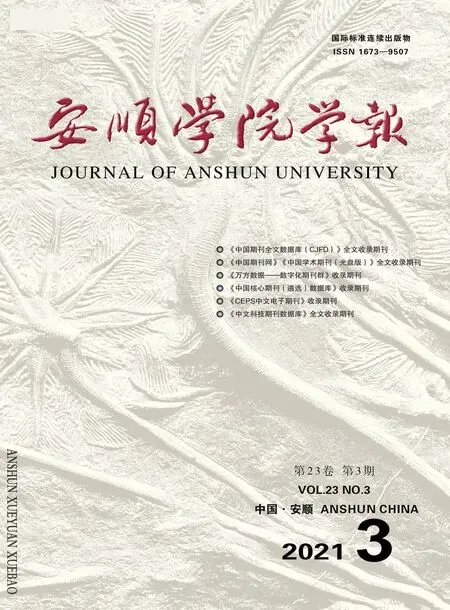解读《安顺城记》中屯堡人“渔樵耕读”具象
王文杰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凝聚几个好人,做成一件好事”,是钱理群先生晚年的口号。“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是《安顺城记》的序言标题。《安顺城记》以“安顺”这座地方中心之城为象征,以其行政辖区为主体而进行历史描述的地方史、区域史。并以现代史观、现代视角,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品格,借鉴国史与方志各显优长的编撰特点,采取通史与专史结合、纪传体与纪事体结合的方法,运用最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整合旧有的地方史资料,重构解放前的安顺历史,修纂一部角度不同、手法新颖且富于现代语境的新方志。这也是一部以安顺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为中心的地方史书,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安顺文化,突出安顺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色。全书涵盖安顺领域的生命史学,是一部融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文学为一体的“大散文”笔调书写的宏篇巨著,是安顺历史文化中值得高歌一曲的大事。作为安顺地方屯堡文化爱好者,本人有幸得了一套,翻阅之后深受震撼和启发,联想起安顺区域屯堡人家的“渔樵耕读”文化具象,并进而对之再深入解读一番,探索其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以飨同道。
安顺屯堡移民既有自己独立发展和不断丰富的艰难历程,也有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遗风,既有山地区域的文化特点,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一方面,他们执着地保留着其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山地耕战耕读生活中,他们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安顺屯堡传统民居多为江淮建筑风格的栖山式四合院或三合院,在众多的屯堡村落,移民而来的屯堡人依然坚守“耕读为本,崇文尚武”的儒家文化。尤其屯堡大户人家将其理想内核表现于建筑体上,在房屋上雕刻“渔”“樵”“耕”“读”图案或题字。这些图案,有的雕刻在垂花门罩上,有的雕刻在门簪上,有的雕刻在墀头上,有的雕刻在窗棂上,有的雕刻在隔扇门上,在典型的屯堡村寨随处可见。渔樵耕读虽出自古代四个历史典故,却有着中国几千年古朴而深邃的文化内涵,屯堡人把它带来了安顺山区并“知行合一”地践行了这一文化具象。
一、“渔”与艺匠列传
“渔”代指捕鱼的渔夫,讲的是东汉才高八斗的严子陵不愿为官,隐身垂钓终老的故事。严子陵是东汉时期浙江余姚人。王莽请他做官,他躲藏起来。几年后,严子陵的同窗刘秀击败王莽,建立东汉王朝,史称光武帝。光武帝思贤若渴,到处寻找隐居的严子陵,三番五次聘请他出来为朝廷效力,严子陵仍旧不肯,跑进浙江桐庐隐居,垂钓终老的故事。安顺屯堡人结合山地文化对“渔”还另有深解,“渔”泛指手艺或技能,学会手艺(技能)不愁谋生;屯堡人认为“技不压身”,并以“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教育子孙,不惜拿出钱粮或帮人做工,也要送子孙去找有技术的能人当师傅,迄今为止,屯堡人依旧信奉此理。
在《安顺城记》第七卷《艺匠列传》里记载:1.鲍大千,安顺鲍家屯人,传为屯堡妇女服饰——丝头系腰制作工艺的第一代传人。丝头系腰是屯堡人的独有服饰,将棉线和丝线用特制的工具以独特的工艺编织而成。当年以返乡学艺的壮举给鲍氏后人带来福荫的鲍大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带子老祖公”的尊称,并因此而在其族人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2.苏石匠,传为清后期屯堡石匠,安顺文庙大成殿前的一对透雕龙柱,乃其惊世绝作。龙柱高齐殿檐,长约一丈五尺,径近三尺,各重十来吨,整石整料,工艺精湛。“极雕琢之巧,双龙蟠曲对起,攫拿云浪中,栩栩如生,昂首相向,鳞爪隐现;下负以狮,巨观也……各国旅游者至此,皆摄影以作纪念。惜作者未留名,但传曰‘苏石匠’。”[1]6443.陈明鼎,约为嘉(庆)道(光)间木工名匠,平坝人屯堡人。所建房屋多在黔中各县,至今犹存者仅白云庄的三个院落。平生得意之作,为道光十七年(1837年)参加安顺文庙修复建设,所承担之木工活,极尽技巧。《平坝县志》记载他在文庙的各项任务:“告成迅速,各柱凿眼无一歪斜,无一加屑。圣座雕刻尤空透玲珑。适西道出巡,见之大为嘉赏。知府遂给以终身免去安顺七属当差之官文,以荣宠之。”[2]4.谢玉清,镇宁城西街屯堡人,修复镇宁钟鼓楼,工艺精湛,雕刻尤为精美;5.陈先才,关岭屯堡人,安顺区域有名的铁匠大师,其品质和工艺超群,远近闻名;6.杨正南,紫云屯堡人,精于石雕,独力修造一幢祠堂,工艺精湛,形态逼真;另外李齐二、胡金庭、吴绍阳、黄炳荣皆安顺屯堡后人,精于面具(俗称“脸子”“戏面”,是安顺地戏的主要特征和标志)雕刻,形神兼备,子孙传承而形成流派至今;王六寿、刘汉培是安顺最著名的戏曲艺人,名满黔中;余建奎,安顺屯堡人,全国闻名的刀具名匠,安顺三刀(剪刀、菜刀、皮刀)奠基人;林清和,著名厨师,最拿手的菜品是宫保鸡,远近闻名。
安顺屯堡艺匠大多来源于江淮移民后裔,因历史原因来到贵州腹地,山地为主的喀斯特地形地貌,无法沿袭江淮水乡的渔业生活,智慧的屯堡人因地制宜进行技艺转型。安顺艺匠其实不计其数,大多至今仍有传人。《安顺城记·艺匠列传》收录以上14人作为典型代表,皆因他们聪明睿智,敬业专注,对技艺精益求精,且敢于改革创新而名满黔中乃至华夏而录入《安顺城记·艺匠列传》,其工匠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和铭记。
二、“樵”与工商列传
“樵”代指砍柴的樵夫,讲的是西汉樵夫朱买臣砍柴为生坚持读书,遭妻子嫌弃仍不改其志的故事。班固《汉书》记载朱买臣出身贫寒,热爱读书,虽满腹经纶,到四十岁还是个落魄儒生,靠砍柴卖钱求生。朱买臣的妻子不堪与其同过贫穷日子,离开他改嫁。朱买臣决心不变,发愤图强。后当了汉武帝的中宪大夫兼文学侍臣,其妻痛悔身亡,朱买臣出资安葬。安顺屯堡人结合山地文化对“樵”另有深解,“樵”泛指资源,安顺山地的茶叶闻名遐迩,奇珍异宝生长在山上,况且山由土石堆积形成,有山便有土地、石材、雨水和生物等生活生产资源,屯堡人占有了山地资源,便想到拿去交易,也就能获取吃、穿、住、用等必需资源,不断地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安顺城记》第七卷《名商列传》里记载:1.邹庭贵,安顺郎岱铁业富商,少时饱经忧患,轻钱财而重德行,创业成功富甲一方,身后仅留存三百亩田产给后人,万贯家财多用于济贫救困和地方公益事业,其美德至今口碑不绝。郎岱官绅商民合赠“修其天爵”匾额,以表彰其德行等美誉。2.简敬斋,安顺旧州晚清儒商,旧州简姓第十二代孙,自幼家贫,然慷慨有大志,处事豁达诚朴,见义勇为,创业成功虽久居在外,对家乡旧州时时牵怀和资助,获知府孙钦晃赐“乐善不倦”匾额,在广西桂林又获得“贤劳卓著”等多个匾额旌表其德。死时旧州乡人设位以祭,空巷往吊,有痛哭失声者,传历时七天七夜,请道士作法事,诵经文以遥祭亡灵。3.孙绍万,安顺蔡官人,少贫以驮煤为生,盐号富商,创业成功后依旧勤俭布施,修孙氏祠堂立“凡我子孙但有贩毒、吸毒者,孙家一律不认,并逐出家门”[1]2399家训,乡人习称“孙苗大公”。4.邓子英,安顺绸布号大儒商,创业成功虽家财累万,生活仍极俭朴,带头捐资助学,喜好早起、养花、读古书、下棋,曾有一副手书对联“满架有书供我读,半生无事为花忙”留世。5.邓羲之,安顺百货巨商,一生热衷公益事业和助学扶困。当时贵州文化落后,安顺地处偏僻,但邓氏兄弟颇具远见卓识,对后辈教育极为重视。无论哪一房的子弟,只要书念得好,就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深造,后人多有建树,造福一方。6.帅灿章,安顺银行创办人,帅灿章的事业,带动了安顺经济、社会、教育的发展,安顺产生了一大批如魏伯卿、伍效高、戴子儒、邓若符、贺少恒、唐用奎、丁纯武等富商,产生了谷家三中委等全国闻名人物。使安顺成为贵州西部最先进的城市。1928年,全省第一条公路,从贵阳修到安顺。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四所中学之一黔江中学也落户安顺。7.伍效高,安顺普定巨商,创业成功后积极兴办学校——普定县私立建国中学,因伍效高先生大量注入资金,在师资、校舍、设施及办学水平等方面属全省一流。为缅怀和铭记先生,著名雕塑家、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为伍效稿塑像于普定一中。古之巨商,当世富且荣者众矣。然后世存念者鲜也。今普定后人,对效高无人不尊,无人不念。何故?贫困发家,不忘桑梓,富而办学,百年树人,一世之功,万世之德也。8.戴子儒,四川来安顺的盐商,其一生理财当家,成就卓著,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干才。他以丰富学识、超凡干练、高尚人格,为商人争得了话语权,为安顺,乃至全贵州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有口皆碑的贡献。写安顺商业史必写先生,先生一生之奉献,长存于安顺商业史中。9.丁纯武,普定玉官富商,虽历经艰辛创业却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积极协助伍效稿先生办学,故去世多年仍常有乡人和学子念叨。10.魏伯卿,安顺蜡染绸布富商,广泛投资,多业经营,渐成全省有名富商。魏伯卿的成功,映射出母亲韩氏含辛茹苦、抚孤守节的感人精神。于是当时的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特请省内大书法家严寅亮为之题词写了“节贤可风”的匾额,高悬门庭以旌母恩。因出身贫寒,虽家拥巨万,犹自奉节俭,不事铺张,创业成功后好义善施而留美名。11.张元吉,安顺文教富商,在书局业拓展业务,心系百姓悲悯多行善,深明大义支持抗日。12.韩云波和叶文,夫妇创业成功后,宅心仁厚,乐于捐资助学。其碑文赞之为“临深履薄,艰苦卓绝,贤哉韩母,女中奇杰”[1]2434,考其平生,当之无愧。13.唐后物,安顺酱业奠基人,发展实业,生活简朴,勤谨厚德,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以上14名商代表,皆因创业富甲一方,且热心公益、心系家国和关怀地方百姓而选入《安顺城记·名商列传》,他们的功业在黔中大地上将名垂千古,后辈必将永世不忘。
这些名商的成就来源于中国地道的“樵夫”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和实践,讲求商业道德,建立诚信机制,心忧家国天下,关怀黎民百姓,这些文化内核已经成为他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安顺名商数百年的成功经营,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安顺名商精神遗产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而悠远。
三、“耕”与屯田店铺
“耕”代指耕田的农夫,讲的是舜耕历山修有功德的神话故事。尧舜时代,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生活。《管子·版法解》记载:“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己所不利利人者也。”[3]舜在历山耕耘,制陶,捕鱼,盖房,制具,修仓,掘井,并将其技能传授给众人,大家共同得利。安顺屯堡人结合山地文化对“耕”另有深解,“耕”不仅是勤劳,更是占有耕地和屯田。古时没有钱庄或银行,人们的财富多为田地、房屋、粮食、布匹、牲畜等实物。每遇强盗抢劫或偷窃,特别是纵火,所有财富尽失。而耕地是抢不走盗不去的,盗贼走了,耕地还在。由于安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田产不丰盛,耕业不发达,因此,屯堡人积有财富便买田买地买店铺,或自己耕种和经营,或租赁给他人耕种或经营而收取租金,就连居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也会在农村购置田地出租给人耕种收取租粮,或雇人耕种,同时农村大户也会在城里购买店铺经营或是出租。安顺商业之发达足以证明屯田和买铺之兴盛,促进了安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
在《安顺城记》第二卷《军屯志》和第三卷《店铺志》里详细记载了明初安顺卫所军屯及其遗存,其中明代卫所分兵屯田,有腹里和边地之别。故《大明会典》载洪武间贵州屯田共9307,000亩,其中,威清卫(今清镇)屯田51,350亩,平坝卫36,112亩,普定卫(今安顺)76,724亩,安庄卫(今镇宁)72,193亩,四卫合计达236,379亩。[1]850这是安顺一带屯田的高峰期。军屯的组织与实施具体来说军户世袭是卫所屯田的基本保障,土地来源及官给牛具种子,为保证收入还定有奖惩,官兵粮饷取自屯田,家属随军和军余在营等鼓励耕田政策。明代屯政在明末清初开始衰落,出现了屯堡大户屯田和土地私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大量的史实记录了屯堡人卫所军屯和民屯历史,贵州也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耕地大开发,屯田保障了当时的战争需要和后来几百年的农业发展,屯堡移民自然的延续了华夏的农耕社会。安顺自明初建城,几百年的城市发展,城市商铺繁多,琳琅满目,商业之兴盛在贵州独占鳌头。据1930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滇黔桂区经济调查队的统计,当时仅安顺一县,“计有洋纱店三十五家,干菜京果店三十五家,绸缎店二十七家,土布皮头店四十八家,杂货店三十家,山货店十二家,盐店十八家,药材店十九家,钱店八家,米店四十家,油店三十家。每年各业交易总值为数之巨,乃为全省之冠”[1]523,也出现了有名的店铺行号如绸布店、洋纱店、棉花店、百货店、首饰店、盐业店、京果酱店、肉铺店、酒坊店、油坊店、米面店、餐馆茶社、旅舍客栈、照相馆、中西药店、印刷、图书及教育用品商店等,另有商行、堆栈、钱庄、银楼和银行等等。从大量屯田和商铺的兴盛可以看出,安顺屯堡人深受传统“耕”文化的熏陶,屯田买铺思想由来已久,成就了很多土地和商贾大户,进而推进了当时安顺的文化繁荣。
安顺屯堡农耕和店铺的发展,虽然奠定和保证了屯堡家族体系的完整和延续,大量屯堡人保留了祖先的生活原型。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部分屯堡人通常是在相对窄小和贫瘠的土地里固守。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片树林或一道道山岗,挡住了他们远眺世界的目光。因此大多屯堡人是多忧虑近况而少忧虑远境的,或者说是急于近事而疏于远事的。安顺屯堡人的“耕”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百年,顽固且顽强的繁殖出庞大的村落社会及城镇并遗留至今而不衰。
四、“读”与院校科举
“读”代指读书的书生,讲的是东周苏秦刺股埋头苦读的故事。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拜学识渊博的鬼谷子先生为师,学习纵横之术。苏秦学习刻苦用功,有时候,他实在累得要打瞌睡了,便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让殷红的鲜血流出来,以疼痛来驱走瞌睡,使自己能坚持下去。学有成就的苏秦游说燕、齐、魏、韩、赵、楚等六国采取合纵之策,联合起来一致抗击秦国获得成功,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安顺屯堡人结合古训对“读”也另有深解,非常重视,“读”既指勤奋好学,更指通过学习涵蕴智慧,参加科举成就功名。屯堡人常说:“有字(智)吃字(智),无字(智)吃力”。一个有脑筋即有智慧的人只要活着,动动脑筋就能找到生路,创造或经营出财富,有脑筋的人即使一无所有,也能白手起家。屯堡人因此把读书列为头等大事或是家训头条,有百姓谚语“先盘(培育)娃儿,后盘(建设)房”即是佐证。
在《安顺城记》第三卷《校院志》和第二卷《科举志》里详细记载了省立安顺中学、黔江中学、三一小学、立达中学、普定等堆敬一学校、普定建国中学、镇宁三民小学、三民中学、清镇省立中学、关岭县城关一小、紫云县城关一小、洛河民族小学,四大寨民族小学、平坝一小、平坝固民小学、天龙小学、陆军军医学校等安顺名校。除了学校之外,出现了双桥书院、习安书院、凤仪书院、源泉书院、岱山书院、爱莲书院、悬鱼书院、梅花书院、坝羊书院、双明书院、维风书院、治平书院、凤梧书院等享誉华夏之书院。安顺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大力兴办学校和书院,为安顺乃至全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读书人和各类人才,为黔中文化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科举制在安顺开始推行之初,举子稀落,寥若晨星。随着办学兴盛和明代贵州科举制的发展,以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提供的中举名单为例,整个明代安顺共出举人243人。清代安顺科举的一大变化是首次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并允许取得生员资格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清代安顺科甲比较兴隆,出了大量的举人,也产生了不少的进士。同时清代安顺生员有岁贡、拔贡、优贡、恩贡和副贡,在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的背景下,安顺文人辈出,蜚声海内外。当然明清安顺除了文举之外,还有与之并存的武举也非常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古人“读”的文化具象与文化成果。
结 语
《安顺城记》是一部仿《史记》体例,以现代眼光、现代视角、采取国史体例与地方志体例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的、角度不同、手法新颖的地方志书。此书揭扫昔讹,正本清源,内容丰富,体例宏达,刊印发行是安顺乃至贵州一大盛事,也是中国文史界一大盛事,反响极为深远。本文选择书中《艺匠列传》《名商列传》《军屯志》《店铺志》《名校志》《书院志》和《科举志》来体现和佐证安顺屯堡人渔樵耕读的家居文化具象,从而解读屯堡人内心深处保留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渔樵耕读”精神与中原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并进而引起屯堡学者和研究者客观审视我们脚下的土地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