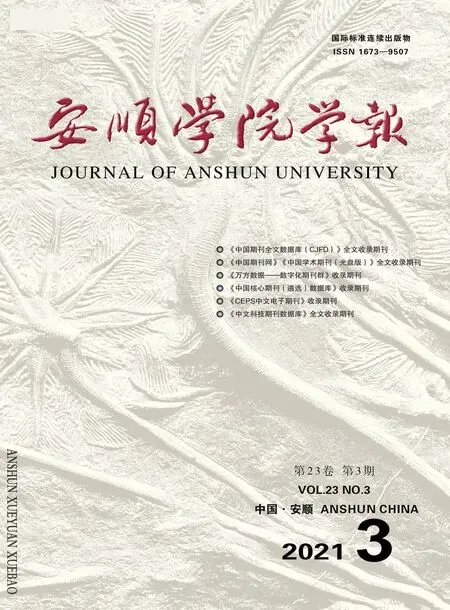乡村振兴与安顺地戏的自我调适
陈忠松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民族音乐与舞蹈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550001)
二十余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无到显,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下至百姓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成了一个高频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渐成社会共识。在学术上,已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愿景与实践。就目前的成果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如何保护”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回应得比较多,对“为什么会成为遗产”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都说得比较笼统,大都归因于遗产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社会急剧发展变革”“现代化的冲击”“强势文化侵扰”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可能并非是某一非物质文化事象成为“遗产”的全部原因。对于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而言,在厘清传承脉络与兴衰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发展措施,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对于特定的文化事象而言,特定人群的需要是否存在,也许才是这一文化事象兴衰的关键。对于流传于贵州中西部的安顺、平坝、普定、贵阳、长顺、镇宁、关岭、清镇、六枝等地屯堡乡村的安顺地戏来说,成为“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功能不再被需要,当代社会需要的功能还未得以充分开发。安顺地戏属于村落小戏,通常以村寨为单位组织展演,一堂戏的表演者一般都是同一村寨的村民。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安顺地戏的创制应主要缘于屯堡人在黔中大地结群自保、教化族人的需要。尽管对安顺地戏的来源学术界还存在分歧,但“其形成与屯堡人这一族群的历史际遇相关”基本上是公认的观点。笔者曾综合各家之言,结合自己的考察与思考,提出并论证了“安顺地戏是屯堡人因在黔中生存发展需要,通过引仪入仪的路径创造的。”①也就是说,安顺地戏也像许多文化事象一样,是基于主体的需要创造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能让我们充分了解安顺地戏在20世纪上半叶前的流传情况,但通过《安平县志》(刘祖宪,1827)、《安顺府志》(常恩,1851)、《续修安顺府志》(黄元操、任可澄,1941)等方志,可以肯定安顺地戏不仅没有因社会局势的动荡而中断,反而因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切合了时势的需要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些文史笔记也支持这一观点,如《黔故谈荟》中就有冯玉祥将军曾于1940年春在贵阳花溪杏花村观看过地戏《杨家将》的记述[1]。1933年出生于普定县号营村的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在《故乡的文艺》中也说他儿时每当过年,村里就跳地戏[2]。20世纪下半叶,安顺地戏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像许多民间传统艺术一样,虽然经历了显隐浮沉,但仍具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安顺地戏的乡土性、仪式性、教育性、娱乐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满足了屯堡人的生存与心理需要,当是其在历史上得以长期传承的内在原因。
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安顺地戏呈现出学界研究热、政府宣传热、戏友参与热、观众反应冷的“三热一冷”现象。而使安顺地戏成为亟待保护的遗产的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一“冷”。安顺地戏虽有一定的仪式性,但主体属于表演艺术,无论是作戏的还是观戏的,都认为是在演戏(或因其表演动作突出“跳”而称“跳戏”),而不认为是在参与一个什么仪式。其实,即便是仪式,也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大多数仪式可理解为娱神娱人的表演。表演艺术的实践包括创作、表演、欣赏三个环节。其中,创作、表演可理解为“生产”环节,欣赏则是“消费”环节。表演艺术的价值必须通过表演并被观众欣赏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对于表演艺术的发展而言,表演者和观众都是决定因素。如果观众的需要不能在观看表演中得到满足,那这一艺术事象的价值就很难得以实现了。或者说,观众不需要这样的“消费”,那这样的“生产”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在安顺地戏曾广为流传的屯堡地区,近年来不少戏队在本村跳戏时,都遭遇了戏友参与“热”,观众反应“冷”的尴尬,最终就难免停鼓息锣,人散戏绝,“香火”难续了。
需要决定价值。虽然观众能左右表演艺术的兴衰,但表演艺术的价值首先取决于表演本身是否被需要。表演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别是表演的形式,更需要考虑观众审美的时代性特征。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针,这给安顺地戏带来了新的时代使命和发展机遇。结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使安顺地戏得以传承,应考虑时代特征,围绕表演来调适。比如:表演目的、表演场所、表演主体、表演剧目等。
一、表演目的的调适:变教育娱乐需要为审美体验需要
屯堡人创造安顺地戏的主要目的,是意图借助仪式的神圣性和戏剧的娱乐性及其二者共有的教育性特征,寓教于仪、寓教于乐,让同为一村之民的表演者和观赏者在跳戏、看戏中受到教育,养成家国情怀、尚武之志和忧患之心,凝心聚力,以应对族群移徙黔中、“开辟草莱”后面临的生存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的民族政策、畅达的流动通道和日益强大的国家力量,使屯堡社区早已实现各民族和平相处、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为国守土、枕戈待旦的使命与生活在当代屯堡人群中早已随祖先远去,只是偶尔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被一些对现代信息关注不多的老年人提及。地戏表演已很难引起大多数屯堡人的历史共鸣。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流行文化、时尚娱乐相比,安顺地戏陈旧的故事、粗拙的动作、单调的唱腔,对大多数从小生长在村里的屯堡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导致其寓教于乐的初衷已很难实现。
不过,戏曲毕竟是综合艺术。它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表演手段上,在艺术功能、审美体验等方面也具有综合性。安顺地戏虽然于大部分局内人而言失去了特定的教育、娱乐功能,但若重新定位表演目的,在“人类文化多样化”和“传统融入现代生活”这样的理念下去进行调适,着力突出戏曲艺术的地方性、审美性和自身表演形态的唯一性特征,充分考虑如何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体验,应能在乡村振兴工程中实现新的价值转换。
安顺地戏传统的表演主要服务于局内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乡村旅游是重要组成部分。安顺地戏作为屯堡乡村的标志性文化,自然是屯堡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旅游意味着外来流动人口(局外人)的增加。安顺地戏应及时按照戏曲艺术的规律,从主要服务于局内人变为主要服务于局外人,针对局外人的观赏目的和取向,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适当对剧目、情节、文本等进行调整。
二、 表演场所的调适:变露天为室内
受限于乡村物质条件,同时为了体现展演的公益性和实现教育娱乐全体局内人的目的,安顺地戏历来多是围场作戏。即在村中平整宽敞的地方,利用简单的场面、道具和人物的站位,围成一个圆圈,剧目故事在圆圈中表演,观众则在圈外或立或坐,围场而观。表演场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观众不受空间和礼节约束,行动和言谈都非常自由随意,观赏秩序通常都比较混乱,甚至常无法听清人物的说白唱词。以前跳戏时,考虑周全的戏队往往会安排一些人员专门提醒约束观众观看纪律,但实际效果仍不能尽如人意。
这种不约束、不区分观众的露天演出,曾经因为屯堡社区娱乐形式的单调而出现过“盛况”,用戏友的话说,就是原来跳戏的时候,不光戏场上挤满了人,连戏场边上的树上、墙上甚至山上都站满了观众。但当下的屯堡社区已今非昔比。人们物质生活的舒适度已大大提升,娱乐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安顺地戏又通常在春节期间表演,室外寒冷的天气和混乱的观演场景,已经让地戏表演对习惯于舒适环境的局内人没有丝毫吸引力了。在不少村寨,尽管还有一些热心戏友在春节想维持跳戏的传统,但多是“只闻锣鼓响,不见人来观”了,跳戏的比看戏的多已成为普遍现象。
通过考察安顺地戏的传承史,笔者发现安顺地戏能传承上百年,还与各村寨的民间经济智慧有关。为了“养戏”,各村寨可谓是“各显神通”。集体经济时期,戏资多由戏友个人和村民共同提供。包产到户后,有的村寨专门留出一方属于集体的田土,谁愿意租种,谁就负责当年跳戏的支出,俗称“娱乐田”。有的村寨设有集市,就用在集市上收取的“摊位费”作为戏资。还有的村寨通过募集本金放贷的形式,以次贷款利息作为戏资。这些形式在屯堡社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笔者调查的田野点中,有好几个都曾在春节期间募集到数万元的“春节活动费”,甚至有一个仅有不到千人的村子,连续几年都能集资十余万元来开展春节活动。其实,跳戏是花不了多少费用的,对于戏友们来说,就是举行开箱、扫场仪式时需要点祭品,跳戏结束后一起吃餐饭(俗称“打平伙”)而已。这些村寨募集到的钱大多都用于举办篮球比赛、拔河这样的活动项目中了。对于这些经济比较活跃的村寨,可以引导他们修建既可供地戏表演,也可用于开展其他集体文化活动的专门建筑,将地戏表演搬进室内,利用小剧场效应,变观演的开放性为限制性。这样既能提升表演的审美性,也能提升观赏的舒适性,当会吸引更多的观众。
就修建公共文化建筑而言,屯堡社区其实可以向侗寨借鉴。在黔东南的许多侗族村寨,都建有公共的文化建筑,比如鼓楼、花桥和戏楼。鼓楼用于议事、对歌。花桥除了交通,还有迎客、交友、休憩等功能。戏楼则就是用于侗戏表演的场所。它们都是侗寨的标识。屯堡村寨也可以将表演地戏的建筑打造成乡村振兴工程中的标识。
三、表演主体:变业余为职业、半职业
纵观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特点:在自觉的范畴内,职业化程度越高的剧种往往越具社会影响力和发展活力。宋元以降,杂剧、南戏的兴盛,与其表演、创作主体的职业化即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战乱频仍,经济萧条,传统民间戏曲受到多重挤压,但仍有不少剧种获得了发展,如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粤剧等,这些乐种的一个共同点是均出现了杰出的职业艺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成立了许多专业剧团和戏曲学校,吸收大量优秀的民间艺术家进入“体制内”,让他们得以成为职业化的戏曲表演者和传授者,对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相较于职业化程度高的剧种,非职业化的“全民性”剧种对小环境的依赖性要强很多。这些“全民性”剧种除了具有戏曲艺术普遍的审美、娱乐作用外,往往还承担族群认同、族群教育等功能,故具有群体性、全民性,并多通过实践记忆的方式集体传承。这种传承方式受群体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生产关系影响很大。也就是说,一旦群体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剧种传承也很有可能受到重大影响。
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深刻变革,社会分工更加深化、广化,行业更加细化,乡土社会的生计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简单的商业交易模式取代了村寨内部传统的互助模式,这一改变动摇了安顺地戏这类公益性剧种的全民性。在传统社会中,安顺地戏是不作为商品参与经济活动的,很少用于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在当前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安顺地戏的经济价值开发成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学界、商界、新闻传媒界,还是作为表演传承主体的戏友,都不得不考虑安顺地戏的价值变现,其中就包括经济价值变现。
如上文所述,安顺地戏虽具有多重属性,但其首先是表演艺术。表演艺术必然要强调审美性、娱乐性,其他社会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审美与娱乐这两个特性的。艺术美虽源于生活,但却要求高于生活。如果艺术技能仅停留在生活技能的层面,组织形式松散粗糙,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不可否认,安顺地戏在表演技能上的不够精致,也是促成其式微的原因。引导部分优秀戏友将地戏表演职业化、半职业化,可以使其更专心于技艺的发展与提升,创造出更精致的审美对象,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受众。同时,受众的增加,也会促进剧种自身的发展。
乡村振兴工程,将使屯堡乡村的产业发展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为安顺地戏表演主体的职业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文旅模式、公司模式、班社模式都是让安顺地戏通向职业化的路径。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可以采用文旅模式,让地戏表演成为旅游资源,通过景点向观光者呈现。旅游景点收入的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让部分戏友将地戏表演作为自己的主要生计来源,进而能将地戏表演传承下去。引导、支持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戏友采用公司模式,成立安顺地戏演出公司,通过承接各类演出活动获得生计支持,进而致力于安顺地戏的表演传承。鼓励在传统戏队的基础上,通过限制性措施和收益激励,成立组织更为严密、纪律更为严格、结构更为科学的地戏班社,利用团队信誉,有偿为企业、公司的开业、庆典、年会和乡民的人生礼仪等提供表演服务,也可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承包”一些演出和传承培训任务,获取成员生计和班社活动经费。
四、表演剧目:在坚持特色的基础上打造经典
中国有三百多个剧种,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主要是十几个,在区域内有影响的会更多些,但大多是流传范围较窄的“小剧种”。这里说的“小剧种”,除了影响范围小、表演要素不丰富外,还有特色剧目少等特征。与之相比,影响较大的剧种首先是有影响大的经典剧目。
安顺地戏留存至今的剧目有三十余个,均为连台本戏。就全部剧目而言,都是搬演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这是安顺地戏与许多剧种的不同之处。但就故事本身而言,其他一些剧种也在搬演,如《三国》《岳传》《隋唐》等。所以,这里说的打造经典剧目,并不是鼓动在传统之外去创编新的故事,而是提倡在剧本编写、表演技巧等方面尽量艺术化。安顺地戏虽然有完整的唱本和“动作跟书走”等明确的表演原则,但却没有形成公认的、成熟的表演体系和评价标准,加之表演者均是业余戏友,各自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悟性参差不齐,即便偶有练习,也常常止于“差不多就行”,致使表演场面虽热烈但却不精致。除了有些唱本唱词冗赘、情节拖沓外,许多戏队表演时还经常出现演员忘词、行头掉落、动作走样、唱腔跑调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表演的艺术性,使剧目难成经典。
安顺地戏要打造经典剧目,首先可在坚持表现家国情怀思想的前提下,对老故事进行新阐释、新表现,利用地戏的特色表演技法和行头道具对一些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地戏化塑造,以区别于其他剧种对同一故事、同一人物的演述。其次,可在传统唱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受众的审美期待,对台词唱句、情节过场精雕细琢,让唱本更精炼,更有文采,让故事更紧凑、更有戏剧性。第三,加强地戏表演形态研究,尽快建立地戏表演体系,在唱腔、动作、行头规范的基础上,追求精致和特色。
结 语
大量现象表明,在艺术领域,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当下的许多新兴艺术形式和新创艺术作品,都有对传统艺术的继承。虽然安顺地戏也像许多乡土艺术一样,随着屯堡乡村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但变化只是外因。人类社会的主流提倡多样化,安顺地戏弘扬家国情怀的思想主题和特色鲜明的行头、唱腔与动作程式,在人类多元化文化图景中独具一格,不可替代。梅兰芳说:“艺术的本身,不会永远站着不动,总是像后浪推前浪似的一个劲儿往前赶的。”[3]屯堡族群本身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作为屯堡文化的标识,安顺地戏更不应在固执中听天由命。乡村振兴是旨在造福于乡村民众的综合性工程。屯堡人创制安顺地戏,目的也是祈保族群的平安长久。当下屯堡乡村的振兴与历史上安顺地戏的创制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故,安顺地戏应借势而进,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利用乡村振兴工程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打造经典剧目,突出表演要素的调适与提升,在不断适应当下与未来的需要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 释:
①参见笔者所著《引戏入仪:安顺地戏的形成路径》(载《安顺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以及《边缘存续——安顺地戏形态与传承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