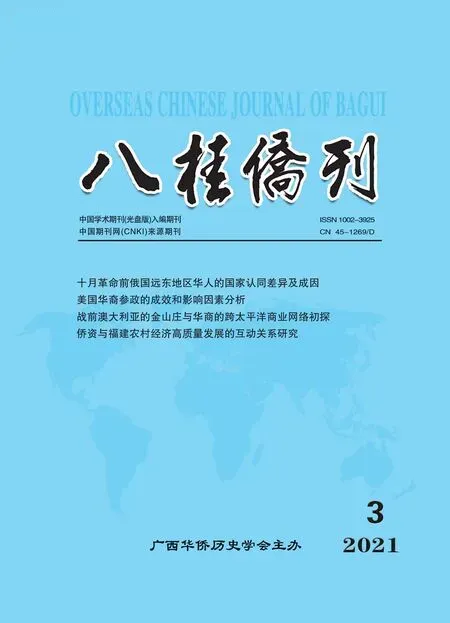坚守与融合
——浅谈马华作家鲁白野的文化认同
[马来西亚]黄薇妮 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在1982年于墨西哥城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给文化作出了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①D.Paul Schafer,Culture:Beacon of the Future,Twickenhan,U.K.:Adamantine Press,1998,p.8.。
若将上述的文化定义放置到马来西亚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更能突显出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信仰等马来西亚文化总体。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形成源自早期马来亚与其他国家的商业与文化交流。马来西亚自古以来处于东西贸易主要通道。在郑和之前就有华人在马来亚的记载②[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修订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版,第43页。。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侵入东南亚各个国家,马六甲陆续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统治。18世纪末以后,英国殖民统治逐渐伸展至马来亚半岛各州,各种现代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展,其中也包括极力开发马来亚的经济。为此,英国殖民地政府开始从中国和印度引入大量劳工。此举使得马来亚慢慢成为大量华人和印度人的集中迁移地。在迁移的过程中,华人和印度人也将自身的文化移植到马来亚,逐渐形成马来亚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现象。
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并未曾质疑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与特征。满清政府在1909年颁布“血缘”准则的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凡是华人的后裔皆为“中国人”或“侨生”。这个“血缘”国籍法是一个联系中国和海外华侨强而有力的纽带,推动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可。此外,马来亚华人社会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之政治思想、教育政策等深深影响马来亚华人社会。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时任中国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签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策后,大量的马来亚华侨华人也在马来亚1957年独立建国时期选择加入马来亚国籍。马来亚华人公民身份的确认,使他们对于在地化的意识高涨,国家的认同也产生转化。
由于长期生活在多元族群的社会之中,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地主流文化——马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生活所需,华人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所在地的文化以适应当地的风俗和习惯。华人除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移民大浪潮时大量移入马来亚,在移民大浪潮之前早有少量华人移居马来亚。由于华人迁移至马来亚的时段不同,故对祖籍地的关系和观念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产生出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由于马来亚各世代华人的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的马华作家鲁白野①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一律使用“鲁白野”。如有必要,则会穿插使用鲁白野或威北华等名字。当使用“鲁白野”之名时,旨在讨论其文化书写,以别于讨论文学书写的“威北华”。为个案,阐述鲁白野如何在经历了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后,作出调适与转化,并在文化认同上建构出自己的视野和坚持。鲁白野在文化认同上的调适和转化,其过程基本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马来亚华人文化认同的调适和转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的鲁白野文学的威北华
了解鲁白野的作品,首先要先了解鲁白野成长的历史背景。鲁白野(1923—1961),原名李学敏,另署名李华、李福民。1923年4月21日出生于英国政府殖民地的马来亚霹雳州怡保,祖籍中国广东梅县,客家人,具有峇峇血统(祖母是娘惹)。李学敏使用的笔名有:鲁白野、威北华、楼文牧、越子耕、华西定、破冰、范畴、姚远、郁强等。他在霹雳万里望(Menglembu)度过童年时期,在怡保育才学校念书,五年级便辍学。鲁白野早年曾不间断地在马来亚半岛不同的地方如拿乞(Lahat)、万里望、金宝(Kampar)、槟城、马六甲等地,以及新加坡经历着不断迁移的生活。
1942—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期间,鲁白野曾流亡到印尼避难。他先后漂泊在棉兰(Medan)、奇沙兰(Kisaran)、亚沙汉(Asahan)、马达山、先达、椰加达等地。在印尼流亡期间,鲁白野为了糊口,从事过农夫、士兵、记者、教员等工作。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鲁白野也曾加入印尼的文艺团体“蚁社”,并与印尼的“四五世代”作家有过密切的来往。
二战结束后,鲁白野重返马来亚,最后落脚在新加坡。战后的这段时间也是鲁白野文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在新加坡直到去世的短短12年期间,以勤奋且狂热的姿态书写、出版及编辑了多部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期,鲁白野分别以笔名“鲁白野”和“威北华”进行书写。他以“鲁白野”的笔名进行历史文化书写,作品有《狮城散记》、《马来散记》、《马来散记续集》、《印度印象》(报告文学)和《马来亚》(国家概况),并编辑了《实用马华英大词典》和《马来语月刊》。另一方面,他以笔名“威北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创作涵盖散文、诗歌、小说等类别,出版的作品有《春耕》(散文集)、《流星》(短篇小说集)、《爱诗集》(诗歌)、《黎明前的行脚》(小说、诗歌、散文)。不管是文史书写抑或文学创作,鲁白野的作品都是马华文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和流亡的动荡生活,促使鲁白野对安定的生活有着迫切的渴望,同时也让他思考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必要。
为此,鲁白野尝试挖掘华人移民马来亚的历史事迹,藉着书写再现华人先贤对马来亚所作出的种种贡献,企图补充华人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的不足。马来亚作为多元族群的社会,鲁白野也清楚要了解华人在马来亚生活,就必须走入其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如此才能达致敦睦和谐。因此,鲁白野的文史书写内容,也涵盖了马来亚其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族群社会和文化的视域下,鲁白野的作品凸显其独特的文化观。与当时同一时期的文人相较,鲁白野以跨越族群边界的观察和描述,借着文字的力量默默推动马来亚华人去了解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为20世纪50—60年代处于独立前后的马来亚各族人民搭建起一座独特且美丽的文化桥梁。由此可见,鲁白野的文史书写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寄寓着作者宏大的理想。
二、华人文化认同与坚持
鲁白野是南来华侨的后代,他没有祖辈早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只是在文章《南方的河》中提到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曾经到过故地——中国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的松口镇①威北华著,张景云编:《威北华文艺创作总集》,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第26页。。虽然对于祖籍地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可是对鲁白野来说故地并非是全然陌生的,在其意识和想象中却是熟悉的原乡,而这个认知也牵引着他对自身中华文化的追寻。
虽然生活在常年炎热的赤道国家,鲁白野没有真正体会过北国的四季天气,可是在鲁白野的文学创作中却时常出现春天、秋天等北方四季国家的气候,就好像在《乡间小札》里,他写道:“在一个不很远的春天,我住在一个印尼乡村的界限上。……草原底海,在春风怒吼的日子,也会跟着咆哮,也会殷殷般地申诉一段湮远年代的故事。春天是可爱的,为了这恰好是耕耘的季节,是播种的好日子。”②威北华著,张景云编:《威北华文艺创作总集》,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第26页。鲁白野在文学创作中频频出现的北国季节意象,正是他对中国想象的一种连接,也成了他对原乡丰富的情感依附和对中华文化的精神寄托。
鲁白野身为中国移民的后裔,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成为他流淌在血液里的重要部分,也是他的中华文化观之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蕴含丰富人文历史与文化的国家,其所记录和保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献,成为鲁白野在进行马来亚历史文化书写时的重要参考资料。鲁白野大量研读中国史书如《汉书·地理志》《梁书》《诸蕃记》《经行记》《宋史·占城传》等,在书写时不厌其详地进行考据和比较。鲁白野的马来亚文史书写以中华文化作为基础,形成其独有的文化与历史观。
鲁白野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依附与精神寄托,却也使他在潜意识里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优越感。鲁白野早期的文章《民族英雄汉都亚》里,他就曾以“天朝”来称呼中国,并在文中将出使中国的马来民族英雄汉都亚描述其身份乃“藩属国”之使者。显而易见,鲁白野的论述视角完全是从中国方面出发,即使鲁白野本身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马来亚人。鲁白野如此写道:“他(汉都亚)曾经出使中国,回来后对天朝繁华念念不忘,逢人便说中国好”③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153页。,中国是“宗主国”,而马六甲是“藩属国”,“……明成祖便下令封拜里米苏刺为王,并赐诰印彩衣黄盖,及封其山为镇国山。”④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2—3页。于鲁白野而言,相较之华族,早期的马来族群仍然处于落后荒凉的状态。他如此说道:“我们可以断定,在狼牙修以前,马来亚人民的政治过得很散漫、根本没有国家或政府的组织。”⑤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2—3页。这个时期(约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鲁白野仍然没能跳出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他对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根深蒂固,以及对祖籍国的情感归顺,都在主导着其早期的文化认同。
鲁白野对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视,包括以自己身为华人而感到光荣。从他早期的作品《狮城散记》、《马来散记》和《马来散记续集》的书写内容,不难看出他这种以华人为中心的视角和意识。在《马来散记》的原序中,鲁白野写道:“我要把故乡成长的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要亲切地写我们的先人曾经怎样流了无尽的血汗在努力开拓它、耕耘它,创造了一个幸福、繁荣的新天地。”①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9页。在《狮城散记》的序文中,鲁白野写道:“从一个荒芜的小岛,在一百多年间,我们的祖宗是如何恩爱地开垦岛上的处女地。在今天,地方是繁荣极了,人口也突破了百万大关,其中有八十巴仙是华侨。是他们用巨大的有力的手,在沿海岸的两边捏成了一行一行的黑巷,一排一排的鸽子屋,是他们在披星戴月,刻苦经营,狮子岛上繁荣之花才能够发芽茁壮。”②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1—2页,第29—30页,第27页。言下之意,鲁白野似乎认为马来亚的繁荣,华人居功至伟,因此必须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鲁白野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强调由于华人的辛勤劳动、克勤克俭,带动了马来亚的经济成长繁荣。为此,鲁白野书写多位华人先贤在马来亚的丰功伟绩,无论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和平老人林文庆》《陈泽生这个人》《吾侨怪杰胡亚基》《吉隆坡开基人叶亚来》等,抑或寂寂无名的普罗大众都曾经是鲁白野笔下的文化人物,受到鲁白野的表彰:“而这繁荣的能够成为事实,主要的还是靠华侨的大量移植和开荒,这个决定因素,是马来人和英人都不得不承认的。”③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164页。
华人民间宗教信仰也是体现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鲁白野在其方志书写中,也对华人的信仰、寺庙有所记叙。华侨南来并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后,也把在中国家乡的民间信仰移植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形成马、新各地寺庙林立的现象。鲁白野在《华侨的庙》中就记录了多所寺庙的故事,例如新加坡的“双林寺”、槟城的“极乐寺”和“清水祖师庙”、吉隆坡的“仙四师爷庙”等,除了详细讲述各个庙宇的成立经过,也阐述了马来亚华人民间信仰如妈祖、大伯公等的由来。这些当年由华侨华人建立的寺庙,其功能除了宗教信仰之用途外,也是当地华侨华人的活动中心。鲁白野在《华侨的庙》中如此形容“……香火鼎盛,仙师爷庙竟然成为当地华侨社会活动中心。”④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1—2页,第29—30页,第27页。因此,庙宇组织的成立和壮大,有助于凝聚和巩固当时的华侨华人社会。
华人初抵马来亚,由于处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之中,心中充满彷徨和不安,这时,信仰成了提供他们精神寄托的力量,因为现实所需,由祖籍地带来的信仰也随着迁徙有了在地化的演变。华人民间信仰融入了马来亚的在地特色,势必要经历一个与当地宗教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新马华人在适应新的时代变迁中,原有的宗教信仰在力求保有其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也吸收当地宗教信仰文化的成分,逐步发展成为有别于中国本土传统宗教的信仰体系和形态⑤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2—3页。。就像鲁白野在文中提到的“都公”“托公”“大舶公”“大伯公”等神明,他们为华人所乘搭的船只护航,让他们安全南渡到马来亚。上岸以后,这些供奉在船舱内的神明就被安奉在码头旁、河岸上或其他合适的地点,建立神龛或小庙以答谢神明。鉴此,我们可从这些庙宇的形成和分布,大略看出早年华侨华人社会形成的经过。这样的想象,引发了鲁白野对于“在地化”的思考。他从马来亚华侨华人对于“大伯公”信仰之普遍,包括也将马来民间的“加拉末”(Keramat)信仰结合的现象,如此写道:“谁是大伯公?看见散布在广辽的南洋群岛上的许多大伯公庙,对民俗学感兴趣的国人,就会这样发问。大伯公的来历,的确是值得探讨研究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大伯公不但是南洋华侨最敬重,也是膜拜最普遍的对象。华侨奉祀的大伯公,其地位远超过国内的城隍。可是,有一个使人百思莫解的事实,在古老的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个庙”⑥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1—2页,第29—30页,第27页。。马来亚华侨对于大伯公信仰的普遍程度,按鲁白野的说法,即“在海峡殖民地中,大伯公庙最多的,要算星洲,大大小小,一共有十多间。其中最闻名的,是源顺街、丹绒巴葛、龟屿、水仙门和梧槽大伯公等处,香火鼎盛。”①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29页,第32页。
诚如前述,庙宇的建立见证了早期华侨在异邦胼手胝足,艰辛生活的历程,同时也扮演凝聚华人社会、建立网络、维护及传承文化的作用和功能。除了膜拜祈福,庙宇也成为华侨思念中国原乡的一种表达形式,可见庙宇在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从鲁白野对马来亚各地华人庙宇的叙述描写和历史考究,其情怀始终离不开他对中华文化的依恋,其中更不时从华人的视角出发,认为这是华侨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辛勤付出的结果,因而才有四处林立的庙宇。他如此写道:“……在都市、在村落,在穷乡僻壤中他们默默地起了一座一座小小的庙,以铭记着中国人民在异乡奋斗的史略。”②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29页,第32页。鲁白野以小见大,借用庙宇的存立赞扬华人先贤对马来亚的建设与贡献。
三、鲁白野与马来文化
华人迁移到他国以后,华人文化逐步与其他的文化互动,以致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比原来的中华文化更具多元性。20世纪50年代初期,马来亚华人陆续申请成为英属马来亚的公民,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样的认同转变也影响了马来亚华人对于本身的文化和属性的认同的转变。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转换过程中,鲁白野和许多马华文化人如马来文词典编纂家杨贵谊、华文教育领航人林连玉先生等人一样,很快便意识到华人若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并成为其公民,除了要与同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共存共荣,求同存异外,马来亚华人也必须掌握好马来语文及了解在地的主流文化——马来文化的重要性。
马来人,马来语为“Melayu”。在中国古书《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就将Melayu称之“末罗游”,不过其所为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某个地方,即今日的“占碑”(Jambi)③[英]理查德·温斯泰德,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修订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3页,第9页。,后来经过演变,Melayu这个名词再延伸成为一个民族的称呼。根据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所指,马来人的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方面是指居住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等岛的马来人,而广义方面则涵盖爪哇人、婆罗洲人、菲律宾人、台湾土蕃(高山族)等。林惠祥引述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是马来人并非同一宗源,而是混合的种族④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理查德·温斯泰德(Richard O.Windstedt)则从语言上的依据,认为马来族的故乡可能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等地,从而文化上来说则接近云南的西北方向的区域⑤[英]理查德·温斯泰德,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修订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3页,第9页。。一般认为,马来民族分批迁徙到马来半岛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马来文化自身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使得马来文化亦包涵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历史上,马来文化先后受到兴都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公元7世纪以来,三佛齐、阇婆、满者伯夷等古国先后在马来半岛和印尼等地建立其王朝。印度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古代马来世界及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鲁白野在论述马来文化时,曾多次提到印度文化对马来文化的影响。他在《印度人的拓殖》一文中写道:“马来民族自印度人取得许多文化遗产,包括文字、宗教、科学知识、哲学,还有算不清的文艺创作。”⑥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182页。可见,马来文化在公元15世纪以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在文学、历法、文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源特征⑦徐月明:《论国内马来文化研究新视角——兼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为了促进贸易,马来群岛诸国多采取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此举让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前往马来群岛各地沿岸港口进行交易,同时也促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宗教信仰的传播。在伊斯兰教还没有传入马来亚以前,马来族群主要是泛灵信仰,即信仰“万物有灵”。泛灵信仰可视为马来人宗教信仰之起源,如今即使伊斯兰已经成为马来族群的宗教,但是马来社会底层或多或少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信仰①马强、张梓轩编译:《马来人及其宗教》,《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鲁白野在《马来人的神坛》中提到:“马来人把神坛叫作加拉末,译意是‘神圣的东西’。加拉末多为古坟,它是马来人生活风俗习惯中唯一没有受到回教或是印度教影响的民俗。它实在是一种原始民族性质的图腾崇拜的变相。”②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页,第98页,第100—102页。他认为:“在马来亚,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加拉末的;其间要以马六甲为最,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二三个加拉末的存在。它们的功用在于庇护人民的安全和繁荣。”③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页,第98页,第100—102页。从鲁白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泛灵信仰在早期的马来亚马来人社会中非常普遍。
马来人的泛灵信仰,使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生灵包括动物,如:牛、蛇、象等也有着同样的崇拜。著名美国考古学家朱莉·齐默曼(Julie Zimmerman Holt)曾指出:“在史前社会,动物除了扮演经济的角色,还扮演象征和宗教仪式的角色。”④Julie Zimmerman Holt,“Beyond optimization:Alternative Ways of Examining Animal Exploitation”,World Archaeology,1996,vol.1.对于马来人的动物崇拜,鲁白野也做了相关记录。例如,他在《蛇年谈蛇》中就提及了一种被称作“珍打万尼”的小黄蛇,马来人相信它是马来王族的化身。这种名为“珍打万尼”的蛇除了被视为马来王族的化身外,还带有好“好兆头”的寓意——“如果能捕获此蛇,养在家中,便会万事如意,幸福无限。巫师在插秧礼仪中念‘珍打万尼’的名字,可以保证丰收。”⑤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页,第98页,第100—102页。除了蛇,象也是早期马来社会崇敬的动物。鲁白野在《劳动的象》一文中写道:“马来人驯象……他们开始感觉象的伟大有力,是神秘的,而把它当作敬畏的迷信对象。信仰回教,没有减除他们对野象的敬畏。”⑥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页,第98页,第100—102页。此外,古代马来社会也有捕捉大象的禁忌,或通过御象法驯服大象。他们也会念《象经》咒以克制野象的精灵、为大象治病或使象肥胖等法术;他们甚至也有勾引雄象的灵魂的法术,使雄象迷恋被驯服的雌象群等等⑦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页,第98页,第100—102页。。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早期马来社会,这些对于万物有灵的思想内涵的体现不言而喻。泛灵信仰反映了古代马来族群依循自然并崇敬神灵,以求神灵庇佑的一种意识。
鲁白野自小在马来乡村长大,因此对于马来社会的许多信仰习俗和流传的故事传说多少都有所耳闻。他书写和分析马来人的信仰、民俗、神话、传说的来龙去脉,因为它们正是理解和感悟马来族群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至为关键的基础知识,包括它们在马来社会中所具有的内涵、功能与作用。基于对马来文化的理解,鲁白野的地方文化书写如《马来散记》和《狮城散记》都有大量的篇章介绍马来文化或各种与马来族群相关的事物,并以此作为向当时马来亚华人介绍马来文化的基本媒介,让马来亚华人藉此走入马来社会。诚如马来谚语所言:“不了解则不会喜欢”(takkenalmakatakcinta),只有了解了马来文化,当时马来亚华人才会对这片土地和新诞生的国家产生感情,在求同存异中并肩合作以开创一片新天地。
四、文化适应
华人迁移到马来亚以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上需要经常和其他族群交流,故大部分华人都得学习对方的语言并了解其文化习惯。从几个世纪以前至今日,马来文化依然是马来西亚的主流文化,早期华人尚未有显著落地生根的意愿,同时作为从中国来马来亚寻找生计的外来者,华人在文化上自然倾向主动去接触和适应马来文化。华人选择留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后,对于学习和了解马来文化的意愿更是强烈,尤其是在1957年马来亚建国前后,华人除了要融入新的国家文化外,也要适应作为国家主流的马来文化。然而,在适应马来文化之际,华人也想在不影响华、马两族关系的情况下极力地维护本身的文化。这样的文化适应之考量,实际上也延续至今日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约翰·贝利(John W.Berry)认为,“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①John W.Berry,Appli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Newbury Park:Sage,1990,pp.243—245.:
其一,融合(integration)模式:即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想融入主流社会,与社会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
其二,分离(separation)模式:即文化适应者只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特征,不想和主流社会的成员建立任何联系。
其三,同化(assimilation)模式:即文化适应者不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特征,只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取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
其四,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模式:即文化适应者既不想或不能维护自己原来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不想或不能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联系。
虽然许多华人移民的后代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后裔被彻底同化,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适应占支配地位的本土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环境②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页,第45页。。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早期的马来亚或现在的马来西亚,因为绝大部分的马来亚华人选择了拒绝被同化。他们在成为马来亚/马来西亚国民时,不但不愿放弃华人文化的特征(例如语言、教育、宗教信仰等),反而极力维护和保存本身的文化。他们尽最大努力在不导致冲突的情况下,选择了融合的文化适应模式。在马来西亚,华人的融合类型是属于渐进变化,是通过社会的互相接触、文化因素的自由借入导致文化混合,而非因军事或政治而强制被改变③洪丽芬,林凯祺:《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和印度生活文化的适应》,《八桂侨刊》2015年第1期。。为此,马来西亚华人通过学习和接受马来文化和其他在地文化,并在这样的适应过程中摒除了一些旧有的文化特质,再接纳新的文化特质,无形中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构建了一种基于在地认同、融合多元文化而产生并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独有的马华文化。这样的观点,鲁白野早在建国前夕就提了出来。他认为华人应该适应居住国的文化,而融入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马来亚华人首先必须了解在地的马来文化,以及掌握好马来语。鲁白野在《谈马华字典的编辑》时,如此说道:
“马来亚华侨没有像印尼华侨一样,普遍地学习及使用马来语。不但如此,不少星马华侨对此地情形是不熟悉,对马来民族是不了解。因此,中马两大民族之间假如有隔阂存在的话,首先得怪我们自己。本来语言是沟通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如果还是固执地坚持着闭关自守的愚蠢态度,甚至表现着一些唯我独尊的自大作风,拒绝了解别人,拒绝学习他们的语言,不去设法搞好中马友好关系,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到,吃亏的还是自己。”④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年版,第191—192页。
要如何与在地文化相互融合,鲁白野不仅仅是提出他的观点,他在马来亚独立后还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交融的文化事业。鲁白野参与了国家文化的建设,提出打造马来亚国族,包括在马来亚华人社会里推广和提升华人的马来语掌握能力。陈志明认为,语言变迁是涵化的根本方面,采用当地的主流语言在过去是必需的,到了今天仍然还是最根本的方面⑤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页,第45页。。鲁白野深知马来亚华人若要融入在地,则认识和掌握马来语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因此,鲁白野选择在马来亚获得独立自主、积极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的族群社会的时期,便积极参与了华文—马来文的翻译工作。鲁白野主编《马来语月刊》和编撰《马华英大辞典》,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马来亚华人社会讲解及推广马来亚历史及其文化,让马来亚华人对这片“马来土地”(Tanah Melayu;“Malay Lands”之意)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学习并掌握好马来语文。鲁白野将促进马来人和华人在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为其使命,以期建设好马来亚的国家文化。
五、结语
文化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第一代的马来亚华侨移民,几乎是心系中国并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然而第二代及其后的马来亚华人,开始出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意识。他们或许不在马来亚出生或在马来亚接受教育,但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经历等的集体记忆,逐渐和马来亚的历史、社会、文化越来越密切交织。马来亚华侨从英殖民时期的“他者”,逐渐转换成为马来亚公民,他们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分享着同样的历史经验。
萨义德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①[美]爱德华·赛义德,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因此,多元文化应是谋求共生,共同发展的②[美]爱德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6—427页。。鲁白野作为建国时期的马华文人是乐于看见这样共存共荣、多姿多彩的愿景。在这样的愿景之中,鲁白野并没有以放弃自身文化去迎合或融入这个新国家的主流文化。鲁白野在坚持和认同其华人文化的同时,也尝试和其他文化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互动。
处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之中,不同文化之间发生碰撞和冲击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层面的内涵底蕴,但这些都没有使鲁白野对其自身族群的语言、身份和文化产生怀疑。反之,多元的文化冲击与交融,让鲁白野可以用充满优越自豪的态度去看待本身的中华文化。他的自豪与信心让他积极参与维护和传承华人文化的同时,也让他对在地的主流文化——马来文化表现出尊重和海纳百川的心态,充分展现了鲁白野在文化认同上的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