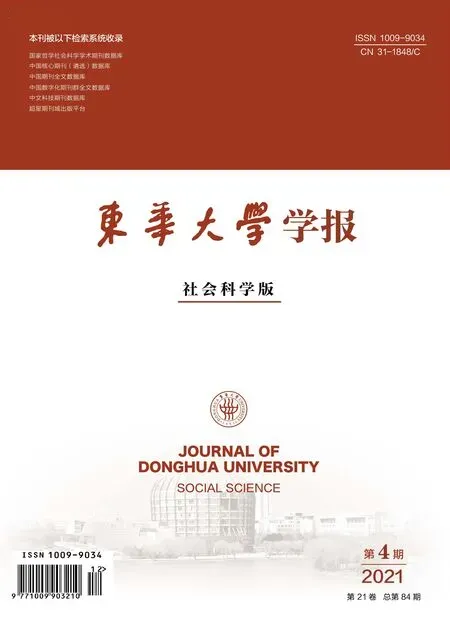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谱系考证
|覃代伦|中国民族博物馆 非遗部,北京 100080
21世纪伊始,生物基因理论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学人们将生物基因理论与文化发生学说有效链接,提出了文化基因理论。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众说纷纭。文化基因主要是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的、自觉与不自觉置入文化本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文化基因支持着文化生命体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文化孕育、生长、凋亡过程中全部的种族遗传信息。近年来,文化基因研究正从抽象的概念借译,转向具象的文化要素萃取以及文化基因间逻辑关系与遗传信息的建构。文化基因一般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因型(genotype),可理解为文化基因要素的结构,类似于生物学的基因组,主要表现为材、纹、型、技、意、制等六种基因元;二是表型(phenotype),可以理解为文化基因中可感知、可观察、可描述的性状,其基因型与表型关系是“表型:基因型+环境+文化符号+传递史+工艺形态学”。[1]本文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视角切入,考证中华织锦文化形成发展史的基因组,包括民族基因、历史文物基因、文学基因、人文基因,多维度地寻找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的原点、支点和衍生点,并对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的基因组进行编码与复制,从而发现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生命体里的DNA结构与基因图谱,以及文化基因里深层次的艺术信念与价值观。
一、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民族基因元
从文化基因的基因型来看,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的技、艺等两种基因元涉及“民族元素”。何为“技”?主要是指技术、技艺、技巧、技能,它是用一定工具将材料进行加工,制作成织锦成品的技术、方法与过程。[1]何为“艺”?主要是指匠意,特指匠人造物的符号与思维体系,包含美意、创意、寓意和真意等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拥有5000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夏商西周时期(约前21世纪—前771年)是华夏集团中原文化区形成的重要阶段。在中原文化区周边,西北地区(今甘肃、青海等地)有羌、戎、狄等部族,分布着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铜时代的遗存;东部地区有东夷和淮夷部族,其中岳石文化是东夷的遗存;西南地区有古巴人、古蜀人,三星堆文化和蚕丛文化是其代表性的遗存;北部地区有肃慎、戎狄等部族,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是这些部族的文化遗存。可以说,夏商西周时期是华夏民族集团的孕育时期,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的原点。《华阳国志·巴志》中的:“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就记载了土家族祖先远古巴人“执玉帛”进贡夏王禹的历史事件,堪为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基因原点。大约成书于西周时代的历史地理著作《禹贡》,也有“厥篚织贝”的记载,意为按贝壳的色彩花纹织成的贝锦。这应该是岛夷(黎族先民)黎锦的文化基因原点。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同时将周边地区生活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这些“蛮、夷、戎、狄”中的大部分部族在与诸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中与诸夏融为一体,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细分之,东部地区为夷、淮夷和东夷,在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北部地区为匈奴、白狄、东胡、林胡和楼烦;西北部地区为北戎、山戎、白氐、氐、羌等;南部与东南部地区为群蛮、百濮、百越;西南部地区为巴、蜀、西南夷。大约春秋战国时期,“百锦之母”蜀锦已经规模生产并成为贡品。《诗经·秦风·终南》记载秦襄公促周平王东迁成功后,“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锦衣只有周平王和秦襄公这样高贵的人才能穿戴,大大提升了牧马人出身的秦襄公的身份地位。《诗经·小雅·巷伯》记载“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这应是纬锦提花的文化基因原点了。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蜀国,置蜀郡,把散落在蜀国各地的织锦工匠集中管理,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织锦管理机构“锦官城”,这也是秦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生产并营销蜀锦的历史节点。
秦汉时期(前221—220年),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生活着强大的匈奴人,秦朝大将蒙恬北击匈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昭君出塞使汉与匈奴和好,都是中华织锦史上著名的历史节点。东北地区,有日益强盛的乌恒与鲜卑部族;东南沿海,分布在今浙江和福建地区的部族称东瓯、闽越;西南地区,分布在今云、贵、川的主要是西南夷,古滇国、古夜郎国是此历史节点的代表;南方地区,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称为南越、西瓯和雒越,百越各族与汉人也多有交往、交流、交融;西域地区(玉门关以西),西域都护府辖乌孙、楼兰、若羌、精绝、于阗、车师、龟兹、疏勒等36个小国。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出土于古精绝国的尼雅遗址。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襌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它们都是秦汉这个历史节点上的蜀锦衍生点。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禀报汉武帝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丈、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云:‘吾国商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西汉官家正史记载佐证了“蜀布”之流通绕道“身毒国”(古印度)而至“大夏国”(今中亚诸国),证明丝绸之路南道“蜀身毒道”早于丝绸之路北道400余年,这是丝绸之路上两大重要历史节点,对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长达千年的历史影响。[2]
经历过三国魏晋南北朝(220—581年)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分裂动荡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隋唐五代民族大融合时期(581—960年)。北方地区,突厥和回鹘两大部族集团称雄;西南地区,吐蕃与南诏两大部族立万;东北地区,渤海和高丽等部族扬名;南部地区,武陵蛮、僚、百越等部族坐大。但大唐帝国是那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包容的国家,万邦来朝,职贡不绝于途。唐太宗李世民第一个提出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中华”概念:“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而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史载有唐一朝共126个宰相,其中胡人36个,这充分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制度自信与民族自觉。阎立本《步辇图》描绘了禄东赞身穿联珠团窠纹吐蕃锦服向唐太宗为松赞干布求亲,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这些都表明“唐蕃和亲”的文化符号吐蕃锦,已成为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图谱中的华章。
辽宋夏金元时期(916—1368年)是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统一时期,北方契丹族之辽国,党项族之夏国,女真族之金国,青藏高原之吐蕃国,云贵高原之南诏国,都是并立周边的多民族政权。只有蒙元王朝才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凉州会盟是吐蕃进入大中国版图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而元代纳石失织金锦,则是元朝织锦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明清时期(1368—1911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时期。清末梁启超先生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学术概念:“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4]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主张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有其历史的局限性。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55个少数民族得以确认。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第一次提出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云锦、蜀锦、宋锦、壮锦四大名锦,加上土家锦、苗锦、景颇锦、布依锦等16个民族织锦,都是中华织锦中的“民族基因元”,其原点、支点、衍生点和遗传信息链路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织锦文化基因谱系中,其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共享型基因与特异性基因、稳定基因与特异基因,都有一定的线型描述。
二、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历史文物基因元
前文所述的文化基因中的表型,其中的“文化符号”与“传递史”,可以用来分析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历史文物基因元。根据文化基因的重要性、文化符号的传递史,历史文物基因元又可分为主导性基因、亚主导基因和嵌合基因。[1]
从考古学的角度追根溯源,长江流域出土的最早丝织品,应该就是江苏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了。这块小小的出土绢片是平纹结构,经碳14鉴定,约为4 752年前良渚文化的遗物,大约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这块绢片是良渚文化先民自织的?从其他部落输入的或是易货贸易的商品?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证明。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之历史文物原点,这块绢片当之无愧。从文化符号的传递史来看,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的主导性基因。
由于丝绸类织锦的有机材质极易腐蚀,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以来考古出土的实物极为少见。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有“桑、蚕、丝、帛”等甲骨文,100多字,证明丝织品广泛见诸最早的甲骨文记载。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刻有“蚕纹”的象牙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玉戈,不仅有朱砂染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还有以平纹为地、云雷纹的丝织物印痕,这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商代丝织物印痕。[5]从这些印痕和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窥见商代织锦文化基因的早期信息,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的早期文化符号。
陕西石泉县前池河出土的西汉鎏金铜蚕(5.6 cm×1.9 cm,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是2015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高领导人提到的两件明星文物之一。这个小小的鎏金铜蚕是西汉皇帝奖励地方养蚕大户的御礼,把陕西关中一带的养蚕历史至少提前了一千年,其地域历史文物基因支点作用明显。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出土的西汉三管跽座青铜俑(张家界市博物馆藏),着交领右祍汉服,身披“賨布”,是2000余年前土家织锦“賨布”唯一现存的实物纹样,显示了土家先民賨人的织锦智慧。同时,也是土家织锦最早的历史文物基因图谱信息的衍生点。从这件文物信息看,土家先民武陵蛮制作的賨布无疑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亚主导基因。
除上述遗留在织锦器物上的历史基因信息外,中华民族还有哪些历史基因信息量大、品相完好和影响久远的织锦文物实物呢?
第一件我认为就是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时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18.5cm×12.5cm,新疆博物馆藏)。尼雅遗址是古代西域精绝国之都城,是丝绸之路北线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节点。首先,这件锦护膊的出土表明汉地出产的蜀锦制作的锦护膊已流通到遥远的精绝国。其次,它所蕴含的文物信息十分丰富。司马迁《史记·天宫书》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司马迁所言的五星,就是汉代天文学家所言的发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五星同出于东方,中国利,这是汉代人占星术的核心,也是中国天文学的萌芽。最后,此文物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汉字纹用的是繁体隶书,让人一睹汉代隶书的神韵,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另类解读的文物佐证。
第二件就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972年出土的“素纱襌衣”(湖南省博物馆藏)。它是当时长沙国宰相夫人辛追的随葬品,它的重量(49.5克)和材质,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朝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当时辛追夫人身上穿有春、夏、秋、冬四季20余套衣服,“素纱襌衣”只是其中一套内衣而已,但是它上面留存着汉朝人生产与生活的基因信息。
第三件就是西藏阿里地区出土的“东汉王侯鸟纹锦”(西藏博物馆藏)。东汉时代,西藏阿里地区在古代象雄国的统治之下。它的出土表明,早在赞普时期,连接古印度和古尼泊尔的丝绸之路南道吐蕃—泥罗婆道就已经存在了,说明通往遥远奇险南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南道的出现早于唐僧玄奘取经天竺国数百年,也早于唐蕃联姻文成公主进藏数百年,其蕴含的信息丰富,历史文物基因十分强大。
第四件就是内蒙古四子王旗出土的元代织金锦辫丝袍(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在元朝,只有成吉思汗家族才配称为“黄金家族”,他们才是《黄金秘史》和《蒙古源流》里当仁不让的主人公。当时,蒙元朝廷在山西原阳设有“纳石失局”,专司织金锦服的生产和销售,蒙古贵胄喜服织金锦服、戴罟罟冠的生活习俗就这样延续下来了。这件锦袍是《元史·舆服志》所载纳石失的实物佐证,是纳石失历史文物基因信息的原点。蒙古人建立的蒙元王朝专司“纳石失”的生产与消费,是在汉民族织锦文化基因中融入蒙古族织锦文化的艺术见证,在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中的嵌合基因作用十分明显。
从考古出土的织锦文物中能发现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的原点、支点和衍生点。可视、可触、可证的文物对基因遗传过程的演示,比从书本到书本的考据学研究更有可信性和实践意义。
三、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文学基因元
根据文化基因的表型特性划分,传统的文化基因可以分为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柏贵喜先生在《文化基因的类型及其识别原则》一文中认为:显性基因是指可以被视听触觉感知的、其性状外显程度比较高的基因,如色彩、材料、图像等;隐性基因是指不易被视听触觉明显感知的、性状外显程度低的基因,如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系统中蕴含的价值观、审美观等。[1]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文学基因元,就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隐性基因。
中华民族织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已从上述考古文物中略知概要了。从文学史的视角梳理中华民族织锦文化遗传基因系列,无疑又是开辟一个全新的学术天地。
许慎著《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年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按偏旁部首编排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云:“锦,从帛,金声。”从字面意义上看,“锦”就是有彩色花纹的贵重的丝织品。东汉刘熙《释名·采帛》云:“锦,金也。作之功重,故惟尊者得服。”在刘熙先生看来,锦像黄金一样贵重,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配穿锦衣。那么,有关织锦的文学基因故事,自然就十分丰富,或浪漫或悲情。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6世纪)共311篇诗歌,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其中《诗经·小雅·巷伯》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此诗歌咏了织锦纹彩的华美。《诗经·秦风·终南》又云:“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此诗盛赞锦衣狐裘的高贵华美与着此装的秦穆公气度不凡。应该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学基因的原点与支点。毫无疑问,《诗经》里的织锦,蕴含着商、周、春秋的礼乐制度,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中的隐性基因。
司马迁的《史记》用报告文学的笔法写西汉以前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人物性格分明,呼之欲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道路出了西楚霸王项羽急欲东归。
《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石崇就“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当时寸锦寸金,石崇居然作五十里锦步障,可见他富可敌国奢靡狂妄。唐人王瀚《豪求》有云,“季伦锦障,春申珠履”,言其大土豪也,这自然是春秋笔法的史记。
如果说有关织锦的历史人物故事有点奢华沉重,那么,中华民族织锦文化里的“唐诗宋词”文学基因组就有点浪漫、有点婉约、有点豪迈、有点多情。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灿若星辰,浩如瀚海。此处仅选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岑参和宋代诗词大家苏轼、李清照、陆游、晏殊为例证之。唐代李白诗云:“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岑参诗云:“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由此可对唐诗中的“锦”文化基因窥斑见豹。
唐诗如此“多锦”,那么,宋词又是如何“咏锦”的呢?宋代词人苏轼曰:“不用缠头千尺锦。妙思如泉,一洗闲愁五十年。”苏词有点惆怅。词人李清照曰:“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词有点婉约缠绵。词人陆游曰:“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词有点豪横。词人晏殊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词又有点凄冷。宋词中“锦”文化基因同样可见一斑。由于上述诗词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强大的影响力,这些诗词自唐宋以降,已经流传一千多年。
其实,成语也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最为普罗大众接受的载体之一,也是织锦文学基因元的组成要素之一。例如“越罗蜀锦”这个成语,典出唐人杜甫的《白丝行》:“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此诗比喻越罗与蜀锦各有所长,文学基因流变过程中不可偏废也。我们不妨看一下有“锦”字的成语:锦上添花、锦瑟年华、锦衣玉食、锦心绣口、锦绣天地、锦绣前程、花团锦簇、衣锦昼行……传播爱与美、真与善的价值观正能量,规避假、恶、丑的负能量,显然,这些锦人锦言锦事,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中的隐性基因,也是稳定性基因。
四、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元
从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看,人类基因组至少包含23 000个编码的蛋白质基因,在人这个生物体中,从测序仪中获得的基因组是一条含有A、T、G、C的长链,其基因的识别是一套生物学的、科学的、精密的方法。[1]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其基因识别主要基于文化基因的基因型与表型,其中所洋溢的丰厚人文情怀,就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元。
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文学基因谱系已略述一二,那么,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元又有哪些呢?
中华民族织锦的史祖是谁呢?我以为是黄帝之元妃嫘祖。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刘恕《通鉴外记》亦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何谓“先蚕”?先蚕者,民间以为“蚕神娘娘”也。唐人赵蕤《嫘祖圣地序》记载,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史家考证嫘祖故里在今四川省盐亭县,经过数千年民间传说的传播,嫘祖作为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元,已是确定无疑了。
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部落群,历经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等,成为异于中原文明的西南部落联盟。其中一个名为“蚕丛”的古蜀王“教民蚕桑”,在公元前1613年前后与商王祖甲战而败,死于岷山,其部众也将织锦技艺传播到四川盆地周边各处。公元前1045年,周王朝册封杜宇为蜀王,建蜀国,是为以四川盆地为地理核心的第一个邦国。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蜀国,置蜀郡,此前蜀国作为一个邦国存在了729年。秦惠文王的伟大之处就是把散落在蜀国各地的织锦工匠集中管理,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织锦管理机构“锦官城”。经国家集中管理生产及营销,蜀锦才得以成为“百锦之母”。秦惠文王驾崩,公元前306年,芈月与秦惠文王之子赢稷继位,史称“秦昭襄王”。芈月(?—前265年)被尊为“宣太后”,摄政于秦王庭。公元前272年,秦宣太后引诱义渠王翟丽入秦,杀之于甘泉宫,在东周时代就活跃在陇西一带的强悍的五戎之一的义渠戎,从此彻底改变了“披发、衣皮、粒食”的戎俗。这些变化也促进了强秦官办的蜀锦向陇西羌戎部落集团的流通。所以蜀锦官办与西迁,入楚,芈月都居功至伟。芈月的母国楚国在楚襄王时代出了一个大文士宋玉,宋玉乃三闾大夫屈原之高足,史称“屈宋”,其名赋《登徒子好色赋》如此描绘心中的女神“东家之子”:“眉如翠羽,肤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宋玉把“东家之子”的杨柳细腰比喻为“腰如束素”(腰细得像手都能握得住的柔滑绵软的素锦),成为战国文学史上的绝唱。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元,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蔚然成风了。
中华民族织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西汉,昭君出塞和亲于匈奴呼寒邪单于,解忧公主和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军须靡和猎骄靡,带去丝绸与百工若干,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锦人锦事。在东汉,赵飞燕(前45年—前1年)作为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任皇后,其“身轻若燕”可作“掌上舞”的锦人锦事,一度传为千年美谈。据《赵飞燕别传》记载:“善行气术,身轻若燕,着云水锦裙,唱《归风送远曲》,能作掌上舞。”此“云水锦裙”之美之轻之透,几乎使汉成帝刘骜荒废朝政。汉朝,王昭君、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蔡文姬等在和亲之路上的锦人锦事,则为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人文基因,为中原汉民族与西域匈奴、乌孙、车师、焉耆等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了有进步意义的注解,是古代丝路上人文情怀的艺术再现。
汉魏以降,大唐帝国锦人锦事更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大唐贞观年间,吐蕃专使禄东赞长安求婚于唐太宗,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唐蕃会盟于拉萨,松赞干布仿唐制,禁禇面,着锦服,“吐蕃锦”一时大行于世。沈从文称求婚大使禄东赞身穿的联珠团窠纹锦袍为“番客锦袍”。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出土的团窠联珠含绶对鸟纹锦,大部分来自吐蕃治下的沙州丝锦部落,少部分来自波斯萨珊式立鸟纹的胡锦。这类锦在敦煌文书中又被称为“蕃锦”“毛锦”“胡锦”。在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的40余幅吐蕃锦中,就有红地小花含绶对鸟纹锦、红地联珠含绶对鸟纹锦、红地花瓣团窠对马纹锦、绿地联珠团窠翼马纹锦、黄地花瓣团窠对鹿纹锦、藏青地联珠团窠对鸟纹锦等数十种纹样。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这些吐蕃锦,就是文成公主进藏后唐蕃(汉藏)交流、交往、交融的艺术结晶,已经入列汉藏友好团结的文化基因图谱中,有其唯一性、关键性和可持续复制性。
大唐帝国锦人锦事,有喜——文成公主和亲,有悲——杨玉环自缢。杨玉环(719—756年),号太真,蒲州永乐人,天宝四年(745年)被唐玄宗册封为贵妃,史称“杨贵妃”。杨贵妃与中国织锦文化人文基因之关系,在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亲自为杨贵妃谱写《霓裳羽衣曲》,钦命杨贵妃主演“霓裳羽衣舞”,饰演仙子,祭献老子。“霓裳羽衣”为何锦制造?史无明载,我推测为“像鸟羽一样轻薄华美半透明的蜀锦锦衣”。一是因为蜀锦在大唐帝国是最主要的皇家贡品;二是因为安史之乱,唐明皇远遁蜀地。但是马嵬驿兵变,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兵谏唐玄宗:“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太监高力士遂用一丈白绫,将杨贵妃缢死于庙堂梨树之下。可怜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杨玉环,香消玉陨于一丈白锦。安史之乱平息后,多情皇帝唐玄宗自蜀返长安,作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密令中使改葬杨贵妃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6]杨贵妃最后的遗骸是“以紫褥裹之”,帝王的锦人锦事如此悲情,好在杨贵妃还留下了“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直径5cm,厚2mm,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可以让上皇唐玄宗“朝夕视之”,也让我们后人把它作为超级国宝,带进央视品牌节目《国家宝藏》。
如果说,大唐帝国锦人锦事人文基因有文成公主与杨玉环各领风骚,那么,蒙元王朝锦人锦事又有哪些风流人物呢?窃以为,蒙元王朝锦人锦事则首推黄道婆。南宋末年,松江府乌泥泾人(今上海市徐汇区)黄道婆不堪作童养媳之苦而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三十余年,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元贞年间回到松江府大力推广,使得“乌泥泾被”在长三角一带广为流行,为汉、黎两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沪、琼两地百姓立祠祭念。何也?因为黎锦是中国织锦文化史上的活化石,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尚书·禹贡》:“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清人胡渭《禹贡锥指》称:“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海南之夷人以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7]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是谓黎幕也。”[8]范成大所谓“黎幕”,乃黎族人最著名的贡品“龙被”。正是宋末元初的这个黄道婆,让活化石一样的黎锦活在了经济发达的松江府,成为蒙元时代黎锦织造的标杆式人物,而为后世永志不忘。
如果说蒙元时代汉、黎两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人物是黄道婆,那么,蒙、藏、汉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人物就是西藏“白兰王”。白兰王是元朝中央政府敕封西藏萨迦首领的世俗王爵。按元制,宗室驸马通称“诸王”,藏文史籍记载有四位白兰王:第一位是恰那多吉(1239—1267年),第二位是索南桑波(1291—1328年)第三位是贡噶勒坚赞·贝桑布(1308—1336),第四位是扎巴坚赞·贝桑布(1336—1376年)。其中第一位白兰王恰那多吉名气最大,元世祖忽必烈把其子阔端所生的墨卡顿公主嫁与八思巴之同母兄弟恰那多吉,册封其为“白兰王”,命他管理西藏事务,并赐金印与锦袍铠甲,是谓“白兰王锦袍铠甲”。此锦袍铠甲现藏于西藏萨迦寺,盔甲顶部周围有一圈梵文经咒,周身锦衣织四条飞龙,护额上有缠枝花卉鎏金纹饰。这件锦袍的人文基因故事的历史意义在于,我们上文所述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解忧公主和亲,都是华夏民族乃至汉民族与周边蛮夷、羌戎、匈奴等少数民族和亲。殊不知,蒙元统治者和西藏统治者在历史上也有过著名的蒙藏和亲,四个白兰王和他们御赐的铠甲锦袍,就是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人文基因谱系中的重要物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基因与嵌合基因的混融。
最后,我们研究明末土司夫人秦良玉的御赐锦袍中的人文基因。秦良玉(1574—1648年),字贞素,四川忠州人(今重庆市忠县),在其夫石砫宣慰使马千乘被害后,代领夫职。在明末乱世中,她应明廷征召率领士兵屡破奢崇明之乱,张献忠之叛,解明末北部边境迁安、永平等四城之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作诗赞其“巾帼之功”:“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崇祯皇帝御赐土司夫人秦良玉的两件蜀锦龙袍(现藏重庆三峡博物馆),见证了土家族土司王与中央王朝无事上贡、有事征调、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特殊隶属关系。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族中的一员,土家织锦作为16种少数民族织锦之一,已经入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因谱系之中。
五、结语
文化基因是文化要素在历史中长期积淀形成的结果。时间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复制的特点。锦说中华,中华民族织锦文化中的民族基因、历史文物基因、文学基因和人文基因,每一个基因系列都值得钩沉挖掘研究,都值得拓展延伸创新,作为中华民族织锦文化基因谱系中的原点、支点或衍生点,都是文化基因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代际纵向传递来看,这些成谱系的织锦文化基因,自然蕴含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念,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存续时间越长,代际复制频次越高,纵向传递与横向传递同构性与同步性越时空密接。一言以蔽之,中华民族共同体,锦绣中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