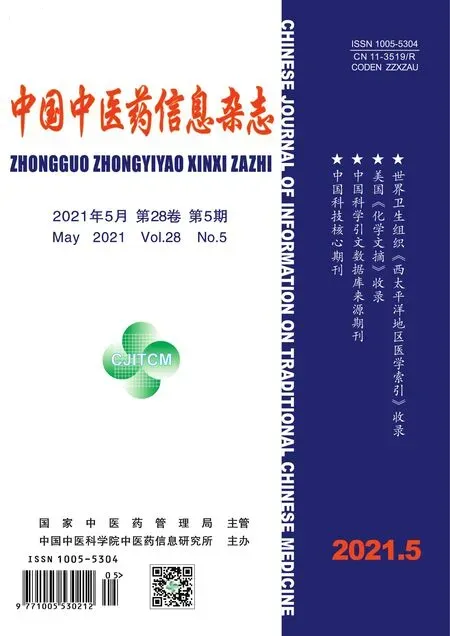溃疡性结肠炎及其不同中医证型肠道菌群研究概况
李红琳,陈江
1.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2.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苏州市中医医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一种难治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临床症状为发作和缓解交替的腹痛、腹泻及黏液脓血便,病程呈慢性经过。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晰,西医治疗多以抑制炎症、促进黏膜愈合及维持缓解为目标,药物常用5-氨基水杨酸(5-ASA)、免疫抑制剂及糖皮质激素等,但长期使用会出现相应的不良反应,而中医治疗优势明显,尤其在维持治疗阶段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肠道菌群对疾病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界也逐渐关注肠道菌群与中医治疗UC的相关性。兹就UC中医证型与肠道菌群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 肠道菌群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1.1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与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差异
褚源等[1]研究显示,与健康人相比,UC活动期患者肠道内梭菌属、乳杆菌属、拟杆菌属及双歧杆菌 属含量减少,而埃希菌属和肠球菌属含量升高,并且双歧杆菌/肠杆菌<1。邱春雷等[2]研究发现,UC患者肠道内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拟杆菌、球形梭菌、柔嫩梭菌及普拉梭菌等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且肠道菌群菌落总数亦降低,而大肠埃希菌和肠球菌的菌落数呈明显增加趋势,可见二者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梁淑文等[3]通过分组比较UC活动期、缓解期及健康组,发现活动期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拟杆菌、真杆菌、消化球菌的菌群数量显著减少,即优势菌属减少,而大肠杆菌、肠球菌和小梭菌菌群等条件致病菌数量显著增加,表明UC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失衡,引起肠道炎症。姜洋等[4]通过宏基因组学16S rRNA测序技术分析了UC患者与正常人群肠道的菌群构成,发现UC患者的肠道菌群整体结构与健康对照人群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含量降低,变形菌门升高。宋军民等[5]将121例UC患者与57名正常志愿者作对照,结果UC患者肠道内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拟杆菌属、酵母菌属、消化球菌属、肠球菌属、小梭菌属的数量明显增加,而真杆菌属的数量显著下降(P<0.05)。
另外,有研究显示UC患者全肠道的微生态相较于正常人均有变化。余今菁等[6]从门和属水平上分别比较UC患者和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差异性,在门水平上,与健康人比较,厚壁菌门在UC患者的肠道菌群中丰度显著降低,而变形菌门和梭杆菌门的丰度呈现增高趋势;在属水平上,与健康人比较,UC组梭菌属、梭杆菌属、乳杆菌属及动弯杆菌属的丰度呈明显增高,而Dialister菌属、粪球菌属、Faecali-bacterium菌属、毛螺菌属及普雷沃菌属的丰度显著下降。可见,有益菌数量或丰度降低,以及有害菌数量或丰度升高,在UC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1.2 肠道菌群在溃疡性结肠炎药物治疗中的作用
在药物治疗UC过程中,肠道菌群变化也较为明显。梁金花等[7]研究显示,黄芪多糖治疗UC模型大鼠7 d后,其肠道内有益菌群(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含量明显增多,而有害菌群(如肠球菌、肠杆菌)含量明显减少,大鼠肠道菌群比例恢复正常。彭怀英等[8]用益气愈溃汤治疗UC患者后,发现肠杆菌含量明显降低,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含量明显增加。另外,芍药汤[9]、复方黄柏液[10]等药物作用于UC患者或动物模型后,均显示有益菌增多而肠杆菌等减少趋势。
随着菌群检测技术不断发展,目前较多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从不同分类水平对肠道菌群进行研究。徐航宇等[11]对黄芩汤干预UC大鼠后肠道菌群变化进行检测,结果显示UC大鼠粪便中乳酸杆菌属明显增多,而理研菌属(毛螺菌属、脱硫弧菌属、罗氏菌属和瘤胃球菌属)显著减少。芦煜[12]研究显示,经祛风宁溃方治疗后,UC大肠湿热证患者病情较前减轻。在肠道菌群方面,门水平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治疗前组厚壁菌门、拟杆菌门丰度显著减少,酸杆菌门丰度增多;与治疗前组相比,治疗后组放线菌门、拟杆菌门丰度显著增多,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减少。属水平上,治疗前组假单胞菌属、拟杆菌属、粪杆菌属、瘤胃球菌属、布劳特氏菌属、Dorea菌属、真杆菌属等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雷尔氏菌属、肠球菌属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治疗后组拟杆菌属、粪球菌属、梭杆菌属、tyzzerella菌属、萨特氏菌属较治疗前组明显增多。
另外,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不同益生菌对UC的积极治疗作用。Llopis等[13]发现,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 DN-114001能一定程度减轻TNBS大鼠UC模型的黏膜损伤、炎症反应和肠道黏膜屏障的破坏。王春晖等[14]发现,以普拉梭菌干预UC小鼠7 d后,其粪便中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明显增多,肠杆菌、肠球菌数量明显减少,免疫应答平衡状态也得到改善。
由上可知,肠道菌群参与了UC发生、发展及药物治疗的全过程,其主要表现趋势为UC发生时肠道内有益菌含量减少,有害菌含量增多,二者比例失去平衡状态,而药物治疗会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促使有益菌和有害菌的数量及结构恢复平衡状态。
1.3 肠道菌群引起溃疡性结肠炎的机制
1.3.1 引起细胞因子变化而破坏肠道黏膜屏障
人体肠道黏膜屏障是保护肠道黏膜的重要结构,包括机械、生物及免疫屏障。一旦肠道菌群失调,如有益菌减少,则肠道内条件致病菌增多,而这些致病菌分泌的肠毒素会直接作用于肠道黏膜,使肠上皮细胞通透性增高,即肠黏膜的机械屏障被破坏。而且,致病菌会产生一些可以诱导肠道炎症的物质,会激活肠道黏膜免疫系统,诱导核因子-κB(NF-κB)的激活,同时分泌大量细胞因子。益生菌对UC的治疗作用机制也可从侧面推断肠道菌群失调引起UC的作用机制。据报道,益生菌能有效抑制NF-κB活化途径,减少一些促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IL)家族中的IL-1、IL-8等表达,同时上调抗炎因子(如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TGF)-β,从而调节肠黏膜免疫耐受,抑制中性粒细胞浸润引起的损伤[15]。大肠杆菌Nissle被证实能降低TNF-α、IFN-γ和IL-2的水平,并提高IL-10表达水平,从而减少肠黏膜上皮T细胞浸润,达到减轻肠道炎症的效果[16]。
1.3.2 对内源性代谢产物的影响
肠道菌群依赖机体营养供给,同时代谢也离不开肠道菌群的参与,二者是共生关系。UC患者体内的代谢物质如氨基酸、乳酸、葡萄糖及脂质等都与健康人有明显差异,而肠道菌群与这些物质有一些共同变化。研究表明,UC代谢组学中大量差异代谢物与肠道菌群关系密切,如梭菌属细菌和拟杆菌门细菌参与对甲酚的合成过程[17]。有学者综合分析UC患者的血清代谢物和粪便中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现其血清中有18个代谢物是肠道菌群和宿主共同参与物质代谢,且苯乙酸、琥珀酸、羟基苯乙酸、3-吲哚乙酸、延胡索酸及苯丙酸的含量变化可间接反映拟杆菌属和梭菌属菌群的活性变化,因拟杆菌属和梭菌属菌群在机体内参与了酪氨酸和苯丙氨酸代谢过程[18]。
1.3.3 基因调控
一些学者认为,UC发病机制与基因易感性有关。研究发现,某些细菌DNA的CpG基序能刺激部分免疫细胞产生以TH1型为主的免疫反应[19]。该项研究使用的是DSS结肠炎动物模型,使用细菌CpGs处理模型动物后,发现急慢性结肠炎病情有加重表现,而在诱导结肠炎前用细菌CpGs处理动物可使结肠炎病情减轻。
2 溃疡性结肠炎常见中医分型及其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
《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20]将UC分为7个中医证型,即大肠湿热证、热毒炽盛证、脾虚湿蕴证、脾肾阳虚证、阴血亏虚证、寒热错杂证、肝郁脾虚证。笔者仅就其中常见证型即大肠湿热证、脾肾阳虚证、脾虚湿蕴证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研究进行梳理。
2.1 大肠湿热证
本证临床症状多见腹泻,里急后重,大便夹黏液脓血,并伴肛门灼热、小便短赤、口干口苦等热象,舌脉象多为舌红、苔黄腻、脉滑。大肠湿热证是UC常见的中医证型,相关研究较多。陈韵如[21]通过对肠道菌群中最重要代表菌双歧杆菌和大肠杆菌的DNA进行荧光定量分析,研究UC脾胃湿热证与肠道菌群关系。结果显示,脾胃湿热证患者粪便中的双歧杆菌含量明显低于脾气虚组及健康人组,而脾气虚组与健康人组的肠道菌群无明显差异。李舒[22]研究显示,相较健康人组,湿热内蕴组的厚壁菌门和普氏菌所占比例减少,而拟杆菌比例增加,放线菌门(主要为棒状杆菌)和变形杆菌门(主要为嗜血杆菌)所占比例高于脾胃气虚组,且相对脾胃气虚组和脾虚湿热组,湿热内蕴组的菌群多样性最低。丁庞华等[23]研究UC大肠湿热证患者与健康人群之间肠道菌群的丰度差异,发现健康人群以类杆菌科、多形杆状菌、硬壁菌门、梭菌属等为主,而大肠湿热证UC患者肠道菌群以乳酸菌、乳杆菌、丹毒菌等为主,并且阿克曼西亚菌在UC患者中处于富集状态。
2.2 脾肾阳虚证
本证多为UC缓解期证型,主要临床表现为久泻不止,大便稀薄、夹有白冻,或伴完谷不化,腹部隐痛并喜温喜按,腰酸膝软等,舌脉象多为舌质淡胖、苔薄白润、脉沉细等。王晓东等[24]研究发现,四神丸可有效促进脾虚小鼠粪便和结肠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类杆菌等有益菌数量增加,且肠杆菌、肠球菌等有害菌数量减少。陈志敏等[25]研究发现,二神丸能促进脾肾阳虚泄泻大鼠肠道中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增殖,同时抑制大肠埃希菌和肠球菌生长。这些研究表明,UC脾肾阳虚证与肠道菌群失调关系密切,主要相关菌群有双歧杆菌、类杆菌、乳杆菌,以及肠杆菌、肠球菌等。
2.3 脾虚湿蕴证
本证临床症状主要有黏液脓血便,且白多赤少,或为白冻,脘腹胀满,伴随症状多为肢体困倦,食少纳差,舌脉象多为舌质淡红、边有齿痕,苔薄白腻,脉细弱或细滑。吴秀等[26]研究表明,四君子汤能恢复脾虚证小鼠盲肠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脆弱拟杆菌及大肠杆菌的数量接近正常水平,并提升细菌定植抗力。
2.4 其他
魏文先等[27]研究显示,用乌梅丸加减联合泼尼松治疗UC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用泼尼松,且联合用药在提升双歧杆菌、乳酸菌水平,降低大肠杆菌水平方面亦明显优于单用泼尼松。乌梅丸具有缓肝调中、清上温下、涩肠止泻功效,是治疗寒热错杂证痢疾的经典方,这表明UC寒热错杂证亦与肠道菌群失调密切相关。情志是影响UC进展的重要因素,情志不畅易致肝郁,肝郁则可直接影响机体肠胃功能,故肝郁脾虚证也是UC较为常见的证型。柯一帆等[28]研究显示,不同中医证型UC患者肠道菌群的构成及菌群代谢特征差异明显,其中副拟杆菌含量下降与肝郁脾虚证相关性最高,所以副拟杆菌有望成为肝郁脾虚证UC的诊断性生物标记物。
3 展望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目前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最多的是消化系统疾病,但中医理论基于辨证论治思想有着“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之说,有些对肠道菌群与中医不同证型的相关性研究,虽不是针对UC患者或动物模型进行,但对UC依然有启示作用,如Xu等[29]对224例湿热证(以臭黏便、黄腻苔为证候特征)的初发糖尿病患者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和临床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能产生短链脂肪酸的菌群如Faecali和双歧杆菌在对照组与湿热证型糖尿病患者中差异明显,而通过清热化湿治疗后,这些细菌显著富集,且与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等密切相关。这些结论从治疗前关联性分析和治疗后反证均被证实,是湿热证与肠道菌群之间相关性的确切证据。
当然,目前关于UC中医证型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大多处在肠道菌群结构失调的宏观层面上,本研究的目的是为UC不同中医证型找出其独特的诊断性生物标记物,以期更好为UC中医不同证型的临床诊断提供便利。然而,目前临床和实验研究尚存不足之处:①中医证型动物模型复制难度大,缺乏科学标准,说服力不强;②UC中医证型与肠道菌群失衡的具体作用机制不明确;③肠道菌群种类庞大,作用机制复杂,要筛选出与证型相关某一项或几项独特的菌种较为困难。笔者认为,今后研究应从UC不同证型的肠道菌群结构差异着手,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部分,逐渐深入研究分析具体菌属、菌种,为UC中医证候提供肠道菌群方面的依据,使UC不同中医证型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