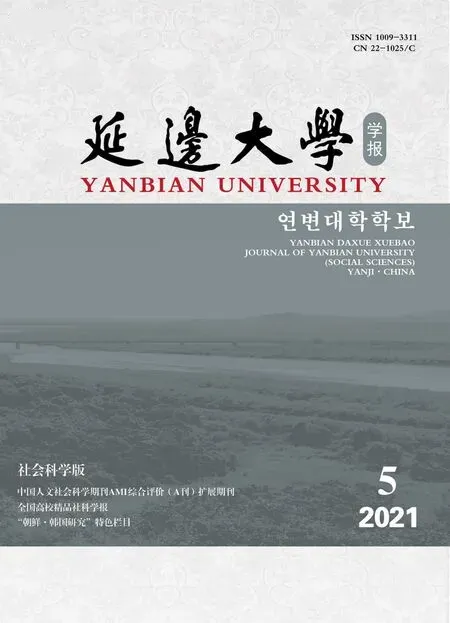《草枕》小说主题与美学新论
王 广 生
《草枕》是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继《我是猫》和《哥儿》之后创作的第三部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厌倦都市生活的青年画工来到偏远山村写生旅行的故事,线索单一,情节简单,人物的形象并不鲜明,甚至没有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称之为小说,但不具备典型的情节化设置,叙述以青年画工的视角和内心活动展开,或描绘,或议论,呈现出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文风。因此,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各个场面独立、多焦点的具有美文因素的小说。(1)渥美孝子:《夏目漱石「草枕」―絵画小説という試み―》,《国語と国語学》,东京:明治书院,2013年,第49页。由于主线是青年画工的“非人情”的写生之旅,夏目漱石在论及《草枕》的特色时,称其为“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小说”。(2)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16卷别册》,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第544页。故目前学界多主张小说的主题为“非人情”的美学,而强调《草枕》艺术审美的纯粹性,或曰呈现了一个隐居而唯美的艺术世界,这似乎已成为学界共识。
不过,朴裕河和藤尾健刚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都注意到了《草枕》美学主题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现实因素和伦理学诉求。前者指出《草枕》中的“美”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带有明确的权力支配意识。(3)朴裕河:《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とジェンダー;漱石·文学·近代》,东京:クレイン,2007年,第79-128页。后者则主张《草枕》的美学实质乃是伦理学,认为夏目漱石早期美学观念以大西祝的《悲哀的快感》为中介,以朱子学的“恻隐之心”为伦理学前提和基础接受了叔本华哲学的影响。(4)藤尾健刚:《「草枕」の美学=倫理学:朱子学、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大西祝》,『漱石の近代日本』,东京:勉诚社,2011年,第55-78页。可惜的是,两者均忽视了禅宗,尤其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下简称“无住”)这一观念在《草枕》美学理念建构中的关键位置。
本文在引述和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基于文本细读和文学发生学的立场,对《草枕》的主题及美学理念提出新的见解,即主张《草枕》并非学界所认为的是一个“非人情”的艺术世界,其主题思想乃是一种“美学—伦理学”的构造。这一“美学—伦理学”的思想构造具有多层指涉,其思想的基础主要是以禅宗为中心的东方思想,并含有个人和国家叙事的双重视角。
一、《草枕》的主题与特色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8月28日,夏目漱石在给弟子小宫丰隆的信函中写道:
我在《新小说》上发表了一部名为《草枕》的作品,预计9月1日刊发。你务必要读一读,这一小说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不过,莫误解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杰作)。(5)夏目漱石:《漱石全集·书简(上)》,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第546页。本文引述的译文,若无特殊说明,均为笔者所译。
“开天辟地”自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未曾有过”无疑也表达了夏目漱石对《草枕》创作的艺术自信和自觉。“未曾有过”指的是什么呢?对此,夏目漱石在不久之后撰写的《我的〈草枕〉》(1907)一文中提供了较为明晰的线索:
我的《草枕》是以与一般意义的小说截然相反的意义写成的。若能给读者留下这么一种感觉,即美的感觉就满足了,其他的没有任何目的。……一般意义的小说,也就是让读者玩味人生真相的小说也是不错的。但我想,还应该有一种让人忘却人生之苦、起到慰藉作用的小说存在。我的《草枕》就属于后者。……以往的小说是川柳式的,以表现人情世故为主,但此外还有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的小说。……如果这种俳句式的小说——名称很怪——得以成立,将在文学界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种小说样式在西洋还没有,日本也还没有,如果在日本出现了,就可以说,小说界的新运动首先从日本兴起了。(6)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16卷别册》,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第544-545页。
由此可知,夏目漱石所说的“未曾有过”即指“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小说”。
夏目漱石在《草枕》的开篇就以叙事者的口吻,可以说是不自觉地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诗和画(艺术)进行了独特解读:
从难居的人世剔除难居之烦恼,将可爱的大千世界如实描写出来,即是诗,即是画,或是音乐,抑或雕刻。具体来说,如若不写也可以。以眼观之,就能产生诗与歌。情思不落于笔端,内心也会响起璆锵之音;丹青虽不在画架涂抹,而心中自有绚烂之色。我观我所居之世,将其所得纳于灵台方寸的镜头中,将浑浊俗世映照得清醇一些,也就满足了。故无声之诗人可以无一句之诗;无色之画家可以无半尺之画,但也可以静观人世,脱落烦恼,步入于清净之界,亦能创建不同不二之天地,扫荡一切私利私欲之羁绊……(7)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3页。
此段叙述,夏目漱石不仅区分了美和美感,即“诗”可以分为有形之诗与无形之诗,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发现“美”的途径与方法,即“我观我所居之世,将其所得纳于灵台方寸的镜头中,将浑浊俗世映照得清醇一些”。我们将这一方法称之为“观照”。换言之,将自身悬置于人世之(上)外,对身处的世俗世界以佛教之眼(灵台之镜)的“观照”,获得清醇(纯粹审美)的经验。而“脱落烦恼”,进入“清净之界”,“创建不同不二之天地”的关键是“扫荡一切私利私欲之羁绊”之方法。
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开篇并非就“美是什么”抑或“什么是美”而展开,而是对“如何发现美”的表述,这一思路不仅显现于此,更是贯穿小说整体,统摄全局,成为《草枕》美学的核心命题。与侧重内容的“非人情”美学之观点相对,笔者将对“如何发现美”的理念称之为“观照”的美学。“观照”一词与上述佛教的“观照”理念相关,也与道家的静观等东方思想相通,这一点容后再叙。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草枕》中,夏目漱石借助主人公“我”之口,把这次寻“美”之旅有时也称为“非人情”之旅:
我本就是为了追求非人情而出门旅行的,用另一种眼光看人,所见到的就和之前生活在逼仄俗世中所见不同。即便不能完全抛弃人情这东西,我也要做到如同观看能乐戏剧时的立场吧。(8)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8页。
夏目漱石虽然没有将《草枕》认定为“非人情”小说,但结合其主线即是对一位青年的逃避、写生之旅的叙事,辅以这一“非人情”的说法,便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主张《草枕》美学主题乃“非人情”的重要依据之一。
那么,《草枕》的主题到底是美的方法论,即如何发现美,还是美的内容之论,即“非人情”呢?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思考和分析其哲学思想以及“非人情”的内涵。
二、《草枕》的美学与思想
截至目前,《草枕》中“美”的核心理念,被研究者命名为“非人情”的美学,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隐居而唯美的艺术世界,似乎已成为学界共识,如丰子恺先生就主张《草枕》的美学贵在“艺术之心”,强调艺术的超现实性。(9)丰子恺:《新艺术》,《旅宿》,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14页。
不过,美学自哲学中独立而来,本质上乃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也即一种哲学思想。因此,解读《草枕》的美学主题,更需从美学及其哲学思想基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在此立场下,《草枕》中的“非人情”并不具有独立的美学内涵,而应理解为基于禅宗思想的“观照”美学的外化与表征。“非人情”之“非”也需站在禅宗的角度来加以诠释。
(一)“非人情”美学观点的理由及其不足
主张《草枕》主题为“非人情”的美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具体的理由:第一,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及了“非人情”这一概念;第二,《草枕》及《我的〈草枕〉》等处涉及“非人情”的内容。
从逻辑上而言,第一个理由不足为虑。因为其事实乃“非人情”美学结论的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即无关条件。就第二个理由而言,固然可以导出《草枕》的内容是“非人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草枕》的美学核心抑或主题也是“非人情”。美学和主题是对具体内容的抽象之概括,是对内容的理性提升,绝非内容本身。我们寻求的是小说内容和题材背后的美学思想,即支撑具体美学意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此外,夏目漱石的职业是作家,是职业的“撒谎”者,他们以艺术而非日常、现实的方式理解和书写这个世界,这一现实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方式去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文字和言语方式。
遗憾的是,文学研究者们似乎没有上述自觉,并在此自觉之下区分内容和主题、题材和美学以及作家这一特定群体的言说方式。日本学者松村昌家曾撰文指出,当时的明治文坛流行的是“人情写实论”、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和自然主义文学风潮,以《金色夜叉》《不如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为代表的描写“情欲”甚至“肉欲”的作品才是主流。因此,松村昌家认为,《草枕》以描写“非人情”为主题,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文坛的一种文学的批评和反抗。(10)松村昌家:《小説美学としての「非人情」——「草枕」の成立》,《夏目漱石における東と西》,东京:思文阁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换言之,松村昌家主张夏目漱石在和主流文学的抵抗中创作了《草枕》,从而实践了“非人情”的美学。我国如陈雪等学者也多继承了这一思路,认为《草枕》中的美学是“非人情”之美学,其目的在于对抗自然主义文学。(11)陈雪:《由〈草枕〉解读夏目漱石的非人情美学》,《滁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3-25页。在他们看来,《草枕》中的美学是一种与描写“人情”相对立的文学审美,也即“非人情”美学。
(二)禅宗视角下的“非人情”与“观照”
综上,《草枕》主题是“非人情”的美学,流行学界,几成共识。但此主流之说有两个主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对于“非人情”之“非”的解读,二是未能区分小说内容和美学主题之间的差异。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发现并分析《草枕》这个文学文本的重要哲学基础,即禅宗思想。
具体来说,持有“非人情”美学观点的学者,基本将“非人情”之“非”理解为对“人情”的排斥与否定,这种以日常语言学的立场去理解具有特定思想内涵之“非”的思路,恰是对“非人情”之误读的根源之一。也就是说,欲理解“非人情”必须理解何为“非”。此外,回到小说本身,我们也会发现:《草枕》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现、获得“美”,而不是“美是什么”。也就是说,《草枕》借助主人公“我”并没有追问“美”的本质和内涵,夏目漱石交付给主人公“我”在《草枕》中的任务是思考通往“美”的方法和途径。换言之,小说集中呈现的“美学”不是本体论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美学,此即为前文所说的基于禅宗思想的“观照”美学。
基于“禅宗”的视角,笔者认为“非人情”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只是“观照”美学的外在表达和内容之一。其理由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渐次论之:
1.《草枕》与禅宗的“无住”观念
《草枕》的美学理念主要体现了禅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观念,而“观照”是“无住”观念内在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无住”观念指导下的方法论。
《草枕》与禅宗思想关系密切,禅宗的意象俯拾皆是、随处可得,文体用语也充满禅机禅趣。鉴于此,韩国学者陈明顺甚至建议称之为禅宗公案小说。(12)陈明顺:《漱石漢詩と禅の思想》,东京:勉诚社,1997年,第128页。不过,迄今为止,鲜有学者指出《草枕》中禅宗的思想实则集中在“无住”观念这一事实。
伽达默尔曾说,一个文本,甚至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及环境的文本,都是能够阅读和被理解的,而且任何人都不需要完全以作者式的理解来阅读文本。(13)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4页。因为,理解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的主观体验性。尤其对《草枕》这样“以美为生命”的小说,回到作品自身,去感受和理解作品中审美的情感和思想活动或许更好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为读者设定了通往文学王国的暗道和密码,因此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且看小说的开篇:
我一边攀登山路,一边这样想:
若是发挥才智,则棱角分明;若是任凭感情,则会随波逐流;若是坚持己见,则可能处处碰壁。总之,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之时,便产生了诗,产生了画。(14)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3页。
这段译文流传甚广,可以看作夏目漱石假借主人公之名,暗含以发生学的角度对诗和画(艺术)进行了独特的解释和说明,即诗和画(艺术)产生于对人世难居的“觉悟”,而且这一“觉悟”是在一刹那、一瞬间发生的。这里的诗和画(艺术)是指生成于内心的诗意和画境,而“觉悟”也十分接近一种审美意识的心理活动。换句话说,此处的“觉悟”即是顿悟,是禅宗式的体悟与认知。
此外,小说的开篇“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之时,便产生了诗,产生了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尤其是《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说,《草枕》的开篇就是“无住”思想的具体化和文学形象化表达。据传,六祖慧能正是听到五祖弘忍讲授到这句话时,豁然开悟。(15)陈秋平、尚荣译注:《金刚经·心经·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2页。受“无住”观念的影响,《六祖坛经》中禅法(无念、无相、无住)的关键也是落在了“无住”这一环上。
“无住”这一观念,体用不二,包括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在方法论上,劝诫人们不要执著万物虚相,而要以觉悟之心、以佛教之眼发现一种纯粹的真实之美(本来面目),这就是“观照”。这一“观照”的过程,若以《草枕》的一段文字来说,就是“我观我所居之世,将其所得纳于灵台方寸的镜头中,将浑浊俗世映照得清醇一些”。(16)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3页。因此,“观照”实际上与“无住”互为表里,相互通联。也可以把“观照”理解为“无住”思想的一部分,是“无住”思想在方法论层面的集中表达。
2.“非人情”之“非”乃是禅意
小说在结尾处抵达高潮,其中也藏匿着理解《草枕》美学的关键线索:女主人公那美在送别前夫之际脸上呈现出哀怜之时,“我”拍了拍那美的肩膀,轻声地说:“就是它,就是它,它就可以成为一幅画”。(17)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92页。
小说中,那美请求“我”为她画一幅画,而“我”一直未能找到可以入画的美感,但在那一刹那,“我”终于在其脸上的“哀怜”中发现了“美”。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此刻的那美不再是那个佯狂、闪现机辩锋芒的女人,而是以“忘我”的方式抵达了本来面目。不过,她的“哀怜”是在旁观者的视角下完成的。因此,此处可以入画的“美”不是“哀怜”本身,而是对“哀怜”的一种“发现”,一种“观照”,从而也是一种审美。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美”自“观照”中来,即对“人情”的“观照”产生出“美”;其二,“美”并不否定“人情”,而是以特殊的方式接受、肯定了“人情”。所以,若是仅仅站在“非人情”美学的立场,就难以解释清楚“非人情”“哀怜”“美”和“观照”之间的互动联系。而对此理解的关键或许就在对一个“非”字的解读上。也就是说,“非人情”之“非”不能按照日常用语的逻辑去把握,而应从禅宗思想的立场去理解。对此,日本学者近藤文刚就曾说过:“世间的‘非’多半含有否定的意味,不过若从佛教特别是禅的思想的视角考察,‘非’表达了对于肯定、否定之意的超越,反而指向了事物的本来面目”。(18)近藤文刚:《禪に於ける非人情の一考察》,《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59年第2期,第559-560页。因此,“非人情”在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视角下,就不再是对“人情”简单的否定抑或肯定,而是在“扫相破执”“无相无住”的观念指导下,用“非”“不”等解构的方法,对世俗人间“人情”的谛观和再发现,从而恢复“人情”的本来面目。总之,如上所言,此处的“非”,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的谛观,也是一种美学的“观照”。
3.“观照”是内因,“非人情”为其外显和表征
从逻辑上来说,“非人情”和“观照”两者有着因果关系,“非人情”是果,“观照”是因,前者依附于后者,且是后者的外显与表征。且看《草枕》第一章:
为了了解这一点,只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这样才有可能弄清楚本来的面目。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戏颇有意思,读小说也是如此。读小说感到有趣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利害念头束之高阁了。在这一看一读之间,便成了诗人。(19)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6页。
又如:
芭蕉看到马在枕头上撒尿,也可将之风雅入诗。我也要把即将碰到的人物——农民、商人、村长、老翁、老媪——都当成大自然的点缀加以描绘和观察。(20)夏目漱石:《草枕》,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08页。
芭蕉马尿入诗,这种超然物外、立地成佛的风采背后是以禅宗思想为依托的。同理,“我”想要学习芭蕉这种态度,将世俗的世界审美化,其方法也必然是禅宗式的“观照”。在日本学者冈崎义惠看来,所谓“谛观”,即“观照”,是实现“非人情”唯一的途径和方法。“非人情”,就是通过“抽离人情而谛观世界”,从而抵达宗教或艺术的世界。(21)冈崎义惠:《鷗外と漱石》,东京:要书房,1956年,第168页。这一观点恰好指出了“非人情”与“观照”之间的逻辑联系。
其实,“非人情”不仅是“观照”带来的结果,经由“观照”这一过程,它也就成为了“观照”美学的内容。日本学者藤尾健刚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非人情”是一种“审美认知的态度”,也是一种“美的观照”。(22)藤尾健刚:《漱石の近代日本》,东京:勉诚社,2011年,第68页。不过,藤尾这一结论并非从禅宗思想视角出发观察而来,而仅仅是从《草枕》的美学特质归纳而来。(23)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者如王成、刘晓曦、马英萍等虽均已指出《草枕》的禅宗思想的特色,但未能进一步指出禅宗中的“无住”这一观念在小说中的独特位置,也未能将禅宗思想联系小说的美学并指出《草枕》的“观照”美学之特质等。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说,“观照”这一禅宗思想的视角和立场正是理解“非人情”的关键。而《草枕》的内在思路就是借助禅宗的“无住”观念,观照世俗情欲,从而抵达一种“非人情”的审美境地。
4.“观照”美学背后是东方思想底蕴
以上论及“观照”之美学思想,主要侧重其与禅宗的关系。其实,此文中的“观照”美学在范畴上可归为东方的静观美学的一种。细而论之,静观美学的思想资源除禅宗之外,还有朱子学的“恻隐之心”、老庄的“虚静”(2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6页。“涤除玄鉴”(2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1页。“见独”(26)斯波六郎:《中国文学における孤独感》,东京:岩波书店,1956年,第15页。等的影响,可以说,儒释道思想一并构建了静观美学的东方特质和传统。
此外,英语文学专业出身、曾留学伦敦的夏目漱石也曾受到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等近代思潮的影响,亦为共识。(27)M.K.Bourdaghs,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Criticall Writing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34.只是,在其“观照”美学的形成过程中,禅宗思想即“无住”观念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三、美学—伦理学
将《草枕》美学界定为“观照”的美学,会发现《草枕》隐含着构建“介入性”美学的努力,理解其美学向伦理学的延展和变异,更好地把握夏目漱石文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深层的思想困境。
日本学者水川隆夫曾认为《草枕》就是围绕日俄战争设置的一个自我想象的隐喻。(28)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と戦争》,东京:平凡社,2010年,第133-134页。其分析虽然有过度诠释之嫌,但也向我们提示了《草枕》并非一个纯粹审美世界的事实。
表面上看,《草枕》描写的是青年画家远离城市,来到一个偏远山村的“非人情”之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寻求一种抽离世俗人情的、静观的、纯粹的美。但这种“美”的最终完成,却是在这个偏僻而封闭的世界被打破的时刻——女主人公那美为远赴战场的弟弟送行,却又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突然看到了前夫的脸——也就是那美脸上露出“哀怜”的那一瞬间:
茶旧的礼帽下,慢慢探出来一张流浪汉似的脸,胡子拉碴的。那美姑娘不经意和这个流浪汉目光交接,也就在此刻,火车滚滚开走起来。流浪汉那张脸也很快消失不见。那美有些茫然地望着火车开走的方向。在她茫然之中,有一种未曾有过的“哀怜”之情奇妙地浮现于她的脸上。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有了这个就可以作画了!”
我拍了拍那美的肩膀低声说。一幅画在我心中刹那间完成了。
这是全篇的结尾,也是小说的高潮。在这一场景中,“美”的发现是在“观照”的视野——男性画家“我”的眼睛——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女性之“美”的发现者以及管理者是来自都市的男性画家“我”。可以说,《草枕》是夏目漱石借主人公“我”之眼创造出的一个“非人情”的审美世界。
韩国学者朴裕河曾论及《草枕》的基本线索是寻“美”之旅:都市青年男性画家来到一个相对封闭——远离西洋/现代文明——的田园世界,发现了日本传统之“美”,这样的“美”带有明确的权力支配意识。(29)朴裕河:《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とジェンダー;漱石·文学·近代》,东京:クレイン,2007年,第110-111页。
藤尾健刚也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认为《草枕》美学思想中有扫除个人情欲、回复人的本性的努力,带有某种伦理诉求:
作为夏目漱石美学成立的条件,即超越利害观念,被更多地表达为排除“私欲”之“人情”以及美的观照、保持心之“本性”的内外一体化。《草枕》亦是如此,发现美,就意味着要养育未被私欲污染的澄澈精神,未被恶俗所附身的清洁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与叔本华哲学相同,《草枕》中的美学,即伦理学也。(30)藤尾健刚:《漱石の近代日本》,东京:勉诚社,2011年,第68页。
藤尾将《草枕》的美学看成伦理学也不为过。只是,他所指的“伦理学”主要是面向个人道德内修的伦理学(ethics),而非政治伦理学抑或服务于国家道德论建设的伦理学。实际上,这一伦理学具有多层指涉,内含个人和国家叙事的双重视角。因此,若结合朴裕河的观点,将《草枕》的美学思想理解为“美学—伦理学”似乎更准确。
在“美学—伦理学”的视角下,可以发现《草枕》美学主题的丰富性,了解到文学文本内含多元文化和思想的事实,可以知道《草枕》并非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纯粹审美世界。
需要明确的是,明治日本文化语境中的“伦理学”概念和范畴不同于汉语中的“伦理学”,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日本近代首先出现以“个人”为关键词的理论性伦理学“ethics”,其后与意在道德层面整合其“国民道德论”潮流形成既对抗又融合的态势。随着日本近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个人的话语受到压制,这两种伦理学最终被统合于“人类共同体之理法”(和辻哲郎语)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色彩浓郁的伦理学之潮流内了。
那么,《草枕》美学中的伦理学是怎样的状态呢?
回到《草枕》文本,还可以发现“我”的美学思考是在西洋/现代vs东洋/传统这样对立的、可以相互“观照”的图式中得以展开的。例如,小说的第一章就颇费笔墨地讨论起东西方诗歌之别,以叙事者“我”的视角,主张与西方/近代入世的诗歌相比,东方/古典诗歌摆脱了世俗人情、同情、爱和正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让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可以抛却一切利害得失、超然世外。
从“美学—伦理学”的立场观之,通过上述比较和参照,《草枕》在美学意义上肯定了东方/古典诗歌的价值,确立了东洋/传统诗歌相对于西洋/现代诗歌的“合法性”。(31)需要说明的是,《草枕》的美学思想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东方思想文化,一个是西方的近代美学思想。《草枕》在美学主题上即可看做这两种美学思想的对话录。换言之,作为夏目漱石早期代表作,刊行于1906年的《草枕》被认为是一部讨论艺术的小说,而出版于1766年的《拉奥孔》是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的美学名著,两者都以“诗与画的界限以及美与表情的关系”为中心展开美学的阐发。有趣的是,前者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多次引述后者的观点而立论,但两者在美学理念上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差别与统一:《拉奥孔》认为诗画有别,突显诗的优越,寻求一个行动的希腊;而《草枕》主张诗画一致,肯定画的美学,看到一个静观的东方,从而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上述事实至今被国内外学界所忽略,却关乎《草枕》美学的深层。
总而言之,夏目漱石在东洋/传统文化比照下发现(指摘)西洋/现代文化之不足,进而思考和建构当代日本文化之美。不过,对当代日本之“美”的确立,并不只是面向西方/现代的否定,还有面向日本内部(国民和政府)的质疑和批评,如在小说结尾,借助“火车”这一强烈的隐喻,夏目漱石对日本现有的文明观念和海外殖民行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女主人公“哀怜”之美的发现(明线),也完成了在国家话语层面的伦理学批评(隐线)。换言之,夏目漱石在“观照”美学的框架下,对西方/现代美学的质疑和否定(向外),实际上和前面所言的对日本女性/传统之美的发现和管理(向内)互为表里,一并构成了《草枕》“美学—伦理学”的“个人—国家”话语两个层面。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文本,它具有一种暗合了男性支配观念下的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和明治时代国民道德秩序的意味。
总体而言,《草枕》的“美学—伦理学”,一方面可视为创作者夏目漱石对日本追随西方列强对外发动殖民战争——以“私欲”的立场暴力占有的国家“美学”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可视为对个体如何建构世界观的道德建言,且两方面共存于作者对日本近代文化之美的追问和思考之中,充分表达了他对日本近代主体性建构的关注思考和不安。
四、结语
美学,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历史维度、意识形态内容,具有一种超越时代又融于时代的特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近代美学的确立者康德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世人眼中,这位无比纯粹的美学家和哲学家,却也是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首倡者和思想革命的引路人。也可以说,审美基于情感的历史维度和人性的哲学深度,以形象和感性的方式显现了人所在的确切位置与生存困境。
夏目漱石的《草枕》之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它“以美为生命”的主题,更在于它寻找、发现美的方式即“观照”。因为“观照”既可以通往美学,也可以抵达伦理学。在“美学—伦理学”的互动中,夏目漱石实践了以文学审美“介入”社会的努力,也贯彻了他自己及那个时代的创作方法论,即通过东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补救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弊病。这至今都富有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