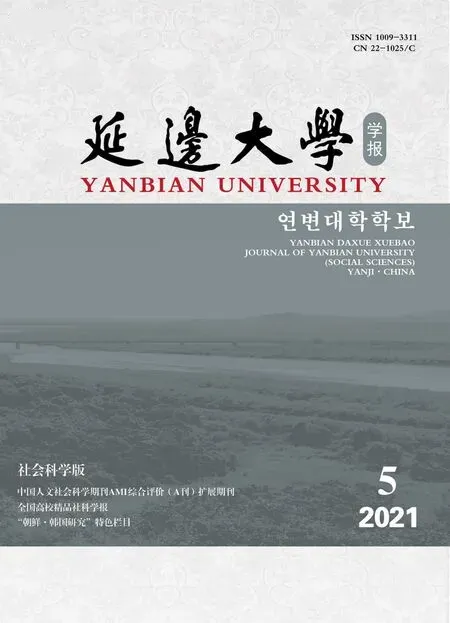“徐福逸书”与近世日朝交涉中的东亚文脉
刘 晨
徐福传说最早见于《史记》,并逐渐演变成为“徐福经朝鲜半岛东渡至日本”(1)参见[韩]许玩钟:《韩国的“徐福传说”考》,《口承文艺研究》第28期,2005年,第80-95页。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暂不论及徐福途经朝鲜半岛的传说。这一将东亚三国都关联在内的共通性传说,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围绕该传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相关实证研究自不必提,传说内容的演变与传播也得到了三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持续讨论。其中,《日本刀歌》(2)本文论及的《日本刀歌》是指收入《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及包括《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在内司马光诸文集中的诗作。参见金程宇:《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刀歌〉》,《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第154-155页。所引出的“逸书百篇”由徐福带至日本、流传后世的传说,不仅在东亚世界中广为流传,而且出乎意料地在近世日本与朝鲜的外交和文化活动中产生了特殊影响。本文尝试在梳理“逸书存日”说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廓清前近代中日朝三国文人阶层围绕该传说展开的日本历史认知的真实样貌,着重分析该传说在近世日朝交往中所引发的思想文化交涉与冲突,以期理解中国不在场的前提下东亚交流活动的政治与文化脉络。
一、“徐福逸书存于日本”说的形成过程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始于《史记》中徐福及其渡海活动之叙述的徐福传说,就其演变、流传过程而言,作为整体的徐福传说可以分为传说出现、止居日本说形成、具体内容基本定型等主要阶段。(3)严绍璗:《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第115-120页;朱亚非编:《徐福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137页;吴伟明:《徐福东渡传说在德川思想史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期,2014年,第161-176页。传说出现之初,并不包括“徐福止居日本”或“逸书百篇”等内容,而这些事关东亚世界政治活动与文化交流的内容,却很少获得从政治或文化交涉视角的探析。特别是“逸书百篇”存日说的出现,事实上构成了徐福传说定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变化与流传事件,但是围绕该说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献与政治、文化背景,尚需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徐福传说出现和演变的早期,的确为日后赴日和逸书两点要素的生成提供了基本前提。最早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言齐人徐福入海的目的地为“蓬莱、方丈、瀛洲”等三神山,《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又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为位于齐地以东海中、山峦众多的日本列岛成为其止居之地提供了可能性;而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等记载,则为“焚书”之前尚存的古文《尚书》等被徐福携带出海提供了可能性。(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7、335、3751页。
同时,《史记》中生动具体的叙述也有利于徐福传说的流传。此后陆续成书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都对徐福传说有所提及,大多基于《史记》加以补充或发展。其中,《三国志·吴主传》中卫温等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且“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5)《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36页。等叙述明确指出了徐福之所在是“亶洲”。《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叙述也与之类似,并且由于倭国(日本)条恰好位于该叙述前,(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2页。也有学者视其为徐福传说与日本产生关联的起点。(7)李岩:《三神山及徐福东渡传说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77-84页。当然,严绍璗等学者已经指出,据《括地志》《史记正义》等文献记述,徐福止居之地直至唐朝时仍普遍被认为是神山所在的亶洲。(8)严绍璗:《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第116页。不过,三神山的位置却始终没有脱离日本所在的东海之外,甚至可以说“止居日本”说已经呼之欲出。
目前所见,五代后周僧人义楚所著《义楚六帖》中首次出现了关于“止居日本”说的叙述:其《国城州市部》日本条中有“(日本)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以及“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等。(9)[五代]义楚撰:《义楚六帖》,京都:朋友书店,1979年,第459页。义楚本人并未去过日本,他的叙述大多来自“日本国传瑜伽大教弘顺大师赐紫宽辅”的讲述。由此可以推断,其记述的“止居日本”说很有可能是徐福传说传至日本,并在当地衍生出蓬莱即富士、秦氏(大陆移民后裔)即徐福子孙等变体后,随着唐宋时期入华的日本人又回传至中国。
由此可见,隋唐五代时期活跃且深入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汉文典籍和文化、历史认知等内容,通过中日之间人员流动(遣唐使、僧侣、商人、移民等)而实现的广泛传播,为徐福传说的流传和演变,特别是“止居日本”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外,各方面频繁的交流还进一步推动了徐福传说在中日双方相互认识方面,特别是历史与文化认识方面的影响。《日本刀歌》一诗正是作者在见到由“越贾”舶来之日本国“宝刀”后,结合徐福传说抒发感受的作品。日本受徐福传说影响,自11世纪起出现徐福止居熊野(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的传说,随后建立熊野徐福祠;(10)吴伟明:《徐福东渡传说在德川思想史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期,2014年,第163页。南宋灭国后流亡日本的禅僧无学祖元(1226-1286)参访熊野徐福祠,也以自身境遇结合徐福传说感慨“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11)[南宋]无学祖元:《献香于纪州熊野灵祠》,新宫市编:《新宫市志》别册,新宫:新宫市役所,1937年,第1263页。室町时期,日本禅僧绝海中津(1336-1404)还在入明时与朱元璋以熊野徐福祠为题作诗唱和。(12)[日]绝海中津:《蕉坚藁》,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和6-79号。换言之,加入“止居日本”内容的徐福传说成为中日双方共通的历史文化脉络,在中日交流中既是感怀历史源流的契机,又是打开交流的有效话题。
另外,随着日本成为公认的徐福止居之地,传说也在徐福以求仙采药为名诈得童男女、百工谷种等早期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了“逸书百篇”的新变化,创造这一变化的正是知名的《日本刀歌》: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长诗以称赞日本刀为起点,重点叙述了日本的历史风俗特别是徐福传说。诗中对日本的认知虽主要基于前代著述或坊间传闻,但也不乏“至今器玩皆精巧”式见闻实感,“令严不许传中国”式主观臆断,无疑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理解与想象。特别是“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如此“逸书百篇”说未见于此前文献,应为作者综合既有传说中的徐福渡海之年代、所携物品之丰富程度,以及止居之地日本“士人往往工词藻”之文化程度而自我想象的创造性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本诗作者有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两种观点,前者在近代以前较为普遍,后者则自清末起为学者所重视。学者金程宇基于诗文流传和文献收录等根据支持后者,并指出司马光曾任职于北宋藏书机构“秘阁”的经历,以及五代以来高丽和日本的献书等“佚书回流”趋势,是其关注并提出“逸书百篇”问题的必要前提。(13)金程宇:《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刀歌〉》,《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第155-156页。可以推断,诗中想象徐福赍书日本,不仅出于当时中日交流的日趋频繁及其所引发的“止居日本”说带来的影响,而且与北宋以来中国文人阶层的“礼失求诸野”认识密切相关。
至此,徐福传说的两个衍生内容“止居日本”和“逸书百篇”基本形成,后者的出现则意味着“徐福逸书存于日本”说的成立。虽然仅就现存史料而言,我们很难确认《日本刀歌》就是该说的最早源头,不过大文豪司马氏或是欧阳氏所作之诗,无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该说的流传。至日本南北朝时期(1336-1392),南朝重臣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1339年)云:
(孝灵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之始皇即位,此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药于日本,日本则求五帝三王之遗书于彼国,始皇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因彼国烧书坑儒,故孔子全经遂存于日本,此事载于异朝之书。(14)[日]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卷二,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和16-139号。
这段内容虽未提及徐福,所述始皇求药于日本并送以“五帝三王之遗书”等情节也有别于前述传说,但核心内容“始皇求仙”无疑出自徐福传说,“孔子全经遂存于日本”则显然是“逸书百篇”说的翻版。由此可见,经《日本刀歌》改造的“徐福逸书于日本”说已逐渐成为中日两国乃至东亚世界的共同认识。
二、近世日朝交涉中关于“徐福逸书”的讨论与思考
正如《神皇正统记》中该纪事被纳入关于早期日本历史的叙述那样,改造后的徐福传说从中国古代史传说,演变为事关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交流的共同传说,甚至成为东亚日本史认识的一部分。元朝周致中著《异域志》认为日本“乃秦始皇时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且“中国诗书遂留于此,故其人多尚作诗写字”。(15)[元]周致中:《异域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周氏此论基本承袭并扩展了《日本刀歌》的日本史认识,又对如编纂《刘氏鸿书》的晚明刘仲达等后世文人有很大影响——考虑到18世纪晚期日本儒者松下见林在《异称日本传》中也引述《刘氏鸿书》所收“日本之学始于徐福”等内容,(16)[日]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リ-05-02260号。可见如此略显荒诞的日本史认识已在东亚世界中广泛流传。
该认识在朝鲜半岛也有影响。曾出使中国与日本的李朝初期重臣申叔舟(1417-1475)著《海东诸国记·日本国纪》中,就有“(孝灵)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州居焉”和“(崇神天皇时)熊野权现神始现,徐福死而为神,国人至今祭之”等内容。(17)[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一,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19-20页。申氏不仅采用了与《神皇正统记》相近的立场并将徐福纳入日本历史,而且进一步注明其来日时间为孝灵天皇七十二年,使这一认识得以流传后世。江户幕府修纂的史籍《本朝通鉴》中也有“七十二年秦人徐福率童女千人,斋先王坟典,以来游,求仙药,遂留不归”(18)[日]林鹅峰等编:《本朝通鉴》一,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和32369号。等叙述,可见日朝文人都已认同徐福“止居日本”说,并将之视为日本史之事件。
不过,对《日本刀歌》提出的“逸书百篇”存日说,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日朝文人间却并未形成统一见解。主持编修《本朝通鉴》初稿《本朝编年录》的江户初期大儒林道春(号罗山),就在编修过程中对“徐福来日”做出过以下批注:(19)[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658页。
发明秦政二十八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三十五年,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世传徐福赍来经书,皆孔氏之全书也。福之来日本,在烧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韦漆竹牒,时人知者鲜矣。其后世世兵燹,纷乱失坠,未闻其传。呜呼哀哉,读书好古之人于是乎未尝泪之不下也。
林罗山本人对徐福传说十分关注,曾多次提及并考证传说内容,甚至在歌颂日本国史人文的《倭赋》中称“彼徐福之求药兮,遂羽化而登仙”,(20)[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4页。还曾直言“(日本刀)其名远传,称于中华,故欧阳公、唐荆川等赋《日本刀歌》以赞之”,(21)[日]林罗山:《相刀目录序》,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575页。可见其不仅熟悉包括《日本刀歌》在内的徐福传说相关文献,并对“逸书存日”等内容持相当确信的态度。
李朝仁祖时期(1623-1649),文臣张维则对逸书问题持质疑立场。在《溪谷先生集》中,张氏指出“世人多言日本有全经,未经秦火者,盖徐福入海时所带去也”的说法“甚无据,而考其原,盖出于欧阳公也”,并根据《史记》中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徐福再度诈秦的记述认为徐福未必渡海赴日,又以徐福的方士兼逃亡者身份质疑其“岂能眷眷于六经者耶”,更臆测日本若存逸书“将夸衔之不暇,何至讳藏乃尔”,并最终断定“此殆好事者俑其说”。(22)[朝]张维:《溪谷先生文集》,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562页。恐怕,张氏等质疑派虽然难以完全否定“欧阳公”即《日本刀歌》的观点,却并不真正认可在吸收、理解中华文化上差于朝鲜的日本竟会存有孔子“全经”的可能。但毕竟海陆相隔且传说日久,在有据传欧阳修所作之名诗作证又缺乏明确反证的情况下,“逸书存日”说确实难以被彻底否定。这无疑刺激了朝鲜方面对该问题的关注与探究,而随着17世纪以降日朝外交的正常化,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成为双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话题之一。
1592-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侵略朝鲜,造成了中日国交的彻底断绝与日朝交往的一度中断,直到德川家康凭借关原之战(1600年)夺取天下后,在对马岛主宗义智的多次交涉乃至军事威胁下,朝鲜才被迫于1607年遣使造访德川幕府并恢复日朝国交。包括“回答兼刷还使”的前三次遣使,以及正式定名“通信使”的9次出访在内,朝鲜共向德川幕府派遣正式使团12次。使团以正使、副使、从事官三人(三使)为首,由译官、从事等相关人员构成,由釜山出发、经对马岛登陆本州并前往江户,在拜谒将军、交换国书、参加招待飨宴等活动之后返回,行使途中还会参加与日方儒者、禅僧、好文武士的笔谈交流。
韩国学者李元植指出,在欢迎飨宴和唱酬之时,徐福和据传将儒教带至日本的百济王仁经常成为双方讨论的热门话题。(23)[韩]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研究》,京都:思文阁出版,1997年,第115-116页。葛兆光和金程宇等学者也曾提及江户后期的朝鲜使节曾向日方追问徐福赍书之事,金程宇还推测这与追求文化正统的东亚意识有关。(24)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62+389-390页。不止如此,仅从通信使记录中便可确认,在12次使团访日中,朝方至少曾5次追问逸书存日与否之事。考虑到这些记录会被之后的赴日使节参考,则如此频繁的追问就更能说明朝方对逸书问题的关注了。
追问在1607年第一次朝鲜回答兼刷使时就已经开始。时任副使庆暹在《海槎录》六月初十日条中记录了如下内容:
晴,留江户。送书于学校处,问徐巿入来时,必赍全经而来,愿一见之,且徐巿庙在何地方耶。学校所答模糊,语不分明。更问于玄苏,玄苏答曰:“全经在于徐巿庙,皆蝌蚪书也。退计三百年间,徐庙为兵火所烧。基在纪伊州熊野山云”。(25)[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二,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48-49页。
庆暹首先肯定徐巿(即徐福)逸书的存在,然后向足利学校庠主三好元佶(1548-1612)求见逸书并问徐福庙之所在,元佶却“所答模糊,语不分明”;另问于专司幕府外交事务的景辙玄苏(1537-1611),回答则是“全经在于徐巿庙,皆蝌蚪书”,且徐庙早已毁于“兵火”。玄苏的回答先以蝌蚪文为由暗示全经难以抄传,再以战乱烧毁表明原本已不可考,巧妙地回避了对于徐福逸书说真伪的判断。
朝方显然并不满意上述回答。1624年第三次回答兼刷还使访日,副使姜弘重在《东槎录》十月二十八日条中记录了如下内容:
午,玄方来见叙话,仍问徐福祠在何处。答曰:“在南海道纪伊州熊野山下,居人至今崇奉,不绝香火。其子孙亦在其地,皆称秦氏云。熊野山一名金峰山云”。又问,徐福之来在秦火之前,故六经全书在于日本云,然耶?答曰:“日本素无文献,未之闻也。其时设或有,日本好战,翻覆甚数,兵火之惨,甚于秦火,岂能保有至今耶”。(26)[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二,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256页。
姜氏在与玄苏门人、对马外交事务负责人规伯玄方(1588-1661)的对谈中,再次追问徐福祠及逸书。关于徐福落脚熊野和后世称秦等传闻,玄方的回答与玄苏无异,不过对逸书存日说却痛快地表示自己闻所未闻,并认为即便有六经传来也必毁于兵火而难以保有至今。玄方的否定见解未必有明确依据,但至少向朝方做出了逸书并不存日的确切回答。
此后,虽然徐福传说在唱酬和诗中被时常提及,(27)比如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第六次朝鲜通信使从事官南龙翼所著《扶桑录》九月初五条中,有“熊野在南四十里,即纪伊州之地,而徐福到此山居焉,山下有墓,子孙皆姓秦氏”之叙述([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三,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20页)。逸书问题却长期不再现于记录之中。直到1711年第八次朝鲜使团造访日本,此时正值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治世。深受将军信赖、参与主持内政外交事务的儒者新井白石(1657-172),于当年即正德元年(日本年号)十一月五日在江户与朝鲜使团成员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的笔谈,副使任守干在《东槎日记》附《江关笔谈》中详细地记载了交流详情。关于逸书问题的讨论被记载如下:
南冈问曰:“贵邦先秦书籍独全之说,曾于六一绣刀歌见之矣,至今犹或有一二流传者耶?”白石曰:“本邦出云州有大神社,俗谓之大社。社中有竹简漆书者数百庄,即古文尚书。”青坪曰:“其书想必以蝌蚪书之,能有鲜之者,而亦有誊传之本耶?”白石曰:“本邦之俗以秘为要,况神庙之藏俗间不得传写。”可恨。平泉曰:“或传熊野山徐福庙有蝌蚪书古文,厄于火而不传云,此言信否?”白石曰:“此乃俗人诬说。”青坪曰:“有书不传,与无书同,若有此古书,则当与天下共之。深藏神庙,意甚无谓,何不建白于朝,誊传一本耶?”白石曰:“殿下亦知其俗。虽然,不悖其情,乃是仁厚之德。”平泉曰:“蔡中郎之秘论谢本不是美事,崇神鬼神又近于楚越之俗,有书不见与无书有何异。”白石曰:故不佞谓之俗,如何如何。”又曰:“尾张州热田宫,诸公所经历也。此宫中亦有竹简漆书二三策,盖蝌蚪文字。”南冈曰:“归时可能得见否?”白石曰:“既为秘文,何得见之。”(28)[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海行总载续编(重印版)》九,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76页。
此段笔谈堪称针锋相对,对于朝鲜使节的反复追问,白石的回答始终出乎意料:不仅竹简漆书之古文《尚书》藏于出云大神社,而且神社私藏概不示人,就连熊野徐福庙藏书都是“俗人诬说”。另外,朝鲜使节故意提到蝌蚪文和熊野藏书说,可见对此前庆暹和姜弘重等人的问答了如指掌,那么此番发问就并非意在追求真相,而是想借白石之口否认逸书说。反观白石之说,虽与玄苏焚毁说一样无法证实或证伪,却暗合《日本刀歌》中“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一句,不由得朝鲜使节心生动摇,直呼“可恨”。
当然,该回答显然不会被朝方接受。1719年第九次朝鲜使节访日,制述官申维翰在与对马藩儒者雨森芳洲(1668-1755)的笔谈中再次提起徐福逸书。申氏在《海游录》中记录了如下内容:
问纪伊州有徐巿冢徐福祠,福等之入海在秦皇燔书之前,故世传日本有古文真本云云,至今数千年,其书不出于天下,何也。东曰:“此说悠悠,欧阳子亦有所言,然皆不近理。夫圣贤经传,自是天地间至宝,神鬼之所不能秘。故古文《尚书》或出于鲁壁,或见于大杭头。日本虽远在海中,自有不得不出之理。日本人心好夸耀,若有先圣遗籍独藏于此,而可做千万世奇货,则虽别立邦禁,当不能遏其转卖,况初非设禁者乎。”(29)[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一,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18页。
申氏再次问起“古文真本”存日而不传于世之说,雨森芳洲表示此说虽源自“欧阳子”所言却“皆不近理”,并从诸多方面明确否定了逸书存日的可能性。不过,这未必就是雨森芳洲本人的真实观点。彼时,试图强化日本(德川幕府)外交地位的新井白石已经下野,对马藩则需要垄断对朝贸易、把持对朝外交特权以稳定自身统治和收入。因此,雨森芳洲的回答看似公允,却不免有迎合朝鲜使节之嫌。此外,申氏在该段记录后又论及徐福传说的另一问题,即世传“福之子孙至今为倭皇,五百童男女各为氏族,始有倭国”之说“乃无稽之言”,(30)[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一,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18-319页。或是其与雨森芳洲交流之后得出的结论。与前次笔谈的针锋相对不同,此番围绕徐福传说的交涉无疑融洽且客观得多。
朝鲜使节关注逸书的最晚记载,出现在1764年第11次通信使访日时。据李朝后期文臣李德懋著《青庄馆全书·蜻蛉国志》中所引使团书记元重举的记录可知,元氏在与福冈藩儒龟井南冥等人的笔谈中曾问起“古文六经徐福赍来否”,龟井言道:“仆亦见欧阳公《日本刀歌》,然本国无此事”,并认为若有古经则“必无不泄之理”。(31)[朝]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78年,第166页。金程宇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刀歌〉》中提到元重举著《和国志》中也有相同记载,惜未见其书。不过,同样参加笔谈的长州儒者泷长恺,却在赠与书记成大中(号龙渊)的《赤马关宾馆赠龙渊》一诗中提到“国风难和王仁咏,秦火独余徐福篇”,(32)[日]泷长恺:《鹤台先生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ヘ-16-00650号。可见日方对逸书存日说的真伪或许并未有一致结论。
围绕徐福是否携逸书赴日、古文全经是否留存于世的讨论,几乎贯穿了近世日朝外交的整个过程之中。朝方频频追问,日方的回答则变化不定。从这些关于“徐福逸书”的讨论与思考中,既能看出双方对逸书或者说古文全经所代表之东亚文化正统的竞争,也可以看出《日本刀歌》的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而这些追求或影响本质上都源于近世日朝关系中并不在场的中国。
三、“徐福逸书”讨论背后的近世东亚政治文化语境
不难看出,朝鲜使节对于徐福逸书的追究中,有着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基本信任,以至于他们不愿也不敢直接否定《日本刀歌》的观点。另外,对于逸书的反复追问,同样说明朝方对古经存日说的质疑多于相信,这种异乎寻常的执着追问与通信使访日这一外交行为相结合,则折射出其背后深刻的政治文化因素。
朝鲜在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受害深重,却又在德川幕府的武力胁迫下被迫恢复国交,甚至无奈默许对马藩在朝方提出的复交条件上公然造假。(33)[日]荒木和宪:《“壬辰战争”的讲和交涉》,《关口全球研究会研究报告》第86期,2019年,第54-74页。朝鲜使团成员在出访日本时带有愤懑甚至敌对态度,恐怕正是缘于上述政治因素。直到1636年第四次朝鲜使团(第一次通信使)访日时,尚有副使金世濂(号东溟)作《大坂诗其二》曰:
彼岸诚乐土,古称神仙室。六鳌岂诞传,三山此其一。仲雍或东入,徐巿来何日。习俗类西秦,富者多侈佚。与我接邻好,壤地亦已密。冠盖共修聘,封疆各息卒。奈何不自量,一朝成蚌鹬。万代不共天,所仇惟秀吉。(34)[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三,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25页。
金氏一方面称赞日本因吴泰伯和徐福之来而“习俗类西秦,富者多侈佚”,另一方面则痛斥其不自量力,以至于两国“一朝成蚌鹬”甚至“万代不共天”,并将罪魁归于丰臣秀吉一人,这恐怕代表了朝鲜使节的普遍心态。
葛兆光认为,以精通儒学和诗文的两班士大夫为主的朝鲜使团始终抱有“维护自家尊严和进行文化比赛的心理”,习惯于对日本学问无端傲慢、对日本学者居高临下。(35)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41-43页。而除了切实存在的文化差距外,朝鲜使团秉持如此“自大”态度也与丰臣秀吉侵略、日朝复交过程中的屈辱经历直接相关。同时,主动寻求复交的德川幕府,其实也没有真正摆脱侵略战争带来的影响。《海槎录》中就曾记载,1607年第一次朝鲜使团途经京都时,长期负责政权外交事务的西笑承兑曾提出“朝鲜使臣非有益于日本,不过探兵机、审形势而来也”并主张“待之以薄”,因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以“主客之礼,不可凉薄,大非将军之意也”为由反对方才作罢。(36)[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二,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0-31页。
德川幕府虽对朝鲜使团礼遇有加,却从未在争议问题上有所妥协,甚至会看似无意地使朝方难堪。第二次朝鲜使团副使李景稷在《扶桑录》中记录,将军德川秀忠在元和三年(1617年)八月二十六日于京都接收朝方国书之后,特意安排使团前往京都大佛寺参观并设宴于寺中。然而,该寺正是供养丰臣一族亡灵之所,寺前还建有收埋朝鲜战俘耳鼻的“耳塚”。李氏得知耳塚之事后“不胜痛骨”,深感“拜此仇贼,初非不知;到此屈膝,心胆欲裂”,使团众同僚更是“相对泪下,不胜慷慨愤惋”。(37)[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三,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150-151页。讽刺的是,让朝方感到如此屈辱的大佛寺观览竟成此后朝鲜使团访日途中的必备内容,直至第十次使团来访时才被彻底取消。(38)[日]仲尾宏:《朝鲜通信使与“耳塚”:江户时代的“耳塚”观与壬辰、丁酉战乱》,[韩]金洪圭编:《秀吉、耳塚、四百年》,东京:雄山阁,1998年,第104-109页;[韩]鲁成焕:《如何思考耳塚的“灵魂”》,《日文研论坛》第268期,2013年,第1-76页。
德川幕府一方面推动日朝复交,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触怒朝方以炫耀武功,足见武力胁迫朝鲜复交之影响在其对朝外交政策中的残留。面对日方的侮辱行为,朝鲜使节在政治上除了抗议和愤怒之外几乎无能为力。那么,他们在文化上频繁地贬低甚至蔑视日方的做法,或许就不仅是简单的文化竞争,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报复心态和政治意图了。在仇恨和报复心态之外,文化上更接近正统的优势地位也让朝鲜使节对“徐福逸书”的怀疑还附带了一定的民族主义式的自大。比如,第11次朝鲜使团正使赵曮就在途经富士山时,在《海槎日记》二月九日条中记述道:
如求延寿之灵药,必无过于人参一种耳。我国既是产参之乡,济州之汉拏、高城之金刚、南原之智异世称三神山,此言亦未必信矣。虽然,如使徐巿欲求灵药,则岂必舍朝鲜多产参之地,往日本不产参之邦乎。吾则尝以此谓三山不在于日本,灵药不产于日本,徐巿不到于日本。此行后闻文士辈之言,则与此处稍有知识者相为笔谈之际,问徐巿庙有无,则答以熊野山虽有所谓徐福庙,而此是妄言,徐巿初无到日本之事云。如果真有,则以日本诞妄之习,岂不夸张而敷演也,于此益可验其齐东野人之说不可信也。(39)[日]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海行总载》四,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235页。
赵氏由富士山想到海中三神山与徐福传说,并以求灵药无过于人参、求人参则应往朝鲜而非日本为依据,质疑徐福来日说为“齐东野人”之语,甚至暗示朝鲜也有三神山,徐福恐是求人参于朝鲜。如此臆测无疑说明赵氏对本国历史与风土怀有强烈的自大心理,其对徐福来日和三神山在日等传说内容以及日本“诞妄之习”先入为主的否定,或许也是这种心理的侧面体现。
另一方面,日方对于逸书问题同样关注。大儒林罗山参与了1624年至1655年之间4次朝鲜使节来访接待,并与使团成员进行过笔谈和诗会。史料中并未留下双方讨论徐福逸书说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没有发生过。其《示恕靖问条》一书以选取重要话题设问于林恕、林靖二子,其中就有以“箕子国聘礼使”口吻提出的“逸书”之问:
仄闻徐福来日本时,赍先秦之书以往,故欧阳修咏日本刀诗有云:“徐福往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犹存。”想夫其科斗篆字之典谟训诰,并诸经传亦有之乎,使臣幸观国光,所望请者,许一窥其古书……(40)[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409页。
该问与前述庆暹的请求如出一辙,可见作为幕府外交事务负责人之一的林罗山也极有可能被朝鲜使节提出过相似请求。此外,“箕子国聘礼使”之称同样寓意颇深。众所周知,吴泰伯渡日和箕子奔朝乃是显扬日朝两国与中华历史正统之关联的重要传说,历来为东亚文人阶层所关注。林罗山刻意强调箕子,恐怕正是为了提醒二子日朝双方文化传统中的中华文化背景。实际上,林罗山以中华正统观处理对朝问题并非纸上谈兵。1636年第四次朝鲜使团来访时,他就在写给朝鲜三使的信中,指出箕子传说“中华群书未之见也,欲知其所据”,并因“檀君神话”不载于“中华历代之史”而斥之为“齐东野人之语”。(41)[日]林罗山:《寄朝鲜国三官使》,[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156页。考虑到徐福和逸书说皆源自中国文献,则林罗山在“逸书”之问中称朝鲜为箕子国,也就绝非无意之举了。
韩国学者郑英实指出,林罗山曾在与朝鲜使节交流过程的诸多方面尽力维护日方尊严。(42)[韩]郑英实:《朝鲜通信使与林家》,《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13年第6期,第237-255页。可见,林罗山关于逸书问题和箕子传说的“预演”式思考及挑衅性论断,显然受制于近世日朝外交这一特殊语境。其行为与其说是文化上的竞赛,不如说是以文化交流为形式进行的和平政治对抗,徐福传说背后的中华正统思想则是对抗的理论前提和潜在动因。
相比之下,同样代表幕府官方立场的新井白石,在日朝交流中的政治意图则更加直接。新井白石不仅立场鲜明地拥护逸书尚存说,还曾大幅简化朝鲜使节的招待礼仪,改国书中德川将军称号为“日本国王”,致使朝方正使赵泰亿抗议其“辱国”。(43)[韩]李元植:《新井白石与朝鲜通信使:〈白石诗章〉序跋为中心》,《日本思想史》1995年第4期,第19-33页。持如此近乎于国家主义立场的新井白石,对于逸书说的坚持更像是在感到本国尊严遭受挑战后的激烈反抗,其政治意义显然取代了原本应有的文化交流意义。
事实上,新井白石对徐福逸书说的真实观点未必与他告知朝方的内容相一致。在其著于1705年早于前述之笔谈的《同文通考》卷二“神代文字”条中,便有如下记载:(44)原文由笔者翻译,【】内为小字插注。
又云出云大社传有以漆书文字于其上之竹简,但其文字不能读。又云尾张热田社亦传有彼物,此皆古来之传闻。又有传说,于竹简之上所书者莫非科斗之文耶。果真如此,则我国古之所用岂不与异朝往昔所用无异也。又有彼国之人传说,秦之徐福来我国时,持百篇之《尚书》而来。故有人以为,此等竹简或为百篇之《尚书》亦未可知【徐福携《尚书》来我国之说,见于宋欧阳修之外集,其后诸儒多有述及此事者】。设若彼之两神社所有之竹简,确系自神代传来之物,则必不可言我国之神代无有文字。若徐福之事见于我国之史籍,则彼国所传之说未必可信。(45)[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东京:勉诚社,1979年,第118-120页。
可知,出云大社与尾张热田神宫藏有漆书竹简之说早有流传,竹简为蝌蚪文写成之说也另有起源,皆非新井白石自创。新井白石还认为,先有中国传来之徐福赍书日本说,后才有人将百篇《尚书》附会于出云、热田竹简之上。换言之,在新井白石看来,出云及热田藏竹简之说、竹简所书文字乃蝌蚪文之说、蝌蚪文竹简乃徐福所携百篇《尚书》之说,其实是陆续形成的三种说法,而他本人虽然基本认可第一说,但对后两说却持明显怀疑态度。
新井白石作此文,意在梳理日本有无“神代文字”之争论,而传说藏于出云、热田两神社的漆书竹简若是日本固有,就会成为神代文字的重要证明;相反,蝌蚪文说将竹简变成“中国制造”,徐福逸书说更是将其全部归为中华传来。之后新井白石也提到中国人携书来日的可能,承认“竹简何以传于彼之二社,全详若不可知,则诸说概难定论”,(46)[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东京:勉诚社,1979年,第120页。但不疑二社藏简说而疑蝌蚪文和逸书之说的立场,还是反映出其试图证实神代文字、宣扬日本文化优越性乃至独立性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在字源考证上表现为认同神代文字而质疑徐福赍书,在日朝交流中则表现为支持徐福赍书以对抗朝方质疑。这种对于真相的随意,与其儒学素养或治学水平无关,而是源于其对日本在东亚世界中地位和性格的政治性思考。这种思考虽有拒斥中华文化正统性和中心地位之嫌,却也是由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脉络延伸而成。
事实上,无论是发起逸书问题讨论的朝鲜使节,还是回应朝方追问的日本儒学者,都认可古文全经(或百篇《尚书》)作为中华乃至东亚文化正统之代表的象征意义,以及该象征意义在近世日朝外交这一特殊语境中的现实意义。与之相比,是否质疑该传说的真伪、是否认同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并不真正重要。另外,中国典籍中的相关记载特别是《日本刀歌》的内容则始终是争论的关键证据,引述其主张难被反驳,质疑其内容则必须谨慎。以中国为核心延伸而成的文化脉络,在近世东亚世界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即便近世初期东亚政治格局的剧变早已深刻地重塑了日朝外交的形态。
四、结语
对于徐福传说流传过程及其在近世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而言,围绕该传说所展开的文化交流本身就起到了塑造内容和引发思考等决定性作用,创造出徐福传说及《日本刀歌》的中华文化则不仅是徐福传说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还构成了近世逸书问题讨论的潜在动因。同时也必须承认,近世日朝外交中对于该问题的反复讨论和思考并非单纯的文化交流,双方融洽或是对抗的表现有着鲜明的外交意图和政治内涵,其直接动因则是丰臣秀吉侵略战争以降东亚政治格局的剧变特别是日朝之间的军事和外交纠葛。
然而,由中华文化延伸而出的东亚文化脉络,毕竟为徐福传说提供了自古代至近世、自中国至朝鲜、日本的流传路径,也的确构成了近世日朝外交语境下双方的交流以及交锋的前提和基础。这样一种在中华文化的巨大向心力之下,由文化交流之下活跃和多元的相互作用所造就的、连接东亚世界整体的文化脉络,不仅在形成和讨论徐福逸书等共通性话题时被东亚各国天然接受并主动利用,还构成了东亚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并最终推动了“东亚文化共同体”内部构成和整体认知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