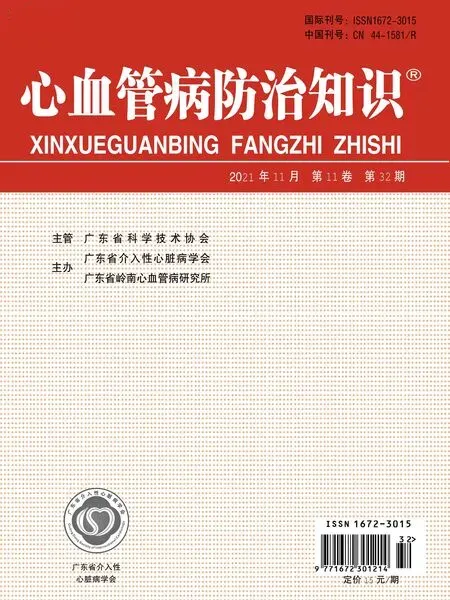药物降糖治疗与心血管获益
李明敏 谭 虹 陈纪言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080)
冠心病合并糖代谢异常/糖尿病的比例在我国及欧美国家都居高不下,据流行病学调查,约1/4-1/2因冠心病入院的患者合并糖尿病。荟萃分析显示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使冠心病的患病风险增加1倍[1]。此外,大型的队列研究显示糖化血红蛋白每增加1%,心衰发生风险增加15%-30%,且独立于其他风险因素[2]。因此,心血管医生尤其关注糖尿病的诊治,迫切希望了解:(1)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的目标是什么?(2)降糖治疗能否改善心血管预后?(3)何种降糖药物对合并冠心病的患者最适合?
上世纪完成的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DCCT)研究和UKPDS研究建立了血糖控制水平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预后的联系[3-4]。研究结果一致显示严格的血糖控制可以降低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并延缓微血管并发症的发展进程。研究的后续分析显示,作为反映平均血糖控制水平的糖化血红蛋白,与微血管并发症之间的关联性最好,从而确立了糖化血红蛋白作为临床试验中反映血糖控制水平的实验室替代指标的地位。
然而,代表平均血糖控制水平的糖化血红蛋白,与大血管并发症,尤其是心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并不明确。本文旨在简述血糖控制水平及降糖药物与心血管结局的相关性,希望给关注糖尿病的心血管医生一些降糖策略的建议,并引发相关领域基础或临床研究的一些思考。
1 血糖控制目标与心血管获益
借鉴血糖控制水平与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本世纪初一批研究血糖控制水平与心血管事件预后的临床试验逐一公布结果,这些临床试验共同点都是探索能改善心血管预后的血糖控制目标,因此也被称为达标治疗(Trial-to-Target)。其中,最为代表性的研究包括ACCORD、ADVANCE和VADT。ACCORD研究纳入10251例平均糖尿病病程10年的2型糖尿病患者,35%的患者入组前有明确的心血管事件[5]。该研究根据血糖控制目标不同分为标准治疗组和严格降糖组,两组在治疗结束时达到的中位糖化血红蛋白分别是7.5%和6.4%,研究的主要终点是首次出现非致死性心梗、卒中和心血管死亡的复合终点。意外的是ACCORD研究在随访到3.5年的时候,由于严格降糖组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标准治疗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2%和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提前终止试验。两组之间在研究终止时严格降糖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尤其是低血糖风险也明显高于标准治疗组。一些事后分析试图找到严格降糖组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但并没有发现确切的答案,也并不能将死亡率的增加完全归咎于严格降糖组的高低血糖发生率。同期公布结果的ADVANCE研究[6],纳入患者与ACCORD类似,严格降糖组和标准治疗组达到的中位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6.4%和7.0%。不同的是,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是包含了微血管并发症在内的复合终点。研究平均随访5年,严格降糖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下降了10%(P=0.01),但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大血管并发症风险并无明显下降。另一项美国退伍军人研究VADT纳入1791例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病程11.5年,其中40.7%合并心血管疾病[7]。严格降糖组和标准治疗组在研究结束时的中位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6.9%和8.4%,研究平均随访5.6年。主要终点事件为包含心梗、卒中、心血管死亡、新发或恶化的心衰、外周血管疾病、截肢等在内的复合终点,研究结束时两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而严格降糖组的低血糖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延长随访至11.8年时发现[8],严格降糖组和标准治疗组的糖化血红蛋白差异已经消失,严格降糖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下降了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然而两组的全因/心血管死亡风险并无显著差异。
从糖尿病发病之初到出现临床意义上的动脉粥样硬化,一般需要10-15年。不难发现,上述三个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纳入的糖尿病患者平均病程几乎都在10年以上,其中约1/3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出现心血管并发症,这时候的严格降糖治疗称之为“晚期干预”。如上所述,晚期干预的达标治疗研究并没有获得与微血管并发症研究相似的结果,即并没有发现严格降糖治疗(糖化血红蛋白<7%)能带来明确的心血管获益,反而在ACCORD研究中得出了严格降糖治疗可能增加死亡风险的意外结果。
那么,早期干预血糖的达标治疗研究结果如何呢?上世纪末开始的UKPDS 33研究[4],纳入了3867例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严格降糖组和标准治疗组的中位糖化血红蛋白分别是7.0%和7.9%,初始研究在平均随访11.1年时终止,两组在全因死亡、致死性心梗等大血管并发症风险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延长随访至16.8年时[9],由于缺乏标准化/严格降糖治疗,两组的糖化血红蛋白均明显升高,分别为7.9%和8.5%。然而,既往严格降糖组的全因死亡率、心梗发生风险比标准治疗组明显下降13%和15%。这种降糖治疗带来的延迟获益被称为“代谢记忆”,其病生理机制并不明确,但是给研究者一个重要提示:严格血糖控制的时间窗对能否改善心血管获益非常关键。换言之,在糖尿病病程早期给与严格降糖治疗,可能在10余年后观察到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谢记忆需要经过足够长的随访时间才可能观察到。
综上所述,在既往的降糖治疗时代,大量的达标治疗试验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果,即并没有找到能够改善心血管获益的确切的血糖控制目标。但是,这些临床研究也提示我们就心血管结局而言,合适的血糖控制目标可能是个体化的,跟糖尿病病程、有无心血管合并症、预期寿命,甚至低血糖发生风险等相关。因此,在最新的欧美糖尿病指南中,关于降糖目标的建议也不尽相同,共同点是推荐制定个体化的降糖目标[10-12]。对于一般患者,建议将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7%以下,对于既往有严重低血糖事件、合并心血管并发症、预期寿命不长的患者,建议适当放宽血糖控制(糖化血红蛋白维持在7%-8%)。当然,血糖控制目标不仅包含了以糖化血红蛋白为代表的平均血糖控制水平,也包含空腹、餐后血糖目标以及血糖的波动性。因此,作为心血管医生,除了关注平均血糖水平,也要注意血糖的波动范围,尤其要警惕严重低血糖事件。前瞻性的队列研究显示,严重低血糖与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相关(HR 1.64,95%CI 1.15-2.34)[13]。
2 新时代降糖药物与心血管获益
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尤其是罗格列酮上市后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报告,荟萃分析[14]显示该类药物可能会增加心肌梗死、心衰以及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因此2008年FDA警告在使用罗格列酮降糖治疗时要警惕潜在的心血管风险,同时强制要求以后研发的降糖药物在上市前要证明药物的心血管安全性。得益于该规定的实施,10年来新上市的降糖药物对心血管疾病预后影响的临床研究逐一公布结果,我们才得以对降糖治疗与心血管预后的相关性有进一步的了解。最近10余年新上市的降糖药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三小类。两大类指肠促胰素类药物和钠葡萄糖同向转运体(SGLT-2)抑制剂,其中肠促胰素类药物又可分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和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两小类。DPP-4抑制剂最先面市,它抑制作为GLP-1裂解酶的DPP-4的活性,延长循环中生物活性形式的GLP-1的作用时间。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种DPP-4抑制剂在心血管结局试验中显示出心血管保护作用,相反,沙格列汀在一些研究中被发现可能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15]。而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在心血管结局试验中却意外地表现出不同的心血管获益。
GLP-1是一种脑肠肽,由回肠上皮内分泌细胞L在人体进食后分泌入血,其生理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胰岛素分泌,发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降糖作用;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同时GLP-1的受体表达广泛,除了主要在胰岛细胞中表达外,还在肺、肾、中枢神经系统、心脏、血管等组织中广泛表达。受体的广泛表达也意味着GLP-1发挥的生理作用的多样性,有研究显示GLP-1除了调节血糖,还具有降脂、抗炎和心血管和神经保护等作用[16-17]。GLP-1的生物活性形式在循环中的半衰期很短,约2min,很快被DPP-4降解。因此,增强GLP-1的降糖作用成为糖尿病药物治疗的重要靶点。迄今为止,陆续有多个GLP-1受体激动剂上市,包括短效的利西那肽、艾塞那肽、利拉鲁肽,以及长效的艾塞那肽微球、索马鲁肽、阿必鲁肽和度拉鲁肽。这些药物的心血管结局试验结果也逐一公布。其中,艾塞那肽和利西那肽对心血管结局事件(包含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梗和卒中的复合终点)的作用不劣于安慰剂,而其他受体激动剂均显示出优于安慰剂的心血管保护作用[18]。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GLP-1受体激动剂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不尽相同。例如,LEADER研究纳入9340例2型糖尿病患者,入组前基线糖化血红蛋白≥7%,合并明确的心血管疾病或慢性肾病,或存在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19]。平均3.8年的随访后发现,利拉鲁肽组患者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较安慰剂组下降13%;分析次级终点时发现,利拉鲁肽组的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率较安慰剂组分别下降22%和15%,但在非致死性心梗、卒中和因心衰入院风险上相比安慰剂组并无明显差异。类似的SUSTAIN-6研究显示索马鲁肽较安慰剂组心血管结局事件发生风险下降26%,而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索马鲁肽使非致死性卒中的发生风险下降39%[20]。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纳入的糖尿病患者中超过2/3合并明确的心血管疾病,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晚期干预”范畴,但心血管结局试验却在平均不到5年的随访期内获得心血管获益的阳性结果,大大出乎研究者及临床医生的预料。为了拓展药物的适应人群,也就是扩大到心血管风险低危的糖尿病人群,REWIND研究纳入了9901名2型糖尿病患者,其中约70%患者是没有心血管事件/疾病的低风险糖尿病患者[21]。该研究结果显示度拉鲁肽组的心血管事件风险下降12%,优于安慰剂组。在次级终点上,度拉鲁肽组的非致死性卒中风险下降了24%,而心血管死亡和非致死性心梗风险较安慰剂组无显著差异。GLP-1受体激动剂在短期内显示出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大大激发了研究者对潜在生理机制的探索兴趣。荟萃分析显示GLP-1受体激动剂除了降糖作用以外,还显示出降压、减轻体重以及血脂调节的作用,而这些也恰好是传统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16]。因此,有研究者认为GLP-1受体激动剂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其中部分源自对传统心血管风险因素的调节。
SGLT是一种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共有6种亚型,SGLT-1主要在肠上皮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表达,而SGLT-2主要在肾小管上皮中表达[22-23]。肾小球滤过的葡萄糖在肾近曲小管被重吸收,正常情况下不随尿液排出。只有当血葡萄糖浓度超过肾糖域(160-180mg/dL),葡萄糖的重吸收饱和,多余的糖才以尿糖形式排出体外。其中,约90%的葡萄糖经过SGLT-2重吸收进循环中,剩余10%的葡萄糖由SGLT-1重吸收。因此,抑制SGLT-2的重吸收葡萄糖作用可以调控血糖水平。SGLT-2抑制剂在发挥降糖作用的同时,通过渗透性利尿促进水的排出。目前上市的SGLT-2抑制剂主要有恩格列净、卡格列净和达格列净。其中恩格列净的心血管结局试验EMPA-REG最早公布结果,其明显的心血管保护作用也使该类降糖药物瞬间成为焦点。该研究纳入7020例18岁以上合并明确心血管疾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恩格列净10mg、25mg及安慰剂组,中位随访时间3.1年[24]。研究发现恩格列净组(包含10mg及25mg组)的MACE发生风险较安慰剂组下降14%,全因死亡风险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下降32%和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然而,药物组和安慰剂组在非致死性心梗、卒中风险上并无显著差异,分析提示恩格列净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得益因心衰入院风险的下降(较安慰剂组下降35%)。类似的结果在卡格列净中再次观察到。为了排除研究中药物治疗组和安慰剂组血糖差异对MACE发生风险的影响,EMPA-REG在后续分析时根据入组时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入组12周时糖化血红蛋白下降的程度将患者分为不同亚组,发现基线血糖水平、治疗后糖化血红蛋白下降程度并不影响恩格列净的心血管保护作用[25]。达格列净的心血管结局试验与前面两个药物不同,它纳入的患者中超过50%没有明确的心血管合并症,在类似的随访时间段内,达格列净治疗组在心血管预后方面总体不劣于安慰剂组[26]。但是,在心血管死亡和/或因心衰入院风险上,达格列净组下降17%,明显优于安慰剂组。由此可见,不同的SGLT-2抑制剂的心血管保护作用高度相似,都主要体现在降低心衰入院风险上[18]。
不论是GLP-1受体激动剂还是SGLT-2抑制剂,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合并心血管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相对短期的药物治疗却带来比较明确的心血管保护作用,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背后潜在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机制目前仍不十分清楚,有待进一步探索发现。
当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时,如何选择合适的降糖目标及降糖药物,以及降糖药物对心血管预后的影响,是心血管医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既往的降糖药物治疗时代,到新近上市的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临床研究的焦点一直围绕降糖治疗的远期获益,而非单纯的血糖控制情况。实际上,疾病不是独立存在的,在患者身上不同疾病之间相互促进发展;在制定治疗策略时临床医生需要综合考虑,而不是关注单一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