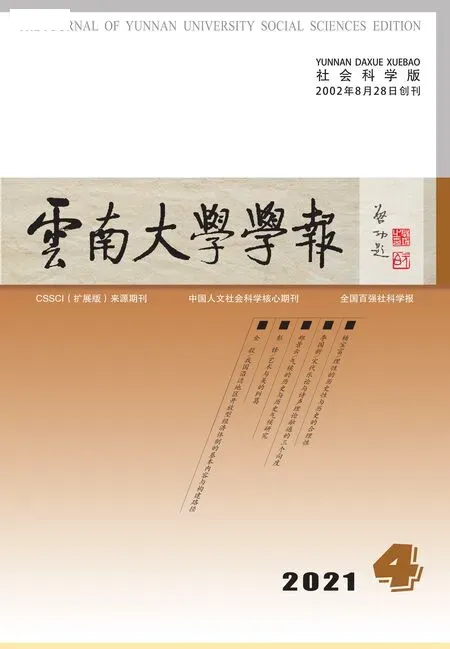实显性与视域性
——论胡塞尔《观念1》时期的突破及意义
李 磊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做出的现象学突破的意义,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第一章中声称自己用被给予性的方式调和了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两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方式,也就是从范畴直观(kategoriale Anschauung)的被给予的可能性中得出存在的被给予的可能性;第二种方式,即使得含义(Bedeutung)摆脱直观(1)[法]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1-44页。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地位以及其自身相对于直观而言的治外法权,并且进一步诉诸更为原本的延异(la différance),从而批判完全在场化的形而上学。
在《还原与给予》中,马里翁引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中的一个脚注,(2)[法]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55页。论述说“显现和显现物的相互关联”的发现比直观的扩展与含义的自主性赢得二者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借此“关联”的发现,便使得显现(Aussehen)不再仅仅被认为是对于意识主观而言的被给予物,而是被看成显现者向意识给予自身、在意识中亲身给予自身的给予方式,其次,唯有借助于这一组“关联”,《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意指与意向性充实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差异性才能得到理解。而马里翁指出这一关联对于以上两种理解《逻辑研究》的突破的方式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一关联中作为显现者的自主性的含义已经在先被给予,而其向意识亲身显现自身、给予自身的要求,则迫使直观不断向隐含的进一步充实的可能性扩展,进而使得直观不再仅仅被理解为感性直观。
这样在马里翁看来直观的扩展,以及通过类比得到的范畴直观等问题的现象学意义在于,它们仅仅为询问更为根本的亦即这一扩展发生的动力根源提供了一个契机。而这一提问是否要以海德格尔式的方式展开,则是马里翁自己着重辨别的问题,本文不再着重论述。而胡塞尔,在马里翁看来只是沉浸于发现这一表面的扩展的狂喜中,而丧失了询问这一问题的能力(3)[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55-63页。。
但我们似乎可以询问的是,在胡塞尔自身看来,所谓的直观的扩展带来的这些问题,与向《观念1》模式的转变有何关联?而马里翁是否真的公正地对待了自《观念1》开启的,直至《共主观性现象学》与《第一哲学》中的双重还原方才完成的视域道路。而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开启真正的向发生意义上的时间意识的还原。
一、《逻辑研究》中实显性突破的现象学意义
在《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中,胡塞尔指出直观的充实性、直观对于含义的显现作用,或者我们对于客体语言的认识性并不能改变含义本身的同一性,也就是含义无论具有怎样的直观形式,其本身均不会因此而改变。在这里,直观作为对于意识主体的被给予内容而言,与含义是完全异质的。含义在此处充实自身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图像式的相似性充实;(4)[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2页。但是,含义的特征以及给予方式的确经历了改变。(5)[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915页。并且,在我们的认识中,显然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直观行为中是同时具有的。那么,接下来便有两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1.如此与含义相异质的直观内容,如何具有了含义展示自身的承载者的功能?它是如何可以隶属于对于含义的充实行为的?2.给予自身的含义,在何种情况下必然在这样的差异性的一个行为中展示自身,或者说,这样的给予方式在何种情况下是必然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要理解的是直观内容,是基于何种可能,不能通过自身而理解自身,或者不仅仅是通过自身而理解自身。(6)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现象学的认识启蒙之要素”中,指出:“我们所理解的‘展示性的内容’或‘直观代现的内容’是指直观行为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内容,它们借助于纯粹想象的或感知的立义(它们就是这些立义的载者)而清楚地指明与它们特定相应的对象内容,并以想象映射或感知映射的方式展示这些内容。”(参见[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955页)也就是说,我们总会在不断变更的直观具体内容中认出另外的一种构型,一种代现性的内容。(7)[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965页。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去追问,作为自身而理解自身得以可能的、不带有任何意向充实特征的直观内容真的存在吗,还是它仅仅是一种抽象?
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在做出自感性直观(sinnliche Anschauungen)向范畴直观的关键突破时,将感性直观称为素朴的直观,即我们关注外部事物时,外部事物已经作为一个整体一举显现给我们,这时它有一部分“‘自身落在实在感知中’其他部分只是被意指”。(8)[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029页。在这里的感知行为之所以被称为素朴的,是因为,这里感知对象的统一并不是通过综合行为形成的,并没有添加新的意向行为,而是“各局部意向的直接融合”。(9)[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030页。但是,胡塞尔紧接着指出,在这样的融合的局部意向中得到认同的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与自身的同一性”,(10)[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032页。而只有我们将这些个别的感知分节并将其置于联系中时,前文所说的“各局部意向的直接融合”才能作为同一性意识的支点,而这些处于联系中的个别感知的相合性则作为新的感知的代现亦即范畴的基础。也就是说,虽然二者(素朴的感知与分节的感知)中都存在对同一对象的感知,但是“同一性”本身的观念形式只能在后一种方式中被给予,被感知。而胡塞尔指出,这样的感知得以可能,只有当分节感知中的一个部分受到“偏好”而其余部分隐含的一同保持在其中之时,这种分节的认识的统一才得以可能。而对于不同的部分环节的偏好的选择的可能性,则意味着不同观念的可能性形式被奠基。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处于联系中的分节的感知不同于素朴感知中的不断变化角度的可能性。胡塞尔指出,在素朴感知中这一对于分节的部分的感知是在统一性中被隐含的意指的,对其部分的意向并没有从总体中得以凸显。而在前一种分节感知的意义上,部分感知成为特殊的感知客体,而其又与对于总体的感知相合。我们发现,在后一种意义上不仅突出给予了一个特殊感知的客体,也突出了在与总体感知的相合中被给予的分节的感知。而在这样的一种给予模式中,作为部分的特殊感知的、客体在意识中亲身给予的性质与作为分节联系中的客体之间的给予性的相合性与差异性被充分表明。
这一问题在胡塞尔对于奠基关系中的感性直观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中得到进一步明示。胡塞尔阐释,作为被奠基行为的范畴直观与奠基性行为的感性直观二者的关系已然存在于观念化的种属关系之中。这意味着,范畴性的被奠基行为并非任意建立在其他行为之上,而是根据种属关系只能这样来认识自身。(11)[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059页。也就是说,在这一关系中,奠基性的行为必然已经处于种属的先天关联之中,才能与被奠基性的行为产生关联。(12)[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7页。另参见马迎辉:《意向性、绝对流与先验现象学》,《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而胡塞尔为何在这里会赋予二者之间一种先天的必然种属关联?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必然指向胡塞尔对于内感知与直观概念的理解,也就是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为何必然会指向一种意向性意指与意向性充实之间的相即关系。
在胡塞尔看来,所谓充实的意思是,当面拥有被感知者的直观性内容,其在直观所给出的事态中自身显现。(13)[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62页。这样的一种在直观性内容中的对于意向事态的证明的把握即是明见性(Evidenz)。因而在这里,胡塞尔理解的真理概念便是直观性的给予方式与意向的给予方式的相合性,(14)[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65页。也就是二者走向相符之际我们给出了实事本身。而相即性的关系只是这一相符的相关项。(15)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五研究“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中,指出:“这种明见性表明,人们将这种内感知理解为相即(adäquat)感知,这种相即感知并不把任何在感知体验自身中非直观被表象的和非实项地被给予的东西附加给它的对象;相反,这种相即感知完全就像它的对象事实上在感知中和随感知一同被体验到的那样来直观地表象和设定这些对象。” (参见[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696页)由此可见,在我们给出直观这一对于意向性的含义、显现者的显现方式的考察时,其已经先天地处于观念之中,已然处于含义的制约之中。而二者又是处于对立性关系中,在胡塞尔在“第五研究”里关于感觉材料与统觉的对立这一描述中更为明显。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五研究中指出:“统觉对于我们来说,是在体验自身中,是与感觉材料的原始存在相对立的描述性内容之中的剩余物。”“感觉材料以及被它们立义或统觉的行为在这里被体验,但它并非是对象性地显现”“对象显现,并被感知,但它却并非被激活”。(16)[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732-733页。而这一对立,并不仅仅表现为感觉材料与统觉之间的对立,而是进一步表现为直观与含义之间的交替性关系,这一点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说明。
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指出,这样的观念性的被给予之物是在先给予的,它有三个显著特点:1.其与主体性意识中的东西是不相关的;2.在直观之中,它是自身可以显现的;3.它不是一种认识的排序系列,也不是一种存在者之间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构造层级上的排列。(17)[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98页。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对于探讨在先的观念性,亦即被奠基的范畴直观的、观念直观的可能性领域的给出,必须首先以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相关性为前提。但是,胡塞尔将其限制于意识领域中的构造层级的做法,恰恰耽误了对于这一结构的自身存在问题的追问。在这样的结构中观念对象一旦给予自身,便立即从属于意识的构造层级结构。(18)[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40页。一旦第一性的存在必须隶属于当下之物的呈现方式、实在之物的给予方式,这样的存在便成了第二性的存在。(19)[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42页。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与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极其相似的评价,在赢得范畴直观的同时,现象学即赢得了对被给予性、存在、先天追问的可能性,却同时又耽搁了对这一问题更深的意义追问的可能性。正因如此,马里翁才迫不及待地将“在场”这一概念如此地扩大化,使其不仅超出了感性直观、范畴直观,甚至超出了普全直观,而达至了对于启示具身化的可能性的承受,达至了最终的被给予性。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胡塞尔这一赢得又耽搁的矛盾描述?或者我们可以问:这是现象呈现自身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吗?
然而,马里翁却在《还原与给予》中做出自己与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决定性差别的前一章,(20)[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48页。又援引了《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节,论述到胡塞尔其实早已对于超出范畴直观的存在问题有所考量。(2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页。马里翁指出,胡塞尔首先在第8节对诸科学进行了等级划分,标明了本质科学对于事实科学的独立;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性,意即所有的经验科学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原则,必须受到对象性一般的本质法则的限制,但其所处理的又必须是质料的本质基础。紧接着,胡塞尔在第9节区分了两种本质科学——区域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而任何事实性的科学都“一部分依赖于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的空形式,一部分依赖于区域本质(eidos)”。(22)[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第20页。马里翁指出,其中区域本体论按照《逻辑研究》中的理解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其必须在与质料基础的关联中给予自身。那么问题便在于:形式本体论与对象性一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自身的给予性呢?(23)[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51页。参见[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靳希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在第10节中,这一问题表现的更为明显,在这种区域本体论中,除了朝向“本质的对象”之外,这些本质、范畴形式却又指示着一种原对象性(Urgegenständlichkeit)意义上的对象。但是这样一种原对象意义上的作为一般的规定性并没有给出新的区域,而是使得任何区域都已成为可以通达的。(2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1页。这一对象性是独一无二的原形式,它比任何区域本体论中的本质形式、狭义的形式逻辑,以及任何普全科学都更为原本。
但是马里翁却接着指出,胡塞尔其实并未在存在论意义上对这一原对象性的给予方式予以追问,而是将其混同于命题学,亦即混同于《逻辑研究》中整个直观的层级结构的给予方式。在马里翁看来,这里的形式本体论不过是像命题学那样,首先赋予一个基底(substrat)谓语,并把这个基底看作逻辑上与存在者层次上的支点,这样便在不可见的意向性所朝向的存在论与述谓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与交互。(25)[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61页。这样,形式本体论便预设了对象性,也预设了区域本体论与范畴直观。在马里翁看来,胡塞尔在这里并未将基底的存在方式像海德格尔那样理解为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并进一步向此在的生存进行突破,从而为厘清两者的关系打开更为适合的问题域(26)[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62页。。
因此在这里的首要问题并不再是范畴直观意义上的直观的扩展,也不再是含义的自主性,而是意向性所朝向的不可见者、不显现者首先提出的显现自身的要求与作为承载这一要求的承载者自身的本质的追问。对于这一追问,我们必须要对意识亦即直观做出相应的形变(溢出与此在)从而诉诸被给予性与存在问题吗?就像我们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所看到的胡塞尔的努力,其将意识区域看成是最为原初的原区域与绝对区域,而所有的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为我存在”,都是依据意识的尺度(Bewusstseinmäβig)而显现自身。这里的绝对意义上的原区域已经不同于《逻辑研究》中的直观区域,其已经将不可见意义上的原对象性(Urgegenständlichkeit)囊括于自身,但是胡塞尔同时也并未抛弃直观问题,那我们将如何理解这样的一种给予方式呢?这样的给予方式能否逃离开海德格尔对于《逻辑研究》中问题的批评,并打开一种合适的问题域呢?或者其又像马里翁指出的那样,胡塞尔在建立起“一切奇迹中的奇迹”自我,从而在逃脱存在论差异的同时却又“隐退”了 ,将一切重新从属于概念化的可理解形式,从属于偶像(idole)从而错失了被给予性?(27)[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77页。
二、视域模式的建立与意义
道恩·威尔顿在《另类胡塞尔》一书中也曾指出这一问题,即整个范畴直观的代现性的模式并不能领会从来不会当下显现自身的东西。(28)[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第127页。也正如保罗·利科在法译本的注释中援引芬克的观点论证说这样的一种态度仍然隶属于自然态度。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486页。而这正是胡塞尔的“世界”(welt)概念。(29)[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第138页。在区域本体论的模式之下,胡塞尔其实并未通达世界的作为整体的给予性,世界只是在盲目的存在信念(Daseinsglaube)中被协同地作为隐含的条件与可能性被给予。同样,如果没有这一世界的给予,那么各区域之间的合理性联结便是不可能的(30)[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第139页。。但是,胡塞尔随后通过悬置(epoch)给出了通达这一整体性的被给予性的可能性。悬置首先使得我们认识到世界不可能在相即性的充实综合中达到一种确信与给予,其次世界只是内在性(Immanenz)中,作为一种联结的关联性可能性而给予,这样的结果便使得胡塞尔将世界的超越性内化于意识区域中而给予自身,这正是视域(Horizont)的给予模式。同样,在这一模式下,对于直观的理解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里的意识区域并不同于区域本体论专题下的各区域,若非如此,它又如何被称为是一种悬置的“剩余物”?(3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59页。
马里翁在这里称,胡塞尔通过这一操作构建了一种“基本差异”。(32)[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70页。这一基本差异体现在绝对的意识区域以及相对的各事实区域之间。在这一意识的绝对区域中的重点也不再是去认识事物本身是什么,而是事物如何在意识中呈现出来,在何种相关项中、如何在体验流的关联体中给予我们。这样胡塞尔便使得意识区域彻底从原先所探讨的区域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的问题域中解放出来,亦即意味着彻底从范畴直观的给予模式中解放出来。在胡塞尔看来这也就摆脱了对于存在问题的可能。(33)[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71页。因为正如我们前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在胡塞尔看来,所谓的存在问题是隶属于整个区域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的问题域的。我们看到马里翁其实指出了,胡塞尔现象学中范畴直观式的给予模式,与《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还原所得的绝对意识区域的给予模式,是对于海德格尔存在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耽搁。首先,马里翁通过论述第一种给予模式与区域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亦即胡塞尔意义上的存在论差异)之间关系,从而得出第一种模式确实耽误了对于存在问题的追问,海德格尔的批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在第二种给予模式之下,马里翁认为,这样的一种耽搁恰恰意味着它可以摆脱存在问题而走向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可能性。但是这样真的是合法的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需要去探讨在意识区域的给予模式下经过改造的直观问题与范畴直观的直观的问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胡塞尔在描述意识区域的基本结构之时,提出意识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体验关联体,但是这种体验关联并不是感觉素材与质素的简单混合,而是朝向对象、朝向显现者的,这一过程同时意味着对于这些感觉素材的激活(3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74页。。这一关联体是通过显现者在对意识显现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关联体,也就是说它就是显现者的显现,显现者给予自身的模式。但是胡塞尔认为,在这里的显现者是永远不可能在意识中内在地被给予的,他的给予性永远不能以一种相即直观的方式获得(35)[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74页。。而这即意味着,无论直观的、实显性的区域如何扩展,其在本质上都有着不可穷尽的剩余。那么这种“剩余”是如何被给予的呢?这里便构成了与《逻辑研究》中给予模式的根本不同:这里的体验流并不是单纯实显性的,其总是包含着一个非实显性的晕圈,(36)道恩·威尔顿在《另类胡塞尔》中指出,这就使得我们不再像《逻辑研究》中那样,把行为处理为属于另外层次上(类 species)和另外的区域(观念 ideal)中的结构的实例。参见[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第153页。也就是说,这里的体验流中的关联性意味着实显性的体验与非实显性的体验之间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亦即这些非实显性总是存在着变为实显性的可能性,而实显性的因素也总是存在着变为关联体中非实显性因素的可能性,二者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相互关联中,这是一种新的给予模式(37)[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61页。。而这一“关联”本身,是由显现者向意识给予自身的可能性所决定的。这里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体验与显现者本身的给予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一体验是直接地给予我们的,它没有任何侧显(Abschattung),而任何的显现者却不可能直接给予我们。但是当我们回归到上文提到的关联体时,确是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变异:首先,在体验流中给予自身的显现者不再要求一种相即给予性,而在一种潜在的假定着永远不可能穷尽的不断变化的关联的体验流中给予;其次,这里根本也不再存在对于单一体验的体验,每一体验总是处于关联体中被体验。但是这种关联体却仍然包含着体验的特征,它的给予不处于侧显之中。
另外,当我们以反思的角度指向每一实显的自我所拥有的体验之时,则进一步发现这里直接给予的并不是单一的体验,而是一个体验附加了某种变异或者说某种关联,或者说这两者即是一体的,即是一个体验的不同描述角度。也就是说这是与《逻辑研究》中单纯的直观模式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这样的一种最为原初的关联式的体验,构成了最初的内时间意识的原意识区域的构建,并为自我的把捉提供了基础(38)对于前者而言,其牵扯到的是原印象与其变异组成的原意识区域以及非原意识区域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也就是双重意向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后者,牵涉到的问题则在于排除了心理学意义上的个性因素之后,绝对意识在什么意义上仍然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自我,以及主体间性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属于先验领域。。这样的变异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外在世界都是假定的存在。但是它们对于我们的显现的体验流确实绝对的设定(setzung)的、不可怀疑的。这是一种在排除了外在所有外在世界的设定之后的一种剩余的“设定”。(39)[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83页。
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首先承认了这一《纯粹现象学通论》中的结构对于《逻辑研究》模式的突破,并指出逻辑研究中的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模式也只有在这一领域中才能得以充分理解。(40)[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27页。海德格尔指出,胡塞尔首先通过先验还原(transzentdental Reduktion)悬置了超越领域的存在,亦即“不再融身于世界之中,追随着行为本身的指向”,(41)[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32页。这就使得意向对象的行为本身(亦即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成了现象学探讨的主题。并进一步通过本质的(eidetisch)还原,使得这种行为本身与体验流都不再通过个别的行为而被理解,而是在观念化、本质化意义上的体验流中被理解。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现在,在具体体验里获得看取的只有那种例如属于一个感知、表象,属于一个判断的自身结构,而不管这一判断、感知是否就是此时此地正在进行的属于我的判断与感知,不管这一判断感知是在这一具体的构型中具有的,还是在例外的构型中具有的。”(42)[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33页,译文有改动。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领域仍然是由反思行为与反思对象之间的“实项的交融关系”(43)[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138页。(这一关系被称为内在性,早在《逻辑研究》时期就已经赢得)而得到锚定,也即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领域仍然只是对于两种存在者(体验流与超越对象)之间联系的规定,而并未对这一联系的存在方式予以追问。从而这一获得突破的领域也不过是在构造的顺序上突出了显现者的以显现的在先的条件,以及更加深入地追问了“意向性”本身的规定而已。(44)[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42,145-147页。
三、视域的两种理解方式
马里翁同样指出了,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指出的纯粹的形式本体论的问题域,虽然使得深入到可能性的深度,但是其仍然无法逃脱对象作为述谓的基底、命题逻辑的基底,从而仍然无法避免直观的基础性的奠基地位,无法摆脱对于《逻辑研究》模式批判的波及(45)[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58-264页。。但是马里翁紧接着指出,在进一步的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运作中对整个形式本体论与区域本体论问题域进行了悬置,并进一步推动了作为世界区域与意识区域的基本区分,并且尤其推动了对象本身与作为意识的对象的基本区分,而作为绝对区域与构造基础的意识区域是先于所有对象的区域,并且也不再是在对于对象的对象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所厘定的。亦即这样的一种处于绝对意识中的对象完全不同于《逻辑研究》模式中的意向对象的给予方式,亦即不同于形式本体论与区域本体论的方式,从而其摆脱了《逻辑研究》模式所引起批判的波及,并进而避开了存在问题的追问。(46)[法] 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265-273页。马迎辉在《胡塞尔论能意-所意——一种基于显现之先天可能性的研究》做出了更为清晰的描述,其指出纯粹意识区域与《逻辑研究》时期的实显性的体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本质上是一种绝对内在的存在,后者为整个超越性的存在奠基。因此整个纯粹意识区域在其看来可以被称为“前—实显”的。(47)马迎辉:《胡塞尔论能意-所意——一种基于“显现”之先天可能性的研究》,《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
接着我们可以对比两种模式中的直观问题,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在胡塞尔那里,单纯的直观是不能起到充实与认知的作用的,其只有处于与空意向的综合关系中,才能作为充实性与认知性的因素出现。而这样的充实行为作为对于空意向的明证性证知的行为,则意味着它是具有程度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把调节这样的程度的标准规定为相即(adäquation)明见性。而这样的部分直观只在其不断朝向完全的充实的增加过程中才具有自身的意义。而在《纯粹现象学通论》,当我们在直观的时候同时具有永远无法穷尽的非实显性的晕圈时,这意味着我们的明证性的证知模式也将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意向对象将永远无法在直观中被同时性的再现、代现。亦即这里的直观虽然包含着再现性的因素但是其却同时包含着非同时性的再现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种视域中的再现的被给予方式,无疑是在视域模式中被建构的再现性。这时候我们对意向对象的意指方式便不再是《逻辑研究》中的模式,而毋宁说是视域式的。因为,既然充实性因素的给予方式与二者之间关联(充实性因素与空意指)的给予方式都得到了重新理解,那么我们具有意向对象的方式也必然得到了重新理解,这亦即马里翁所说的发生的根本性的位移。因此似乎这里的新的模式无须与《逻辑研究》中模式的任何关联便可以理解自身,其似乎是摆脱了那一模式。但问题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摆脱?其意味着彻底的放弃吗?
因此,在马里翁与海德格尔看来,能否受到存在问题域的涵盖的关键在于视域模式与《逻辑研究》中模式之间的关联。虽然在马里翁看来胡塞尔的这一模式可以摆脱存在问题,但是其仍然无法摆脱被给予性或者说饱和现象的冲击,因为在饱和现象看来,这一受视域所钳制的直观,仍然不具有完全的事件性(48)Marion Jean Luc, Being given :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 Trans. Jeffrey L.Kosk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179-189.。但是正如萨里斯(Saulius Geniusas)所说,马里翁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视域的更深层次(纵意向性与时间流)的结构(49)Geniusas,Saulius, The Origins of the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Dordrecht:Springer, 2012:139.,在视域的更深层次的结构,胡塞尔完全可以逃脱这一批判。那么,我们将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胡塞尔所展现这一更深层次结构的被给予性模式能否避开被给予性的问题域?但在此之前,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这里具有对于视域的两种看法:第一种,以实显性为中心,为锚定将其余看成是有待、尚未实显的潜能性而存在;第二种,将非实显性的结构看成实显性结构的更为深层的基础。但在这里,仅仅就被给予视域本身而言,就不考虑其更深层次的构造与还原而言,我们有足够的现象学上的依据做出断言选取其中一种视角而判定另外一种是错误的,换言之,如果在这里仅仅做出这样的断言而没有其他考量的话,这并不是严格的现象学操作。
这更深层次的结构首先展现在noesis-noema 的结构中。首先在noesis一侧,就像德里达所引用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中的德累斯顿画廊的例子(50)[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98页。“我们穿过大厅并站在一幅苔尼尔思的画前,这幅画表现着一个绘画陈列馆。假如说,我们使后一幅画中画廊里的图像再呈现出那幅绘画,后者又显现着可识别的题词等等。”中所表明的那样,其中每一层套接性(ineinanderschachteln)的关系都表明了一个层级,也即是对其中纯粹自我反思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在反思中便可以不断地进行套接。但这并不是为了表明对于一种在场性的必然回返,而是为了表明在noesis中我们对于相互关联的体验之间的具有并不是一种“共时性”的具有,而是属于纯粹自我的不同功能之中(处于套接关系之中),而这为“历时性”差异性中关联性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可能性。也即不再仅仅探讨对象化意向中的意识呈现问题,而是拥有了一种指向意向自身的关涉。而后者也为对于内时间意识流中的纵意向性(区别于对象化带来的横意向性,其构成了体验流自身的统一性)问题的探讨得以可能。(51)此处可参见马迎辉:《胡塞尔论能意-所意——一种基于显现之先天可能性的研究》。其认为此处的套接关系即是胡塞尔对noesis交织结构的最初回到。另外,此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析均参考列维纳斯的分析。但是这一分析只是存在于各种价值特性的分析中,也即是说它只是存在于各种价值特性之间的套接关系。(52)这样的套接的可能性来源于它们自身具有的跟原信念的特殊的关联。胡塞尔指出,各种价值特性并不意味着是对于原信念(urdoxa)的彻底改变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在其中必然存在着原信念的痕迹,也就是说价值特性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变样了的原初的存在信念。同样,胡塞尔论述说,在对每一个价值客体的体验中我们显然存在着两种目光的可能性:第一种指向每一个具体的,例如喜欢等价值目光;而后一种目光也可以指向被喜欢的目光所朝向的客体本身(而非“被喜欢的客体”),其自身处于原信念之中。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04页。在这个意义形成了新的对象客体——处于某种设定态度中的客体,以及新的形式本体论,即多设定态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形式关系,例如其中存在的汇集以及析取的关系。(53)[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30页。对于这一问题,在noema一侧则表现为对于同一的X极的探讨。在noema一侧存在着两种对象关系,即起着载者作用的中心核点(Zentraal-punkt des Kerns)的统一性以及意识内容、意义(Sinn)(即通过此关联于对象)而建立起的统一性。(5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54页。也可参见马迎辉:《胡塞尔论能意-所意——一种基于“显现”之先天可能性的研究》,《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前者使得不同的意义可以进一步相关于同一个对象,并结合成新的意义统一体成为可能。显然在被意指的noema中它是一种不同于《逻辑研究》中意向对象与意义所带来的统一性。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中,直观的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其直接于设定产生了关系。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在noema侧,我们发现了与纯意义融合在一起的躯体性(Leibhftigkeit)性质(作为原初的充实性):而且具有此性质的意义现在起着作为noema的设定性质的基础的作用,或者换言之:存在性质的作用”。(55)[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66页。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意识中原初给予的直观区域在《纯粹现象学通过》中发生了两次扩展。第一次使得直观区域不仅只局限于实显性而是使得其自身与非实显性的给予体验之间有了内在性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仍然是由于显现者向意识的显现、意义的统一体所决定的。而在第二次扩展的意义上其归属于设定特性,归属于套接关系,在这种意义真正实现了体验流自身之中的指向意向自身的关涉。而第二次扩展涵盖了第一次扩展。(56)正如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显现者当然也是在侧显的流形结构中显示自身的。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69页。
但是胡塞尔在这一时期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量。正如胡塞尔指出,这样的体验关联体的形式虽然可以被看作内在反思在的相互统一观念化的时间流,但是其并不会下降到意识的晦暗的深处,对于原意识区域的自身构造进行分析。这其中自然包括未被详细探讨的纯粹自我与质素(hyle)(57)道恩·威尔顿在《另类胡塞尔》中指出,通过《被动综合分析》中的分析,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将这里的质素理解成为被意向行为赋予生命力、激活的元素。这里对质素的问题域的关注只能是通过把意向行为与充实行为中被给予的内容相互对立,并且有选择的映现(screening)后者,才可以得以关注(参见[美]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第272页)。而这样一种操作是否同时伴随着像《逻辑研究》中给予模式的回退,是考察前文中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理解视域模式与《逻辑研究》中模式关系的关键性问题。的问题。在这里胡塞尔指出,在经过现象学还原所指向的纯粹意识的体验流中,我们并未遇到纯粹自我,自我显然既不同于体验本身也不等同于体验的内容,它是属于每一体验中的同一之物。在这里的纯粹自我仅仅具有一种“指向于”与“关注于”某某态度的功能,除了其行为方式之外,其不具有任何可以说明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这里在体验本身和体验行为之间,在体验方式的纯主观因素与体验内容之间,永远存在着区别。(58)[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51-152页。胡塞尔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反思的体验,对于其中实行性目光的主题化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发现纯粹自我与体验流的关联体之间的必然性关联(各种“目光”的实行与转化)。(59)[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43页。虽然通过这一模式可以通往《观念2》中的习性自我的问题,但是却不能提供通向本性自我问题的路径。同样也包括质素的问题,虽然胡塞尔在这里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质素(hyle)的问题,亦即其不再是隶属于先天的种属规则的内容片段,但是胡塞尔紧接着指出其实不存在纯粹无形式的质素,存在的只是质素自身的流形综合体,其指向的是意识更深层次的构造。(60)此处可参见James Mensch 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章Retention And Schema (参见Lohmar,Dieter, Yamaguchi,Ichiro,On Time - New Contributions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Dordrecht:Springer,2010:p.153)。也可参见Rudolf Bernet的研究,其在Hussel’s new phenomenology of time conscious in Bernau Manuscriptis(参见Lohmar D,Yamaguchi I,On Time - New Contributions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1)一文中指出这一概念不过是从静态空间现象学中,形容外部空间物体的立义模式中借鉴过来的概念,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而已。方向红在《时间与存在》中指出,这里的质素问题只有到《贝尔瑙手稿》更深层次的构成问题上才予以讨论,亦即这里的质素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感觉材料问题,而是牵涉到胡塞尔现象学中更深层次的构成问题。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2页。
这些问题进一步引发了道恩·威尔顿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指出的胡塞尔无法逃避笛卡尔式的批评的问题。其原因其无法证成意识区域自身的现象学地位,其自身好像是非法地逃离了现象学还原。这样的批评意味着胡塞尔将现象学所有的成果限制在纯粹的主体的内在性领域,从而无法构造世界的客观性,无法进展到交互主体的世界。这是误解了现象学还原的操作所致,这一点在《第一哲学》中有了更充分的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更为详细的讨论也意味着noesis一侧体现在对于中性变样(die Neutralitatsmodifikation)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在胡塞尔看来中性变样意味着对于信念,对于存在态度的根本取消,其不同于肯定态度与否定态度,在其中即便是否定态度也暗含着某种“存在”的假设。它们是不受前面所讨论的视域的一般结构所制约的,亦即尽管它们也有实显性与潜在性之间的关联性结构,其完全可以是一种“中性变样”中的结构。亦即这种实显性的目光,完全可以是一种纯想象的注意,而不包含任何现实存在的设定。胡塞尔指出,这一中性变样是比信念中的套接关系,更为深层次的。(6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23页。其完全可以意味着超出视域结构走向更深层次还原的可能。对于这一问题与还原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则要进展到《第一哲学》与《共主观性现象学》中的还原问题予以探讨。届时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中性变样问题的提出,尽管在套接关系下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纯粹自我,并进而探讨习性的问题,但是其无法深入到内时间意识中的原区域自身构造与发生性的问题,也将无法对于纵意向性与横意向性的交织关系进行更为充分的探讨。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