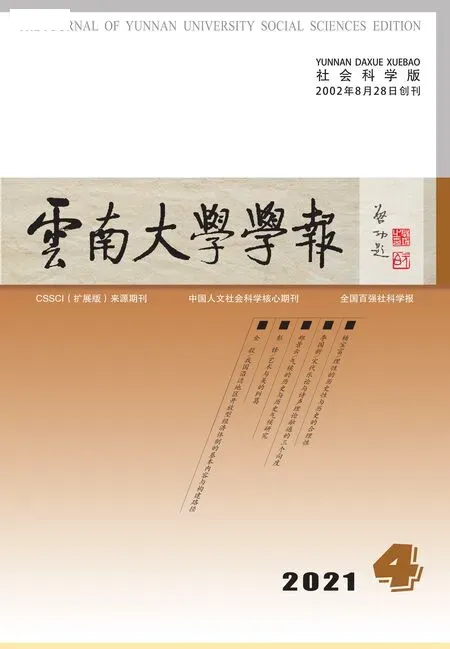从反美学到感性的回归
——当代美学与艺术的一种新趋势
金影村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2]
1917年,杜尚将一个小便器放进美术馆中展出,他的这一大胆之举影响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西方艺术,堪称当代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时至今日,西方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多年的历程。其中,当代艺术与美学的关系,成为重重迷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当代艺术不美了?曾几何时,艺术开始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介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是如何颠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迫使我们思考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为什么当代艺术不再像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那样,只供我们驻足欣赏?曾经的艺术享受,何时变成了对我们智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艺术,又对当代艺术批评提出了怎样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晚近艺术批评领域的何种态势?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要深入了解当代艺术,对当代艺术批评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将围绕反对美学与回归美学,展示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中的复杂性。
一、历史:美学与艺术的蜜月之旅
要了解艺术与美学在当代语境中的博弈,我们首先应追溯艺术与美学的关系。18世纪中期,德国美学家鲍姆嘉登(Baumgarten)首次将“美学”(Aesthetica)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庞大的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1)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1-185页。继而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充分分析了审美判断的几大契机。尽管康德对于美的概念分析不限于艺术而指向自然界,但他对于美的“非功利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分析却对整整一代近现代美学家起到了深远影响。直至黑格尔在《美学》演讲录中开篇便对当时流行的美学研究对象做出了归纳,即美(beauty)、艺术哲学、感性学。(2)在黑格尔《美学》演讲录中,他讨论了当时流行的三种说法,aesthetics(感性学)、callistics(美学)和艺术哲学,这说明当时学术界将美、感性和艺术当作美学的研究对象。但黑格尔主要赞同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说法。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4页。由此可见,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审美与艺术创作在漫长的西方艺术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相应的,从艺术史的角度,美学与艺术的历史也源远流长。艺术史学者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Elizabeth Prettejohn)在《美与艺术》(BeautyandArt)(3)该书以分析美与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关联为主题,但并不是为当下的艺术创作设立准则。书中回顾了四个时期的艺术审美,基于美的主观性,作者希望以往昔的审美来启发当下,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审美是永恒的,反而激发我们在当今重新反思“艺术美”的问题。见Elizabeth Prettejohn,Beauty and Art:1750-2000(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9-13.一书中,归纳了艺术中包括内容、形式、情感等诸多审美品质,并将审美与艺术的关系分为了四个代表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以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提倡古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为学院派艺术的最高准则,并将古希腊雕塑中的美视为永恒的、唯一的美的标准。(4)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中倾注了自己大部分的美学和艺术思想,其中,对希腊艺术的高度赞扬称为温克尔曼艺术史思想的核心。在中文译介领域,一般以劭大箴所译的《希腊人的艺术》为参考对象,内容包含了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中的重点内容和6篇重要论文。温克尔曼的艺术思想以论述希腊艺术为代表,通过歌颂古希腊艺术及人民对美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他借此为其所处时代的艺术创作树立了典范,认为只有不遗余力地模仿古希腊艺术中的人体美学,才是艺术创作永恒不变的原则。见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trans. G. Henry Lodg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Rivington, 1881), vol.1.第二个时期则是19世纪的法国,以浪漫主义和早期印象派为代表。在这一时期,艺术家追求个体情感的自由表达,通过创作实现自我超越的力量,而“美”成为了实现内在心灵解放的媒介。这一时期不得不提的艺术批评家还有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他为浪漫主义的辩护及对19世纪巴黎现代生活的描摹均为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个时期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这一时期,唯美主义运动达到高峰,“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口号让艺术与社会道德和日常生活彻底分离开来,由此,将维多利亚式的多愁善感之美(the Victorian sentimental)以及雌雄同体和同性之美推向了顶峰。(5)艾莉森·史密斯(Alison Smith)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裸体:性、道德与艺术》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裸体绘画与公共展览之间的关系,追溯了什么样的情色主题可以为公众所接受,并阐述了这一时期艺术与道德的隐秘联系。总体而言,追逐理想的人体美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它区别于作为“裸体”的题材,成了艺术家追逐美的理想形式。见Alison Smith, The Victorian Nude:Sex,morality and art(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3-5.
二、美学与艺术的裂隙
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提到的第四个时期,即以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等形式主义艺术批评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时期,实际恰恰是艺术“为美学”与“反美学”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内部革命和外部社会变迁的巨大冲击都对艺术风格产生了激烈的影响。19世纪中后期,印象派画家首先对绘画模仿自然、再现现实生活的传统提出了挑战。继而在欧洲遍地开花的现代主义运动包括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等。这些艺术虽然在风格语言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颠覆了学院派写实主义的传统,通过点、线、面、色彩、构图等媒介语言及抽象形式表达个体内心对外部世界的独特体验。在西方艺术从再现走向表现的过程中,主体的精神世界得到张扬,塑造出了一个个带有英雄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艺术家神话。与此同时,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再奉古典美的准则为圭臬。他们摒弃了和谐、秩序、理性、端庄,以及其他一切悦人耳目的视觉元素,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自发、随性、狂野甚至破坏性的视觉语言。
古典美与现代艺术的分道扬镳,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欧洲社会的动荡格局也密不可分。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纷争践踏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心中的诗意与美好,使他们堕入了一种普遍的怀疑、悲观与虚无之中。欧洲前卫艺术家开始了一种“反艺术”或“非艺术”的艺术创作。杜尚以自我嘲讽对艺术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博伊斯则通过实践 “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将历史上被视为精英的艺术拽下神坛。如果说对于强调媒介性与艺术自律性的现代派绘画尚有弗莱和格林伯格等人捍卫其形式美,那么,以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诸多前卫艺术则彻底背离了与美有关的任何因素。美已经不再是前卫艺术家的关注点,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介入与批判。
二战以后,艺术的中心由西欧转向美国。现代主义对于形式美的探索也旋即成为历史。尽管1940—1950年代亦有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独占鳌头的辉煌,然而,1960年代波普艺术的盛行让艺术彻底被美国式的商业文化所吞噬。波普艺术对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广告宣传册等的拼贴挪用,即使在理论上产生了美的效果,艺术家创作的意图也不是制造艺术美,而演变成了一场消费社会的狂欢。另一方面,同样是1960年代兴起的新观念主义,沿袭着以杜尚为代表的历史前卫主义,以概念、语言、智性分析取代了以感性认识为基石的视觉艺术。更不可忽视的是,当代艺术全球化的过程打破了西方话语的霸权主义,同时又为西方国家消费少数派艺术(如第三世界国家艺术创作、女性艺术、LGBTQ群体、土著艺术等)提供了新的理论空间。一种新兴的“政治正确”席卷全球艺术创作。正如W.J.T·米歇尔 (W. J. Thomas Mitchell)在《图像理论》中所言,1980年代以后,艺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已经向一门政治学科转向。(6)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由此,当代艺术在迅猛变化的过程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已经在背离视觉愉悦及形式美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彻底转变成观念上的智力游戏。
然而,在观念艺术与全球化的政治艺术走向极端之后,历史的钟摆开始出现新的偏移。1980年代以后呼声甚高的架上绘画的回归催生了绘画领域的新表现主义,(7)正如简·罗伯森、克雷格·麦克丹尼尔在《当代艺术的主题》中概括的那样:“尽管70年代就有油画艺术将会消失的预测,然而当代艺术时期油画并没有消亡。实际上在80年代初期,美国油画艺术在新表现主义如日中天时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这一时期,以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大卫·萨利(David Salle)、埃里克·菲舍尔(Eric Fischl)等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见简·罗伯森、克雷格·麦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匡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4页。来自意大利的“超前卫运动”也用具体艺术实践质疑了前卫艺术的传统。(8)“国际超前卫”是由意大利批评家阿克比勒·波尼托·奥利瓦(Acbille Bonito Oliva)提出的一个概念,1970年代,意大利在“贫困艺术”之后掀起了一股回归表现主义绘画的浪潮,并涌现出了数位“超前卫”绘画大师。奥利瓦宣告“再次出现的绘画创作,将问鼎艺术世界”,并提出:“以艺术作品的非物质化和创作过程的客体化为典型特征,且严格遵循杜尚风格的70年代的艺术,正被渐渐回归艺术领域的传统绘画取代。传统绘画由手工创作,往往给人带来创作的快感。”参见迈克尔·阿舍:《1960年以来的艺术》,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除此之外,发端于英国随后席卷世界的“反概念主义”(Stuckism)似乎预示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新方向。(9)反概念主义(Stuckism)是由英国两名艺术家发起的国际艺术运动,他们倡导具象绘画的回归,强调艺术的“正统性”,反对杜尚以来的“反艺术”传统,并在其宣言中批判后现代主义,呼唤现代主义精神的回归。见The Stuckists manifesto,http://www.stuckism.com/stuckistmanifesto.html,access,17th,Nov,2017.进入1990年代,艺术界对主体性、原创性、艺术品质、情感表达等美学特质重新予以了关注,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诞生的解构、挪用、社会批判与反讽等艺术手段则显示出了疲乏之态。正如托比·坎普斯(Toby Kamps)所言:“一个意识形态模糊未定的时刻,80年代的艺术策略——挪用、商品化、批判、解构——显得既空洞又工于心计。而艺术家开始对可及性、交流、幽默和游戏产生兴趣。那个曾提出风格上的折中主义、社会批评和反讽的历史终结论的、作为一种风格而流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业已枯竭。”(10)Toby Kamps, ‘Lateral Thinking: Art for the 1990s’, Lateral Thinking: Art for the 1990s(La Jolla, Calif: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San Diego, 2002), p.15.在批评话语中,对当代艺术审美回归的预言、呼唤、反思也逐步成为对未来最重要的关切之一。美学再次回到当代艺术的视野中,对艺术实践、当代美学、艺术批评及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美学与艺术的拉锯
当代艺术从反美学到感性回归的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潜藏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反美学”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扩展了当代审美的范畴,另一方面,当代着重“审美”的创作导向有时包含了对当代社会更深切的关照与批判。总结起来,当代艺术对美学的回归更为深化地释放了美学作为一门感性认识的学科的含义,而不仅仅限于作为狭隘审美范畴中的“美”(beauty)。
历史地看,当代艺术批评对审美的反叛,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卫艺术批评。从历史前卫运动到新前卫运动的反美学抵抗路径来看,前卫艺术和理论对美的批判,从来不是针对某件特殊的作品,而是关于某种观点、意识形态、社会实践和文化等级制度的批判——如体制批判、社会介入、将艺术融于生活等。而“反美学”本身,只不过是前卫运动到达他们预期目的的手段。前卫艺术将“美”重塑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由此产生了两种对立的美的概念:其一是纯个体的主观经验,亦即美学史上广为认同的康德式审美判断;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美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自始至终都受着周遭社会的影响。(11)Dave Beech,ed.,Beauty (London and Cambridge: Whitechapel Gallery and The MIT Press, 2009), p.14.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便是秉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明确表达了趣味的阶级划分与审美作为一种认知的意识形态功能。(12)参见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第一章《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的详细论述。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除此之外,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以及各种跨学科的艺术批评也纷至沓来,对西方正典化的艺术史叙事与当代艺术批判产生了巨大冲击。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定义,现代性被定义为祛魅、理性化与等级化。标准化、效率、方法论与辛勤劳动在现代社会中被结合起来,产生了韦伯所称的“西方文化中特殊而古怪的理性主义”。(13)Dave Beech ed., Beauty,p.15.这种理性主义导致的结果便是个体的审美能力被淹没在现代社会的商业大潮中,成为总体社会分工的一个环节。在这样的现代世界中,一切知觉、情感、快乐都被网罗在意识形态当中。(14)Ibid.然而,随着历史进入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社会运作机制也随之逐渐解体。“个体的声音”“他者的声音”取代了标准化的文明指挥棒。在艺术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等“身份认同”的问题,已经溢出了社会学的领域,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另一种政治学,并在1970年代以后全面介入到艺术体制之中。(15)参见《1960年以后的艺术》之《身份、自我认同和与众不同》一章。迈克尔·阿舍:《1960年以来的艺术》,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由于艺术中的美天然地与西方白种男性精英为主导的艺术史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美”便不可避免地成了前卫艺术和女权主义共同攻击的对象。正如戴夫·比奇(Dave Beech)所言:“美之所以被攻击,是因为它一直为塑造西方审美中的愉悦所殖民。不管杜尚还是阿尔恩(Rasheed Araeen),都通过重新框定美的范畴,将其视作始终为地方性的、局部性的,以此精密地挑战这种美的观念。”(16)Dave Beech,ed.,Beauty,p.12.然而,以上这些观点对美的罢黜,要么是将“美”的概念放在十分狭隘的定义框架中,要么就是政治立场高于艺术本体论,试图将“美”塑造成霸权式的享乐主义压迫少数派与弱势群体的“恶之花”。我们必须注意到艺术中的美有着十分广阔的外延,并且随时代与风格的变迁不断自我更新为一种隶属于“感受力”的审美经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1960年代便提出了“新感受力”的概念,并区分了以智性分析为基础的感受力与以美学快感为基础的感受力。(17)关于桑塔格对“新感受力”的论述,详见《一种文化于新感受力》一文,收录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22-333页。尽管桑塔格认为智性与审美经验可以融合在一起(这似乎也反映了1960年代美国艺术的真实境况),但她仍然警觉地意识到过分快速的形式更迭,将会耗尽艺术的本体价值,从而导致图像的过剩与欣赏的疲软。(18)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利兰·波格编,姚君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2、22页。
正如当代艺术实践领域的自我更新一样,艺术批评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对“美的回归”展开了多元而深刻的讨论。正如朱利安·斯塔拉布斯(Julian Stallabrass)所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艺术批评中,曾有一次关于美的讨论的复兴,而这是一个一度被忽略的话题,这一现象反映出随着经济的复苏,装饰性和商业性艺术逐渐兴起。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摆脱政治、金钱、差异性和精英主义等问题的一种方式。(19)朱利安·斯塔拉布斯:《当代艺术》,王端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66-267页。
朱利安所说的关于“美的复兴”的探讨,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便是美国作家戴夫·希基(Dave Hicky)。1993年,戴夫·希基撰写了《潜入神龙:论美的土俗性》(Enter the Dragon: On the Vernacular of Beauty)一文,收录于同年出版的《神龙:美学论文集》(TheInvisibleDragon:Fouressaysonbeauty)一书中,由此将“美的回归”作为议题搬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艺术批评界对美展开了重新反思。希基从市场与大众趣味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圈子化的当代艺术体制对普遍趣味与审美民主的扼杀。(20)具体论述见《神龙:美学论文集》第一章《潜入神龙:论表达美的世俗话语》。戴夫·希基:《神龙:美学论文集》,诸葛沂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在他看来,被艺术体制严格操控的当代艺术终将回到普通民众所能接受与认知的审美体系中。希基的这一论点,不仅反驳了哲学家阿瑟·丹托对于当代艺术所提出的“艺术终结论”的看法,(21)1980年代,阿瑟·丹托受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影响,撰写了专著《艺术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之后》等,他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代艺术的审美判断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化。同时,丹托也针对希基的论点挑战了他提倡的视觉审美,认为当代艺术品的审美不应从事物的外表出发判断,而应当完成一种寻常物迈向更高“理念”的嬗变。还突破了自前卫艺术诞生和发展以来,在批评界一直弥漫的“反美学”浪潮。然而,希基从审美快感出发的视觉理论,遭到了当代艺术史家、哲学家与美学家的挑战。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与政治、道德的复杂关系,他的观点的确从侧面反映了当代艺术体制对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收藏与流通等方面设置的重重壁垒,但这也不可避免地淹没在了后现代语境里普遍的反中心主义趋势中。尽管如此,希基在20世纪90年代高度体制化、观念化的艺术圈提出“美的回归”,仍然不乏真理性的价值,弥补了学术界普遍缺失与忽视的关于艺术本体的讨论。
事实上,早在希基之前,就有学者意识到,一味地用扼杀“艺术”来体现当代艺术的价值,反而会将当代艺术卷入无处不在的商业文化中,成为一场资本运作的游戏。不同于希基对“视觉美”的捍卫,新时期的艺术批评体现了对前卫精神与当代风潮更深的理解。例如,美国批评家唐纳德·卡斯比特(Donald Kuspit)于1983年出版的《艺术的终结》一书,通过后现代主义商业文化对高雅艺术的侵蚀得出了悲观的“艺术终结论”。然而,在本书的后记《工作室的废弃与重建》中,卡斯比特提出了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能够在当今社会得以维系的可能性。他呼吁当代艺术家重返工作室,通过对艺术语言的进一步探索,创造出结合古典技艺与当代观念的艺术作品。并将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就的艺术家,称为“新派老大师”(The New Old Master)。卡斯比特所提倡的“新派老大师”,指的是一批具有思考能力,同时又不失技艺的人文主义者。具体而言,“新派老大师”包括卡斯比特高度赞扬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22)卡斯比特撰写了大量德国艺术评论,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德国新表现主义的综合论述及个案研究,详见Donald Kuspit, The New Subjectivism: Art since 1980s(Michigan: UMI Press, 1988).同时,对美国本土坚持绘画技艺又不是观念性的艺术家,作者也提出了独到见解。(23)2005年,卡斯比特以策展人的身份在美国加州举办了“新派老大师”展览,推出了多位当代美国艺术家的经典画作。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卡斯比特对结合当代思想与精湛技法的艺术的推崇,并对作品的美学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详见Donald Kuspit, California New Old Master(California: Literary Press, 2004), ix.总的来说,卡斯比特的艺术批评立足于当代绘画,反映了对西方20世纪80年代架上绘画回归的趋势的乐观态度,(24)在《二十世纪晚期绘画的重生》中,卡斯比特详细论述了架上绘画的回归对主体表达的重要性,认为当代绘画是艺术家身体与心灵自由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见Donald Kuspit, The Rebirth of Paiting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5.同时也将“回归”的思想渗透在对“新派老大师”的论述中。
更进一步,对当代艺术中所体现出的新感性的认识,也在前卫文化的大浪淘沙中留下了闪光的砾粒。其中最受瞩目的理论之一便是法国学者朗西埃的美学理论。他突破性地将“美学的政治”与“政治的美学”联系起来,提出艺术作品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可感性”的环境,让那些原本被艺术体制排除在外的人都能通过“可感性的重新分配”参与到艺术中。在平等的原则下,感性之间发生的冲突与对撞(朗西埃称之为“歧感”),就是艺术作品的价值。(25)关于朗西埃对“可感性”的论述,详见Jacques Ranc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trans. Gabriel Rockhill(London: Continuum,2004),pp.12-19.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让“美感”本身变成一种解放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粗暴地让艺术直接介入到社会活动当中,沦为实现某种政治乌托邦的工具。
由此可见,当代艺术批评领域以戴夫·希基、卡斯比特、朗西埃三者为阶梯递进发展,分别对内容、形式、感性三个美学研究重要对象的反思,构成了当代艺术“感性回归”的完整话语体系。就本文的出发点,笔者更愿意将“反叛”与“回归”这两股势力的对垒当作一封寄给未来当代艺术的信件,一面折返回杜尚的时代,追溯前卫艺术的传统,另一面则面向未来,在未知的时空领域探索艺术的本质。当我们将“反叛”与“回归”放在1980年代以后的语境中共同加以探讨,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把握20世纪西方当代艺术在自我认知过程中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聚焦于美学领域,探索当代艺术审美面向在未来的可能性趋势。
结语:“反叛”还是“回归”? ——当代艺术新起点
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其著作《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中,开篇便引用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一位中国皇帝请宫中的画师将宫殿墙上刚刚画成的瀑布抹去,因为他在睡觉时感觉听到了瀑布的水声,以至于夜不能寐。(26)[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这个故事以绝佳的寓言方式说明了图像的魅力,它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感性连接点,是主体情感运动得以再现的最原始、最永恒的方式。在漫长的图像史中,作为“艺术”的图像,也就是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图像的唯美化”,始于15世纪,终于19世纪。(27)雷吉斯·德布雷以观看的角度界定了图像从“偶像时代”到“艺术时代”的过渡,在前者中,观看为宗教的集体功能服务,因此“有目光而无主体”,而后者“艺术时代”以两种主体的诞生为标志,即艺术家和观者。有了主体,遂产生了对美的判断力。对应西方艺术史,这个时期大约为文艺复兴至现代艺术运动时期。正是在这400年的历程中,图像的“艺术时代”与“美感”发生联系。参见《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第201-205页。这样看来,美与艺术的联姻其实只持续了约四百年。如果仅仅将“美”理解为“美的艺术”,图像固然不需要承担传递“美”的职责。然而,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学科,图像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作为主体,才是图像与美学真正产生交集的地方。换言之,有人的地方就有图像,有图像的地方就会产生“美学”。前文故事中的这位皇帝,就是以主体性的“通感”搭建了美学与图像的桥梁。固然,美学与艺术的关联是历史化的——只有在特定的时期,“美”才在图像生产中占据核心甚至唯一的地位。但美学与图像的关联,却是去历史化的——只要人类文明还在生产图像,美学便不会也不可能消失。对应当代艺术,图像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装置、影像、摄影、现成品,甚至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成为新兴的图像。尽管创造它们的媒介千变万化,但只要图像的制造和接受中还包含了作为主体的“人”,美学与艺术的历程便不会终结。
反美学的当代艺术试图将艺术工具化,将其作为介入现实社会的载体。然而事实上,它们都没有真正逃离“图像之框”,从本质上只是改变了人与图像之间的联结方式。这种方式,在观念艺术家看来或许是抽离感性的、极端机械主义的,然而,在他们表达这一态度的同时,已不自觉地将感性注入了他们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在艺术中其实从未失落过,所谓的“感性回归”,只是美学在艺术中重新回到了显著的位置。1980年代以后的艺术批评经历了从“反叛”到“回归”的审美历程,其本质是将美学重新拉回到艺术批评的视野中来,重建美学在当代艺术中的新维度。
黑格尔主张将美学精确定义为艺术哲学,并预测艺术终将走向终结。在他看来,艺术在经历了自我认知的上升过程后,终将为最高心灵层次的哲学所取代。(28)黑格尔将心灵分为三个层次:最初级的层次是艺术,它是真理的感性显现;继而是宗教,它的侧重点从客体感性形象转到了膜拜者的主题虔诚心理;而最高级别的认知方式是哲学,它统一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体现为“绝对真理”。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130-133页。丹托沿袭了黑格尔的思路,对“艺术终结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29)“艺术终结论”的观点,参见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当代艺术中感性回归的趋势,就会发现艺术创作并不会简单地走向终结。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断言,当代艺术批评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即“艺术的终结”“反美学”及“美感失效”。相反,“回归”也是当代艺术的一大议题。只是这种“回归”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轮又一轮前卫艺术的洗礼,已经不再是古典艺术中单纯的视觉愉悦,也不是现代艺术体系中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演变成了一种更成熟、更具当代风貌,同时又不失社会关照与人文关怀的当代艺术“新感性”。“反叛”还是“回归”?这其中或许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正所谓“兼听则明”,在日益多元的当代社会,我们需要这样一封信,来迎接未来艺术可能回馈给美学的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