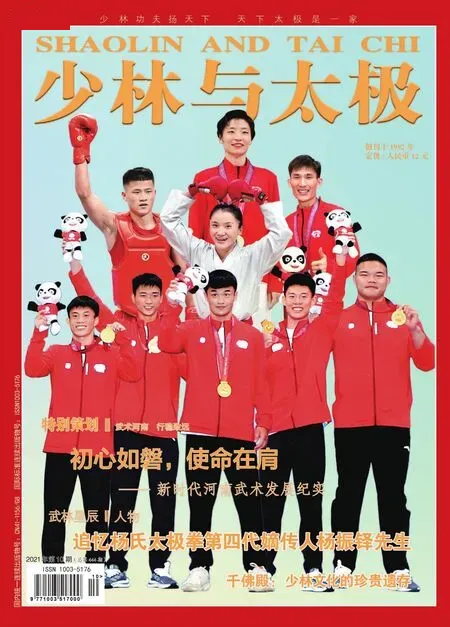武林圣典及其崇拜
◎龚鹏程
刀经拳谱、武籍秘录,在我们社会上,因小说电影电视之渲染,已形成一种“圣典崇拜”。
大家相信最高的道理即存在于经典之中,只要获得经典,依法修参,便能证得无上菩提,登至最高境界。所以,为了获得经典,不惜巧取豪夺,大动干戈。取得经典后依之修行,亦为必循之径路。
圣典崇拜,其实是各宗教、各文明中普遍之现象,武侠世界自然也不例外。但武侠文学中出现这个现象的时间甚晚。早期只有侠义小说曾有宋江获得九天玄女三卷天书之类的故事。
可是天书玄秘,通常都是没有字的;仅在危难时焚香祝祷,才会示现天机。此亦为圣典崇拜之一种类型,然非尘俗世界得能仿效。
尘世的武林,把拳经秘籍讲得最活灵活现的,是金庸的小说。
我们试想:若无《九阴真经》《九阳真经》,射雕神雕诸传的英雄侠侣们还唱得成戏吗?若无《辟邪剑谱》《葵花宝典》,令狐冲林平之的曲折故事恐怕也讲不成了。同理,小胡斐的本领,全凭一册胡家刀谱。有人偷练了前面几页,便成了技击名家,经典之义,斯可谓大矣!
金庸之前的武侠小说名家,谈论秘籍者甚少,金庸则几乎每本小说均以秘籍为其情节核心,秘籍又特别多。《九阳真经》《九阴真经》《辟邪剑谱》《葵花宝典》《胡家刀法》之外,如《六脉神剑》《易筋经》《紫霞神功》《玉女心经》《乾坤大挪移》等均是。
其小说之模式既以此为特点,当然也就因此而形成了格套,看来看去,似曾相识,不免有自陷窠臼之嫌。故以秘籍为叙事核心,乃其创格之成就,而亦遂为其缺点之所在。
何况,秘籍固为昔贤所创,笔录以传世。后世岂定无贤能之士,不能自我创获,非取而诵习不可?
金庸笔下的圣典崇拜,往往被形容成武功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谁只要能得到圣典,便可练成当世最高的武功。此固为圣典崇拜之常态,但经是死的,人是活的,因崇拜经典,遂拒绝灵活通变、因革创益之机,恐亦非智者所应为。
此非苛责金庸,也不是要讨论武侠小说该怎么写。金庸之所以特别注意到圣典秘籍,并以此来作为情节核心,料想他有个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令他对此有感会,故下笔不觉其然而然,就表现出了圣典崇拜诸征象。

一
中国兵器,以剑为尊。但后世剑法失传,剑在战阵中亦无所用,剑遂仅成为装饰性或表演性的道具。
所以现在所有所谓古剑术,都是杜撰、瞎掰或虚构出来的。讲故事,听听就好。
真正讲武术的第一本剑经,其实乃是一部棍法谱。以棍谱名为剑经,自有以棍代剑之意。剑的传统地位及作用,依作者看,是该让位给棍了。
这位作者,乃明嘉靖万历间之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曾任其副将,对他的棍法非常佩服,所以在编《纪效新书》时,把这本《剑经》全文收录书中,且增绘了二十四图势,以助了解。
后来民国初年写《江湖奇侠传》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也曾注释此经,并增图势若干幅,改名《子母三十六棍法》。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不仅具有历史地位,也深受内行推崇的经典。
俞大猷的棍法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或者说它的要诀何在?
综合俞大猷与戚继光的看法,有几点可谈:一、棍为兵器之首:“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耙,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 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二、棍虽重要,但练棍者跳跃闪滚,多是花样,中看不中用,故棍法以实用为要:“俞公棍,所以单人打不得,对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无虚花法”。单人打不得,就是说棍法不是个人表演用的;无虚花法,就是说不准练者“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三、使棍时,须懂得短兵长用的道理。棍不如长枪大刀,乃是短兵器。短兵利在速进,要抢到近距离才能发挥作用。所谓短兵长用者,是长驱直入之意。四、两人对阵,不是演套路、耍招数,而是要乘其机、因其势的。所以他强调:“须知他出力在何处,我不此处与他斗力,姑且忍之,待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然后乘之,所以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也”“不外乎‘后人发,先人至’一句”。
这些论点,都是武学上的至理名言。习武者卖弄气力,矜炫姿势,乃人之通病。此经所说,可谓切中要害。
可惜后世武术之发展仍然是以演套路、打招数为主,每家各派,以此自鸣得意。既罕实用实战之效,又跟俞大猷博采各家之精神相违(他的棍法吸收了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的技法与实战经验),实在令人感慨。幸而,“后发先至”“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之原理被太极拳等内家拳派吸收而发扬光大了,否则后人对此《剑经》岂不愧煞!
二
以拳相击,古称手搏。但自古罕有以拳法闻名者,与今日不同。
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序,记其麾下奋威将军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能空手入白刃”,似是擅拳技者。
然曹丕记其术,乃是击剑,而非拳搏。曹丕弟弟曹植论手搏也不详。足证此道于古不盛。
也正因为如此,清初编《古今图书集成》,在“拳搏部”,就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录,勉强把古代的角抵列入其中。
但角抵只是摔跤、相扑、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拳术搏击仍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可以看出拳术的发达实在是很晚的事了。
现今论拳术,动不动就说少林、讲达摩,或上推太极拳之类拳法于唐代道士许宣平、宋朝道士张三丰,其实哪有那些事儿呢?
就连《水浒传》里说拳脚,也粗略得很。李逵、鲁智深,三拳两腿即置人于死者,非其术惊人,但凭一身气力耳。唯武松醉打蒋门神时,用了一招,说书人特别记了一笔,谓此乃“鸳鸯脚”“连环腿”,可说已为拳术之滥觞。
《水浒》写成时代甚晚,但武松所处的宋代,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拳招的。因为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创立长拳,岳飞也曾创立拳法。其技虽乏文献可以稽考,但后世拳术,泰半与它们有渊源,则是可以确定的。台湾民间,流传最广的,也就是太祖拳。
宋代这些拳法,传到明朝,颇有发扬。其间最重要的人物,即名将戚继光。
戚氏《纪效新书》末尾为《拳经捷要》。此为拳经之祖。
它一方面延续传统见解,谓“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一方面又提高它的地位,说“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大抵拳棍刀枪叉耙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有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之源”。拳法自此,才成为武技中的入门功夫。
其次,戚继光又是当时拳术之集大成者。他主张“博记广学,多算而胜”,故将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八闪番,十二短,以及鹰爪王之拿、李半之天腿、千跌张之跌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编为廿八势,绘图、注诀以教人。后世拳谱均循其体例。

后世一些拳法,其实也多脱胎于此。例如太极拳中的懒扎衣、金鸡独立、单鞭、探马、七星、跨虎,均本于此。
此外,戚继光不是经典主义者,他主张在实战中增进技艺,而非熟读图谱即堪应敌。因此他说:“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以胜负为愧为奇。当思何以胜之、何以败之、勉而久试。怯敌还是艺浅”。
后世许多人都妄想寻获一本秘籍,以为据本子练习之后,就能立刻天下无敌。依戚继光看,天下是没这种便宜事的。这才是它成为经典的原因。
——67公斤级拳法技术趋势分析
——基于对《拳经拳法备要》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