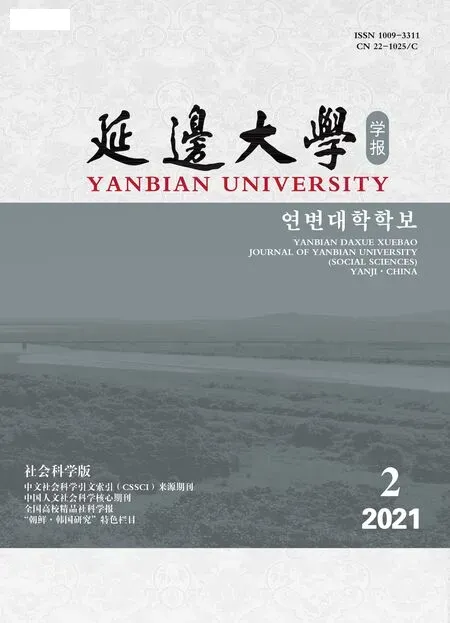试论金庸武侠小说成长主题下的母女关系
曲俐俐 张文东
作为20世纪武侠小说巅峰之作的金庸武侠小说,其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叙事研究(对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人物塑造的拓展等)、对小说中武侠文化的内涵研究(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与现代性等)。本文试图撇开这些角度,从容易被忽视的金庸武侠小说成长主题入手,探讨女性侠客与“父一代”母亲(生身之母或替代性“精神之母”)之间的情感关系及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冲突,以此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侠客的自我认知与江湖定位,进一步理解金庸对武侠小说中性别观念调整与权力秩序修正的多重意义。
一、成长小说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一)成长小说与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成长小说和小说中的成长主题并非同一概念。成长小说起始于西方启蒙时期,到18、19世纪德国文学时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叙事模式和主题思想。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颇富洞见地指出成长小说的四种类型即漫游小说、考验主人公小说、传记小说和教育小说。以教育小说为例,他指出“大部分小说(以及小说的各种变体)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除了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数量众多的小说类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见的小说类型,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9-230页。虽然成长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20世纪初才被引入中国,但成长主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要叙事元素。小说中的成长主题是针对小说中的人物成长而言的,这里的“成长”包含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成熟和个体性格与心理上的内在成长过程,又必然联系着在文化背景、成长环境与人际交往等外在因素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情感认知与精神追求。在这种内外因交互作用下,个人与他人、个体与世界、内在与外在、欲望与情感、感性与理性等复杂而丰富的变化,正是小说中典型人物独具魅力的成长轨迹。正如老舍所说:“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2)老舍:《老舍谈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83页。而小说成长主题交织下的家庭主题、情爱主题、英雄主题等多重主题,恰恰反映出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价值在于巴赫金所指出的“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3)[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在20世纪的武侠小说创作中,涉及成长主题层次之广、涵盖类型之全面者,非金庸莫属。金庸武侠小说的成长主题涉及以下三个层面:
1.成长主体——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的侠客群体。如果说受众偏爱武侠小说,是因为小说中以武行侠的场面描写与快意恩仇的潇洒简单满足了读者对故事情节曲折紧张的阅读需求,那么金庸在15部武侠小说中塑造的众多侠肝义胆、有情有义的男性形象,无论是令狐冲的潇洒恣意、杨过的至情至性,还是韦小宝的义气为重……,都承载了一代代读者对侠客的美好想象,满足了大众面对生活重压与命运颠沛时,渴望被拯救的“侠客—英雄”崇拜心理。而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则成为“武侠”之外更为动人的爱情付出者,如王语嫣对慕容复的痴情至极,小龙女为救杨过舍弃生机决绝地跳下悬崖,任盈盈对令狐冲的默默支持与守护,抑或是郭襄的单恋、李莫愁因爱生恨下的畸形之恋……。这些爱情至上的个性化女性形象,这一幕幕爱恨情仇与生死离别时或潇洒或纠结、或理智或绝望的选择,都引发了身处不同地域、拥有不同身份与不同情感的读者的一次次心灵共鸣。这是女性人物对情与爱的付出与坚守,是对情的至性表达与对爱的深刻诠释。
2.侠客的成长空间——男权秩序规约下的江湖世界。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是一个崇尚义气的世界,侠客们将有情有义、见义勇为看做江湖的最高道义,但是这种“以暴制暴”原则的单一性中暗藏着无法逃脱的巨大焦虑,即个人意愿必须服从于绝对的“义气”。金庸也不无批判地表示:“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4)张大春:《诸子百家看金庸(四)》,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第38页。而江湖中各种派别的争斗与厮杀,多源于正邪不两立的派别立场。因此,个人的恩怨情仇与派别间的种种争斗,都被简化为武力至上的“丛林法则”。这种安排更利于突出侠客个性,由正邪之争引发的大型比武场面也是推动武侠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将文化性与哲理性的人生思考带入这个虚构的江湖世界,从而提升了武侠小说人物性格的丰满度,也借武侠世界的伦理观念与价值冲突展现出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3.侠客的成长史——男侠与女侠的成长经历。金庸笔下的群侠形象之所以被一代代读者铭记,主要归功于小说中描绘了男性侠客们颠沛流离的成长史:他们大多幼年丧父丧母或自小无依无靠,经过自身的一次次奋斗,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造福了社会,最后在一片溢美声中飘然而去,退隐江湖。这种成长型英雄的塑造不仅打破了以往武侠小说塑造人物的平面化与类型化的沉疴,更改变了武侠小说松散化的结构模式,为突破武侠小说阅读与欣赏的娱乐状态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而在侠客们的众多情感中,“子一代”与“父一代”之间的亲情关系,是侠客情感的原点,也是其对情与爱等观念的建构基础。宋伟杰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父子关系进行了颇有建树的分析,将父亲形象分为生身之父的缺席与“替代性”父亲(师父)的多样性。生身之父与理想之父无意识或有意识的缺席与权力置换,造成了“子一代”的身份危机与精神裂变下的痛苦与焦灼。(5)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7-107页。金庸武侠小说的“子一代”,不仅包括成为大侠的男性群侠,也包括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女性侠客。这些在小说中被归为仙女、妖女、恶女或悲剧性的女性人物,与其“父一代”的生身之母或“替代性”母亲(师父)之间,构筑起了金庸武侠小说成长主题的另一重要维度。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母女形象
武侠小说历来着重描写男性侠客的成长史,不仅因为武侠小说多是男性作家创作、供男性读者阅读的作品,更因为武侠小说中侠客们赖以生存的江湖空间遵循武力与侠义并重的道德原则,始终无法逃脱以男权秩序为主的性别准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侠客成长史中,依然可见众多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侠客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仙女类、妖女/魔女类和悲情女子类三种。
(一)仙女类
这类女性被形容为容貌美艳动人,身姿绰约有致,气质娴雅超逸,性格不谙世事,最为典型的代表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等。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时,一见她如明珠、似美玉的容颜,“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6)金庸:《金庸作品集——书剑恩仇录(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第一次出场也是惊艳绝伦:“只觉这少女清丽秀雅,莫可逼视,神色间却冰冷淡漠,当真洁若冰雪,却也是冷若冰雪,实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乐。”(7)金庸:《金庸作品集——《神雕侠侣》(一)》,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二)妖女/魔女类
这类女性侠客武功超凡且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顾他人死活,自我意识较强,能够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立足于江湖世界之中。金庸着重强调她们的狠绝与聪慧,希望塑造出全新的女侠形象。同时,赋予这类女性明显的外貌优势,以及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忠贞态度。无论是收获美好爱情的黄蓉、任盈盈和赵敏,还是遭遇背叛的王夫人和李莫愁,都是不忘所爱、因爱生恨的典型代表,如《天龙八部》中的王夫人,遭遇风流成性的段正淳背叛,便憎恨天下所有负心之人,她说:“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8)金庸:《金庸作品集——天龙八部(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405页。还专门打造了阴气森森的“花肥房”,对素不相识的人经常挖眼割舌、砍手砍脚、活埋做花肥。因此,只要听到“王夫人”三个字,曼陀山庄的人都被吓得胆战心惊、面如死灰。
(三)悲情女子类
这类女性因外貌形体受损而命运悲惨,如《倚天屠龙记》中因练功导致容貌扭曲的殷离和为盗取乾坤大挪移而故意扭曲形态的小昭;《神雕侠侣》中因幼时意外失误成为跛足的陆无双等。身体的残缺与由此带来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她们在江湖中处于弱势与次要地位,成为被欺凌或被怜悯的对象,成为江湖世界中特定的游离者与旁观者。“红颜祸水”和“厌女症”等词汇一直是形容武侠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固有词汇。这些对女性外貌的批评和心理的嫉恨,都是江湖世界男性权威的隐秘规则。“男性的某项欲求及这项欲求惯有的内容支配女性、控制女性——其背后就是对女性的憎恶与恐惧”(9)[英]亚当·朱克思:《扭曲的心理:为何男人憎恨女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正是“红颜祸水论”的心理根源。而“把女人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把反抗的女性都丑化成母夜叉”(10)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年,第49页。又为男性的“厌女”心理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种对女性标签化、符号化的分类,不仅体现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男性人物的态度上,更体现在女性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之中。
三、母女关系的特点与成因
分析隐藏在男性群侠背后的女性侠客成长史,能够窥探出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性别价值的特殊性。其中,最为重要的互动关系是母女关系,即“父一代”母亲的身份、情感观念与价值原则对“子一代”女性的自我认知与情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成长中的女性人物,需要同时面对来自男性世界与女性群体的双重窥视与规约,在内外交困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艰难的自我认知与身心抉择。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大体分为冷漠型、扭曲型与溺爱型三类。
(一)冷漠型
金庸武侠小说中母女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冷漠型关系模式。造成这种情感淡漠的主要原因是“父一代”的生身之母直接或间接地缺席“子一代”的养育。而这种直接或间接的退出使得“子一代”女性展现出不同的成长样态。一类是生身之母完全不在场,“子一代”女性被后续养育者过早地保护甚至隔绝起来,“塑造”出最受读者追捧的仙女、玉女类女性形象,如上文提到的香香公主和小龙女。这类女性被小说中的所有男性赋予了想象中的神圣地位。另一类是生身之母虽在世,但由于自身的冷漠与疏离,以保护的名义间接缺席“子一代”的成长,如《天龙八部》中王夫人与女儿王语嫣。王夫人不仅对外人心狠手辣,对女儿王语嫣也是冷漠到了极点。她严禁女儿出门或与家人以外的异性交流。她从不与女儿亲近,面对女儿的态度是“眼光如冷电,在女儿脸上扫了几下,半晌不语,跟着闭上了眼睛”。对女儿严声厉色,先是说:“反正你如今年纪大了,不用听我的话啦。”看女儿委屈,又说:“我是为你好。世界上坏人太多,杀不胜杀,你年纪轻轻,一个女孩儿家,还是别见坏人的好”。(11)金庸:《金庸作品集——天龙八部(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软硬兼施、恐吓威胁与虚伪关心并用,这种“父一代”的在场,非但没有为“子一代”提供任何保护与支持,反而造成了“子一代”的性格缺陷。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段誉痴恋下次次舍生忘死的保护,王语嫣闯荡江湖的过程一定比香香公主和小龙女要凶险不止百倍。
生身之母的直接或间接缺席造成了“子一代”女性人物的单一化与标签化而被归类为玉女或仙女。这类女性是武侠小说的重要符号象征,是江湖男权社会结构中符号化的“被看”对象。武侠小说中的四种视觉视角(男性人物的“看”、女性人物的“被看”、男性读者的“看”、女性读者的“看”)共同构成了小说内部与外部微妙的情感张力。小说中的男性对仙女的推崇,恰恰反映了大多数男性读者对女性表象化的偏爱,如《天龙八部》中被王夫人豢养在曼陀山庄中的那些“好看却水土不服、生性脆弱无比”的山茶花一般的女性,又何“美”之有?正如三毛发出的感慨:“香香公主不食人间烟火,又如何有血有肉有风情?化了省事。”(12)三毛:《不懂就算了——金庸百家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页。而在一次次被理想化的情感幻想之中,女性人物体现了其唯一的情感价值——引发读者阅读过程中的保护欲与崇高感。
(二)扭曲型
如果说冷漠型母女关系中,母亲是以保护的名义疏离、隔绝与女儿的情感互动,其冷漠背后还能感受到对“子一代”的些许关怀,那么站在道德制高点,以家庭权威来胁迫“子一代”的母女关系,则体现出金庸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反叛与犹疑。这一关系的典型代表为《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与周芷若这对“母女”。
周芷若从小丧父,孤苦无依,后被张三丰所救,被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收留。灭绝师太看似完美地履行了对周芷若的养育之职,但仔细辨识后便可发现,她的付出与爱护皆因周芷若有继承峨眉掌门的潜质。因此,在面临责任与情感抉择时,灭绝师太展现出自己的狠绝之态,逼迫周芷若发下重誓、斩断情丝,之后又将峨眉掌门之位传于她,将她一生的选择与自由全部断送。如果说前面这一系列举动尚有不得以之处,那么后面的阴谋诡计只能用厚颜无耻、枉为人师来形容:“为师要你接任掌门,实有深意。……我要你以美色相诱而取得宝刀宝剑,原非侠义之人份所当为。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且试想,假设倚天剑在那姓赵的女子手中,屠龙刀在谢逊恶贼手中,他这一干人同流合污,一旦刀剑相逢,取得郭大侠的兵法武功,以此荼毒苍生,天下不知将有多少人无辜丧生,妻离子散,而驱除鞑子的大业,更难上加难。芷若,我明知此事太难,实不忍要你担当,可是我辈一生学武,所为何事?芷若,我是为天下的百姓求你”。(13)金庸:《金庸作品集——倚天屠龙记(四)》,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1351-1352页。说到这里,灭绝师太突然双膝跪下,向周芷若拜倒。
周芷若虽然屡次为争取爱情与自由而努力抗争,但精神上对师父的依赖最终导致其反抗行为的失败。在放弃抗争之后,她为了取得屠龙刀和倚天剑,做出了不逊于灭绝师太的狠毒行动:“一行人来到了那无名小岛上,我毫不费力地便从赵敏身边摸到了那瓶‘十香软筋散’,悄悄下在汤里把大家迷晕,又到岸边把波斯船支走,又在珠儿脸上划下十几道血痕,将她和赵敏二人抛入大海。将屠龙刀和倚天剑搬到远处的山洞之中,再用剑削去自己半边头发,又忍痛削了只耳朵,吃了一点十香软筋散,回到原处睡倒。”(14)金庸:《金庸作品集——倚天屠龙记(四)》,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1353页。其后周芷若又陷害赵敏,在少林寺屠狮大会时陷害张无忌(伙同赵敏)害死武当七侠之一的莫声谷,并带领峨眉派弟子滥杀无辜,以至连旁观者(夏胄)见状皆不忍直视:“你峨眉弟子多行不义,玷辱祖师的名头。别说郭女侠,便灭绝师太当年,纵然心狠手辣,剑底也不诛无罪之人。似你这等滥杀无辜。你掌门竟然纵容不管。峨眉派今后还想在江湖上立足么?”(15)金庸:《金庸作品集——倚天屠龙记(四)》,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1299页。
周芷若在生死抉择时缺少侠女应有的光明磊落与敢作敢当,其原因之一是灭绝师太教导之失。生身之母的完全不在场,导致其基本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情感诉求、一切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方向,全部来源于师父灭绝师太的管教与江湖正统价值观的规约。原因之二是周芷若个人心性摇摆不定与价值观偏差。她将自己的一切纠结与矛盾、偏狭与过错都归结于师父临终前的逼迫与张无忌的忘恩负义。这类无法摆脱“父一代”庇佑的“子一代”女性侠客,终究无法逃离师父的精神束缚与外部的环境压力,只能黯然回归到既定人生轨道之中。灭绝师太想要凭借峨眉派的女性之力夺回倚天剑和屠龙刀,从而以武力称霸武林、驱除鞑虏;周芷若要用阴谋诡计和美貌伪善获得爱情和权力。这对师徒虽然遭遇不同,但其行为方式和精神理想并无二致,都是希望借用女性力量反抗与改变江湖世界的男权价值体系和侠义道德原则。而二人的失败,是女性侠客在行动和精神上一次次决然“出走”与无奈“回归”的最终印证,是对江湖男权秩序下女性抗争与臣服的最直接展现。
(三)溺爱型
金庸武侠小说中母女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是溺爱型模式。《神雕侠侣》中黄蓉与郭芙这对母女尤为典型。郭芙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身世显赫至极。其父是人人敬仰的一代大侠郭靖,其母是聪明绝顶的女侠黄蓉,祖父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桃花岛之主、“东邪”黄药师。郭芙的性情中缺少郭靖般耿直纯粹,没有黄蓉般剔透玲珑的心思,从小在父母和祖父的赫赫威名和娇惯溺爱下长大,因此缺乏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等方面基本的理解力与判断力。连平时对她骄纵袒护的母亲黄蓉,心里也承认“芙儿就是个草包”。(16)金庸:《金庸作品集——神雕侠侣(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398页。因为郭芙的莽撞与任性,迫使父母屡屡为她犯险,杨过也多次不顾安危地救她性命。郭芙却并无半分感恩之心,甚至对因自己一时任性斩断杨过手臂的大错也始终未有悔意。而黄蓉为使女儿逃脱郭靖的惩罚,运用自己的“小聪明”点了郭靖的穴道、私偷令牌,助女儿逃离襄阳。又私自行动营救小女儿郭襄,置自己的职责和襄阳城的安危于不顾,最后只能由父亲黄药师力挽狂澜、挂帅前来营救,才解了襄阳之危。
如果说,听闻小龙女失身的遭遇,郭芙“顿起轻蔑之心,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17)金庸:《金庸作品集——神雕侠侣(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833页。已经让人感到她的性情冷漠,那么面对砍人手臂之大错,她也无半分悔改,“郭芙含泪答应,好生后悔,实不该以一时之忿,斩断了杨过手臂,以致今日骨肉分离,独自冷清清地回桃花岛去,和一个瞎了眼的柯公公为伴,这样的日子只要想一想也就难挨了”。(18)金庸:《金庸作品集——神雕侠侣(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935页。这悔意没有半点分给杨过,只是因为不愿承受独自去桃花岛避难的冷清和孤独。真是让人感叹郭芙无情无义至极,又何谈“侠义”二字。而郭芙的脾气秉性与行事风格,与母亲黄蓉的骄纵放任脱不开关系。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在初遇郭靖时,面对王处一的受伤,黄蓉说:“那就让他残废好了,又不是你残废,我残废”。(19)金庸:《金庸作品集——射雕英雄传(一)》,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吓得郭靖大叫一声,脸有怒色。而后在密室疗伤,黄蓉想杀傻姑也让郭靖非常不悦。黄蓉绝顶聪明,看到郭靖的反应才懂得收敛本性,方能与郭靖长久相处。黄蓉只身闯荡江湖,最终收获了“完美”的爱情——与一代大侠郭靖结为伉俪之交,夫妻二人成为保家卫国的侠侣典范。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中完成了从人人鄙夷的妖女到众人敬仰的侠女的转变,成为被男权江湖世界接受与认可的女性代表人物。
曾昭旭在《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评价黄蓉是“清畅自然的生命”之代表。黄蓉的生命毫无委屈,但缺乏意义。(20)三毛、冯其庸等:《诸子百家看金庸I》,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的结合,不仅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更因郭靖坚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义,为黄蓉肆意挥洒的人生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意义,且完美契合了江湖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种种机缘促成了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中从个体情感到被江湖社会认可的双重圆满。而《神雕侠侣》中的黄蓉,“已不再是那么天真自然、灵动如水了,生命的消损与后天经验的累增使她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些黏滞、一些成见、一些私情”,(21)三毛、冯其庸等:《诸子百家看金庸I》,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她的“成见”体现在对杨过之父杨康仇怨至深而对杨过的处处提防与算计;她的“私情”体现在对郭芙的无限纵容至不辨是非的地步。郭芙斩断杨过手臂后,黄蓉为郭芙求情而与郭靖争辩说:“这件事,也不全是芙儿的过错。杨过和他师伯李莫愁两人抢了襄儿,要去绝情谷换取丹药,以解过儿身上之毒。芙儿要救妹子,恼怒之下,下手稍狠,也不能说罪不可恕”,“芙儿有什么不好了?她心疼妹子,出手重些,也是情理之常。倘若是我,杨过若不把女儿还我,我连他左臂也砍了下来”。(22)金庸:《金庸作品集——神雕侠侣(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925-926页。正是黄蓉的偏狭与自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多面的母亲和一个骄纵蛮横的女儿。而这对母女的互动,导致了家庭关系中不易察觉的情感裂痕,成为《神雕侠侣》中情节变化的间接动因。
在武侠小说中,想要写尽侠客的一生已为不易,而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将黄蓉这一女性人物的整个成长过程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描绘。《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的妖女身份使先入为主的男权江湖世界遭遇女性角色“非常规”地闯入与对抗,而黄蓉的郭靖之妻与丐帮帮主身份,则成为其女性地位转变与性别抗争的胜利表征。这体现出男性在既定江湖规范被破坏与被解构下的焦虑与恐慌。而《神雕侠侣》中,黄蓉舐犊情深之心情尚可理解,但枉顾守城之责且对“子一代”的不加管束,则成为她对道德理性冒犯和职责身份失位的佐证。婚后的黄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探索与怀疑精神,完全沦为男权江湖世界和家庭结构中传统母亲的完美代表。如果婚后的黄蓉只周璇于日常琐事而失去灵动洒脱,那么读者必定会大失所望;如果为人母却仍如少女时期肆意随性,则又与中国文化恪守的传统家庭观念与伦理道德要求不符,这实在是个左右为难的选择。面对这一难题,金庸从正面和侧面着手刻画黄蓉的性格变化。一方面从正面描写黄蓉在处理各种大小事务时的伶牙俐齿、妙计迭出,女侠风范不减当年;另一方面在处理家庭关系时,黄蓉又屡屡暗用心机、任性纵容,最后虽屡次化险为夷,但实则早已使家庭关系危机四伏。
究其原因,黄蓉“为国为民、守护襄阳”的侠者职责是因为与郭靖的结合而被间接赋予的,并非她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也不是她道德与理性的至高追求,一旦出现外力的干扰与纠缠,她的责任与信念必然存在被动摇与被左右的可能,甚至会有被颠覆的危险。而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写了黄蓉的被动摇,却没有让她遭遇更大的冲击与危险,其原因之一是黄蓉在《射雕英雄传》里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作者不能轻易打破读者对小说人物的想象期待与情感寄托,因此黄蓉的聪明才智总能让她屡次化险为夷;原因之二是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其本质是寄托大众对“侠”的乌托邦想象,是“写梦”的文学。正如陈平原在分析武侠小说与时代思潮关系时所阐述的:“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前卫,也不保守,基本态度是‘随大流’。”(2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页。因此,想要承担打破传统道德观念与颠覆文类叙事策略的重担,必然要承担被读者质疑甚至被否定的风险,这是武侠小说的文类局限,也是武侠小说作家不得不考量的创作原则问题。
四、女性价值的定位与修正
金庸笔下的女性侠客在与男性侠客的交往中多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体现了男性读者对女性抽象化、过度化的性别想象。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认定首先来自于其出身的正派与否。这种以出身论正邪的原则是江湖世界男性权利秩序的另一重佐证。女性人物虽然有独自闯荡江湖、脱离父母庇佑的行动尝试,但在遭遇重大磨难与人生选择时,其身边总不乏男性侠客的陪伴和保护。男性在江湖世界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些仙女或丑女、妖女或魔女的定义,“都是男人心目中的女人,是男人臆造的女人;是对男性不构成威胁的女人,是男人内在化狂想的外在投射。而女性读者无法共享这一男性‘恋物癖’式狂想”,(24)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都是正派人士们的主观臆想和“道德”评价。两代女性人物的自我定位、情感归宿和价值观念,始终无法脱离男性世界“侠义精神”的“拯救”与“被拯救”而独立存在。不必说香香公主和王语嫣这类不会武功的弱女子始终依靠男性侠客的保护;就是如小龙女般武功超绝、赵敏般机智聪慧、周芷若般心机深重的女性侠客,仍然逃不过作为男性侠客辅助与陪衬的命运安排。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结局,无非与爱人携手隐去,或独自情殇孤独终老。这类被塑造成用情至深、从一而终、无怨无悔的女性典范,从本质上迎合了大部分武侠小说读者认同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主流道德观念,但其对女性单一维度的情感表现与臆想性的过度美化,都成为江湖男权秩序抽象后的性别规范与合理化表征。
黄蓉这一侠女形象的成功塑造表现出金庸对武侠小说性别价值的多维度思考。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中多面而丰富的前半生,在《神雕侠侣》中从少女到母亲的身份转变后看似不完美的后半生,展现了她一生情感与经历的复杂变化,也使这位绝代女侠更具有真实灵动的人性魅力,为武侠小说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全新的探索与突破。女性人物的成长之路“正因其是子的故事,那么它必然关乎欲望、反叛、秩序与臣服”。(25)戴锦华:《镜城突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在金庸武侠小说母女关系之中,母亲的个人能力、个性气质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对“子一代”女性侠客的自我认知、女性价值定位起到了基础性与决定性的作用。母女关系关乎“子一代”与“父一代”直接或间接的权力博弈,关乎两代人之间个体身份危机下的渴望与挣扎、幻想与绝望。而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母女关系,恰恰缺少了因血脉传承与身份焦虑而产生的认同与反叛、游离与回归。
四、结语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大侠的成长既要经历武功的升级与加持,又要秉持侠义为重的江湖道义,女性人物作为其情感的重要寄托与辅助性存在,在其成长环境与未来生存的江湖空间之中,必然成为一个游弋者与离轨者,其选择与归宿也因世俗秩序与伦理要求而被限定与规范。介入新的社会空间与个人空间的女性人物,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爱情圆满,虽有个人化的挣扎与反抗,但最终选择仍然是对江湖规范的接纳与认可。孟悦、戴锦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客观地分析出古代俗文学中的侠女角色无法摆脱的性别悲剧与无奈归宿:“要么……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要么,则卸甲还家,穿我旧时裳,待字家中,成为某人妻,也可能成为崔莺莺、霍小玉或仲卿妻,一如杨门女将的雌伏。”(2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虽未能彻底改变武侠小说的性别传统与权力秩序,但她们通过个体对爱情的忠贞与奉献使旧有的江湖世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微妙位移与重新修正,如《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最后取代父亲成为日月神教的教主,并且将教中口号从“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改为“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从人人口中的妖女与小叫花成为江湖第一帮丐帮的帮主。《神雕侠侣》中的郭襄从秀美豪迈的“小东邪”到40岁大彻大悟、出家为尼并创立了峨眉派……。这些女性侠客的出场与其人生抉择的差异,为传统江湖的伦理规范和男权意识形态增加了新的变化。如《神雕侠侣》中“双剑合璧”剑法对武功境界提升的绝美比喻一般,金庸借武功阴阳合并后的威力无穷与男女侠客患难与共的爱情经历,对江湖世界既有的以男性为中心和以父权为秩序的性别价值标准进行了颇具建设性的调整与修正,为武侠小说的成长主题与性别关系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