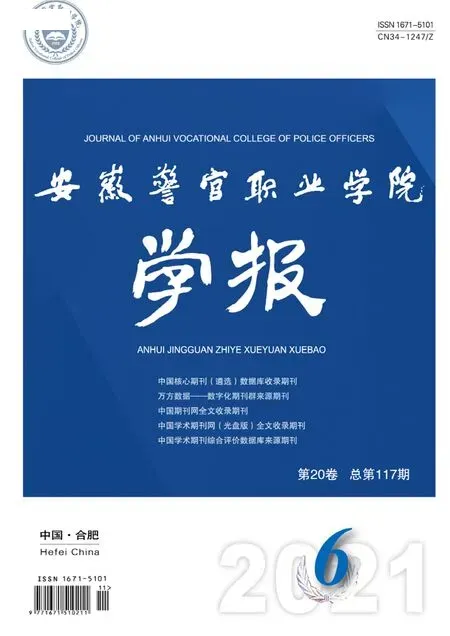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之我见
张 梅
(宿州市艺术研究所,安徽 宿州234000)
一、宿州戏曲异彩纷呈
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唱、念、做、打、歌舞演故事的综合艺术。宿州戏曲作为我国地方戏曲的一部分,历史悠久,成果辉煌,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影响深远,是宿州文化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宿州是戏曲大市,有五大剧种(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鼓戏、砀山四平调)均先后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有三个市直剧团、五个县(区)级剧团和两个民营剧团。可谓是剧团遍布城乡,各有演出阵地,剧种多样、各具特色、各显风流、多姿多彩、争奇斗艳,老调新曲唱满城乡,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着宿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江淮大地戏曲舞台上占有独特的优势位置,乃至在全国戏曲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牵魂摄魄的泗州戏
泗州戏是安徽省四大剧种(徽、黄、庐、泗)之一。解放前至上世纪50年代初称为“拉魂腔。”它起源于海州(今江苏省东海县)发展形成于宿州市泗县,与山东、江苏柳琴戏淮海戏有根脉相连的血缘关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泗州戏主要流行在皖北和黄淮海区域,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是一种典型的板腔体的戏曲剧种。
泗州戏的艺术特色集中表现在唱腔道白、压花场、音乐伴奏等方面。泗州戏以唱为主,而且是大段唱腔为主。如传统剧种《四告》中的皮秀.英,《休丁香》中的郭丁香,都是以唱功见长的演员来担当。泗州戏的曲调板式分两类:一类是慢板、一类是二行板;在唱腔上自由无拘,要求音乐伴奏跟着唱腔走,男唱腔常加入衬词拖后腔,女唱腔常在尾音处翻高八度拖一个小小的上翘的“尾巴”,明快野艳风情万种,“拉魂腔”也因此而得名。泗州戏的表演艺术是在说唱的基础上,吸收了淮北地方“花灯舞、小车舞、旱船舞、跑驴舞”等形式具有活泼、朴实、爽朗、豪放、泼辣的特点。“压花场”是泗州戏表演艺术的根本,分“单压”、“双压”两种,具有明快、爽朗、粗犷有力的鲜明艺术特色。
(二)刚柔相济的淮北梆子戏
淮北梆子戏是以演唱时用枣木梆子击节,唱词多带衬字、曲调吸收了淮北“灶王戏”坠子嗡、鼓书说唱、叫卖声、劳动号子等高亢激昂的唱腔音调而得名,被称为“高梆”、“大戏”、“沙河梆子”等。宿州淮北梆子戏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淮北梆子戏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唱腔结构、角色行当上,在唱腔结构上淮北梆子戏唱腔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行当则以红脸、黑脸为主要角色,唱腔慷慨激昂、高亢雄健,洋溢着浑厚豪放的阳刚之美,以前全用大本腔(真嗓)演唱,旦角尾音翻高,后来逐渐变化多用二本腔(假嗓)演唱,也有用大本腔(真嗓)吐字,二本腔(假嗓)拖腔的。其中“净”的发音则带沙音和炸音,使唱腔粗犷奔放,女声各行当则采用真假嗓相结合的方法来演唱,发音多用口腔共鸣,声音圆润,音域宽广。淮北梆子戏板式曲调丰富多样,突出的特点是花腔多、甩腔多,在唱法上有独特的风格韵味。在板式结构上虽与河南豫剧相近,但又有所不同,细品韵味具有明显的区别,各具所长。其主体板式是以慢板、流水、二八、飞板为基础,根据剧情内容需要进行转换,变化来构成演唱。淮北梆子戏在表演风格上动作粗犷、架势夸张、幅度较大;剧目方面,传统剧目有“四大征”“四大铡”“老十八本”“新十八本”等,现代戏剧目有“白毛女”、“小女婿”、“金沙碧浪”、“大树参天”、“金星寨”、“红色三少女”、“村官牛小乐”、“唐三彩”等。
(三)韵味醇厚的坠子戏
坠子戏起源于上世纪初的萧县民间,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萧县曲艺史明确记载了第一位坠子艺人韩教香(女)1914年在萧县黄口演出一炮打响,后与当地一史姓男子结婚,安家落户,从此开始发展形成了坠子戏。坠子戏是由曲艺坠子兴起,并逐步向戏曲坠子演变,其重要标志是“清音大杨琴班”“萧县道情班”的创建。新中国成立后,萧县人民政府在“萧县道情班”的基础上成立了“萧县曲艺实验剧团”,1958年底成立安徽省坠子剧团,1999年更名为安徽省宿州市坠子剧团至今未变。
坠子戏是带有鲜明宿州地方特色的剧种。从起源、发展、形成、流传100多年来,它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音乐,行当与表演,语言与唱词题材的乡土特性上。唱腔方面,坠子戏音乐体制为板腔体,唱腔优美动听,韵味醇厚;曲调板式多姿多彩,演唱时以本嗓发音,唱法有“大口”、“小口”之分。“大口”以庄(庄重)洪(洪亮)刚(刚劲)厚(浑厚)为其个性;“小口”则以俏(俏丽)巧(口巧)脆(脆甜)柔(柔美)为其特点。坠子戏的音乐伴奏是以大坠胡为主弦(主奏乐器),大坠胡形状类似小三弦,琴杆和弦轴均为紫红木制成,“山口”为骨质镶嵌,共鸣筒为椭圆形,蒙以梧桐板。中低音区音色苍劲浑厚、高音区清新细腻,与坠子戏人声说唱音色相近,这是坠子戏与众不同的独有的音乐艺术特色。在行当与表演方面,坠子戏的角色虽有生、旦、净、丑、行当之分,但在唱腔分行上并不十分严格,只是在唱法、润腔和使用衬字方面有些区别加以不同的处理即可。在坠子戏班里素有“戴上胡子演老头,拿掉髯口演小生,扎上裤脚演老妈,顶上花巾演小旦”之说的演员兼行习惯,在表演上偏重于写实、贴近生活、自然朴实、洒脱自如的表演风格。坠子戏的剧目题材地方化,语言、唱词方言化等也是其独特的艺术色彩。
(四)泥土芳香的淮北花鼓戏
淮北花鼓戏是在淮北地区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剧种,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淮北花鼓戏具有独特的地方艺术风格,在表演上“手、眼、身、法、步”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程式”,它可以形象而生动地把淮北人民群众豪爽、热情、奔放、好强的性格特点和善良、朴实、诙谐、乐观的心态刻画表演的活灵活现。花鼓戏大走场、大武场、盘鼓和压花场是淮北花鼓戏最具有代表性的“绝活”技艺。淮北花鼓戏的唱腔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歌言情”的艺术风格,充分展示了淮北地区劳动妇民“哭言泣语”的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彰显了亲切感人的地方特色,同时还挖掘吸纳很多民间小调民歌的营养原素,融合成宿州调、口子调、浍北调、货郎鼓、寒板、颠板等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唱腔曲调。这些曲调唱腔源于民间,挖于本土,群众喜爱,耳熟能详,随口能唱,是极具淮北乡土特色而还未被完全开掘出来的“原生态”的艺术,是醉人的芳香沃土孕育出来的艺术奇葩。
(五)砀山“花鼓戏”——四平调
砀山四平调戏曲发源于砀山县周寨镇,是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边区民间的一种花鼓戏演变而成,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由于四平调是民间花鼓戏演变而后又吸收了评剧、京剧、梆子等剧种诸多原素融合而成,故被人们称为“四拼调”,后又因该剧演唱四句一平、四平八稳又改称为“四平调”一直延续至今。“四平调”戏曲剧种形成以后,不仅改变名称也逐步走上了规范之路,开始了剧目、表演、舞台、服装、演出道具的更新创造,向其它剧种学习看齐,应有尽有。从当初的三小戏(小生小旦 小丑)逐步改成“生、旦、净、末 丑”行当,既演小戏,也演大戏和连台本戏。在表演艺术方面,既保留了原来花鼓戏载歌载舞、说唱结合、生动活泼的优良特点,也 开始重唱取胜。从表演程式、服装、道具乃至化妆脸谱逐步向京剧和其它地方剧种靠近。因为四平调与二黄声腔很接近,所以也叫平板二黄。四平调的演唱语言大都从民间提炼出来,比较通俗易懂,乡土味很浓厚,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色。
根植宿州沃土的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鼓戏和砀山四平调戏堪称宿州“五朵金花”。历经风雨洗礼,昂然挺拔,生生不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色泽迴异,异彩纷呈,相辅相成,共同装扮着宿州大地的美好春天。
二、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状况
宿州戏曲是我国地方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果辉煌。其主要剧种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鼓戏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古老宿州的文化内涵中,宿州地方戏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但由于古代历史中戏剧行当难入正史,戏剧演员被视为“戏子”,地位低下。志书文字对其活动记载较少,因此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而是时隐时现的穿行在宿州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研究发现,这几个“时隐时现”的历史节点,恰逢中国戏曲处于萌芽、形成、繁荣的三个关键阶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宿州戏曲并没有姗姗来迟,而是始终踏着中国戏曲这个母体文化的节拍迤逦前行。翻阅宿州史册,代表这几个珍贵节点的应该是:汉画像石中的《百戏乐舞图》《双人建鼓图》《九女舞蹈图》(阅自宿州博物馆)以及《资治通鉴》《通鉴记事本末》里记载的“唐代庞勋兵变在泗州闹戏场事件”。明清时期,宿州地方戏曲孕育成型,中国戏曲进入了大繁荣、大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优秀精典的传奇剧目激剧增多,如《牡丹亭》《浣纱记》《鸣凤记》《红梅记》以及连台本戏《西游》《三国》《水浒》等,著名剧作家也大量涌现,如汤显祖、梁辰鱼、王玉峰、周朝俊等。地方戏曲风生水起不断涌现,据史料载,1956年全国第一次戏曲剧目统计时,统计出全国传统剧目有51867个,属清代地方戏的剧目剧本上万个,其中就包括宿州地方戏曲主要剧种的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鼓戏的不少剧目。
安徽是明清时期中国戏曲的摇篮之一。“徽班进京”以后,安徽各地方戏曲出现了空前发展的局面。目前,宿州地方戏曲的起源、形成、发展,有史可查,戏曲传承可考的史段也就是从清代末期开始。其中就包括以民间歌舞和说唱艺术的宿州地方戏曲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淮北花鼓戏和砀山四平调戏。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宿州地区广大戏曲工作者创作排演了军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戏,为弘扬爱国主义、鼓舞军民斗志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史段的戏曲发展人们忘记不了曾经战斗在宿州大地的彭雪枫将军,也可以说是由他创建的“拂晓剧团”带动了宿州地区戏曲演艺人员积极投入到了抗日宣传工作中去,影响巨大。拂晓剧团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总方针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一脉相连、意义相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政策为文艺界带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也为宿州地方戏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宿州地方戏曲的专业剧团相继成立,由农村民间“草台”班社逐步进入城市剧场,开始进行规范化的专业演出。这一巨大嬗变,也为宿州地方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创造了有利条件。
宿州地方戏曲的主要剧种都是从乡土民间孕育、形成再到城市发展,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发展到今天,也是坎坷无限,艰难多多。在解放前,戏曲艺人地位低下,愿意学戏的大都是家庭贫困儿童或无依无靠的孤儿,根本上不起学没文化,传艺教戏都是口对口教唱、手把手的教练。如坠子戏早期表演艺术家“三大元”(刘元芝、陈元孝、陈元同)在表演和唱法上各有“绝活”、各具特色,在向弟子传授技艺时,无一不是口传身教方式。以刘元芝之为例,刘元芝演唱坠子戏以“喷口”见长,特点是先吐字、后拖腔、讲究吐字清晰、字字珠玑、运腔自如,韵味醇厚。她对她的关门弟子、著名坠子戏表演艺术家、唯一的坠子戏国家级传承人朱月梅就是这么“口对口”“手把手”教出来的。直到后来坠子戏发展到音乐谱系传承之后,朱月梅老师的亲传弟子、著名坠子戏表演艺术家张莉才能按谱教唱和到练功房教习基本功。泗州戏早期表演艺术家周凤云,梆子戏早期表演艺术家张福兰、朱琴,花鼓戏的老艺术家牛正印等大都是用这种原始方式传授弟子的。
在传承方面,各个剧种按照各自的艺术特点,形成不同的传承风格样式,即使同一剧种,也有不同的流派。以坠子戏为例,可见一斑。坠子戏早期表演艺术家“三大元”(刘元芝、陈元孝、陈元萍)在唱法上就有“大口”、“小口”和“喷口”之分。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既不失坠子戏韵味醇厚,让人听得懂,领悟快,品得透。她的后期传人朱月梅、中期的张莉、李连民、吴亚莉、王芳等坠子戏表演艺术家都以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吐字清晰而见长。泗洲戏早期的表演艺术家周凤云、李宝琴,中期的荣爱坡、陈若梅、李书君、陶万侠、张玉龙、张丹、孙立海,当代的王浩、戴兵、孙梅、孙杜鹃、张亭等和花鼓戏的牛正印、吕金玲、吴月玲等艺术家都有不同艺术绝活,形成不同艺术流派,各领风骚。梆子戏早期的表演艺术家朱琴、张福兰、韩宝珠、郭守恒、张晓东等既有梆子戏大气磅礴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吐字发声运腔方法的不同,形成各自流派,各有传人,共同扮美宿州地方戏剧百花园,使其芳香四溢。泗州戏、坠子戏、淮北梆子戏由于土生土长在宿州沃土,扎根群众,服务群众,基础厚实,影响深远,都创造了不同的业绩和辉煌。早在上世纪50年代,泗州戏剧团就创作演出了生活小戏《拾棉花》,包括80年代创作演出的《摔猪盆》、90年代的《八月桂》等经典保留剧目。著名泗州戏表演艺术家周凤云曾应邀走进怀仁堂演出,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摔猪盆》参加省文艺调演,获创作一等奖,荣爱坡、苏婉琴获表演二等奖,同年五月,再次进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演出三等奖等殊荣。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本土主创人员创作演出的《秋月惶惶》《母亲的嘱托》《送羊草》等脍炙人口具有代表性的好剧目,不仅深受本地群众喜爱,在省级舞台、华东六省一市比赛乃至进京演出和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演播,都产生很大的反响并获得一致好评。
坠子戏剧团人才济济,好剧不断。早在解放初期,创作演出的坠子戏《小菜园》《白云五女》便在省级剧团上一炮打响,誉满江淮。进入新世纪以后,创作演出的《故土情深》《歪脖子树上落凤凰》,连续两届荣获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6年创作演出的《少年闵子骞》在省艺术节新剧目展演后,应邀代表安徽省赴宁夏进行文化交流演出获得好评。上世纪在宿州大地广大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种地荒了田也要去看“三大元”(坠子戏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元、陈元孝、陈元萍),“卖了牛不耕地,也要去听坠子戏”。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对坠子戏的热爱程度。
淮北梆子戏早期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福兰,早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以创作演出的《红色三少女》中的“三妮”少女形象在省会合肥江淮大戏院光彩亮相,好评如潮。她的亲授弟子和传人、当代梆子戏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晓东凭借《大树参天》中大树婶和《穆桂英下山》中穆桂英的精美演技,夺得了皖北地区仅有的一朵“梅花奖”。梆子戏的领军人物、著名梆子戏表演艺术家朱琴塑造了不同类型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被誉为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生”。此后的营辉、李玉萍、李新志、张凤云、刘玉玲、李亚军等梆子戏著名演员,共同创作演出了《平安是福》《春风化雨》《医者仁心》等精彩剧目同样创造了辉煌。
淮北花鼓戏著名表演艺术家牛正印、李孔兰、吕金玲、吴月玲等于上世纪60年代共同创作演出的《新人骏马》《姐妹易嫁》《六月雨》《王小赶脚》等唱响淮北大地。70年代初,《新人骏马》《六月雨》《出差记》等小戏奉调进京演出获得成功。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演出了《阳光下的召唤》。2021年创作演出省级孵化剧目《守望者》大放光彩,重现淮北花鼓戏的艺术魅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的娱乐形式受到多元化冲击,戏剧演出市场越来越不景气,宿州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自然也受到严重的阻碍和影响。由于演出收入不高,工资报酬没有保障,不少演职员工改行或退出另谋职业,一些老艺人相继退休或逝世,新学员招收不进来,一度造成青黄不接,行当断层,演出困难,收入骤减,无以为计,淮北花鼓戏剧团曾几年都演不成戏,宿州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陷入低谷。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扶持戏曲艺术的政策和举措,加上泗州戏、坠子戏、花鼓戏、淮北梆子戏申报国家级“非遗”相继成功,这无疑给宿州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各剧团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广大戏曲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一系列讲话精神鼓舞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目标,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创作演出了《八张村笑声》《少年闵子骞》等一大批新剧目,并深入农村下基层,送戏下乡进校园,进行巡回演出,扩大演出市场,重新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在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各剧团都注重以老带新,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注重培养和力推新人,一些颇有造诣的老艺人,甘当绿叶衬红花,让青年演员多担当主演,多锻炼,多实践,使一大批青年演员很快有了进步并且崭露头角。如李琳洁、戴兵、王浩、魏董、孙杜鹃等戏曲艺术新秀在不同剧目中担纲主要角色,闪亮登场,一鸣惊人,彰显了宿州地方戏曲后继有人、前景无限。此外,宿州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还为宿州地方戏曲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支持帮助各剧团建立演艺人才培训基地,招收一批具有戏剧艺术天赋的少年儿童,聘请当地有很深艺术造诣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路长、陈若梅、陶万侠、朱月梅、吕金玲、孙梅等担任教师。他们树德授艺、言传身教,从练基本功开始,经过几年的教学培训,现已蓓蕾初绽,生机盎然,不少艺术新秀开始闪亮登场,也为未来宿州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希望。
三、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和发展存在的问题
宿州地方戏曲在传承和发展上呈现出逐渐转好和向上的形势,但也存在诸多的障碍和瓶颈。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一)精品剧少
长期以来,宿州地方戏曲剧团创作演出不少剧目,如《雪之夜》《平安是福》《唐三彩》《医者仁心》《羊村欢歌》《文明乡村》《书香门第》《万家灯火》《守望者》等,其他剧团如萧县梆子戏剧团创作演出的《布包书记》,灵璧县泗州戏剧团创作演出的《白芷花开》《半条棉被》,泗县泗州戏剧团创作演出的《镇长嫁女》《红色催款单》,砀山四平调剧团创作演出的《爱在梨花湾》等,但总体看来,一般性剧目居多,真正能上得去、打得响、留得住、传得远的好剧目屈指可数,精品剧目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是获省级,甚至文化部立项、财政扶持的剧目,仍需要继续打磨,才能成为精品剧目。
(二)资金不足
剧团改企之后,基本处于求生存状态。除了财政按比例拨款扶持外,剧团收入来源主要靠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的政府补贴和“非遗”保护资金补助。勉强可以维持发工资、交保险等一些基本开支,根本就拿不出多余的钱去进行艺术创新、剧目加工提高和其他有关活动建设之用。即使申报项目成功,其扶持资金除了支付编导、作曲、舞美的劳务费、购置服装、道具、发放演职员工排练补贴外,剧团本身所剩无几。单位平时办公开支经费没有保障,只有到市场艰难找演出,来补贴一些。
(三)人才匮乏
剧团转企改制之后,由于演艺人员的收入不高,老一辈艺术家又相继退休,有的剧团行当不齐,人员断层缺乏演员,各个剧团都存在本团演员不能满足现在所排剧目的需要,便从别的剧团借调演员,出现了剧种不同,专业性不强的情况。比如:坠子戏、泗州戏演员唱梆子戏、花鼓戏,而梆子戏、花鼓戏的演员又要帮忙唱泗州戏获者唱花鼓戏等,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剧种的特色,对剧种的传承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怠于作为
个别剧团只管等靠要,不知自己去努力创新、创造和创收。能争取到上级立项拨款就排戏,就演出;没钱排戏、没演出就放假休息,不去主动作为,靠自己多创收来改变现状,闯出一片新天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结果是越等越靠,越靠越没出路。
(五)青黄不接
各剧种的存续,离不开“传帮带”。现在是老艺人自然减员在加剧,有些老艺术家年岁已高,身体行动不便,而新生代尚未完全接替或到位,加之缺乏传承平台,各剧种非遗传承人也未能有效发挥传承作用。
四、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和发展的路径思考
(一)加强领导创新局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领导,严把政治关,使地方戏曲始终按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传承和发展,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尊重艺术规律,充分发扬民主,为戏曲艺术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环境,让广大地方戏曲工作者能甩开膀子加油干,努力开创宿州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新局面。
(二)多出好剧多演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系列讲话精神,执行落实国家颁发的关于传承与保护戏曲的政策措施。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多出好剧本,认真做细做好项目申报,尽量争取财政资金的扶持,尽量争取多演出,除了政府买单演出场次,要主动出去找演出,除了政府安排的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演出以外,应该积极主动的找演出,如参加地方庙会、祝寿、喜庆、行业晚会的演出等,要千方百计增加收入。
(三)特色发展葆青春
要守正创新,吐故纳新,吸取符合本剧种特质的艺术精华,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新内涵,既保持住本剧种特色优势不变,又不断使自身艺术风貌永葆青春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出更加适合群众欣赏水平的现代剧目,只有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才能使宿州地方戏曲立得住,走得远,保持长青不败。
(四)以师带徒传薪火
戏曲是综合艺术,要培育自己的编剧、导演、作曲、舞美人才,戏曲更是“角”的艺术。一个剧种,一个剧团要有两三个“打得响”“过得硬”的好“角色”和领军人物才能带得动、走的远;要提倡“崇德尚艺”、“德艺双馨”,乐于奉献,健康成长;要提倡“以老带新”,“以师带徒”,“尊师重教”,把好的传统传下去,把技艺绝活接下来,才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五)培养观众接地气
地方戏曲,顾名思义,它是富有某一地域特色的艺术产物。它像这里土生土长的儿女一样,血脉相连,永远不能脱离这里的乡土。因此,地方戏曲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民众,汇演交流学习提高很重要,但是长期更多面对的还是当地老百姓,剧目创作内容、演出形式和服务方式都要尽可能符合当地群众的需要,要做到“接地气”。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扎根人民,服务基层,要尽量争取多到农村社区去演出,新创剧目要精益求精,传统剧目要古戏新排,要赋予新的内涵,不能老戏老演,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这样才能既留住老观众,又不断吸引扩大新的观众群体,使他们成为新时代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保护和支持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