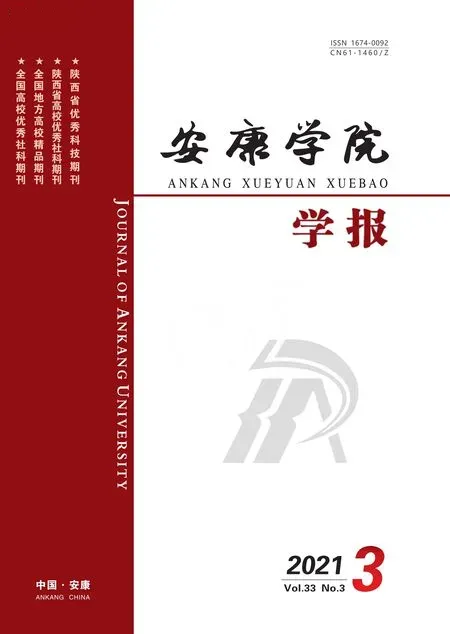落为“他者”的故国
——形象学视域下《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形象解读
张琛雯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追风筝的人》是卡勒德·胡赛尼的处女作。该作品自2003年6月在美国出版后,曾在美国《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等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榜首,并迅速被翻译成了50多种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与2007年出版的《灿烂千阳》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胡赛尼热”。胡赛尼也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正如诸多书评所说,这部小说以阿米尔和哈桑的友谊为脉络,是对阿富汗人的成长与创伤、背叛与救赎的深重描绘,更是对阿富汗及其历史文化的悲悯书写。在新千年,阿富汗成了全球政治焦点,但其实际上仍是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的视觉盲点。而作者以其细腻真实的笔触、扣人心弦的情节,揭开面纱,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既残忍又温情的阿富汗形象。
作为美籍阿富汗裔的作家,胡赛尼所勾勒出的阿富汗形象具有双重性,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文化结构。本文试图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研究理论与方法,以《追风筝的人》这一文本为中心,对胡赛尼笔下多维立体的阿富汗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结构进行解读与剖析。
一、镜之彼端:阿富汗形象的双重表述
《追风筝的人》是“对阿富汗人与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1]评论2,“这本书的力量来自作者让文化在书页上栩栩如生的功力”[1]评论3。如果说之前人们对阿富汗的印象是一幅被火舌燎蚀的灰色意象画,那么读过胡赛尼的书写之后,这幅硝烟弥漫的苦难灰色里,一抹温润丰富的亮色渐渐清晰了起来。胡赛尼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立起来的阿富汗,他笔下的阿富汗具备双重色彩:既是意识形态化的人间地狱,又是乌托邦化的美好梦乡。
随着主人公阿米尔人生历程的坎坷推进,胡赛尼将一个专制落后、等级严苛的阿富汗血淋淋地揭露在读者眼前。这一形象贯穿于民族、宗教、性别等各个领域。
在民族领域,阿富汗是民族不平等问题突出的国家。阿米尔和哈桑虽有胜似亲情的友情,但这种友情却因为民族的不平等而不对等,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正如阿米尔的父亲“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一样,阿米尔在被阿塞夫质问怎么能将哈桑当朋友时,几乎冲口说出“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民族的隔阂一代代顺延,在孩子们心里深深扎根,使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走上迥异的道路。作为“优越”一方的普什图人,阿塞夫对哈扎拉族人表露出赤裸裸的歧视,他以高昂的“正义”姿态屡次对哈桑施加暴行,坚信种族优劣论,后加入塔利班致力于种族清洗;阿米尔虽不像阿塞夫一般偏激,但也因为民族问题无法正视和哈扎拉人的友谊,背叛了一直为他追风筝的哈桑,逃至美国;而作为“卑贱”一方的哈扎拉人,哈桑已被无形奴化,他的善良真挚与卑微的忠诚掺杂在一起,最终在捍卫主人家利益时被民族歧视推向死亡。
在宗教领域,阿富汗的宗教极端政治化将民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阿富汗是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但在20世纪70年代,宗教倾向于极端政治化。“‘宗教政治化’就是以宗教作为手段,利用被曲解的宗教教义掩盖和庇护丑恶行为,最终实现统治社会、控制人民的政治目的。”[2]24当阿米尔2001年回到阿富汗时,喀布尔在战乱的摧残与宗教极端政治化的控制下已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曾经街道散发着的烤羊羔味已被熏得人眼泪直流的柴油味代替,昔日的街巷屋舍已成为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无数裹着长袍的妇女抱着孩子跪在街头巷尾乞讨,高呼着“真主至尊”的塔利班开车游走着以寻找可能激怒他们的人来发泄暴戾;恤孤院的孩子们衣衫褴褛食物短缺难以生存还面临着被贩卖的风险;无辜的恋人被宣判为通奸被石头投掷至死仿佛只是球赛中场休息的例行戏码……在塔利班极端宗教主义的统治下,阿富汗像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黑暗国度。
这种黑暗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加深重残酷。在性别领域,阿富汗是个男权国家,具有双重标准。男性作为第一性其地位不可撼动,女性作为第二性则被男性牢牢控制着,不具备话语权,甚至处于隐匿状态而未曾上场。雅米拉就是茫茫阿富汗妇女的一员,被男性牢牢压制而隐匿在家庭中。她的个性完全被抑制,有唱歌天赋的她自从嫁人后就被丈夫呵斥永远不得在人前歌唱,她的天赋展露被定义为失态。其女儿索拉雅则因为年少一时失足而被社会流言吞没,永远被异样的眼光看待,即使终于结婚得到了好归宿,也仍被亲友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视作“不洁”的反面案例被言说。目睹了岳母和妻子的境况,阿米尔明确意识到性别之于阿富汗是一场大而不当的博彩,仅仅因为身为男性就可以占尽便宜。
战争的破坏、宗教控制的威慑及民族和性别的歧视,胡赛尼笔下的阿富汗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是一个可怖的梦魇,但他的描述不止于此——灰烬之下掩埋着燃之不去的善美温情,这个国家仍是阿富汗人乌托邦式的梦乡。
阿富汗的动荡不安产生了大量难民,很多难民迁居国外成为移民者。借着移民者的书写,阿富汗和美动人的一面跃然纸上。
《追风筝的人》中的移民者可以分为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两类。第一代移民者是以阿米尔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阿富汗人,他们心目中的阿富汗虽不算尽善尽美,但也是无与伦比的。美国的一切似乎都比不上阿富汗:在物质上,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树林和原野永远不够多;在精神上,人永远缺少真情,而这一点是第一代移民者最无法忍受的。在美国加州,在光顾了两年的店铺买水果开支票时,却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这一点让阿米尔的父亲大发雷霆。要知道,在阿富汗喀布尔,人们相互熟识、相互信赖,儿童尚且可以用树枝当信用卡记账。对阿米尔的父亲而言,美国是个用来哀悼过去的地方,是个用来怀念美好故国的地方。
对于阿米尔而言,美国本是个用来埋葬往事的地方。作为第二代移民的代表,阿米尔一方面能看清阿富汗的专制落后,他眼中的阿富汗不似父亲的一般无瑕而是偏向意识形态化的;但另一方面,通过走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也看到了阿富汗闪闪发亮的温暖和善。阿富汗是个友善的国家,阿富汗人珍视客人。即使在种种灾难折磨下,生活极度艰难,食物极度匮乏,瓦希德也尽力招待着阿米尔,阿米尔吃上了面包配蔬菜汤,瓦希德夫妇连同孩子们却默默挨饿着,“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在绝境之中,阿富汗人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亏待客人。阿富汗是个温情的国家,阿富汗人重视家人。名誉和尊严是阿富汗人的骄傲,但为了自己和家人能活下去,他们甘愿放弃这些。残疾的男人抱着自己的义肢讨价还价,妇女和老人低下身姿沿街乞讨,青涩的孩子揣着所谓的性感图片紧张贩卖,他们只想为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多地换来吃食。阿富汗还是一个坚韧的国家,重压之下他们没有选择,但放下骄傲不代表舍弃底线。阿米尔和随行者法里德发现恤孤院卖孩子时,法里德大怒而险些杀害负责人察曼。法里德作为底层阿富汗人依然坚守人性的底线,但察曼也并非丧尽天良的恶徒。察曼用尽毕生积蓄来维持恤孤院,而不是独自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国度,只为给孩子们保留最后的栖身之所,他忍气吞声,用卖掉少数孩子的脏钱来维持多数孩子的生的希望。
友善、温情、坚韧,在文本中,即使经过第二代移民者的理性审视,阿富汗依然是一个值得阿富汗人怀想,值得全球人悲悯的乌托邦式的有情国度。
二、文本之外:双重文化语境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他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3]157,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3]154。异国形象不是注视者直接描摹出来的真实异国,而是注视者想象建构出来的镜子彼端的幻象。注视者身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特定的文化语境影响,因而其建构出来的异国形象是个人的想象物,也是其所属社会的集体想象物。
《追风筝的人》里胡赛尼描写的阿富汗形象看似是对现实阿富汗的客观反映,其实是注视者胡赛尼对自身文化语境的主观表达(representation)。因胡赛尼作为美籍阿富汗裔流散作家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受双重文化语境影响,他表述的阿富汗形象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
胡赛尼是美国作家,《追风筝的人》是用英文写成的,其构建的阿富汗形象在美国文化语境下产生。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胡赛尼一家无法回国,其父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举家移民到美国,胡赛尼更改国籍开始了他的美国生活。他的经历和文本中阿米尔的经历非常相似,《追风筝的人》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余年,胡赛尼自然受美国文化环境的影响,他的观念在美国文化语境影响下生成。
相对阿富汗民族林立、等级严苛的文化境况而言,美国的民族文化氛围较为宽松。美国是世界族裔的大熔炉,由众多离开族裔的人共同建立,欧洲白种人、亚洲黄种人、非洲黑人共存于美国土地上,共同构成美国族裔文化。美国的族裔歧视的现象虽不可说全然不存在,但不同族裔的地位和待遇不会与阿富汗的一样有天壤之别。移居美国的胡赛尼和其他族裔的人境况相似,他接受美国高等教育,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系毕业,取得了行医执照后成了一位内科医生。在族裔相对平等的语境下注视阿富汗,阿富汗族裔的不平等境况越发彰显:族裔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第一大民族普什图族占据统治地位,是贵族,是主人;第三大民族哈扎拉族却因其蒙古血统和信仰什叶派而被压迫至社会底层,是奴隶,是仆人。位居低等的民族备受歧视和损害,这种歧视以集体无意识的惯有思维形式存在着,渗透在整个阿富汗民族血液中。
宗教是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较之于阿富汗,美国的宗教文化更自由。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但人们也有选择其他信仰的权利和自由。而虽然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皇统治社会,禁欲思想控制伦理环境,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和近现代人道主义等思想的反拨下,现代基督教总体是提倡以人为核心的。人们受宗教原罪思想指引,善于反思和自视。胡赛尼受美国基督教文化语境影响,将“赎罪”意识作为小说主题使之贯穿于文本之中。在宗教自由化、人性化的语境下注视阿富汗,其宗教的极端化、政治化无处遁形。信主独一原则作为阿富汗伊斯兰教的核心神学价值,要求信奉者“摒弃一切欲望,净化灵魂,绝对信仰安拉、顺从安拉、接近安拉”[2]13,这是信徒人生的最终目的,也是道德的核心内容。宗教教义富于控制力,塔利班遂将宗教与政治高度结合起来,以便于控制和奴役阿富汗人。
与民族与宗教文化相似,性别之差在美国远没有达到分属两个等级的程度。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女性创造了大量能够胜任的岗位,为女性地位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女权运动的开展分析了男女两性的境况,为女性地位上升提供了精神支持。美国的女性不再是被圈养在闺阁中的一方,她们能进入社会,和男性一样选择职业,发出一定声音。以美国性别相对平等的语境反观阿富汗,其性别鸿沟之深显而易见。雅米拉和索拉雅都是移居到美国的阿富汗女性,她们的境况尚且不佳,那么,还在阿富汗国内的女性的处境就更加严峻。即使移居到美国,阿富汗的性别歧视状况仍然未曾改变。在阿富汗,“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4]。
美国文化语境中的阿富汗被想象为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它的民族、宗教、性别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状况都不容乐观,胡赛尼描述的阿富汗也因此带上了美国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子。但由于胡赛尼出生在阿富汗,在喀布尔度过了童年时光,十年的光阴让胡赛尼与阿富汗建立了深深的羁绊,阿富汗的民族文化记忆牢牢扎根于胡赛尼的意识深处。
虽然阿富汗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可相提并论,但移居到美国的阿富汗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提升。相反,经过坎坷的移民,许多原本有高贵地位、富余家产、体面工作的阿富汗人到了美国变得一无所有。阿米尔父亲的状况就是如此,为了不靠救济金而在美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他只能进入加油站没日没夜地工作。两国生活状况的云泥之别让阿米尔的父亲像个再婚的鳏夫,总忍不住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阿富汗,阿富汗的形象就在与美国的反复对比中被美化了。
见微知著,文本中阿米尔父亲的感受代表着现实中阿富汗移居者们的普遍感受,胡赛尼心中的阿富汗受父辈与童年记忆影响,也保持着特有的鲜活与温度,与阿富汗文化语境联系甚密。胡赛尼是美国作家,却也是阿富汗作家。阿富汗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给他留下了美好记忆的故国,仅仅“追风筝”这一项古老的游戏就能使他的思绪翻山跨海地回到阿富汗。这项游戏需要两个孩子合作,一个孩子负责将对手们的风筝割断,另一个则追逐风筝将战利品带回,但在胡赛尼的小说中,追风筝不仅仅是个游戏——它关乎竞争者的骄傲,关乎合作者的友谊,关乎爱的追逐与救赎。虽然民族、宗教矛盾使不同的族群分属主仆两端,但这并不能阻止民众的真挚感情的生发,“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改变得了。没有。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人的感情不是编程,国的形象不是版刻,阿富汗不是意识形态化形象能建构完全的,那违背了现实,也违背了胡赛尼的文化情感根基。阿富汗文化环境对胡赛尼影响至深,其民族文化即便跨越时空距离仍是胡赛尼心底的情感归宿。他仍旧感怀故国,才在偶然看到塔利班禁止市民放风筝的报道后写下这篇关于阿富汗特有的风筝的故事。受这样文化语境影响,胡赛尼构建的阿富汗形象融合了阿富汗社会集体想象,于是冲破了意识形态而带有乌托邦化的追忆与怀想。
胡赛尼的身份带有混杂性,他既熟悉美国文化的自由平等,又深谙阿富汗文化的善美温情,兼具多元文化视域。两个国家铸就了胡赛尼的双重文化身份,两种文化语境生成了阿富汗的双重形象。夹杂在双重文化语境之间,胡赛尼所想象建构的阿富汗形象必然不会成为被纯粹意识形态笼罩的黑暗国度,也不会成为被一味乌托邦化的桃源梦乡。跳出单一文化语境,糅合了美国意识形态化想象和阿富汗乌托邦化想象的阿富汗成了一个更经得起审视与品味的多维立体形象。
三、西方权力秩序及跨文化间性的可能
异国形象是注视者的想象物,也是注视者所属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表述。“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5]异国形象源自注视者及其社会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注视者一方用来自视的镜像中的他者。异国形象本质上是注视者自身恐惧与欲望的投射物,表现的永远是本国形象。“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6]前言1胡赛尼笔下的阿富汗是镜子彼端的幻象,镜子的此端指向美国。
胡赛尼描写的阿富汗是在塔利班宗教极端政治化专制统治下国家动荡不安、民众朝不保夕的阿富汗,是在严峻的民族对立与歧视问题中族群等级分明、弱者遭遇奴役的阿富汗,是在男权占领统治下两性地位不等、女性备受压迫的阿富汗。从表面上看,对阿富汗的意识形态化书写是针对现实阿富汗存在的诸如国家落后、宗教专制、民族歧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进行批判,期望其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和改善;但掘开表层,建构阿富汗形象的意义不止于此。落后的对面是进步,专制的对面是民主,歧视的对面是平等,奴役的对面是自由——镜子彼端意识形态化的阿富汗照出的是此端乌托邦化的美国。在曼海姆社会学知识意义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否定的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指向现在,其功能是通过否定他者向心地整合巩固自我权力,维护自我的现实秩序。在阿富汗的形象建构中,美国的现状被肯定,权力被整合,进步、民主、平等、自由形象的乌托邦化自我认同也就达成了。
相应的,乌托邦作为一种肯定的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指向未来,其功能是通过肯定他者离心地颠覆自我权力,否定并超越自我的现实秩序。镜子彼端乌托邦化的阿富汗照出的是此端意识形态化的美国。通过肯定在深重灾难中依然保持着美丽、友善、温情与坚韧的阿富汗形象,美国社会在资本主义理性制度中的倾向利益、冷漠生硬被揭示出来。物质的资本主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将人们的幸福感一定程度上同化了,人们的幸福之一是拥有财富和利益。为了儿子的将来,父亲舍弃了自己心仪的生活方式辛劳工作,将车作为体面送给儿子;严谨规范的制度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一切按规则行事,但却抹去了个体应有的温度,社会上似乎不存在相互完全熟悉、信任的人,“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世界被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两极:西方与非西方(东方)。西方将东方构筑为自我认同所需的他者,在进步大叙事中否古肯今,以今优古,结束了时间上“古今之争”;在自由大叙事中否东肯西,以西优东,结束了空间上的“东西之争”。两种叙事共同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结构以西方为权力中心,构建的是一种以进步、自由为现代性价值核心的知识秩序和价值等级秩序。置身于这样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现代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认同都不自觉地向西方或非西方站队,将自身归入东方或西方、专制或自由、停滞或进步、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
“西方”指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基督教地区[6]12。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定位是典型的西方。在当代受美国文化语境影响的胡赛尼无法脱离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在以西方为权力中心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他不自觉地将美国划为西方,将阿富汗划为东方,在二者比较中对美国及其背后的西方自我进行想象性认同。他所构建的阿富汗形象不再是故国而是作为“他者”存在的,意识形态化将阿富汗形象置于西方进步与自由的大叙事中,以否定阿富汗来肯定西方;乌托邦化将阿富汗形象置于物质与理性的大叙事中,以肯定阿富汗来否定西方,从而作为文化和形象补充被西方纳入。阿富汗形象带有隐喻性:对阿富汗意识形态化的隐喻性表述指向对美国的想象认同,对阿富汗乌托邦化的隐喻性表述指向对美国的反躬自省。西方权力秩序下,胡赛尼对美国的社会想象和自我认同建立在与阿富汗比较的向心的整合巩固与离心的超越颠覆之间的张力上。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受双重文化语境影响的胡赛尼对阿富汗形象的构建是否存在超越西方权力秩序,走向跨文化间性的可能。通过不断地回归文本可以发现,胡赛尼对阿富汗形象的想象性表述带有复杂而深沉的情感,他笔下的阿富汗既残忍又温情,与对美国形象的肯定与否定的双向认同有关,但似乎又不仅仅是如此。
忽略胡赛尼对阿富汗的深层情感而只谈其西方形象自我认同将使《追风筝的人》这一小说文本的分析走向模式化。“过于强调注视者作为西方文明话语与权力的建构者这一身份,未能充分考虑到注视者本身情感的复杂性。”[7]卡尔维诺曾谈到哲学与文学的区别,哲学发现“观念关系、秩序规则,于是,世界被简化了,变得可以理解表述”;文学发现“世界在简化中僵化,教条正抽空意义”,于是冲破教条,使“世界恢复了生动与丰富,意义变得模糊不清”[8]。哲学与文学的区别令人发省:《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何尝不是生动丰富而又模糊不清的呢,因而形象学视域下的分析应关注到文本的独特性,关注到作者的独特感受。
阿富汗之于胡赛尼,在西方权力秩序中因美国自我认同的需要落为他者,但它仍然是胡赛尼心中不可替代的故国。弥漫在文本中的温情表述来源于作者内心为故国存留的柔软,意识形态化遮盖不了阿富汗的善美温情,乌托邦化也不单单指向对美国秩序的完善。有温度的形象体现了双重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作者叙事立场的复杂性,其中蕴藏着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迈向跨文化间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