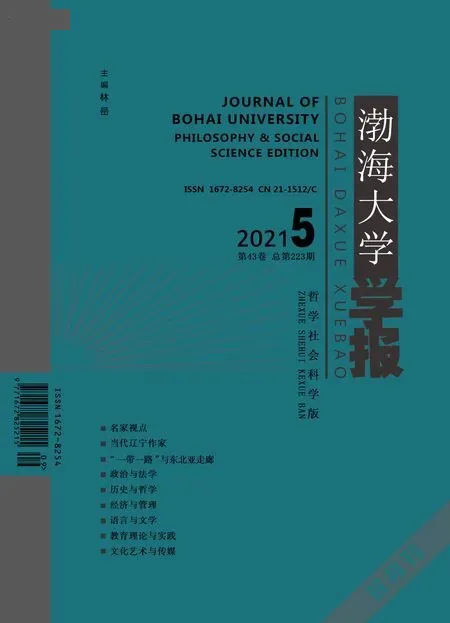论辽西走廊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崔向东(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锦州 121013)
辽西走廊是中国四大民族走廊之一,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重要的民族—经贸—文化廊道。辽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多元一体进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族走廊研究的不断深入,辽西走廊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走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辽西走廊地理区位
在“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特殊的交通地带恰处于民族混居区域,持续发挥着不同民族间的纽带作用,可称其为民族走廊。民族走廊沟通内地与边疆、中国与世界,连接不同的民族—文化板块,是典型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民族走廊以民族与文化的交融互动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的重要视角。
“民族走廊”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在讨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时,提出了区域板块和“民族走廊”的概念,很好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断互动融合,而连接不同地理板块和民族区域的便是具有地理、民族、文化等多重意义的民族走廊。1982年,费孝通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谈到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1],对于东北地区,费先生意识到也应有这样的民族走廊,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走廊的名称。从东北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看,无疑存在一条民族走廊,而东北地区的这条民族走廊就是“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以辽西地理区域命名。辽西地区是文化地理学概念,不是仅指行政区划上的辽宁西部。辽西作为郡名出现在战国时期,秦开却胡后,燕国于其北边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本文所谓“辽西”,大体指医巫闾山以西、七老图山以东、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范围,处于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的交界处,是东北与中原的连接部位,域内地级市主要有承德、秦皇岛、赤峰、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以地处辽西走廊上的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为核心区域。辽西地区的文化遗存——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前后延续五千多年,在文化内涵上表现出一定的承继关系,是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古文化区”。
从地理环境看,辽西地区位于不同地理板块的衔接处。辽西地区西部背靠蒙古高原,东部面临渤海,北面是东北腹地,南面是燕山山脉,其内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辽西走廊纵贯其间,联通南北。该区域内西高东低,地势由蒙古高原向丘陵山地到海滨梯级下降,即高山—低山、丘陵—大海。从气候看,辽西地区处于华北向东北过渡地带,在动植物、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辽西区域内自南向北主要有滦河、青龙河、大小凌河、老哈河及西拉木伦河等,区域内山脉基本呈东北—西南走向,主要山脉有努鲁儿虎山、医巫闾山、松岭等。在辽西地区,河流山脉交错,山脉与大海相间,形成了两条历史上著名的廊道,即穿行于山谷之间的大凌河廊道和蜿蜒于山海之间的滨海廊道,我们总称这两条廊道为“辽西走廊”。
大凌河廊道形成较早,它以燕山各关口为界,又分为多个廊道。我们从东北进入中原的方向来考察大凌河廊道,依据辽西重要古城和燕山各关隘来命名这些大凌河廊道。其一,柳城(今辽宁朝阳)—平冈(今辽宁凌源)—古北口道;其二,柳城—平刚—卢龙(喜峰口)道;其三,柳城—平刚—无终道。从辽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看,大凌河廊道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商周时期成为常行之道,后世则广为沿用,在历史时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2]。现在开通的京沈高铁,基本走的是大凌河廊道,这使大凌河廊道再一次焕发青春。
辽西走廊之傍海道位于渤海西侧海岸沿线,基本沿海岸而行。傍海道由临渝关出发,沿渤海西岸向东北抵达碣石,再东北行至锦州,再向东进入辽东。傍海道的开通分为两个时期,辽金以前,由于海浸和辽泽的阻隔,傍海道虽已出现,但并非一直畅通。辽金以后,随着汉族、契丹、女真人口的大量迁入,傍海道位逐渐提升,碣石至锦州段州县相连,民族杂居,滨海廊道逐渐畅通,地位日渐上升[3-4]。明清时期,随着明朝对东北亚的控制和满族进入中原,“辽西走廊”之傍海道战略地位变得空前重要,扼山海冲要,为京师藩篱,成为东北与中原相互联系的命脉要道。历史上,决定明清易鼎和国共两党胜负命运的“松锦大战”“山海关大战”“辽沈战役”都发生在辽西走廊傍海道,可见傍海道的重要性。
二、辽西走廊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特征
(一)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连接地带
从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文化等方面看,辽西走廊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民族—文化区域。辽西走廊属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连接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不断转换,历史上属于多元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
春秋战国以后,辽西成为华夏的边缘区,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这里就此基本形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对抗并存的局面,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在此不断碰撞、交流,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头戏都在此上演。统一多民族国家出现,中华民族形成,中华文化的不断重构及多元一体化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辽西走廊上寻找答案。
(二)辽西走廊催生古代文明起源
交通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明起源与交通联系密切,二者可谓共生互动、相互促进。
文明的中心也必然是交通道路之枢纽。从考古发现,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高等级的重要祭祀地,自然也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从交通地理看,牛河梁遗址正位于大凌河古廊道上。辽西地区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起步”,最早出现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古廊道基本形成,从“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到“社会交通”的演变正是社会组织不断强化的结果[5]。从这个意义说,辽西走廊催生了古代文明起源,红山文化最早放射出人类文明曙光,将中华文明起源提前一千年,提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辽西地区较早地形成“古国”,出现文明的曙光,无疑与“辽西走廊”密切相关。
(三)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场域——民族大熔炉
辽西走廊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东胡族系、肃慎族系、濊貊族系和华夏族系在辽西走廊交流融合。历史上先后在辽西地区活动和迁徙流转的部族、民族众多,都在辽西地区留下历史足迹。如史前时期的鸽子洞人和红山文化先民;商周时期的孤竹、屠河、伊虑、俞、肃慎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令支、山戎、东胡、濊貊等;秦汉魏晋时期的乌桓、鲜卑、高句丽等;隋唐辽金时期的契丹、库莫奚、靺鞨、女真等,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满族、锡伯族、回族等。这些民族与华夏、汉民族通过辽西走廊实现了彼此间的迁徙融合和文化的碰撞交流,这种融合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
自战国以来,辽西走廊就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对峙、融合之场域。辽金元明清时期,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不断碰撞融合,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民族迁徙、融合,形成了近代以来辽西走廊民族分布和共生互动的基本格局。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民族文化、心理认同越高,民族矛盾冲突越小。从“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到“华戎同轨”“车书一家”,形成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多元一体化道路。东北成为中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得益于辽西走廊这一过渡地带的民族融合。
(四)民族文化交融与多元一体
辽西走廊一直是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独特区域,不同民族以自己的文化特色塑造着辽西走廊的文化面貌。在不同历史时期,辽西走廊的文化交融体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汉化,如秦汉时期,乌桓、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制度和文字,日渐与汉人同化。“三燕”时期,慕容鲜卑“渐慕诸夏之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6]。二是胡化,唐代营州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高适的《营州歌》曰:“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真实地反映了唐代辽西走廊民族杂居和“胡”化为主的文化倾向。明清时期,辽西走廊汉族也“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7],在很大程度上受蒙古族文化影响。无论是汉化还是胡化,都体现了走廊地带的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借鉴、融合,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都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国的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终熔铸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五)走廊与丝路交汇
辽西走廊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相连接。所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指的是横贯于亚欧北部草原东西的古代经贸、文化交通线路,它位于北纬40~50 度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往来其间,称得上最早的“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辽西走廊”在朝阳交接,不同文化在辽西交汇。西亚、中亚的物产如玛瑙、珊瑚、玉石、玻璃器、琥珀、毛织品、香料等由西而东输入,并由朝阳经“营州道”运达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连接,使东北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形成了更大的历史格局,对东北亚各民族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国家廊道——辽西走廊的边疆经略与军事意义
与其他走廊相比,辽西走廊的边疆经略与军事意义更为突出。历史上,辽西走廊是中原政权控制边疆的国家廊道。中原政权对东北亚的控制实行藩属朝贡,辽西走廊是藩属朝贡体系中交通道路骨干,向北连接渤海道、海西东水陆城站路;向东连接营州道。在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七)辽西走廊文化符号——诗书之路
从辽西走廊的交流物品和民族交流的结果看,辽西走廊的文化属性十分鲜明,因此我们提出辽西走廊的文化符号是“诗书之路”。
从交流物品的文化属性看,辽西走廊更侧重于文化、精神层面。这可以从诸多事例加以说明:红山文化的玉器属于精神层面,玉以通神;箕子“之明夷”,带领族人及“诗书医药百工”迁往辽西,后至朝鲜半岛[8];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窖藏商周青铜器,属于礼器[9-10];三燕时期,佛教从辽西走廊传到朝鲜半岛①;契丹东丹王耶律倍到中原购书,在闾山建读书堂;金人占领汴京,把大量中原典籍运往金都,“典章文物尽入于金”。历史上,朝鲜、日本的使者到中国,歆慕汉文化,“尽市书而还”,“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其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看,北方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并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如慕容鲜卑的汉化;契丹人大规模吸收学习汉文化,“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11];金世宗提倡学习汉文化,翻译《孝经》《论语》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2]这些都是诗书之路文化交融的结果,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
朝鲜、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形成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以文字、儒学、佛教、典章制度为标志,实质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朝鲜人便自称为“小中华”。东亚文化认同依靠的不是物品、技术,而是书籍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从辽西走廊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看,“诗书达于礼教”,辽西走廊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路”。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辽西走廊当代价值
辽西走廊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既关注辽西走廊的历史、也关注辽西走廊的现实。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唤醒辽西走廊,重新认识辽西走廊在当今的地位和作用,赋予“辽西走廊”以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是时代发展提出的重要课题。大体说来,辽西走廊的当代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区域
辽西走廊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辽西走廊以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互动成为从走廊认识“中国”,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及中国疆域形成过程的一个极好视角,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疆域形成的“多元互构”过程的理解,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对促进民族和谐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提升区位优势和地位
辽西走廊连接不同的地理板块和经济区域,辽西走廊地带是辽宁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节点,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互连互动之路,与当今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密切相关。辽西走廊地带对于辽宁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推进“辽蒙欧”经济廊道实施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趋势逐渐形成的今天,历史悠久的辽西走廊也有了新的称谓——“经济发展带”,然而不论古今,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内部与外部连接作用。在古代,辽西走廊连接农耕、游牧和渔猎文明区,在当代,辽西走廊连接不同的经济区域。南面是京津冀、北面是内蒙古东部、东北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区域在资源、物产、产业、技术、劳动力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形成区域合作。
2020年,中共辽宁省委制定了《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在《规划纲要》中,中共辽宁省委提出,要建设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发挥辽西毗邻京津冀的区位优势,依托阜新、朝阳、葫芦岛等,率先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打造辽宁开放合作的西门户和新增长极。这是对辽西走廊地带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的高度认识,通过辽西走廊的地理交通、多元经济和区位连接优势,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度合作,将极大地带动辽西地区的快速发展,必将成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极。时代发展为古老的辽西走廊提供了新的机遇。京沈高铁的开通,使辽宁建设“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将带动辽西走廊所在的辽西地区的快速发展,实现资源、产业、技术、生产力、人才、物流的再配置。辽西走廊之大凌河廊道再一次焕发生命力,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本身,而是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资源。辽西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却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要善于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
辽西走廊地带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众多,类型丰富,是打造线性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区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辽西走廊也是一条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廊道”。历史上,各民族在辽西走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景观,这些文化遗产和景观呈线性分布,数量多,民族特色鲜明,线性结构突出。因此,辽西地区在发展文化旅游时,一定要转变思路,重视“遗产廊道”开发利用,打造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如设计文明起源之旅、通往契丹之路、中朝友好燕行路之旅等,建设辽西旅游大环线,打造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线性文化旅游大格局。
(四)辽西走廊这一“历史的地理枢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辽西走廊已经成为辽宁的一种重要文化符号
辽西走廊的文化符号是“诗书之路”,这一文化符号是辽宁独特的文化资源,是辽宁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要充分挖掘、利用辽西走廊文化符号内涵。东北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也应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要利用辽西走廊文化符号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重新树立辽宁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自信。
总之,时代发展为辽西走廊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也为辽西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辽西走廊这条古老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又将在辽宁全面振兴和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布局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辽西地区应以辽西走廊为纽带,主动、率先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只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辽西人民一定能如他们5000 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们一样,在同样的这块土地上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我们坚信,辽西地区的未来一定更美好。
①史载:“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等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第2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