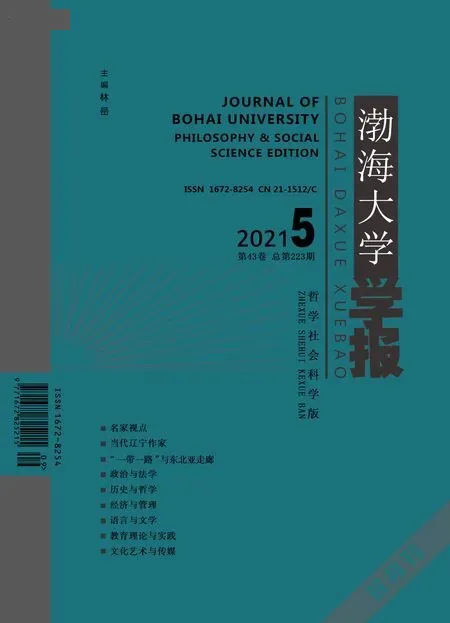坚守与超越: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
林雪飞(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说到当代文学研究,孟繁华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学术重镇”。他的“声音频繁出现在一场又一场作家研讨会上,出现在各种名目的评奖活动中,出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会上”[1]。“他的文章,点面结合,论述雄辩而有说服力”[2],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文集20 余部,发表论文500 多篇。在3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孟繁华始终坚守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阵地,追索其发展的规律,解析其深蕴的内涵,提出了许多富于个性的判断和见解,构建了自己特色鲜明的研究体系。当代文学之于孟繁华,不仅是他挚爱的研究对象、坚实的事业堡垒,更是他探知社会和心灵的切实切入口,参悟世界与人生的精神栖居地。他从文学出发,发现了超越于文学的诸多问题;他以文学为依据,展开了超越于文学的广阔思辨。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活动家、文学史家,更是一位卓越的“问题中人”[3]“精神探险家”[4]“出色的思想者”[5]。
一、文学与文化
文学是人学,为人而作,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反映着人的生活、情感和心理,也表现出作家的认识、感受和理想。所以,文学绝不只是一个个故事、一种种情愫,更包含着异常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内涵,隐喻着社会存在与时代发展的十分复杂的逻辑和理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西方传入中国并迅速盛行的文化研究思潮,不仅进一步消解了文本阐释的政治和阶级视阈,而且“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去考察”[6]“把众多的文学研究者从狭小、封闭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地中解放出来,让文学研究者也关注更多的公共话语空间,带给了文学研究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学术成果的伸展性”[7]。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正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典范。他以兼具历史广度和深度的文化视角,全面审视当代文学及其存在“语境”,发掘出许多深隐于文本的精神意绪,阐明了不少“‘超文学’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6](75),展现出敏锐的文化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力度。
孟繁华总是以“一个真正有血性、有思想、有良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6](76)的立场,直面当代中国最严峻的文化问题,并力图从特定的角度作出富于启发性的阐释。而且作为“学院派批评”,孟繁华自觉“屏蔽庸俗社会学对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干扰和强侵入”“用一种很知识化的方式”,真正实现了批评的“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强化”[8]。《众神狂欢》和《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前者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冲突,揭示了带有明显消费、享乐、欲望属性的“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的消解与吞噬,以及传统余续和现代性因素扭缠纠结的文化境况。“狂欢”作为一种虚假的时代表征,不仅凸显了人们价值断裂、理想失落的精神困境,也无法遮蔽全球化背后多重霸权的隐现及反抗。后者通过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传媒变化的分析,阐明了其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确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文学生产和文化认同的有效影响。另外,孟繁华多达几百万字的各式单篇论文,则涉及了更广泛的人文话题,“意识形态”“国族理想”“民粹主义”“知识左翼”“无产者写作”“新人民性”“启蒙”,等等,都是孟繁华不断讨论的文学关键词。显然,孟繁华已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建构起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思维结构,一方面透过文学归纳其所体现的时代和社会文化伦理,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时代和社会文化现实探讨其对文学的塑造与制约。
孟繁华似乎比一般的研究者更能透视文学的文化价值,而其中他最看重的还是文学“作用于世道人心”[9]的功能。在他看来,文学从本质来说“要处理的还是人的心灵、思想和精神世界的问题”[10],因此对文学所反映的心理进行解读、对文学所呈现的精神进行分析,自然也就成了他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任务。所以,《众神狂欢》透过“狂欢”看到的终是“众神”的精神困境;《传媒与领导权》在文化领导权和传媒的作用机制背后也隐含着复杂的心理根源;《梦幻与宿命》更是直接进入了“精神”这个核心,从宏观上完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历程的系统梳理,从微观上呈现了当代作家的多种创作心态,特别是对何其芳、艾青、蔡其矫、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创作心理的分析尤其出色。此外,对于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解读,孟繁华也十分注重精神内涵的分析,《女性的故事——林白的女性小说写作》《忧郁的荒原:女性漂泊的心路秘史——陈染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评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对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关怀——评杨黎光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评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等都颇有代表性。
总体而言,孟繁华的文学研究确实很少“纯文学”的论述,而总是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之下,进行触及社会本质与精神本源的深入阐释。
二、现场批评与历史总结
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完型”状态不同,当代文学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作品时刻涌现,资料浩如烟海,新人辈出”,“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奋力跟踪追赶,无休无止”“阅读量极大”;虽然“很是不忍”,但也“必须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筛选,保留下来那些精品,而后予以归纳、总结”[2](192)。谢冕先生这段颇感性的描述,不仅说明了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的特殊性,也指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两大主要任务——“现场批评”和“历史总结”。孟繁华“不是一个古板的学问家——钻进单纯学术的‘象牙塔’只进不出,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情怀的现代型学者”[11],他的研究兼具“现实”与“历史”两种向度,既“着意于对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的评述与反应”,也“着意于对文学史进行表述”[5](5),真正实现了“现场批评”与“历史总结”的融合并进。
孟繁华是一个真正“始终坚持在文学的现场”[12]“和当代文学发展血肉相连的在场的批评家”[2](196)。面对当代文学不断推出的“海量”的作家作品,他的阅读量之大、阅读速度之快、阅读之深入细致,就连与之比肩的许多大批评家、大学者也都大加赞叹。孟繁华说:“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的基础上的”[13],“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并尽可能比较快地写出评论文章表达我的看法。”[14]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批评涉及极广,既有早已知名的“老”作家,又有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既有经典作品的重读重释,又有新作的推介推广;还积极地展开了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可以说,孟繁华的批评几乎涵盖了一切不断涌现的文学现象。对“当下”的关注,是孟繁华“现场批评”的一个醒目表征,显示了他清醒的“在场”意识。通过知网查询他所发表的论文,仅题目明确标示出“当下”这一研究对象的就有20 多篇,而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批评文章都以“当下”为核心或旨归。此外,近20年来孟繁华几乎每一年都会以“年度”为单位,对当年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述。尽管孟繁华也认为:“以年度的方式评价小说或其他文体形式”,从“史”的视角来看,“在学术上的根据非常不充分”[5](7),但它却是对文学现场及时反映的一种有效形式,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所以他的“年度”批评还是持续了下来,并集成了一个颇为独特的“文学现场”系列,记录并呈示了21世纪文学创作的许多重要问题。
孟繁华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史家”[5](5)。虽然他并不热衷于传统文学史的书写,但却格外瞩意于用单篇论文的切实论述,逐步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在孟繁华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同质化的文学史太多了”[8](17),所以他强调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文学史的研究。他的三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程光炜合著)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论》都独具特色,与一般文学史相区别。《学术史》运用了许多新的资料,系统记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十分别致而有深度,揭示出了其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中的元理论价值;《发展史》和《史论》则开发了不少新的历史关照角度,凸显了当代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无论结构还是观点都有不少创新之处。
“百年中国文学”是孟繁华的导师谢冕先生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正是在此指导下“重新书写文学史的一个实践”,由孟繁华协助谢冕组织、统筹完成,“它并没有线性的构建‘文学史’的历程,也不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的‘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镜头’的方式深入之前文学史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8](17)。其中的《1978:激情岁月》由孟繁华执笔著述,透过20世纪70年代众多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学景观,系统呈现了当代文学结束“一体化”、开启“新纪元”的复杂的历史进程,颇能代表整部书系的特点。此后,“百年中国文学”也成了孟繁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阈,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当代文学,而总是在“百年”的背景之中,历史地赋予当代文学应有的位置,并进行全新的分析和论述。如《百年中国:作家的感情方式与精神地位》《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新时期文学的百年文化背景》《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哲学思潮与文学变体》《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等,都鲜明地展现了他强烈的历史意识。
“新世纪文学”则是孟繁华主导的一个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观念,它的诞生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文学史叙述意图,但同时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现场指认。它作为孟繁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的言说场域,勾连起了他的“现场批评”和“历史概括”,具有双重的价值。孟繁华一方面时时深入到“新世纪文学”的创作现场,对各种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做出及时的反应、评判;一方面又不断地将现实纳入历史审视的空间,对“新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整体的理性归纳与概括,并做出富有个性的历史阐释和价值判断。《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作品》《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现场》等文集,集中展示了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丰厚成果,其涉猎之广、论述之深,尚无能出其右者。
三、现实关怀与理想主义
孟繁华在谈到对作家的评价时说过:“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5](6-7)这样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对批评家的评价,孟繁华就是一个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的批评家。他曾明确地提出:“一个批评家除了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表达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怀,是对公共事物的关怀和介入热情。……批评更应该对公共事物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感兴趣,并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问题。”[15]这是孟繁华对当代文学批评及批评家的一种期待,更是对自己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性设定。他作为一位学者,虽身处“象牙之塔”,但视野十分开阔,始终心怀天下,坚持做“入世”的文学研究。“他的每本著作或每篇文章,都几乎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联系着每一个时期的重大理论命题”[16]。这本是孟繁华评价谢冕的话,这里借用来说明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也是极其恰当的。
自20世纪90年代始,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存在生态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于文学的“边缘化”,孟繁华始终处之泰然,他坚信“文学不会死亡,它于社会和人心的关系,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来”[9](26)。由此,他又进一步确认了文学批评应是“有用之学”,“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批评家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不公、非正义等现象的批判是不能放弃的”[17]。但他同时也强调,“批评是对话,批评不是指责,不是怨恨”[18]“批评不应该是简单的否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现象,但也不意味着一味地说好话”[19],文学批评应该是“有用”的、“合宜”的。所以,他反对那种对当代文学没有对象的全盘否定,而坚持做有极强针对性的具体的文学评论。孟繁华充分肯定了当代文学中的“高端文学成就”,并将中篇小说誉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更一再申说“底层写作”的价值,因为这些文学所表现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的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20],有着强烈的现实言说意义。他也曾激烈地指出,“乡村文明的崩溃”“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50 后的终结”“失去了青春的文学”“没有了经典的时代”……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经过了严密推导的理性判断,并落实到对乡土文学、城市文学、青春文学乃至整个未来文学更热切的期冀。
显然,孟繁华“始终怀有对文学、对社会的理想”,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2](190)。按他自己的说法,孟繁华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进入了文学批评与学术的核心,但面对90年代“世俗”对“崇高”“日常”“理想”的解构大潮,他内心深处的理想情怀却始终不曾消解,并凝结成了支撑他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线索与品格。在孟繁华的文章中,“八十年代被谈论得最多的那些命题,诸如理想、价值、意义、正义、精神、灵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识分子、反思、批判等等”[4](7),一直不断被提及,持续彰显着他理想主义的反复追问。但这种理想主义已不同于那种“早已为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拒绝”的“旧理想主义”[21],“文学家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22],因此孟繁华将其命名为“新理想主义”。“所谓新理想主义,包含着对文学的如下理解: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都应当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在文学的娱乐功能之外,也应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当然,它不会再去讲述集体的梦幻,不去编织幻觉和假象,而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使这种文学又充满了必要的批评精神,良知与正义感是新理想主义基本的精神内涵。”[21](191-192)这种“新理想主义”使孟繁华的文学研究有了更高远的立足点和关照视角,“并总能切中社会文化心理时弊”[11](117),与他的现实关怀形成有力呼应。
当然,孟繁华也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不可能承担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23]“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文化试验场,一切问题都让文艺批评来解决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19](7)但内心的理想主义,又使他无法放弃批评家的责任,带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坚守着明确的“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维护着“批评的最高正义”。[19](9)于是,他的文学研究也就分外鲜明地展现出了“他的人格、他的个性、他的人文情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6](76)。
四、理性与诗意
综上所述,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内涵是极其丰富而深厚的。但在他而言,却又总是举重若轻,将如此厚重的思想呈现得极其轻盈而灵动。因为他认为,文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属性虽是“理性”,但文学又赋予了它“感性”的特权。孟繁华本身也“既有感性,又有理性”,“这种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品格”[2](193)铸就了他文学研究理性与诗意融合的个性风格。
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蕴含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黑格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丹尼尔·贝尔,从本雅明到葛兰西、萨义德,到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状态”[2](195),这里“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旧式理论,有福柯、杰姆逊、海德格尔的新式理论,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甚至还有中国古典理论”[1](101)。但任何理论到了孟繁华这里,都不再是孤立、外在的知识性存在,而是经过了他的吸收与阐扬,真正融入了他的精神血液的一个全新的知识谱系。“这样一个知识谱系构成了他批评的总体性框架,以及看问题的历史与社会高度”[2](195),也使他可以把多种理论自如地应用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考察,而毫无“隔膜”与“嫁接”之感。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论文,他的文学研究都散发着令人信服的理性气息。
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纤细敏锐的感性,“读过孟繁华先生的文化评论和文学批评文章的人,大多都会情不自禁地被他蕴涵在文字中的激情与智慧所感染”[12](109)。孟繁华在大学期间就曾有过诗歌创作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是个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尽管后来他听从了系主任“做一个好的学者”的劝告,“把诗歌创作放下,读书去了”[8](16),并最终走进了文学批评和研究,但诗意却始终是他心灵的底色。这使他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字,也总是体现着诗人一般炙热的情感、灵性的感悟,呈现为诗人一样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表达。《众神狂欢》《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想象的盛宴》,他的著作常会有一个令人遐想的诗意的名字。“滚滚红尘”“心在人间,笔在云端”“温婉如四月熏风拂面春雨无声润物”,他评论时代、作家、作品的文字也时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动人的诗意韵味。“他的文章豁达洒脱,不刻板沉闷,也不轻浅浮泛,就是那么富有诗性而又掷地有声地敲击着阅读者的心性之门[12](109)”。
所以说,孟繁华“是一个特别具有当代文学学科特点的学者和批评家”[2](195),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坚守是他的品格,超越是他的精魂。